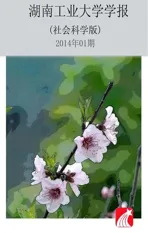再论嫖宿幼女罪之存废*
2014-03-31黄明儒向夏厅
黄明儒,向夏厅
(湘潭大学法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再论嫖宿幼女罪之存废*
黄明儒,向夏厅
(湘潭大学法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关于嫖宿幼女罪的论争,保留论者对嫖宿幼女罪合理性的论证理由不够充分,因为该罪名在立法目的、条文设置、司法实践与效益对比诸方面均存在缺陷,并且无法通过解释论进行解决。从短期来看,在没有相关司法解释或者立法修改时,司法上应该废弃嫖宿幼女罪的适用,将相关行为纳入相关犯罪条目进行规制;从长期着眼,应该坚持平等保护幼女合法权益的基本刑事政策,彻底废除嫖宿幼女罪罪名。
嫖宿幼女罪;保留论;解释论;强奸罪;猥亵儿童罪
在1997年刑法修订新增嫖宿幼女罪这一罪名前,嫖宿幼女行为一般是按强奸罪处理的。由于该罪名是从强奸罪脱胎而来,其成立条件有许多类似于强奸罪的地方,致使该罪名自产生以来一直遭遇各种非议。尤其是近年来,全国各地爆发的大量嫖宿幼女事件,更是将该罪名推上了风口浪尖。不仅普通大众对此议论纷纷,而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全国妇联也通过提案、报告等多种形式呼吁废除本罪。[1-3]甚至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等机构也开始就是否废除嫖宿幼女罪展开调研。[4]那么,嫖宿幼女罪遭受如此广泛质疑的根源是什么?
就这一问题,笔者曾专门撰文从法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嫖宿幼女罪的设置远未达到真善美的要求。[5]当然,由于真善美是法律文本的最高目标,该文分析更多的是从法律规范的应然价值展开嫖宿幼女罪的探讨。那么,回归到刑事法规范,嫖宿幼女罪罪名可能存在什么问题呢?本文拟从刑事法规范的理想构造角度出发,在评析现有观点的基础上,剖析嫖宿幼女罪可能存在的问题,希望本文的分析能够对如何正确处理嫖宿幼女行为有所裨益。
一 保留论观点及其评析
在现有关于嫖宿幼女罪的论争之中,只有少数学者完全肯定该罪名,他们认为,当前对嫖宿幼女罪指责的观点并不恰当,嫖宿幼女罪的罪名设置是合理的,应该予以保留。这种保留论者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论证:首先,嫖宿幼女罪具有不同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为了论述方便,下称奸淫幼女罪——引者注)的不法本质,与奸淫幼女罪相比,嫖宿幼女罪侵害的法益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有必要将两者区别开来。奸淫幼女罪中有两种行为,一种是强迫奸淫行为,是对幼女现实人身权的侵犯;还有一种是和奸行为,是对幼女未来身心健康发展可能性的侵害。而与这两种奸淫幼女行为相比,嫖宿幼女罪侵犯的则是幼女的社会健康人格之养成。其次,从法定刑来看,嫖宿幼女罪的设置也是合理的。我国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的“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是指将奸淫幼女行为比照同样情况下的强奸成人妇女的行为从重处罚。换言之,只有上述奸淫幼女罪中的第一种行为即强迫奸淫行为才能“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而和奸行为只需要按照强奸罪论处即可,因为毕竟和奸的行为没有暴力,所以按照强奸论处已经是加重。因此,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幅度是5到15年有期徒刑,而和奸幼女行为则是3到10年有期徒刑,两相比较,嫖宿幼女罪处罚较强奸罪为重。为了防止刑罚轻重失衡,在许多以非性交为表现方式的嫖宿幼女行为中,如果是轻微的猥亵行为则应按照猥亵儿童罪论处,如果是带有更为直接、强烈的性色彩的猥亵行为则按照嫖宿幼女罪论处。[6]
但保留论者的理由站不住脚,值得商榷。首先,保留论者的论证逻辑自相矛盾。保留论者将与幼女性交行为分为强迫奸淫行为、和奸行为、嫖宿幼女行为,并且提出每一种行为侵害的法益具有差异性,而认为“嫖宿幼女罪中的犯罪对象是卖淫的幼女,虽然卖淫的幼女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性的自己决定权,但却具有现实意义上的认识能力和意思表达能力。”“而作为嫖宿幼女罪犯罪对象的具体幼女而言,在事实上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辨认和表达能力的。”但是,论者得出的结论却是“嫖宿幼女罪的犯罪对象并非卖淫幼女,而是幼女。”[6]论者这种以肯定卖淫幼女具有不同于普通幼女的差异性为前提,得出嫖宿幼女罪的犯罪对象并非是卖淫幼女,而是幼女的结论,显然自相矛盾:如若不将卖淫幼女与普通幼女区分,又如何得出与两者发生性行为侵犯法益的差异性?如若将卖淫幼女与普通幼女区分,又如何得出嫖宿幼女罪的犯罪对象是普通幼女的结论呢?
其次,保留论者对嫖宿幼女罪侵害的法益解释也值得商榷。这种以是否存在强迫手段作为侵犯人身权行为的划分标准是不准确的,至少是不严谨的。按照论者的逻辑,和奸行为侵害的是未来的人身权,而这种未来的人身权作为幼女未来身心健康的可能性,那就既可能被侵害,也可能未被侵害。得出的结论则理应是被侵害了则成立强奸罪,未被侵害则不成立强奸罪甚至不成立犯罪,因为可能不存在法益侵害,这种结论显然无法为人接受。以此推之,就会认为只要不存在强迫手段,而是以其他手段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都不是对现实人身权的损害。这样,哄骗、利诱行为,甚至是以诸如糖果这样微小物品为诱饵与特别年幼无知的幼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都会被认为对幼女的现实人身权没有造成损害。这种结论恐怕连保留论者自己都无法接受吧。实质上,和奸行为侵犯的也是幼女的身心健康权。未满14周岁的幼女的身体发育尚不成熟,与之发生性关系会损害其生殖器官与生理发育,也会损害其心理健康,甚至给幼女未来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利影响。而且,从形式上说,刑法并没有将和奸幼女行为排除在强奸罪之外,而是直接适用强奸罪的规定,这也是在立法上肯定了和奸行为对幼女身心健康的损害。因此,无论是强迫奸淫行为还是和奸行为,都会给幼女的身心健康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不能因为没有强迫行为就否定这种现实损害的存在。很难想象,同样一个不谙世事的未满14周岁的幼女,仅仅因为是否自愿发生性行为就在保护法益上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同理,认为嫖宿幼女与和奸幼女两种行为侵害的法益不同的理由也不具说服力。人格权是依附于人身权而存在的,如果不注重幼女的人身权而仅仅强调人格权,对同样是与幼女发生性行为的嫖宿幼女行为仅仅认为是针对幼女的人格权之侵犯,显然是一种避重就轻的处理方式。按照论者的逻辑,卖淫幼女具有现实意义上的认识能力和意思表达能力,所以与之发生性行为则更多的是对其人格养成的损害。但是同样一个未满14周岁的幼女,为何在卖淫时就具有认识能力和意思表达能力,在不卖淫时(比如与自己的男友发生性行为时)又不具有认识能力和意思表达能力了呢?这种观点要么否定嫖宿幼女行为对幼女身心健康的损害,要么认为人格养成包含幼女的身心健康,无论何者,都是对生活常识的背离。这点很难让人理喻,想必保留论者也无法解释。
最后,保留论者对“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的解释也是错误的。既然认为立法已将和奸行为认定为强奸罪,那么该条文中的“奸淫”自然既包括暴力、胁迫、哄骗、利诱的行为,也包括所谓的和奸行为。因此,无论是强迫行为,还是和奸行为,都是对幼女身心健康的损害,都理应受到刑法的严惩。既然未满14周岁的幼女对自己的行为还不能够产生足够认识,不具有性自主权,那么无论是采取什么方式,只要是与幼女发生性行为的,都应该按照强奸论并且从重处罚。同时,保留论者将猥亵行为分为轻微猥亵行为与直接、强烈的性色彩的猥亵行为并对其予以不同的定性,也违背了犯罪定型的要求。既然行为符合嫖宿幼女罪的犯罪构成,那么就不可能再将其认定为猥亵儿童罪。而且,何为“更为直接、强烈的性色彩的猥亵行为”也很难界定。
综上所述,保留论者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也正是因为存在上述问题,刑法学界纷纷将目光转向解释论的立场,试图从解释论的立场出发为嫖宿幼女罪的适用找到一条“康庄大道”。
二 解释论观点及其评析
“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而是法学研究的对象”,[7]当我们面临一个法律条文时,首先想到的不应该是怎么批判它,而是如何解释它从而更利于其适用。但是,如果无论如何解释都无法得出妥当的结论时,对其批判就显得极为必要了。对待嫖宿幼女罪这一罪名,笔者的态度也是如此。首先我们应该检视一下现有解释论的观点是否妥当,然后再进一步论证是否有必要“废、立、改”本罪名的刑法条文。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关于嫖宿幼女罪的解释论观点都是将其与奸淫幼女罪进行比较得出的,主要有如下两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罪是想象竞合或者法条竞合的关系。如张明楷教授认为:嫖宿幼女行为完全符合奸淫幼女罪的构成要件;与幼女发生性交行为的,只要不属于嫖宿幼女行为的,均应该按照奸淫幼女罪的规定处罚;与幼女发生性交行为的,属于嫖宿幼女的,则按照嫖宿幼女罪论处,但是如果具备刑法第236条第3款规定的加重情节之一的,就应认定为奸淫幼女罪。[8]但是,这一观点为笔者所不取。
首先,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罪不可能是想象竞合关系。张明楷教授在论述这一观点时,引用了日本山口厚教授的观点,“法条竞合时存在一个法益侵害事实,想象竞合时存在数个法益侵害事实。”[9]而“嫖宿幼女一个行为既侵犯了幼女的性的自主权(或者身心健康),也侵犯了社会管理秩序,存在两个法益侵害事实,属于想象竞合犯,因而应从一重罪论处。”[8]但是,按照日本刑法的规定,要成立想象竞合必须具有“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以上的罪名”,按照山口厚教授的观点,这里的“罪名”既可以是同样的罪名,也可以是不同的罪名。[10]易言之,日本刑法中的想象竞合以侵害的两个法益可以独立构罪为必要。而嫖宿幼女罪中对幼女身心健康的损害可以独立构罪,但单纯的对社会风尚管理秩序的损害并不能独立构罪,因为单纯卖淫嫖娼行为在我国虽然是一种违法行为,但并没规定为犯罪行为。另外,笔者认为,要成立想象竞合,必须以刑法未就想象竞合行为规定独立的罪名为前提。例如开一枪打死一个人和打中一个名贵花瓶的行为,打死人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打中花瓶的行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刑法并未就这种想象竞合行为规定独立的犯罪,因此该行为可以成立想象竞合犯,从一重论处。但是,在诸如强迫卖淫罪中,虽然强迫卖淫行为既侵犯了他人的性自主权也损害了社会风尚管理秩序,但是由于刑法已就此行为规定了独立的罪名,就没有想象竞合犯成立的空间。同理,刑法已就嫖宿幼女行为规定了独立的罪名,因此嫖宿幼女罪不可能与奸淫幼女罪成立想象竞合犯,最多也仅仅是涉及到法条竞合的问题。
其次,按照张明楷教授的观点,行为成立法条竞合时,一般应该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但是特殊情况下,则适用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这种“特殊情况”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法律明文规定按重罪定罪量刑;一种是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按普通法条规定定罪量刑,但对此也没作禁止性规定,而且按特别法条定罪明显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时,按照重法条优于轻法条的原则定罪量刑。[11]423当法律有明文规定时,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是没有问题的,但当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时,仅以符合罪刑相适应为由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是有一定问题的:坚持这样的原则有侵害立法权之嫌疑,也有架空刑法条文之风险。因为罪刑相适应的判断会因为标准的不同而不同,为了防止恣意,立法者在规定法定刑时就等于已经对此做了罪刑相适应的判断。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一般就仅能适用法条,而不能更改法条。尤其是在当刑法已经就某种行为作出了特殊规定时,法官的任务就是准确适用本条文,否则,法官如果以罪刑不相称适用重法,就会导致本来规定的特殊条文完全被架空,其设置的意义也就无法体现出来。应该说,“刑法之所以设置特别法条,就是为了更好地揭示某种犯罪的本质,更充分地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只有适用特别法条的规定,才符合立法精神,才可能实现立法的目的。如果在法律没有例外规定的情况下,不适用特别法条的规定,那就是有法不依,并且是在刑法某个条文对某种行为有明确的处罚规定的条件下,以该条文规定的处罚过轻为由,而适用处罚更重的其他法条,明显违反罪刑法定原则。”[12][既然立法者已经按照罪刑相适应原则规定了嫖宿幼女罪名并且也规定了特别的法定刑,那么法官的唯一任务就在于准确地适用该条文。因为只有这么做,才是真正体现特殊法条的意义,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最后,退一步而言,即使承认法条竞合关系时重法优于轻法的适用原则,仍有可能面临无法判断何者为重法何者为轻法的困境。准确判断法条之间的轻重关系是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的前提。但是,由于现有立法的某种缺陷,关于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之间的轻重关系的判断往往不清楚甚至也不准确。按照这种观点,嫖宿幼女一人的,适用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由此推之,嫖宿幼女一人的危害(A)大于或者等于奸淫幼女一人(B);嫖宿幼女多人的,适用奸淫幼女罪的法定刑,由此推之,则嫖宿幼女多人的危害小于奸淫幼女多人。显然,这里存在一个A≥B,A+A+A却又<B+B+B的逻辑悖论。因此,到底是嫖宿幼女罪重还是强奸罪重显然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如若认为嫖宿幼女一人者重于奸淫幼女一人者,其逻辑结果必然是嫖宿幼女多人者亦重于奸淫幼女多人者,则根据重法优于轻法的适用原则,行为都应按照嫖宿幼女罪论处。因此,上述关于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何者为重何者为轻的论证逻辑与结论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基于竞合论存在上述难以解决的问题,有学者提出了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是互斥关系的观点,笔者姑且称其为互斥论。互斥论认为,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为互斥关系是解决两者关系最妥当的方式。缺乏有效同意是强奸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具备有效同意则是嫖宿幼女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两罪的构成要素不是竞合关系,恰恰相反,是A与非A的互斥关系。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刑法典的章节设置为两罪互斥提供立法支持。嫖宿幼女罪被归类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表明嫖宿幼女罪侵害的主要法益是社会风尚管理秩序,次要法益是保护幼女的社会观念,因此,必须从性交对象是否为“卖淫幼女”来区分两罪,方能合理说明刑法典的体例结构和法益指导功能。其二,被害人同意能力为两罪互斥论提供理论支持。虽然奸淫幼女的司法解释排斥了14周岁以下幼女的性同意能力,但是不可能在所有情形下都绝对地排除幼女的同意能力。同意能力没有一个僵化、固定不变的标准。当嫖宿对象是“卖淫幼女”时,应当认定“卖淫幼女”已经具有性同意能力。[13]但是,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嫖宿幼女罪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也为笔者所不取。
首先,互斥论者主张的第一个理由并不能成立。我国刑法将嫖宿幼女罪放置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并不必然推出嫖宿幼女罪侵害的主要法益就是社会风尚管理秩序,更不能以此推知嫖宿幼女罪侵害的法益是一种保护幼女的社会观念。虽然我国刑法分则是大致按照侵犯的同类法益对具体犯罪进行分类,但是这种分类标准并不严格。正如有学者所说,“很多时候,立法者是基于便宜性的考虑(甚至根本未认真斟酌)而将特定犯罪放在某一章之中。”[14]因此,不应完全以某种犯罪被分类到某一章节为标准来判断该犯罪侵害的主要法益。例如,不能因为传播性病罪被归类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就否认该罪名主要侵害了他人的身体健康权。这主要是基于便宜性的考虑,将具有卖淫、嫖娼行为的传播性病罪归类到“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这一章节。另外,如若认为嫖宿幼女罪侵犯的主要法益是社会风尚管理秩序,那为什么嫖宿成人妇女的行为又不构成犯罪呢?难道嫖宿成人妇女行为不是对社会风尚管理秩序的破坏吗?即使论者可能以嫖宿幼女罪还侵害了保护幼女的社会观念为反驳依据,但是刑法对行为的入罪是极其严格的,入罪的一个主要根据是对行为侵害的主要法益的审视。立法者既然没有将嫖宿成年妇女的行为入罪,就表明其认为这种嫖宿行为对社会风尚管理秩序的破坏不足以入罪。因此,仅以嫖宿幼女罪主要破坏社会风尚管理秩序作为入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同时,刑法法益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生活利益,只有极其重要的国家、社会或个人的利益才能上升为刑法法益,受到刑法保护。论者将保护幼女的观念作为刑法法益,无疑会导致法益的概念虚无化。而且,保护幼女的社会观念是一种道德层面的要求,就如同“尊老爱幼”的社会观念一样,将其作为刑法法益进行保护,有道德刑法化的嫌疑,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要求。
其次,互斥论者主张的第二个理由也不能成立。论者认为:“虽然都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但在成立强奸罪的场合,‘幼女’是指没有同意能力的幼女,而若要成立嫖宿幼女罪,则该‘幼女’必须是在该特定案情中具备同意能力的卖淫幼女。”[13]问题是,为什么同样是未满14周岁的幼女却仅仅因为是否“卖淫幼女”而具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呢?一个未满14周岁的幼女,在卖淫时,则其具备性同意能力,当其不卖淫时,则不具有性同意能力,这种时有时无的结论显然不妥。如一个年仅10周岁的幼女,当其卖淫时是有性同意能力的,但当其成长到13周岁的时候,不再从事卖淫活动,则此时其没有性同意能力了,这种推论显然不符合实际。刑法之所以以年龄为限,将人分为儿童、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就是基于各自的身体发育情况不同,而给予区别的待遇。在此过程中,不排除会因为具体年龄的差距不大而导致这种分类不符合客观情况的问题。如某些17周岁的未成年人可能比某些19周岁的成年人身体发育更成熟,认知能力更强。但是,刑法是面向社会大众的,为了防止刑法适用上的不平等,必须在社会整体利益上与个别利益上做出取舍。如果不以年龄作为形式上的限制标准,那么可能导致的后果就是刑法的统一适用将难以进行。因为18周岁与19周岁之间,13周岁与14周岁之间的认知能力的区分极为困难,完全可能因为个人认知的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结果。为此,立法者只能以年龄为限,“为是否具有性同意能力的判断提供了一个形式标准:只要是未满14周岁的幼女,均被不可反驳地推定为欠缺性同意能力。这意味着,未满14周岁的幼女不具有性同意能力是作为一项立法事实而被确立下来,它完全排除了将之留交裁判者进行自由裁量的可能性,后者必须接受立法机关的这种判断。”[14]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互斥论只是试图为嫖宿幼女罪的法条适用提供理论根据,却并没有解决该罪名本身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因而其意义有限。要从根本上解决嫖宿幼女罪可能面临的问题,还必须从该罪名本身的特点进行分析。
三 嫖宿幼女罪的缺陷分析
(一)嫖宿幼女罪的立法目的混乱
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所谓法益,是指刑法保护的个人的各项合法权利,以及可以还原为个人权利的社会、国家的利益。幼女的身体发育尚不成熟,与男子性交会对其生殖系统及其生理发育造成伤害,会损害其心理健康。[12]因此,嫖宿幼女罪的立法目的只能是保护幼女的身心健康。也就是说,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罪侵害的法益具有一致性,都侵害了幼女的身心健康。
既然如此,那刑法为何要将嫖宿幼女行为从强奸罪中独立出来,规定单独的条文呢?对此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立法者为了突出对陷入色情行业的幼女的特殊保护,因此将嫖宿幼女行为独立出来,规定特殊的法定刑,以加强对这类行为的打击。如有关立法机关解释:“之所以需用刑罚打击嫖宿幼女行为,是因为它‘极大地损害了幼女的身心健康和正常发育,且对幼女的思想具有极大的腐蚀作用,使有不良习性的幼女在卖淫泥潭中越陷越深,有的幼女被染上性病贻害终身。’”[15]二是认为,“在嫖宿幼女的场合,多是幼女‘自愿’,甚至是在幼女主动纠缠的情况下进行的。换言之,犯罪行为的实施,受害幼女本人也有一定的过错。相比(奸淫幼女)而言,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较小。所以对于嫖宿幼女的行为不加区别地按奸淫幼女罪定罪处罚,有违罪刑均衡的刑法原则。”[16]那么,嫖宿幼女罪的立法目的到底是为了加强对幼女的保护还是为了减弱对幼女的保护呢?显然嫖宿幼女罪的条文设置使其陷入两难困境。与一般的猥亵儿童行为相比,嫖宿幼女罪的起点刑为5年有期徒刑,而且其法定刑的幅度为5到15年有期徒刑,似乎有加强对“卖淫幼女”的保护之势。但是,从最高刑来看,嫖宿幼女罪的最高刑仅为15年有期徒刑,而奸淫幼女罪则最高刑可达死刑,似乎又是为了减弱对“卖淫幼女”的保护。而且,从犯罪成立条件来看,嫖宿幼女罪的主体须达16周岁,而奸淫幼女罪的主体则仅为14周岁,似乎也是为了给予“卖淫幼女”低于奸淫幼女罪的保护。通过上述分析,嫖宿幼女罪的立法目的存在混乱之处,在“强保护”与“弱保护”之间徘徊不定,这也是导致嫖宿幼女罪遭致非议的根源。
(二)嫖宿幼女罪的条文设置模糊
罪刑法定是现代刑事法治的基本原则,其实质性内容是“刑法法规的内容必须清晰明确,必须让国民容易理解。”[17]只有行为人明确知晓自己的行为后果,才能把握自己行为的界限,才有可能不去实施违反刑法规定的行为。而嫖宿幼女罪的条文设置则具有较大的模糊性,违反了刑法的明确性要求。
嫖宿幼女罪的模糊性主要体现在对“嫖宿”一词的规定。《辞源》《辞海》等大型辞书中并没有“嫖宿”这一语词,对此只能按照常识来理解。“嫖宿”中的“嫖”,根据《辞海》的解释,是指男子玩弄妓女[18];“宿”作动词用则是指住宿、过夜。但如果要求成立嫖宿幼女罪还必须有住宿、过夜的行为,那显然误解了刑法规定的本旨,而会导致放纵犯罪。因而,嫖宿幼女罪中的“嫖宿”实质上应当是指“嫖”,而不应包括住宿、过夜在内。但这样的解释仍然使人无法理解“嫖宿”的真正含义。事实上,理论上对此也有几种不同的见解。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最广义说,这种观点处于通说地位。该说认为,嫖宿幼女行为是指以交付金钱或者其他财物为代价,与不满14周岁的卖淫幼女发生性交或者从事其他猥亵活动。[19-20]也就是说,行为人只要是针对卖淫幼女,无论实施性交行为,还是其他的猥亵行为,都应该视为嫖宿幼女行为。但如果按照这种解释,行为人只是实施了针对卖淫幼女的某种猥亵行为也作为嫖宿幼女罪处理,那猥亵儿童罪估计就没有适用的余地了。而且即使按照嫖宿幼女罪从奸淫幼女罪分离出来的逻辑,针对“卖淫幼女”实施的猥亵行为与普通的猥亵行为在行为方式、行为对象上也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如此定性显然与刑法的协调性与系统性相悖。二是广义说。该说认为,所谓嫖宿幼女,“是指以交付金钱或者其他财物为代价,与卖淫幼女性交或者实施类似性交的行为。”[11]1026也就是说,这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一样将嫖宿的对象限定为卖淫幼女,却对嫖宿行为作了相对缩小的解释,只是认为与其发生类似性交的行为也视为嫖宿行为。问题是什么叫“类似性交”仍然语焉不详,如果认为嫖宿一词仅限于性交的理解,那么嫖宿幼女就要与强奸幼女做类似的解释,这样没有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不能视为嫖宿,最近的司法判例也证明了这一点[21]。三是狭义说,该说认为,嫖宿幼女,“是指以金钱、财物为交换条件得到幼女承诺后,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22]这种观点将本罪的适用做了最狭义的解释,而仅仅将嫖宿解释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但问题是,幼女身心还没完全发育,对即使是自愿卖淫的有些幼女也不一定能够发生真正的性关系行为,而且如果认为所有的嫖宿幼女都只能是与幼女发生性交行为,那么与词源意义上“嫖”之本意“玩弄妓女”就存在本质上的差异。这样就存在适用上的障碍。正是因为嫖宿幼女罪条文的规定过于模糊,使其在司法认定过程中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另外,嫖宿幼女罪的模糊性还体现在对“卖淫幼女”的认定标准上。何为嫖宿幼女罪中的“卖淫幼女”?这是认定本罪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幼女如果不是出于一时好奇或者是被诱骗等,而是对以身体换取金钱有清醒的认识,也明白性行为本身的性质、意义和后果,并且长期在色情场所从事卖淫活动,就可以认定其为“卖淫幼女”。[13]但笔者认为,这种认定标准仅仅是以一些形式内容作为判断依据,并没有提出一个准确的实质标准,而依然是模糊的。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也不能将幼女区分为“卖淫幼女”与非卖淫幼女,更不能对卖淫幼女予以进一步的划分。我们不能因为幼女的身份不同就给予不同的刑法保护,这显然不符合我国基于未成年人处于身心还没发育健全,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保护的基本法律精神。
(三)嫖宿幼女罪的司法实践存在罪名滥用的倾向
嫖宿幼女罪不仅在立法目的、条文设置等问题上存在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也有滥用的倾向。以贵州习水嫖宿案[23]为例,该案在犯罪对象与行为方式的认定上就存在诸多问题。按照对嫖宿幼女罪的一般理解,该罪的犯罪对象为“卖淫幼女”。而习水嫖宿案中,被害人则均为当地的中小学生,很难让人能够把这些还在上初中甚至小学的学生认定为具有卖淫习性的“卖淫幼女”。另外,从该案的行为方式来看,许多被害人都是被人以打毒针、拍摄裸照并散播相威胁而被迫卖淫,后又为了逃脱控制而被迫诱骗其他学生顶替进来。这与“卖淫幼女”的“主动纠缠”行为则是相距甚远的。本案中,嫖宿幼女罪的适用是极其随意的。
另外,实践中许多嫖宿幼女案的犯罪主体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他们大都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员、教师或者人大代表等。例如贵州习水案中的罪犯李守民系习水县移民办主任,冯支洋是习水县职业高中教师;福建安溪案中的罪犯郑文山系安溪县人大常委会常委、科教文卫委主任,许新建是安溪县华侨职业学校校长;浙江临海案中的罪犯池全胜是临海市气象局原副局长,王宗兴则是临海市人大代表,等等。这些案件行为主体的特殊性,加上被害对象的特殊性,使老百姓在直观上感觉嫖宿幼女罪已经沦为为特权阶层实施性犯罪进行开脱的工具。
最后,实践中也并不排除许多幼女因为家庭、教育或其他各种原因沦为色情场合的卖淫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因为无知而根本不知道自救,或者因为无法生存而甘愿通过卖淫赚钱,或者因为“破罐子破摔”的心态而继续从事卖淫活动。此时,他们属于比普通幼女更糟糕的弱势群体,理应通过法律获得救济。但是,由于卖淫场合的包庇,卖淫嫖娼的双向性与隐秘性,而实际上使得这种幼女的卖淫行为几乎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法律救济。从目前媒体所曝光的案例来看,几乎很少有针对那些真正长期从事卖淫活动的幼女的嫖宿案件的报道,而并非不存在这种现象。这就导致一个问题:许多本不应属于嫖宿幼女罪规制的案件被定性为嫖宿幼女罪,导致定罪错误;而本应受到保护的长期从事卖淫活动的幼女,其合法权益却没有在嫖宿幼女罪这一罪名中受到合理保护。这种情况的存在,也使得嫖宿幼女罪的立法意义无法真正实现。
(四)嫖宿幼女罪的效益对比失衡
犯罪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是对社会良好秩序的破坏,是一种“恶”。对犯罪的惩治是为了抑制这种“犯罪之恶”而实施的迫不得已的手段。但这种惩治手段也可能因使用不当而侵犯人权。因此,作为刑法惩治手段的刑法罪名必须要符合一定的效益性,这里的效益性亦可称之为作用对比,即刑法罪名在达成预防犯罪与保护法益的目的过程中应当全面考察其消极作用与积极作用,如果消极作用过大而积极作用过小则不符合效益均衡原则,反之亦成立。
也许嫖宿幼女罪的保留论者认为嫖宿幼女罪具有合理性的最大理由在于“就基本刑而言,嫖宿幼女罪比强奸罪要重。”[24]因此,“与强奸罪的法定刑相比较,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具有较强的合理性。”[10]姑且不论这一结论的合理性,仅以法定刑为重来判断嫖宿幼女罪之合理性的论证逻辑就存在一定疑问。“因为刑罚本质上归根到底只是一种实现其他目的手段,刑法的最高理想是自由与正义的维护,而不是对犯罪与犯罪人的惩罚,惩罚犯罪和犯罪人只是实现刑法理想的一种必要手段。”[25]因此,对于任何犯罪,并非法定刑越高越好,而应该考察其社会危害性配置必要的刑罚,否则对任何犯罪只需配置最重法定刑即可,根本无刑法的谦抑性之讨论余地。对嫖宿幼女罪而言,也并非法定刑越高越好,而应该结合嫖宿幼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配置必要的法定刑即可。因此,嫖宿幼女罪的基本刑高于强奸罪既非该罪名合理性的根据之一,也非该罪名表现出来的积极作用。
退一步而言,即便认为嫖宿幼女罪的基本刑高于强奸罪属于该罪名表现出来的积极作用,但其也远远低于该罪名所起到的消极作用。嫖宿幼女罪的消极作用主要体现为两点:其一,嫖宿幼女罪对罪犯的否定评价远不如强奸罪。刑法一般通过施加刑罚实现对罪犯的否定评价,但刑罚并非是对罪犯进行否定评价的唯一形式。社会往往还通过道德否定、社会谴责表达对犯罪人的否定态度。在古代中国,卖淫嫖娼是一种合法行为,而在德国、巴西等许多国家嫖娼也依旧是合法行为。虽然现在我国将卖淫嫖娼规定为违法行为,但对卖淫嫖娼入罪化仍持否定态度。相反,强奸罪则古今中外都被认为是一种最严重的犯罪,因此,“‘嫖客’和‘强奸罪’的社会谴责度是不一样的。”[26]社会给予嫖娼行为的道德否定与社会谴责要远远低于强奸罪。同理,“卖淫幼女”的标签与“强奸罪的被害人”也是社会给予的完全不同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即使没有通过刑罚的轻重体现出来,但也通过社会一般人的“异样眼光”显露无疑。其二,嫖宿幼女罪仅仅设置一个5到15年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也容易使其在适用过程中产生诸多负面影响。由于仅有一个法定刑幅度,这使得该罪名体现的不同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无法通过法定刑的梯度选择表现出来,而5到15年的跨度过大,使得法官在司法裁量中很难准确把握合理的宣告刑,而且也容易给法官任意出入刑提供有利空间。在这种意义上,嫖宿幼女罪所产生的消极作用远远大于其所发挥的有限积极作用,而显然不符合刑法设置罪名的效益均衡原则。
综上所述,嫖宿幼女罪在立法目的、条文设置及司法实践中均存在各种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无法通过刑法解释进行解决。那么,嫖宿幼女罪罪名应该如何完善呢?在立法尚未修改之前,较为可行的模式是就嫖宿幼女罪的模糊之处通过理论充分探讨,而予以明确合理的解释,以便统一司法。当然也可以按照中国刑事司法的惯例,对嫖宿幼女罪与强奸幼女行为的司法适用做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以减少司法适用过程中出现不应有的分歧。
“我们应当明确对嫖宿幼女行为进行规制的相关刑事政策。”[5]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司法上,如果将幼女区分为“普通幼女”与“卖淫幼女”,则是一种歧视性的表现,也不能体现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有效平等保护。如果认为这种区分法是立法上的规定,则应该承认这是一种立法歧视,更应当予以纠正。加强对幼女尤其是深陷色情场所漩涡中的幼女的保护应作为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从这一意义上,笔者主张,在既没有废除嫖宿幼女罪这一罪名,也没有统一司法解释出台前,停止对这一罪名的适用是最为妥善的做法。
在停止适用嫖宿幼女罪这一罪名后,对现有嫖宿幼女罪所可能包含的一些行为,则应该由相应的刑法规范来调整。具体而言,如果行为人在嫖宿幼女过程中实施性交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奸淫幼女型强奸罪,从重处罚;如果行为人嫖宿幼女过程中仅仅是实施诸如一些类似性交性的猥亵幼女的,应认定为猥亵儿童罪;如果行为人在嫖宿幼女过程中对幼女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伤害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则应当按照故意伤害罪或者其他相应的犯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在嫖宿幼女过程中,并未实施上述行为,而情节显著轻微的,则应当不认定为犯罪。另外,行为人在嫖宿过程中既有性交行为又有猥亵行为的,则属于想象竞合犯,而以强奸罪从重处罚,当然如果猥亵行为不能为强奸罪所包容,则以强奸罪与猥亵儿童罪数罪并罚。
当然,从长远着眼,笔者依然主张,刑法应该直接废除嫖宿幼女罪这一完全缺乏真善美的罪名。只有这样,刑法的运作才能做到真正公平合理,才能最终实现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
[1]王春霞.全国人大代表孙晓梅:再提废除“嫖宿幼女罪”[N].中国妇女报,2013-3-7(A02).
[2]黄晖.委员呼吁废除嫖宿幼女罪获舆论支持[EB/OL].[2013-08-19].http://www.jcrb.com/zhuanti/szzt/2012qglh/yqgc/201203/t20120312_823807.html.
[3]佚名.全国妇联:建议废除嫖宿幼女罪[EB/OL].[2013-08-19].http://news.sina.com.cn/o/2013-06-22/063927467749.shtm l.
[4]权义.人大法工委调研嫖宿幼女罪存废争议[EB/OL].[2013-08-26].http://news.sina.com.cn/c/2012-06-27/035724662833.shtm l.
[5]黄明儒,欧阳爱辉.也谈嫖宿幼女罪的存废——一种真善美的分析进路[J].人大法律评论,2013(1):19-37.
[6]牛牪,魏东.驳嫖宿幼女罪取消论[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4):54-57.
[7]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
[8]张明楷.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关系[J].人民检察,2009(17):8-11.
[9]山口厚.日本刑法[M].东京:有斐阁,2007:379.
[10]山口厚.日本刑法[M].付立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82.
[11]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12]刘明祥.嫖宿幼女行为适用法条新论[J].法学,2012(12):135-138.
[13]车浩.强奸罪与嫖宿幼女罪的关系[J].法学研究,2010(2):146-149.
[14]劳东燕.强奸罪与嫖宿幼女罪的关系新论[J].清华法学,2012(2):35-38.
[15]张永红,吴茵.论嫖宿幼女行为的刑法规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11):46-47.
[16]叶良芳.存与废:嫖宿幼女罪罪名设立之审视[J].法学,2009(6):121.
[17]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M].2版.王昭武,刘明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44.
[18]夏征农,陈至立.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1734.
[19]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5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602.
[20]黎宏.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5,906.
[21]佚名.佛山多名男子涉嫌卖淫嫖娼法院称手淫服务不算卖淫[EB/OL].[2013-8-25].http://www. s1979.com/news/society/201306/2692376526.shtm l.
[22]百度百科.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EB/OL].[2013-08 -25].http://baike.baidu.com/link?url=F7AGsDXig CMoBo ROBAi 8RMWV dFP4I2 Bum IXXIz4RDZnAo7 THiUTHNpK 0f Bw TgQinJch JH3Bk6UTXX1is 2nubMa.
[23]周光权.刑法各论[M].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95.
[24]刘娥.从习水案探析嫖宿幼女罪[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0(1):106-109.
[25]黄明儒.论刑事立法的合理性原则[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3):20-24.
[26]黄云波,吕哲如.嫖宿幼女罪的困境及其突围[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1):94-97.
责任编辑:黄声波
Reanalysis of Reserving or Abolishing Crime of Prostituting Girls under the Age of 14
HUANG Mingru,XIANG Xiating
(School of Law,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Hunan 411105,China)
Those who are for reserving the crime of prostituting girls under the age of 14 don't give enough argument.The crime has several defects in legislative purpose,provision's setting,juridical practice,benefit imbalance and etc.What's worse,these defects can't be settled by theory of interpretation.For the short term,the crime of prostituting girls under the age of 14 shall be ceased to apply in justice,and relative behaviors shall be regulated bymeans of being involved in relative crime until relativ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r legislation amendment come out.For the long term,we should keep the basic criminal policieswhich equally protect the legal rights and benefits of girls under the age of 14,and abolish the crime of prostituting girls under the age of14 completely.
crime of prostituting girls under the age of 14;theory of reserving the crime;theory of interpretation;crime of rape;crime of child molestation
D924.34
A
1674-117X(2014)01-0079-08
10.3969/j.issn.1674-117X.2014.02.015
2013-10-1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刑法修改与解释的限度关系论”(13YJA820017);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刑法修改的理性研究”(13A101)
黄明儒(1967-),男,湖北监利人,湘潭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刑法研究;向夏厅(1989-),男(土家族),湖南张家界人,湘潭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