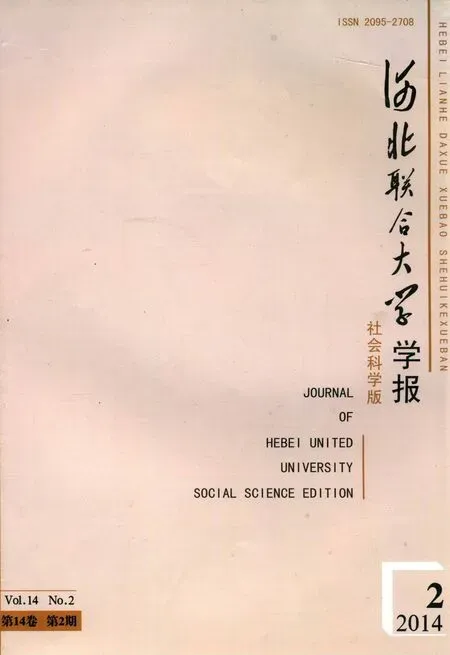晚唐五代女诗人诗歌情感体验
2014-03-30张丽丽
张丽丽
(河北联合大学,河北 唐山 063009)
晚唐女性诗坛是有唐一代人数最多,但身份地位最低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占据诗坛的大多数诗人是歌妓。晚唐时期,唐王朝一步步走向衰败,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中提及“历史说明自中唐以后,唐朝向衰亡的途上走去,藩镇跋扈,宦官窃柄,内乱外患,相逼而至,……晚唐的诗坛充满着颓废、堕落及不可救药的暮气;他们只知道沉醉在女人的怀里,呻吟着无聊的悲哀。”[1]其实晚唐女性诗坛也具有她独特的艺术感情。
而自成阶段的五代十国文学,是在不同于唐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唐王朝覆亡(907年)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南北朝以来又一次分裂割据的局面:兵火连年,战祸惨烈。诚如韩偓在《凄凄》诗云:“风雨今如晦,堪怜报晓鸡”,处在如晦长夜的诗人盼望着雄鸡一唱,看不到太平时节的隐痛时刻在他心头跳动。诗人耳闻目睹的是政权频易、郡县陷落;居尸成丘、庐舍为墟;田园荒芜、饿殍遍地。正是由于这种动荡不安,“五代文学虽然是唐代文学史不可分割的延续,但与已至衰微的唐末文学相比,显然更见衰蔽。……五代时期的文坛最终形成以西蜀与江南为中心的两大文人群落。”[2]
在前后蜀统治的近六十年间,以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为标志,呈现出一个集聚蜀地的较为稳定的文人群落来。而在南唐,主要是以李璟、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宫廷诗人,他们也写朝云暮雨、腻粉脂香,总体上呈现浮艳之风。然而,南唐地理形势比不上西蜀恃险自固,因此“南唐文人在与西蜀文人同样集中描写逸乐生活状况的女人姿色情态之外,又较多着眼于内在的心理感受。在文学创作中,他们也就往往不仅透过艳色表面去揣度内含的哀怨情思,而且将自身的虚落惆怅意绪幽微细腻地表达出来。”[3]
晚唐五代女诗人是中国诗歌史上重要的女性文学群体,人数众多、作品丰富,在诗歌园地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题材和内容非常广阔,有题叶诗、闺怨诗、忆夫诗、爱情诗以及战争诗等等,在女性诗歌史上有较大影响,本文拟从她们诗歌中体现的情感来展示那动人心魄的心理世界。
一、孤独体验
孤独是人类常见的生存状态,也是一种情感体验。晚唐五代中有许多女诗人都有过这种体验,表面上看晚唐的鱼玄机在被丈夫李亿抛弃之后,与当时的名士往来酬唱,看起来过着很热闹的生活,但她的心迹无人倾听,孤寂在噬咬着她的心灵,表面风平浪静的生活与她本真的性情存在莫大的疏离,鱼玄机是空虚落寞的,她的作品中也留下了孤独的痕迹。
试看,鱼玄机给曾经与李亿一起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温庭筠写了封《冬夜寄温飞卿》:
苦思搜诗灯下吟,不眠长夜怕寒衾。满庭木叶愁风起,透幌纱窗惜月沈。疏散未闲终遂愿,盛衰空见本来心。幽栖莫定梧桐处,暮雀啾啾空绕林。
此诗中诗人直接陈事,抒发了自己的孤寂苦闷之情,向温剖白了自己的心迹。首联叙写诗人冬夜灯下苦吟,以致长夜难眠的情景,增加了诗意的跌宕,也表现了她内心世界的矛盾。颈联两句,诗人独卧在冷被之中,听着满院落叶飒飒作响,目光透过帐幔、纱窗,看着月亮渐渐西沉,不免惆怅满怀。秋去冬来、叶落满阶,标志着一年即将逝去:月影移窗、西降,意味着新的一天即将开始。这些韶光时序的自然变化,不能不在诗人那敏锐的感觉中留下痕迹。颔联写诗人欲过与世无争的疏散生活而不可得的苦恼境遇。尾联借梧桐暗示自己的爱慕之意,希望能与之双宿双飞,但从温庭筠存留下来的诗集看并未见有与之相关的诗歌。
由此可知,鱼玄机时刻感受着一种幽冷凄寂之情,寒衾、木叶、纱窗,这些看似闲笔的意象,实际上是女主人公情感的外在体现,满腔的愁绪迎面扑来,她措辞淡雅,而寄意深微,将读者带入一种寂寥之境,正如西方作家梅特林克所言:“有些话语看起来在作品中是无用的,但作品的灵魂正在其中。”[4]
女诗人会产生孤独感是因为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缺少爱,心灵时刻在漂泊,没有停靠的港湾。当她们与人类交流的欲望实现不了,与社会沟通的愿望满足不了,就会将爱的目光投向大自然,那些花草树木、水光山色在她们看来有着生命情味,能够听懂她们的心灵声音、理解她们的真情实感。女诗人是将诗歌当作心灵的抒写、情感的慰藉。那些承载着美好感情的自然风物与她们内心丰富的感受相辅相成。
晚唐五代女性诗中不乏这种富于人情味的自然意象。再看晚唐张琰的《铜雀台》:
君王冥漠不可见,铜雀歌舞空裴回。西陵啧啧悲宿鸟,空殿沈沈闭青苔。青苔无人迹,红粉空自哀。
这首诗,纯朴简净。前四句明显为七绝,后二句忽改成五言,声调陡然变动,出人意表之外,以“青苔”、“红粉”对偶诗句作结,情景交融,戛然而止,更见其悲怨的悠长。诗中的“青苔”已不是单纯的自然物,而是饱含人情味的意象。张琰将旅途中的所见所感形诸笔墨,以自然景物的静寂来衬托内心的孤寂,全诗蕴藏着一种幽静思绪,给人清幽疏宕之美。
人在孤独时会对自身的生存状态、心理世界进行沉思,孤寂的状态给个体更多的沉思时间、空间与心境。伴随着情感的投入,沉思的主体不仅参悟到自身生命存在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并且会使这种沉思不再局限于一己人生之起伏,而升华为对整个宇宙人生的深切关怀与领悟,上升为一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深层思考,也同时具备了普遍的人类情感的性质。
如晚唐元淳的《寄洛中姊妹》:
旧国经年别,关河万里思。题诗凭雁翼,望月想蛾眉。白发愁偏觉,归心梦独知。
这是一首思乡念姊妹的作品,因为“离乱”、“弟兄俱尽”,使她怀念洛中幸存的诸妹。当时她已生“白发”,叶落归根之念尤浓。但洛阳离长安相距万里,关河阻隔,有家不得归,只有在梦中飞归故上。“梦独知”三字写出思乡之情不为人理解,唯有梦知,说得非常凄苦。钟惺说:“用得警直”,“只一独字,觉有历乱难堪意。”[5]面对现实,她心中无比孤独,却又无可奈何,只有朝着家乡的方向洒泪偷泣。
元淳在背井离乡中将这种个体沉思升华为对整个人类生命状态的思索与关怀,于广阔的空间与亘古的时间中感受到个人渺小的微不足道、生命短暂的转瞬即逝,发出人生空幻的沉思。处境越是孤独悲戚,这种沉思越是深入。
二、缺失性体验
“缺失性体验的概念来自心理学缺失性动机的概念。缺失性动机是指‘以排除缺乏和破坏避免或逃避危险和威胁的需要为特征的动机’。与之相似,缺失性体验大致是主体对各种缺失的体验。”[6]在社会生活中,人类的各种需要若不能在数量或质量上充分实现,个体就会产生缺失性体验。在缺失的状态中,那些积极向上、热爱生命的个体会采用多种方法消解缺失,追求满足。
晚唐五代女诗人生命中的缺失是不计其数的。就晚唐鱼玄机而言:第一,因妒杀婢女、社会不容,最终被京兆尹温璋杀死,导致毁灭的结局,这是安全需要得不到满足;第二,被丈夫抛弃之后,她过的是种“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的孤寂生活,没有亲友和家庭的温暖,这是归属和爱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五代徐月英而言:第一,尽管她终日陪侍着达官贵人过着轻歌曼舞、花天酒地的生活,但却掩盖不了内心深处的屈辱和痛苦,虽然她有着充沛的物质生活,却缺少爱情这种基本生理需要;第二,徐月英原本是一位纯朴善良的妇女,误落风尘,她以娼家不幸的遭际,写出内心深处的苦悲。她被迫为娼,为自己不能履行“三从四德”而悲泣,也无法满足归属与爱的需要。
这些女诗人们共同缺失的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艺术经常能成为寄托、消解生命体验的媒介,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缺失性体验造就了她们的文学创作,她们用文学作品表现了体验带来的痛苦和摆脱这种体验的努力。
人类在缺失性体验中造成的痛苦可以凭借艺术来排遣和得以慰藉。弗洛伊德曾说过:“在实际生活里不能满足欲望的人,死了心作退一步想,创造出文艺来,起一种替代品的作用,借幻想来过瘾。”[7]艺术有时可以作为痛苦之人的安神剂或止痛药。晚唐五代女诗人各种需要都有所缺失,于是她们在自己的文学的世界中寻觅精神绿洲,以此来抚慰伤痕累累的心灵。
其一,缺失性体验更易成为文学创作的驱动力。这是因为“创伤作为一种记忆的痕迹,积储着艺术家一定的激动量和刺激量,它像病灶一样残留在艺术家的心灵深处,一旦外在刺激或内部需要偶然碰到这个痛点,便立刻形成心理张力而使创作者心理能量的分布发生失衡。要恢复平衡,平复创伤,就必须把多余的激动或刺激宣泄。艺术创造就是宣泄的手段之一”[8]。晚唐慎三史的《感夫诗》正是创作于被夫抛弃、孤苦无依之时,对痛苦的宣泄与排遣是她创作的动力;五代周仲美的诗也作于在丈夫弃官、独入华山出家后,她痛苦喘息、拼命挣扎,却无力解脱。她们都借助敏感的心灵与卓越的文学才能将现实世界中难以排解的缺失痛苦放在艺术世界里排解,以获得内心的平衡、创伤的治疗。
其二,缺失性体验更易产生优秀的文学。许多文论家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予以探究,如张煌言说:“‘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盖诗言志,欢愉则其情散越,散越则思致不能深入;愁苦则其情沉著,沉著则舒籁发声,动与天会。故曰:‘诗以穷而后工’。夫亦其境然也”[9]。陈兆仑说:“‘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此语闻之熟矣,而莫识其所由然也。盖乐主散,一发而无余;忧主留,辗转而不尽。意味之深浅别矣。”[10]他们认为忧伤愁苦情绪比欢乐情绪更容易在读者心中保留,更有深远意味。除此之外,晚唐女诗人抒写悲哀忧愁苦痛的文学作品源自真情,是她们真实遭遇下的产物,这种忠于心灵的真实感使得这些作品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缺失性体验是人类共有的体验,有时欲望无穷,而物质条件、个体能力有限,因此人们总会面临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不满足,缺失感普遍存在。晚唐五代女诗人在文学创作中不仅对自身的缺失状态予以细致深入的刻画,而且站在一个较高的位置上俯视,将之升华为对人类普遍的缺失性体验的体察与思考。正如叔本华所说:“他意识着一切生命的痛苦,不只是意识着自己的痛苦。但是,必须由于自己本人经历的痛苦,尤其是一次巨大的痛苦,才能唤起这种认识。”[11]这些女诗人们以个体的缺失性体验为基点,向社会与人类扩散辐射,表现的情感超越了一己之私,具有了普遍的意义。她们已不再是自己心灵的保姆,而使作品具有普遍的价值取向。
鱼玄机欲与丈夫相伴一生却被残忍抛弃、欲过平淡生活却偶然被杀,这是一种戏剧性命运的捉弄,作者将之升华为对人类普遍存在的面对冥冥不可知天数命运无能为力之感的揭示;鱼玄机昔日有着甜蜜的爱情和悠闲自在的生活,如今全都失去了,诗人又将之升华为对美好事物难以停驻、遗恨之感常在的体悟;鱼玄机昔日是无所羁畔的女冠,如今沦落为屈辱悲惨的囚徒,人生的巨大落差被诗人升华为世事变幻无常、万物变动不居的沉思。
王福娘在爱情与尊严面前两难取舍,于是她将矛盾痛苦升华为人类面临两难抉择时的共有挣扎;刘媛由于失恋,十分痛苦,而后又摆脱这种痛楚,因此在她的诗歌中,我们能看到人间诸事因缘聚合、缘散时无须强求的哲理;莲花妓对爱情义无反顾、奋不顾身,她将其升华为对人类对所有美好事物应保持一种执着的姿态。
这些女性诗作来源于她们自身的缺失性体验,蕴涵了社会普遍规律,抒发了人类共同的情感,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效果与感染力。
三、感发生命的意识
在晚唐五代女性诗人中,有的作为帝王之妃万众瞩目;有的作为市井歌妓心灵空虚;有的作为征夫之妻孤独寂寞;还有的作为道观尼姑是远离精神家园的流浪者。她们中有的人曾有过巨大的人生落差和命运遗憾,敏感的心灵使她们觉察到青春与美丽的转瞬即逝,意识到无可奈何的各种缺憾。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不平等社会中,这种对生命的执着与关注使得她们的作品有一种感发生命的意识,这种意识能引发读者对人生的深深喟叹。
晚唐五代女诗人作品中渗透着生命意识,首先表现在对生命强烈的珍视。她们喜欢使用富于生命色彩的自然意象,这些意象生机勃勃,但在自然规律面前却显得凄凉而孤独。源于一颗仁爱之心,女诗人们对有生之物满怀怜悯之心,她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旺盛的生命活力;而悲惨的命运,又使她们比常人更加体味到美好的生命惨遭摧折的痛苦。当生命中曾经拥有的一切美好都远去不可复得的时候,对这些美好事物的回忆和眷恋充斥于作品之中。
其次表现为对爱情的留恋与追求。尘世的繁杂并非她们生存的目的,而心灵的充实才是她们孜孜以求的人生价值。对她们来说,爱情是无比美好的,是鲜活的生命中并不可少的元素。表现于作品中,是对爱情的留恋和深深的怀念。
再次表现为作品含有一种理性生命之思。青春和生命力是如此美好,而人们热爱的有生之物却脆弱的不堪一击,留恋的的自由生命却在无常的命运与难测的天意面前虚弱的无能为力。她们作品中有对欢乐的尽情的贪恋执着,有在欢欣中对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的担忧焦虑,有在极大的人生落差与极悲的生命体验对难测的天意与无常的命运的怀疑与超越。这些时间的流程中物是人非的无奈感伤,天道自然永恒中有限个体生命的体验感悟,空幻痛苦人生中虚无空梦之感的哲思,以及她们对生命中记忆、感情等生命中至关重要的要素及无可避免的孤独、伤感等人类共同生命体验的思考,不仅展现了自我的生命历程,而且感染着千千万万类似的心灵欢乐或悲伤,拥有或失去,美好或丑陋,永恒或无常等等是人类普遍的情愫和共睹。二人从自身出发,由己及人,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这些人类共有的类似经验、感触、情思在词作中出现,以意味深永的体悟哲思这种形态升华为了对全人类悲剧命运的思索与感触,从而超越了她们具体的经历而获得了一种普遍性、人类性。
四、情真意切的抒发
情真心诚是诗歌具有感染力量的根本,能够忠实于内心且忠诚的抒发真情的作品的确具有巨大的感染力。真情之言跃然纸上,后世读者若深入其中,以心来聆听其心声,就有无穷的会心。试看五代民间女诗人程长文《春闺怨》:
绮陌香飘柳如线,时光瞬息如流电。良人何处事功名,十载相思不相见。
时光流失,青春不再,在绮陌香飘、杨柳如线的大好春光里,良入何苦外出从事功名,让个闺中少妇十载相思,老却韶光呢?唐人诗中写闺怨的比比都是,这首诗以女人独到的眼光和感受抒写春闺怨情。她感到时光易逝,瞬息柳丝又绿,暗写独守空闺的少妇叹青春难驻,盼望良人早日归来,共度佳期。可“良人何处事功名,十载相思不相见。”丈夫追求功名,十载不归,杳无音信,不顾妻室;而妻子却相思成灾,翘首以盼。这一切尖锐反映出唐代社会男子追求功名与妻子追求爱情的矛盾。正如张宏生所言:“不论女性采取的是柔性的体恤还是强烈的质诘,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种倾斜的夫妻关系,落在祈求对话而不可得的情境中。……‘何处’一问道出多少难堪,‘十载’又是何其轻易,准确写出时空暌违下无从对话的艰难处境。”[12]
晚唐五代女诗人具有真心而作真情款款之文,作品中的情感是毫无掩饰的,对于读者来讲就可直接体会感知,就更有亲和力。而语言上的毫不矫揉造作,遣词造句上无浮而不实的虚假之态,对于读者而言也不会产生雾里观花的隔离感,而是更具有直观的亲切。因此她们的作品必定可深入读者的心灵,其感人之力不仅仅在形式上雕琢刻镂。
五、结语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女性只有从自己心灵里把自己的意志流淌出来,用自己的才智把人生经历刻画出来,才能真正获得一种永恒的解脱,才能发现自身的重要价值。试看鱼玄机用诗歌对自己的爱情做出炙热的追求,花蕊夫人用百首宫词来抒写宫中的清新俊雅,千百年来触动着一代代读者的心弦,使读者的灵魂与她们的情感产生极大的共鸣。
谭正璧先生曾这样评价中国古代的女性:“她们是闭锁深笼的小鸟,她们是埋藏地底的宝玉,地位愈珍贵,行动愈不自山,天才愈不易发展。偶然她们突破藩笼,……便充实了她们的干枯的生命,助长了她们蕴藏未露的天才的发展,使她们都得在中国文学史占一位置。”[13]中国文学史上,晚唐五代诗歌的发展流变并不代表这一时期女性诗歌的发展状貌。晚唐五代女性诗歌是女性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作为文学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后代女性诗歌的创作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也为文学史的发展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通过分析这些女性诗歌,诗作中表现出来的对爱情这种跨越时空永恒存在情感的渴望与赞美、对生命的留恋、对流光的怅惘、对自由本性的不懈追求,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的人性,是人人都具备的心理追求。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便是人人感觉似曾相识的共性之美,具有极大的感染力。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527-528.
[2]许总.唐诗史下册[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6;501.
[3]许总.唐诗史下册[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6;505.
[4]托比·柯尔.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38.
[5](明)钟惺辑.名媛诗归卷十二[M].上海:有正书局,1918;56.
[6]童庆炳,程正民.现代心理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13.
[7]钱钟书.七缀集(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25..
[8]童庆炳,程正民.现代心理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38.
[9]钱钟书.七缀集(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27.
[10]钱钟书.七缀集(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28.
[11](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43.
[12]张宏生、张雁.古代女诗人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147.
[13]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