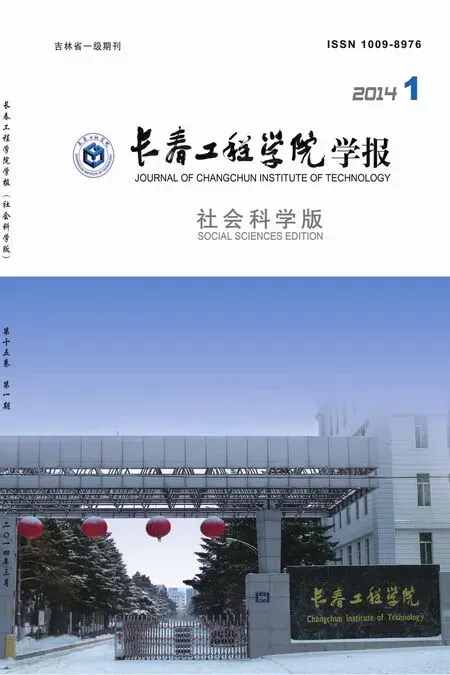《泰西新史揽要》的诗学改写研究
2014-03-29吴瑾宜
吴瑾宜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芜湖 241003)
《泰西新史揽要》(以下简称《揽要》)是晚清“销量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西方历史学译作”[1],它向国民传达的信息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意义。
《揽要》相关学术研究涉及的领域有文学、历史学以及新闻传播学,研究角度有历史人物形象的描写与重塑(陈建华:2007),西学传播热潮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刘雅军:2004;张昭军,徐娟:2005),译者的文化身份和职业评述(田中初:2004)。相关译学研究多散见于论文中,没有独立专著对此进行详尽分析,研究涉及方向多为译本评述性介绍(邹振环:1996)和译介行为评价(欧阳东峰,穆雷:2008)。然而,译本自身的语言特色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本文将从诗学改写的角度出发,通过文本对比和综合分析,归纳出该译著的具体改写策略,从而分析探讨译本的译学价值与改写策略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功能与效果。
一、制约《揽要》改写策略的要素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所持的操纵理论认为,翻译是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影响翻译的重要因素,因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在这三要素的操纵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译本进行改写。从译本的诗学层面来看,《揽要》采用了古雅的文言表达,行文方面深受中国传统史传体例影响,在细节描述上有明显的古典演义小说的痕迹。这些语言特点是在三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其中主流诗学观念和赞助人这两个要素对译作的改写选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揽要》在《译本序》和《凡例》中指出译者是“详而译之,质而言之”[2],“一字一句不敢意为增损”[2],但从文本阅读和分析中即可得出,译者在传达原文内容时遵循了译入语的主流诗学观念,选取了符合译文读者习惯的表达方式,译文流畅明快,最大限度地淡化了原文的陌生感,并发挥了改写译文的最大优势。笔录并对译文进行润色加工的是晚清学者蔡尔康,在与“西儒”的合作的过程中,面对的是东西方文化尖锐对立的局面,蔡尔康游离于中西之间,既认同传教士和西方文化,也不背离本土文化和民族主义,“从他的言论看,越来越倾向于中西之间的协调。他声称:孔子是东方圣人,耶稣是西方圣人,教士与吾儒岂有异哉!”[3]在这种协和的心理定位与精深的传统文学修养的共同作用下,蔡尔康在行文处理上偏向了国内的主流诗学观念,采用了古雅的文言表达,使用传统史传体例等方法,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语文化。
在译作产生和传播的过程中,赞助人的作用不可忽视,它控制着作品的意识形态、出版、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可以是宗教团体、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和大众传媒机构,也可以是个人势力[4]。《揽要》的赞助人之一是作为出版机构的广学会,其创办人员为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外交人员及商人,“广学”意为“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宣传新教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以期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揽要》初以《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为题在广学会所创报刊《万国公报》上连载,1895年以《泰西新史揽要》为名,由广学会出版出版单行本,单行本的发行促进了《揽要》的传播。另外,晚清政府上层官吏也是其赞助人之一,洋务派领袖张之洞曾捐银一千两,以示赞赏。译者为了迎合广学会的需求,在译介中宣扬西方的基督教的救世作用,甚至直接称之为救世教;针对晚清统治已然日薄西山的局面,译者在译本中提出可以借鉴西方的治国之道,通过进行符合赞助人审美的诗学改写,将先进的自然科学和变通进化观点用语言装点成易于赞助人接受的儒家“治国”思想,这在包括上层官吏在内的赞助人看来无比新鲜,值得尝试。
二、《揽要》的改写策略
《揽要》的诗学改写满足了读者的审美需求,不仅是由于译者娴熟练达地使用了古雅文言的表达方法,契合了当时知识分子及上层官吏的阅读习惯,另一个原因则是译者破除了东西方文化间的藩篱,实现了中西思想与文化的互融会通。这两个因素在具体的改写方法上可分别视为显性改写策略和隐性改写策略。
就翻译策略而言,隐性改写策略主要是思想方面的改写,奠定了译文以主流诗学观念为基调的思路与风格,是显性改写的基础和前提。《揽要》中隐性改写采取的方式有:增添华例、换例译法以及穿插本土习语或经典,译者也在《凡例》中明确指出,“是书所纪全系西事,在西人之习闻掌故者自各开卷了然,及传译华文,华人不免有隔膜处,故间采华事以相印证”[2],这三种方法就是译者所指“间采华事”的主要途径。
原文在描述18世纪法国人民反抗虐政酷刑时,引用了伏尔泰的名言:“I am the son of Brutus,and bear graven on my heart the love of liberty and horror of kings.”[5]译者在处理该句时,对 Brutus做了夹注,“普鲁士斯,罗马古时人,常杀无道之君,如武王之伐纣”[2]。Brutus今译为布鲁图斯,公元前44年,布鲁图斯领导元老院成员组织策划了刺杀凯撒的行动,将凯撒刺死于庞贝剧院的台阶上。虽然19世纪中国文人士子对世界的认知开始从“天下”渐渐向“万国”转移,但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主体文明仍然对人们的心理认知有着相当牢固的作用和影响。武王伐纣是国人熟知的历史事件,象征着道义的胜利、秩序的重建,同时也是与传统伦理道德相悖的弑君行为。而布鲁图斯刺杀罗马共和国独裁者的做法并非每个译入语读者都能理解其背后的意义,因此译者将其与武王伐纣相比,通过激发读者的联想来促进对篇章的进一步理解。
因此,译者常用国人熟识的古人典故来换例添例,文中描写欧洲各国间的战争,常用“飞将军”来形容对方行军布阵的出其不意。如:“奥人大惊,以为飞将军从天而下”,“奥将大骇,谓飞将军从天而下也”;介绍友军双方开掘隧道准备会战,将掘地及泉的作战方法喻作“欲如郑庄姜母子之隧而相见”;列举19世纪的医学成就时,译者用战国神医扁鹊的传闻来称赞测喉镜,“昔扁鹊饮上池水洞见五藏症结,其说近于荒诞,今制此镜则信而有征矣。”另外,在中国古典演义小说中常常出现的习语,如“不敢越雷池一步”、“人争一口气,佛仗一炷香”、“宁做太平犬”在译文中也比比皆是。
除添例换例、穿插习语之外,儒释道及诸子经学的思想也通过隐性改写融于文本之中。原书没有用科学历史的发展观点来评述或解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的大发展,认为在这之前,人类极其落后,愚昧无知,生活困苦,通过此次大发展获得了空前的进步。佛教的苦难和救赎的观点与之相契合,因此,译文中频频出现“地狱”、“苦海”、“彼岸”、“功德圆满”等意象。原文很大篇幅用于介绍西方各国经济发展及国家争战的情况,而儒家以治国、明明德于天下为最高目标,兵家则以征战计策和行兵谋略为重,因此译本在诸子经学中,以改写为儒家和兵家最多。例如,译文中有演化自《孟子·滕文公上》的“有恒产始有恒心,放辟邪侈之事以有顾恋而不敢为”,以及直接引用《尚书·五子之歌》的“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译文中“或献策曰:兵法,制于人不若制人”和“兵,凶器也;战,危事也”则分别演化自《孙子兵法·虚实》和明初刘基所著《百战奇略·好战》。
隐性改写策略奠定了译文的基调与风格,是显性改写的基础和前提。那么显性改写则是隐性改写的外在表现,集中突出了译文以译入语主流诗学观念为核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具体字词的使用,句式修辞的选择,以及改写风格的偏向。《揽要》采用的显性改写具体方法表现为:采用文言表达译文和文学化改写。
文言的特点是句式短,结构紧凑,多用四字格、成语典故、排比对仗以及委婉代称,在论述问题时常用问答、反问、感叹、添肯定之词等表现手法。就使用委婉代称而言,译文中用“干戈”、“锋镝”、“烽烟”代指war,“狴犴”代指 prison,“金瓯”代指 territory,“名登鬼箓”表示 death,用“七更寒暑”、“阅月圆二十度”表示for seven years和after twenty months这两个时间状语,遣词尽显雅致婉转。中国传统史书与史论散文习于发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情感,《揽要》的译者也在译文中表达了自己对历史事件的态度和评价,多用感情强烈的呼告型表达。如评价拿破仑兵败俄国,“通盘计算之下,六十七万八千子弟中,得庆生还者实属寥寥无几,此真自古至今罕有之浩劫也!”[2]另外,译文中频繁出现“诚为亘古以来所未有”、“自古至今从未有”等字句,书中浓厚的进化论观点也从这种强调和感叹中得以展现和表达。
文学化是译文显性改写的另一重要特征,这种改写生动具体,往往倾向于展现具象,极其富有表现力。从正反面论述通商重要性的一段译文就是典型的文学化改写:“凡欲禁止通商者,如使人棹舟于山涧中,适有飞瀑下注尚可活泼泼地,倘使泉源偶涸直将坐困枯鱼,若能各国通商,则如使人扬帆大海,无论旱干日久,终无涸辙之虞。”[2]而原文并无如此生动的用词和描述。文学化改写在描写心理活动和女性境况时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叙述路易十六公主随法王外逃,译者在文本中加入了自己的感叹,“然回忆公主少年时已经国破家亡之惨,甚至身佝狴犴与狱吏为伍,幸获省释则又栖香于外,不敢还乡二十余年,岂料幸返故宫,复重有流水落花春去也之感哉。抚时感事之君子知食荠与茹茶相倚状,益凛然于高位之不易居也”[2]。其中“流水落花春去也”出自李煜感伤故国的词作《浪淘沙·帘外雨潺潺》,译文将法国王室的没落、公主颠沛流离的境遇和李后主思念亡国故土的情感相类比,深化了读者对异国人物心理与处境的认知和了解,激发了读者对描写对象的同情与感叹。
三、采取诗学改写的效果影响
通过显性改写和隐性改写的综合运用,《揽要》完成了中西传统文化心理的互融与会通,出版后立刻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巨大的市场需求,成为“同时代最风行的读物”[6]。力行变法的维新派代表梁启超称赞它是“述近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7],康有为还将其进献给光绪帝,从而坚定了皇帝的变法之志。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和张之洞也是该书的忠实读者,一时间高官显贵以互赠《揽要》为风。李提摩太在自传中写到,“1985年,当麦肯齐的《泰西新史揽要》和广学会的其他几部书出版后,中国的书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这时,长期以来横亘在基督教和非基督教文学之间的藩篱被拆除了。书商们不再认为广学会的出版物不值得一顾,反而为能销售我们的书籍而异常高兴”。据李提摩太自己统计,该书先后销量达三万余部,全国流通的盗版总价值约有一百万元[8]。
然而,麦肯齐原书中有着明显的为殖民主义辩护和污蔑东方国家的言论,这令译作不可避免地保留了扩张性的文化侵略性质。译作的口述者李提摩太的身份又是立志传播福音的英国传教士,而传教士本质上是殖民主义战营中的文化先锋,充当着思想领域中的十字军,他们所信奉的基督教文化有着对外扩张的传统和特性。当时的西方物质文明和东方比起来有着压倒性的优势和力量,因此传教士在布道和传输文明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展现出文化殖民和思想侵略的趋势。改写的最显著特征是顺应译入语国家的主流诗学,思想和行文表达上的改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文中的教义传播与殖民征服的色彩和倾向,起到了某种缓解与中和作用,保留了本土文化身份,发扬了译入语的文学性,同时也在帝国主义殖民文化的浪潮中确保了汉语的话语权力。
《揽要》所引起的广泛社会影响及其历史地位,与译者采取的诗学改写策略息息相关。虽然有批评称倾向于主流诗学的改写即滥用本土典故与四字格成语,易造成无端具象化,但余光中也形象地指出,偏向原语诗学译文的常见毛病则是“当当乱响”与“的的不休”,[9]往往不堪卒读。改写策略将译文向译入语读者的知识框架靠拢,使原语的文化背景与本土思想相融合,在提高译本可读性和淡化原语的文化侵略方面,诗学改写的作用和意义都是不可忽视的。虽然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改写论偏向宏观的文化层面,缺少对具体翻译实践的指导价值,但《揽要》的成功也为改写策略的应用和实践提供了良好的参考典范。
[1]苏慧廉.李提摩太在中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25.
[2]麦肯齐.泰西新史揽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5,38,96,222 -223.
[3]田中初.游离中西之间的职业生存:晚清报人蔡尔康述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3):44-49.
[4]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e Education Press,2004:17.
[5]Mackenzie,Robert.The 19thCentury:A History [M].Fourteenth Edition,Thomas Nelson And Sons,London,Edinburgh,and New York,1893:13.
[6]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103.
[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64.
[8]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211.
[9]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