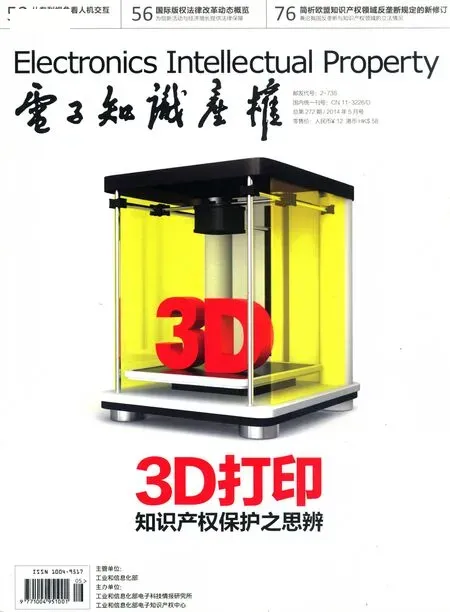3D打印行为的著作权规制:旧瓶能否装新酒?
2014-03-29熊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熊琦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著作权法作为主要规制传播行为的法律,每当新传播技术得到普及时,就面临如何在新技术条件下进行权利配置的问题。3D打印技术的发展和成本的降低,使得立体物能够被3D打印设备的使用者所轻易扫描和复制,由此引发了关于3D打印对象的可版权行和打印行为的合法性讨论。但由于3D打印技术的行为也并未在著作权领域产生新的法律关系,因此通过对现有规则的类推适用和已有判例的解释经验,仍然能足够解决3D打印行为带来的著作权问题。
一、引言
3D打印技术作为一项以三维数字模型为基础,采用逐层制造方式将材料结合起来的制造工艺,已呈现出代替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一体化大规模生产的趋势,使得制造业开始由标准化向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在3D打印技术的帮助下,产品从创意设计到制造的环节将被改变,设计者甚至消费者都可以直接利用3D打印设备将所设计或所需打印出来直接获取产品,从而省略了制造者的环节。虽然从现阶段看,由于暂时性的技术和成本瓶颈,通过3D打印获得的产品在制造业中所占比例极低,但从长远来看,3D打印将如前述网络技术一样实现普及化,并对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1.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11年即把3D打印技术视为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参见The printed world,Economist (2011-2-10).作为与传播技术密切联系的法律,著作权法往往需要根据新的传播技术调整制度安排,在著作权制度变革历史中,录音技术、录像技术和网络技术先后在不同程度上迫使著作权法改变其规范设计,以适应传播技术的发展。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当3D技术如前述传播技术那样能够为公众所使用时,著作权法必然需要做出应对。然而难以预测的是,著作权法应以何种方式规制3D打印行为,究竟是通过对既有著作权规则的解释来涵盖,还是另设新规则来调整。上述问题既关乎3D打印商业模式的未来,也是历史上著作权制度每次面临传播技术冲击所必须回应的。
二、著作权语境下的3D打印对象和行为
不同于音乐作品和电影作品等无体物,著作权领域内的有体物更多是作为作品的载体存在,而没有与著作权直接发生法律上的关联。但如果美术作品、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以有体物为载体时,对该有体物的复制就属于著作权法规制的范围。与以往传统的复印、摄影甚至数字技术以再现二维对象不同,3D打印能够直接再现三维立体物。2.技术介绍可参见Hod Lipson, Melba Kurman, The Ten Principles of 3D Printing, Bigthink (Mar. 2, 2013), http://bigthink.com/experts-corner/the-ten-principles-of-3d-printing.(2014年4月30日访问)。从技术流程上看,3D打印过程中诸如分层加工和叠加成形等技术原理,与著作权制度并无直接关联,但技术流程实施所依据的前提与结果,则可能涉及著作权法的相关规范。由于历史上著作权法乃基于二维再现技术来设定的权利体系,因此在适用于3D打印行为时,当然会产生特殊的问题。
1. 3D打印所涉著作权客体
3D打印所涉客体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作为3D打印前提依据的可执行文件。在实践中,CAD文件是3D打印设备形成最终产品的依据,使用者既可以独立创作新的3D造型,也能够通过扫描已有的产品来形成【1】。使用者将CAD文件转换成打印设备可读的.stl后缀文件后,即可以数字形式被广泛传播【2】。从上述文件的功能出发,CAD文件及其转化后的文件类型,可视为著作权法中的图形作品或软件作品,鉴于两类作品保护范畴的差异,在界定上还需要进一步分析。第二种类型是作为3D打印技术结果的实体产品。在打印设备根据CAD文件完成打印后,根据文件记载数据和形状所形成的实体产品或实体作品上的图形,如果具备独创性,当然可以视为相应的美术、图形、模型甚至建筑作品,以及立体物中其他符合作品要件的部分。
从3D打印的效果来看,打印行为主要涉及的是从平面到立体的复制,即把载有三维产品相关参数的数字文件通过打印设备转化为实体化的立体产品。
2. 3D打印所涉著作权内容
从3D打印的效果来看,打印行为主要涉及的是从平面到立体的复制,即把载有三维产品相关参数的数字文件通过打印设备转化为实体化的立体产品。2013年美国有线电视网HBO就曾向制造商Fernando Sosa发出律师函,禁止其售卖3D打印的一款手机保护壳,因为保护壳的样式仿制于HBO享有著作权的美剧《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中的铁剑王座,3. 关于该案例的介绍可参见Business Insider, Here is the 3D Printed “Game of Thrones” IPhone Dock That’s Banned by HBO,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game-of-thrones-iphone-dock-2013-8.,(2014年5月4日访问)。该铁剑王座作为模型作品,制造商的打印行为显然侵犯了HBO的复制权。同理,3D打印设备的使用者在制作打印所依据的CAD文件时,如果是对他人作品的扫描或模仿,那么同样涉及到从立体到平面或者从平面到平面的复制行为,属于著作权法复制权的范畴。另一项涉及著作权内容的,是对3D打印设计图的传播行为。随着3D打印设备的逐步普及,通过网络传播CAD文件的行为也有增无减。如同数字录音制品和电影作品通过网络传输一样,这其中不但包含潜在侵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还涉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间接责任问题和网络最终用户的下载行为。
三、3D打印行为的著作权解释规则
根据上述对3D打印行为与著作权制度的关联分析,可以发现无论从权利客体的判定方法还是权利类型的范畴解释上,针对3D打印行为并无需专门创制新的著作权规则,而是直接通过对既有规则的解释即能解决多数问题。事实上,制度创新抑或守成永远都是著作权法律应对技术发展和社会变革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每当新技术冲击既有版权产业和市场时,上述讨论即会在著作权立法和司法界全面展开。从在音乐著作权领域引发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的自动钢琴,到改变合理使用解释规则的录像设备,再到颠覆音乐产业并引发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责任承担问题的P2P网络传输技术,4. 相关代表性案例参见White-Smith Music Publishing Co. v. Apollo Company, 209 U.S. 1 (1908), Sony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464 U.S.417 (1984),A&M Records, Inc. v. Napster, Inc., 239 F. 3d 1004 (9th Cir. 2000).著作权制度创新都是体现在传播技术改变了著作权法律关系的情形下。强制许可制度的创制,乃是录音制品代替乐谱(音乐作品)成为了供使用者消费的新权利客体,需要强制许可调控音乐作品著作权人与录音制作者之间的关系。5. 关于强制许可制度与产业主体争议之间的关系参见熊琦:《音乐著作权制度体系的生成与继受》,载《法学》2013年第12期。“索尼案”对合理使用解释规则的改变,则是因为录像设备的普及使得对复制权的界定出现争议,但由于并未增加新的权利主体、客体或内容,所以并未专门创制著作权规则来加以应对。同理,在20世纪末著作权制度首次面临网络技术的冲击时,各国并没有专门为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法律关系创制新的规则,例如美国即通过扩大既有著作财产权的范畴来解释网络传播行为,欧盟和我国也多借助侵权责任法中的共同侵权来调整网络环境下的间接侵权问题。6. 即使是美国间接责任中的帮助侵权、替代责任和引诱侵权,也主要是对传统侵权责任形态的扩大适用。因此,对于3D打印行为而言,更多需要的是类推适用和解释,而并非新规则的创制。
1. 独创性判断:3D打印对象的可版权性界定
从区分性的角度看,只有当立体物的艺术性能够与功能性明确区分时,对审美性部分才能够获得独立的著作权保护。在3D打印行为的对象中,存在大量艺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立体物。
关于3D打印行为是否需要得到他人授权,首先需要判定3D打印过程中的扫描和复制对象是否具有可版权性。与以往文字作品和视听作品等著作权客体不同,著作权法对有体物作品类型的保护总是存在诸多模糊之处。在实践中,3D打印技术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复制行为不同于传统复制之处,在于其复制对象更多是立体物。然而,将上述立体物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不但需要对其进行独创性解释,还需要能够将其艺术性区分于功能性。
从区分性的角度看,只有当立体物的艺术性能够与功能性明确区分时,对审美性部分才能够获得独立的著作权保护。在3D打印行为的对象中,存在大量艺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立体物,伯尔尼公约将其称为“实用艺术作品”(works of applied art)。从实用艺术作品艺术性与实用性的关系看,美国法院在判例中将其分为了“物理性可分离”(physicalseparability)和“观念性可分离”(conceptual separability)两种类型【3】。对于从物理上即可直接分离的前者而言,例如立体物上的美术作品或者具有艺术审美意义的模型作品等,3D打印行为显然会直接涉及对独创性作品的复制,因而无论是前期扫描抑或后期打印,都需要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但对于无法从物理上加以分离的后者而言,例如装饰品和玩具等,3D打印行为对象的可版权性,则要求立体物的艺术特征能够从概念解释上独立于其实用功能,即满足“可分离性”标准。7. See U.S.C.§101 (2010).然而,在如何界定观念性可分离的标准上,即使是明确保护实用艺术作品的美国也没能拿出明确的评判规则,相反还出现了法院的判决摇摆不定的情形。8. 相悖判决可参见Kieselstein-Cord v. Accessories by Pearl, Inc., 632 F.2d 989, 993 (2ndCir. 1980); Brandir Int’l, Inc. v. Cascade Pac. Lumber Co.,834 F.2d 1142, 1145 ((2nd Cir. 1987).一般而言,在界定观念性可分离上,法院仍然采取的是“融合理论”(merger doctrine),即如果当思想只能通过极为有限的方式表达时,该思想即因与表达方式融合而不受著作权的保护【4】。对于3D打印的对象而言,如果艺术性的表现只能通过功能性表现出来,那么应视为艺术性与实用性不可分离,则该对象不适用著作权法保护。9. 关于实用艺术作品因艺术性与功能性融合而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判例,可参见Lanard Toys Ltd. v. Novelty Inc., 511 F. Supp. 2d 1020 (C.D.Cal. 2007).
虽然在界定实用艺术作品的可版权性上存在困难,但著作权法承认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显然能够为保护3D打印行为的诸多对象提供更为直接的法律依据,著作权法在自动保护,长期保护和可版权性标准低等方面的特点,能够在3D打印设备逐步普及的未来给著作权人提供及时有效的保护手段。遗憾的是我国著作权法至今没有将实用艺术作品纳入作品类型中,但1992年国务院颁布的《实施著作权国际公约的规定》,却又要求对外国使用艺术作品加以保护【5】,导致我国对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只能类推解释美术作品的规定。但如今在国家版权局起草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中,实用艺术作品首次被纳入保护范围,意味着我国未来著作权法可能在此问题上取得突破。10. 也有学者认为此举会造成著作权法和专利法对同一客体的重叠保护。参见张伟君:《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法保护与外观设计专利法保护的协调》,载《知识产权》2013年第9期。如果我国著作权法将来增加对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那么在界定3D打印行为对象的可版权问题上,将有助于防止3D设备使用者对实用艺术作品可能造成的大规模侵权。
2. 私人复制问题:3D打印行为的合法性考察
回顾著作权制度发展史上因录像设备和网络技术普及所引发的争议,能够发现两者所涉都是新的复制和传播技术由私人掌握后,著作权人因私人复制对相关著作权市场造成影响而争取自身权利的努力。在以往的技术条件下,之所以大量私人复制行为被视为合理使用,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复制效果上看,该行为并未对权利人利益和著作权市场造成消极影响或替代,第二,从制度成本上看,无论是著作权人还是其他著作权管理机关,都难以在合理成本范围内控制私人复制行为,所以著作权法将规制范围集中在商业使用行为上。11. 据不完全统计,美国法院在涉及合理使用的判决中,超过百分之九十都将商业使用视为排除合理使用的标准。See Mattew W. Wallace,Analyzing Fair Use Claims: A Quantitative and Paradigmatic Approach, 9 U. MiamiEnt. & Sports L. Rev. 121 (1992).一旦私人复制突破了上述两个条件,都会随之在司法上被排除在合理使用之外。
从通过3D打印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来源来看,无论是从平面到立体抑或从立体到立体的复制行为,如果是以商业目的大规模打印,显然需要得到原作品著作权人关于复制权的授权,但如果3D打印为个人以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为目的进行扫描或者复制,该私人复制究竟属于合理使用抑或侵权行为,则需要重新解释。从3D打印所涉的私人复制方式来看,这种复制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打印设备实施的复制行为,二是借助网络传播记载三维立体物数据的可执行文件,使其他不特定的3D设备使用者获得可执行文件。与其它私人复制相似,关于通过打印设备实施的复制行为,主要争议焦点仍然集中在侵权行为与合理使用之间的界限上。一旦当3D复制设备的成本能够为普通消费者所承担,私人即可自行利用3D打印技术实现“私人定制”。这种私人定制既可能表现为通过取得记载三维立体物数据的可执行文件直接再现他人作品,也可能是在扫描他人三维立体物的基础上生成可执行文件并自行打印。从本质上看,上述两种行为显然与录像设备使用者录制视听作品和网络最终用户下载数字录音制品的行为具有相似性,但索尼案中复制视听作品的主体仍然是合法首次取得作品的使用者,复制后的作品利用范围并未因此扩大,所以得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而适用合理使用。相反,P2P软件服务提供者则帮助网络用户将数字录音制品传播给了更多使用者,即说明网络用户的私人复制行为对相关著作权市场产生了替代。12. 美国法院对网络环境下利用P2P软件进行私人复制的合法性问题分析可参见A&M Records, Inc. v. Napster, Inc., 239 F. 3d 1004 (9th Cir.2000).由上述分析可以认为,3D打印行为究竟属于对复制权的侵犯还是视为合理使用,区别并非在于使用者是否以3D打印技术实施私人复制,而是私人复制是否对著作权人利益或者作品潜在市场与价值造成消极影响。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的规定,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为目的使用他人已发表作品,以及对设置或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和录像,都属于合理使用的范围。但单从上述条文出发,并无法准确得出3D打印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范围,因为私人实施对他人作品的3D打印,很可能就是为了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的需要,但由于作品的许可和发行同样是针对个人的上述使用,那么合理使用与授权许可之间就可能出现矛盾。另外将公共场所艺术品扫描制作成能供3D打印设备识别的文件是否能类推为临摹,也难以得出明确的答案。
有鉴于此,3D打印行为虽然无需通过创设新的权利进行规制,但作为限制制度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应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即在《著作权法》中列举属于合理使用行为的具体情形外,还应增加一般性的判定标准,明确规定合理使用行为不得对著作权人利益或者作品的潜在市场价值造成影响。事实上,我国正在进行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在完善这一规定上已经形成了共识。13. 无论是来自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项提供的三步检测法,还是由美国著作权法创设的合理使用“四要件”,利用行为对作者的合法利益或对作品潜在市场与价值不得造成消极影响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判定要素。相关介绍可参见Tyler G. Newby, What’s Fair Here is not Fair Everywhere: Does the American Fair Use Doctrine Violate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 51 Stan. L. Rev. 1633 (1999), p. 1647.当然,如果对他人作品进行扫描后创作者又加入了新的独创性元素,那么当然也可依据“转换性使用”被视为合理使用。14. 2006年美国玩具制造商曾在其品牌的玩具上戏仿路易斯威登的设计,被法院认定为“戏仿”而适用合理使用,See Louis Vuitton Malletier S.A.v. Haute Diggity Dog, LLG, 464 F. Supp. 2d 495 (E.D. Va. 2006).
关于通过网络传播记载三维立体物数据之可执行文件的行为,关键问题则在于如何保证对原作品权利人的充分救济。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规定,著作权人可通过绝对权和侵权(相对权)请求权两种方式寻求救济。根据绝对权请求权救济方式,著作权人可“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来排除妨害。根据侵权请求权救济方式,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未及时或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或者知道网络服务提供者实施侵权行为而未采取必要措施的,著作权人即可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损害赔偿和其他责任。显然,对于直接通过网络传播CAD文件的行为,著作权人可以直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适用“通知-删除”程序,或向相关侵权主体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然而,在上述救济方式的适用上,通过网络传播CAD或相关文件的行为在认定上却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与文字和音乐等作品不同,由于如前所述之立体物艺术性与功能性的关系,无论是权利人抑或使用者,在通知和反通知中都很难根据“初步证明”侵权或不侵权,网络服务提供者自身显然也不具备初步判断是否侵权的条件。这一方面是因为前述立体物独创性判定的技术性和复杂性,各方都缺乏做出可行证明的知识储备和资格;另一方面是由于CAD文件并未直接体现立体物的整体形象,而是以计算机软件的方式记载立体物的数据供3D打印设备读取,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现有注意义务标准下,根本无法判断CAD文件是否涉及侵权问题。所以,基于侵害传统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所构建的避风港规则和红旗标准,都需要根据再次进行解释,否则“通知—删除程序”的便捷性功能将不复存在。
针对这种法律适用上的困境,法院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涉及传播CAD文件的注意义务需要根据2012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调整。根据该司法解释第9条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应知,重新从CAD文件类型的特点、知名度及侵权信息的明显程度来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
四、结论
早在1996年,美国第七巡回法院的Easterbrook法官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就对面向新技术的造法活动提出批评。Easterbrook法官颇具讽刺地将针对网络技术的造法比作专门围绕马匹的行为创制“马匹法”(Law of Horse),并认为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法律解释在既有规则框架内解决新问题,而无须频繁为每种新产生的行为设计规则【6】。从这一角度观察
3D打印行为,Easterbrook法官所持观点仍然能够适用。制度创新虽然能够为新问题量身定做解决方案,但会在制度成本的提高与制度适用的协调上造成新的障碍。是否选择以新规则规制新问题,最为稳妥的方法是观察该问题对既有法律关系的影响,如果新问题导致新法律关系的产生或改变原法律关系的性质,就需要创制新规则,反之则借助既有规则调整。从可预见的技术发展空间来看,3D打印技术并未给著作权法既有制度设计带来颠覆性的挑战。基于3D打印行为并未在著作权领域产生新的法律关系,即使是需要修订和完善著作权法的部分,其实在针对其他著作权问题时也早已提出,并非为3D打印行为所专门设计。因此,通过对现有规则的类推适用,借助已有判例的解释经验,我们已基本能够解决可预见技术条件下3D打印行为带来的著作权问题。
【1】Brian Rideout.Printing the Impossible Triangle: The Copyright Implications of 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J】.5 J. Bus. Entrepreneurship & L.161 ,2011:163.
【2】 Michael Weiberg.What’s the Deal with Copyright and 3D Printing【J】. Institute for Emerging Innovation , 2013(1):14.
【3】Carol Barnhart v. Economy Corporation, 773 F. 2d 411 (2nd Cir. 2005), p. 418.
【4】See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s v. Katzman, 793 F.2d 533, 539 (3rdCir. 1986).
【5】管育鹰.实用艺术品法律保护路径探析【J】.知识产权,2012(7).
【6】 Frank H. Easterbrook. Cyberspace and the Law of the Horse【R】.1996 U. Chi. Legal F. 207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