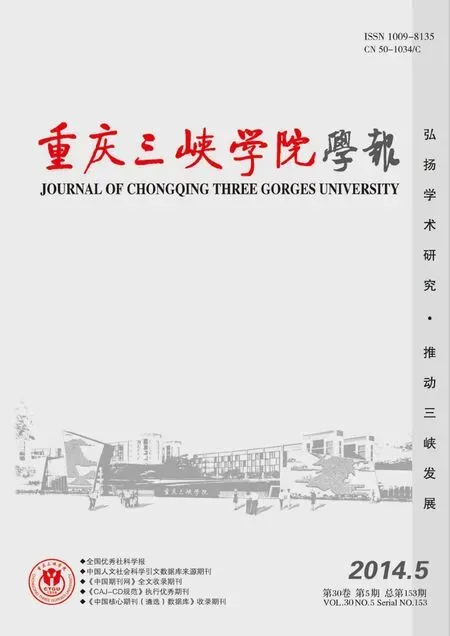叙事学视角下托马斯·哈代儿童小说的教育寓意
2014-03-29郭高萍
郭高萍
叙事学视角下托马斯·哈代儿童小说的教育寓意
郭高萍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广东东莞 523808)
结合叙事学相关理论,对托马斯·哈代的儿童小说进行文本细读,探索在故事和话语两个层面,哈代将“成人——儿童”的关系顺利转变为“教育者——被教育者”的关系,表达出儿童小说的道德寓意和教育功能。
哈代;儿童小说;叙事;教育
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是19世纪后期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他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53部中短篇小说、近千首诗歌和2部诗剧,尤其是他塑造的一批维多利亚女性群像,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然而,鲜有人关注到,哈代还曾创作过儿童小说。纵观哈代的创作历程,有两部小说可算作儿童小说,一部是《忍不住打喷嚏的小偷》(),一部是《西波利村探险记》()。《忍不住打喷嚏的小偷》于1877年12月刊登在《圣诞老人》()杂志上,是一本“供儿童阅读的年刊”[1]163,主要讲述一个小男孩运用智慧和勇气制服一群小偷的故事。《西波利村探险记》则是1883年夏天,哈代应美国著名儿童杂志的邀请而写的,1892年11月至1893年4月,该小说在波士顿的一家期刊上连载,这本刊物“主要是满足和服务于美国家庭主妇的阅读兴趣”[2]448。与《忍不住打喷嚏的小偷》相比,《西波利村探险记》的内容显得更为复杂,情节更为曲折,所蕴含的道德内涵也更为深刻。所以,本文将运用叙事学研究方法,对《西波利村探险记》进行文本细读,解读其中的成长主题,以及哈代试图表达的道德意义,教育儿童如何经过社会化和成人化过程,成为符合社会要求和道德规范的社会人。
一、故事层面的成长主题
在当代西方叙事理论界,大多数学者将作品分为“故事”和“话语”两个层次,“故事”主要涉及叙述了什么,包括事件、背景和人物等;“话语”主要涉及“怎么叙述的”,包括叙述形式和技巧等[3]13。
《西波利村探险记》主要叙述斯蒂夫和“我”(伦纳德)这两个十几岁小男孩探险,最终解决西波利村和东波利村这两个村庄用水之争的故事。在小说中,我到姑妈家作客,表哥斯蒂夫带我到鬼袋洞里面探险,无意间改变洞中溪水的流向,却发现将原本流淌在西波利村的溪水引到东波利村去了。没了溪水,西波利村磨坊的水车声停止了,村民的生活用水成了难题,但残暴磨坊主格里芬的学徒乔布却得到了自由。这两个小男孩认为伸张了正义,而且自认为东波利村比西波利村多了一百多人,他们更需要溪水,所以决定将溪水留在东波利村。同时,他们还假扮魔术师,向东波利村小孩显示自己超凡的力量,可以让溪水的流向和时间听从自己的安排。可是,他们却发现,如果溪水留在东波利村,一个贫苦寡妇的菜园将被淹没,而且她将被粮食批发商赶出家门。这两个村庄都因为溪水的问题而存在残暴的行为,斯蒂夫的正义感再次涌上心头,斯蒂夫和我为将溪水引向哪个村而感到苦恼。刚获自由的乔布成为了新的玩伴,为了不再回到残暴磨坊主身边工作,他便将溪水引向第三个洞,这虽避免了流向这两个村庄,却导致溪水在洞内急剧上涨,将三个孩子都困在了洞中。在西波利村村民的帮助下,他们才被救出。斯蒂夫吐露了溪水源头在鬼袋洞的秘密,却引发东波利村和西波利村争夺水源的斗争,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斯蒂夫炸毁了洞口,恢复了长年以来溪水流向西波利村的状况,也避免了今后两个村庄再起争水冲突。
从情节上看,叙述是按照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排列的,虽然参与探险的主要人物包括斯蒂夫、“我”和乔布,但是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人物是斯蒂夫。如果细读文本,就会发现这部小说试图表达的成长主题。文中在情节发展、人物性格变化等方面设立了几个对比关系:以斯蒂夫为代表的儿童和以“失败者”为代表的成人、以“失败者”为代表的正义善良与以磨坊主为代表的自私残暴、探险前的斯蒂夫与探险后的斯蒂夫。通过这几个对比关系,斯蒂夫从爱冒险、贪玩轻率、爱走极端、不讨人喜欢、不顺从家庭安排的儿童成为了伸张正义、勇敢善良、继承父业、当地富有声望的乡绅。
(一)以斯蒂夫为代表的儿童和以“失败者”为代表的成人
故事中的儿童主要包括斯蒂夫、“我”伦纳德、乔布,成人主要包括“失败者”、磨坊主、鞋匠及斯蒂夫母亲。斯蒂夫爱冒险,有胆量,准备好工具和干粮带着我到西波利村的鬼袋洞探险,获得乐趣。而且,为了显示自我的超能力,二人假扮魔术师的样子,在帽子上围金边,找马鬃粘成胡子,把柳枝削成精致的魔杖,到东波利村去糊弄小孩子。他们故作威严的身姿步态,还“施行魔术”,口中念“咒语”——通过让乔布控制溪水流到东波利村的时间,来骗取那些孩子的苹果。游戏是儿童的天性,而儿童或多或少也都有冒险的欲望,魔法可以满足儿童好奇心,符合儿童喜欢探索的天性,而且在游戏、探险和施展魔法的过程中,有两三个伙伴共同参与,这都对儿童读者产生了吸引力。可是,儿童的游戏行为却与成人的社会规则发生了冲突。在故事中,由于斯蒂夫和“我”挖山洞,导致磨坊主无法正常工作,全村人面临用水困难。
(二)以“失败者”为代表的正义善良与以磨坊主为代表的自私残暴
故事中围绕溪水的流向问题,出现了一些成人自私残暴的行为,叙述者将这些行为与正义善良的行为作了对比,也将这些丑恶的成人与善良的儿童作了对比,弘扬正义善良、乐于助人的精神。故事中主要通过磨坊主与乔布的关系展现这一对比关系。磨坊主长期欺压虐待学徒乔布,当没有溪水推动水车转动时,磨坊主不仅不遵守合同,而且打骂乔布,不允许离开磨坊,不支付工资。最后,还是靠“失败者”出面调解,磨坊主才不得不让乔布离开。而且,在“失败者”的帮助下,乔布也在邻村找到了新工作。
斯蒂夫和我虽然是儿童,但也同情乔布的遭遇,所以运用自己的方式——让溪水流向东波利村,来维持乔布的自由。尤其是当磨坊主与三个儿童都落入山洞而无法脱身时,三人运用智慧,要求磨坊主立下字据,不再欺压乔布。无论是“失败者”还是斯蒂夫和我,都一直与自私残暴的行为作斗争,伸张正义,帮助无辜贫苦的弱势人群。
(三)探险前的斯蒂夫与探险后的斯蒂夫
从社会学角度讲,一个人刚来到世上,还只是一个“自然人”,只有经过群体生活,才逐步成长为“社会人”。一般情况下,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三个阶段:儿童期、少年期、青年期[4]458-459。斯蒂夫十五六岁,正处于少年期阶段,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具备一定的独立意识,有自己对事物的认识,但还是无法完全摆脱对成人的依赖性。探险前的斯蒂夫天真淘气,敢作敢为,爱憎分明,充满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不想按照家里的安排当农民,而是一心想当探险家。可是在无意改变溪水流向而引发一系列矛盾冲突之后,他意识到自己给村民带来了麻烦,也造成了西波利村与东波利村的用水之争,他就冒着牺牲自己的危险,炸毁了洞口,恢复了溪水流向。
斯蒂夫这种勇于承认错误,敢于承担责任,乐于助人和自我牺牲精神获得了全村人的认同和赞赏,他也开始学着管理父亲留下来的农场,不仅获得了全教区人们的好感,自己也成为当地最有声望的乡绅。可以说,通过探险一事,斯蒂夫从叛逆变得顺从(子承父业),从不计后果变得成熟稳重,从以自我玩乐为中心变得以全教区人们的利益为重心,这些道德品质使他最终得以进入成人世界,完成社会化和成人化的过程。
二、话语层面的教育意义
小说叙事是一种语言交流的艺术,美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中,提出如下叙事交流图:
叙事文本
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隐含读者→真实读者
这个图表中有六个参与者,但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是被置于叙事交流范围之外的[5]155,文本内的隐含作者是信息的发出者或文本的创造者。根据美国叙述学家韦恩•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中的观点,隐含作者是处于创作状态、以某种立场来写作的作者,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的区分实际上是处于创作过程中的人(以特定的立场来写作的人)和处于日常生活中的这个人(可涉及此人的整个生平)的区分[3]71。布思还指出,隐含作者“有意或无意地选择我们会读到的东西”,作品是隐含作者“选择、评价的产物”,他是“自己选择的总和”[3]74。而隐含读者就是隐含作者心目中的理想读者,或者说是文本预设的读者,与隐含作者保持一致。
在《西波利村探险记》中,一直存在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与隐含读者的相互交流,而在各类交流中,也同时体现出成人与儿童之间的权力关系。在文本之外,是成人作者与儿童读者之间的关系;在文本之内,是以“失败者”为代表的成人与以斯蒂夫为代表的儿童之间的交流。无论文本内外,都是为了搭建“成人——儿童”之间演化为“教育者——被教育者”的权力关系,从而实现儿童的社会化过渡,使其最终成为符合社会要求和道德规范的成人,顺利进入由成人确定的社会体制。
(一)文本之外:成人作者与儿童读者的交流
19世纪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涌现出了中产阶级,这一阶级成为小说的主要阅读群体,而且该阶级的儿童开始接受良好的教育,阅读能力得到提升,而儿童读者尤其对历险类小说情有独钟。细读文本就会发现,故事中的主要儿童都是中产阶级,斯蒂夫是农场主之子,“我”是教师之子,作为探险的主要人物,他们的视角、经历和情感体验必将影响到同为中产阶级的儿童读者。
如前所述,这部小说是哈代应美国著名儿童杂志而写,读者是儿童群体,而所刊登杂志的主要读者是家庭主妇。根据19世纪社会情况,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出现分离,家庭成为私人领地,家庭主妇主要负责打理这个小圈子的各种事务,包括教育孩子,所以孩子与母亲的关系比较亲密,而对父亲充满敬畏。可以说,通过这本供家庭主妇阅读的杂志,小说中所蕴含的儿童教育主题同样可以通过母亲而传播给家中的儿童。
当代英国评论界马丁•格林在《冒险的梦想与帝国的事业》中指出,英国文学中除了“伟大的传统”外,还有另外一个传统,那就是“注重行动与男子气概的历险小说传统”[6]81。在小说标题下面,有一个副标题“写给男孩们的故事”(A Story For Boys),可见,隐含作者创作时所预设的隐含读者是男性儿童。进一步讲,是具有阅读能力的中产阶级出身的男性儿童。
小说的隐含作者是成人,隐含读者是儿童,一般情况下,少年阶段的儿童是儿童文学的主要阅读群体,可塑性最强,最易接受形象化的教育。他们正处于被认为不具备成熟品质,必须接受知识及道德储备要求的阶段,成人作者可通过生动形象的作品向儿童读者讲述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促使儿童完成塑造道德品质、承担社会义务的蜕变。儿童读者通过文本中的情节变化和人物关系进一步认识了自我,明确了成长目标,明辨了是非标准,知晓了善恶行为,也逐步向符合成人社会规则的方向努力,最终成长为合乎规范的“社会人”。
(二)文本之内:成人叙述者与儿童受述者的对话
在文本中,叙述者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叙述者“我”参与故事,是“同故事叙述者”,这就拉近了叙述者与隐含读者之间的距离。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又有两个不同的视角:一是叙述者“我”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我”处于往事之外,属于外视角;一是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叙述者放弃处于故事外的观察角度,转而采用当初正在体验事件时的眼光来聚焦,当时的“我”处在故事之内,故构成一种内视角。在文本叙述中,叙述者经常交替使用以上两个视角,达到引导隐含读者判断是非、识别善恶的目的。小说一开始,叙述者就交替使用两个视角。
“一个早秋的黄昏————天气晴朗,我在拉萨默塞特郡西波利村的一家农舍前,跳下绿色的轻便双轮马车。,作为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我虽然个子矮小,却身体结实,行动敏捷。”[7]178
在上面这段文字中,划线部分的“我”是追忆往事的视角,其他则是经历事件的视角,追忆的视角虽然让读者感觉到叙述者与往事之间的距离,但可让其以比较理性的态度接受故事及其所传达的道德寓意。当使用经历事件的视角时,叙述者进入故事情境,则使故事更加生动活泼,能极大调动读者的参与性,使其产生感同身受的阅读体验,不自觉跟随“我”的视角去认识文本中的人物和事件,认同“我”的道德判断。
尤其是关于“失败者”的叙述,更体现出叙述者的引导作用。在“失败者”第一次出场时,叙述者就采用预叙方式,奠定了全文的道德评价基调。
“听了这样的介绍,我也同斯蒂夫一样,不去理睬失败者的话了。,我们都还年幼,谁都不理解,那些人生斗争中的失败者,往往正是最清楚地了解怎样才能成功的人,虽然对他们自己来说已经为时过晚;而那些成功者,则往往被自己的成就蒙住眼睛,兴奋得看不见成功的原因”。[7]179
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第一人称可指称两个不同的主体意识,回顾往事时的“我”是“叙述自我”,是故事外的同故事叙述者;当初经历事件时的“我”是“经验自我”,是故事内的同故事叙述者[8]744。在上述引文中,第一个“我”正与斯蒂夫讲话,处于故事之中,是“经验自我”;但从“那时”开始,叙述者“我”从“经验自我”转入“叙述自我”。“失败者”告诉斯蒂夫,“小伙子最好是继承父业”,可是遭到斯蒂夫的嘲笑。如果说故事中的“经验自我”和斯蒂夫一样,表示了对“失败者”忠告的不屑,那么随后的“叙述自我”马上就对前面“经验自我”的态度就表示了否定的意识,认为虽然这个成人自称“失败者”,可是他却是最了解如何成功的人,他的忠告也是值得听取的。在故事快结束时,斯蒂夫果然按照“失败者”所说,成为继承父业的儿子,帮助母亲经营农场。
在文本中,“失败者”一共出现了六次,第一次是忠告斯蒂夫继承父业,第二次是安慰磨坊主,第三次帮乔布获得自由,第四次是组织村民救人,第五次是预言东波利村将来争夺水源,第六次是点明他帮乔布介绍工作,并组织村民救斯蒂夫,还对其进行教育。可以说,每次“失败者”都作为预言者或正义的化身而出现。在斯蒂夫的成长过程中,缺乏父亲的管教,但“失败者”适时扮演了“缺席”父亲的角色,一次次解救斯蒂夫,并引导斯蒂夫走上顺从成人社会规则的道路,帮助其实现社会化。通过“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的融合,叙述者从一开始就引导隐含读者肯定“失败者”的言行,更随着情节的发展,进一步强化隐含读者认同“失败者”价值观的意识,并同时引导读者根据斯蒂夫的成长历程来反省自我,促使自身也能像斯蒂夫一样,改掉顽皮贪玩、轻率任性的毛病,成为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人。
综上所述,《西波利村探险记》达到了儿童小说的教育功能、认知功能、娱乐功能等多种功能的统一。总之,哈代在创作中,将故事层面和叙述层面的“成人——儿童”的关系顺利转变为“教育者——被教育者”的关系,生动表达了儿童如何完善自我、提升道德品质、步入成人社会的教育主题。
[1]Kristin Brady,The Short Stories of Thomas Hard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2.
[2]Page, Norman. Oxford Reader’s Companion To Hard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宋林飞.现代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5][以色列]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M].姚锦清,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6]陈兵.英国历险小说:源流与特色[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7][英]托马斯•哈代.西波利村探险记,哈代精选集[Z].朱炯强,编选,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
[8]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张新玲)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Thomas Hardy’s Children Literature under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GUO Gaoping
The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moral thought and educational function in Thomas Hardy’s children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criticism. This paper, from the aspects of story and discourse, explores Hardy’s efforts to transform the adult-children relationship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education.
Hardy; children literature; Narratology
I106
A
1009-8135(2014)05-0102-04
2014-05-18
郭高萍(1980-),女,湖北襄阳人,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助理研究员,文学硕士,主要研究19世纪英国文学,比较文学与中西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