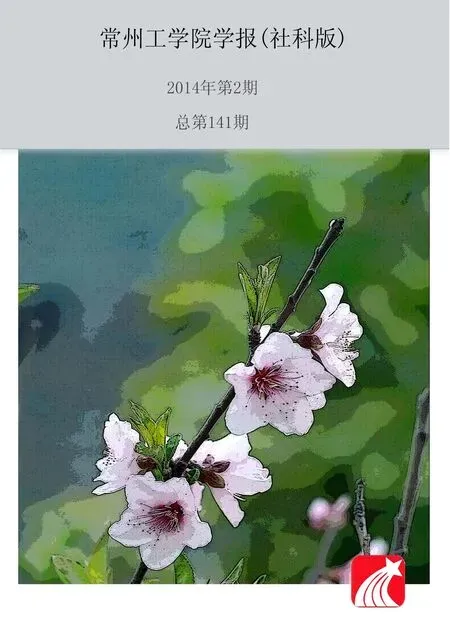人格障碍者的阶级梦魇
——论达夫妮·杜穆里埃《瞬间》中埃利斯夫人的身份焦虑
2014-03-29郭看
郭看
人格障碍者的阶级梦魇
——论达夫妮·杜穆里埃《瞬间》中埃利斯夫人的身份焦虑
郭看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苏州215006)
英国女作家达夫妮·杜穆里埃的短篇小说《瞬间》讲述了一个时空穿越的超自然故事。文章通过分析埃利斯夫人表现出的三种人格障碍特征,管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中产阶级女性的生存状态,揭示个人在面对时代和社会变迁时的无力与无奈。
《瞬间》;女性;中产阶级;身份焦虑;人格障碍
英国女作家达夫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1907—1989)于1971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现在别看》。作为一名作家,杜穆里埃一贯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单纯地界定在某种文学体裁之内,她的早期作品被认为是“哥特小说、罗曼史和家族传奇的杂糅”[1]159,而其晚期的短篇小说作品又在这一基础上加入了“神秘、科幻和鬼怪故事的因素”。文章所要探讨的短篇小说《瞬间》就属于其典型的晚期作品。
杜穆里埃对女主人公埃利斯夫人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自我身份的思考。达夫妮·杜穆里埃虽然出身高贵,但是她并不安于这一身份。20世纪,尽管女性地位有了极大提高,但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束缚依然难以根除,杜穆里埃看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被边缘化的地位,伴随女性身份而来的焦虑使她疏远家庭、不断创作,以求抵御社会对她的性别定位。早在1947年,杜穆里埃就在给同性密友艾伦·达博德的信件中提到,自己不得不把心中的“一个小男孩”锁进箱子,只能在无人的夜晚打开箱子,放出自己“脱离肉体的灵魂”。杜穆里埃对身份的焦虑在她笔下的女性人物身上同样也有所体现。
《瞬间》的女主人公埃利斯夫人的形象塑造首先与她的女性身份密不可分。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数年中,社会舆论强烈要求女性回归家庭生活,“她们迫于压力,不得不放弃在战争时期负担的工作,把这些岗位留给回家的士兵们”[2]32。战争让女人走开,这一时期的女性被边缘化的程度也相对较高,她们的社会身份一再被淡化,只能回归家庭生活,扮演“家中天使”的角色。
《瞬间》开篇的时间背景是1932年,这时社会最认可的女性形象当属中产阶级贤良淑德的妻子和母亲:
一位优秀的女性应该为自己是一位妻子和母亲而感到心满意足。在她们中间,中产阶级女性尤其被视为母性和女性气质的榜样。实际上,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数年(inter-war years)中,中产阶级女性所受到的社会行为规范对其的约束远远多于工人阶级女性所受到的约束。[3]18
埃利斯夫人就是这样一个“理想女性”:丈夫在世时,她以丈夫为中心,尽心尽力照顾他,甚至不惜搬到乡村以求获得更好的养病环境。丈夫过世后,她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女儿身上。埃利斯夫人习惯依附于丈夫和女儿,当她被当作可疑分子带到警察局时,她反复强调自己的身份:“我住在艾尔姆赫斯特街十七号,我是一个寡妇,我有一个九岁的女儿正在上学。”[4]325“寡妇”和“女儿”无疑彰显了她的女性身份,而“艾尔姆赫斯特街十七号”所代表的阶级身份却是她真正看重的东西。
埃利斯夫人生活富足安逸,而长久的焦虑最终导致她患上多重人格障碍症。文章主要分析了埃利斯夫人的三种人格障碍,从而说明上世纪30年代英国中产阶级女性心理及生存状态。
一、骄傲的中产阶级:孤立冷漠的人格障碍者
埃利斯夫人的阶级身份与她的家——艾尔姆赫斯特街十七号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她为自己居住地段所代表的中产身份感到自豪,认为这些住宅都是“坚固的”“未遭破坏”[4]301,任何“出租的房屋”都会让“整个街区掉价”[4]305;另一方面,她对有可能到来的阶级下降感到极度的担忧和恐惧。她不由自主地鄙视着“无政府主义者”“罢工者”和“失业者”。时光的倒错让她无家可归,面对警察和医生的质疑,她仍然能够保持良好的风度。面对前来寻找精神病人的家属她尚且能够冷静持重,只是暗暗懊悔自己没有戴上象征身份的帽子和手提包出门。然而,当医生怀疑她是患有臆想症的女仆时,埃利斯夫人第一次失去自控力,愤怒到“几乎要打他”的程度[4]336。女主人公对于自己被误认为精神病患只是略有微词,却因被视作下等人感到极端屈辱,由此可见她对自己阶级身份的深重执念。事实上,中产阶级的确在战争间隔年里终日惶惶然于如何捍卫自己的阶级身份和物质财产:
战争间隔年里的中产阶级者通常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上保持着保守的姿态,他们奉行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对外界漠不关心,一味沉浸在对战前生活最后的回顾以及最后的周末时光的回味中不能自拔……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乱了许多社会阶层的结构……[2]32
这种自我保护、孤立冷漠的态度在埃利斯夫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根据1994年美国精神科学会出版的《DSMIV分类与诊断标准》,分裂样人格障碍的鉴定标准有:
分裂样人格障碍(schizoid personality disorder)是一种脱离社交关系,在人际交往时情感表达范围狭窄的普遍模式……患者没有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愿望,亦不能从中感到乐趣;几乎总是单独行动;对几乎任何活动不感兴趣;除了一级亲属外,没有亲密的朋友或知己;表现情绪冷淡、隔膜或情感平淡。[5]220-221
埃利斯夫人的行为基本符合以上四项条件,足以证明她在人际社交方面的问题。丈夫死后,她把全部的感情都投射到了唯一的一级亲属——女儿苏珊身上。她自己也坦言:“仔细想想,我的生活都是围绕着苏珊进行的。”[4]301她精心为女儿准备零食,购买各式各样的礼物,隔三差五地给她写信。这位母亲数着月份盼着女儿回家,对她而言,女儿在家的假期时光宛如“背景上色彩鲜亮的珠子”,其他时光则是“模糊一片”[4]302。
然而,她的感情付出并未收获同等的回应,苏珊宁可留在寄宿学校也不愿回家走读。女儿的这种反应让母亲“很受伤”,但她“丝毫没有在女儿面前流露出失望的情绪”[4]302,只是不断地压抑自己的情感,希望能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这种做法让她的焦虑与日俱增,她常常感到莫名的心悸,这昭示着她人格障碍症状的加深。
在女儿处受挫的埃利斯夫人根本无法拥有正常的社交,与朋友、亲戚和邻居的关系冷淡疏远:她家里的客房一尘不染,等待着“永远不会来的客人”[4]300。她在警局打电话请求朋友的帮助,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求助的人,只得暗暗懊悔当初“应该对邻居们更友好一些”,“应该请他们来家里喝喝茶”[4]327。她和小姑多萝西的相处更是冷淡隔膜,丈夫去世后,她就“再也没有关心过这个亲戚,甚至从不写信”[4]339。埃利斯夫人没有任何朋友或者知己,不管是上街购物还是出门散步,她总是独自行动,甚至在咖啡馆她也是独自一人默默地消磨时光。在她的观念里,这种“你不扰我,我不扰你”[4]314式的孤独是一个有身份的人才配拥有的,是她引以为傲的阶级的象征,乡村式的热情友好早就是“过时”的了[4]327。
时光倒错之后,埃利斯夫人在颠沛流离中再次见到了业已长大成人的女儿,令人惊讶的是,她们彼此都未能认出对方。苏珊一方尚可以母亲早逝为由,可是埃利斯夫人的反应实在称不上合理:
“多么惊人的巧合,”埃利斯夫人微笑着说道,“我也叫埃利斯,我的女儿也叫苏珊,更巧的是你长得好像我已故丈夫的妹妹。”[4]341
撇开时间飞逝二十年这一客观原因暂且不谈,埃利斯夫人的迟钝反应很大程度上源于她对阶级身份的固执。潜意识里,她不愿意承认眼前这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年轻妇人就是自己娇生惯养的苏珊。这对母女不能相认的原因应该归结为她们阶级身份的差异。埃利斯夫人最惧怕的是阶级的沦丧,而苏珊的落魄现状则像一场恐怖电影,“暴露了隐藏已久的恐惧,这种恐惧威胁到了当前的社会身份,宛如梦魇成真一般”[6]20。
二、挑剔的女主人:追求完美的人格障碍者
因为为人孤僻冷漠,社交狭窄的埃利斯夫人拥有大量的时间打理自家住宅。作者在小说的开头这样形容她:
埃利斯夫人总是有条不紊,干净整洁。她讨厌混乱。一切尚未回复的信件、没有支付的账单和翻得乱七八糟的书桌都让她痛恨不已。[4]299
随后小说的展开更让我们对埃利斯夫人的这种“洁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这天恰逢某月一号,正是她“清洁”情绪高涨的日子:所有的床单枕头都要叠放整齐,洁净如新;储藏柜里的水果罐头都要按照日期标签排列整齐;文件格里过期的收据和信封都被扔掉;吸墨纸板里重新装满吸墨纸;新的铅笔削好待用;杂志在边桌上码得整整齐齐;书架上的书绝对要贴着书架外沿排好;花瓶里装满新换的水。她对于“秩序”的要求达到了一种强迫性人格障碍的程度:水果罐头本是为苏珊准备的,然而,当女儿回家享用这些东西时,她又对即将到来的美味感到“失望”,因为它“意味橱柜里有了空位”[4]200。这一举动是典型的“专注于细节、规则、条目、秩序、组织或日程,以致忽略了活动的主要方面”,强迫性人格障碍患者通常“不惜牺牲灵活、宽大和效率,专注于有次序、完美无缺及精神活动,人际关系拘谨”[5]226。患者除了做事要求完美无缺之外,也“不愿将任务委托别人或与别人共同工作,除非他们精确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使”[5]227。作为房子的女主人,埃利斯夫人恨不得事事亲力亲为,她宁愿自己保存橱柜的钥匙,也不愿交给经常使用橱柜的格雷斯。在不得不放手的时候,她也要求格雷斯在细节上精准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准备开饭时必须走进房间请她用餐,不能在门口喊一声就完事;书架上的书必须贴着对齐书架的外沿,不能贴着内沿摆放等等。埃利斯夫人对其他人同样缺乏信任,在她眼中,他们的行为都有不妥的地方:学校的舍监会因健忘疏忽对苏珊的照料;开洗衣车的司机在转弯时开得太快,总有一天会发生事故。
埃利斯夫人对“秩序”强迫性的渴望同样可以归咎于她的中产阶级身份。在埃利斯夫人所处的年代,面向中产阶级读者的杂志不断鼓吹“战争间隔年需要更高标准的家庭管理”[7]116。一个秩序井然的艾尔姆赫斯特街十七号不仅是衡量女主人尽心尽职的标准,更是界定家庭社会地位的标尺。
相比之下,二十年后已经成为出租房的艾尔姆赫斯特街十七号成了一个极其脏乱的地方:“太可怕了,他们把房子搞得一团糟。”[4]309而已为人妇的苏珊家里同样也是“一团乱”,到处都是“吃剩的饭菜”“玩具”和“裁剪的布料”[4]340。下层社会住宅里的混乱和中产家庭里的井井有条构成强烈的对比,彰显着下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不同。因此,自恃身份的埃利斯夫人面对来自较低阶层的女仆、舍监和司机时,自然而然地带有一种优越感。她不断苛求自己、挑剔他人来追求一种有“秩序”的生活。这种举动正是她对于自己阶级身份的捍卫。她害怕的不仅仅是失去有“秩序”的环境,更是混乱环境所代表的阶级沦丧。
三、落魄的流放者:妄想成瘾的人格障碍者
埃利斯夫人的身份焦虑不仅表现为人际关系的疏远和对“秩序”的强迫性渴望,还以一种偏执性人格障碍的形式彰显。偏执性人格障碍是一种“对其他人普遍地不信任与怀疑,将他人的动机理解为恶意”的人格倾向。其鉴定的标准包括:
毫无根据地怀疑他人利用、损害或欺骗自己;总是毫无根据地怀疑他人的忠实性和可靠性;无正当理由便害怕他人会利用信息来恶意地反对自己,因此不乐意信任他人;一些本来是善意的谈论或事件被病人看作含有贬低或威胁的意义;容易感到名声被别人攻击,并马上发怒或回击。[5]200
上述标准描述的无根据的臆想在埃利斯夫人的经历中比比皆是。二十年时光在一瞬间飞逝,埃利斯夫人不再是艾尔姆赫斯特街十七号的主人。当她散步归来发现自己的钥匙打不开房门时,她立刻判断“肯定是上门服务的洗衣工做了什么手脚,损坏了房门”。面对前来应门的陌生男子,她立即认定他是格雷斯的情夫,认为女仆“彻底地欺骗了她”[4]307。面对一群陌生的房客,她怀疑他们是一群“逃出精神病院的疯子”[4]312。甚至连上门的警察都被她视作腐败分子、罪犯的帮凶。不一样的街道、变迁的人事,甚至二十年后的日历牌,这一切都在向她暗示:这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时代。可是埃利斯夫人仍然选择无视这些证据,只是一味地恶意揣测:“他们都在撒谎,所有的一切都是谎言,他们不是警察,只是控制了警察局的房子,有人监视着他们,政府即将被颠覆。”[4]330
二战的炮火洗礼使英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埃利斯夫人熟悉的人事也都经历变迁:街道被毁重建,女子学校改制为男女同校,旧日的亲友已然搬迁,曾经的私宅变成出租房,女儿也成了终日辛勤忙碌的劳动阶层一员。一瞬间,原本衣食无忧的埃利斯夫人失去了家,她引以为傲的中产身份也被击碎,她由一位受人尊敬的夫人沦落为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疯女人”。她对这些变化的麻木漠然俨然是一种无力的抵抗。噩梦因为时空的错乱提前变成了现实,而她根本不愿意,也无力承受这一变化。她只能依靠偏执的妄想在自我与现实之间构筑起一道脆弱的屏障,以求保全自己身为中产阶级的最后一丝尊严。
小说的尾声,埃利斯夫人摆脱了护士的看管,逃到了街上。路人都行色匆匆,无人注意这个狼狈的女人:
她人生中第一次感到如此无助和孤单。她渴望她的房子、她的家,她渴望回到那令人安慰的环境中去,回到她那被残酷打断的正常生活中去。[4]334
最后,沉浸在回忆中的埃利斯夫人再次撞上了那辆使时间错乱的洗衣车,小说在这里戛然而止,关于女主人公到底会被撞身亡还是重回原来的时代,作者并没有交代。但是不管结局如何,有一点却始终不变:时光的流淌和社会的发展都远非个人之力所能阻止。
个人的身份与以性别、阶级和种族为基础的群体身份密切相连。埃利斯夫人的命运也暗示着英国的衰败。两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经济被严重削弱,其在非洲、亚洲、大洋洲的殖民地也纷纷宣布独立。英国在经济、政治上已受制于人,曾经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逐渐走向了瓦解。因此,《瞬间》不仅表达了个人面对历史潮流时的无奈,同时也为衰落的帝国吟唱了一曲最后的挽歌。
[1]Light A.Forever England:Femininity,Literature and Conservatism between the Wars[M].New York:Routledge,1991.
[2]Watson N J.Daphne Du Maurier,Rebecca[M]//The Popular&the Canonical:Debating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Oxford: Routledge,2005:13-56.
[3]Horner A,Zlosnik S.Daphne Du Maurier:Writing,Identity and the Gothic Imagination[M].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98:18.
[4]Du Maurier D.Split Second[M]//Black Water:The Anthology of Fantastic Literature.Toronto:Lester&Orpen Dennys,1983: 299-344.
[5]美国精神科学会.DSM-IV分类与诊断标准[M].庞天鉴,译.西安:杨森科学研究委员会中国分会,2010:200-227.
[6]Wisker G.Don't Look Now!The Compulsions and Revelations of Daphne du Maurier's Horror Writing[J].Jounal of Gender Study,1999(1):19-33.
[7]Lewis J.Women in England,1870—1950:Sexual Divisions and Social Change[M].Brighton:Wheatsheaf Books Ltd,1994:116.
责任编辑:赵青
I106.4
A
1673-0887(2014)02-0040-04
2013-10-08
郭看(1989—),女,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