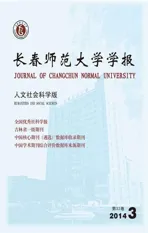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的翻译研究
2014-03-29郝俊杰
郝俊杰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国际商务系,广东 广州 510640)
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的翻译研究
郝俊杰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国际商务系,广东 广州 510640)
新历史主义不仅为翻译在历史认知和文化建构中的意义提供了新的参照,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探讨了新历史主义对翻译研究的渗透和参与。在翻译本体论方面,认为翻译是对历史文本无限阐释的实现途径;在策略论方面,提出厚重翻译是新历史主义厚描理念在翻译领域的策略实践;在批评论方面,指出翻译批评的历史维度和多重视野映射出新历史主义批评观的影响;在翻译史论方面,强调翻译史研究旨在发掘社会能量在翻译文本和社会历史之间的双向流通。
新历史主义;翻译本体论;翻译策略论;翻译史;文化史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于1982年应Genre杂志之约,在文艺复兴论文专辑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启动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之舟。新历史主义学者以文艺复兴时期为批评的历史疆域,以福柯的权力体系为理论话语,以历史文本的当代构建为理论导向,发表了一系列让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其代表人物有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等。这种学术思潮迅速席卷人文研究的各个方面,并在美国“正在成为最新的学术正统”[1]3。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勃兴始于20世纪90年代,伴随文化研究和历史文学的热潮而来,其影响力遍及多种人文学科,在翻译研究中也有所渗透。明确将新历史主义与翻译研究并提、值得注意的文献如下:朱安博把福柯的权力话语体系作为新历史主义和翻译研究的共通渠道,认为后殖民译论的兴起和翻译研究对政治权力的关注为新历史主义提供了介入空间[2];段峰认为,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应包括本体研究、外部研究、译者研究等[3];张景华指出,新历史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历史视角,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疆域,推动了后殖民主义等翻译观的发展,还能为翻译哲学、译者地位等作出新的理论解释[4]。然而,正如格氏所言,新历史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教义。更常见的是翻译研究中融入了新历史主义思想,或采纳了其研究方法,但未明确表述;抑或研究者对自身理论视角的潜在来源习焉不察。新历史主义与翻译研究之间含混的理论结合状态表明二者的交叉研究尚待深入。为此,必须先厘定二者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重叠论域,找出目前的翻译研究在何种程度上呈现出新历史主义话语特征,方能为新历史主义和翻译研究进一步的结合指明道路。本文拟从翻译本体论、策略论、批评观和翻译史研究四个方面探讨新历史主义在翻译研究领域的渗透和实现。
一、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的翻译本体论
翻译本体论旨在寻求翻译“是什么”和“如何是”。张柏然认为,过往翻译研究多着眼于译者、译作和读者,而忽略了翻译本体“形而上”的思考[5]。许钧将对翻译本体论的认知分为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6]。语言学派视翻译为基于共同意义的语言形式转换,强调翻译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文艺学派视翻译为跨越文化藩篱的途径,注重翻译的主观性和创造性。无论是本体论的阙失和迷惘,还是不同学派的各执一词,都说明翻译本体是个复杂多维的研究对象,对它的探究要循序渐进。新历史主义有关历史文本当代解读的理论表述为翻译本体论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新历史主义强调文本是历史的产物,文本蕴含了历史背景中的政治话语、权力博弈、经济关系等。文本蕴含的阐释层面无限丰富,历史文本的现时解读永无止境。新历史主义有关历史文本现时解读的表述,既强调意义的客观性,也兼顾意义的主观性;既关注阐释活动的当下性和局限性,又注重其无限性和延伸性,渴望在历史与文本、文本与文化、历史与文化之间搭建认识的通道。新历史主义反复强调的历史文本的现时解读,从本质来说恰是一种广义的翻译活动。因此,历史文本现时解读所具有的局限性和无限性,也正是翻译的重要属性。作为历史文本无限延伸的阐释链的实现通路,翻译具有局限性、无限性和主体阐释性。
翻译的局限性既包含时间、地域等客观局限,也包含学养、能力等主观局限。在客观局限方面,正如许钧所言,“在于阐释者总是在一定的历史空间中进行。”[6]118翻译者不可能脱离时间、地域的限制。在主观局限方面,翻译者能力、背景、价值观念各有不同,且“个人有限的阐释,只不过是理解循环中的一站,不是萨特所说的凝固的瞬间,也不是凝固的终点。”[6]118翻译的主客观局限性揭示出,翻译是个体基于所在世界与历史的文本对话,是一种历史的相遇。任何翻译文本都是一定历史空间内的文化产物。它必然带有时代的烙印。
翻译的无限性建基于阐释的无限性。新历史主义认为阐释无边境:文艺复兴本是文学史上研究最深入的领域之一,但通过对这一领域的深耕,新历史主义学者发现了过往被忽略的声音和痕迹。翻译是一条无限延伸的阐释链。“历史永远在发展,一个个阐释者有限的追求,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构成连续不断的无限生命历程。”[6]118经典重译现象便是历史文本无限延伸的阐释链的最佳注脚。译者为何要重译经典?相信大部分译者不满于过往译本中的各种局限,而自己能够见他人之未见。由是观之,翻译的无限性恰恰植根于其局限性。译者处于不同的历史时空,其视角受到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知识结构等制约,对于历史文本的认知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译本中所存在的缺陷、误译、错译,便等待着后来人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加以改进。”[6]117翻译的无限性确保了文本生命的延续,“一个文本的生命,既有时间意义上的延续,也有空间意义上的拓展。”[6]124“复译是不可避免的,译文的‘现时化’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6]122认识翻译的无限性,并承认这种无限性的必要性,对加深我们对翻译本体的认知有重要意义。
“任何阐释者,都是带着自己的‘先见’、‘先有’、‘先把握’去进入文本的。”[6]117翻译文本必定有译者的主观因素在内,有多少译者就有多少译本。无论译者如何宣称客观,都无法杜绝主观因素的影响;换个角度看,正是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才使得翻译成为可能:译者必定要调动自身的知识储备和理解能力,才能化原始文本为主体阐释,完成从语言到思维的转换;也一定要调动自身的语言储备和表达能力,方能化主体阐释为翻译文本,实现从思维到语言的跨越。无论是从语言到思维,还是从思维到语言,其主导因素都是主体阐释,翻译文本不可避免地是主体阐释的产物。如果说翻译的主体阐释性在译者层面表现为译者的介入,那么在读者层面它便表现为读者的阐释参与。任何文本要获得意义,都离不开阅读者的主体阐释;也只有在读者的接受中,意义才能实现。人类生活在语言搭设的世界,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借他人之口表自我意图的意义重建活动。在理想的状况下,脱去的是语言的外壳,留下的是思想的本真,关键是,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留下思想的本真?翻译文本中的思想究竟属于原文作者,还是夹带了译者的介入,抑或只是读者的主观再现?意义的澄明之境是否存在,假使它存在,又何以达致?新历史主义揭示出,无论是译者的翻译生产,还是读者的阅读接受,其实现主轴都是主体的阐释,这也决定了主体阐释性是翻译的本质属性之一。
二、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的翻译策略论
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厚描”法肇始于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兹于1973年提出的“厚度描写”概念。格兹认为,文化人类学家的阐释乃是“对他人自身构建之构建”,因此须对阐释的语境作厚重详细的描述[7]。厚重描写要求“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希望在过往被忽略的事物中发现深层规律[8]。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厚描”法正是在文化人类学启示下的方法论突破。格林布拉特明确指出,厚描“使我们已经在做的事情显出意义,将我们的职业技巧作为比我们自己的把握更重要、更关键和更具说明力的东西重新交还我们手里”[1]138。
在“厚描”理念的启发下,美国翻译理论家夸梅·阿皮亚提出了“厚重翻译”的策略,即在翻译正文以外提供大量注释与解析,将译文置于丰富的历史语境之中[9]。其目的是超越语言形式的浅层对照,力求揭示原文社会、历史、文化的多维层面,使译文读者能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厚重翻译所提倡的厚语境化方法,正是基于文本历史性的策略实践。新历史主义强调文本的历史性,认为文本植根于历史,以文化形式蕴涵了社会能量的流动。逆转视角来看,要全面认识文本,对文本历史语境的考察必不可少。厚重翻译也映射出福柯权力体系的影响。作为新历史主义理论话语的福柯权力体系认为,构成历史的正统文本是权力博弈中的胜出者,文本中历史的痕迹已经被抹去,而要还原历史的真实图景,我们唯有转向那些被压抑的声音和文本。与历史厚描相仿,厚重翻译提倡将以往翻译中被忽略的声音纳入翻译中,正是新历史主义在翻译中的策略实践。
厚重翻译提出之后,受到翻译界的广泛关注,其学术意义有三。其一,它是对翻译策略二元论的历史反拨。提及翻译策略,以往无非就是直译、意译或异化、归化。厚重翻译的提出打破了翻译策略的二元论,在形式真值和内容真值之间找出一条调和性道路。其二,它是对翻译浮躁之风的理论警醒。厚重翻译的实现,要求翻译以研究为根据,研究以翻译为目的,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对“那种捕风捉影、浅尝辄止的流行病具有一种天然的免疫力”[10]。其三,它为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提供了新的方法范式。厚重翻译通过丰富的注释,为原始文本的历史定位和翻译文本的意义再生提供了良好支撑,不仅有利于文化产品在不同地域空间的传播,匡正语言沙文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话语扭曲,也有利于文化产品在未来时间视域内的传承,达到文本解码和文化祛魅的历史效果。虽然金无足赤,厚重翻译有其操作层的弊端如译文的冗长化等,但绝不能因此抹杀其积极意义。
三、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的翻译批评观
纵览翻译批评史,翻译批评主要有四种取向。第一种围绕翻译文本的美学属性展开,着眼于“信”与“美”的交锋,“文”与“质”的对抗。第二种针对翻译文本的语言属性进行,以词汇、句法、语义分析为切入点,运用语言学的成果对翻译文本和原始文本进行多维对比分析。第三种聚焦于翻译文本的主体属性,注重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意在揭示文本意义是在主体阐释下的“延异”。第四种注重翻译文本的社会属性,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轮番登场,旨在翻译批评领域中响应社会思潮的涌动。而近20年间,无论是翻译批评对历史维度的追求,还是批评话语的多重视野,都表现出新历史主义批评观的渗透和参与。
脱离了历史,一切批评都无深度可言。文学批评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发现文本之中和文本周边的社会存在。同样,翻译批评也渴望通过历史维度进行深度构建,旨在发现翻译与历史的互证与互动。如果说翻译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翻译文本性是新历史主义翻译批评观的逻辑起点,那么翻译批评中历史维度的追求就是它的实现途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策略认为需要返回历史,把历史当作重要的出发点来理解文化生产、批评概念、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的范畴”[1]3。翻译批评要获得历史维度,同样不能在美学和语言学的批评疆域内画地为牢,而要全面研究翻译文本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和权力关系背景,从社会能量向文本流动的方向分析译者的翻译目的和策略;同时要考察翻译文本对历史的反推和重塑,分析社会能量由翻译文本反流至社会历史的进程。
作为对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双重扬弃,新历史主义既反对形式主义对作者的彻底抛弃和对文本的全面皈依,也不同意解构主义对意义的全面颠覆和对文本的多方质疑。它承继了文化人类学的整体视野,而非“局限于研究文化中某些我们认为是文学的部分”[1]1。新历史主义尤其重视过往被忽略、被压制、被边缘化的声音。这种研究旨趣也反映在翻译批评中。翻译批评同样重视过往批评话语中忽略的成分,以“构建从表面走向深层、从单一走向多元、从静止走向动态的多重视野”[11]。格氏还指出,“新历史主义与20世纪初实证论历史研究的区别,正在于它对于过去几年的理论热持一种开放的态度。”[1]2翻译批评的多重视野也体现在多种研究话语和社会思潮的介入,例如女性主义、历史研究、叙事研究等。从女性主义出发,弗洛托发现,译者倾向于选择推崇女权的文本,但在翻译中会遇到一系列语言问题,例如如何翻译“身体”[12]。从历史视角出发,陈福康指出,林纾“不忠实”的译法并非孤立行为,而是受到晚清把“译笔”和“文笔”相提并论的译评方式影响的结果。[13]从叙事学出发,盛宁在考察《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译本后指出,“中译本中被删节的部分,对于原作来说,非但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相反,正是这些间杂于故事叙述之中的议论和插话,赋予了这部小说以某种‘旧瓶装新酒’的特色”[14]。翻译批评对各种理论话语兼容并蓄,极大拓宽了批评视野。同时,通过批评的理论化和理论的批评化,翻译批评积极参与当下的理论构建。
四、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的翻译史研究
尽管翻译活动历史悠久,但系统的翻译史研究在近几十年才发展起来,这一时间点恰与新历史主义理论崛起的时间相符。翻译史从以往作为被遮蔽的话语空间,到近年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话题,正响应了新历史主义对历史叙事再发现的理论提倡。如果说翻译史本身的崛起便源于新历史主义的影响投射,那么其研究方法则进一步实践了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话语构建观。皮姆在《翻译史研究方法》中提出了四项研究原则:翻译史应解答翻译的社会起因问题;翻译史的中心研究对象是译者;翻译史应围绕译者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展开;翻译史研究要着眼当前[15]。这种对文本起因和历史建构高度重视的理论渊源,正是新历史主义反复强调的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
新历史主义提倡发现文本周围和文本之中的社会存在。它认为,权力话语的影响导致了历史认知的断裂性和片面性,因而主张“以今人之眼观古人之事而知历史之图景,在历史文本中解读意识形态的文化踪迹并揭示权力与颠覆之类文化动因之间的辩证关系。”[16]152这种研究旨趣也投射到翻译史的研究中。从新历史主义历史与文本互动观出发,翻译史研究不仅考虑到翻译文本的历史性,也注意到历史的翻译文本性,即翻译文本一旦产生,便会在历史书写中留下烙印,影响历史进程。翻译史研究在于发现翻译文本的产生、接受与批评语境,并以之为基础,“结合历史背景、理论方法、政治参与、作品分析,去解释作品与社会相互推动的过程。”[17]对马礼逊《圣经》翻译最新的研究成果称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由翻译触发的社会运动”,便是发现翻译与历史互动关系的突出例证。[18]概言之,翻译史研究旨在发掘社会能量在翻译文本和社会历史之间的双向流通。
五、结语
甫一诞生,翻译学科便有跨领域的特质。正是在与文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的交叉博弈中,翻译理论家们才挣脱语言学的束缚,构建了自身的理论话语。终获独立地位的翻译学并未从此自我设限,而是更加注重吸纳各门学科派系、各种理论话语的有益影响。翻译研究的疆域扩容和学术增值依赖的正是其开放性特质。20世纪后半叶,伴随反本质主义的兴起,各种“后学”你方唱罢我登场,占据了历史舞台的显要位置。作为“后学”中引人瞩目的一种理论建树,新历史主义日益渗透和影响着翻译研究,促进了翻译本体论的认知、翻译策略论的深入、翻译批评观的发展以及翻译史研究的兴起。本文探讨了新历史主义与翻译研究的重叠论域。在本体论方面,认为翻译是对历史文本无限阐释的实现途径;在策略论方面,提出深度翻译是新历史主义厚描理念在翻译领域的策略实践;在批评观方面,指出翻译批评的历史维度和多重视野映射出新历史主义批评观的影响;在翻译史研究方面,强调翻译史研究旨在发掘社会能量在翻译文本和社会历史之间的双向流通。
[1]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朱安博.翻译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话语[J].中国翻译,2005(2):10-13.
[3]段峰.论翻译的文化诗学研究[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181-187.
[4]张景华.新历史主义与翻译研究[J].当代文坛,2008(4):59-61.
[5]张柏然.翻译本体论的断想[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4):46-49.
[6]许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7]Geertz, C.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M].New York: Basic Books,1973:9.
[8]段峰.深度描写、新历史主义及深度翻译——文化人类学视阈中的翻译研究[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6(2):91.
[9]Appiah, K. A. Thick Translation[C]∥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awrence Venuti ed.. Routeledge, 2000: 427.
[10]郭大为.重估费希特的价值——《费希特著作选集》编译告成[J].哲学动态,2000(10):29.
[11]刘云虹.从林纾、鲁迅的翻译看翻译批评的多重视野[J].外语教学,2010(6):104.
[12]Flotow, L. V.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on in the ‘Era of Feminism’[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14-17.
[13]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15.
[14]盛宁.思辨的愉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5-6.
[15]Pym, A.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M].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ers,1998: xi-x.
[16]王进.从社会批判到文化祛魅:文化唯物论视角下的文化诗学批评[J].云南社会科学,2009(2).
[17]廖炳惠.新历史观与莎士比亚研究[M]∥形式与意识形态.台北:联经,1990:221.
[18]王悦晨.一场由翻译触发的社会运动:从马礼逊的圣经翻译到太平天国[J].中国翻译, 2013(3):31-38.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istoricism
HAO Jun-ji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epartment, Guangdong Teachers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Art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0, China)
New historicism sheds light on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erme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new historicism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proposes that in terms of translation ontology, translation is the path of infinit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texts; “thick translation” is the strategic application of “thick description”;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and holistic view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underlies the influence of New Historicism; translation history studies aim to find the mutual flow of social power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history.
New Historicism; translation ontology;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al history
2014-01-02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3YJA752021)。
郝俊杰(1982- ),河南清丰人,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国际商务系讲师,硕士,从事翻译与语言学研究。
H059
A
2095-7602(2014)03-006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