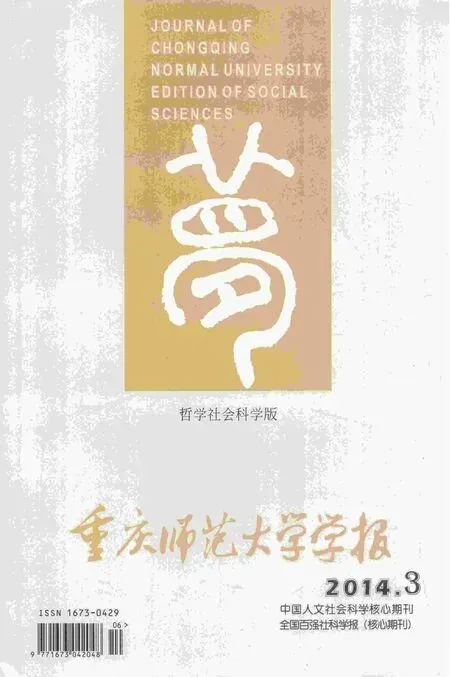学界关于鲍德里亚方法论批判的研究
2014-03-29顾建红
顾建红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210098;淮阴师范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淮安223001)
张一兵教授在《反鲍德里亚》中认为鲍德里亚“是我们迄今为止见识过的,马克思将要面对的最为深刻,因而也是最危险的理论对手。他在《生产之镜》中对马克思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攻击和批判无疑也是当代学术史上我们看到的最深刻、最全面,然而却也是最致命的批判”[1](194-195)。“如果按照黑格尔的话来说,理论只能从内部的自我矛盾中攻破,那么,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就真是一枚从内部解构和祛序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重磅炸弹。”[1](450)王南湜教授在《马克思会如何回应鲍德里亚的批判?——对于鲍德里亚的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一文中表示了同样看法。
正因为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判和解构是如此深刻,本文拟从方法论角度来评析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判。之所以选择这一角度,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任何哲学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到方法论上,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判最为根本的就是方法论批判。第二,关于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方法论的批判,学界反对与赞成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双方的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是南开大学的王南湜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慧平研究员。王南湜在上述文章中对鲍德里亚批判马克思方法论持明确的反对态度,认为他的批判误解了马克思。陈慧平则在《鲍德里亚的辩证法及其人文意义》中认为学界对鲍德里亚批判马克思的方法论所做的批判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理解鲍德里亚的方法论,更不可能正确理解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方法论所做的批判。为此,本文想就此话题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方法论所做的批判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理论最主要的批判集中在其代表性著作《生产之境》中。在这部著作中,“他直接准确地定向爆破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内部最重要的支撑性结构——物质生产基始论和历史现象学批判逻辑。”[1](670)而鲍德里亚对马克思这一批判的完成与他对马克思方法论的批判密切相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建构自己理论大厦的方法论基石,鲍德里亚要完成对马克思理论的全面攻击是绝不会放过这一方法论基础的。大体而言,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方法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方法论带有很明显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心论的色彩,是“‘批判的’帝国主义”方法论。
鲍德里亚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生产方式、劳动力——正是通过这些概念,马克思主义理论打破了资产阶级思想中抽象的普遍概念(自然和进步、人与理性、形式逻辑、劳动、交换等等)。然而,马克思主义又以‘批判的’的帝国主义将这些概念普遍化了,就像其他理论一样。”[2](29)在鲍德里亚看来,尽管马克思的方法论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姿态出现的,但却是站在西方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前现代和非西方世界的,带有明显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心论的色彩,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西方文化是第一个批判地反观自身的文化(这开始于18世纪)。但这种危机的结果是西方文化的自我关照,并将自己理解为一种普遍性的文化,这样,所有其他文化都被放进了博物馆中,成为西方文化想象中的遗迹。”[2](74)马克思的理论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中心论色彩,因而不能准确地理解前工业社会和其他的社会形式。“所有这些事实说明了一点:(马克思)以劳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来说明前工业组织,在我们看来是不合适的,对封建的传统的组织也同样如此。”[2](86)在他看来,无论意识到与否,历史都是研究者眼中之物,人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看待他物的,真正的历史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也不能例外,基于这一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不能成立的。
(二)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在方法论视野上没有走出西方启蒙运动以掌控自然为目的的人类中心论的思维模式。
鲍德里亚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无力和无为的,它对自然的描述在理论上没有任何重要性和创造性。这主要表现为历史唯物主义在以下两个方向上未能实现去自然化:第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产品的最终有用性在于满足需要”;第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自然的最终有用性在于劳动对它的改造”。[2](25)这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依然沿袭了传统的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即将自然作为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性存在。这种二元对立是西方基督教的传统,在“启蒙的道德哲学”[2](39)中达到了它的理论最高峰,而历史唯物主义在对自然的描述中没有提供任何新的理论质点,依然沿袭传统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思维模式。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但没能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局限,而是达到了它的顶峰。“马克思把这一概念转译成物质生产的逻辑和生产方式的历史辩证法。但生产方式差异的最终决定性力量——生产力,不再是不可动摇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将经济学的理性方式普遍化了,并作为人类生成的一般模式推广到整个人类的历史中。他以宏大的模拟模式来描述整个人类历史。他用以反对资本秩序的分析工具,正是资本精心阐述的最为巧妙的意识形态幻象。”[2](14)
(三)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方法论在理论根源上犯了黑格尔主义的错误。
在鲍德里亚看来,虽然马克思力求超越资产阶级的眼界而极力摆脱资产阶级文化中心论,但始终未果。这主要是因为他在理论根源上犯了黑格尔主义的错误。“在所有这些背后,存在着两个假设:一是,历史的发展过程在所有的早期社会就已经存在(生产方式、矛盾、辩证法),但人们没有生产出这些概念,因此,也就无法超越这些社会。二是,开始意识到这个过程的时候(批判概念的生产同资本主义形态的条件有关),也是革命的关键阶段。所有这些都是彻底的黑格尔主义的观点。”[2](97)显然,鲍德里亚所说的马克思所犯的黑格尔主义的“错误”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的理论架构在方法论上体现了黑格尔理论中所强调的“绝对精神”先行的原则,即一切理论,包括概念、原理、规律等都是人的理性的一种预设,外部世界在这种预设中存在和发展。第二,马克思的理论架构的错误是由其所推崇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所决定的。因为,只有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历史才可能是一个连续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概念才可能被超历史化,进而使文化中心论成为可能。“认为一个概念不仅是一个解释的前提,而且是对普遍运动的解释,这种观点依赖于纯粹形而上学。马克思的概念也没有逃出这个陷阱。因此,从逻辑上看,历史的概念必须被理解为历史的,它必须回到自身,这仅仅说明了这样的语境,即通过否定自身而将自身生产出来。相反,在马克思主义中,历史被超历史化了,通过放大自己而普遍化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辩证法必须辩证地被超越并且废除自身。”[2](29-30)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正是马克思文化中心论这一“‘批判的’的帝国主义”方法论产生的根源,它在根本上推动着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概念的超历史化。
二、学界对鲍德里亚批判马克思的方法论所做的回应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方法论的批判和解构是从攻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开始的,而这关系到马克思理论大厦的基石,所以学界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大体而言,这一回应有两种基本的观点:一是认为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方法论的批判是一种误判;二是认为学界对鲍德里亚批判马克思的方法论所做的批判实质上建立在对鲍德里亚所持方法论的误解这一基础之上。这两种观点具体展开如下:
(一)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方法论的批判是一种误判。
持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是南开大学的王南湜教授。王南湜认为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方法论的批判是一种误判,这主要表现为鲍德里亚在方法论上把马克思误看成是黑格尔主义者。他认为:“鲍德里亚这里对马克思方法论的最严厉的指责是马克思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所谓对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的质疑,事实上是质疑他所认为的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辩证法。”[3]显然,王南湜对鲍德里亚的反驳是从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是黑格尔主义者这一观点开始的。为此,王南湜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区别,并坚决维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认为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方法论的批判是犯了纯客观主义的错误。他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这一点使马克思与黑格尔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一方法论唯物主义,必然导出的结论就是思维主体不可能离开他的社会环境去认识对象,而只能自觉地从其所处的环境出发去进行认识。如果说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认识可以比拟为对人体的解剖的话,那么,对于古代社会的认识就只能通过这一解剖来透视,而不可能有其他超越这一处境的纯客观的认识方法。鲍德里亚认为可以跨越现代社会这一认识的中介,而直接对古代社会进行认识,纯属自欺欺人。”[3]在他看来,鲍德里亚之所以提出这一批评,是因为鲍德里亚认为“人体”与“猴体”不具有同构性,故而要认识“猴体”则必需要从“猴体”本身出发,即从“猴体”所代表事物的具体历史环境出发去理解事物,而不应从不同于“猴体”的“人体”出发,人是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历史环境中去认识事物的。所以,王南湜认为鲍德里亚在这一点上犯了纯客观主义的错误。
对王南湜的这一说法,本人不太认同。原因如下:第一,固然鲍德里亚在批评马克思的过程中显露了其思维逻辑的纯客观主义的意味,但这只是一个浅层次的意思显现,而不是问题的实质。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回到过去,不可能脱离当下而置身于过去与未来,作为当代思想大师的鲍德里亚不可能不知道这样一个浅显的常识。第二,鲍德里亚批评马克思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这一说法,其实质是批判其逻辑上的线性思维模式,即反对单纯地根据理性逻辑而主观推断事物的内在联系,而不是浅显地纠缠于客观主义的可能性问题。“当我们从生物解剖领域过渡到人类的象征和历史社会领域时,是什么保证着这两个领域的图式具有同一性?没有什么比下面这点更确切了,即成人只能从成人的角度来理解孩子。无论如何,在这种连续性的假设中,起作用的都是实证主义的线性分析方法,它号称是精确科学的方法。如果人们不承认这一假设,并保持着象征和意义的特殊性,那么,马克思就包含对断裂的误解,这种断裂比阿尔都塞所能看到的更为深刻。”[4]因此,王南湜从鲍德里亚批评马克思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这一说法就认定鲍德里亚犯了纯客观主义错误,这一论断是有待商榷的。
在认定鲍德里亚在方法论上犯了纯客观主义的错误之后,王楠湜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在方法论上有其理论的自觉性,即承认人的思维的有限性。也就是说,在认识论问题上,马克思认为只能如此认识并不代表这是唯一的真理性认识。所以,王楠湜认为马克思在方法论上不是一个理性思维至上的黑格尔主义者而“更接近于承认人的有限性的康德。如果我们正确地把握了马克思辩证法中的康德元素,而不再站在黑格尔主义的立场上,就能够对鲍德里亚进行更有力的批判。”[3]
在笔者看来,康德承认人的有限性是对人类未知的彼岸世界的一种沉默的表达,他所预设的理论前提是此岸与彼岸世界的存在以及隔离。人类理性所能理解和把握的只有也只能是此岸世界,对于超乎人的理性的彼岸世界只能保持沉默。而且,对于康德而言,存在于此岸世界的理性也只是一种规则论意义上的理性,他与马克思的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人的理性有着实质性的差别。“在自由的个人主义的传统中,最彻底否定任何诉诸人性或人的社会环境者的乃是康德,因为那些必须接受的正义规则,乃是那些适用于所有理性存在的规则,进而在他那里,社会理论与界定正义规则的问题毫无关联。罗尔斯的自由个人主义也是如此,他与康德一样,只有一个理性的理论而没有一个人性的理论。”[4]马克思虽然也认识到了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但他的这种理性的有限性与康德的建立在两个世界基础之上的人的理性的有限性是不同的。康德的理性有限性更多的是强调一种对未知世界的敬畏,马克思的理性有限性则更多的是指,由于受时代条件的局限,人的理性有其无法超越的历史限度。换句话说,在对理性的有限性的理解上,康德是“不可”,而马克思是“不能”,两者有着本质性的差异。
(二)学界对鲍德里亚批判马克思的方法论所做的批判实质上是建立在对鲍德里亚方法论的误解这一基础之上的。
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陈慧平。陈慧平在《鲍德里亚的辩证法及其人文意义》一文中认为,学界对鲍德里亚方法论的批判不是因为鲍德里亚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的方法论,而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地理解鲍德里亚的方法论,没能正确地理解鲍德里亚的系统辩证法。在她看来,鲍德里亚的系统辩证法是更为深刻和彻底的辩证法,因为“鲍德里亚的辩证法是建立在突破了启蒙时期的人文遗产所建构起来的时空框架之上的。他的辩证法在时空层次上远远超出了牛顿的时空观,也超越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而与新物理学中的时空观不谋而合,从而使思想跨越到一个更大的时空参照系。因而,他能在一个制高点上不妥协地批判一切可批判的事物,包括人文科学共同体约定俗成的一切”[5]。正因为如此,利奥塔指出,“鲍德里亚在拟像、仿真等新名词下建立的符号理论绝非唯心主义和理论恐怖主义,而是对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时间性模式变化的反思。”[6](34-35)
陈慧平认为,在鲍德里亚看来,传统辩证法已经被肤浅化和误用了,它被敷上了浓厚的人文主义情怀,这主要表现为,“在辩证法中有一种乡愁(nostalgia),例如在本雅明和阿多诺的作品中。最精致的辩证法往往会在乡愁中终结。与此相反,也是更深刻的,在系统中有一种忧郁(melancholy),会不可救药、无可辩驳地通往辩证法,这种忧郁通过某种具有讽刺意味的透明的方式,在今天已经占据主流地位。”[7](4)鲍德里亚这里提及的辩证法正是他所批判的目的论式的封闭辩证法,也是具有浓厚人文主义情怀的思想家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表露出来的一种辩证法情形。不可否认,在开放的环境中,人总会呈现出一些不完美的生存状况,因此人们常会怀有一种忧郁的情绪,而这种忧郁的情绪往往会弥漫于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进而腐蚀辩证法。鲍德里亚认为人的这种忧郁的乡愁情节会使辩证法丧失其固有的客观的精神领地,它最终会终结辩证法。因为乡愁会驱使人去寻求理想的生存状况或稳定的精神家园,而当辩证法被用于成就人的乡愁情结时,也就意味着它在时间维度上被封闭起来,从而走向形而上学。系统辩证法就是要纠正传统辩证法的这种错误倾向,重申辩证法拒绝停留、永恒运动的品质。所以,鲍德里亚拒绝“以人为本”的目的论,认为没有永恒的价值,价值只是系统中的流动因子。也正因为如此,在鲍德里亚的系统辩证法中,任何对立都是虚假的,真实存在的只是相互依赖的各种关系项在虚实相间中不断运动的过程,而关系项本身没有独立的意义,也不会永恒存在,它们产生于运动,又充实了运动。故而,“鲍德里亚所论述的任何事物,只有放在系统辩证法的运动中来考察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如果只抓住其中的某一项,如用符号理论来解读鲍德里亚,恐怕只能得出盲人摸象般的结论,因为符号作为‘所指’并不是从事物(能指)中抽象出来的象征、虚拟的独立存在物,在鲍德里亚那里,变化、运动是绝对的,符号、象征交换等都是运动的必要中介,它们是系统辩证法的产物和表现形式。”[5]
当我们解开鲍德里亚系统辩证法的真实面目时,那种难以名状的虚无感会久久盘踞于每个人的心头。万物流逝,无物永存,人也只是时间隧道中的匆匆过客,死亡与虚无是人类的最终结局,人文情怀所关注的永恒与美好只是一种幻象,那么,执着有何意义?至此,笔者能深深体会到张一兵面对鲍德里亚文本所产生的那种难以释怀的愤怒,也能深刻理解王南湜极力维护马克思方法论立场的那份执着的情怀。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许会产生出这样的思绪,即鲍德里亚批判马克思没能突破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局限这一论断固然值得商榷,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人文情结在鲍德里亚的系统辩证法中却也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理论只不过是辩证法中的“乡愁情结”而已。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方法论的批判呢?
三、我们应以历史发展的眼界和境界去看待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方法论的批判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一方法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在鲍德里亚的系统辩证法中却变成了虚无。这说明这两个体系所遵循的价值标准是不同的,也可以说两者的哲学眼界和境界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方法论的批判?愤怒是无力的表现,对待理论问题还是要回到理论本身。具体而言,对待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方法论的批判还是应该放在理论产生的宏观历史背景中去看待和理解。
(一)立足于传统哲学背景去看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方法论的批判。
鲍德里亚建立在系统辩证法基础上的思想体系固然切中了当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要害,但其思想理论中所显现出来的尼采式虚无主义的哲学根源也是显而易见的。从西方哲学发展的脉络来看,鲍德里亚在价值理念上秉承了尼采的思想。鲍德里亚自述:“我是尼采的绝对信徒。我很早就阅读了他六种版本的作品。我甚至把尼采的文章作为德语写作和口语考试的材料……尼采对我来说不是外在的参考资料,而是与生俱来的思想胎记。”[8](1)在哲学方法论这一层面,鲍德里亚也继承和发挥了尼采的视觉主义传统。在《生产之镜》中,鲍德里亚这样表达自己的方法论立场:“一个概念不只是个解释的假设,而是一个普遍运动的翻译,依赖于纯粹的形而上学。”[2](71)这就说,概念只是我们基于一种视角来观察世界时的言说可能性,虽然它更多地强调自己是对现实本身的唯一再现。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也没有逃出这个陷阱。鲍德里亚的这一方法论基础正是奠基于尼采的视角主义。而尼采主义的观点正是要解构最坚固的概念大厦的想像普遍性,并保存着这些概念的相对性和症候性。简言之,它是要揭穿意识形态的面具。无论是尼采还是鲍德里亚,之所以坚持这种基本的理论建构,主要是因为他们对真实的蔑视,借用张一兵的话来说:“因为在他那里‘真实’的确已经死亡了。”[1](29)
因此,对于如何看待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方法论的批判,不能仅仅局限于两者之间的争论,而应站在整个西方哲学发展的宏观视野上去解读这一问题。这样,鲍德里亚的论点也许就不会诡异得让人愤怒不已。即使其著作中显现出来的对人类未来的悲观情结让人难以释怀,但如果世界并未因尼采的思想而终结,那么鲍德里亚的思想体系也不会对人类生活产生实质性的冲击。因为,鲍德里亚的思想充其量不过是尼采后现代哲学的一种发展和创新而已。鲍德里亚以虚无来批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符号来虚化和抽象现实,以终结和死亡来消解人类的未来,纵然有理论上的自洽性,却缺少了现实生活的鲜活性和实在性。而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理论所具有的那份执着的生命激情和实在感,是鲍德里亚所难以企及的。故而,纵然鲍德里亚立足于后现代哲学的思想体系是如此完美,终究难以摆脱其唯心主义情绪化的嫌疑。
(二)立足于后现代视野去看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方法论的批判。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方法论的批判也是典型的后现代式的批判。对于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方法论的这一批判,我们还应该从后现代的视角去审视。后现代思潮作为现代性的一种伴生现象,其实质是对现代性的审视和反思。随着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它所引发的极为强势的发展模式席卷了全球。在这一发展模式的驱使下,可供人类选择的生存模式变得极为有限。现代性发展模式的缺陷及其所携带的自身不可治愈的病症,引发了对这一发展模式的反思与反抗,这就是后现代思潮。鲍德里亚的思维模式正是后现代思潮的一种典型表现。
故而,当我们把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判和解构放在后现代语境中去解读时,就更能理解其言说的意向了。后现代作为对现代性本身的批判,其切入点更多的是对主流和强势的抗议,它是以解构主流话语和主导价值为目标的。在内容上,它积极强调对差异与弱势的关注,积极强调被现代性所忽视和遗忘掉的生活的细节;在格调上,它以解构传统和权威,反对宏大叙事为主要特征;在话语体系上,它以极其凌厉的进攻姿态为主要表达方式。正是在后现代思潮的激烈批判之下,现代性过于粗线条化所掩盖了的生活的细节得以更好的呈现,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也得到了更真实的彰显。就此而言,后现代思潮正是以反向行走的方式完成了对现代性缺失的弥补。作为后现代思想家的卓越代表,鲍德里亚的思想极为有力地彰显了后现代思潮的重要价值。在此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方法论的解构会显得如此冰冷。其实,这正是后现代批判话语体系的固有方式。至此,对置身于后现代背景之下的鲍德里亚,我们有了更为真实的认识。
马克思和鲍德里亚作为两位思想巨人,其自身具有的独特的理论魅力对后人而言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因此而对其产生情感上的偏爱,自然无可厚非。但情感的喜好不能替代客观的学术评价。如何看待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方法论的批判,客观、公正是我们应该坚守的基本态度。对于鲍德里亚方法论的客观评价,需要坚持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公正、客观地看待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方法论的批判。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待于进一步完善。
[1] 张一兵.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深化的祛序[M].商务印书馆,2009.
[2]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3] 王南湜.马克思会如何回应鲍德里亚的批判?——对于鲍德里亚的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A].南京大学驳鲍德里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 邓正来.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研究[J].浙江学刊,2002,(4).
[5] 陈慧平.鲍德里亚的辩证法及其人文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4).
[6]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Inhuman[M].Polity Press,1991.
[7] Jean Baudrillard.Cool Memories[M].Verso,1990.
[8] Jean Baudrillard.Fragment[M].Routledge,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