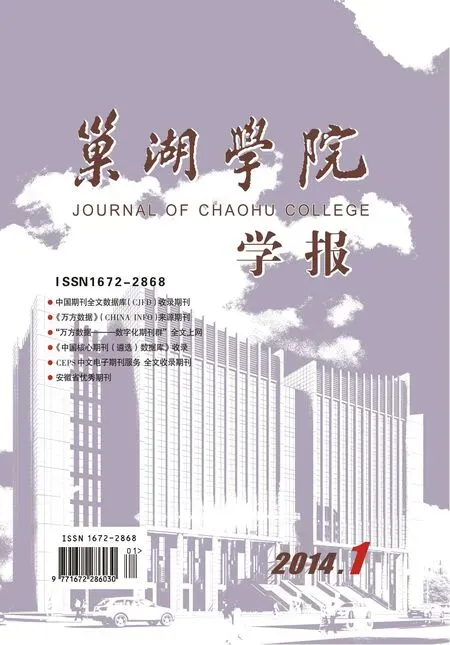朱元璋开创“百年廉政”透视
2014-03-28周怀宇
周怀宇
(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039)
朱元璋(1328~1398年),出身安徽濠州(今安徽凤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候讨饭放牛,饱受流浪飘泊之苦。淮河之滨,天灾连年,讨饭无门,朱元璋被迫揭竿而起,会合无数穷苦兄弟,武装推翻腐败的元王朝,自己当了皇帝,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帝王之路。他执政之后,怀着“救民”水火的政治情感,减轻赋役,建章立制,兴廉反贪,推行惠及民生的廉政,严厉打击腐败分子,创建了清明的廉政局面。朱元璋死后,其廉政路线和局面延续了好几代皇帝,“百余年”[1],而后廉政不幸退色,夭折,令人叹息。透视这一历史现象,有无穷的启示,也有无尽的哀叹!
1 立廉养民
朱元璋亲历元末乱世,深刻认识“丧乱之民思治安,犹饥渴之望饮食。”[2]他谘询朝廷第一顾问大臣刘基:“天下次第已平,思所以修养生息之道,如之何可行?”
刘基回答说:“恤民之道,在于宽仁”。
朱元璋不满意刘基笼统的大道理,指出:“不施实恵,而概言寛仁,亦无益耳!”他从实际出发,自问自答:“以朕观之,宽民必当阜民之财,息民之力。”[3]在他看来,为民谋“实惠”最重要。为此,他提出了“节用”、“省役”、“教化”、“禁贪”四件实事。
朱元璋简明扼要解释了这四件实事的缘由,认为:“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无以遂其生。”[4]这次君臣之间关于“休养生息”的讨论,逐渐形成了“节用”、“省役”、“教化”、“禁贪”为主要构成的廉政路线,朱元璋的廉政思想与实践,沿着这条路线展开。
朱元璋廉政路线的着力点在“宽民”,在“息民之力”。朱元璋常回忆父母吃草渡日的时光,说:“皇考皇妣凶年艰食,取草之可茹者,杂米以炊。艰难困苦,何敢忘!”[5]朱元璋25岁参加农民军,汇合徐达等24人南略定远(今安徽定远县),拉起了一支上万人的武装队伍。他带兵之日,即开始廉政,军纪严肃,禁止劫掠妄杀,怀着“拨乱救民”的情怀,[6]立志“为民除害”。农民军所到之处,“救民涂炭,除暴去苛,纵还妇女,不贪玉帛”,[7]号令严明,赢得了百姓的拥护,1368年结束了元朝的统治,削平群雄,建立了明王朝。
朱元璋登上君位,即明确了自己的使命,他说:“天地生财以养民,故为君者,当以养民为务。”[8]为了履行这一使命,他确立了一个信念,要成为一名“好德”、“好廉”的君主,力戒“好功”、“好财”。他认为君主“好功则贪名者进,好财则言利者进”,鲜明提出:“好功不如好德,好财不如好廉。 ”[9]朱元璋“好德”、“好廉”的信念,支配了执政的思想,成为最初实施廉政的思想基础,直到他71岁驾崩,这一思想贯通他31年执政生涯,矢志不渝,史称“洪武之治”。
历史上,“洪武之治”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并称,属于中国历史上的三大“治世”。考察“洪武之治”,其最精华的成分,即是实施廉政,切实在“廉政”四大构成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自始至终,惠及民生,“养民”、“惠民”的旗帜十分鲜明。
2 节用省役
“节用”和“省役”是朱元璋廉政构成中的两个重要内容,二者互相联系。朱元璋认为国家节用,官府减少开支,就可以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他分析了“节用”和“省役”的内在联系,说:“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撙节用度,自有余饶。减省徭役,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10]
为此,朱元璋在政治实践中,着力把握“撙节用度”和“减省徭役”两个环节,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促进男耕女织,发展生产,提速社会经济发展。
2.1 “抑奢侈,弘俭约”
朱元璋检查国库,看到丰富的储藏,慨然对群臣说:“此皆民力所供,蓄积为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茍奢侈妄费,取一己之娱,殚耳目之乐,是以天下之积为一己之奉也。今天下已平,国家无事,封赏之外,正宜俭约,以省浮费。”[11]他又勉励群臣说:“淡泊可以养志,俭素可以养徳,纵欲败度,奢侈移性。”[12]
朱元璋从自身做起,自己居家克勤克俭,出门轻车简从。江西地方官贡献一张华丽的镂金床,是剿灭陈友谅缴获的战利品。朱元璋拒绝说:“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孟昶是后蜀的君主,奢侈亡国。朱元璋引为铜镜,告戒百官:“既富岂可骄乎!既贵岂可侈乎!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乎?处富贵者正当抑奢侈,弘俭约。”[13]
朱元璋下令:“宫室器用,一从朴素,饮食衣服,皆有常供。唯恐过奢伤民害财。”[14]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从自身衣食住行小事着手,做出勤俭朴素的示范。先改革皇帝新衣,“乌纱折角向上巾,盘领窄袖,袍束带间用金、琥珀、透犀。”进而实行官服简约。[15]朱元璋平日生活,“节于自奉,食不用乐,罢四方异味之贡。非宴群臣,不特设盛馔。功业益崇,益尚俭朴。”朱元璋严于律己,风行草偃,从中央到地方,勤俭节约之风大长。
方克勤,是地方清廉官员的代表。他赴任济宁知府,关注养民、恤民,恢复和发展本地生产,“视事三年,户口增数倍,一郡饶足”,济宁府州县,“民有积粟,野无饿殍;鸡犬牛羊,散被郊垧(原野),富庶充实。”方克勤“自奉简素,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两次)肉食。”吏治考核,评为“六府之最”。洪武八年春,方克勤入朝,朱元璋赐宴表彰,称其“善治民”。[16]
2.2 “宽赋”“养民”“富民”
“省役”的核心意义,即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这是朱元璋推行廉政惠及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朱元璋执政伊始,即派遣周铸率领164人往浙西考察,主要任务是核实田亩。朱元璋对中书省臣说,“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今遣周铸等往诸府县核实田亩,定其赋税。”[17]朱元璋通过核实田亩,制定赋税额度,轻徭薄赋。
遇到灾荒年月,及时下令免收赋税。洪武十一年二月,朱元璋对中书省臣说:“人君视天下犹一家。一家之内,一人不安,则事为之废。天下之广,尺土不宁,则君为之忧。近者雷州府海康、遂溪二县田地为潮水所渍,斥卤不收,租税从何而出?其令有司核实免之。”[18]洪武十三年,“苏、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给,皆为重租所困”,朱元璋下令户部,苏、松、嘉、湖“宜悉减之”。
朱元璋在“养民”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富民”的理论,认为:“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19]又云:“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20]这一理论不仅丰富了廉政思想,也推进了大力发展经济的社会实践。洪武时期(1368—1398),移民屯田,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奖励农桑,降低商税,减免赋役,务求富民实效。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户数10652870,人口60545812,土地8507622顷,超过了以前各个朝代。就在这年,米麦两项田粮达3000多万石,钱钞达45000锭,绢达288000多匹,[21]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这正是洪武时期廉政路线下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增强的成就。
3 教化官吏
推行廉政,必需让全体官吏接受廉政理念,树立执政的廉政观念。朱元璋采取各种形式宣传教化,推行“廉政”思想。
3.1 谆谆告诫
朱元璋采用大会教育,君臣谈话等各种方式,向百官宣喻自己的廉政思想,期望群臣树立廉政为官的理念。
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登基不久,召集地方府、州、县官员进京,在朝觐大会上告诫大家:“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勉励各级官吏“惟廉者能约己而爱人,贪者必朘(音juān,义,剥削 )人以肥己。”[22]郑重要求官吏廉洁自律,成为洪武十七帝“廉者”,不要做“贪者”,要“约己”,不要“肥己”,尤其不能够雁过拔毛。
洪武二年,朱元璋对群臣说:“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他提醒百官:“守己廉而奉法公者,行如坦途,从容自适。”相反,“贪贿罹法者,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23]
凡新任官员,朱元璋常有一番教诲。翰林院两名新官员,侍读编修张信,侍讲戴彝,朱元璋勉励他们说:你们虽然是文职,是“编修”和“侍讲”,“然旦夕在朕左右,凡国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当知无不言。”[24]勉励他们关心民瘼,为廉政效力。
凡新任地方官员如“守令”者,朱元璋尤其重视,常常召见谈话,教诲道:“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养民者,守令也。”[25]希望他们廉正、恤民。他亲手编订《诸司职掌》、《责任条例》、《到任须知》等文件,规定各级官员职责、责任和禁令。刻板印刷《责任条例》,张贴宣传,规范官吏职守。洪武末年,这些条例和谈话的原则融入了官吏考核制度。
朱元璋不仅教育官吏,也向百姓宣喻廉政思想。他第一次修订洪武法令,即诏谕全国百姓,说:“近朕为尔等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尔等当循分守法,能守法则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贫,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亲族,周给贫乏,逊顺乡里,如此则为良民。若效昔之所为,非良民矣。”百姓廉政觉悟提高了,有利于监督官吏。
3.2 时刻警示
朱元璋不仅谆谆告诫百官,也时刻警示自己。他向顾问大臣宋濂说:“自古圣哲之君,知天下之难保也,故远声色,去奢靡,以图天下之安。”[26]朱元璋一生基本上“远声色,去奢靡”而自律。他采取各种方式,警示自己,教育百官。例如:
谯楼报更。登基不久,他让谯楼的值班官员五更报时高唱曹子建编的“谯楼三弄”:“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成更难,难也难!”勉励百官勤于政事,君臣齐心协力治理国家。
建置“申明亭”。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建置“申明亭”,[27]作为读法、明理、彰善抑恶、剖决争讼事件、辅弼刑治之所。命令刑部记录在案的官员罪状,书于申明亭内,公示众人,晓谕百姓。
张榜家门。凡官吏徇私,初犯者,即书其过错,张榜贴其居家门侧,令其自省;如再犯,便重罚。
百官观斩。每次诛杀贪官污吏,行刑前,规定刑部印发罪状,张贴各级衙门、市井;传令百官聚集刑场观斩。
3.3 颁发文《诰》
选编重要文件,颁发官员,提高官员的廉政意识,这是朱元璋执政的一个重要作为,其目的是把全体官员的思想统一到廉政的轨道上来。
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1382—1387),朱元璋效法周公告诫天下臣民,编辑《大诰》,颁发百官。继而又颁发《大诰续编》、《大诰三编》,陆续印发全体官员和天下百姓。
朱元璋宣喻说:“朕制《大诰》三编,颁示天下,让官者知所监戒,百姓有所持循。若能遵守,不至为非。其令民间子弟扵农隙之时,讲读之。”[28]这些文件,不仅传递了朱元璋廉政思想,也表达了朱元璋坚持惩贪的决心,也是凝聚社会力量助推廉政的大动员。
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编纂了《醒贪简要录》,颁布朝野上下,亲御奉天门大殿,向百官宣读。《醒贪简要录》中,统计了一组数据,文武百官的品级和每岁官俸数额;全部官俸换算市价稻谷总量;这些稻谷按照亩产换算为多少田亩;再换算多少劳动人力等。朱元璋公示这些数据,表现了朱元璋心系百姓的情怀,表达了朱元璋廉政的基本出发点。
3.4 奖惩劝诱
朱元璋用廉政思维,向吏部提出了“任人”的一项原则,提出了灵活性:“为国以任人为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贷之;果贤者,不以小疵而弃之。奸者必惩,庶不废法宥过,而用则无弃人。”[29]朱元璋示例指导:诸城县(今属山东潍坊市)知县陈允恭,因薄书之过,谪戍云南充军。朱元璋听说他治县,爱惜百姓,便谕吏部说:“为民之长而能爱民,可称贤者,虽有过,可用也。”[30]召其回来,恢复原职。体现了朱元璋爱护、保护有些过失的廉吏。
朱元璋常特派官员到各地慰问,旌表廉能之吏。平阳县(今属浙江温州市)令张础、建阳县(今属福建建阳市)令郭伯泰等人,因为廉洁公正,得到特派官员旌表;兴化(今属江苏泰州市)丞周丹,为政清平,任满去职。当地父老诣阙上书,挽留再任。朱元璋大悦,手敕奖励,复其职,并加赐衣币等物;对于善始善终的循吏清官,朱元璋不仅给予重赏,还为他们修建府第;清官寿终时,朱元璋亲自为他们撰写祭文,以彰其德;他还命人将清官廉吏的事迹列入 《彰善榜》、《圣政记》,弘扬清廉正气。
陶后仲在福建任按察使,惩治贪官数十人,尽除宿弊,抚恤军民,朱元璋予以表彰;循吏陈灌,是元末很有政治远见的儒生,看到元末的腐败,结邻里以自保,1364年,朱元璋占领武昌时,他上“救乱安民之说”,朱元璋任他为地方官。陈灌赴任,创立了本土“户帖制”,禁豪右兼并,抑制不法行为,境内生产恢复,人口增长。洪武三年,朱元璋下令将户帖制推行全国。洪武四年,朱元璋召其赴京,另行重任。
4 建制立法
反贪倡廉,奖廉惩贪,应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朱元璋实施廉政,同步建制立法。一方面建立完善严密的监督和考核机制;一方面立法、修法,在国家大法中强化惩贪的各种法令。洪武时期,朱元璋洪武时期,一直立法、修法,从未中断。“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日久而虑精一代法始定中外决狱一准三十年所颁”[31]一直到洪武三十年,制定了一部相对修订是廉政的社会实践,许多实际问题,不断反映在立法和修法的条文上。倡廉惩贪的一系列制度和法令,廉政的思想和意志制度化、法律化,加强了廉政实施的力度。
4.1 制度层面:建置“六科”
洪武六年,朱元璋创立了 “六科给事中”机构,对应监察“六部”官员。规定,“六部”下发的文件诏书,要经过“给事中”复核,不妥之处,封还奏报。各地上报皇上的奏章,“六科”按类抄报各部,提出驳正意见。六科建置仅七品,权力却很大。他们侍从皇上,每日一人上殿值班,“记旨”。皇上交派各衙署办理的事件,六科负责检查督办,拖延迟缓者,他们向皇上报告;各衙署完成了皇上旨意,由六科核销。六部官员考核,有六科官员参加。朱元璋建置“六科”,加强了监督机制,也加强了皇权。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进一步改革中央监察机构,建置“都察院”,取代御史台。职责为:“专纠劾百司,辩明寃枉,提督各道。”其行为直接对皇帝负责。都察院最高官员都御史与六部平行,合称“七卿”。都御史之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都御史的权力很大,参与吏部考察黜陟官员;会同刑部、大理院审理重大刑狱;又设十三道监察御史,任命110名监察御史,分掌13道。
朱元璋建立了御史巡按地方的制度。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凡吏政、刑名、钱谷、治安、档案、学校、农桑、水利、风俗、民隐都是其职责考察范围。巡按御史的权利很大,“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32]
4.2 法律层面:立法惩贪
明朝初建,官员构成非常复杂,一部分是元朝保留下来的官吏,一部分是农民军的各路将领,一部分是荐举、选拔或投幕的文职人员,一部分是朱元璋的旧部。元朝降臣,生长富贵,骄奢淫逸,极易贪赃纳污;朱元璋旧部,开国元勋,占据国家上层机构,位高权重,一部分人逐渐腐化堕落;其他人,希图名利,遇到发财机会,也不会轻易放过。虽然朱元璋苦口婆心教育百官,倡导廉政,照样有“拔鸟毛”、“挖树根”的腐败分子。这些贪官徇私枉法,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奢靡腐化。建国不久,就相继发生“空印案”、“胡党案”和“郭桓案”,为了遏止腐败,朱元璋本着“治乱世用重典”的态度,严惩贪官污吏,不惜法外用刑,惩治贪官污吏,甚至大开杀戒,以儆效尤。
洪武年间(1368—1398),制定《大明律》30卷,规定“贪墨之赃有六:曰监守盗,曰常人盗,曰窃盗,曰枉法赃,曰不枉法赃,曰坐赃。”凡枉法者,其量刑标准很严,“受财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八十贯绞;受财不枉法者,一贯以下杖六十,每五贯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三千里;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物,不分首从,并赃论罪,在右小臂上刺‘盗官钱’三个字,一贯以下杖八十,至四十贯斩。”凡贪赃枉法官员,罪不及诛者,统统发配北方充军。官吏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枭首示众。
又制定了“行贿”“通贿”罪,朱元璋下诏刑部,制定了一系列“行贿”“通贿”的细化条例。其中“官员受赃者,并罪通贿之人,徙其家于边,着为令。”所谓“通贿”,就是行贿的人员,一并治罪,充军流放。
《明史》记载,有两条法律,朱元璋亲自制定,其一,“剥皮囊草”;其二,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贯,论绞。”[33]
为了防止功臣们居功自傲,朱元璋制作了“申诫公侯铁榜”,向百官宣布,无论地位多高,身份多贵,功劳多大,贪赃枉法,一概按照《铁榜》的处罚标准,严加惩治。所谓“铁榜”,就是绝不宽恕。
5 重典严惩
“禁贪”是廉政的重要构成,也是保证廉政畅通不可或缺的环节。
为此,朱元璋采取了切实举措,整肃吏治,反击腐败,不惜一切代价挖掘官场的毒瘤,不论贪污团夥有多大,朱元璋老虎苍蝇一起打,毫不手软。斧钺之下,十几万贪官污吏人头落地。[34]表面看,朱元璋杀气冲天,遭到一部分史家批评,认为他有悖君臣伦理,“屠戮元臣宿将”,性格“残忍”。[35]实际上,朱元璋真正动用重典,始于洪武九年“空印案”,距明王朝建国约10年。这10年中,廉政建设取得了很多收获和进步,“亲民”、“养民”、“富民”、“节用”、“教化官吏”等环节基本畅通。
但是,元朝官场旧习,不学而沿袭。反观这一段历史,贪污之风,蔓延官场。有些贪官污吏气焰嚣张,或上下勾结,蚕食国有资财;或分割赋税,中饱私囊;或明目张胆造假账,掩盖财政窟窿。凡此等等,猖狂的贪污之风,“倒逼”朱元璋作出政治抉择。朱元璋只有两条路:一是网开一面,同流合污;一是奋起反击,突破重围。朱元璋选择了后者,勇抓大案,不避权贵,不阿亲戚,掀起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廉政风暴。
5.1 勇碰大案
朱元璋直接关注了四宗疑难大案。其中,有二宗是经济贪污案,另外两宗是政治案,夹杂“贪赃”、“通贿”,乃“数罪并罚”。
这四宗大案,依次发生在洪武九年(1367)“空印案”、 十三年 (1380)“胡惟庸案”、 十八年(1385)“郭桓案”、二十六年(1393)“蓝玉案”。 每一起大案,因案情复杂,“拔起萝卜带起泥”,波及朝野一大批官员。
“空印案”,本质上是经济造假案。其案情是地方官吏携带加盖官印的空白文书和账册,赴户部结算钱谷数额。地方官员申报的数额常被户部驳回,则按照户部的数据,任意填写交差。据《明史·刑法志》记载:“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豫(同‘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以为常。”毛佩琦教授指出:“这种做法行之已久,上下已经习以为常。”[36]户部是朝廷的职能机构,府州县是地方官府,上下勾结造假,麻木到“以为常”的程度,各府州县皆视为例行公事,可见,范围之广,贪污之风病入膏肓。朱元璋洪武九年(1367)发现这件事情,经过6年调查,洪武十五年(1382)论罪严惩:“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邉。”[37]户部官员也受到严惩。这件事情震撼了全国上下,一下子扳倒了各府州县正职官员(掌印),全部处死,副职官员杖一百棍,充军边疆。实际上是一次全国性的贪赃、渎职官吏大清洗,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洪武十八年,发生了“郭桓案”,又是一件高官贪污案。案情是户部侍郎郭桓等人利用职权,勾结北平(今北京)布政使司李彧、提刑按察使司赵全德、胡益、王道亨等,合夥贪污,私吞巨额税款和秋粮,总共两千多万石。赋税之外巧立名目,征收水脚钱、口食钱、库子钱、神佛钱等,中饱私囊。案情牵连全国十二个布政司和朝廷六部,“赃七百万”。朱元璋毫不手软,“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吏部侍郎熂、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麦)至德等高官,[38]都据法“罪诛”。案情牵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39]朱元璋下令追回赃粮,牵涉到社会上豪门富户被抄家破产不计其数。史称“郭桓案”。
空印案和郭桓案,表达朱元璋严惩“贪暴”的廉政方针,他痛斥贪官“害民之奸,甚如虎狼。”
“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是谋反案,两案都裹挟贪赃受贿的罪行,通贿受贿,成为党人勾结“谋反”身份证。“胡党”和“蓝党”皆如此。首恶胡惟庸、蓝玉确是“元勋宿将”,但是,在朱元璋廉政的决心面前,亲戚私情,征战之旧,统统粉碎。
溯源中国廉政理论,最早的廉政定义,即包含惩治一切“邪恶”。《管子》曰:“廉不弊恶”,[40]其含义是揭露邪恶,廉政,就是一切善与恶的分野。《老子》曰:“廉而不刿”,[41]“刿”是“割伤”、“刺伤”的意思。可见“廉”的本义是“利器”。《老子》强调“以柔克刚”,但是却点明了“廉”的“斧钺”本质。朱元璋推行廉政,采取完全不同于《老子》的方法论,“除恶务尽”,彻查“胡党”、“蓝党”,把廉政推行到底。
朱元璋极其重视地方官的作用。在他看来,地方守令贪赃枉法,直接损害百姓对朝廷的感情,十分可恶。朱元璋特立几种严酷的刑罚,予以严惩。
“剥皮实草”,史载这一刑罚是“太祖法,剥皮囊草。”[42]据明代叶子奇撰《草木子》记载,朱元璋“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何谓“剥皮实草”,即在“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警心。”这一法令,其警示的意义大于惩罚的形式,震慑灵魂。
5.2 不阿贵、不私亲
朱元璋重典惩贪,不阿贵,不私亲,不因君臣之情而“废法”,不以征战之旧而“宥过”,[43]凡贪赃纳污,彻查到底,格杀勿论,直到晚年,心不变,手不软。
开国元勋华云龙,在北平私自占据元朝丞相的住宅,被撤职罢官。1385年,北平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人,伙同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人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查明他们种种劣迹:盗窃国库金银宝钞;盗卖官仓的粮食;贪污未入库的税粮和鱼盐税款。贪污盗窃总额折成粮食,达2400多万石,下令:赵瑁、王惠迪等人弃市;郭桓等六部侍郎以下的犯罪官员处死;各布政使司有牵连的官吏几万人全部下狱,严加治罪;追赃牵连到各地的地主豪绅,抄家处死者不计其数。丞相胡惟庸广收贿赂,“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44]又有其它各罪并发,朱元璋定罪“擅权枉法”,处死。株连者达15000人,后来扩大到30000人。朱元璋毫不手软。
高级将领“吉安侯陆仲亨,自陕西归,擅乘传。帝怒,责之曰,中原兵燹之余,民始复业,籍戸买马,艰苦殊甚,使皆效尔所为,民虽尽鬻子女,不能给也。责捕盗于代县。”[45]
高级将领 “平凉侯费聚奉命抚苏州军民,日嗜酒色。帝怒,责往西北招降蒙古。”[46]
朱元璋执法相当坚决,即使是皇亲国戚也决不姑息。驸马欧阳伦“数遣人私贩茶出境”,触犯刑律,沿途驿站检查,皆被骚扰,“虽太史不敢问,有家奴周保者尤横”,沿途擅自科派“民车至数十辆,过河桥廵检司,擅捶辱司吏。”朱元璋“大怒,赐伦死,保等皆伏诛。”[47]朱元璋侄儿朱文正,战功显赫,官拜大都督,镇守江西任上,骄侈荒淫,朱元璋先免其职,后又诛杀;[48]晋王朱棡 (音gāng)是朱元璋与高皇后生的第三子,因“在国多不法”,朱元璋将他逮到京城,“欲罪之,太子力救得免。”[49]开国功臣汤和的姑父因隐田漏税而被治罪。
6 启示与太息
朱元璋廉政,其“尚严峻”的特色,堪称十四世纪东方“廉政风暴”。朱元璋之后,其开创的廉政局面持续推行,“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百年廉政”,这是一个奇迹!它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启示;也留下了掩卷之后的思考和太息。
朱元璋廉政,历来有不同的认识。其批评者认为:立法过于严峻;用法过于残酷;杀人过于残忍;一句话,廉政“太过了”。如何看待这一批评,只有回到历史环境中,才能够讨论清楚。
朱元璋立法严峻,执法残酷,杀人残忍,这是史实。朱元璋自身也有清楚的认识,毫不讳言予以承认。
洪武二十六年,蓝玉党案结束后,朱元璋逐步减轻刑罚。二十九年,他接受皇太孙朱允汶的建议,修改“畸重者七十三条”。他对皇太孙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
如何看朱元璋的廉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有三点值得思考:
其一,没有激起民变,所杀贪污腐败分子,赃官墨吏,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社会不但没有出现“民变”,恰恰消灭了发生民变的因素,稳定了社会。现代史学家孟森先生的《明史讲义》评价说:朱元璋严刑苛法治理天下、驾驭群臣,为什么不但没像秦朝那样二世而亡,还奠定了明朝近三百年国祚的基础?就是因为他“不得罪百姓”。他说,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得国最正”,就是因为他心系万民,懂得如何爱护老百姓。
其二,明朝初年的社会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全国统一,统治范围扩大,漠北战争的胜利,永乐年间,持续廉政,七次下西洋,加强对外联系和经济贸易;从各个方面考察,明王朝走向治世,成为举世瞩目的强国。
其三,朱元璋一手抓教育,一手抓严惩,经过二十多年的反贪倡廉实践,一大批贪官遭到惩处和打击,官场风气迅速清正,明初吏治日趋清明。《明史·循吏传》说:“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这一记载,至少说明:明初吏治比较清明,廉政取得了一定成绩。著名清官海瑞高度赞扬朱元璋惩贪:“毫发侵渔者加惨刑。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
朱元璋确乎是铁石心肠,在他“御宇”的三十一年间,“重绳贪吏,置之严典”,毫不留情诛杀贪官,他是中国历史上治贪最严、出手最狠的君王。他杀了多少贪官,据《大诰》、《续诰》记载,仅在两浙、江西、两广、福建等省,被处决的贪官已很难以数目计,许多州县的官位经常空缺。
应该看到,朱元璋下狠招“澄清吏治”,惩治贪官,确实收到了实效。当时的官员们终日胆战心惊,收敛很多,顶风作案的人少了。有人夸张说:“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悚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发出法度,悖礼仪,朝按而暮罪之。”这种气象一直延续到仁宗、宣宗时代,“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其反贪成果,可谓斐然。
然而,朱元璋铁腕惩贪,不惜“剥皮食草”、“刷洗”、“抽肠”等严刑酷手段,扫荡贪官污吏,最后仍然“人亡政息”。朱元璋凭借个人权威、个人意志、个人品质,拼力创建了人民叫好的廉政,然而仅仅维持“百余年”,明王朝共计16代君主,五六代之后,即出现反弹,朱元璋的子孙们骄奢淫逸,怠于朝政,文恬武嬉,贪污受贿之风遍及朝野,正如《明史》所说:“仁、宣之盛,邈乎不可复追,而太祖之法蔑如矣。”严嵩、魏忠贤之类的巨贪滑吏,蔑视朱元璋制定的严刑峻法,气焰嚣张,横行朝野,朗朗乾坤重新笼罩阴霾。朱元璋的“百年廉政”,在历史的长河中,向过山车一样短暂一瞬,百姓再堕贪官污吏的深渊。令人扼腕,哀哉!一声太息。
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历史的启示: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只有政治上高度透明,发动人民起来监督,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才能够与时俱进,创建廉政万岁的历史。
[1] (清)张廷玉.明史·循吏传·序(卷 281)[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卷14)[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 (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卷14)[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 (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卷14)[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 (明)俞汝楫等撰.礼部志稿[(卷 88)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6] (清)张廷玉.明史·陶安传(卷 136)[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太祖起兵(卷1)[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8] 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35)[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年校印本.
[9](隋)王通.中说 钦定执中成宪(卷4)[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
[10] 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77)[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年校印本.
[11] (隋)王通.中说 钦定执中成宪(卷4)[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
[12] (隋)王通.中说 钦定执中成宪(卷4)[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
[13] (清)张廷玉.明史·陈友谅(卷 123)[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4] 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76)[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年校印本.
[15] (清)张廷玉.明史·舆服二·皇帝冕服(卷 66)[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6] (明)程敏政辑.明文衡·墓表·方克勤墓版文(巻91)(集部-104)——钦定四库全书荟要[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
[17] (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卷14)[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8] 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17)[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年校印本.
[19] 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76)[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年校印本.
[20] 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250)[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年校印本.
[21] (清)张廷玉.明史·食货一(卷 77)[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2] (清)张廷玉.明史·循吏传·序(卷 281)[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3] (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 2)[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4] 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249)[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年校印本.
[25] 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88)[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年校印本.
[26] (隋)王通.中说 钦定执中成宪(卷4)[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
[27] (清)乾隆三十二年敕撰.钦定续通志[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8] (明)俞汝楫等撰.礼部志稿·圣训·太祖高皇帝(卷1)[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9] 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8——史部·杂史类——皇明修文备史·皇明宝训(卷3)[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30] 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88)[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年校印本.
[31] (清)张廷玉.明史·刑法一(卷 93)[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2] (清)张廷玉.明史·职官二·都察院(卷 73)[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3] (清)张廷玉.明史·海瑞传(卷 226)[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4] (清)张廷玉.明史·刑法二(卷 94)[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5] (清)赵翼撰.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6] 毛佩琦.明代十七帝·空印案之谜(2)[Z].电视演讲.
[37] (清)张廷玉.明史·刑法二(卷 94)[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8] (清)张廷玉.明史·七卿年表(卷 111)[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9] (清)张廷玉.明史·刑法二(卷 94)[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0] 周怀宇.论《管子》“廉维论”的理论价值[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4).
[41] 李存山,注译.老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42] (清)张廷玉.明史·海瑞传(卷 226)[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3] 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8——史部·杂史类——皇明修文备史·皇明宝训(卷3)[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44] (清)张廷玉.明史·奸臣·胡惟庸(卷 308)[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5] (清)张廷玉.明史·奸臣·胡惟庸(卷 308)[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6] (清)张廷玉.明史·奸臣·胡惟庸(卷 308)[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7] (清)张廷玉.明史·食货四·盐法(卷 80)[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8] (清)张廷玉.明史·诸王·朱文正(卷 116)[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9] (清)张廷玉.明史·诸王一·太祖诸子一·晋王棢(卷 116)[M].北京: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