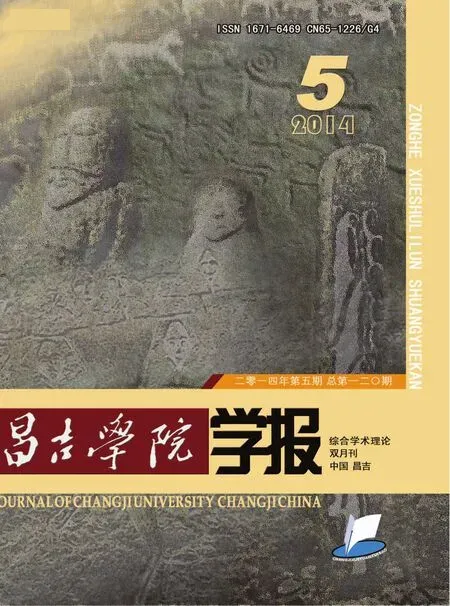僭越、困顿与危机
——霍达《穆斯林的葬礼》的伦理学分析
2014-03-28凡党文静
张 凡党文静
(1.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 新疆 石河子 832000;2.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 100871)
僭越、困顿与危机
——霍达《穆斯林的葬礼》的伦理学分析
张 凡1,2党文静1
(1.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 新疆 石河子 832000;2.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每个民族在漫长的发展中业已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伦理习俗,这些基于民族情感、心理机制及思维特质的伦理习俗,注重信仰、责任与义务的高度一致。对具有特定信仰的民族来说,这些伦理习俗具有广泛的认同性、约束性与不可僭越性。《穆斯林的葬礼》讲述了一个穆斯林家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荣辱兴衰史,其中交杂社会政治、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及生命理想等复合要素。作家从宗教、家庭、社会等伦理视角出发,以两代人复杂的情感关系为主线,通过对主要人物在理想与现实、信仰与世俗、激情与忠诚的剧烈冲突中所做的艰难抉择的叙述,呈现出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穆斯林传统文化所遭遇的某些危机,并对这些人物在生存抉择、情感表达及社会身份的历史承担上给予了伦理学意义上的理性观照。
僭越;困顿;危机;伦理学分析
T.W.阿多诺在《道德哲学的问题》一书中有这样的表述:“‘Moral’(道德)这个词来自于拉丁文‘mores’,我希望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词,‘mores’就是‘Sitte’(伦理,道德)的意思。”“如果人们不是从一开始就想完全抽去伦理这个概念的内容,而不至于使自己对这个概念根本做不出任何表象,那么,人们就必定会在这方面思考共同体内部中现成的各种伦理习俗,这些伦理习俗在各个特定民族内部占据统治地位。”[1]阿多诺在这里探讨的是“伦理的实体性”问题,即是一种正确生活的选择与可能性。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每个民族业已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伦理习俗,这些基于民族情感、心理机制及思维特质的伦理习俗,注重信仰、与责任、与义务的高度一致。对具有特定信仰的民族来说,这些伦理习俗具有广泛的认同性、约束性与不可僭越性。小说《穆斯林的葬礼》是个独特的艺术存在,它以一个穆斯林家族为叙述对象,讲述了这个家族长达半个多世纪荣辱兴衰的演变史,其中夹杂着社会、政治、宗教及生命等复合要素。作家把两个发生在不同年代、不同背景下的爱情悲剧,和深陷苦难泥沼中的男女主人公们同置于文本之中,将他们多舛的遭际和艰难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表现了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信仰与世俗、激情与忠诚的艰难抉择中对真爱真情的一种向往、一种坚守,进而彰显了霍达小说世界不朽的艺术魅力。
一、僭越:复合的人性
在卢卡奇看来,“小说创作就是把异质的和离散的一些成分奇特地融合成一种一再被宣布废除的有机关系。诸抽象成分的凝聚关系就抽象的纯粹性而言是形式上的关系;因此,最终的
结合原则必定是创作性的主观性在内容上变得明晰的伦理。”[2]《穆斯林的葬礼》是以复线的形式展开小说叙事的,这种有机交错的叙事形式既是一种连贯性表达,同时也将发生于各部分之间的伦理关系互联其中,彼此照应。小说以两代人的爱情为叙述线索,勾勒出一幕幕温婉感伤的凄美画面,不论韩子奇与梁冰玉,还是韩新月与楚雁潮,都无法挣脱宗教伦理的规约和家庭、社会伦理的诸多藩篱。身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一个热爱祖国和民族的作家,我只是写了自己所了解、所经历、所感受的北京地区的一个穆斯林家族的生活轨迹,而不可能涵盖整个民族。”[3]这里可看出,霍达在小说中着重关注的是伊斯兰文化统摄下人的生存需要、情感选择与现实境遇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性本能与伦理习俗之间的冲突。在整个伊斯兰教文化体系中,婚姻与家庭占有核心的地位,伊斯兰教鼓励婚姻,因它关系到种族的繁衍绵延;伊斯兰教也强调婚姻是建立在男女双方忠实感情的基础上,彼此必须宗教信仰一致,否则就会同床异梦,没有共同的精神寄托,没有共同的语言,终究无幸福可言。伊斯兰教允许一夫多妻,反对违反人性的禁欲,但禁止淫乱,“《古兰经》中赫然载有这样的戒律:‘真主严禁你们……同时娶两姐妹’!”[4](P665)韩子奇未能恪守这一戒律,与姐姐梁君璧发生了婚姻关系,与妹妹梁冰玉产生了爱情关系、并都有了孩子,而“伊斯兰教在教义学上由信仰(穆斯林对安拉赐予穆罕默德的‘启示’基本信条的确认)、义务(穆斯林必尽的五项宗教功课)、善行(穆斯林必遵的道德规范)三部分组成。”“去行善止歹以便后世赏善惩恶,这是真正的穆斯林相信的正义的内涵,是他们恪守的信仰与所希求的道德生活。”“中国伊斯兰教在教义、组织、教仪诸方面都是大致一致的,从而使各信仰民族在伦理上表现出很大的共同性。”[5]从这个层面来看,韩子奇这种破戒行为是严重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教义的,而这正是导致韩子奇一生坎坷复杂、悲剧丛生的主要根源。
身为“玉器梁”的传人,韩子奇始终处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激情与理性、亲情与爱情、信仰与生存激烈碰撞的漩涡之中。从随吐罗耶定浪迹天涯到成为“玉器梁”的徒弟,与“奇珍斋”结下了不解之缘。“玉器梁”梁亦清是个传统的穆斯林,技艺超群却为人低调,不习惯与人明争暗斗,过着与世无争的清贫生活。为了信仰,为了民族,他把一生的气力与心血都凝聚到雕刻“郑和航海图”上,三年琢一玉图,未了却吐血而亡。“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凸显了梁亦清与众不同的气度与风范,他身上特有的浑厚气韵对韩子奇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师徒二人惺惺相惜,情如父子。等处理好梁亦清“无常”之后,韩子奇冒着被梁家人误解,忍辱负重追随梁家的“堵施蛮”蒲寿昌;三年后,他满怀抱负与胆识开始了重振“奇珍斋”的复兴征程。日本侵华全面爆发,为保存好心爱的玉,他离妻别子,与因失恋而受伤的梁冰玉出走英伦半岛,颠簸流离于异国他乡。“文革”十年浩劫,他忍气吞声、默默捍卫那些以生命为代价保存下来的玉,终被红卫兵“抄家”,直到死亡。
人生路上的坎坷磨难练就了韩子奇复杂而笃定的性格特点。自小深受穆斯林文化的熏陶,同时也深受中国传统伦理与现代文化的双重影响。由此,形成了他独特的心理镜像:他心怀抱负,渴望成功,对真爱有本能的呼唤与诉求,而内心深处固有的民族文化、心理机制约束了他的身与心,使他无法超越现实与突破信仰。韩子奇饱受多重精神伦理激烈的冲击,在煎熬之中痛苦前行,他试图通过与现实的一次次抗争来获得个体价值的上佳表现。由穷困潦倒到名满京城,成功的轨迹再现了他倔强而执着的强大内心,也突显了他在人性方面坚守的力量与一种价值倾向。为不辜负师傅“玉器梁”,他忍辱负重三年,为重振“奇珍斋”赢取了翻盘的资本;为给“回回”争光,他勇敢面对残酷的现实,努力寻求改变个人及家族命运的转机,主动接受汉文化与外来西洋文化,与重逢的梁君璧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喜结连理,履行了一名穆斯林起码的责任;他忍受苦难,致力于收玉、赏玉,历经十年而终使“奇珍斋”名冠北京城。生于动乱年代的韩子奇,现实让他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被迫离妻别子,背井离乡,踏上流亡英伦三岛的漫漫征程,走上了身在
异国他乡的漂泊之路。
梁冰玉自小聪明可人,受过旧式学堂和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的教会学校的双重教育,是一位有个人主见、生性温柔的现代知识女性。她生活于穆斯林家庭,童年时在姐姐梁君璧与姐夫韩子奇的呵护下,少了几分失去双亲的痛苦;青年时代接受了“五四”新思潮及现代文化的感染与熏陶,追求个性解放,性格刚强,常与“管家婆”式的姐姐发生冲突。她崇尚恋爱婚姻自由,却不失正义感与爱国热情,当得知初恋情人杨琛出卖革命的真相后,毅然与卖国者决裂,“我这辈子决不会嫁人,当做饭、生孩子的机器,我谁也不爱!谁也不爱!”(P302)遭遇恋人背叛的梁冰玉,心灵受到巨大创伤,跟随姐夫韩子奇出走英伦半岛;身在异国土地上的她,没有勇气接受英国男孩奥利弗的爱,因而回绝了奥利弗的追求,使得无辜的奥利弗为急赶回家送她一支红玫瑰而在空袭中丧生。纷飞的战火从北平波及伦敦,几乎要将世界的一切摧毁。美好的未来憧憬、昂扬的生活期待被丑陋的人性、残酷的战争所摧毁,一次次遭遇现实巨大冲击的梁冰玉,太多的委屈堆满了她的世界,也煎熬着她原本脆弱的内心。
“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韩子奇和梁冰玉,在炮火连天的异国他乡相拥而泣,战争的残酷几度把他们推向死亡的边缘;正是这种绝处逢生的患难与共让他们俩倍加珍惜彼此,一直以来的相濡以沫唤醒了他们内心深处对真爱的渴望,终使他们不顾一切地走向爱情。抛开长期束缚在他们思想上的种种宗教戒律、伦理道德,被压抑久了的人性犹如奔放的激流,以巨大的爆发力和盘托出;他们以前所未有的胆魄打破了千年以来禁锢在人们心身上的宗教禁忌,强烈地冲击了必须恪守的信仰体系,让人的真实自我得到最大化的本性呈现。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到了一起,以一种寻求爱的寄托让彼此接受对方,在相互抚慰中唤回了个体生命的本真需求。梁冰玉勇敢地追求属于自己的爱与幸福,以巨大的勇气冲破宗教、道德、伦理、亲情等重重障碍与韩子奇走到一起,尽显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动人形象,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女性意识觉醒、自我解放的时代歌者,“女儿们在传统禁令下的反传统的爱情,她们的内心理想与内外压力的交战,女儿们步入成熟后面临的矛盾和选择以及无可选择的规避,……,以及对未来生活命运发生的思虑、向往、担忧、恐惧,她们有的背叛家庭,违抗父母之命,毅然寻求爱情和人格独立。”[6]梁冰玉至真至纯的爱给了处于生命最危难时刻的韩子奇莫大的鼓舞,让他有了支撑下去的理由,也让人到中年的韩子奇尝到真爱带来的美好。
然而,“伊斯兰教有个明显的特征,即以宗教的手段干预穆斯林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个人到家庭直到整个社会生活。”[7]韩子奇与梁冰玉的异国恋情也不例外。他们的爱情发生于“二战”最残酷时期的伦敦这一特定时空下,缺乏持久下去的伦理土壤与信仰支撑;他们的爱情背离了伊斯兰教的教义,触犯了穆斯林根深蒂固的伦理习俗,是真主与穆斯林们所不允许的。当韩子奇与梁冰玉带着新生儿返回北京时,随即遭到姐姐梁君璧近乎疯狂式的抵制。梁君璧是个虔诚的传统穆斯林,随父母信仰无处不在的真主,时刻按照真主的意志来生活。可以说,恪守伊斯兰教义教规是她做一切事情的精神动力。当看到韩子奇与妹妹梁冰玉带着孩子从异国归来时,她怒不可遏地狠狠地打了梁冰玉一记耳光,并将妹妹逐出家门,在教义与亲情之间发生冲突时,她坚决捍卫了信仰;一个苦苦等候丈夫十年的妻子,她无法容忍丈夫和妹妹的“私通”,更何况她要维护好历经艰辛才取得的“博雅宅”女主人理应拥有的一切。无法面对眼前的一切,因梁君璧身上背负了复杂的情愫,“既有伊斯兰的美德,又不乏性格负面,教规教义影响制约着她,扼杀了亲人的幸福,自己也为传统习俗的牺牲品。”[8]
从传统文化层面来看,韩子奇与梁冰玉的爱情有悖于正常的道德伦理与社会价值:一方面韩子奇面对眼前历经战争磨难与离别之苦的妻儿,他无法超越心中沉淀已久的道德伦理和传统穆斯林固有的文化心理机制,他深爱着冰玉,却又无法了断与梁君璧无爱的婚姻家庭。当看到心爱的男人无法鼓起勇气与她一同寻找心中的家时,梁冰玉悲愤地喊出了“我是一个人,独立的
人,既不是你的,更不是梁君璧的附属品,不是你们可以任意摆布的棋子!女人也有尊严,女人也有人格,……!人格,尊严,比你的财产、珍宝、名誉、地位更贵重,我不能为了让你在这个家庭、在这个社会像‘人’而不把我自己当人!”(P660)这是捍卫真爱的宣言,也是面对残酷现实的一种无畏的抗争。面对容不下自己的姐姐和不敢正视现实的韩子奇,梁冰玉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再次出走。到这里,选择尊重人性还是遵从伦理习俗?其结果都无关紧要了,真心相爱的人从此天各一方,这种“活生生的离别”造成的人间悲剧分外凄凉。
二、困顿:错位的生命
从社会伦理文化复杂性来看,“民族宗教伦理的功能是多重复杂的”,“这种多重功能有突出的复杂性,主要在于:经济影响、政治影响、文化影响内在一体、同时并存;正面作用、负面作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积极效应中有消极效应,消极效应中有积极效应。”[9]深受传统汉文化与穆斯林文化双重影响的霍达,其写作视野是宏阔而多元的,她文学世界中的一切都处于相对多元的状态之中。然而,作家自身固有的民族感情与穆斯林文化因子却时常闪现在她的字里行间,不时地左右着小说主人公的命运及未来。韩新月是作家在《穆斯林的葬礼》中着力塑造的一个清纯美丽、聪慧坚强、近乎完美的回族少女形象,她是回族漫长文化传统美的精灵。小说以错落有致的方式展现了韩新月与楚雁潮这对年轻人纯美而圣洁的爱情,文本深处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与年轻的活力。他们之间的情感碰撞所激发的爱的火花理应是绚丽多姿、美丽动人的,然而他们的爱与乐、悲与苦却被蒙上一层凄美的迷雾。他们的纯美爱情令人动容,却终因阴阳两隔让人分外惋惜。直面他们所处的现实境遇,这对年轻人的爱情被理想化了,是作家对浪漫爱情的一厢情愿式的纯美想象。韩新月与楚雁潮之间,既有民族之别,更有信仰之异,而这些差异是不可跨越与不可逆转的。这些差异的存在,注定了他们之间发生的爱情终会以悲剧收场。
韩新月的出场,犹如出水芙蓉一般,“她不必特别地打扮自己,便有一种天然去雕饰的朴素的美。”(P33)她美丽自信,坚持填报、并如愿考进北京大学,进入北大后便以全身心的投入取得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少女韩新月时刻散发出一股清新的味道,她身上少有传统文化的负累,更多体现的是现代知识青年的文化人格。与楚雁潮的相识相知,从入学报到、“备斋”里谈人生理想、以及病中面对楚雁潮无微不至的关怀,她激动、兴奋之余又极力保持着少女的矜持。她的思想是现代的,认为人的灵魂是平等的;她憧憬未来,渴望真诚、平等的爱情,当楚雁潮怀着满腔的热血与赤诚的心将圣洁的爱捧到她面前时,“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两颗心紧紧地贴在一起。”(P531)她具有生命的尊严感,当得知病情救治无望、手术与复学终将成为泡影时,强烈的自尊心和对楚雁潮深深的爱让她陷入无比痛苦之中,毅然提出要与楚雁潮分手,“原谅我,我不能接受您的爱情,……,也许我们之间并不存在爱情?”“爱情总不等于同情、怜悯和自我牺牲吧?……,不要让慈悲心肠误了你的终生,把我忘掉吧,您并不属于我,而属于您自己!”(P556-557)善良的天性又让她无法漠视楚雁潮炽热而极富耐心的爱,最终放下顾虑并决心与楚雁潮执手相爱,“只要楚老师还留在身边,她就要坚强地活下去!……,楚老师和她在一起,肩并着肩,手拉着手,两个身影已经融成了一个生命。”(P568)身患重病的生命之所以得以延续,源自生命本身对爱的呼唤。尽管韩太太从中作梗、百般阻挠,也熄灭不了她内心熊熊燃烧的爱的火焰,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鲁迅的《起死》以及流传千古的爱情神话《梁祝》都给韩新月的生命以不尽的力量,不断延伸新月的爱的生命力与持久力。
深深爱着新月的楚雁潮,他的存在让韩新月这个青春美少女的悲剧人生显得更加哀婉与悲凉。深受传统文化滋养的青年教师楚雁潮,为人简约朴实,一身儒雅气度;他性格沉稳坚定,有一颗强烈的事业心;他学习优异,是严教授眼中“最喜欢的学生”;他热爱翻译事业,懂得人生真正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北大需要教学人员,我就留下来了,我也是北大培养出来的啊!”(P178)毅然放弃了令人羡慕的翻译工作,甘愿选择留在北大做一
名普通的教师。他与韩新月惺惺相惜,亦师亦友。面对有着强烈上进心的韩新月,他不断地鼓励与支持她再接再厉;面对被病魔折磨的韩新月,他主动与主治大夫卢大夫沟通,为韩新月筹划最佳的治疗方案;面对因治疗无望而情绪烦躁的韩新月,他耐心细致地开导她、引导她能正确对待现实,“一个人了解了自己的真实情况,不管是长处还是短处,都应该感谢幸运,这使我们自知!古往今来,有成就的人首先是自知的。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的弱点,然后才能克服它,战胜它,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P342)当韩新月即将走到生命终点时,他依然以生命的真诚与爱的火热去温暖、感动韩新月即将冰冷的心,陪伴她顽强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爱是真诚的给予,爱更是无私的付出。楚雁潮用尽他的一切去呵护新月,他明白“自己在出生之前就命中注定要走一条坎坷的路,……,只要新月能得到幸福,哪怕他最终失去新月,也愿意忍住自己的痛苦!”(P530)楚雁潮的坚持与笃定感动了病中的韩新月,让她真正感受到活着的意义,使她有了与病魔作最后斗争的希望与动力。
马克斯·韦伯在论述伊斯兰教早期的一些特征时说,“其他的一些特征亦可看出伊斯兰教所保留的一种特殊的封建精神:……;本质上为仪式主义性格的宗教义务;以及最后,极为简单化的宗教性要求,与更为简单化的有限的伦理要求。”[10]再者,“在穆斯林的婚姻条件中,宗教信仰一直是穆斯林婚姻的先决条件。”[11]在传统穆斯林家庭里,“卡斐尔”是不可能得到穆斯林的爱情。在韩太太眼中,楚雁潮是一个“卡斐尔”。当楚雁潮一步步走进韩新月的情感世界时,韩太太从最初的百般阻挠,直至最后歇斯底里的反对。作为忠实的穆斯林信徒,韩太太一生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从未想过也坚决不同意像楚雁潮一样的“卡斐尔”进入她的家庭,并与韩新月由爱情走向婚姻。韩太太不顾楚雁潮是为给新月以爱与力量、给新月得以活下去的勇气这一初衷,断然拒绝了楚雁潮的苦苦哀求,迫使楚雁潮不得不做出无奈而痛苦的妥协。面对弥留之际新月的乞求,韩太太没有表现出一位母亲应有的慈爱,而是声严色厉地拒绝了新月生命最后的乞求,“你就不知道自个儿是个回回吗?回回怎么能嫁个‘卡斐尔’!……,我宁可看着你死了,也不能叫你给我丢人现眼!”(P597)韩太太粗暴的拒绝让“新月的心仿佛突然从空中坠落,她懵了,呆了,傻了!炽烈的爱使她忘记了楚雁潮原是另一种人,他们属于两个不可跨越的世界!”(P596)从这里可以看出,与楚雁潮的差异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少数”的孤独感与压抑感令她窒息,一种前所未有的彻底的无妄将新月逼进蹩脚的死胡同。
死亡正在此刻慢慢逼近新月,生命的烈焰即将黯淡下去,“新月没有等到她盼望的那个人,终于丢下一切,走了!对这个世界,她留恋也罢,憎恨也罢,永远地离开了。”(P696)花季少女香消玉焚,一场隆重庄严的葬礼在“月落”时分进行。这是个略带寒意的穆斯林的葬礼,也是一场纯美爱情的冰冷埋葬,韩新月与楚雁潮的爱情因信仰的差异、民族的有别,彼此都成为宗教禁忌与伦理传统的牺牲品。这场葬礼,既埋葬了两颗纯洁、真诚的年轻的心,也把原本属于他们的青春与未来的幸福给彻底埋葬了,从“月梦”到“月落”,新月的生命如同一颗飞过天际的流星,刹那间走完了她短暂的人生旅途,一弯“新月”在没有走向圆满便从天空中陨落。韩新月与楚雁潮之间的爱情注定是短暂的,如同新月与楚雁潮打算上演的那场《哈姆雷特》中,楚雁潮的那段话:“不,不,太苦了,这戏太苦了,让我在她的葬礼中上场,跳下她的墓穴?……,这太苦了!”(P260)与死亡纠缠如此激烈的爱情令人心痛:有了“死亡”,“爱情”才变得弥足珍贵;有了“爱情”,“死亡”才更加凄美动人。
三、危机:伦理学追问
德里达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独特性的存在,不是依赖它的独特的文学魅力,不是依赖它的独特的文学性,它依赖的是文学外的东西。”[12]长篇《穆斯林的葬礼》这一文本之所以拥有如此巨大的艺术张力,原因在于小说中主要人物的人生抉择都在能否坚持信仰、恪守伦理与尊重人性这三点之间左右徘徊、并发生着激烈的冲突。他们最终所做的这些有悖于常理的选择及行为,从很大程度上危及到伊斯兰教自身伦理体系的历
史架构,这势必会给伊斯兰伦理价值构建带来某些危机。就人物形象塑造而言,韩子奇无疑是小说中的主线性人物,前半生风生水起,后半生沉默孤独,一种宿命意味镶嵌其间。然而,他悲剧的一生是其内在性格与外在环境复合作用的直接后果,而外在环境对他一生的影响格外突显。自小是个流浪儿,先是被云游四海、一心向往麦加圣地的吐罗耶定收养,后因缘际会,拜了梁亦清为师并成为“玉器梁”的传人。由此,他将个人的生命、家庭与事业都与玉紧紧捆绑在一起,他爱玉,护玉,守玉。为保护玉,他离妻别子、出走异国十多年;亦是为玉,放弃与梁冰玉之间的真爱而郁郁终老。可以说,韩子奇直到临死时才明白一个道理,“那些玉,本不属于他这个‘玉王’,也不属于当年的‘玉魔’老人,不属于任何人,他们这些玉的奴隶只不过是暂时的守护者,玉最终还要从他们手中流失,汇入滔滔不绝的长河。”“他自己,只能赤条条归于黄土,什么也不能带走,只有一具疲惫的躯壳,一个空虚无物的灵魂,一颗伤痕累累的心,和永不可饶恕的深重的罪孽……”(P591)在这里,作家将生命的有限与玉的永恒粘附在一起,引发人们对宇宙、对人生更多的思考。然而,悲剧的魅力就源自这“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反抗精神,即使“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也要勇敢地走向那无尽的未知世界。韩子奇为了玉耗尽一生,临终前对于玉、对于生命意义的彻悟虽令人叹息,但一生与玉为伴,其传奇一生充满诗意之美。韩子奇一生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内在心灵不断历练与完善的过程,也如霍达在小说的《自序》中所说:“人生在世应该做那样的人,即使一生中全是悲剧,悲剧,也是幸运的,因为他毕竟完成了并非人人都能经历的高洁、纯净的意境。人应该是这样的大写的‘人’。”(P747)韩子奇身上杂糅了太多的矛盾因子,复杂的情感造成了他苦难的一生。这种带有宿命意味的命运安排是他的个体性格、伊斯兰教、回族文化及社会伦理等因素混合作用的直接后果。
与妻子妹妹梁冰玉的“英伦之恋”,是韩子奇人生轨迹的转折点。他们之间发生的爱情破了《古兰经》中严禁同时娶两姐妹的戒律,这种违背伊斯兰教规戒律的行为从根本上挑战了伊斯兰教所持的伦理立场;因此,他们之间发生的爱情的合法性自然受到宗教传统的质疑与拒绝。站在梁君璧的立场看,妹妹与自己丈夫之间发生的爱情直接威胁到自己在“博雅斋”苦心经营所得的家庭地位;作为传统保守的伊斯兰教信徒,对妹妹与自己丈夫的这种违背教义戒律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就韩子奇自身而言,与梁氏姐妹之间发生的情感纠葛具有多重意义:出于一种担当,与梁君璧结为连理,为振兴“奇珍斋”而忍辱负重;出于一种责任,与梁冰玉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发生爱情,让身在异国他乡的他们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心;出于一种道义,从跟随吐罗耶定到师从“玉器梁”,坚持为信仰、为“玉”的事业而鞠躬尽瘁。活着的价值和对“玉”的执着在韩子奇身上积压了太多太久,这些来自宗教教义、伦理道德、家庭家族及人生追求等方面的种种压力使得韩子奇不得不选择一种妥协、唯唯诺诺的姿态来面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不幸的一切。可以说,韩子奇苦难与不幸的一生并非是他先天性格的懦弱无能,现实境遇使他不能随心所欲,在信仰与伦理两难取舍的困境之中,只好将个人的真性情压抑在内心深处而踽踽独行,并且每向前一步便如履薄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批评家能够进入文学的历史现场,而不是在远离历史现场的假自治环境(false autonomy situation)里评价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甚至要求批评家自己充当文学作品中某个人物的代理人,做他们的辩护律师,从而做到理解它们。”[13]可以说,惟有回到小说文本之中,立足于人物成长的历史场域之中,方能理解韩子奇为何在其后半生中,每当与梁君璧发生争执时常常表现出一种妥协退让、息事宁人的姿态,在处理儿女问题上也显得犹豫不决,之所以出现这些情态并非因其软弱的缘故,而是他深藏于内心深处对梁君璧、对家庭的愧疚之意。这种尴尬的家庭处境让韩子奇时常处于一种悖论式的选择与被选择之中,甚至有时不得不舍弃珍藏多年的玉器来求得一种平衡。为支持女儿新月报考中意的北京大学西语
系,他不得不做出让步,与韩太太达成某种微妙的妥协。当被韩太太倒卖出去的那块乾隆年间的翠珮回到自己手中、并请求鉴定时,一种仿佛失去亲生骨肉般撕裂的巨痛让韩子奇顿时失魂落魄,导致其滑倒骨折被送进医院。韩子奇一方面为实现女儿的大学梦,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弥补心中对冰玉母女的愧疚之感,被迫答应梁君璧的无理请求;同时也为儿子天星的婚事做了资金储备,弥补因出走英伦离家十年,未能对儿子尽到父亲义务的一种物质补偿。到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韩子奇日常在家中所表现的懦弱是有原因的。因此,只有将韩子奇这一人物置于特定的伦理关系中,才能理解导致其性格改变的复杂原因。进一步而言,当自由意志与伦理秩序发生冲撞时,人的性格往往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由于信仰的个人选择,韩子奇要时刻铭记真主安拉的教诲,顺从主、归依主,而这时宗教伦理习俗对他的日常行为发生一种规约作用。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影响下的韩子奇,考虑到家庭、家族的责任、民族未来的前途以及社会文化的传承,不得不为一生的承担与负疚去付出各种艰辛。“二战”风云、“文革”动乱等重大历史事件都成了韩子奇一生命运重要的转接点,多股力量的犬牙交错、相互制衡扼住了韩子奇这一人物命运的咽喉,他只能放弃来之不易的真爱,屈从于宗教教义、社会人伦与家庭责任。可以说,韩子奇的软弱不是不去抗争,而因经历过太多的磨难与命运的艰辛,他选择了无爱的婚姻,选择在“博雅斋”里生活下去。他的选择是复合伦理框架内的一种危机规避,这种带有悖论式的选择方式无形中透出深处夹缝中生命个体无法言说的悲剧美学。
再者,“几乎所有的文学文本都是对人的道德经验的记述,几乎在所有的文学文本的伦理结构中,都存在一条或数条伦理线(ethical line),一个或数个伦理结(ethical knot or ethical complex)。在文学文本中,伦理线同伦理结是紧密相连的,伦理线可以看成是文学文本的纵向伦理结构,伦理结可以看成是文学文本的横向伦理结构。”[14]就《穆斯林的葬礼》而言,信仰与宗教禁忌、伦理习俗就是那条或明或暗的伦理线,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及丰富小说结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本中以这条伦理线代言人自居的便是梁君璧,可以说她是伊斯兰教信仰的捍卫者与伦理习俗的执行者。伊斯兰教《圣训》中规定凡穆斯林必尽的念、拜、课、斋、朝“五功”的基本义务,她都事必躬亲。她时刻将真主的教义教规牢记心中,并视为自己言行处事的标准贯彻执行,且坚定而不可动摇。因此,家中的大小事务基本上都由她说了算。韩子奇则属于这条伦理线上的线索人物,也是伦理线上不可或缺的伦理结的构成者。与梁君璧的结合是其在艰难环境下的一种担当与责任,目的在于报答师傅梁亦清的培育之恩,在于照顾梁氏姐妹重振奇珍斋,在于对得起“玉器梁”的祖祖辈辈。起家于困苦的艰难年代,与梁君璧的结合更多的是道义与使命使然,其中是否含有真爱值得考量,也正是这桩嫌有温存、饱含复杂情愫的婚姻为其日后的家庭生活埋下了悲剧的基因。在这里,韩子奇与梁君璧已构成一对伦理结,而他与妻妹梁冰玉发生的爱情不仅触犯了伊斯兰教的禁忌、也有悖于正常的社会伦理道德,这两人亦构成一对伦理结。同样,韩新月和楚雁潮之间的爱情虽不惧生死、可歌可泣,然这两人之间的爱情则是隔着“教门”发生的。梁君璧眼中的楚雁潮是个“卡斐尔”,尽管楚雁潮出于一份真爱,试图以爱的力量延长新月的生命之旅,换来的依然梁君璧的严词拒绝。可以说,楚雁潮与韩新月从出生那刻起就分别属于两个世界里的人,不同的宗教信仰是他们无法逾越的鸿沟,而这两者又构成了一对伦理结。梁氏两姐妹虽是血缘至亲,由于都与韩子奇发生了情感关系,并都育有后代,导致姐妹俩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与矛盾,继而也构成了一对伦理结。而韩天星也在母亲梁君璧的预谋下与初恋容桂芳告吹,稀里糊涂娶了其母比较中意的、且门当户对的陈淑彦,可以说韩天星对淑彦基本没有爱恋,只是觉得应该娶,却并不明白为何要娶。他们俩的结合又产生了一对无爱的婚姻:男方是为了责任,女方是为了感恩,所以他们俩也可算作一对伦理结。而这些纠结着爱恨离愁的伦理结都和韩子奇这个线索人物的行为
——娶了姐姐梁君壁又爱上了妹妹梁冰玉——发生着或远或近的关联。可以说,韩子奇的破戒行为直接导致了固有伦理体系中内在秩序的混乱,从而给这个传统的穆斯林家庭带来了一连串的不幸与恩怨。韩子奇的行为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教义,已构成对既定宗教伦理秩序准则的巨大冲击,而这种冲击则给伦理体系中固有的内在秩序造成一种危机。文学大师鲁迅曾认为,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5],在这场生命的“葬礼”中,每个人都试图与既定的命运进行抗争、与固有的伦理秩序展开抗衡,也正是这种对立与冲突造就了小说人物性格的自我升华,这种带有不可逆的危机感使文本焕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结语
从审美角度来看,“《穆斯林的葬礼》从头到尾都是美的。”[16]纯真的亲情,炽热的爱情,质朴的人物,简洁的叙事,无不体现小说文本作为美的一种存在。作家试图通过小说文本向人们呈现出一幅唯美爱情的凄美画面,到处萦绕着忧伤的气息。“冷酷”的作家总不愿意让人们去享受纯美爱情的美满结局,把世上最纯洁美好的东西打碎,让读者亲眼目睹爱情之花在痛苦的泪水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爱情也从美好走向凄冷。美好的爱情是情感的诗意表达,始于快乐,却终于悲伤。作家在小说的叙事中善于把令人动容的美展现出来,毫不留情地撕去怜悯的面纱,力图通过展现僭越人性的苦难后果、个体遭遇的生命困顿以及冲击既有伦理体系造成的危机把现实最残酷的面目暴露出来,进而呈现出人性中最为痛苦不可改变的一面,让那些理想化的人物饱受痛苦的煎熬。作家用生与死两难取舍来考验爱情,给人们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与心灵震撼。可以说,《穆斯林的葬礼》中这两场爱情的凄美结局,是两种文化、不同信仰之间矛盾与冲突的结果。作家通过小说的精心布局,显现了其创作的某种文化征象与精神指向。韩子奇与梁冰玉的爱情,是向穆斯林传统禁忌和伊斯兰教婚姻固有体系的双重挑战;韩新月与楚雁潮的爱情,是可以忽略信仰、超越民族、抛开传统而义无反顾的真爱,是对穆斯林文化固有的种种束缚的新一轮叛逆。从宗教、家庭与社会多重伦理视角来看,作家是以一种悲悯的情怀去观照两代人的两场爱情悲剧,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撞击,不同信仰间的彼此冲突,虽没能在小说中走向融合,碰撞的火花也未能将宗教的禁忌化为乌有,他们或是天各一方,或是阴阳相隔,他们的行为早已超越其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
[1]﹝德﹞T.W.阿多诺,谢地坤等译.道德哲学的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1.
[2]﹝匈﹞卢卡奇,燕宏远等译.小说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75.
[3]霍达.二十年后致读者:为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珍藏版而写[N].光明日报,2007-09-14(11).
[4]霍达.穆斯林的葬礼[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12.(自此有关小说的引文均引自本书)
[5][9]王文东.宗教伦理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666,683.
[6]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5.
[7]车红梅.论梁君璧形象的悲剧意蕴[J].名作欣赏.2007,(4):81.
[8]朱育颖.同一民族壮歌的两个音符《心灵史》与《穆斯林的葬礼》的比较[J].民族文学研究,2000,(1):41.
[10]﹝德﹞韦伯(Weber,M.),康乐等译.宗教社会学;宗教与世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16.
[11]胡献锦.爱情的葬礼——解读《穆斯林的葬礼》的爱情悲剧[J].安徽文学,2007,(7):16.
[12]陈晓明.守望剩余的文学性[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51.
[13][1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20.
[15]鲁迅.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59.
[16]王晓云.《穆斯林的葬礼》的悲与奇[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6):174.
I29
A
1671-6469(2014)05-0045-08
2014-09-1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疆当代双语作家群研究”(项目编号:11CZW079)阶段性研究成果。
张凡(1982-),男,安徽舒城人,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