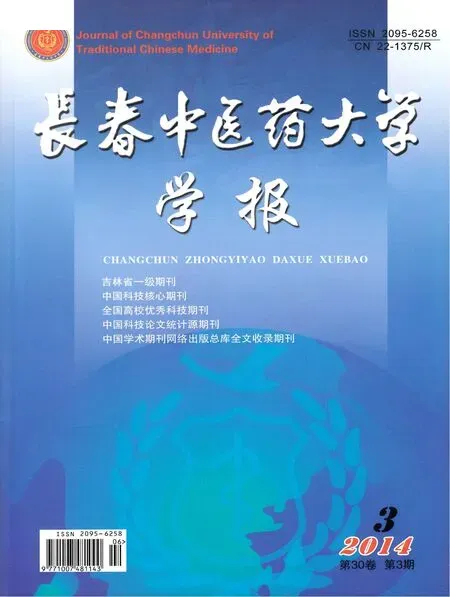从《内经》理论探讨中医对大肠癌的认识
2014-03-27金经美章永红
金经美,章永红
(1.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210029;2.江苏省中医院 肿瘤内科,南京210029)
大肠癌是全世界范围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近年其发病呈显著上升趋势。该病手术治愈率低,对放、化疗不敏感,病死率高,是亟待解决的医学难题。中医对该病的认识很早,早在《内经》就有大肠癌的相关记载。本文从《内经》角度探讨了直结肠癌的病因、病机特点及辨证治疗,旨在能加深对大肠癌的理论认识,提高临床治愈率。
1 《内经》中有关大肠癌的相关病因病机
1.1 病因 1)外因:《灵枢·百病始生》曰:“积之始生,得寒乃生,绝乃成积也”。《素问·举痛论》也记载:“寒气客于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血泣不得注于大经,血气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积矣”。寒邪侵犯小肠膜原之间的血络之中,使络血凝涩不能流于大经,气血留止不能畅行,日久便形成积聚。可见,《内经》强调,生于腹部之积块如大肠癌等病,最常见的病因为寒邪。此为大肠癌发病的外因。寒邪侵袭人体、深达脏腑,寒气停留在肠外,与卫气相搏结,营卫之气运行失常,邪气与营卫之气停附肠外,癖积留滞体内,卫气营血巡行失常,致病的恶气随之产生,形成息肉。如果邪气继续积聚不散,息肉逐渐生长恶化,寒与热相搏,息肉破溃渗血渗液,最终形成大肠癌。2)内因:体虚及先天不足因素。大肠癌形成,外感寒邪乃其外因,内因则为人体正气的亏虚以及情志、饮食失调。脏腑虚弱,正气不足,不能对抗邪气,邪气逐步侵袭体内。《灵枢·百病始生》篇云:“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正气不足是疾病发生的内在根据。情志因素。“其生于阴者奈何?忧思伤心;重寒伤肺;忿怒伤肝;醉以入房,汗出当风,伤脾;用力过度,若入房汗出浴则伤肾,此内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治之奈何?察其所痛,以知其应,有余不足,当补则补,当泻则泻”。忧愁思虑过度损伤人体的心气,外感寒邪,饮食寒冷损伤人体的肺气,忿恨恼怒过度,损伤人体的肝气,酒醉后房事,汗出后受风,损伤人体的脾气,用力过度,或房事出汗后洗澡,损伤人体的肾气。该条论述的就是因情绪诱因,发生于人体上、中、下部及内脏三部的疾病。大肠癌病本身高凝状态,情志不佳,长期肝郁气滞,气血经脉疏通不畅,病情加重。临床上能看到恶性肿瘤病人胸腹水及血流方面恶性度越高黏度高。肿瘤外邪以寒邪为基础,加之情绪不稳或者津液不足的身体虚弱协助,病情逐步进展[1]。
1.2 病名 《内经》的“积聚”病不一定是恶性肿瘤,应该解释为“在体表可触及包块统称的病”。如各种慢性病晚期肠梗阻、卵巢囊肿、饮食不佳引起的肠内或腹腔内气积,急性腹膜炎、阑尾炎、肠痈等。真正与大肠癌有关病名是肠瘤。《灵枢·刺节真邪》云:“虚邪之入于身也深,寒与热相搏,久留而内著,寒胜其热,则骨疼肉枯,热胜其寒,则烂肉腐肌为脓,内伤骨,内伤骨为骨蚀。有所疾前筋,筋屈不得伸,邪气局其间而不反,发为筋瘤。有所结,气归之,卫气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为肠瘤,久者数岁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结,气归之,津液留之,邪气中之,凝结日以易甚,连以聚居,为昔瘤,以手按之坚”。“肠瘤”即肉眼看出的“瘤”,其形成原因是虚邪和营卫气不畅所致,如果邪气结聚体内,气不流行而郁于内,卫气留滞而不能往复循行,津液不能输布而留聚,在肠与邪气相合,则形成肠瘤。这里“瘤”可以指现代医学的肠息肉。虽然中医解剖学比不上西医解剖学,但是《内经》原文明确使用“瘤”字,息肉形成原因是卫营不和,病位在肠道。“癌”字始见于宋代,故在《内经》记载时,大肠癌称为“肠覃”。《灵枢·水胀》云:“肠覃何如?歧伯曰: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得荣,因有所系,癖而内着,恶气乃起,瘜肉乃生。”覃通蕈,意即蘑菇,可见当时的医家就已认识到:大肠癌发病,最开始时是肠道内有类似蘑菇状的积块生长。
1.3 病机 《灵枢·百病始生》载:“气有定舍,因处为名,上下中外……,是故虚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肤。留尔不去,传舍于肠胃,在肠胃之时,贲响腹胀,多寒则肠鸣食泻,食不化,多热则溏出麋;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外,募原之间,留著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外邪伤人,首先侵犯皮肤,入侵后逐渐到达深部,邪在肠胃则出现肠鸣腹胀,若寒邪盛肠鸣,泄下不消化食物,饮食不消化;热邪盛则便溏如糜。邪气在肠胃留而不去,就传入到肠胃外面的募原之间,并在该处的血脉中留而不去,邪气与气血搏击长成积块。从虚邪开始邪气逐渐深入,到肠道留而不去,日久瘀不散不去而形成包块。病情逐步进展至晚期如下。《素问·玉机真脏论》记载:“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内通引肩项,期一月死,真脏见,乃予之期日”,大肠癌晚期,因恶液质,脏腑衰竭,可以出现大肉陷下、大骨枯槁的消瘦状态,以及腹痛、黄疸、肝肿大等症状,甚至出现无根、无胃气之真脏脉症状。此时患者的平均生存期基本不到3个月。如合并脑转移或者肺转移则生存时间更短。到这阶段无论中医、西医治疗疗效均有限。肿瘤的发生归结于癌毒致病,正气亏虚。由于外感四时不正之气、饮食不节、情志因素、先天性脏腑亏虚等各种病理因素的综合作用,酿成癌毒。侵袭人体,耗伤脏腑气血、津液,导致气滞、血瘀、痰凝、水饮等各种病邪,交结于肠道,形成癌肿[2]。癌毒的性质可表现为火郁热毒、寒凝、痰聚、湿浊、水饮、气滞、血瘀等。临床肿瘤种类繁多,病理性质各种各样,所处部位,所涉及部位的脏腑不同,表现的临床症状也不同。大肠癌的主要病机特点以湿浊、湿热蕴结、腑气不利为主,但是中医大家临床经验指出,这些邪气形成最基础是正虚、脾胃虚[3-4]。
2 辨证论治
2.1 治疗原则 《素问·五常政大论篇》载:“病在中而不实不坚,且聚且散,奈何?无积者求其藏,虚则补之,药以祛之,食以随之,行水渍之,和其中外,可使毕已。有毒无毒,服有约乎?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宜。大毒治病,十去气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气正也。不尽,行复入法。必先岁气,无伐无和。无盛盛,无虚虚,而遗人夭殃。无致邪,无失正,绝人长命”。即:如果病在中,无实邪坚积,有时聚而有形,有时散而有形,对于这种无积滞的病人,应当审察内脏的情况,精气虚的则用补法,若兼有表邪,可先用药去邪,随后用饮食调补,也可以用水渍法疏通其腠理经络,使其内外调和,就可以使疾病痊愈。药性峻烈的药物和药性平和的药物,服用有一定的规则,疾病有新久之分,处方有大小之别,根据药性的峻烈和平和,服用有一定的规律。凡药性非常峻烈、毒性很强的药物,病去十分之六,就不可再服,用药性比较峻烈的药物,病去十分之七,不可再服,即使是药性平和的药物,病去十分之九,也不必再服,以后就可以用五谷、肉类、果类、蔬菜等饮食作调养,使正气恢复,邪气尽去,不要过分使用药物,以免损伤正气。如果邪气未尽,可重复按上法服用,一定要了解岁气的太过或不及,不要误用药物而伤伐天真和平之气。不能用补法治疗盛实之症,不要用泻法治疗虚弱之症,而使生命遭殃。不要误补而致使邪气更盛,不要误泻而致使正气亡失,使人性命断绝。从而提示:第一,大肠癌化疗的原则,第二,化疗间隔时间适当的休息养生的重要性[5]。
另外,古代的“毒”概念与现代的“毒”概念不同[6],古代的“毒”是药物的偏性,偏性大即毒性大,现代“毒”是药物对人体的伤害,其概念比古代偏狭窄。《灵枢·刺节真邪》提出的“虚邪”,现代中医肿瘤学进一步发展至“癌毒”概念[7-8]。现代中医肿瘤学所讲的癌毒包含恶性肿瘤的侵润性及转移性,所以在辨证用药时加上解毒药,即细胞毒性的抗肿瘤中药,例如红豆杉、白花蛇舌草、半枝莲、半边莲、全蝎等抗肿瘤药。解毒药属于抗肿瘤药,无论中药,化疗药用药时不能以癌细胞消灭为疗效标准,应该考虑患者体质情况,避免严重消化道反应、骨髓抑制、免疫功能低下伴有感染等严重损伤正气。
2.2 辨证论治 中医的诊疗体系是建立在辨证论治体系上的,立法、处方、用药无不以临床证候病机为依据,肿瘤也不例外。肿瘤的中医治疗有两个方面:扶正祛邪,当有主次轻重,祛邪重在消除水饮、痰、瘀、郁、火、毒的凝结。肿瘤总属癌毒蕴结,气血失调,正气受损,但不同发病部位及患者素体差异,病理性质本虚标实,在初中末不同病、不同个体主次有别,原发性脏腑的肿瘤可影响相关他脏,随着病程进展,正愈虚,邪愈盛,至晚期正气耗竭,邪气独盛。所以必须以辨证为主导,根据患者不同的病位、体质、证候及病理因素,全面分析,综合考虑确定个体化的治疗思路,进行论治。一般大肠癌常规辨证为湿热蕴结证、寒湿凝滞证、肝肾阴虚证、气血两虚证[9-11]。
3 结语
总之,失去手术机会者,放化疗不能忍受者,或者放化疗后严重毒副作用所致身体虚弱者,通过中医用药抗肿瘤治疗后抑制病灶,提高正气体质,能明显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显示中医治疗肿瘤的优势。
[1]谭一松,何文彬.黄帝内经《灵枢》《素问》[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8.
[2]周仲瑛.周仲瑛医论选[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196-199.
[3]尤杰,刘嘉湘.扶正治癌学术思想初探[J].中华中医药学,2011,29(8):1829-1831.
[4]奚胜艳,岳利峰,李卫东,等.《黄帝内经》胃本源理论临床意义及对消化系统肿瘤防治的作用[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1,26(6):1267-1270.
[5]王素玲,郑爱平.调理脾胃在现代肿瘤治疗中的作用[J].中医药临床杂志,2008,20(6):563-564.
[6]孙朝润.中医学对“毒”的认识[J].中医研究,2011,24(9):1-3.
[7]王震.《黄帝内经》“虚邪”源流[J].西部中医药,2014,27(1):58-60.
[8]章永红,叶丽红,彭海燕,等.论癌症从虚毒治疗[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25(6):408-411.
[9]朱文君,戴建国.结肠癌的中医药治疗研究进展[J].吉林中医药,2013,33(5)535-537.
[10]杨维泓,周华妙,郭勇.中医药治疗大肠癌的探讨[J].吉林中医药,2011,31(6):521-522.
[11]孙桂芝.孙桂芝实用中医肿瘤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296-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