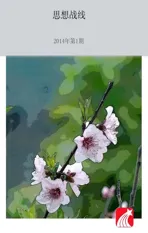“祖先在上”:我国传统文化遗续中的“崇高性”
——兼与巫鸿的“纪念碑性”商讨
2014-03-25彭兆荣
彭兆荣①
美籍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的经典著作《祖荫下:中国文化与人格》,[注]FRANCIS lk HSU(许烺光), Under the Ancestors'shadow: Chines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8.借用“荫庇”的隐喻,以突出中国文化传统和人格养育上的特征。“祖荫下”指活着的人离不开“祖先”的庇佑;祖先不仅以另一种方式“存在”,而且具有不可抗拒的“至高性”和“神圣性”。因此,我们也可以将“祖荫下”转换为“祖先在上”。这非文字转换,而是涉及中国传统亲属关系制度和社会结构,因为“中国的亲缘关系上追祖先,下至子孙;在时间上是一连线,在组织上是文化的基石”。[注]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台北:经联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53页。“上—下”贯通,“下”崇拜“上”,以保证传承的延续性;这一基本关系从不同角度、方向、层次“凸显”祖先之“实在”,它不独为这一“实在”的神圣化、秩序化和制度化的伦理阶序,同时又是代代相传、相承的无形文化遗产。
毫无疑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是“天人合一”。其自身不仅形成了一份完整的文化遗产,也融化在了认知、经验、知识、技术等各个层面,表现在自然与天道、精神与物质、德性与教化、伦理与秩序、有形与无形等整体的存在与延续上。品性上,“天人合一”集中表现为“崇高性”,并全面贯彻在文化遗产中。然而,近代以降,西方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技术主义、物质主义等的入侵,将我国传统“天人合一”的传承纽带拦腰截断,横亘出利益至上的价值趋势,致使崇高性受到严重侵蚀,中国社会也由此产生了许多历史上从未出现的问题。
崇高性涉及中国传统亲属制度和社会结构,从不同角度、方向、层次“凸显”祖先之“实在”,因为中国的亲属关系是“上追祖先,下至子孙”,这种延续性的关系被称为“世交”;这种从“绝地天通”(《国语》)的原始而变为“天人感应”的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先验性所决定的。[注]参见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台北:经联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51~53页。它既是神圣化、秩序化和制度化的物质形态,同时又是代代相传的无形文化遗产——这是中国人认识“文化遗产”的本义,建立在“天人合一”的世系延续性之上。西方文化的特质是分裂、断裂和“破裂”(rupture)的。[注]参见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台北:经联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51页。因此,文化遗产中的延续性成为我们检视的重要视点。我们将文化遗续中的这种凸显至上的特点、品性和原则总结为“崇高性”。
“崇高”二字为同义词汇,《说文》释:“高,崇也。”甲骨文形“”,其形意不言自明。[注]王心怡:《商周图形文字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89页。借《诗·小雅》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可为概括。作为一个原则,崇高性的表现形态复杂多样:自然高耸山岳在视觉上被赋予“天”(“载天”)神秘而神圣的经验和认知;君王“天命神授”的政治意图与之契合,“帝王—天子”由此成为“家天下”无可置疑的权力和权威,构成了中国传统等级社会金字塔建制必需和具备的核心部分;而“以德配天”又是帝王政治作为的一个检验指标,“德高望重”为必备品质和功业;崇高性承担着“祖—宗—社”的伦理周转遗袭,并以礼制形态一脉相承;人们以特殊的礼仪方式与祖先达成“先验—经验”与“和谐—践行”关系,进而化作社会常伦和道德明鉴,即“祖先在上”。
这也因此成为我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一个理解理路、阐释路径和表述路数,即“凸显范式”——以具体、有形、外在、物质的“突出”形态和形体为视觉对象和经验感受,具体形态表现在诸如“山岳”、“祖社”、“祭台(坛)”、“丘墟”、“树碑”等一系列带有“崇高性”的价值依附,并由此生成超越“有形”的“无形性”(intangibility)表示、表达与表述。[注]A. Kearney, “Global Awareness and Local Interest”, In Laurajane Smith and Natsuko Akagawa(eds.) ,Intangible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87,p.210.
当我们将崇高性的“凸显范式”置于更大的维度时发现:崇高性远不只表现在现世与祖先之间的简单关系,它是中国人民自古而下的一种思维形态,是祖先认知世界的一种经验智慧,是中国特色的知识体制的内在结构,是建筑中国传统礼制的奠基石,形成了一个以崇高性为核心价值的无形文化遗产的传承机制。本文以几个关键词为线索,通过特殊知识考古的方式管窥崇高性无所不在的品性与特质,兼与巫鸿先生的“纪念碑性”商讨。
“祖(宗)”、“社”的崇高性务实
毫无疑义,“祖”是阐释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它与“宗”、“社”等组合成为理解历史遗产的一组连带性关键词。“祖”在甲骨文中多作“”,即与“且”通,是一个常用词汇。比如1976年12月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公社出土的古遗址,发掘出商周青铜器“史墙盘”(“史墙”,人名,史是官名,子姓,名墙)铭文之二共有135个刻符,“且”符就有5个之多;开句便是“青幽高且”(沉静深远的高祖),[注]且即祖,卜辞习见。高祖在此指远祖。史墙盘之铭文所述为具体氏族,即微氏家族。此铭自高祖之下,尚有烈祖、乙祖、亚祖、文考,至墙已六代。参见马如森《商周铭文选注译》“史墙盘”之注(69),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2页、第184页;《商周金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52页之注(28)。铭文中还有“剌且”(烈祖)、“亚且”、“乙且”等。[注]参见马如森《商周铭文选注译》“史墙盘”之注(69),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1~174页。这些不同的名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亲属称谓和制度雏形,诸如“高祖”、“始祖”、“远祖”、“烈祖”等在后世的传承中皆泛指祖先。“祖”有特指和泛指,现代的“祖”指父亲的上一辈,如祖父,如需明确则可加诸如伯祖、叔祖等,至于更远的辈分则用高祖、远祖通称;泛指则可以通称远古的祖先。但在商周卜辞中的“且”则是一切祖的通称,其辈分顺序以十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名。[注]赵 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1页。
“祖”有字源、字形的注释历来为方家所热衷,其中它与生殖崇拜的意象虽然存在争论,但视觉上的形体和形态已非训诂和考据可以完全解释,人们只要观察一下古代的祖形崇拜物便无法反对“且”及“祖”的生殖意象。[注]参见凌纯声《中国古代神主与阴阳性器崇拜》,《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59年第8期;安志敏《一九五二年秋季郑州二里冈发掘记》,《考古学报》1954年第8期;许进雄《中国古代社会:文字与人类学的透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70页。这类形态、材料以及对材料的解释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考古工作者甚至认为,管形神器是对男性生殖器官的模拟和尊崇,在祭祀时是祖先的象征。[注]参见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224~229页;邵学海《先秦艺术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第111页。作为“公理”,生殖、生产是人类生存和生计的首要事务,祈求丰产属于人类的基本需求,而这一意象在父系制社会里便会得到合理的表现和表达。不过,与“帝”一样,其中仍需有更细致的材料和更充分的解释将史前的关系厘清,特别是氏族社会史所涉及的相关问题,毕竟形态只是对形态的自然描述。
祖先作为一种特殊的灵魂形式存在于天,俯视人间世道;“祖先在上”,不仅掌控人们的现世生活,更在指导和左右人们的世代生活。“世代”原本即为传承,故有“世代传承”之言。因此,这种传承价值观念不仅像一面镜子时刻观照人世,其方式也就蕴含了不间断的实践意义,民间的“天地君亲师”高悬正厅不啻为一种无形的“凸显”格局,检验、鉴定凡间人情世故、行为举止等一切事务,形成高高在上的统摄力量;同时庇佑亲属后人,维护社会秩序,并成为世世代代传承的“公正”与“公证”。
与祖先的沟通和交流最具代表性的方式即祭祀活动。“祖”与“宗”原本即是祭祀方式(禘、郊、祖、宗、报为我国古代基本的五种祭祀形式),通常配合使用,强调规定的形式与行为。“示”(甲骨文,其象用两块大石头搭起祭台形),《说文·示部》释:“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上);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可知其本义为祭祀上天,即“禘”。天、地、人在传统观念中相互通缀,《礼记·丧服小记》有“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说明王者禘祭是崇拜诞育他们始祖的天帝,所以以祖配天,而立高曾祖祢四个庙。[注]参见王云五《礼记今注今译》,王梦鸥注释,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台湾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87页。
“祖”与“社”存在密切关系,或者说二者具有同源性。有学者认为,宜与祖古本一字,宜社亦即所谓“出祖释祓”,《左传》谓之“祓社”。《尔雅》所谓“宜于社”即“俎于社”,而“祓礼”也就是祖道之礼。[注]参见丁 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499~501页。《尚书·甘誓》:“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礼记·祭法》:“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白虎通·社稷》释之曰:“大社,为天下报功;王社,为京师报功。大社尊于王社,土地久故而报之。”据学者考释,殷商时期的亳社为成汤故居,亳社也叫蒲社,王国维译作邦社,其为冢土。古以土为社;邦土,亦即祭之国社。[注]参见丁 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45~47页。我国自古有“家天下”的传统,构成今日“中华民族”之“天下共祖”的理念渊源。而“家”是一个家长制宗法等级秩序下的各种“分”的原则(分封、分社、分支等),这一切都围绕着“土地”,为“乡土中国”的“本色”。[注]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页。“祖—社”同构。
“社”为“地方”(与“天圆”对应“地方”的结构),“四方”自然成了“社”的维度范畴,因此,四方神与社神为不同的神祇,二者皆重要。《诗经·小雅》:“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诗经·大雅》有:“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则不我虞。”丁山因此认为,“后土为社”,应祀于社壝之上,不必再祭于“四坎坛”。[注]参见丁 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101页。“以四方之神合祭于邦社,恰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的‘五行之官,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祀四方于社稷之典相合。足见四方之神,在商、周王朝的祭典里,本属地界,不隶天空……当是祭四方于社稷的遗制,与天神无涉。”[注]丁 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169~170页。四方之神在《国语·越语下》中亦称“四乡地主”,云:“(王命)环会稽三百里者为范蠡地……皇天后土,四乡地主正之。”韦解:“乡,方也。”四方神主,见于盟誓。[注]丁 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157页。
总之,“祖”与“社”是两个链接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词,二者不独相互关涉,且各自支撑着“祖国—祖宗—祖籍”,“社稷—社会—社火”从大至小的单位表述。 若“祖先在上”的崇高性具有“正名”的意义和意思的话,那么,这种崇高性的“务实”在“祖—社”的社会结构中得到了完整、完满的实现。
“丘”与“墟”:崇高的“形意之合”
“祖先在上”的“无形”与现实中的“有形”是相通缀的。在传统文化认知中,高山与“天”有着密切而神秘的关联,甚至认为是一体性的,如所谓“载天”。《山海经·大荒北经》和《海外北经》中在言及优父逐日中有:“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山海经·大荒北经》);“成都载天”虽为山名,却有形意之合;高山“载天”完全符合直觉和经验认知,这虽可归入原始思维范畴,[注]在西方人类学史和思想史中,“原始思维”(列维-布留尔),有学者称为“野性思维”,如列维-思特劳斯;“神话思维”,如卡西尔;还有“前逻辑思维”等,名称不同,所指则共通。却鲜明而生动地将因山高“载天”转化和转变为崇高价值与意识,并用以指导生活。在考古遗址中出土不少相关的器物符号,如河姆渡遗址、良渚遗址出土的一些文物中的骨器、牙器上刻有“日月山”的符号,学者译之为“炅山”,“炅”是太阳的光芒,“炅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注]参见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页。“崇高”之“崇”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表述,《说文》:“崇,嵬高也,从山,宗声。”“嵬”指高双耸立,原即指高山。在甲骨文中表示神、祖或已故之父王暗中施予的各种吉凶。[注]参见赵 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85页、第326页。
在人们的经验中,太阳的升起仿佛出自山顶,比如文物中就有“”的符号,用于表示“日”(古文字学释之为“旦”)。若以崇拜太阳为依据有“祭日”说,古代的太阳神崇拜以及祭祀仪式全世界极为普遍,叶舒宪认为,我国古文字符号是以“日”为关键字形而成为宇宙认知模式的结构素。[注]参见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0页。有些学者根据我国古代陶器上最有代表性太阳纹的“宗日式陶器”为据,概之以“宗日文化”。[注]20世纪90年代末,在青海省同德县发掘出一个古墓葬遗址,发掘出大量陶器,而陶纹以太阳纹为常见,并以遗址之地名“宗日”(藏语“人群聚集的地方”)命名为“宗日文化”。参见刘宝山《黄河流域史前考古与传说时代》,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112页。在同类的符号中,“”很特别(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的几件大汶口文化作为祭器使用的大陶尊,代表性符号就是“”),符号的基本意思是“日”和“山”——太阳从山峰上升起的情况。[注]参见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史前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72~173页。此图像符号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有认为“上日中云下山”,或为“旦”(于省吾);有认为此符为“炅”,释之“上为日中为火下为山”(唐兰);有认为是祭祀的法器(高广仁);有认为此符代表先民自然崇拜。[注]参见汤贵仁《泰山封禅与祭祀》,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第10页。大家对于符号上部为日月的争论不大,争论较多者主要在下部,有的认为是山丘,有的认为是祭坛。其实二者不悖。[注]参见刘宝山《黄河流域史前考古与传说时代》,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117页。笔者识,无论崇日月抑或崇山岳,皆属崇高,此符乃以具象之形表达崇高之意。
“丘”是“山”的一种特指的形态,《礼记·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丘在甲骨文中是一座小山,《说文·丘部》释:“丘,土之高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昆仑东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象形。”注:“土高曰丘”,“非人所为也”。有学者认为它特指河川两旁的台地形。[注]许进雄:《中国古代社会:文字与人类学的透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2页。“土”、“山”、 “且”、“”[注]《说文·部》释:“,小(阜)也,象形。释为小山堆,即‘堆’的本义。”参见谷衍奎《汉字源流字典》,北京:语文出版社,2008年,第289页。等部在形态上皆呈凸显。[注]王心怡:《商周图形文字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53页、第256页。所以,筑台的历史在我国可谓久远。在已发现的若干原始社会晚期,诸如辽宁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江南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等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类型的台、坛遗迹,较早的可追溯到5 500年以前。从这些原始遗址的情况看,早期的人民对天敬畏和原始崇拜之故,筑台是原始信仰的表达。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筑台遗址看,多根据山地环境而筑建,有山岳崇高的象征性意味;至殷商时期,除保留宗教祭祀的崇高性活动外,开始修建园林设置。[注]参见杨鸿勋《园林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山丘是自然高耸的实体,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古代重要的遗址和祭祀地大多见于神山圣岳的缘故,山岳有时也可以代表神灵而与人类交通、咨询。基于同样的理由,古代帝王的生、居、死等也经常与丘岳有关。《史记·夏本纪》:“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嗟,然!’”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居轩辕之丘”,“黄帝崩,葬桥山”。[注]以上参见《史记·夏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页;《史记·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页。《史记·封禅书》: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尚书》曰,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皆如岱宗之礼。中岳,嵩高也。[注]《史记·封神书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55~1356页。
短短的一段话,将三山五岳的重要神性一并囊括。至于“崇”、“岱宗”、“嵩高”(即中岳嵩山)等崇高之意表露无遗。换言之,上帝和祖先喜倚山而居,山丘也就成了与天沟通的媒介,张光直曾经这样论述:
中国古代巫师沟通天地时所用的工具与全世界萨满式文化使用的工具大致相同。这些工具可以举出来的第一个是神山。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有五座神山,这在《史记·封禅书》里有最早的完整的记载。《山海经》里提到几座山,特别讲到巫师上下这些山的情况。当中有个登葆山,是“群巫所从上下也”……《山海经》中还有:“灵山……十巫从此升降”,“肇山,有人名曰柏高,柏高上下在此,至于天”等等。……可以看出山是中国古代一个通天的工具。[注][美]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7页。
“居丘”由此形成了一种价值,民众亦从其范。胡厚宣等在《殷商史》中有“殷商民众之居丘”的说明,殷卜辞中的地名,凡举某京、某、某丘、某山、某麓者,皆有高亢之义。[注]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9~321页。“墟”常作“大墟”解。《吕氏春秋·贵言》:“使人之朝不草而国为墟。”注:“墟,丘墟也。”墟也就是“故城”。《吕氏春秋·古乐》载:“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故有“都帝丘”之谓。
就“国家”建设的雏形看,“帝丘”为重者。《帝王世纪》:“始都穷桑,徏商丘(帝丘),于周为卫。”《左传·昭公十七年》:“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杜预注:“卫,今濮阳县,昔帝颛顼居之,其城内有颛顼冢”,是为氏族聚落之原始城建的造型。[注]参见雷从云,陈绍棣等《中国宫殿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5页。历史上周朝立有所谓“凤鸣岐山”之说。在古代,新王朝的建国立都一方面综合考虑当时的历史情形,特别是与周边民族间的战争因素,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根据“天意”。当时周武王为在何处立都一事曾“自夜不寐”(《史记·周本纪》),《逸周书·度邑解》说武王专此到洛水至伊水下游一带,因其地势向阳,是夏人旧居之地,遥望河、岳,靠近天室嵩山,可以在此管理国家,这便是“岐山”。[注]参见张天恩《宗周文物与西周社会》,载《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馆(台湾),2012年,第299页。《诗经·颂·清庙之什》:“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周颂·天作》亦有:“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其中对“天作高山”之“高山”,学者们共识为岐山,只是对岐山所处的地理位置有不同的争议。[注]有关情况可参见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8~53页。另外,古之帝王建国立基以城邑为核心,而城郭的建设在原始时期则以平原或高地突兀处进行。简言之,在传统的中国自然与文化遗产体系中,“丘”、“墟”形成了特殊的形制表述。
“纪念碑性”与“崇高性”之对话
巫鸿先生曾经提出一个概念:“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纪念碑性”来自于纪念碑,二者的差异在于:
“纪念碑性”和“纪念碑”(monument)这两个概念都源自于拉丁文monumentum,本意是提醒和告诫。我的讨论中,“纪念碑性”(在《新韦伯斯特国际英文词典》中定义为“纪念的状态和内涵”[注]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s.v.“monumeniality”.(原注))是指纪念碑的功能及其持续;但一座“纪念碑”即使在丧失了这种功能和教育意义后仍然可以在物质意义上存在。“纪念碑性”和“纪念碑”之间的关系因此类似于“内容”和“形式”的联系。由此可以认为,只有一座具有明确“纪念性”的纪念碑才是一座有内容和功能的纪念碑。因此,“纪念碑性”和回忆、延续以及政治、种族或宗教教义有关。“纪念碑性”的具体内涵决定了纪念碑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意义。……我国并不存在一个可以明确称为标准式的“中国纪念碑”的东西,换言之,我对纪念碑性的不同概念及其历史联系的有关讨论有助于我对中国古代纪念碑多样性的判定。……于是出现了两个历史——“纪念碑性的历史”和“纪念碑的历史”——综合入一个统一叙事。[注][美]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李清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文版序”第5页。
巫先生曾以“九鼎”为例证明“纪念碑性”,认为“九鼎”有3层意义:(1)铸九鼎以求对国家形态之中央政权的认可与合法化——确立王朝的“纪念碑”意义;(2)通过对历史事件记忆的形态化将既定后果“合法化”,赋予九鼎政治权力的象征意义;(3)铸造与拥有九鼎意味着“天命的所有者”。[注][美]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李清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因此,对河南安阳出土的一块公元前13世纪的卜铭文:“乙巳卜,贞,丘出鼎”(乙巳那天,一个叫的王室卜者问先灵,丘中可否出现鼎?),[注]彭邦炯,谢 济等:《甲骨文合集 补编》第3册,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第8388片,第887页。巫鸿的解释偏向于认为,鼎为宝藏,而丘则为古代庙堂。“墟”与“丘”(包括“台”等)都属于中国古代的“废墟”观念,即过往的建筑已经消失,留下了历史的废墟(主体已经荡然无存),而西方教堂的“废墟感”(ruination)使之成为“完美的废墟”。[注][美]巫鸿:《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1~33页。
笔者认为,以中西方历史建筑遗存比较作此评述值得商讨。巫鸿将中国的“丘”、“墟”、“台”等视为“废墟”是一种取其形而去其意的判断。就词义论,“丘”确有“废墟”之义(丘与虚、墟作同义连用),但中文语境中的“废墟”指“非人所为也”,这在《说文》中已阐明,甚至连昆仑都在其列。西方的“废墟”在所谓的“主体性”方面则完全不同,更莫说其与“丘出鼎”的卜辞不合,与我国传统的历史事实、历史价值和历史认知皆不合,尽管可能其中存在“ruin”、“ruination”与“废墟”在翻译上概念不尽相同、语义不全吻合的问题;但这些都是相对次要的问题,根本的原因在于,即使具有相同、相似的“能指性”遗墟、文物,但中西方完全不同,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礼仪传统、等级阶序森严、亲属结构特殊、继嗣制度严格,以农业伦理为本的社会,任何具有历史性纪念和记忆性的遗墟、遗址、遗物都“不可废”;“废”意味着“中断”、“死亡”、“丢弃”和“非永续”。这与西方强调具有纪念性意义及事件和事物却并不讲究传承关系的“废墟”有着重大差异。
大致而言,对于废墟的时间性同样也包含着几种异质性:(1)祖先经验智慧之大者来自于对自然的观察、体验和认知,人们除了在高山大象之形中表达崇高外,日、月及天地周转给了人类生命轮回的启示,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即以日月星辰为依据,“时辰”也因此而来。我国神话“羲和观日”即作说明,《尚书·尧典》中说,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而这一传闻在我国许多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注]卢嘉锡,席泽宗:《中国科学技术史》(彩色插图),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祥云(美国)出版公司联合出版,1997年,第19页。它不仅涉及我国的历法,还涉及“时”的特殊性。这也是为什么崇高性在中国表现为天地人、生死的周转。(2)中国的实物遗存其实并非最为重要,无论是石质的还是木质的,重要的是借其表达另一种崇高的形态——永恒性。永恒性也包含一种特殊的纪念——无论是实物遗留还是已经化为“废墟”的,都不妨碍其具有“纪念性”,但纪念性只是崇高性的一种说明和表述;其具体的表现形态是:以一个在空间上凸显的具体,将流逝的时间固化,以突出“不朽”、“永恒”。(3)说中国传统的“废墟”是建立在木质建筑消失后的“虚无”之上也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在中国仍然存在大量丘陵、石坛等石质遗存,特别是以夯土形制的遗存,它们多被当做纪念物。我们只要到西安的碑林做一番探访就会发现,历史上的“石质碑文”足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性博物志叙事体系。(4)中国传统中的祭祀活动需要有诸如“台”、“坛”一类的场所,其中要者皆为祭礼遗产,它们以纪念为名实践社会常伦。另外,作为对祖先和亡灵的处置方式(比如丧葬和吊祭形制)所遗留的“丘”、“墟”、“碑”等,都以凸显范式表达崇高性。
笔者所以强调“崇高性”,主要原因在于,在中国历史上崇高性存在着一条明显和明确的由神圣到世俗的演化轨迹,这与朝代更迭,外来因素影响有关,特别是崇高性原本是建立在服务于社会生活,确立帝王权威、礼化阶序、常伦规约,监督日常实践等功能。至为重要者,西方“纪念碑性”的核心是人,即“人本”的价值,而中国“崇高性”的人的思想在于沟通天地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注]王尔敏:《中国古代于地人之齐等观念》,载王尔敏《先民的智慧——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经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1页。“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构造。季羡林先生据此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天与人配合,所以“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注]季羡林:《“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创刊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9~16页。
小 结
如果我们将欧洲和中国的文化遗产中的某些类型做一个比较,比如欧洲有许多的“凯旋门”类的文化遗产,[注]巫鸿在解说“纪念碑性”时所采用的第一幅图像就是凯旋门。参见[美]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李清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而我国没有凯旋门,却存在大量以山(诸如:泰山、黄山、武陵源、武当山、庐山、峨眉山、武夷山、青城山、三清山、五台山、嵩山等)为类型、为名目的世界遗产。[注]它们以“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混合遗产”、“古建筑群”等不同名目获得,如果加上另外还有一些以地质特点为主的世界遗产名录就更多。不言而喻,凯旋门的“纪念碑性”强调对战争(历史战争事件)、英雄武功,特别是将“胜利”(甚至“正义”都并非必需的条件)作为“生命史”的赞颂和纪念。而我国以山为核心价值的突出和凸显,却刻意于天人合一的崇高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天下体系”。如果说“天下体系”的原则是“无外”,[注]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41页。即强调天下大同的话,那么西方借以“帝国”传统建立起的现代“帝国主义”的理想,则是“以一国而统治世界”——秉承的哲学精神是“以部分支配整体”的霸权。[注]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页。二者所建立和经历的认识论有着重大的差异,可以说,差异是表达性的,更是思维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