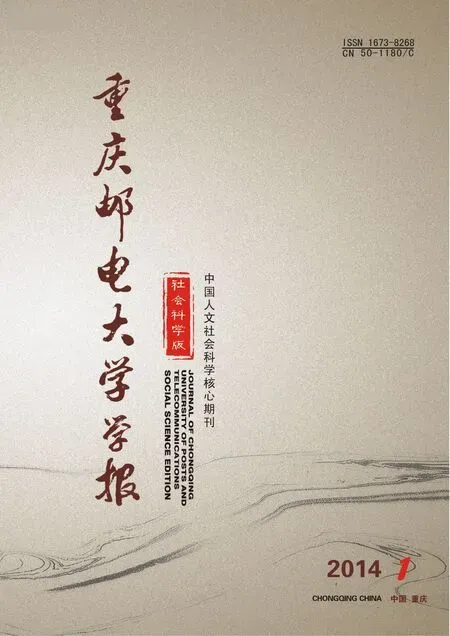“瘫痪”主题下《都柏林人》儿童篇中的叙事策略研究*
2014-03-25董梅
董 梅
(四川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外语系,四川 雅安625014)
从1904年第一则故事《姐妹们》问世,到1914年整个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在伦敦出版,詹姆斯·乔伊斯用十五个故事把那个时代爱尔兰的风土人情展示在了世人面前。他除短暂时间住在爱尔兰外,大部分时间在瑞士、意大利和法国度过,但还是把他所有的作品都定位在了爱尔兰,《都柏林人》也不例外。按照乔伊斯的说法,《都柏林人》依赖用童年、青年、成年和公共生活四个方面谱写出一章“故国的道德史”的意图,形成一个艺术的统一体[1]249。
细读《都柏林人》中的每一个故事,无一不透露出遗憾和惋惜。生活在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男女老少都有自己的追求和梦想,然而,在现实的冲击下,他们最终遭遇的都是无奈和遗憾。这里的都柏林是一个瘫痪的世界,正如乔伊斯本人在谈论《都柏林人》时所说:“我选择都柏林作为场景,乃是因为在我看来,这里是瘫痪的中心。”[1]2这里的瘫痪,不是一种单纯的肉体或者物质的瘫痪,而是一种精神的瘫痪。
作为《都柏林人》的第一个部分,儿童篇中的三个故事,即《都柏林人》的前三个故事——《姐妹们》、《遭遇》和《阿拉比》,乔伊斯虽然从儿童的视角对其进行叙述,却也一样用他特别的叙事策略把“瘫痪”这一主题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在乔伊斯书写《都柏林人》的众多叙事策略中,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策略和双空间叙事策略在其儿童篇中显得尤为突出。
一、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策略
在《叙事话语》中,热奈特将叙事模式分为三大类:一是零聚焦模式,即无固定观察角度的全知叙述,其特点是叙述者说的比任何人物知道的都多;二是内聚焦模式,即固定式人物或者变换式人物或者多重式人物的有限视角,其特点为叙述者仅说出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三是外聚焦叙事,即仅从外部客观观察人物的言行,不透视人物的内心[2]97。
《都柏林人》十五个故事当中,虽然从第四个故事开始都是用第三人称的视角进行描述,但是儿童篇中的三个故事却全部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三个故事中的“我”作为处于童年的男孩,对故事所涉及的人、事作了全面的讲述。这是从固定人物的有限视角来谈论事件,属典型内聚焦叙事模式。
梅洛·庞蒂对笛卡尔的“我思”进行了批判,提出“真正的我思”是我存在于世界当中,可以揭示出我与世界的一种深刻的联系,即主体在感知世界的时候,他可以怀疑投入的情感,但不能怀疑“投入的意识”本身,因为投入的意识构成其实际存在的意义[3]。作为第一人称的“我”进入叙事,展示出“我”作为主体而感知的世界,这种意识的投入构成的存在是可信的。
由于采纳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模式,《都柏林人》的儿童篇中的“我”生动地再现了作为都柏林的一员对那时那刻的都柏林市民生活的真切感受。作为童年时期的小男孩,第一人称视角下的“我”的叙述和感受会受到年龄和经验的限制,许多成年人理解的事,“我”只能感受,却未必能体会。但是,正是童年的天真规避了成年人对于事物的修饰,加深了描述的真实性。
《姐妹们》开篇就是“我”对弗林神父的担忧:“他曾常常对我讲:‘我在今世待不久了。’而我却以为他的话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明白这些话原是当真的。”[4]3这即将来临的死亡在“我”心目中唤醒的是对于“瘫痪”的思考——“夜夜我抬头凝视着那扇窗,轻轻自言自语‘瘫痪’”[4]3。作为成年人的姨父和老科特肯定了弗林教父的死亡,但是,在宗教承担着重要角色的都柏林,教父的死却没有带给他们任何遗憾。相反,老科特毫不支持自己的孩子和他有任何交流,姨父对老科特的意见也表示了支持。他们的交流表达的是对“我”和弗林教父交往的不满。作为他们交流的倾听者,“我”不能理解大人们要表达的准确含义,因为他们在“我”面前谈论弗林教父时总是用一些不完整的句子,内聚焦视角下处在童年的“我”没有能力补充完整这些句子。最终,“我”只能以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身份将其原话展示给众人,却没有丝毫的话语权——从故事开始到结束,“我”的每一个想法都得到了展现,却一直处在失语状态。虽然“我”只是在一次交流中失语了,却由此影射出的是生活中“我”和家人或者长辈交流的瘫痪状态。连基本的表达意愿的机会都没有,“我”只能在精神上寻找寄托,而精神上的最好寄托就是宗教信仰,对于“我”而言,那就是和弗林教父的交往。在“我”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弗林和“我”确实有过较多的交流,“他曾经教了我很多东西”,至少,我曾经回答过他很多问题,虽然是“吞吞吐吐”的,“我”也曾背诵他让我用心学的经文[4]6。可是,这个精神寄托的对象却在故事一开始就面对了死亡,受到了成人们的批判。《姐妹们》中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下的“我”,不仅体会了和成人交流的瘫痪状态,随着精神寄托——弗林神父的死亡,“我”的宗教信仰也进入了瘫痪状态。
《遭遇》中的“我”也有着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过这里的“我”不再是那个在长辈们喋喋不休面前没有任何发言机会的小男孩了,和“我”相处的是同辈人,而且,在这群人中间,“我”拥有了自己的发言权,不再失语。在众多同伴中作出逃学决定的人只有三个,“我”是其中之一。虽然“我”的言语不多,话语也没有马奥尼或者狄龙来得果断,但是,“我”可以发言,拥有了自己做决定的权利。这个故事描述的背景是学校,是提升意识和满足精神需求的地方。在这里,有着正统的精神食粮的传递,巴特勒神父会在学校聆听“我们背诵罗马历史的四页书”[4]13。同时,也有狄龙带着“我们”去了解“西大荒”的离奇和神秘,甚至扮演其中的印第安人之类的角色。这样的经典文化和荒野文化的冲突,是超乎“我”这样的儿童的理解力的。第一人称视角下的“我”虽然不是这个冲突的始作俑者,却是这个冲突的切身体会者。内聚焦视野下,“我”不知道作为经典文化传承者的教师和作为荒野文化传递者的狄龙对于这个冲突的产生有着什么样的认识和体会,但是“我”能真实地描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感受。狄龙绝对不是一个正统的好学生——“他实在玩得太凶,他看上去倒是有那么一点印第安人的样子,满园子蹦来蹦去”[4]12。在狄龙的带领下,“我们把教养和天性的差异搁置一边,有些人是为了显示胆量,有些人是为了玩闹,还有些人是心怀恐惧”,而印第安人的“我”,就属于“心怀恐惧”的一类[4]12。这里的恐惧不是一种怯懦的表现,那是作为儿童的“我”遭遇古板而无趣的正统文化和神秘而有趣的荒野文化的冲突时的矛盾心理的体现。这种不能抗拒西大荒的吸引却又了解它对于正统文化的颠覆带来的矛盾心理论证了“我”在理智上还是接受传统观念、尊重学校教育的人。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冲破学校生活的枯燥乏味,至少要冲破一天”,和马奥尼以及狄龙一起逃学了[4]14。更有甚者,连狄龙这个“罪魁祸首”最后都没有勇气真正逃课,而“我”不仅将逃课付诸了实践,并且是第一个到达相约逃课地点的人。《遭遇》中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下的“我”,最终放弃了按规定和实践走进传递正统文化的学校,随着哪怕只是一天的逃学计划的实施,正统教学的效应在“我”这里进入了瘫痪状态。
当和家人及长辈们的交流不能顺利进行,宗教信仰和传递正统文化的教育都进入瘫痪状态时,外部的精神依托也就瘫痪了,这种情况下,就只能找寻精神寄托了。《阿拉比》中的“我”似乎找到了精神支柱,“我”在玩伴的亲人中找到了一个内心仰慕的对象——曼根的姐姐。“我总让自己眼中有她棕褐的身影,……就算在最不适合想入非非的地方,她的形象也伴随着我。”[4]22这里的“我”只是一个处在童年期的小男孩,对于男女之间的情感不可能有很深的了解,借助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我”把这种少年的懵懂情感生动地展示了出来。“我这躯体就像一架竖琴,她的一言一笑、一举手一投足就像在琴弦上划过的手指”,“我”会躺在前厅的地板上透过百叶窗的空隙看她[4]22。可是,她一开口和“我”说话,“我就茫然得都不知该怎样回答她才好”[4]23。最终,“我”鼓足了勇气和她交流,得知她很羡慕“我”能去阿拉比集市,“我”立马许下了诺言——“要是我去的话,我给你带回点好东西”[4]24。内聚焦视野下的“我”没有办法了解曼根姐姐内心的想法,却坚持要想办法兑现自己的承诺。这种看来盲目的行为其实最贴近于真实的情感——这种情感在施予方心中是神圣的,而对接受方的内心却又只能是揣测。此刻的“我”因为情感的驱动多了一些主动,提出周六晚上去集市的请求。虽然连“婶婶都吃了一惊”,“我”还是坚持要去集市的愿望获得了叔父的同意,我激动得几乎没有了严肃生活的耐心[4]24。能提出基于自己需求的愿望并坚持得到长辈的应允,是第一人称视角下“我”的一大进步。可是,到了星期六的早上,尽管叔父在“我”提醒他的时候说:“行啦,孩子,我知道啦”,他还是在晚上九点钟才回家,并且忘记了“我”的请求[4]25,因此,“我”只能在晚上才去了集市,而此时的集市已经基本散去了,“我”没有买到心仪的礼物。最终,《阿拉比》中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下的“我”,由于叔父简单的不经意终结了自己热切的愿望,“我”内心情感的寄托也就如其他一般进入了瘫痪状态。
二、双空间叙事策略
每个故事都有发生的地点和由其中人物讲述自己感受和事件的地点,地点的概念充斥在每部小说中。叙事中的地点和空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如杰弗里·R·斯密顿所说:“只要环境能从人的控制中脱离开来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就是说当地点具有自己的力量和意义,那么该叙事可称为空间叙事。”[5]
乔伊斯的所有作品故事的发生地点都是在爱尔兰,无一例外。直接以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命名的《都柏林人》更是把乔伊斯对地点的重视体现到了极致。正是在这里,形形色色的都柏林人和事都找到了自己的叙事空间,展示着自己的力量和意义。基于这个大空间背景,《都柏林人》中的每个故事都涉及到小地点的转换,而在作为儿童篇的前三个故事中的地点转换更以双空间叙事特点被展示了出来。
乔伊斯在创作《都柏林人》时曾说:“我正在写一系列‘求降显灵文’……我给这一系列取名为《都柏林人》,我要暴露血液麻痹,即瘫痪的灵魂,也就是许多人称之为一个城市的灵魂。”[6]所谓的求降显灵文是对基督教求降显灵仪式的笔误,在《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初稿中,乔伊斯称其为“顿悟”并对其作了界定——“所谓顿悟,是突然的精神感悟。不管是通俗的言词,还是平常的手势,或是一种值得记忆的心境,都可以引发顿悟”[7]。《都柏林人》所有的故事确实都充分展示了这种精神顿悟所产生的效果,儿童篇的三个故事自然也不例外。顿悟显然需要在某个时间点上有思想的转变,而在《都柏林人》儿童篇对其的展示中,这个时间点往往出现在两个叙事空间的转换中。
在《故事与话语》中,叙事学家查特曼首次提出了“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这两个概念。他认为,“故事空间”指事件发生的场所或地点,“话语空间”则是叙述行为发生的场所或环境[2]129。《都柏林人》儿童篇的故事正是在“话语空间”和“故事空间”的交替叙事中进行的。
《姐妹们》中对弗林神父的引入是姨父和老科特在餐桌上对他死亡这个事情的叙述和探讨,而“我”作为该叙事的主要对象,虽然只字未说,却也在这个话语空间中回忆和思索着有关弗林神父的一切。其实,“我”的失语并非是因为餐桌上的人剥夺了“我”的话语权,而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有巨大差异性。老科特谈论弗林神父的话语半遮半掩,毫不清晰。看到他在审视“我”,“我”连抬头来满足他的兴趣都没有,“我”对他意见的不能苟同最后达到了在心中诅咒他的程度——“红鼻头的老蠢货,真讨厌”[4]7。终于到了独自安静地上床休息的时间,“我”却不能正常入睡了,“在黑暗的房间中我想象着又看到了那瘫痪病人忧郁灰暗的脸庞”[4]7。这张脸一直追着“我”,“我”却没有那种对活着的人所产生的厌恶感,也没有那种对逝去的人所产生的恐惧感,反而是一种愿意了解它的心态。“我明白它很想忏悔什么事”,甚至在想起它已经死于瘫痪后,“我感觉我也无力地微笑起来”[4]5。对活着的人,“我”没有信任感,对于他们传递的弗林教父死去的消息,哪怕他们已经讨论了那么久,“我”也要在次日看到系着黑绉纱的花束的丝带下的卡片才相信。对于想象中的一个死去的人,“我”充满了理解和同情。在家这个话语空间里,“我”追寻着昔日和弗林神父交往的点点滴滴,“他曾经教会我正确的拉丁文发音”,“有时候他为了给自己取乐就拿问题来为难我”,“在我背诵经文的时候,他就常常沉思地微笑并点点头”[4]7。这个被成人们所不屑的神父在和“我”的交往过程中,带给“我”的不是压抑和不解,而是贴近日常真情实感的喜怒哀乐。“我”在他这里找到的是一种从话语空间里的人物所带来的压抑和不解中解脱出来的慰籍。在“我”的思想意识中,有弗林神父存在的空间其实已经成为了相对于带来无奈的现实空间的理想空间。然而,当“我”走出话语空间,真实地步入弗林神父的家,最后一次去探望他,进入这个“我”作为当事人参与行动的故事空间的时候,一切却在微妙地变化着。作为弗林神父的姐妹,伊莱扎和南尼都是近暮年而未婚的孤身老人,他们一生的努力只能换来一句“上帝知道我们尽了我们的所能了,虽说我们穷成这样”,对兄弟的死他们无能为力。“我踮着脚”走进陈放神父棺木的房间,原本想要非常肃穆,却因为看到伊莱扎的“裙子在她的身后是多么笨拙地扣在一起”而突发奇想,“觉得那老神父正躺在棺材里微笑”[4]8。棺材里的神父也就如常态下教徒的死亡一样:“在死亡中显得庄严而博学,胸前搁着一只无用的圣杯。”[4]11在印证了神父死亡的消息后,“我甚至觉得烦恼,因为我发觉自己由衷自由的振奋,仿佛他的死亡把我从某种东西中释放出来了”[4]6。随着“我”的顿悟,这个理想空间也坍塌了,一切的期待随着对教父死亡的确定而进一步进入了瘫痪状态之中。
《遭遇》开篇就展示了一个特别的形象——狄龙。在常规叙事下,这无非是一个比较调皮的男孩子,他看着《半便士奇闻》之类的书籍,排演着印第安人的打仗游戏,“不管我们怎样苦战,我们的包围战火对阵战就从没有打赢过,所有的较量都以乔·狄龙庆祝胜利的战舞告终”[4]12。但是,在对这个形象作了展示之后,狄龙马上被放入了故事相关的话语空间中——学校。学校教学的内容和狄龙展现给“我”们的一切是不相容的。巴特勒神父在听大家背诵罗马历史的时候抓住了带着《半便士奇闻》的狄龙,否定了狄龙所关注的西大荒文化,并对他训斥道:“不要让我在这所学校再发现这种蹩脚货色。”[4]13在这个话语空间里,狄龙完全被升华成了异文化的代言人,哪怕有消息说“他有志于做一名教士”,大家都不相信[4]12。在学校里,在清醒的时刻,西大荒的辉煌随着狄龙的被责而变得暗淡,学校正统的教育还是占了上风。然而,一旦离开了学校的约束影响,是狄龙的西大荒故事激起了“我”对学校教学的不满,虽然那些故事“跟我的天性相去甚远,但它们起码打开了逃避之门”[4]12。在他的影响下,“无法无天的精神在我们中间蔓延”,包括平时年龄小、胆子小的“我”也开始了对“狂野的刺激”的渴望,想逃离学校的“枯燥乏味”,“来点真正的冒险”[4]13。于是,“我”们制定了一天的逃学计划,决定沿着码头渡过海湾再去梗的鸽棚城堡看看。简单的一次逃学,于“我”而言却意义非凡,这是对正统教学的突破,是挑战自己进入另外一个想象的神秘空间的实际行动。随着这次行动的实施,故事的叙事就从话语空间进入到了故事空间,开始了对于“我”所参与事件的描写。可是,随着“我”的行动一开始,所有的期待和幻想就开始逐一瘫痪了。首先是决定逃课的三个人中本应该最积极的狄龙爽约了,导致“我”们连最简单的围攻游戏都玩不了,“因为围攻至少得三个人才成”[4]15。等到过了利菲河,时间已经晚了,“我”们也没能实行拜访鸽棚城堡的计划,连最初制定的目的地也成为了不能企及的地方。“我”和马奥尼走进田野,里面“除了我们没有旁人”[4]17。就在一切期待的事情似乎都没有发生的时候,却有一个神秘的人物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和他最初的交流似乎是令人愉快的,他说一个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无疑就是做小男生的时候,他赞扬“我”和他一样都是书虫,他甚至对“每个小男生都有一个小小的情人”作了令“我”感到很有道理的评论。偶遇这样一位老人,听着他大谈特谈生活,在一个原本被“我”带上了神秘色彩的地方,生活的乐趣似乎又回来了。然而,在马尼奥去追逐猫,老人离开一会儿回来以后,“他好像已经忘却刚才他那开通态度”,开始提出和之前完全相反的观点。“我”开始慌乱不安,终于找到机会向他道了日安,快速离开去找马尼奥了。就在马尼奥跑过田野向“我”奔来的那一刻,“我”的心跳剧烈,这个“我曾经有一点瞧不起”的人成了“我”的救命稻草[4]20。一瞬间的顿悟,把“我”从想象中拖回了现实,颠覆了“我”对学校之外美好世界的幻想。学校是枯燥的,外面的世界也是无聊甚至令人恐惧的,现实的话语空间也好,想象中的故事空间也好,不过都是瘫痪的,没有生气的。
《阿拉比》更是在话语空间和叙事空间的转换中把作为小男孩的“我”所看到的瘫痪状态展现得生动无比。《阿拉比》一开始就引入了叙述的话语空间——里士满北街,这是一条“死胡同,很寂静”,街上的房子“彼此凝视着,个个是一副冷静沉着的棕色面孔”[4]21。死亡的气息在这里蔓延,连“我们家原先的房客”也是个司铎,“他死在后屋的起居室里”,一切都是毫无生气的瘫痪状态[4]21。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我”的乐趣就是能和伙伴们在凛冽的寒风中嬉闹,在黑暗泥泞的胡同里“同破烂屋棚那边来的野孩子交手”[4]22。就这么简单的娱乐活动还得忍受四处刺鼻的异味,甚至躲着叔父。这是一个瘫痪的空间,生活在这个空间里,生活一如既往地老调和枯燥。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曼根的姐姐,“我”躲在以为她看不到的地方偷偷看她;“当她出来走到门阶上,我的心就欢跳起来”;我们没有太多交流,可是单是她的名字就“像一声传唤,会调动我全身血液喷发愚蠢的激情”[4]22。在这个死气沉沉的话语空间里,“我”终于找到了热情,终于也等到了她对我说话,而在此交流中,她表现了对于“我”能去阿拉比集市的羡慕,“我”也顺势许诺要去集市给她带回礼物。在辛苦的挣扎和等待以后,“我”终于在周六晚上的九点以后从叔父的手中获得了一个弗罗林的硬币,“大步沿着白金汉大街朝车站走去”[4]25。“我”迈向了即将转入的故事空间——阿拉比集市,那是“我”自认为能兑现诺言的地方,是“我”实现梦想的空间。然而,从“登上一辆乘客稀少的列车”到最后“空寥的车厢里,我始终一个人”,随着故事的展开,已经能够猜测这个集市并非想象中那么神秘多彩了[4]26。怯怯地走在集市上,“我”听着开着的摊位上两个男人数钱的声音,“我勉强记起了自己为什么到这里来”[4]26。好不容易等来的硬币在口袋里撞击着,卖东西的年轻女士甚至不屑于和“我”交流,“她走过来问我可想要买点东西,她的语调并不很殷勤,好像就是为了尽义务才对我说话”[4]27。“我”想象中的美好最终没有发生,原本是圆梦的地方成了梦破碎的地方。“我抬头凝视着黑暗,发觉自己是受虚荣驱动又受虚荣愚弄的可怜虫;我的双眼中燃烧着痛苦和愤怒。”[4]27纯真的爱慕带来的心跳和激动此刻在“我”的顿悟中成为了一种虚荣的代言人,所有的努力都成为无意义的付出,随着集市的关闭,这份年少时珍贵的情感也进入了瘫痪状态之中。
三、结 语
在《都柏林人》儿童篇的三个故事中,乔伊斯极好地展现了其特殊的叙事技巧。基于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的叙事策略,乔伊斯把儿童篇的叙事交给了处在童年期的“我”,增强了叙事的可信度。基于故事空间及话语空间双空间叙事策略,乔伊斯把现实和理想的矛盾投入到了空间的交替转换中,进一步提升了叙事的生动性。在这些特别的叙事策略下,基于叙述者一次次的精神顿悟,乔伊斯在儿童篇中把都柏林人宗教信仰的迷失、教学的无助和情感的未果展现得恰如其分,达到了凸显整个小说集“瘫痪”主题之目的。
[1] 乔伊斯.乔伊斯诗全集[M].傅浩,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胡经之.西方文学理论名著教程: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72.
[4] 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M].徐晓雯,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5] 王永梅.从地点到空间:《无名的裘德》中的空间叙事[J].理论月刊,2010(8) :137.
[6] 理查德·艾尔曼.乔伊斯传[M].金隄,译.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6:181.
[7] JOYCE J.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M].Hertfordshire:Wordsworth Editions,1963: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