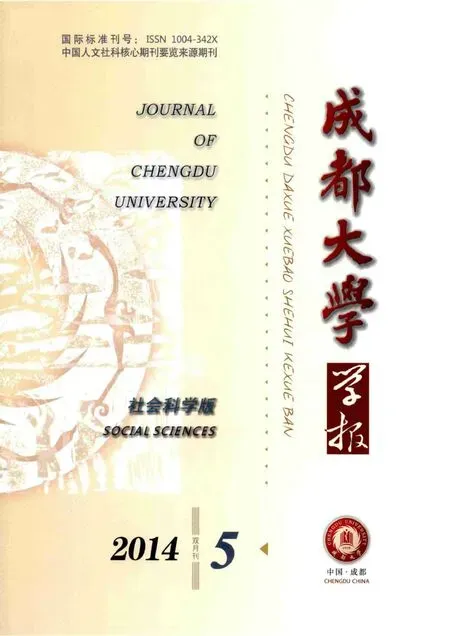翻译优美,韵味各异*——从耐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看钱稻孙译的《万叶集精选》
2014-03-25田寨耕
田寨耕
(成都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106)
《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诗歌集,收集了四世纪至八世纪数百年间众多诗人写的诗歌4500余首。诗歌作者包含了社会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人物,上至王公贵族、官宦富商,下至兵僧艺丐、农樵渔猎。因此诗集反映了那段时期日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万叶集》又被称为日本的《诗经》。我国已有一些学者从事过该书的翻译,其中钱稻孙的译本影响较大,受到读者的推崇。译者钱稻孙(1887-1966)是民国时期知名的翻译家和学者,浙江吴兴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其祖父钱振常是清代同治举人,做过礼部主事、绍兴龙山书院院长。其父钱洵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官,曾先后担任过中国驻日、英、法、德、俄、荷、意等国使馆的参赞和公使。1900年起他随父先后到过日本和欧洲各国并在当地接受教育,因此精通日、意、法、德语。1927年起在北京清华大学教日语等课程,1931年起专任该校正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日军占领北平期间,在日伪政府任文职,成了文化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判刑入狱。释放出狱后从事日本古典文学的翻译工作。他是我国第一个从原文汉译《万叶集》和《源氏物语》的译者,虽然都没有译完。除翻译方面外,他在音乐、医学、历史等学科方面都有杰出成就。本文拟从耐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的角度来看一看钱稻孙译的《万叶集精选》。
一 耐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简述
尤金·耐达(1914-2011)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1943年获密西根语言学博士学位,长期在美国圣经学会主持翻译部的工作,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在长期的《圣经》翻译过程中,耐达从实际出发,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翻译理论,最终成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一。耐达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功能对等”。所谓“功能对等”,就是说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语言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为使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耐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65)。耐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词汇对等,句法对等,篇章对等,文体对等。
二 “功能对等”理论在诗歌翻译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本文认为,将“功能对等”理论运用到诗歌翻译实践中,可以具体化为下列三条基本原则:1.意义上的对等;2.韵律和格律上的对等;3.韵味、意境和风格上的对等。首先让我们来看意义上的对等。忠实于原文是所有翻译实践都必须做到的最起码的原则。但是,诗歌翻译不同于其他文体的翻译,因为还要考虑到韵律、格律和美感等因素,要做到百分之百的忠实是不大可能的,只能说尽量做到或基本做到。其次,韵律和格律上的对等,这是诗歌翻译的一大难点。如果原诗有韵律和格律,译成目的语后也必须要押韵和有节奏,否则只能叫译文,不能叫译诗。当然,要做到与原诗押相同的韵肯定是不可能的,译诗各句之间做到押韵就已经不错了。不过格律、节奏上可以尽量接近原诗。最后,韵味、意境和风格上的对等,这是诗歌翻译的最高境界,可能也是最难做到的。原诗是伤感的还是喜悦的,是豪放的还是婉约的,是田园牧歌式的还是宏伟华丽式的,是积极进取的还是悲观颓废的,译者应在译诗中体现出来。
三 下面就用上述三条原则来分析钱稻孙《万叶集精选》中的诗歌翻译
(一)意义上的对等
译者在日本求学多年,而且学贯中西,对日本文化有着深刻认识。据20世纪50年代联系钱稻孙翻译《万叶集》的人民出版社编辑文洁若回忆,钱对日本文化的了解与周作人不相上下。再加上译者对原诗的仔细研究以及曾经得到日本知名学者佐佐木信纲的指点,充分理解原诗基本上不存在问题,这是保证意义对等的前提条件。但是,按照耐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意义上的对等,并非是指字面意思上的死板对应,因为同一个意义在不同语言里有着不同乃至迥异的表达形式。如果只顾及形式上的对等,就必然会导致意义上的不对等。所以要想保证意义上的对等,就不能拘泥于形式上的死板对应。在这个问题上译者处理得很好。例如第二首,《天皇登香具山望国之时御制歌》,译者是这样译的:“猗欤大和,丘陵孔多。天香具山,冠服峨峨。爰跻其上,瞻我山河;烟腾自原,鸥飞凌波。腴哉国也,有秋之大和!”。这首诗可以用白话文直译如下:“大和地方,虽有许多山冈;要数天香具山,披着丰厚的衣装。登上山来,一望平阳;地上炊烟升起,水上鸥岛飞翔。真是美地方呢,这个有秋收的大和之邦!”两相比较,二者意义大致相同,但是显然前者没有拘泥于逐字对译,因为逐字对译翻成中文听起来就不那么优美。
(二)韵律和格律上的对等
如前所述,翻译诗歌时,由于不同语言的词汇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译诗要想与原诗押相同的韵是不可能的,译诗自己各句之间做到押韵就已经不错了。在这一点上,译者是做得相当出色的。《万叶集精选》里的译诗基本都做到了押韵,而且平仄得体,抑扬有致,反映了译者深厚的文字功底。比如《启航令》:“熟田夜幕罩航津,浩浩艨艟泊海滨。玉兔东升潮水涨,一声号角奋军心。”在这首诗里,第一、二、四句句尾的“津”、“滨”、“心”押“in”韵,而且声调都为一声,可见韵律之整齐。又如《松枝愿》:“途经岩代海滩边,手系松枝许愿签。鸦鹊啼声何切切,安还与否靠苍天。”在这首诗里,第一、二、四句的“边”、“签”、“天”押“an”韵,声调均为一声。再如《怜爱》:“朝鲜锦褂纽徐开,几度春风袭满怀。万缕怜情千种爱,卿卿我我且重来。”这首诗四句都押“ai”韵,实属不易,且用了不同的声调,以避免读音单调乏味。这三首都是七言诗,下面再举一首五言诗,《太宰帅大伴卿赞酒歌》:“出言居圣贤,莫若且饮酒。酒醉涕滂沱,犹似胜一筹。”在这首诗中,“酒”与“筹”押韵。《万叶集精选》中还有一些译成白话文的诗歌,仍然保持了韵律。如第897首,《山下臣忆良老身重病经年辛苦及思儿等歌一首并短歌》:“寿命出不了大限,/至少在这期间,/也希望平平安安,/没有灾,没有难。/无奈人生多忧患,/有道是,最不堪,/伤口里撒盐,/马背上堆满了还添。/我这已老之年,/还添上病魔缠,/白天叹气夜来喘,/累月长年烦苦煎。/每每想要死了算,/孩子象像蝇一般,/扔下而死又不忍,/看着心里燃;/左思右想,惟有哭喊。”在这首长达十七行的长歌里,有十六行都做到了押韵,而且全都是押“an”韵。
下面再来看格律。《万叶集》所收录的诗歌里面,绝大多数都是短歌,此外有少量的长歌和旋头歌等。所谓短歌,是指一种形式为“五七五七七”的日本诗歌体裁,意即此诗总共有五行,第一行有五个音节,第二行七个音节,第三行五个音节,第四行七个音节,第五行七个音节。长歌是在重复短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据本文观察,钱稻孙在翻译《万叶集》时采用了不同的文体,大致有如下四种:1.诗经楚辞体。2.唐诗体。3.宋词体。4.白话文体。不同的文体有着不同的格律、节奏。
1.所谓诗经楚辞体是指《诗经》和《楚辞》里所呈现出的文体,其特点是晦涩难懂,古朴、深奥、神秘,因为毕竟是远古的文字。而且《诗经》的诗句和《楚辞》的部分诗句都短小精干,通常为每句四个字。对于《万叶集》中早期出现的某些诗歌,译者采用了这种体裁,大概是想给这些译诗增添一些像《诗经》和《楚辞》那样的古朴神秘、年深久远的氛围吧。如第28首,《(高天原广野姬)天皇御制歌》:“春既徂欤,夏其来诸;有暴白纻,香山之陬。”这一首是诗经体。又如第317首,《山部宿祢赤人望不尽山歌一首并短歌》:“自天地之初分,永尊严于高雯,崇镇乎骏河之郡,不尽乃神山之君,仰云天以瞻望,既运日之自戢其光,亦明月之不竞其雱,传之诵之以靡足,厥维不尽之高岳。”这一首听起来则像楚辞。如果没有深厚的国学功底,是译不出这种诗经楚辞体的。但是从格律、节奏上来说,未能与原诗的“五七五七七”节奏达成对等。
2.唐诗体,顾名思义,就是指唐诗的体裁,即我们常见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书中有许多诗歌都是用唐诗体译成。如《狩猎》:“宇智坡前圣主骑,精英伺驾踏晨曦。风光浩瀚青纱帐,万马奔腾逐鹿麋。”又如《忆婵娟》:“从军远戍在陲边,夜半更深欲饮泉。忽见河中妻姣影,相思泪尽梦难圆。”再举一个五言律诗的例子,第893首,《贫穷问答歌一首并短歌》:“亦知人生世,无非忧与羞。所恨不为鸟,何当飞去休。”从这些译诗我们可以看到译者深厚的古文功底。不过,分成五行的、每行字数分别为“五七五七七”的短歌,译者在翻译时,许多都译成四行的七律汉诗或五律汉诗,即每行都是七个字或五个字。这种做法从翻译技巧上来说未尝不可,不过从功能对等的角度,从忠于原文的角度来说,本文认为改变还是太大了一点。
3.书中有些诗歌译者在翻译时还用了宋词的文体,其特点是长短句,即各句长短不一,这一点与唐诗的整齐划一是不同的。如第1428首,《草香山歌一首》:“过了难波光弥漫;日暮翻来路窄,风靡草香山。马醉花儿开遍,良不恶,足可观。几时捷足去,与君快相见。”长短句式的宋词体与短歌的“五七五七七”句式比较接近,有异曲同工之妙。
4.除了以上文体,钱稻孙有时还尝试用白话文来翻译。如第103首,《天皇赐藤原夫人御歌一首》:“我这里下了大雪;大原原是古僻的乡村,还该晚一些时吧。”及其答诗,第104首,《藤原夫人奉和歌一首》:“我叫冈上龙神下的雪,怕是一些零残碎屑,飞散到那里了。”这两首白话文体的译诗与短歌的格律离得更远。首先,短歌的五行译成汉语后被合并为三行;其次,中文的字数与短歌每行的字数“五七五七七”也不对等。
上述四种文体的译诗,除了宋词体比较接近以外,其他三种与短歌都未能达成格律、节奏上的对等。格律上不对等就会影响到韵味、意境上的对等,从而最终影响到译诗对原诗的忠实度。那么,日语的短歌能否在汉语中找到对等的形式呢?答案是肯定的。办法就是:五行的短歌,译成汉语后,仍然处理成五行;根据短歌“五七五七七”的节奏,第一行安排五个字,第二行七个字,第三行五个字,第四行七个字,第五号七个字。要做到这一点不大容易,但也不是不可能,且已有他人翻译的实例存在。如:“茅庵倚田边,金穗金风带笑看。檐上乱草苫。淡淡星光撩新梦,盈盈玉露溽青衫。”又如:“不觉春已去,熏风袅袅漫步还,翠笼香具山。往岁白衣一片片,今年谁又晒衣衫?”再如:“芳菲花色凋,红泥满径雨潇潇。空令看花人,朱颜成雪凭栏泣,往事如烟带泪抛。”这三首译诗就完好地保留了原诗的格律、节奏,而且还做到了押韵。
(三)韵味、意境和风格上的对等
关于这一点,逐项来分析。
1.诗经楚辞体。从文体和风格的角度来说,用这种体裁来翻译《万叶集》里早期的诗歌,本文认为还是对等的,因为那些诗歌毕竟象《诗经》和《楚辞》一样,是很久以前的诗歌(虽不及《诗经》和《楚辞》古老),用诗经楚辞体来翻译,可以使它们增添一种古朴、神秘的气氛。只是诗经楚辞体的格律、节奏与原诗不同,所以译诗的韵味和意境也会与原诗不同。前面已举有诗经楚辞体的实例,此地不再重复。
2.唐诗体。本文认为,格律、节奏上的不对等,造成了韵味、意境和风格上的不对等。唐诗的特点是每句字数相同,听起来显得整齐划一,铿锵有力;而短歌各句长短不一,朗读起来给人一种曲折婉转、荡气回肠的感觉。此外,钱稻孙用唐诗体译出的诗歌,的确优美流畅,给人以美的享受,但是,译诗里面增添了一些原诗所没有的内容,降低了译诗对原诗的忠实度。如第8首,《额田王歌》:“乘舟熟田津,待月把帆扬;潮水涌,操棹桨!”(赵乐甡译);而钱稻孙的译文是:“熟田夜幕罩航津,浩浩艨艟泊海滨。玉兔东升潮水涨,一声号角奋军心。”两相比较,显然赵译更忠于原诗,而钱译则增添了不少内容(如:夜幕、罩、浩浩艨艟、泊海滨、号角、奋军心),且韵味和意境也大为不同,听起来好像场面浩大、气势雄壮,似乎大军就要出征了。
3.宋词体。虽然宋词各行的字数与短歌各行的字数“五七五七七”不尽相同,但由于都是长短句,所以在韵味、意境和风格上也彼此接近,它是这四种文体中最接近短歌的。
4.白话文体。一千三百年前创作的诗歌,无论当时用的是文雅的语言还是通俗的语言,到现在都成了古语,都带有古味,所以最好用文言文来翻译,至少也应该是半文半白。如果用白话文翻译,译诗就会缺少古韵,在韵味、意境和风格上自然就与原诗不对等。不知背景的读者还会误以为是现代人写的诗。试想,在一部历史古装电影中,人物之间的对话没有几句古语,全是现代汉语,甚至还出现一些时髦词汇,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感觉?无疑会让人觉得不伦不类。
钱稻孙是民国时期的知名学者和翻译家,国学功底深厚,而且学贯中西,精通日本语言和文化。他采用四种文体来翻译《万叶集》。诗经、楚辞体古朴而神秘,用来翻译那些古老久远的诗歌是比较适宜的,尽管其格律、节奏与原诗有所不同;唐诗体诗歌译得优美流畅,婉转动人,但是格律、节奏与原诗相差较大,所以韵味、意境和风格也有较大不同,且意义上也增添了一些原诗所没有的内容,对原诗不够忠实;宋词体是这四种文体里最接近原诗的体裁;白话文体,本文认为,钱稻孙用白话文来翻译古代诗歌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的格律、节奏、韵味和风格都不对等。总而言之,钱稻孙的《万叶集精选》凭借其深厚的国学功底译得优美动人,但是韵味、意境和风格与原诗不同,有时还差异悬殊,未能原汁原味地展现原诗的风味,实乃美中不足。也许这正是诗歌翻译的难点所在,鱼和熊掌难以兼得。
[1]钱稻孙译,《万叶集精选》,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