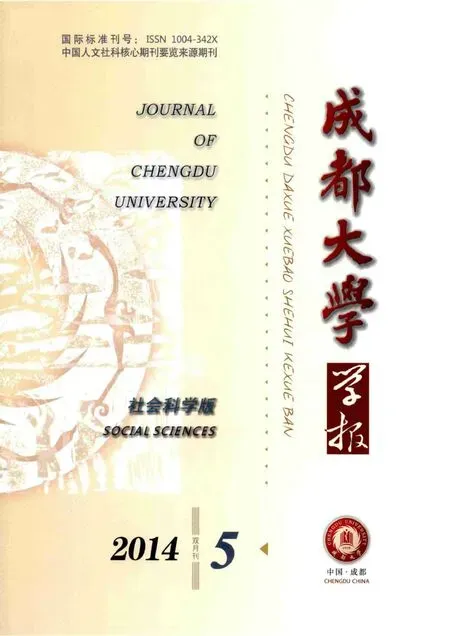“巴盐古道”在“国家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2014-03-25陆邹杨亭
陆邹 杨亭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巴盐古道”在“国家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陆邹 杨亭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中国历史上,“巴盐古道”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巴蜀地区盐业的发展,其不仅是西南地区经济连接的纽带,也是国家权力主导之下极力发展的民族走廊。随着历代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经营以及民族社会的不断进步,盐道的历史地位也在不断凸显。而且“巴盐古道”本身作为交汇区和过渡带,对国家力量渗透、族群社会发展、区域市场建立以及西南移民活动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也体现了“巴盐古道”早已被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之中。因而,“巴盐古道”作为一条传统通道,对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互动和变革有着重要意义的同时,在民族走廊历史进程的研究领域中亦不容忽视。
巴盐古道;国家化;盐业;族群;运销;移民
在传统封建社会里,盐业、盐利成为直接影响国家政权安危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历代国家对盐资源保持高度重视。历代盐的生产和运输关系“民生民计”,从而形成了各种盐运通道,这些盐运通道有着网络密、跨度大、历时长的特点。其中在巴蜀以及武陵山区不断进行着的运盐活动已有上千年历史,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巴盐古道”。盐道上历经了各种销盐、移民、战争等历史活动,这些国家和民族活动使得整个西南地区的民族政策和制度不断更迭,也体现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融合下各种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
目前,学界对于中国西南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民族走廊、交通路线有着诸多研究和梳理,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中诸如蓝勇的《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对四川交通网络的形成发展有着详细论述,而西南地区盐运路线的主要研究成果是赵逵的《川盐古道:文化线路视野中的聚落与建筑》,其从“文化线路”角度审视“川盐古道”,深入研究古道形成历史及区域分布。但就西南民族史来看,民族走廊的发展离不开国家与民族的交流和联系,亦是国家社会、经济、文化互动的结果。鉴于此,“巴盐古道”概念的提出,不仅因为其是重要的经济和文化线路,而且“巴盐古道”的形成和发展史是对国家社会的观照和映射,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更体现了西南巴渝地区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国家化”进程。目前由于现代交通体系的完善,“巴盐古道”已失去往日的繁华和喧嚣,但历史上沉淀于这些线路上的政治和文化特征却仍旧以物质或非物质的形态存在。
一 “巴盐古道”的历史背景和分布结构
(一)“巴盐古道”的历史背景
盐作为人类生存的重要资源,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历史上,古巴蜀地区盛产井盐(锅巴盐)已有1000多年历史,其中巴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以盐立国的国家,它“因盐而起、因盐而兴、因盐而亡”。巴国盐井多,今忠县、云阳等地都是制盐中心,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已明确记载:临江县(今重庆忠县)“有盐官,在监、涂二溪,一郡所仰。”[1]301其盐主要运销巴楚地区,继而形成了一条盐运大陆“巴盐古道”。
对于研究“巴盐古道”,“巴国”的历史是一条重要线索。据《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2]241其中“咸鸟”的“咸”字,正表明巴国与巴渝地区盐泉有着密切关系,而且也能了解到巴族早期活动的中心地区即在整个长江三峡地区以及鄂西清江流域。起初,巴人首领廪君,带领部族溯流而上,战胜原住民载人,控制了清江流域及巫溪河流域的盐业生产。巴族不仅是长江三峡地区以及鄂西清江流域的古老民族,而且建立了巴国。在渝东地区有三大盐泉,即:巫溪宁厂镇宝源山盐泉,彭水县郁山镇伏牛山盐泉和湖北省长阳县的盐水,[3]均被巴人部落控制着。巴国因盐资源,迅速壮大并积极向外扩张,最后在江州(今重庆)建立了政治中心,巴人依靠盐过上“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2]215的生活。“西周王朝建立后,大封诸侯,巴也被周王室正式册封为诸侯,其首领称为巴子。”[4]这为巴国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为此不断开始向南扩展,同时巴国也成为周王室控制南土的战略重地。
武陵地区巴人食用巴盐的历史悠久,而且巴国周边的秦、楚之地均不产盐,他们的食盐供给主要是依赖巴国。巴国据盐泉之利,利用盐运通道,不断以“盐巴”与周边民族展开贸易活动。渝东丰富的盐业资源,早已被秦、楚、蜀所觊觎,这让巴国后期不断陷入战争漩涡。春秋中叶(公元前477年)“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败于鄾。是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1]297巴国战败失利,开始不断转移向西南地区。在“公元前361年,楚国攻占了巴的三峡地区和清江流域。到巴国灭亡前,楚国已经逼近巴的先王陵墓所在的枳,此时的巴国疆域仅剩下嘉陵江流域和乌江下游地区了。”[5]25战国中期,楚国大举西进,致使巴国三大盐泉相继丧失,失去主要经济来源,渐渐走向衰亡。在公元前316年,秦军南下将巴蜀吞并。巴国虽灭,巫盐依旧,因为三大盐泉的经济利益,公元前223年,楚国亦为强秦所灭,巴蜀地区盐业资源即全部归属秦国。“巴楚之战”以及“秦灭巴蜀”体现谁拥有盐泉谁就取得强大的经济实力。
因为巴渝地区的地理形势和民族生态环境,当时运盐就有着发达的水运和陆路交通,“巴盐古道”在巴国统治的时候就已逐步形成。巴蜀地区的先民与渔盐之利息息相关,巴人虽然亡国,但是巴盐经济和“巴盐古道”在巴蜀地区一直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军事和经济上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影响。“巴盐古道”穿越整个武陵山地,地跨川鄂湘黔,其形成与国家行为有着重要联系,盐道也在巴以后的各个朝代也逐步得到完善,而且在历代各种国家行为中,盐道上历经着各种军事和移民活动。秦汉、唐五代时期,中央政权不断向湘鄂渝黔的民族地区渗透。宋元时期,国家更加注重西南民族地区开发和管理,“国家化”进程随之加强。明清时期延续历代的发展经略,不断完善整个西南地区“内地化”的体系,为构建整个国家的边疆防御体系,加强对这一地区经营。再者,西南地区有着众多部族和王国,而且“巴盐古道”成为了重要的交流和贸易通道,这样的通道必然成为汉族政权对民族区域开发和经营的重要桥梁。
(二)“巴盐古道”的分布结构
历史记载,巴国最强盛时的疆域,以重庆为中心,东到汉水,南到渝东南、黔东北及湘西北,西接蜀国,北邻秦国,地跨今川、渝、鄂、湘、黔、陕数省市。巴国境内民族众多,除巴族和很早定居于此的中原民族外,还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等民族,而且现在这一地区土家人的祖先正是当时的巴人。当时巴楚之地的族群获取食盐的途径除水运通道,还有大量人力运输的陆路通道,古时称“三尺道”,也称“盐大道”,纵横交错形成了“巴盐古道”。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石柱、利川等地仍在世的挑盐老人口述得知,巴渝地区古盐道有很多条,但是“巴盐古道”作为重要的通道,主要从巴渝产盐之地向鄂、湘、黔等省辐射。根据川盐在鄂、湘、黔的运输网络,有学者认为其中“川鄂古盐道”至少有“四横一纵”几条主线路[6]71,而“四横”中的“清江线”,主要是由“忠县涂井、泔井盐和自贡井盐经水运汇集忠县西沱镇,陆运经石柱-利川-恩施,再由恩施经清江水运,过长阳、宜昌,进入湖北腹地。”[6]73“一纵”即“由万县、云阳、奉节、巫山盐运码头山发,向南翻越齐跃山脉,过利川、恩施到宣恩,再经咸丰-来凤-龙山-桑植-张家界-凤凰,进入湖南地区[6]75”,水、陆相互配合,构成了巴渝东部至鄂、湘、黔的盐运网络。其中川鄂古盐道,在历代亦称为“川鄂峡路”,这条路线自春秋战国以来在军事和经济上有着重要作用。在宋代,峡路“不仅沿途置有水驿,水路通畅,而且沿江置有地铺、陆驿,使水陆兼济,峡路交通发展在四川交通史上发展到了高峰。”[7]179在清代巴蜀亦有一条“东大道”,其中“可延伸东取分水驿、垫江驿、梁山驿、万县驿、云阳驿、奉节驿、巫山小桥驿入湖北。”[7]268以此再拓宽陆路网线。基于以前的盐路古道,“从北宋开始,逐步建成起于西界沱的‘川盐销楚’的盐运大道。主道由西界沱翻楠木垭,经青龙场、石家坝、黄水坝、万胜坝、冷水溪,翻七曜山至湖北利川县汪家营,再到利川、恩施等县,全程300多公里。”[8]这条陆路运输的交通线,见证了武陵地区的盐运历史。
综合以上几点,“巴盐古道”主要是从西沱古镇—利川—咸丰-来凤-龙山-花垣-吉首-凤凰古城的这条路线,“川盐入楚”的主要路线也是基于此,再以此辐射延伸。“巴盐古道”的起点石柱西沱镇的周围密布盐场,如涂井溪旁的忠县涂井盐场,大宁河旁的巫溪大宁盐场,乌江支流郁江旁的彭水县郁山盐场,汤溪河畔的云阳县云安盐场等。这些盐场分布在长江各条主干支流上,围绕其发展的水陆通道构成了西南地区的盐运交通网络。历代长江航运常因自然和战争因素被阻断,而且两湖地区崇山峻岭,地势险恶,淮盐难以达到。巴渝有忠县、郁山、云安、大宁等这样的产盐重地,“巴盐古道”地处川鄂湘黔的交界处,地理位置尤为重要,易成为“川盐销楚”的主要通道。
“巴盐古道”从巴渝西界沱到荆楚之地,历经少数民族生态分布区,从非汉族地区的“巴蜀之地”向汉文化中心“两湖”地区过渡,在历经产盐、运盐、销盐的同时与国家政治活动紧密联系。而且国家行为对于盐道的发展和分布亦有着深刻影响。历代王朝为拓展疆域,治理西南民族地区,施行羁縻制度、土司政策,建立行政机构,修筑大量经济军事通道,“巴盐古道”这样的通道作为对国家官道的重要补充得以不断发展,让国家资源得到充分调配。在国家力量不断渗透的同时武陵地区的族群之间得到了交流和互动,这也映照了这条通道的形成是历朝历代各个族群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
“巴盐古道”形成时间长,跨度大,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而且也是中国政治格局之下衍生的结果。盐道的发展与民族生态分布、移民活动以及西南地区经济贸易有重要关系。
二 “国家化”进程与“巴盐古道”的关系
“巴盐古道”的产生和发展有经济发展和族群活动的因素,但更有着国家行为的因素,这体现了盐道的发展是国家政治经济格局的结果。
(一)国家力量的渗透与族群及盐道互动
历代国家力量不断向西南延伸,各种通道走廊被纳入国家体系之下,“巴盐古道”也不例外。“巴盐古道”作为各种要素的交汇区,政治和军事的作用突出,中央及地方民族政权异常重视,而且盐道沿线区域也最早设立建制,更是重大政治活动的边际地带。封建统治时期,为控制巴蜀湘黔地区,频繁加强与西南地区的交流,实行羁縻、土司政策,恩威并施,“以夷制夷”,不断利用纵横贯通的官道。“巴盐古道”作为区域交往的纽带,始终与地方发展紧密联系,也是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行政管辖的重要工具。
国家的发展必然伴随着重重的民族矛盾,对于西南民族地区来说亦然。汉末至南北朝时期巴渝地区社会动荡,东汉中晚期以来,政治腐败,社会以及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起义不断。永嘉元年(公元145年)巴郡人服直起义,184年张修在巴郡发动五斗米道起义[5]82-83;宋元时期,嘉定十五年到十六年(1222-1223年),蒙古军队南下,四川、重庆地区成为宋蒙战争的主要战场。后期,更是围绕着川东和川南的军事要塞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巴渝亦成为南宋抗击蒙元战争最久和最后的基地。
元朝为了巩固自己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大量设立行政机构。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重庆设四川南道宣慰司,管辖重庆路、夔州路(今奉节县),绍庆府(今彭水县),怀德府(来凤县东北)。紧接着,实行屯田,设置大量的水陆路驿站,“元朝在全国共设水陆站约1500处左右,形成了一个以大都为中心,连接全国各地和国外的交通网……四川便是元朝京城通往西南的一个驿站交通枢纽。”[9]258譬如在“川鄂峡路”的川江水路一线的忠县设有溉云根乌蒙大水站(咸淳府水站),石柱西界沱的梅沱小水站,云阳县云阳水站等[7]181。明清也主要承袭元制,依然水路置驿,大力发展交通,而且巴渝地区的交通线上各种政治军事活动不断。早在至正七年(1357年),明玉珍西征,抵夔州、万州等川东州县,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在重庆建立大夏政权。明代前期和中期,主要是天顺年间川东和川西赵铎起义,以及正德年间曹甫、方四起义。起义队伍的基本成员主要是流民和盐业工人,这主要是政治腐败和土地兼并的社会根源,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9]40再到明末,张献忠在崇祯年间几次入川。“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率军自湖广第五次进入四川……正月,大西军攻占夔州、云阳;二月夺取万县;经休整补给后,五月至六月,连克忠州、酆都、涪州等沿江州县;六月中旬进抵重庆下游之铜锣峡,形成对重庆的进攻态势。”[5]187在“巴盐古道”的沿线网络成为了军事活动的承载体,各种国家力量交织不断。
再者,元明时期是巴渝地区军事战争次数最多的时期,主要类型大多是少数民族族群和统治者之间的控制和反控制,这亦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而引发的战争。中央王朝大力推行羁縻政策,“以蛮制蛮”,西南各地区的土司大量被征调,进行诸如“征蛮”、“抗倭”、“援辽”此类的战争。其中在明代,石砫宣抚司土兵被征调次数多,规模大,“先后被征调参加的大的军事活动达19次之多。特别是明末秦良玉执掌土司时期,石砫土兵参加的战争多,人数动辄上千、上万,最多时达到3万。”[10]众多军事征调主要有以下几次:1.正德七年(1512年),参加对四川方四领导的农民起义的镇压。2.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镇压土司杨应龙反叛。3.天启元年(1621年),秦良玉率兵援抗辽。4.天启二年1622年,征讨永宁土司奢崇明与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反叛。[11]土兵被征调战事的不断,这些征调活动的路线也当与盐道网络相重合。
以上种种巴渝地区的军事活动,都将会利用到历史上早已形成的各种官道商路,这也体现了“巴盐古道”作为政治和军事活动的主要载体,必然因此被纳入国家体制。
(二)盐法制度和川盐销楚
历代,盐作为国家的经济命脉,关乎整个国家的兴衰,正所谓“国家正赋之外,充军国之用,惟盐法、关税、钱法而已。”纵观整个西南地区的盐业史,我们能从这条线索了解到整个区域的发展历程以及民族社会的变迁,而且整个盐的生产和运销直接关系民生大计,体现了盐业经济意义异乎寻常。西南民族地区在唐宋时期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经过元明清的中央王朝的管辖和治理,形成了以巴蜀为中心的经济圈,而这一地区地处长江中下游流域,统一的区域市场经济不断加强和完善,食盐贸易市场也得以扩大。四川井盐资源尤其丰富,与整个巴蜀地区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在全国亦有重要地位,与盐业发展有着紧密关联的“巴盐古道”更体现重要价值。国家加强对西南特别是对巴蜀民族地区的管理,开辟和利用经济、军事上的通道变得尤为重要。
盐业经济历来都是国家垄断经营,这是历代封建王朝的传统政策。中国古代的盐法号称繁芜,政策形势以及运销体制反反复复,春秋战国及汉代推行“食盐官营”,采取民产、官运官销方式;唐代实行“榷盐法”,运销以商人为主;宋代执行专卖制;元代推行“食盐法”防止私盐,保证盐课收入;明代实行“开中法”,主要“按地区划定销盐范围的制度,称为‘行盐疆界’,行盐疆界的划定,是依据前朝的习惯以及和行盐路线的便利由朝廷所确定”[12];清代,制定专卖制度和销盐区域,食盐销售区域化,构成了运销的总体网络。其中盐政实施和运销制度主要针对的是经济影响很大的淮盐和川盐。
清朝对盐业的控制尤重于控制流通环节,采取的方式是封建专商引岸制度。“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实行计口授食盐,推行分岸分场‘引岸制’,规定盐销本省为计岸,销外省为边岸,销两湖(湖南、湖北)为楚岸,并且不同盐场都有各自的销售区域,以云阳的云安盐场为例,朝廷规定云阳盐计岸有云阳、奉节、开县、新宁、梁山、万县、巫山、达州、东乡、太平、建始11个州县,边岸有石柱直隶厅等。”[6]66这样的销盐市场划分,利于地区经济发展,也利于运盐通道的发展,不管是官运、商运还是民运,这些都是销盐的必备条件。致使历代王朝先后划定石柱县西界沱、云阳县新军口、巫山县大溪口、彭水县郁山镇为“川盐销楚口岸”,“巴盐古道”的意义不断凸显。其中,“巴盐古道”起点石柱西沱古镇(古为巴郡与巴东郡交界地,今是石柱、忠县、万县交界地),在唐、宋时已是川东、鄂西边境物资集散地之一,在北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作为川盐外销的重要起点,成为川盐销楚的必经驿站,故元代在此设立“梅沱小水站”,以连接川鄂交通。清乾隆时期,在此设巡检司,商贾云集于此,川盐以及各种物质,经长江上游等地运到西沱,再由西沱历经“巴盐古道”转运到恩施、利川、咸丰、来凤、龙山等地。再者,巴蜀作为盐业的核心地带,主要运销方向为东南地区:向东销往川东(主要是重庆)及两湖(湖南、湖北)地区;向南主要销往贵州和云南,运销中鄂湘黔的陆路占了很大比重。而且,历代水路运输易被各种国家和自然因素影响,这无疑发挥了“巴盐古道”的重要作用。
巴蜀民族地区军事活动频繁,其中有着较大影响的是明末清初张献忠农民起义和湘、鄂、川、黔地区的几次生苗起义,各种起义和战事使该地区人口锐减、经济萧条。咸丰年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淮盐运输受阻,清政府迫于各方压力,允许川盐行销两湖,实行了“川盐济楚”的政策,这大大刺激四川井盐业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税收。“‘川盐济楚’历时26年,四川仅向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运送的食盐就达80亿斤以上,上缴朝廷各种课税约合白银67亿两。鼎盛时期,川盐占全国食盐销量的1/4,占全国税收的30%。”[6]29而且盐业经济迅猛发展之下,“盐商资本踊跃转向井场,亦在此时。‘川民以济楚而增辟井灶,费本不资,商人以运楚而经营其业,投资甚巨’正是如实的写照。”[13]这是盐业经济以及运销通道发展的体现,而且大量盐商应运而生,反之亦影响了盐业经济和运销通道。而1937年抗战爆发后,东部依然是淮盐受阻,国民政府为解决战时资金问题,也为解决两湖地区“淡食”之苦,再次发起“川盐济楚”运动。这一时期部分古盐道被临时改为战备公路,大大改变了西界沱、里耶、谷城等盐运古镇,更繁荣了“巴盐古道”沿线。
不管是历代各种盐法运销制度,还是清代和民国“川盐济楚”的国家活动,实际上都是对盐业经济控制,进而达到掌控国家政权的目的。
(三)传统移民活动及“湖广填四川”
历代的西南地区移民活动频繁,而且每次大规模人口迁移都会对迁入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影响。巴蜀地区原本就是因为移民而产生的地区,而且盐业发展和“巴盐古道”与移民活动亦有着重要联系。
秦统一巴蜀前,中原华夏族已有不少人入川,秦统一巴蜀后,为加强对巴蜀地区的统治与经济开发,也为了转移各种对抗力量,决定向巴蜀移民,正如《华阳国志·蜀志》所说“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1]312公元前361年,秦向巴蜀的大规模移民的同时,长江中游的楚人也有大量移民入川,以至“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1]300而且,秦之后的巴渝地区移民浪潮并末停止,这些移民活动无外乎以下几种情况:1.国家开发边疆;2.北方灾荒;3.流民谋生;4.战乱与征调不断; 5.土司朝贡;6.商业交流。这些各类迁徙活动,进行着物质和文化交流,而且这些迁徙活动具有时间长、地域广、内容丰富等特点。其中,历史上为争夺渝东盐泉而发生的战争结束后,都会引发向三峡地区大量的移民活动,这种移民最先是军人,接着不断影响逐渐扩大人口范围和数量。南宋末年,蒙古兵侵蜀,烧杀抢掠,导致四川境内人口急剧下降,到元代末年的农民起义,明玉珍率领的军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14]明初,鉴于巴蜀地区人少地多,更好控制巴蜀局势,明中央更是有意组织湖广移民入巴蜀,这也是“湖广填四川”的主要部分和历史雏形。
明清两代,因为战乱,更使巴蜀人口发展雪上加霜。明代中晚期,李自成和张献忠转战四川各地。“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又波及四川。长期的战乱,造成了清初四川境内人口大幅度下降。由明初的300多万人,下降到50万人左右。”[15]加上天灾人祸,经济备受破坏,百业凋敝,明末实已衰微的井盐生产,清初更破败之极。为此,清代统治者采取和推行了促进盐业的措施和政策,颁布了减轻课税、招诱耕垦的律令,对于移民活动产生和发展具有极大的鼓动作用,大量从湖广、江西、陕西、福建等地移民入蜀。相对而言,水路进入巴蜀地区,较为方便,但是部分湖南、广东和福建的移民入川除了水路之外,他们主要还是通过古盐道进入巴蜀地区。渝东三峡地区与湖广毗邻,对于湖广移民,陆路是他们最近和最好的选择。在移民入川的活动中,大体分为三个方向:一是自北向南,主要是陕西、甘肃以及河南等地的移民;二是从东向西,主要是湖北、湖南和广东、福建以及江浙等地移民;三是自南向北,主要是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的移民。而其中,移民的主体,主要是后两个方向,后两者迁徙路线必然利用“巴盐古道”。移民活动不仅有国家行为下的,也有内地自发式的,而且从事商业贸易、手工业、农业的移民成为入巴蜀的主力。“从顺治末年开始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活动,如以雍正五年(1727)宣布停止移民截止,前后延续60多年;如以实际延续至乾隆中叶的下限计算,前后将近1个世纪。”[9]178整个移民延续时间长、规模大,使得整个四川人口迅猛增长。
“湖广填四川”的活动使得大批移民直接介入盐业发展,逐渐臻于兴盛繁荣。“作为三峡地区产盐重镇之大宁、云安、开县温汤、忠县涂井等各大盐场所在地,是广大移民聚集之地,这些地方也正是由于盐业的兴旺发达而带来了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反过来当然又吸引着更多的民众涌向该处,故而到了乾隆之后,渝东三峡地区各大盐场所在地,已呈现出标准的移民社会形态。”[16]在国家行为下形成的规模巨大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通过“巴盐古道”等交通网络为渝东地区井盐业的生产发展注入大量新鲜血液,使得社会繁荣,人口激增。再者,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被迫迁移四川,大批长江中下游的居民也迁移到重庆地区。这些移民活动间接和直接带动了地区工农商以及交通发展,整个巴蜀地区社会经济以及“巴盐古道”沿线异常繁荣。
三 “巴盐古道”的社会影响和文化意义
(一)盐业经济发展和国家市场的统一
盐是中国上古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盐运通道对国家发展有积极意义。盐业经济不断发展中,“巴盐古道”作为封建国家计划经济的一部分被有目的的纳入到官方话语中来。国家不断借助盐业经济为政治与军事服务的同时,“巴盐古道”为国家实行民族政策以及巩固对民族地区的经济管理提供了便捷。而且其也在不断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促进生产发展为目的,对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盐业经济是国家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巴渝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盐业,成为国家的坚实后盾和“避难所”。既如此,无论采用何种体制与政策,只要有益于民,盐业既能大有发展,国家财政亦也增长。国家盐政即像一面镜子,其影响下的销盐和运盐又十分真实映现出各个朝代由盛而衰的历程,这也充分表现了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中,盐业贸易以及运输交通的经济地位至关重要。清代的“川盐济楚,即指川盐经营摆脱封建盐政桎梏,以‘纯粹经济的形式’,夺取两湖淮商世袭引界的广阔市场。这一首开封建盐法破岸之举,既有其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又有其特定的政治历史背景。”[17]因而,“巴盐古道”有着极其明确的目的性和功能性,商业和政治特征较为浓郁,作为经济载体的同时,也为“国家化”进程提供了条件。
巴渝盐业发展赋予“巴盐古道”的经济意义为历代之统治者高度重视。“巴盐古道”作为盐业贸易的需要,不仅带动了我国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更形成了一批城镇和商会,经济资本迅速积累,对经济市场建设和交通发展有着积极作用。而且沿线历代移民活动使得本土和周边地区经济不断发展,纵观清代的移民活动,“可以认为清初的大规模入川移民是促进川盐内部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18]因为移民使得有更多的机会交流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这也体现了生产方式的变革有着政治制度变革的烙印。
“巴盐古道”使武陵民族地区和中原各大区域形成交流的经济网络,这样的经济网络必然衍生出更为复杂的社会网络,国家力量正是通过这样的网络不断把巴渝地区以至整个西南地区统一到中央王朝。“巴盐古道”被纳入到国家体系之下,促进西南地区加强与内地的经济交流,改变了区域经济结构,以此完成整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的一体化进程。
(二)族群社会的交流和沟通
“巴盐古道”的形成和发展是时代的特殊产物,不仅作为经济的通道,而且带动西南地区的民族交往与流动。“国家化”下“巴盐古道”的发展,加快了国家体系下中央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统一。“巴盐古道”作为商贸和迁徙重要纽带的同时,更渗透着国家意志,其与“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等“商道”以及其他“民族走廊”相比,有着相同更有着不同,在结合区域与族群的发展中,“巴盐古道”是对巴渝地区“国家化”进程清晰而完整的反映。
从巴族因盐而兴再到历代在西南权力构建,以及民族政策的实施,无不利用“古道”。而且国家对“巴盐古道”的统辖、管理也反映出了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盐道作为交通要道的交汇点,各地民族的社会和文化不断相互影响和熏染,频繁的商贸和移民活动,形成了多样性的民族关系和特征。在此基本状况下,少数民族与汉族往来密切,互通婚姻,加强了与中央的联系,民族地区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改变,少数民族也在不断“汉化”。
“‘民族走廊’对于在其中活动的历史民族或族群而言,既有山水交通之便,又有山水屏障之用;既可为迁徙、流动的交道,又可为退避、封锁的庇护地,以求民族及其社会文化的自我保存。正因为有保存的条件,才能使‘民族走廊’积淀民族文化,成为历史文化的沉积地带。”[19]这是走廊内族群的复杂性,以及在互动中的多样化,而且在盐道上各个族群之间互动和依存的关系,正形成了一种“地域文化”。而且在“国家化”下推行的民族政策和汉文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社会有着多样性和特殊性的地域情结,即是民族凝聚感和认同感的表现。“巴盐古道”的地域特征是多元的,这一空间区域除汉族,还有土家族、苗族、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盐道上机械和自然移民潮使得民族不断融合,而且移民活动给这一地区带来先进文化和技术的同时,各种语言、风俗习惯又在不断碰撞和交流,形成了极其复杂的民族关系。
所以,巴蜀地区盐业和盐道的发展必然成为维系中央王朝与民族区域的重要物质手段,在记录着民族地区互动的同时,也强调了在各民族文化融合之下中原文化的主流地位,这也是对“国家化”的历史见证与文化记忆。
(三)地域和盐业文化的呈现
“巴盐古道”有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是一条文明交流与传播通道,且古道上的各种自然和社会元素滋生出的盐业文明,体现出一种文化大交融的局面,是极为珍贵的遗产和旅游资源。可以说“巴盐古道”不仅是经贸之道、政治之道,也是重要的文化之道,像“巴盐古道”这样即是连接“边缘”与“中心”的通道,不仅对所遍及的周边地域及族群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这样的影响已经又从政治文化形态不断延续,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巴蜀地区本身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因为盐道的发展,当地族群不断利用其扩展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以此与外界进行广泛交流,学习和吸收先进文化的同时不断发展创新。加上国家力量的渗透和移民文化的融合,巴蜀地区在文化交流和发展历程上具有鲜明的特点。
文化是历史的投影,“巴盐古道”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各种各样的文化因素不断产生,时刻反映着社会关系的互动,这样的互动在盐道集中反映了盐文化的特征,而且“在运盐过程中,沿途上各大名城名镇逐渐成型,成为了‘中国内陆最重要的文化沉积带”,“即所谓‘因盐成市’、‘因盐成城’。”[20]其中,一种是因产盐而兴的古镇,集中于渝东长江沿线,如巫溪县大宁古镇、云阳县云安古镇。另一种是因运盐而兴的古镇,如石柱县西沱古镇。西沱古镇作为”川盐销楚“盐道的起点和物资集散地,亦见证了历代的盐业文化活动。这些城镇大都呈现出强烈的地域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形态,这体现“巴盐古道”对于沿线的地域文化和传统集镇有着重要影响。再者巴蜀地区因为大量移民的涌入,形成许多帮派组织,而且这些组织兴建了各种宫、庙、馆、堂,“引起了巴蜀文化多方面的流变,诸如语言、风俗时尚、建筑风格、行为方式、衣物饮食、歌舞戏剧、婚丧嫁娶、祭祀礼仪等,都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21]因为盐业的发展,形成的“盐文化有着显著的地域性、民族性和连续性,有着极强的生命力、渗透力和传播力,在其不断变化和发展中,涵盖了从物质到精神的诸多领域。”[22]这样的文化特质是盐业历史多层面的表现,各种盐业文化资源的形成和发展充分体现了民间风俗以及族群集体行为。
再者“巴盐古道”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作为一种载体,它不仅发挥了自身的基础作用,而且作为维系民族发展的生命线的同时,更是文明进程的重要载体。
四 结语
“巴盐古道”作为古代巴蜀地区对官道的重要补充,它纵横交错数千里,对不同区域间交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巴盐的外运形成了中国资源跨区外运的典型工程,这样的通道不仅利于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管理,更促进了西南民族地区的发展,对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
“巴盐古道”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整个武陵地区“国家化”进程,对西南广大地区人民的生存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其亦成为连接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的纽带,促成了我国重要的民族区域文化形成。其重要的历史及社会地位不亚于“茶马古道”、“丝绸之路”。通过对“巴盐古道”的研究,以此能找到更多线索,能更加系统地了解该地区的社会发展情况,为相关学科研究整理重要的资料。
[1]常璩辑撰.华阳国志[M].唐春生,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301;297;312;300.
[2]郑慧生注说.山海经[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241.215.
[3]管维良.大巫山盐泉与巴族兴衰(上)[J].四川三峡学院学报,1999,15(3):16-21.
[4]陈世松主编.四川简史编写组编著.四川简史[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6:7.
[5]周勇.重庆通史:第1卷古代史、第2卷近代史(上)[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25;82-83;187.
[6]赵逵.川盐古道:文化线路视野中的聚落与建筑[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71;73;75;66;29.
[7]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79;268;181.
[8]石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石柱县志[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249.
[9]陈世松等撰.四川通史:第5册[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258;40;178.
[10]李良品.石砫土司军事征调述略[J].军事历史研究,2007(4):125-132.
[11]石亚洲.土家族军事史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11-115.
[12]郭正忠.中国盐业史:古代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79.
[13]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101.
[14]袁庭栋.巴蜀文化志[M].成都:巴蜀书社,2009:282.
[15]封明静,姚辉.“湖广填四川”与川东地区的开发[J].科教文汇,2008(8):192-193.
[16]任桂园.第二次“湖广填四川”与三峡井盐业及社会的发展变迁[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7,23(6):7-13.
[17]鲁子健.川盐济楚与四川盐业的发展[J].社会科学研究,1984(2):75-82.
[18]王果.移民入川与四川井盐的开发[J].盐业史研究,1991(2):29-40.
[19]李星星.论“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格局[J].中华文化论坛,2005(3):124-130.
[20]赵岚.“生态文化学”视域下的川盐文化体系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2013(1):72-75.
[21]赖悦.清代移民与四川经济文化的变迁[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5):147-153.
[22]宋良曦.盐史论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2.
K29
A
1004-342(2014)05-56-08
2014-07-11
本文系石柱基地科技创新专项基金项目(项目编号:SZ201209)。
陆邹(1986-),男,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杨亭(1975-),男,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