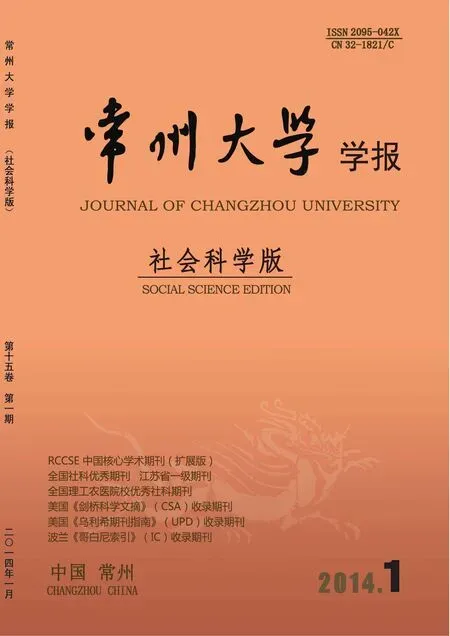论亚里士多德对“范畴”的理解
2014-03-25蒋鹏
蒋 鹏
(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275)
论亚里士多德对“范畴”的理解
蒋 鹏
(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275)
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是通过分析“S是P”这种基本句式而建立的。他将谓项的一般化,进而将范畴作为谓词系列的终点,并且,他依据“实体”与“属性”的不同内涵,将范畴分为十大类。然而,在《范畴篇》和《论题篇》中,亚里士多德却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范畴表”。之所以存在这种很少引人注意的细微差异,其原因还在于《论题篇》中的范畴表是通过追问《范畴篇》中的每一个范畴的“是什么”而获得的,二者之间承纳着一种递进的追问关系,而非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彼此之间相互独立。
范畴;述谓;第一性实体;是什么
一、“范畴”的正义
“范畴”一词的希腊文是kategoria,其来源于动词kategorein,其原意是“责备”、“责怪”,又有法律上“起诉”的意思。由此,动词kategorein可引申出“定罪量刑”的意思,即对被告所犯之罪行进行裁定,也是对罪行进行分类。亚里士多德将它引进到逻辑著作中,其意思就变成对主词的“述谓”。于是,它就成为句子中的“宾词”。因而,英文在翻译这个词时,则将之译为“category”,有的也将其译为“predication”,以凸现它在句子中的“述谓”角色。
在基本的句子形式“S是P”中,S则是P述谓的对象,是主词(或主体),P则是S的谓项。范畴则可以称为谓项的一般化,比如,某某东西是如何如何的,那么,范畴就是对“是如何如何的”中的“如何如何”的一般化。换言之,范畴即是最一般的“如何如何”,是主词(或主体)最为一般、最基本的谓词。在《范畴篇》第4章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基本的语言形式句子是由单个词结合起来而形成的,而单个词本身是非复合的。这些非复合的单一谓词分为10类,即实体、数量、性质、关系等等,它们即10大范畴。10个范畴体现为10种谓项,它们也就是“述谓”主词(或主体)的10种方式,比如(1)这是人(实体);(2)这是“三丘比特长”(数量);(3)这是黑色的(性质)……
由此观之,范畴就是谓词系列的终点。每一类谓项自身都是一个种属系列,比如这张桌子是两米长,两米长是长度。然而,“一个谓项表述一个主项无论在向上还是在向下都不能构成一个无限的系列”[1]290。“谓项在向上或向下方向都不可能进展到无穷”[1]289。于是,谓项之系列往下回溯的起点便是个别的、具体的事物,中间则是种、属,而往上的终点便是范畴。然而,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又在“实体”范畴中,区分出第一性实体与第二性实体。①“实体在最严格、最原始、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是既不述说个主体,也不存在于一个主体之中,如‘个别的人’、‘个别的马’。”而“第二性实体是指作为属而包含第一实体的东西”[1]6。包含第一性实体在内的第二性实体,可以述谓第一性实体,如张三是人,张三是动物。其划分的依据则根植于谓词的表述功能。然而,第一性实体是个体,只能作为主词而不能作谓词,这就与“范畴是谓项最高的属”相矛盾,范畴建立的依据在于对谓词系列的考量,将范畴作为谓词系列向上的终端。然而,第一性实体与第二性实体的区分也则主要集中在主词与谓词的区分之上。它们之间的区分原则似乎就有违范畴理论建立的大原则。
对此矛盾合理的解释是,在依谓词系列而建立的10大范畴中,实体与其他9大范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他9大范畴都可以成为实体的谓项,而实体可以作为它们的主项。而实体内部又存在着区分,它有只能作主项的部分,即第一性实体;又有既能作主项又能作谓项的第二性实体。第二性实体作主项,只是相对于其他9大范畴而言,而它作谓项则只能相对于第一性实体而言,第二性实体体现了第一性实体“是什么”。其他9大范畴也可以用来表述第一范畴,因为,“当一件东西被用来表述作为主体的另一事物时,一切可以表述宾词的事物,也可以被用来表述主体”[1]4。那么,它们体现了“第一性实体‘怎么样’”,因而,第二性实体——种、属——作为第一实体的谓项,与其他范畴作为第一性实体的谓项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相对于其它范畴而言,实体是“被述谓”的对象,是主词。然而,亚里士多德却将它放在依谓词特性而建立起来的10大范畴之首。为了化解这一矛盾,他才要对实体范畴本身进行再区分,以便区分出来其内部可以作为谓项的部分。如果说范畴理论的建立依据于谓词特性的话,那么,第一性实体与第二性实体的区分则依据于“一般语言的句式”——主词加谓词——的区分。实体的这种既可作主词又可作谓项的特点,也表现了它的独特性,因为,它是其它范畴的含义的中心指向,是其他范畴的中心,而其他范畴最终都必须载附于它。因而,它与“是”具有天然的亲缘性联系。
二、“范畴”之分
从范畴的功能起源的角度上来讲,它是对句式结构中“谓项”意义的提炼。范畴因此也是最一般化。由于范畴是个别物,种、属这一系列的终端,因而,它也是事物最高的属概念。从而,“那些事物被说成是‘在属上不同的’,则是由于它们分属于是的不同范畴”[2]141。这清楚地表明,那些属于不同范畴的事物就没有共同的属。从而,范畴就是那些归属于自身的一切事物更高的属。如此,如果有人把归属于一类属之下的事物同时归属于两种范畴,那么,这一定就是荒唐之举。
亚里士多德将具体的个体物称作第一性实体。由于个别具体的事物只能作主词,而不能作谓词,那么,能作为主词的谓词就只是作为种或属的类概念。如前所言,范畴是最高的属概念,它是种属系列的终端。因此,范畴也可以述谓第一性实体。因为,“当用一事物来表述作为主体的一事物时,一切可以表述宾词的事物,也可以被用来表述主体”[1]4。因而,范畴也是第一实体的最高谓词。如前所言,由于所有那些本身不是实体的事物只作为属性而归属于实体,并且,仅仅由于他们属于一个实体而存在着。因而,那些归属于其他范畴的事物也都可以述谓第一性实体。然而,我们必须正视如下差异,即第二性实体述谓第一性实体所表示的意义,与其他范畴述谓第一性实体所表示的意义之间的差别。前者意在说明第一性实体之“是什么”,而其他范畴则意在表明第一性实体“怎样”。第二性实体与第一性实体在本质上相关联,而述谓第一性实体的其他范畴与第一性实体没有本质上的关联,它们只是第一性实体的属性。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第一性实体是各种范畴都最终会依附的终端或基点,其他各种范畴都用来述谓第一性实体。然而,其他范畴来述谓主词第一性实体所表示出的意义却不一样,由此可知,它们与第一性实体存在着不同的关系。比如,第二性实体——种、属——与第一性实体的关系就是本质上的,它们意在说明第一性实体的“是什么”。其他范畴则只能说明第一性实体之“怎么样”,为第一性实体的属性。并且,它们都存在于第一性实体之上,而第一性实体是它们最终的载体。然而,即便如此,其余9种范畴存在于第一性实体中的方式却不一样,换言之,其他9种范畴各自与第一性实体中的关系存在着差异。比如,属于数量范畴的“五尺高”,我们可以用它来述谓第一性实体“苏格拉底”,即“苏格拉底是五尺高的”。该范畴则表示第一性实体的身高数量,因而,它与第一性实体之间只存在着量上的关系。另外,属于性质范畴的“有教养”,我们也可以用它来述谓第一性实体,如苏格拉底,即“苏格拉底是有教养的”,该范畴则表示第一实体的品性,因而,它与第一性实体之间只存在着质上的关系。“五尺高”与“有教养”都为第一性实体——苏格拉底的属性,然而它们之间是相异的,即“五尺高”与“有教养”不能相互述谓。因为,“一个谓项表述一个主项,除了表明是什么而外,谓项不能相互表述”[1]290。也就是说,一种属性不能是另一种属性的载体,它们都必须以实体为载体。这也就表明,各范畴之间是不相同的,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就体现为各自与载体——第一性实体——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关系。因而,“有多少个范畴,我们就必须对‘x属于y’以及‘x真实地表述y’这类论述作多少种意义的理解”[1]169。换言之,有多少种范畴,就有多少种事物存在于其载体中的不同方式,从而也就体现了它们与第一性实体之间存在的不同关系。
虽然各范畴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诸范畴之间的区分仅仅只是理性上的区别,是理性对它们与第一性实体之间的不同关系的提炼。它们之间的区分不是现实上的区分。因为,在现实中,诸范畴往往交织在一起而体现在第一性实体身上,比如,我们根本不能想象一个有一定身高的人没有肤色,没有一定的品性,没做出一定的动作(哪怕坐着和站着不动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动作),没有位于一定的空间之中,没有处于时间的链条之内。范畴之间的差异不是现实中的差异,即使第一性实体与第二性实体的区分也是理性上的区分,因为,人们所说的第二性实体,是指作为属而包含第一性实体的东西,就像属包含种一样,如某个具体的人被包含在“人”这个种之中,而“人”这个种自身又包含在“动物”这个属之中。这表明,第一性实体与第二性实体并不指两种不同的实体,第二实体是第一实体的类,而类概念是一个理智上的概念。
三、《范畴篇》与《论题篇》中的“范畴表”之间的差异
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第9卷第9章中,也谈到了对范畴的区分。②他说:“它们的数目是十个,即是什么(ti esti),数量、性质、关系、何地、何时、所处、所有、动作、承受。事物的偶性、种、特性和定义总是这些范畴之一,因为通过这些谓项所形成的任何命题或者表示事物的本质,或者表示它的性质、数量或其他某一个范畴。从这些显而易见:揭示事物本质的人有时表示实体,有时表示性质,有时表示其他某一个范畴。因为当有人在他面前,而他又断言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人或一个动物时,那么,他就是说出了是什么并且指名了那是实体;当在他面前的是一种白的颜色,而他又声称在他面前的是白或某种颜色时,那么,他也说出了是什么并指明了那是性质。同样,如果在他面前的是肘的量度,而他又断言在他面前的是肘的量度,那么,他也说出了是什么并且指明了那是数量。其他情形也是如此”[1]362。
这段引文也证实了我们前面的论述,即范畴主要依据主—谓这一基本句式而建立起来的。然而,与《范畴篇》中的范畴相比,这里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差别,即这里的首要范畴变成了“是什么”而非实体。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的现象呢?在笔者看来,这取决于我们对《论题篇》中对范畴的确立或划分原则的理解。
我们都清楚,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中最主要的任务是对命题的谓词进行划分,他主要依据的是如下两条原则:a.谓词和主词可以互换与否;b.表示本质与否。由这两种原则而组合成了4种变形规则:a.可以互换且表示本质;b.可以互换但不表示本质;c.不可互换但表示本质;d.不可互换且不表示本质。这4种情况依次表明的谓词就是定义,固有属性、属、偶性。而这4种情况下的谓词的进一步扩大就体现为上面引文中所列举出的10大范畴,换言之,这10大范畴就体现了定义、固有属性、属、偶性,正如前文的引文所言,“事物的偶性、种、特性、定义总是这些范畴之一。”由此观之,这里的范畴理论是严格依据谓词的意义而划分的。
如果说4种谓词的区分主要是相对于命题中的谓词与主词的关系而言,那么,范畴的分类则严格依据命题中谓词本身的意义而建立起来。在此,我们有必要回顾《范畴篇》中范畴的情况[3]。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主要依据这两条原则来进行范畴划分:a.述谓主体与否;b.在主体之中与否。据此又产生4种变形规则:a.述谓主体,却不在主体之中,即种、属、第二性实体;b.述谓主体又在主体之中,即一般的偶性;c.不述谓主体,却在主体之中,即特别的偶性;d.既不述谓主体,又不在主体之中,即个体、第一性实体。③
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关键在于区分出能作主词的与不能作主词的。重心在于分离出第一性实体,它只能作主词,而第二性实体与其他范畴则作谓词。因而,可以看出,《范畴篇》中范畴的划分很大程度上着眼于主词与谓词之区分的考虑,那里的范畴本身则是相对于一般的语言形式而来。反观《论题篇》,范畴的建立则严格围绕命题中谓词本身的意义而展开,而谓词之间区分关键还在于其表示“是什么”与否。[4]因而,“是什么”位居10大范畴之首就可想而知。④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上面引文中的这几句话,“当有人在他面前,而他又断言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人或一个动物时,那么,他就是说出了是什么并指明了那是实体;当在他面前的是一种白的颜色,而他又声称在他面前的是白或某种颜色时,那么他也说出了是什么(本质)并指名了那是性质……”这几句话初读时意思含糊,为了提取它的确切含义,我们有必要再次对它进行一番“解剖”。首先,在这几句话中,已经出现了上面所言的两类范畴表的交织,第一类:实体、数量、性质……;第二类:是什么、数量、性质……那么,它们两者的关系如何呢?王路先生认为,第二类范畴表位居首位,而第一类范畴表则是对第二类范畴表的进一步说明,其理由在于,第二类范畴表是针对谓词的类,重点在于说明范畴与谓词的关系。第一类范畴表则是“让人们注意语言差异,同时阐述本质,但表示的东西可以不同。比如,‘动物’阐述人的本质,表示一个实体”[5]。但笔者认为,王路先生对这几句话的解释仍然不够清晰。按王先生的理解,就是当一个人被置于他面前,他说那呈现出来的东西是人或动物,于是乎他便说明了本质(是什么),表明了它的实体。当一种白色呈现于他面前时,他便说这呈现出来的东西是白的、或者是一种颜色。于是,他便说出了本质(是什么)且又表明了它的质。对这几句话的确切意义的理解还是含糊不清,因而我们必须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具体文本。
它的意思是表明每一个范畴都具有自己的“是什么”,换言之,“是什么”(本质)也出现在每一类范畴中,实体有实体的“是什么”,量有量的“是什么”,质有质的“是什么”。如下这句引文可佐证这层意思,即“从这些显而易见:揭示事物是什么(ti esti)的人,他有时在表明实体,有时表明性质,有时表明其他一切范畴”[2]152。然而,亚里士多德在其他地方又说:“我们说它是什么时,就不说是白净的、是热的、是三肘长,而说是人,是神”[2]152。如此以来,“是什么”就只是对实体而发出的提问,“是什么”就只限于实体身上。面对这样的矛盾,我们就难免发出这样的疑问:“是什么”属于全部范畴呢,还是只属于实体范畴呢?对这一疑问,亚里士多德已自行做出了答复,“在一种意义上,是什么表示实体,表示着这个。在另一种意义上,则表示每个范畴,量、质以及诸如此类。正如是适用于万事万物,而意义却有不同,有的是在原始的意义上,有的则在附带的意义上。同样,是什么在单纯的意义上适用于实体,在某种意义上适用于其他。例如,我们可以问,质是什么,故质也是一种是什么,但并非在单纯意义上说”[2]158。这样一来,我们马上就会明白,“是什么”虽然体现在每一种范畴之中,但却要立足于某种意义上才能做出这样的表述。在“单纯的意义上”,“是什么”适用于实体;在“另一种意义上”,即“附带的意义上”,“是什么”才适用于一切范畴。如此,“是什么”体现在各种范畴中的地位就不一样了。换言之,实体范畴所体现出的“是什么”才是第一位的,才是单纯的、原初的;而其他范畴所体现出的“是什么”则是附带的、衍生性的。比如,当我们面前呈现出红色时,我们可以说,这种红色是一种颜色,这样的表述表明了红色的“是什么”,“是一种颜色”就成为“红色”的“是什么”,这也就指明了红色自身之所“是”。然而,红色这样的“是什么”却是一种性质,是另一种“是”的属性。因而,“红色”本身所具有的“是什么”就不是原初意义上的独立的“是什么”,它必须依附于另一种“是”,即依附于一个主体,红色总是某物的红色。因而,实体的“是什么”才是独立的、自足的,它的“是什么”不会沦为属性的地位,其他范畴的“是什么”都是实体的属性。
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前面那几句意义含混的引文。在亚里士多德这几句引文中,交织在一起的两类范畴表的地位就不像王路先生所解释的那样,其真实的情况却与之完全相反。第一类范畴表(实体、数量、性质……)则应该居于首要位置,第二类范畴表(是什么、数量、性质)才是对第一类范畴的进一步说明,这样做根本不是为了“让人们注意语言的差异”,其重心而是为了让人们注意到“是什么”的不同地位。当人们知道红色、数量等之“是什么”时,同时意识到它们的“是什么”也是实体的属性,依附于实体。为了明晰起见,我们用更直观的方式呈现出两者之间的递进关系:
第一类范畴表:实体、数量、性质、关系……
第二类范畴表:是什么、(是什么)+数量、(是什么)+性质、(是什么)+关系……
第二类范畴表是通过追问第一类范畴表中的每一种范畴的“是什么”而获得的。由于除“实体”之外,其他一切范畴的 “是什么”都不具有最终的独立性、自主性,因而它们就最终沉落为实体的属性,从而依旧挂着自己的“旧名”。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有意将两类范畴表交织在一起,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让人们明白,除“实体”之外,其他范畴自身只拥有相对的独立性、自主性。同时,他也是为了突出其他范畴对实体的绝对依附关系、以及实体的独特地位。照此来说,《范畴篇》中的范畴表与《论题篇》中的范畴表就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彼此相互独立,而是承纳着一种递进式的追问关系。“是什么”是对“是什么?”这一疑问的回答,而之所以能够发出此问,其前提必定是“是”。只有当这个询问的对象“是”时,才能去追问它“是什么”,进而才能得知它的“是什么”。换言之,只有先“是”,才能“是”出点“什么”。
注释:
①“实体”一词的希腊文是ousia,它是由动词不定式einai的现在分词的阴性单数形式所形成的。波埃修斯在译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时,最早用“substantia”来翻译ousia,之后该译法也为英语学界所采纳。不过,欧文斯(Owens J)批评了这种译名。他认为,用substance去翻译ousia就没有体现它与einai的直接联系;另外,在亚里士多德那,ousia乃是“是”的核心,其他所有的是者都依赖于它,它带有“事物中是的原因”的意味,如果用“substance”去翻译ousia,就会给人某种处于某事物“之下面”的意味,似乎ousia就是在某物之下的支撑点、载体,而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本意相差甚远。因此,他建议用“entity”来翻译ousia。在《范畴篇》中,与其他范畴相比较而言ousia还有载体的意味,用substance来翻译还显得比较适宜。但在《形而上学》第7卷第3章中,当亚里士多德着手研究具体事物时,他则认为具体事物乃是质料与形式所构成的复合机构。在这种复合结构中,他继续追问,这种结构的组成部分中哪一个才是primary ousia(第一性的本是)?如果按《范畴篇》中实体即主体的观点,具体事物内部的质料就该为primary ousia,因为我们把具体事物的所有属性(长、宽、高……)都剥离开去,剩下的唯一载体就是质料。然而,亚里士多德断然否认实体为质料,因为质料是毫无规定性的、无限潜在的基质,只有“形式”才凸现出实体的“这一个”和“分离”的特性,所以用“在某某之下”、拥有“载体”意味的substance来翻译就体现不出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推进。为凸显ousia与einai的联系,以及ousia本身所具有的“根据”意味,余纪元先生建议将ousia翻译成“本是”,王路先生则建议将其译成“所是”或“所是者”。
②在《论题篇》中译本中,ti esti被译成“本质”。而苗立田先生则将《形而上学》中的ti esti翻译成“是什么”,其理由是,“这个是什么,既可以当作谓词,又可当作所以是的是,当作本质和形式。在作谓词时就是一般。……但在它不再单纯是表示是什么,而是表示其所以是什么(to ti en einai)的时候这个ousia就是在原理、认识和时间方面的第一”。基本上讲,一个ti esti就是某物的ti esti,是对“这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它也含有本质的意思,但如果翻译成“本质”,就体现不了其与希腊文esti的联系。
③陈康先生认为,这里的“主体”一词是多义的。“在第一条原则中,它指某某东西所表述的那个主词(subject),在第二条原则中,却是指有某某东西附存在其中的那个基质(substratum)。因为,这两条原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一个是逻辑原则,另一个是形而上学原则”。
④布伦塔诺(Brentano F)将其称作“定义力度”(the defining power)的强弱程度。
[1]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2]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3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3]陈康.论希腊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84.
[4]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笺注[J].哲学译丛,2000(1):92.
[5]王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42.
On Aristotle′s Understanding of“Category”
JIANG Peng
(Institute of Advanced Humanities Studies,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Aristotle′s theory of category is based on his analysis of this basic sentence-“S is P”.He made the category as the generalization of predicates,as well as the end point of these series.Based on the different connotations between“entity”and“property”,Aristotle ultimately divided category into ten categories.However,he gave two different tables of categories in Categories and Interpretation.The reason why there is this delicate difference is that the table of categories in Interpretation is obtained by asking“what it is”to every category in Categories.These two kinds of categories are not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There is a progress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category;predicate;primary entity;what it is
B811.22
A
2095—042X(2014)01-0016-05
10.3969/j.issn.2095—042X.2014.01.004
(责任编辑:刘志新)
2013-11-05
蒋鹏(1984—),男,四川遂宁人,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