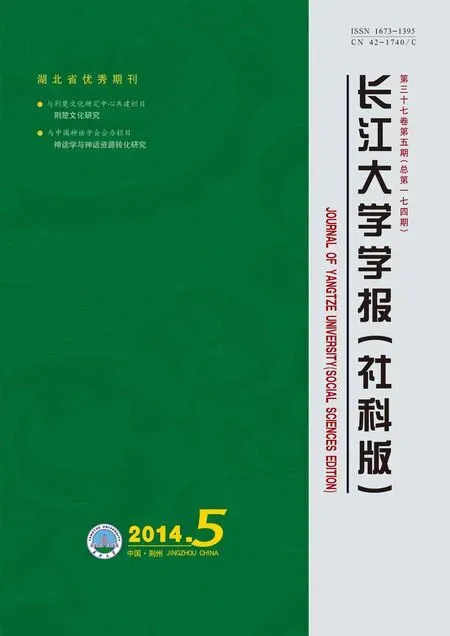文化交流视域下的甘南藏区汉传佛教
2014-03-25陈改玲刘红梅
陈改玲 刘红梅
(西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甘南是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藏族、汉族、回族是其主体民族。就宗教信仰而言,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多宗教并存,是甘南宗教最为突出的特点,宗教间的交流借鉴,是甘南宗教文化的普遍现象。本文主要探讨甘南汉传佛教和当地藏传佛教及内地汉传佛教的关系,以揭示其在汉藏文化交流、民族团结和地方稳定发展中的作用。
一
汉传佛教在甘南传播历史悠久。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开始传入甘南。吐谷浑政权在甘青立国350多年,其佛教文化对甘南的影响不可忽视。据学界研究,甘南州卓尼县阿子滩乡和临潭县交界处的牛头城遗址,即为吐谷浑衙署驻所,其地出土有莲花纹瓦当和头上有髻,双手捧莲花枝形鷯足的供养人状瓦当,说明吐谷浑佛教的兴盛。[1](P111)唐朝中叶,吐蕃占陇右,在河、洮、岷广修佛寺,此时甘南汉传佛教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明代,汉族大量移居甘南,汉传佛教随之复兴。明代甘南境内较大的汉传佛教寺院,有临潭县永宁寺、慈云寺,临潭冶力关桥头寺,临潭扁都红崖紫云寺。清代,甘南所属有不少汉传佛教寺庵:“云山观在城北凤山之第二峰;清凉寺在本城东,俗呼东庵;重兴寺在西城外半里,今圯;慈云寺在旧城,一名水月庵,明万历四十年建,国朝顺治十八年重修,乾隆十二年补葺之,道光八年增修;永灵寺在旧城内,有古钟一口,雍正九年建,嘉庆九年邑人重修;势至庵在旧城东城上,相传为吐谷浑家神,乾隆十年修,道光二十二年重修;铁头庵在本城西,今废;李家庵在本城西街,今废;冯家庵在本城西街,今废;姚家庵在本城北街,今废;洛藏庵在厅治南三十里;天竺寺在厅治五里,石壁上有茶马;迎水寺在厅治东十里,一名扁都庵;回龙寺在秋峪山;普朝寺在厅治北七十里;中禅寺在厅治北六十里羊撒河阴,山明水秀,古松参天。”[2](P240~243)据研究,清光绪年间,临潭、卓尼一带还有为数不少的汉传佛教寺院:临潭县扁都有汉传佛寺迎水寺,红崖有天竺寺,羊沙有中禅寺,冶力关有桥头寺,安乐山有普朝寺,临潭县城有慈云寺。宣统时,洮州佛教寺院多达54所,其中番寺45所,汉寺9所。[3](P50)汉传佛教在甘南传播历史虽远,但并无清楚的承继和连续性,大体上随着汉族势力的进退而兴衰。
当代汉传佛教仍是甘南多元宗教的重要一元。寺院的新建和恢复,居士佛教的发展,民间佛教信众的增加,昭示着甘南汉传佛教发展新阶段的到来。当代甘南汉传佛教主要分布在甘南汉藏杂居地区,以临潭、卓尼汉藏杂居地区、合作市为最集中。甘南汉传佛教发展的地区与历史上的分布大体相同。当代甘南汉传佛教与历史上没有明确的承继关系,其大多是改革开放后,在党的宗教信仰政策自由的背景下,受周边的影响而发展传播的。
甘南汉传佛教信仰以寺院为中心。当代甘南汉传佛寺主要有临潭县城的慈云寺、合作市的二郎庙上寺、临潭县新城重兴寺、冶力关宏慧禅寺等,其中规模最大的为临潭慈云寺和合作二郎庙上寺。甘南汉传佛寺在寺僧人很少,信众比较分散,远不如当地的藏传佛寺那样繁荣昌盛。在非宗教节日,寺内也很冷清。
甘南汉传佛教的中坚力量为居士。甘南的居士分布比较分散。其主要分布在汉族人口居住较为集中的临潭、卓尼的汉藏杂居地区和合作市等地。临潭县的城关、冶力关、新城、新堡等乡镇和临潭、卓尼交界一带的阿子滩乡、木耳乡等地,居士最多。居士主要为净土宗。当地百姓能够念诵净土经典。甘南州府合作市也有不少居士,并成立了自己的宗教活动场所居士林。居士林在合作市西路,供奉着西方三圣,有佛缘网赠送的净土大藏经。合作居士林是开放的汉传佛教信仰场所,受市佛教协会和宗教局管理,有严密的戒规和组织。
民间汉传佛教信仰是甘南汉传佛教的基础。民间佛教是佛教流传于中国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而形成的,属于正统佛教的一种变形,是民俗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4]受自然环境和浓厚的宗教氛围的影响,甘南汉族民众的宗教渴求比较强烈。由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藏传佛教对他们来说可望而不可及,所以,汉传佛教在甘南普通民众中有着广泛的基础。但是,要成为汉传佛教信徒,需经由一系列复杂的程序、仪轨,民众因此望而却步,因此,普通民众选择在念佛堂或嘛呢房寄托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不皈依。甘南许多汉族聚居村和汉藏杂居村落,都有自己的宗教活动场所嘛呢房。嘛呢房有的以汉传佛教为中心,杂以汉藏民间信仰,如卓尼县古战川村的嘛呢房;有些以民间信仰为主,杂以佛教信仰的成份,如卓尼县那子卡村和菜子村的嘛呢房;也有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融合的,如卓尼申藏乡申藏村的嘛呢房。甘南民间汉传佛教信仰具有多元化的特点。
二
甘南藏族自治州主体民族为藏族,信众最多影响最大的宗教为藏传佛教。从信仰场所的选择到建立,从重大佛事活动到日常的礼佛仪轨,甘南汉传佛教无不体现着藏传佛教和藏文化的影响。
甘南汉传佛教的发展与当地藏传佛教高僧大德及藏族民众的支持密不可分。二郎庙上寺在甘南州府合作市,其北千米之遥,便是合作市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米拉日巴佛阁(民众俗称九层楼)。二郎庙上寺山坡下的居民,也有不少院内贴着十相自在图的藏族民众。二郎庙及上寺建于民国年间,在文革时期毁坏殆尽。1988年,信徒罗尕宝联络合作市上卡加、下卡加、夏河县唐尕昂、博拉等地的汉族群众,筹措资金,准备重新建寺,请藏传佛教大德德尔隆寺六世活佛赛仓·罗桑华丹举行净地密乘“萨乔”破土,安放养地宝瓶,卜算吉日动土兴建,由甘南夏河隆瓦林场赠送木料,经当地信士的筹措,建成了现在的二郎庙上寺。二郎庙作为上寺的护法殿,2012年重建影壁时,得到了合作市和附近各族民众的大力支持,各界纷纷捐款资助。据《甘南发展》编辑马旭先生的调查,二郎庙上寺在2005年,信众近10余万,主要分布于合作市的那吾、上下卡加、夏河县的唐尕昂、博拉等乡。这些地区都为藏族聚居区,不难推测,其信众不完全是汉族。合作居士林建于1990年,林内除有净空法师、上海大德长老郑颂英居士题字外,还邀请著名藏学家、德尔隆寺六世活佛赛仓·罗桑华丹为居士林题写了藏文名字。2009年,经居士林新一届民主管理委员会和广大居士的努力,迎请供奉了西方三圣坐式铜像,邀请合作寺崴日仓活佛亲自为佛像装藏,并进行了各种加持。在合作居士林网站的照片中,有四位藏传佛教喇嘛在护法韦陀装藏仪式上诵经。
信仰仪式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吸收了大量的藏传佛教因素。甘南汉传佛教信仰吸收借鉴了大量的藏传佛教因素,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汉藏文化融合的特点。第一,在日常诵经时,汉传佛教信徒把南无阿弥陀佛和藏传佛教的唵嘛呢叭咪哄六字真言并用于念诵的过程中。在民间佛教信仰中,地方民众把念佛经俗称为念嘛呢,即念诵六字真言。六字真言为密教咒语,又称六字大明咒、观世音菩萨心咒,在藏区广为流传。藏族民众时时处处念诵六字真言,并将其刻于建筑物、山岩、法器上,以示尊崇。藏传佛教把六字真言看作经典的根本,主张信徒要循环往复吟诵,才能积功德。藏区的汉传佛教信徒也以念诵六字真言为积公德和求福祥的重要手段。合作市东山念佛堂的信众多为未皈依的普通汉族信众,以女性居多。她们不会念高深的佛教经典,主要念诵六字真言。民众俗称其嘛呢阿婆。在民间汉传佛教信仰场所,念诵六字真言为最普遍的礼佛祈福的仪式。民众坚信:念诵六字真言,可以积无上公德,死后可以进入西方净土极乐世界。汉藏杂居地区民俗:人辞世后,要在其口中放入嘛呢籽,据说是为将来见到佛祖,以证明自己念诵了嘛呢,这样就可以进入佛国净土。第二,藏传佛教的煨桑炉和煨桑习俗,在甘南汉传佛教信仰场所十分普遍。煨桑是藏民族一种特有的宗教与民俗仪式,又称烟祭。藏民族认为:桑烟能够到达天神居住的地方,可以使人间的美味传递上去,使得众神欢喜。[5]在藏区,有人烟的地方就有寺院,有寺院就会有燃着的桑烟。藏区普通人家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煨桑炉,有的砌在院子里,有的砌在高高的屋顶上。受藏传佛教的影响,甘南的汉传佛教寺院及民间佛教信仰场所都有煨桑炉。二郎庙上寺的大门口有白色的煨桑炉,笔者几次进行访查时,煨桑炉都有刚燃烧过的灰烬,煨桑的材料有松柏枝、糌粑、各种水果和馒头等。合作二郎庙大门口有一对白色煨桑炉,所用燃料与上基本相同。临潭慈云寺的山门右侧即是白色的煨桑炉。民间嘛呢房都有煨桑炉,在重大节日会伴有隆重的煨桑仪式。甘南汉传佛教在重大佛事活动时,几乎都先要煨桑。第三,酥油灯。点酥油灯是藏传佛教信徒礼佛的主要仪式。在甘南汉传佛教信仰场所也供着酥油灯,其燃料有两种,一种为酥油,一种为菜籽油。甘南汉藏杂居地区多以农为业,酥油比较稀缺和珍贵,多以食用菜籽油代替酥油。临潭慈云寺、古战川嘛呢房、申藏嘛呢房、木耳念佛堂等均在佛前供酥油灯。其与藏传佛教点酥油灯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灯的形制也与藏传佛教相同。点酥油灯是当地汉传佛教信徒礼佛不可缺的仪式,地方民众称做灯。第四,风马旗。风马,也叫“经幡”、“祭马”、“禄马”、“祈愿幡”等,藏语称之为“隆达”。“隆”就是风的意思,“达”意为马。风马即:风是传播、运送印在经幡上的经文远行的工具和手段,是传播运送经文的一种无形的马。[6]在藏区,婚丧大事,建房,外出朝拜,无一例外地都会插挂五彩风马旗,以表达自己的求吉心愿,祈求佛的庇佑。风马旗随风飘动,代表着信徒不断地念诵经文。甘南汉传佛寺和民间佛教信仰场所都挂着各色的风马旗,风马旗上印着藏文六字真言、经文、咒语。慈云寺的山门外,风马旗和黄红绿各色缎带一起飘扬在寺院门前,使人觉得和谐而安详。合作二郎庙上寺正对着山门的护发殿后挂着各色风马旗。哈达,作为藏传佛教祈求吉祥的象征,在藏传佛教寺院随处可见。甘南汉传佛教信仰场所都有献祭的各色哈达。二郎庙、二郎庙上寺和念佛堂的共同山门上挂着长长的白色哈达,在远远的山坡下清晰可见,使人感觉和谐安详。作者调查的古战川嘛呢房、那子卡嘛呢房、申藏村的嘛呢房的佛像前,堆盖着各色哈达,合作东山念佛堂的堂内挂着精美的华盖,在西方三圣前还献着诸多的哈达。哈达是甘南每个汉传佛教信仰场所必不可少的饰物。第五,朝拜藏传佛教寺院。在甘南,不论是藏传佛教信徒还是汉传佛教信众,拉卜楞寺和禅定寺都是他们心中最为神圣的地方。嘛呢房的老人们视能去拉卜楞、禅定寺朝佛为最大的心愿,若能得到高僧大德的摩顶赐物,更是其莫大的荣耀。居士林的信徒也会到藏传佛寺礼佛,有些居士也参加藏传佛教高僧大德举行的重大佛事活动。2013年,赛仓·罗桑华丹活佛在阿子滩玛纳举行佛塔落成赞礼,附近汉传佛教居士也积极参加。在普通信众心中,佛是相通的,不论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的佛,都能庇护他们。
建筑特色和装饰受藏传佛教影响。甘南汉传佛教信仰场所的建筑,也处处体现出藏文化的影响,具有汉藏文化融合的特点。有的建筑采用汉藏合璧式样的建筑风格,那子卡的嘛呢房和阿子滩乡古战川村新建的嘛呢房,外观都是汉藏合璧的建筑风格,顶部为汉式的飞檐斗拱,墙体为藏式碉楼建筑风格。莲花山上的莲花宝殿,更是鲜明的汉藏合璧的装饰风格,体现出汉藏佛教文化在当地的融合和借鉴。藏传佛教的十相自在图,在甘南的汉传佛教场所也不乏见。十相自在是时轮宗概括其宗教教义的一个图形,在藏传佛教的壁画、唐卡、塔门等许多地方非常常见,有的刺绣成护身符或者制成胸章佩戴在胸前。十相是汉语的翻译,在藏传佛教中为十个符号所象征的须弥山和人的金刚体的各部位。这十个符号包括三个图形和七个梵文字母,具有神圣力量,意义十分复杂。它标志着密乘本尊及其坛场(曼陀罗)和合一体,表达了无上密乘里时轮乘的最高教义,被认为具有神圣意义和无比巨大的神秘力量。[7](P81)慈云寺的观音菩萨殿和地藏王菩萨殿的大门上,都刻画着十相自在图,古战川村嘛呢房的大门上,也是两幅对称的十相自在图。
三
甘南汉传佛教不仅受当地藏传佛教和藏文化的影响,作为内地汉传佛教的组成部分,它和内地佛教也有着不可分的各种各样的联系。它联系着藏区和内地,沟通了藏文化和汉文化。
当代甘南汉传佛教是在内地佛教的影响下发展壮大的,和内地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甘南汉传佛教历史悠久。随着汉族移居甘南各地,在汉族居住较为集中的地方,就逐渐形成了汉传佛教信仰场所。据调查,合作二郎庙上寺在民国年间已经存在,当时,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脚户和商人到甘南经商,为了祈求生意兴旺,就在二郎庙上面建立了礼佛场所,此即今之二郎庙上寺的前身。当代甘南汉传佛教信仰多是在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从发展过程看,其离不开内地宗教界人士的帮助和支持。1990年初,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就有在家礼佛的居士;1992年,甘肃省原佛教协会副会长、酒泉法幢寺方丈融照法师来合作弘法,座前受皈依的居士有300多人。为方便居士的交流,在上海大德居士郑颂英的指导和支持之下,建立起合作华藏安养念佛堂,后念佛堂改称居士林,聘请原安养堂居士现分别为西安卧龙寺常亮法师、杭州天钟禅院大藏法师为住持和顾问,同时也经常得到苏州重元寺能广法师的关心和帮助。
得到了内地佛教界的支持和帮助。甘南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寺院发展的最大困难是资金短缺,所以寺院和居士林及民间信仰场所,都不可能有资金为信徒购买相关的佛教典籍。寺院、居士林、念佛堂的佛教典籍,多为内地汉传佛教寺院、佛缘网、内地高僧大德赠送。合作东山念佛堂、慈云寺、合作居士林等的净土大藏经,都为佛缘网所捐赠。慈云寺的发展,更得到了内地及周边佛教界的帮助。1994年,甘肃省临夏潮音寺向慈云寺捐赠各类经书两千多册;1996年,南京金陵刻经处赠《般若经》一部及其他法宝;1997年,香港宝莲禅寺赠《大方广佛华严经》及其他法宝;2000年,福建莆田广化寺及甘肃临洮县、甘谷县佛教协会,向慈云寺捐赠各类经书三千多册;2001年,兰州佛教界的大德居士从缅甸请回1.6米高的西方三圣像赠给慈云寺;2008年,慈云寺能广法师在南华本纯法师相助下,迎请华严经250部及其他法宝上万册,为慈云寺佛教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常请内地法师弘法。为丰富甘南广大汉传佛教信徒的生活,甘南汉传佛寺和居士林经常迎请内地汉传佛教高僧弘扬佛法。2009年农历二月二十四日,西安市佛教协会秘书长、西安卧龙禅寺西堂释常礼、副寺释常印、释常亮等法师来合作,在合作佛教居士林为众居士答疑解难,授三归五戒,举行放生法会,东山念佛堂随之邀请三位法师讲经布道。2010年6月29日,西安卧龙禅寺西堂常礼法师、合作居士林主持常亮法师、定西佛教协会会长本觉法师,为合作居士林西方三圣佛像举行了开光典礼。参加法会的有北京大佛寺、定西华严寺、甘南藏传佛教曲宗红教宁玛尼姑寺,以及临潭慈云寺、临潭新城重兴寺、临潭冶力关宏慧禅寺、合作东山念佛堂等。临潭慈云寺、合作二郎庙上寺等也定期或不定期地礼请内地汉传佛寺高僧来弘法。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与汉文化、藏文化结合,分别形成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两者都属于大乘佛教,在宗教教义和仪轨等方面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加之历史上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在汉藏交界地区的不断融合和吸收,更密切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甘南处在汉藏结合部,是汉藏文化交流的前沿。在这里,汉藏佛教文化的融合已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汉传佛教在甘南传播历史久远,甘南汉传佛教的信众主要为汉族。甘南汉传佛教和当地藏传佛教以及内地的汉传佛教之间都有密切的关系,是沟通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桥梁,在甘南多元宗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甘南地区的和谐稳定与民族团结意义重大。甘南汉传佛教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吸收借鉴藏传佛教因素,寻求藏传佛教的支持和帮助,加强汉藏佛教间的了解,得到了藏传佛教信众的认同,加强了汉藏两族间的团结。此外,处在藏区的汉传佛教也不是孤立的,其强大的支持来自于周边及内地的汉传佛教寺院和高僧。甘南汉传佛教和内地佛教界有经常性固定的联系,如迎请内地的高僧大德来甘南弘法讲经,到内地的汉传佛寺学习和深造,内地佛寺和佛教机构在资金、佛教典籍等多方面给与其帮助,所有这一切,使得甘南汉传佛教不断得到发展壮大。
[1]李振翼.甘南藏区考古集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2]张彦笃.洮州厅志(卷三·建置)[Z].光绪三十三年抄本影印.
[3]马晓军.甘南宗教演变与社会变迁[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
[4]宇恒伟.民间佛教基本结构解析[J].五台山研究,2012(2).
[5]钟静静.藏族煨桑仪式及其文化内涵的研究[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1).
[6]李连荣.藏族风马旗观念的起源与民俗象征[J].中国藏学,2008(2).
[7]黄明信.西藏的天文历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