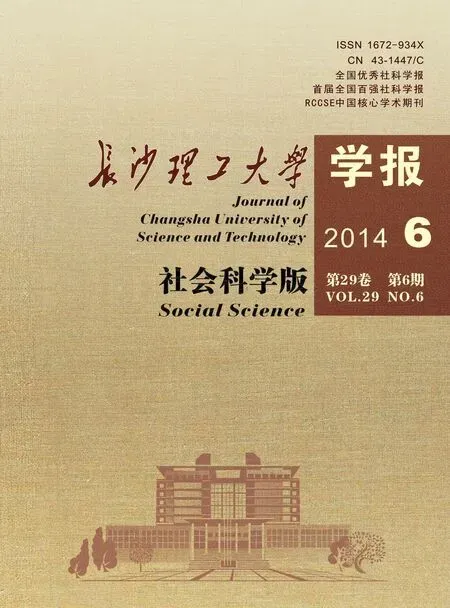汪曾祺短篇小说《复仇》的修辞艺术
2014-03-25王雨佳
王雨佳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汪曾祺短篇小说《复仇》的修辞艺术
王雨佳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文章意在从W.C.布斯关于修辞的理论出发,通过对叙述声音、叙述视角、叙述人称、画外音的分析,探索汪曾祺短篇小说《复仇》是如何体现“氛围即人物”这种修辞技巧的,并着重分析作者是如何通过这种修辞技巧形成他自己的文体特色的。
小说修辞;叙述声音;叙述视角;叙述人称;画外音
W.C.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中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这种关系就是一种修辞关系,即“作者通过作为技巧手段的修辞选择,构成了与叙述者、人物和读者的某中特殊关系,由此达到了某种特殊的效果。”[1]这就回归到了古希腊的修辞学本义:研究作者叙述技巧的选择与文学阅读效果之间的联系。
汪曾祺说:“(我的小说)有时只是一点气氛。但我以为气氛即人物。一篇小说要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人物。”[2]他还说,“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3]“气氛即人物”就是汪曾祺的修辞选择,其产生的阅读效果就是使小说蒙上一层清淡而平和的氛围,让读者感觉其小说不重故事而重感觉、重印象、重意境,并且其中散文的味道很重,凸显出一种怀旧的情绪,由此形成了汪曾祺独特的文体特色。笔者意在从“氛围即人物”出发,以汪曾祺青年时代标志性的作品《复仇》为重点,着重分析汪曾祺是如何通过这种修辞技巧来形成他自己的文体特色的。
小说《复仇》的主题显然是刻意对中国古代传统武侠小说的一次模仿,但如何演绎这样一个主题,使“复仇”最终变成了“弃仇”,如何把传统意义中有仇必报的复仇者,例如割下自己头颅献给黑色人来完成复仇的主人公,诗意的演绎成一个四处漂泊、在孤独的旅途路上落寞寂寥,最终却又顿悟的弃仇者?我们认为不仅仅是因为汪曾祺采用了意识流的方法,使我们能深入弃仇者的内心去感知了解他,从而能相信他最后选择弃仇是合理的;更是因为作者在行文架构中,通过对叙述声音的变化和叙事视角的转换烘托出一种氛围,使人物在这种氛围的包围下去选择弃仇,即烘托出主人公在复仇的旅途中所显示的疲倦、孤独、矛盾和坚持等纠缠在一起的情绪意识氛围。加之,作者又通过叙述人称的变化来象征暗示主人公矛盾的心理;通过叙述者的画外音,规制了主人公的选择,最终才塑造出这一生动独特的人物形象。
一、叙述声音的变化:由混乱变得清晰
任何小说都离不开叙述,任何叙述都离不开叙述者,只要有语言,就有发出声音的人,这就叫叙事声音。《复仇》中很明显有两种声音纠缠交替出现:故事讲述者的声音和主人公的声音。文本中故事的讲述者,他像上帝一样居高临下俯视作品中的人物,自由的展示小说中人物的观念和情感。文本中的主人公则凭借独白、梦境、回忆、话语等,强烈的显示出自己的声音。这种两种声音在小说开始时呈现的是混乱的、纠缠的状态,但随着小说的发展这两种声音逐渐分开,变得清晰起来,这也意味着作者的叙述意图从混乱到清晰,最终直达“弃仇”这一抉择,显示出作者精心的设计。
根据小说文本段落的设置,同时也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可以把《复仇》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一支素烛,半罐野蜂蜜……这是一条线的尽头了,再往前没有路了。”我们称之为“意识混乱的夜”部分。第二部分为:“他阖了一会眼。他几乎睡着了,几乎做了一个梦……万山百静之中有一种声音,丁丁然,坚决地,从容地,从一个深深的地方迸出来。”这一部分是“旅行人的梦和客人的夜”部分。第三部分为:“这旅行人是一个遗腹子……他为自己这一句的声音掉了泪,为他的悲哀而悲哀了。”这一部分叫做“复仇的原因”部分。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是剩下的篇章,即为“复仇的消解”部分。
“意识混乱的夜”部分,是小说中叙述声音最混乱的一部分,叙述人叙述的声音、叙述人评价的声音以及主人公的声音,通过自由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等方法自然的混合在一起。自由直接引语是指在没有引述句情况下,一字不动的保持了意识活动本来的语言形态,避免了叙述人的介入,主要用于人物的内心独白。间接引语是指引用时或多或少地使用了叙述者的表达方式,采用了以叙述者为基准的人称,人物的意识活动是通过叙述者间接传达给读者的。小说第一部分,叙述人的声音和主人公的声音主要就是在这两种方式之间频繁滑动,因此给读者的阅读造成一定的困难,使阅读的感受充满朦胧和困惑。例如:
“他一生没有呕吐过几回。一生,一生该是多久呀?我这是一生了么?没有关系,这是个很普通的口头语。谁都说:‘我这一生……’。就像那和尚吧,——和尚一定是常常吃这种野蜂蜜。他的眼睛眯了眯,因为烛火跳,跳着一堆影子。他笑了一下:他心里对和尚有了一个称呼,‘蜂蜜和尚’。这也难怪,因为蜂蜜、和尚,后面隐了‘一生’两个字。明天辞行的时候,我当真叫他一声,他会怎么样呢?和尚倒有了一个称呼了。我呢?他会称呼我什么?”[4](P126)
从修辞上来说,这一段话以非常复杂的方式从人物外部一直描绘到人物内心,并且不动声色的加入了作者的评论。“他一生没怎么呕吐过”到“一生,一生该是多久呀?”采用了直接引语的方法,自然的从人物的概括转向人物内心独白的描写。“他的眼睛眯了眯”,“他笑了一下”,又从主人公的叙述声音转换到叙述人的叙述声音,并且使用了间接引语的方法,让读者从叙述人的角度去理解主人公的内心。“这也难怪,因为蜂蜜、和尚,后面隐了‘一生’两个字。”则在叙述人描绘人物心理活动之中,悄悄的加入的叙述者评价的声音,因为这样有寓意的,有概括性的声音,既不可能是主人公自己发出的,也不同于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声音,只能是作者借助叙述者发出的评价的声音。
到第二部分,这样叙述的方式就开始慢慢减少,如此复杂的修辞手段只在个别的段落出现,大部分篇幅中叙述的方式变得明朗清晰起来,人物内心独白也会用显著的方式标明。比如,在段落中遇到主人公内心独白就会用引号引起来,“渐渐的,和尚那里敲一声,他心里也敲一声,不前不后,自然应节。‘这会儿我若是有一口磐,我也是一个和尚。’佛殿上一盏像是就要熄灭,永不熄灭的灯”;甚至会另起一行独自成段,来表明这是主人公内心的独白。这两种声音在这一部分慢慢分开,主人公的声音通过梦境和回忆逐渐占据了主要的叙述篇幅,叙述人的声音在这一部分则起着铺垫和象征的作用。例如叙述人在第二部分的结尾说:“我要走遍所有的路……很好。有人还要从没有路的地方走过去。”[4](P133)这是对后文仇人出现所做的一种铺垫,其中的“路”是对“弃仇”结果的一种暗示和象征,“走遍所有的路”即执着于复仇之路,“从没有路的地方走过去”却是放弃复仇之路,开辟新路。
到第三部分,叙述人的声音和主人公的声音则完全分开,我们能清楚的听到叙述人的声音在概述复仇者复仇的外部原因,我们也能清楚的了解主人公自己内在的复仇动机,只是这二者有着清晰而不同的音色,一个冷静客观,一个执着激烈。
第四部分则主要以叙述人声音为主导,引领读者观察复仇者一步一步走向最后的“弃仇”,很少出现的主人公的声音则在于揭示了“弃仇”部分原因,读者完全跟随着叙述人的声音完成了最后的阅读。
叙述声音从混乱到清晰,显示了作者对于最后“弃仇”的抉择所作的种种努力,即先由叙述人和主人公的声音的交错描绘出复仇者内心意识流动的混乱和复杂,从而烘托出一种疲倦、矛盾、困惑的复仇氛围,再凭借叙述人或明或暗的叙述声音对读者进行引导和控制,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使读者接受这样一个“弃仇”的结果。
二、叙事视角的转换:人物内视角向叙述人外视角的逐步转换
与小说声音从混乱到清晰变化同步的是小说逐步从描写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逐渐向描写主人公外部行为变化。也就是说,作者小说的安排从着力讲述主人公的内心慢慢向显示主人公的行为选择进行转换。在第一部分“混乱的夜”中,叙述者居高临下自由展示主人公的意识、想法,并辅以主人公内心独白来讲述复仇者的空虚无助,到第二部分“旅行人的梦和客人的夜”里,叙述者对主人公意识的挖掘进行了刻意的压缩,并以主人公的梦境和回忆的展示来代替其内心独白的发声,到第三、第四部分,则完全从外部进行描写展示,零星的主人公内心的描写则或多或少凸显了故事的寓意和走向。
叙述人的外视角与人物内视角的转换是视角转换中最常见的模式[5]。《复仇》中则使用了从人物内视角慢慢转换到叙述人外视角的叙述手段。因为小说大部分篇幅都是通过人物内视角进行叙述的,所以读者往往会忽略作者有意转向的叙述人外视角的描写。叙述人外视角所描写的部分对于消解复仇,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起了重要的作用。
读者从小说第一、第二部分的描写所烘托的氛围里,已经感知到了主人公在复仇的旅途中所显示的疲倦、孤独、矛盾、向往等纠缠在一起的心绪。而在第三部分的描写中,在叙述人外视角和人物内视角的滑动间,读者则会强烈感知到复仇的荒诞与虚无。作者通过叙述人外视角的描写,仅仅告诉读者:复仇者的父亲被人杀死,并且临死前留下了仇人的名字,母亲拾起父亲的剑,然后交给长大成人的儿子,于是主人公就走上了复仇的道路。简简单单的一段描述客观冷静,同时又没有讲述父亲被杀的原因,也没着力去挖掘在父亲死后,这个家庭的生活状况会是怎样不堪,明确的只是复仇者所必须担负的复仇使命。由此慢慢浮现出复仇的荒诞性质。之后小说开始滑入人物内视角进行描述,用复仇者的内心独白来加强这种使命感的强度:“复仇者是谁不重要,父亲是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肩上所背负的复仇的使命。”继而转入叙述人外视角,通过复仇者的话语:“你们知道这个人么?听说过么?……但是我一定是要报仇的!……即使我一生找不到你,我这一生是找你的了!”[4](P135)把“复仇”这个使命推向了一个极致,在复仇显现出荒诞的性质的同时,使之成为复仇者的人生。由此这部复仇的故事消解了鲁迅以来现代文学作品中关于复仇的意义:鲁迅借之唱出了一曲弱势者反抗强权者,平民抗击暴君的悲壮颂歌[6]。
第四部分“复仇的消解”部分,则如实的从叙述人外视角来进行描述,我们无法深入复仇者的内心,不能跟上文一般自如的感知复仇者复杂的心绪,只能跟随叙述人从外部去观察复仇者的行动,直到最终发现:“忽然他相信他的母亲一定已经死了……有一天,两副錾子同时凿在虚空里。第一线由另一面射进来的光。”[4](P136)由是我们才明白《复仇》的故事原来是一个“弃仇”的故事,除了知道象征道德钳制的母亲的死去,意味着复仇者所得到的精神上的解脱以外,我们很难准确把握复仇者“弃仇”的真正原因。又因为我们不能进入复仇者的内心,再加上前文所烘托的矛盾纠结氛围,作者留给读者想象复仇者“弃仇”的空间非常的大,整个小说的意味也就开阔起来。
在中国的山水画中,人们常常用留白来形容作品画面或者章法中有意留下的空白,这种空白给观者以很大的艺术想象空间,能产生一些特别的美学效果。《复仇》中,作者有意从人物内视角向叙述人外视角的转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最后的“弃仇”留白,使读者能产生无穷的想象和回味的余地,并且又由前文铺垫烘托的氛围解释了“复仇”的荒诞性和“弃仇”的合理性,从而在消解现代文学传统意义上复仇的同时,展示了作者对于复仇的理解和认识,寄托了他自己的情怀,最终使“弃仇”成为符合逻辑又能充分想象的世界。
三、叙述人称的变化与叙述者的画外音:规制人物的行为选择
《复仇》通篇以第三人称“他”为主要的叙述人称来进行叙述,但中间又加入了“旅行人”、“客人”用来指代复仇者,用其区别复仇者不同的心理,从而完成了对复仇者形象的充分刻画,并且在小说的结尾刻意添加“旅行人”来替代“他”进行指代,暗示复仇者最后的选择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人称的反复变化也象征复仇者从混乱的“他”到决绝的“他”的完成,突显了叙述人称变化的意义重大。
“旅行人”和“客人”的不同人称设定体现着复仇者身上两种不同的心理,叙述者已经在文本中告诉了读者,但需要读者去仔细的寻找。“旅行人”和“客人”第一次出现是在文本的第二部分,汪曾祺通过“旅行人”的梦境和“客人”的回忆的各色夜晚,继续烘托着一种朦胧纠缠的氛围,但同时作者也显示出这两种人称代词所代表的复仇者的性格:
“客人,这仅仅是一夜……
‘但是我知道我并不想在这里出家!’
旅行人一身都是力量,一直贯注到指尖。一半骄傲,一半反抗,他大声地喊:
‘我要走遍所有的路。’”[4](P138)
作者用了相同的方式告诉读者这两种人称代词所代表的不同的心理,即通过使用叙述人称+人物的独白的方式(并且通过独立成段的方式强调人物独白的意义)。客人象征着复仇者内心想放下仇恨,皈依佛门的心理,“旅行人”则象征着一直走在复仇这条道路上的复仇者执着的心理。通过叙述人称的变化,读者才可以更加明白第一部分中“他”混乱思绪的原因以及笼罩在全篇小说的这种矛盾纠缠的气氛的原因,即复仇者心里两种不同声音的碰撞所造成的混乱矛盾。并且在文本的最后刻意出现的叙述人称的变化显示了汪曾祺精心的设计:
“他直视前面,一个又一个火花爆出来。好了,到了头:
……旅行人看见两只僧衣的袖子。……旅行人看见他的手。……旅行人后退了一步。……旅行人木然。……他差一点晕过去:和尚的手臂上赫然有三个字,针刺的,涂了蓝的,是他的父亲的名字!
他简直忘记自己背上的剑了,或者,他自己整个消失,只剩下这口剑了。……
……忽然他相信他的母亲一定已经死了。”[4](P134-135)
路到了尽头,叙述人称从“他”开始转变为“旅行人”,这表明复仇的执着心理在这时压过“客人”的心理成为复仇者的主导心理。似乎复仇者要走到路的尽头,即人生的尽头。这时作者笔锋一转,开始描写复仇者身上背着的那口剑。文本前面说:“客人的手轻轻地触到自己的剑。这口剑,他天天握着,总觉得有一分生疏;到他好像忘了它的时候,方知道是如何之亲切。剑呀,不是你属于我,我其实是属于你的。”[4](P137-138)读者在这时才能体会,原来这时的“他”其实体现的是 “客人”的心理。于是“旅行人”和“客人”的心理在这里争锋相对。“忽然他相信他的母亲一定已经死了。”这一句话告诉读者“他”内心最后的抉择即“弃仇”。
由此复仇者“他”完成了内心的一次深刻的变化,作者并没有像前文一般从人物内心去描绘这样一种变化,而是以叙述人称的变化来记录这样一次激烈的碰撞,以一种不是很明显的方式完成了对人物的深刻刻画,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使这篇小说更难理解,但这种叙述人称的变化体现了汪曾祺独特的修辞方式。
从另一方面说,如果读者无法从叙述人称的变化中体会复仇者选择“弃仇”这个行动的原因,作者还通过画外音的方式继续引导读者去理解自己的意图。画外音原是指凡影片中发出的声音,其声源不在画面内的,即不是由画面中人或物直接发出声音,都称为“画外音”。在本文是指叙述者跳出叙述的故事本身所发出的声音,也就是说在文本中出现的第三种声音,既不是人物发出的声音,也不是叙述者叙述故事的声音。在文本中这样的声音很微弱,一点即过,但却体现了作者对于文本人物的规定和对读者的引导。例如这一系列的画外音:
“这也难怪,因为蜂蜜、和尚,后面隐了‘一生’两个字。
就是这一朵没有戴上的花决定了他的命运。
万山百静之中有一种声音,丁丁然,坚决地,从容地,从一个深深的地方迸出来。”[4](P129-135)
汪曾祺说过:“蜂蜜本身有一种香甜……老和尚代表了佛教教义。”[7]由此就能解释蜂蜜和和尚这两个意象所体现的作者的意图。和尚象征着依据佛家教义所进行的修行,蜂蜜则体现了人们能从这种修行中所得到的香甜,“一生”说明这种修行是需要坚持的。作者或许要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修行的人,最终才能得到这样一种香甜的回报,这种坚持可能用尽了人的一生。“花”则象征着一种美好,因为他的母亲没有戴过一朵花,即说明她的人生被复仇的执念所控制,于是决定了他的一生也终要被复仇控制。最后这句画外音:“万山百静之中有一种声音,丁丁然,坚决地,从容地,从一个深深的地方迸出来。”则体现了作者想出的解决仇恨的方法。杀人者通过开凿新的道路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去消解以前的仇恨,使其能过完他的余生,并终能体味甜蜜的味道;并且路的意象象征了解决仇恨的新的通途。通过这一系列的画外音,作者煞费苦心的引导读者去理解复仇者选择弃仇的决定,大部分读者最终也能通过这一方面(宗教教义)去理解复仇者弃仇的行为。
由此通过叙述人称的变化和叙述者的画外音,作者规制了复仇者的选择,使复仇者的弃仇行为得到合理的解释。
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里说,“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8]从《复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真正领悟了沈从文先生的这句话的。从叙述声音的变化到叙述视角的转移;从叙事人称的变化到叙述人画外音的凸显,作者无不是为人物服务,无不是为深刻挖掘人物服务。由此读者才能从这故事性不强甚至没有多少故事的小说中,强烈的感受到人物的存在,感受到作者的存在。通过对《复仇》如此细致的分析,我们才最终能体味到汪曾祺所说的修辞立其诚的真正含义。
[1][美]W C布斯.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
[2]汪曾祺.自序[A]//汪曾祺短篇小说[Z].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2.
[3]汪曾祺.桥边小说三篇[A]//中国当代才子书:汪曾祺卷[Z].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346.
[4]汪曾祺.复仇[A]//中国当代才子书:汪曾祺卷[Z].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
[5]董梅梅.小说叙述视角论[D].西安:西北大学,2010:34.
[6]李俏梅.鲁迅、汪曾祺和余华三部复仇小说之比较[J].广东社会科学,2006(01):137-142.
[7]杨鼎川.关于汪曾祺40年代创作的对话[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02):188-201.
[8]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A]//中国当代才子书:汪曾祺卷[Z].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104.
On the Rhetoric of the Short Story Revenge by Zeng Wangqi
WANG Yu-jia
(School of Liberal Art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Starting from W.C.Booth's theory on rhetorics,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voice,narrative perspective,voiceover,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Wang Zengqi embodies the idea of"atmosphere being the character"in her short story Revenge.It also analyzes how the author forms his own style by this rhetorical skills.
the rhetoric of fiction;narrative voice;narrative perspective;narrative person;voice-over
I207.427
A
1672-934X(2014)06-0134-05
2014-09-22
王雨佳(1990-),男,湖北浠水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