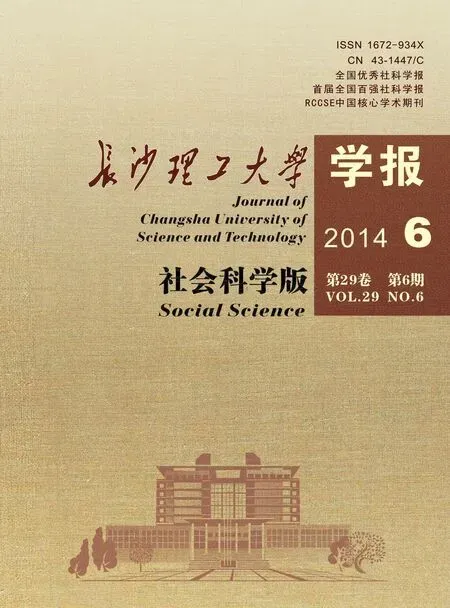流散与文化认同
——《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评析
2014-03-25张艳霞
张艳霞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流散与文化认同
——《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评析
张艳霞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多米尼加裔美国作家朱诺·迪亚斯的小说《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以多米尼加共和国遭受的殖民侵略与独裁统治为背景,描写了多米尼加流散群体受到的历史与现实的创伤。小说中过去与现在交替、人物的“缺失”与“再现”并存,不仅重塑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历史以及奥斯卡家族历史,还展现了流散者在美国遭遇的文化冲突与边缘化境遇。种族、阶级与文化差异以及无法逾越的他者身份造成流散者的文化归属与认同陷入困境,而多元的文化背景使杂交性的文化认同成为渴望寻找自己文化定位的流散者的一种生存选择。
朱诺·迪亚斯;殖民与独裁;流散;冲突与边缘;杂交文化
《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以下简写《奥斯卡》)是多米尼加裔美国作家朱诺·迪亚斯(Junot Díaz,1968-)的首部长篇小说,也是继其小说集《沉溺》之后的又一部佳作。迪亚斯凭借这部作品先后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及普利策小说奖,成为备受评论家关注的当代族裔作家之一。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采用片段式的叙述方式,从不同视角讲述了特鲁希略独裁统治背景下,多米尼加移民群体在美国的流散经历。两个家族三代人的故事不仅描绘了族裔流散群体移民后遭遇的文化冲突与边缘化,更展现了多米尼加乃至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历史,进而揭示殖民侵略带给多米尼加人民的创伤。对此,黄淑芳通过后殖民主义视角分析了小说多个层面展现的多元化特征,揭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族裔群体必然经历的多元生存环境。李保杰通过探讨文本重构历史的作用,分析虚构的文本如何再现多米尼加共和国历史。笔者从多米尼加移民群体的流散经历着手,分析殖民与独裁下的流散群体在美国遭遇的文化冲突及其造成的流散者边缘化身份,揭示多元文化环境下流散者的杂交性文化认同的必然性。
一、被迫流散与文化错置
流散(Diaspora)原指犹太人受到迫害后离开故土,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在当代后殖民语境中则指人们自愿或被迫地迁居他乡,并始终与故土存在割不断的联系[1]。流散主题是当代拉美裔文学叙述的主要内容,作为拉美裔文学一支的多米尼加裔文学也具有流散文学的普遍主题。这部小说中,除小说题目所指示的主人公奥斯卡的遭遇这条显性线索外,以母亲贝利西亚(以下简写为“贝利”)为代表的移民第一代的流散经历也以隐性叙述的方式,使小说情节错综复杂,这也是迪亚斯的目的所在:“使读者了解多米尼加历史和现实以及人们的流散。”[2]小说对贝利的集中叙述以重塑多米尼加历史为背景,特鲁希略的独裁统治及其推崇的男权主义思想是造成贝利被迫流散的直接原因,也是她与拉英卡极力避而不谈的创伤,然而根深蒂固的多米尼加文化又使贝利同时成为受害者与执行者。这样,少数族裔女性的身份以及文化的错置使她成为“流散地女王”,即“边缘”中的“边缘”。
小说在对多米尼加历史的重建中也对贝利的家族史进行了交代。卡布莱尔家族的破灭与特鲁希略的独裁密切相关,贝利的父亲因坚决抵抗特鲁希略的强权政治落得家破人亡,而家族最后一名幸存者不仅未能如拉英卡所愿光复家族声望,反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特鲁希略牵扯上联系,并因此几乎丧命,最终不得不流亡他乡。“匪徒”的抛弃及拉斐——特鲁希略的妹妹——的致命殴打并非偶然,而是特鲁希略独裁统治及其包庇的特权势力下多米尼加人民无以阻挡的悲惨命运的写照。
正如伊芙琳·钱(Evelyn Nien-Ming Chien, 2008)所说,奥斯卡的故事交织着“历史、罪恶与暴力”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3],造成贝利移居至美国后依然流离失所的根源并非特鲁希略的独裁统治,而是被称为“诅咒”的欧洲殖民侵略活动。迪亚斯这样描述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征服:“自从欧洲人踏上伊斯帕尼奥拉岛,诅咒就被释放到这世上,于是我们所有人便在劫难逃。”[4](P)一方面,欧洲的暴力征服与掠夺使美洲经济遭受重创,因而长期处于贫困弱势的第三世界,而对于多米尼加移民群体来说,在美国生活不仅是地域上的变化,更是以“第三世界”的身份直接迈入“第一世界”的领域,他们必然遭遇的阶级边缘化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欧洲的文化入侵打破美洲原有的文化体系,正如张德明所说,“欧洲的殖民/父性话语植入被殖民地/加勒比文化的母性内部”[5],也就是说欧洲的“父权制”文化代替了加勒比的“母权制”文化,这种以男性支配女性思想为中心的男权主义思想是多米尼加女性处于社会边缘的根本体现。对于宣扬“平等”的美国社会来说,坚持这种特权思想的移民者无疑是主流文化的他者。
而贝利身上显现的这种双重边缘身份集中体现在其文化错置上,文化错置使移民者“不属于任何体制或这个国家的任何一部分”[6]。深受独裁暴力与男权主义迫害的贝利选择逃离苦难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如同所有流散者一样,她将希望寄托在“他处”,还将美国比作“世外桃源”[4](P123)。然而,阶级、种族及民族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其无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处于边缘的贝利不得不通过坚守自己的民族文化寻求归属与认同,这也是她对洛拉和奥斯卡坚持采取“多米尼加式”教育的原因。与此同时,多次被男性抛弃的贝利逐渐开始依靠自己的努力支撑整个家庭,这种“强悍”的行为打破了原有多米尼加女性“弱势”的形象,也体现了她超越原有多米尼加传统文化,对如何在迥异于故国的“新大陆”生存的探索,正如李保杰所说,这种文化的错置是她作为“幸存者”在文化冲突的环境下“不得不做出的改变”[7]。
二、冲突、边缘与自我放逐
相对于移民第一代在美国坚持多米尼文化传统的“返乡”意识,出生于美国的移民第二代也经受着两种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一方面,贝利推崇“多米尼加式”的家庭教育及以“男权主义”为核心的多米尼加男性气概,这对于接受美国新式教育的奥斯卡和洛拉来说无疑是种负担,无法适应这一文化特性的他们选择逃避与抵抗,使自己更加积极沉迷于大相径庭的美国文化。另一方面,移民第二代处于美国社会边缘的命运并不能因其“美国公民”的身份而改变,经济的贫困、社会地位的地下以及无法抹去的多米尼加文化印记造成他们无法在美国主流文化中找到自己的归属,导致他们更加急迫地将希望转向曾带给自己极大困惑的多米尼加传统文化。
拉美男性气概侧重于强调男性在两性关系中的支配性地位,代表着“大男子主义”(machismo)的社会理念。传统的“多米尼加崽”(Dominican Tiguere)具有“聪明机智、有勇有谋、狡猾却令人信服等特质”[8],以“花花公子”的形象对女性进行征服与消费。而作为与女性气概相对应的文化概念,拉美男性气概也暗示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她们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因而不得不依附男性成为其“所属品”。男权主义宣扬的这种男子汉形象却被史提芬·格雷戈瑞(Steven Gregory, 2007)称为“罪犯”,认为拉美文化标榜的男性气概使得男性“沉溺于迫害他人”[9]。在这部小说中,奥斯卡与洛拉就是这种文化定位下典型的受害者。
贝利作为家庭的大家长(matriarch),代替“缺席”的父亲延续着多米尼加父权制的体制,她对奥斯卡与洛拉的家长式教育反映了多米尼加人民受到殖民与特鲁希略独裁文化的侵入与渗透,而这种必须服从年长者的价值体系注定与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美国价值观背道而驰。奥斯卡长相肥胖丑陋、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不符合社会审美的他因得不到女性的青睐而始终无法成为母亲期望的“多米尼加崽”;而叛逆、崇尚自由的洛拉显然也无法像其他多米尼加女孩儿一样对母亲毕恭毕敬,这样移民两代之间的矛盾加深,尤其是同样强势的母女二人更是水火不容。亲情的淡漠、传统文化的不认可使二人转向美国文化,奥斯卡沉迷于科幻小说这一流行文化,而洛拉选择离家出走跟“白人”男孩一起生活,这种投靠美国文化的尝试恰恰反映了移民第二代对第一代所代表的传统文化认同的无奈与抵抗。
然而,奥斯卡并未因其追求美国流行文化,甚至自己也用这种文体写作而受到人们吹捧,反而始终受到他们的讽刺与排挤,而洛拉不仅未能从她的白人男友身上找到依靠,还受到他公然的民族歧视。他们的遭遇表明,对于以“白人文化”为核心、宣扬“金钱至上”的美国主流社会来说,移民第二代本身体现的“黑人”特性及其难以改变的下层阶级身份决定了他们永远无法完全摆脱自身的差异性,正是这种差异性使他们在美国文化中依然得不到认可,而“返乡寻根”的意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不幸的是,他们对于陌生的“故国”的寻根之旅不尽人意,进一步揭示了移民第二代无法逃避的文化杂交的多元文化认同。
奥斯卡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获得短暂的平静,不仅得到拉英卡的支持,更是认识并爱上了妓女伊本。对于多米尼加男性来说,男性气概可以被认定为其“多米尼加身份”象征,小说中奥斯卡男性气概的缺失直接威胁着他的多米尼加身份[10](P395)。而“没有哪个多米尼加男人死的时候还是处男”[4](P131)更是困扰奥斯卡一生的问题,为此奥斯卡竭力追求伊本,甚至不惜为此丧命。迪亚斯对上尉的刻画使其成为奥斯卡的对立面:“他是那种身材高挑、举止傲慢、英俊冷酷的黑人,能令绝大多数人自惭形秽”,而奥斯卡最终被上尉枪杀,是上尉代表的“过分的”男性气概对奥斯卡代表的“失败的”男性气概进行“惩罚”[10](P396),从中不难看出男性气概所表现的权力关系,也注定了奥斯卡寻根的无望。而在拉英卡身上体会到母爱的洛拉最终还是不得不离开多米尼加,过上漂泊不定的生活,说明移民第二代选择逃避现实的做法不可取,也进一步暗示多米尼加并非他们的避风港这一事实。正如丹尼·门德斯(Danny Méndez,2012)所说,“他者”的遭遇不仅仅发生在文化错置之时,流散者“寻根”的过程中也是在见证自我他者的身份[11]。
三、差异、协商与杂交性文化认同
流散的经历使移民者不得不遭遇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并逐渐意识到自身“非此非彼”的“居间”状态,也就是说,移民者既无法完全融入移居国的文化环境,也不能保持移民前的故国文化,从而成为两种文化的他者。这种尴尬的文化身份也受到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的关注。在探讨文化定位时他指出,在殖民地与被殖民地文化之间存在着混杂的、居间的“第三空间”[12],这种空间超脱了二元对立的知识与抗拒,而当今的文化就定位在这种罅隙性的居间地带。在这种文化定位之下,移民者文化的认同不再拘泥于“同一、完整与同质的共同体”[13],而是提倡一种更加正视文化差异的杂交性文化认同,强调不同文化的交流、协商与演现,从小说的叙述与故事情节不难看出迪亚斯对这一观点的认同。
马里塞尔·莫雷诺(Marisel Moreno,2007)在研究迪亚斯的作品时提出,传统的多米尼加裔作家倾向于坚持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描述充满乡愁情绪的移民生活,而迪亚斯的写作极力打破这一点,运用代表移居国主流的英语,阐释流散者在移居国遭遇的二元文化[14]。小说《奥斯卡》中,迪亚斯将英语作为主要的表达工具,不仅描述多米尼加移民在美国的流散经历,以及文化冲突下移民者难以找到文化归属的边缘身份,还展现了处于混沌的居间空间的流散者对其文化差异得到认同与包容的渴望,并通过自身对两种不同文化的协调确定其杂交性的文化认同方式,这一主题在移民第二代奥斯卡与尤尼尔身上得以体现。
奥斯卡坎坷又戏剧化的一生充满着他对自身文化归属的探索,一方面,他尝试了解并实践多米尼加传统文化:不断声明自己是“多米尼加人”,向洛拉的女朋友表示自己喜欢“说西班牙语的女孩儿”[4](P16),甚至将多米尼加比作“天堂”。然而坚持“同一性”的民族文化必然对奥斯卡“美国化”的文化差异采取排挤与隔离的措施,因此即使他在多米尼加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平和,依然会听到在“耳畔回荡的窃窃私语‘你不属于这里’”[4](P209)。另一方面,受到自己民族排挤的奥斯卡沉迷于科幻小说以及电子游戏这样的美国流行文化,希望在幻想的世界里逃避无处安身的现实,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书呆子”行径只能使他更加脱离人群,成为美国社会所遗弃的“黑鬼”。而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刻,奥斯卡所谓的“美国公民”身份并未使自己免遭毒手,反而遭到上尉的嘲讽,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美国主流文化并不能成为移民者的依靠。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90)指出,文化身份是流动的,永远处于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15],而小说中奥斯卡对自我文化的定位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漂泊不定的生活以及孤立、边缘的他者身份使他逐渐意识到,对于移民者来说完整的单一的文化认同是无法实现的,移民者的文化差异性使其文化认同多元杂交化。奥斯卡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多米尼加却受到伊本排斥,他表达了对居间及杂交性文化认同的赞同,认为移民者不只属于单一的国家,而是拥有“两个家”[4](P242),这种说法已经展现了奥斯卡对两种文化的融合协调,并保持自身文化差异的思想。而在小说最后,尤尼尔在奥斯卡的呼吁下写下这些故事,不仅刻画了生活在罅隙之间的移民者漂泊动荡的流散经历,更通过尤尼尔对多米尼加历史的重建及流散者体现出的文化差异的描写,强调多元文化环境下杂交性文化认同的必要性。
从小说的故事情节可以看出,尤尼尔作为迪亚斯第一部作品《沉溺》的叙述者,以洛拉的前男友、奥斯卡的朋友形象出现,并由他再现奥斯卡的家族史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历史,在使小说情节复杂戏剧化之余,也将移民第二代尤尼尔的流散与文化认同经历展现出来。相对于奥斯卡在两种文化间较为明显而激烈的纠葛,尤尼尔的边缘化遭遇隐蔽却也令人震撼。不同于奥斯卡肥胖丑陋的外部形象以及书呆子气的行为方式,尤尼尔对男性气概的实践使他更加能够融入移民聚居区文化,同时追求自由的思想也是美国主流文化对其同化的痕迹。然而即使这样,尤尼尔也难以逃避因其无法割裂的民族特征及地下的阶级社会地位而被边缘化的命运。在参与并见证了奥斯卡一家的经历后,尤尼尔逐渐意识到,要想改变困扰多米尼加移民的“诅咒”,单纯靠继承多米尼加传统文化或反之对多米尼加历史避而不谈是不可行的。
在面对洛拉的女儿希帕蒂亚时,尤尼尔从她身上看到了希望,认为她能够“让它(诅咒)彻底结束”[4](P251),而被尤尼尔寄以希望的希帕蒂亚呈现的就是两种文化杂交后的形象:“她黝黑、敏捷,……她爬树,顶着门框上蹭屁股,以为没人听见的时候她就学说脏话,说西班牙语和英语”。这样一个文化混杂的移民第三代被其称为民族的希望,也说明尤尼尔对杂交性文化认同的信心。
四、结论
在全球化环境下,流散这一文化现象已经不再陌生,而流散引发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也逐渐变得不容忽视,如何在多元文化环境下寻找自我的定位成为困扰移民群体的重要问题。作为一名多米尼加裔美国作家,朱诺·迪亚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展示了遭受殖民侵略和独裁统治的多米尼加移民及其后代受到的历史与现实创伤。拥有特殊时代背景的多米尼加流散者既不能完全割裂与故国的联系因而沦为移居国主流文化的他者,又无法改变自身不同程度上被同化的事实,陷入非此非彼的居间状态。在迪亚斯的作品中,处于这种尴尬地位的流散者相应地选择了一种杂交性的文化认同,即有意识地做出改变以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同时不掩盖其独特的族裔文化特征,渴望自己的文化差异得到包容与认可。通过描述奥斯卡一家及移民第二代尤尼尔的经历,迪亚斯不仅展现了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表层现象之下,无法逾越的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的排挤与同化,还试图证明杂交性的文化认同对多米尼加乃至全世界流散者来说也是一种可行的生存选择。
[1]生安锋.后殖民主义的“流亡诗学”[J].外语教学,2004(5):61-63.
[2]Marisel Moreno.‘The Important Things Hide in Plain Sight’: A Conversation with Junot Diaz[J].Latino Studies.2010,8(4): 532-542.
[3]Chien Evelyn Nien-Ming.The Exploding Planet of Junot Diaz [DB/OL].Granta.27 April 2008.26 June 2011.http://www. granta.Com/Online-Only/The-Exploding-Planet-of-Junot-Diaz.
[4]朱诺·迪亚斯.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M].吴其尧,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5]张德明.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构: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71.
[6]Ligia Tomoiaga.Elements of the Picaresque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Diss[M].Babes Boylai University,2010.Cluj-Napoca:UBB Press,2010:26.
[7]李保杰.论《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中的历史再现[J].当代外国文学,2012(3):109-116.
[8]Christian Krohn-Hansen.Masculinity and the Political among Dominicans:The Dominican Tiger[J].in Macho,Mistresses, Madonnas:Contesting the Power of Latin American Gender Imagery[M].Edited by Marit Melhuus and Kristi Anne Stolen. New York:Verso,1996:108-133.
[9]Steven Gregory.The Devil behind the Mirror:Globalization and Politics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
[10]Dixa Ramirez.Great Men′s Magic:Charting Hyper-masculinity and Supernatural Discourse Of Power in Junot Diaz′s' The Brief Wondrous Life of Oscar Wao'[J].Atlantic Studies, 2013(3):384-405.
[11]Danny Méndez.Narratives of Migration and Displacement in Dominican Literature[M].New York:Routledge,2012.
[12]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
[13]贺玉高.霍米·巴巴的杂交性身份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50-151.
[14]Marisel Moreno.Debunking Myths,Destabilizing Identities: A Reading of Junot Diaz′s'How to Date a Browngirl,Blackgirl,Whitegirl,or Halfie'[J].ProQuest.Afro-Hispanic Review.2007,26(2):103-117,215.
[15]Stuart Hall.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J].Identity: Community,culture,difference.London:Lawrence& Wishart,1990:222-237.
Diaspora 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Junot Diaz's The Brief Wondrous Life of Oscar Wao
ZHANG Yan-xi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dong University,Jinan,Shandong 250100,China)
The Brief Wondrous Life of Oscar Wao,the second work of Dominican-American writer Junot Diaz,depicts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trauma that Dominican diasporas have suffered from colonization and Trujillo's dictatorship in Dominican Republic.By alternating past and present with juxtaposing"absence"and"reappearance"of some characters,the novel not only reconstructs Dominican history together with Cabral family saga,but also portrays diasporas confronted bitterly with cultural conflict and marginalization in America.Racial,class,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he inescapable identity of being"the other"cause them to be lost in the sense of cultural belonging and identification.Thus,living in a multicultural circumstance like America and eager to search for self-positioning,the desperate Dominican diasporas have no choice but to seek for hybri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Junot Diaz;colonization and dictatorship;diaspora;conflict and marginalization;hybrid culture
I106.4
A
1672-934X(2014)06-0129-05
2014-10-03
张艳霞(1988-),女,河南焦作人,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