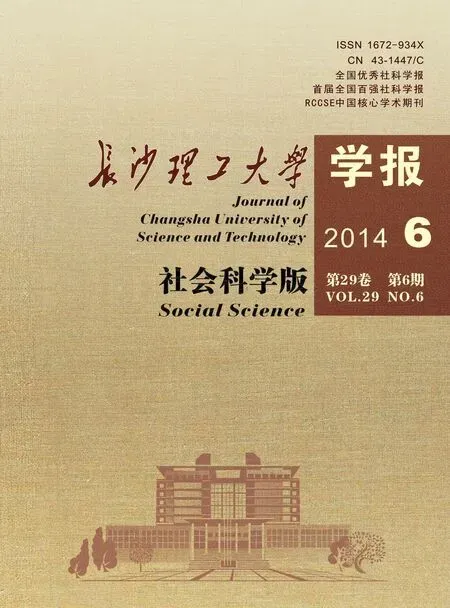论彭燕郊晚年诗歌中的视听生存体验
2014-03-25刘长华
刘长华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一
《画仙人掌》约略为彭燕郊“归来”后向暌违已久的诗坛之“首祭”,颇具象征意味。它是作者历经劫波后的人格自白,且其以体验的方式道出了“言”与“象”的思辨关系困窘——“这些带刺的简单的形体/它不需要描绘,不需要赞美。”由此切入全篇所包涵的“言外之意”。第一,大言炎炎不仅是对“象”的失实且背后的动机值得怀疑:“绘画的语言”的“光”和“色彩”从来都是使“花”“无限地丰富”,其可能的旨意是让“花”“沉醉在美里面”“也使人沉醉”;第二,大道至简,“天道不言”、“美而不言”,“言”是难以尽“象”的;第三,被缧绁、被禁言多年后的彭燕郊似在慨叹面对生存世“象”自己已变得无语、无助——“词不达意”了。对“言语”的尊重与敬畏之情溢于言表的同时,“言语”的不可信性、无力感在彭燕郊这儿也是毫不掩饰的。确乎,一方面,诗人就是活在“言语”中,他的全部生存就是一部对语言不断赋魅的历史。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诠释就把这点演绎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事实上,中国民间民俗一直存在“语言崇拜”的事象:“言语禁忌”和“敬惜字纸”等是深入人心、广为流布;另一方面,儒、道、释诸家对语言的否定和鄙视也是显而易见的:“语言其实不重要或不那么重要”[1],何况经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非常时期,“废话,套话//大话,空话”(《芭蕉叶上诗》)漫天飞舞和横行霸道,与之同时“因言获罪”的冤假错案比比皆是……总之,语言不能不让怀揣良知的人们小心翼翼、噤若寒蝉,“说”还是“不说”成了此时彭燕郊的生存难题,一如多年后他在一首唯美的诗歌《湖滨之歌》中所写道“话语 断断 续续/续续 断断 有时候/好像有很多话要说
有时候/又好像找不到要说的话”。不过,直面“说”与“不说”的难题,彭燕郊还是掷地有声地摆出自己的语言价值观和言说姿态。
首先,在对“自我”或“主体”的肯定上依然坚持“说”的必要性。一句世人耳熟能详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2](P302),这是海德格尔从形而上的角度肯定了“言语”和“主体”两者水乳交融的关系。落实到现实生活来看,“说”也是个体的天赋权利,在令人沉默的年代,“说”是人格的承担、尊严的维护、道义的捍卫……这点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尤为重要。曾经的“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很大程度上可归咎于知识分子的自甘“失语”、自甘喑哑,当然也是失掉了自我。《绝叫——题蒙克的〈绝叫〉》对此感同身受——“而我知道叫喊是什么,知道为什么叫喊/突然明白我存在,我没有消失”,而且“突然间一切已经确定,犹豫变成坚定”,意即“说”还是“不说”的彷徨已经被洞穿,“叫喊下去吧,叫喊吧,就是要宣泄,就是释放/不叫喊会更加悲惨,会消失在没有声音的空虚里”等都高扬了“自我”发现、“自我”肯定的必然性,是主体性的恢复体验,从中隐现着对“文革”等白色梦魇般记忆的心灵惊悸和循此而来的精神上的绝大反拨。毋庸置疑,彭燕郊是借题发挥的,蒙克的创作由来则是:“我和两个朋友一起去散步,太阳快要落山了,突然间,天空变得血一样的红,一阵忧伤涌上心头,我呆呆地伫立在栏杆旁,深蓝色的海湾和城市上方是血与火的空间。友人继续前行,我独自站在那里,突然感到不可名状的恐怖和战栗,大自然中仿佛传来一声震撼宇宙的呐喊。”[3]《听杨靖弹〈霸王卸甲〉》亦将“说”与主体性认同紧密联系——“失去音乐,失去自己”。“说”作为个体存在于世的基本证明,在高压极端时期尤显珍贵。民间文化中某些“狂欢化”场景给了彭燕郊相应的体验和启示。一首《雷》是弥漫着“春夜喜雨”的意蕴,但在深层次中是称道了“说”这种“狂欢化”的意义。雷“说过一阵/我们又热热闹闹地议论起来/大声细声议论又商量/你讲的我的,也就是他讲的那一些:/春天送雨来,田里工夫不等人了”,“雷”似乎是恩主,但“我们”是不给它精神加冕的,没有等级、没有权威,大家平等对话、和平共处,在言语盛宴、精神狂欢中回归本我——大写“人”字。“在狂欢节上,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就在其中生活,而且是大家一起生活,因为从观念上说,它是全民的。”[2](P350)彭燕郊、巴赫金在民间文化有裨助主体性的建构之认知上是异口同声、奇妙遇合的。
其次,对异化“话语”或“说”的行为深表弃绝。“左倾”思想泛滥时,“假话、大话、空话”洪水滔天。种种政客话语、江湖话语、教条话语、帮闲话语等都背离了本真话语,也是以牺牲他人的主体性和异化自我即伤害列维纳斯所说的“主体间性”[4]为前提的。虽无理论的先行,但并不妨碍彭燕郊就此感触极深。《话语》就批判了装腔作势、哗众取宠的“话语”。诗歌除了描述讲述者“这个的这个”等无聊套话一堆外,还不惮细节繁琐,采用白描手法——“嘴角,眉尖/颤动的两颊,全是/最有感染力的/够了够了的话语/在不断地/涌出,还有//那手势/放开,收拢,推出,收回/全是比说来的还要多的话语”,一副官僚主义、布道者的嘴脸穷形尽相而出。这话语反证的正是他内心的虚无——“全明白了:我的天!/一个哑巴”——没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思想。无独有偶,《循环往复》同样直指心口不一、表里分裂的套话和无聊话。“已经——已经——这样已经,已经这样”“出了什么事——什么事出了”“说的什么——什么说的”(《循环往复》)等“循环往复”话语模式不仅作为修辞手法表征言说者的敷衍苟且、虚以委蛇,而且更是他一劳永逸、周而复始、通吃一切的生存法宝。“身体里面的声音”“身体外面的声音”的长期分裂,这些老于世故、毫无风骨之人难道就不会“憋”坏?《听歌》一句:“不跟你玩,你撒谎!”说谎者终究都会被小孩所嫌弃。“救救小孩”反倒要被“小孩救”,中间演绎出了多大令人啼笑皆非的反讽。
最后,在“真善美”面前,沉默是最好的话语。《初夏》是怀人之作,君子之交淡如水:“这繁忙生活里的短暂相聚/千万句话在片刻里说完/难道不就是诗?”同理,《怀榕树——悼念邵荃麟》亦说:“他,人间的奇迹,坚强意志的化身/无言的怀念悠长又悠长/也许,就是我能给他的最好的赞美”。《黄昏之献——呈半九兄》也是挚友间的酬答,心有灵犀,无声胜有声:“水手们的怪癖,/整个航程,/很少说话,//话语在海上最珍贵,/海上的感受不容易说准”,人生路上风雨险阻,难以说清道明,默默互勉才是正道。美好甜蜜的事物不需要言语,美而不言。“我有一个秘密,/我把它保留得很好,/谁知还是让人知道了”,原因在就在于“本想把话讲得从容些,/一开口总是结结巴巴,/连自己也听得出/那声音好像是别人在讲话”,这个“秘密”就是“我爱上了一个人,他也爱我!”(《秘密》)。这种情形还延伸到《田头即景》中的恋爱男女——“‘就你会说……’/说的,听的心里都明白/光只会说是不够的”,爱不仅仅“谈”,更在行动。《水库》再度营造了“春夜喜雨”的氛围:“山林、田野不说话/笑盈盈的清爽替它说话了/大伯、大娘、小伙子不说话/笑盈盈的清爽替他说了”,冗言赘语都是对丰盈爽朗心境的破坏,美是用心去感受、享受的。确乎,不用心去感受“真善美”,而一味诉诸语言便是对它们的大破坏。《桂林怀邵荃麟》、《独秀峰》等都相关诗句都流溢出类似的看法。所以,“以自己不发声的沉默的存在/这里,那里,形成节拍,形成停顿”(《钢琴演奏》);“听,无声,那也是一种音乐语言吗”(《听杨靖弹〈霸王卸甲〉》)等都强调了沉默的意义,以至于“无言”才是有力反抗——“只用无言的旋转与狂风抗衡”(《三叶》)。从中,我们似乎看到老庄的“道”不在于“言”而在于“体”的意味,以及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首先而且根本地遵循着说话的本质显身,即:道说。语言说话,因为语言道说,语言显示。”[5]即倾听“道说”。确乎,设若“真善美”不是“大道”,那么舍“此”其谁呢?
二
通过梳理,彭燕郊的语言价值观和言说姿态似已廓清。然而,这种“说”与“不说”一旦进入形而上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等的博弈之中,不免令人混沌迷惘。何况近二三十年来,整个社会价值观急剧蜕变,新与旧、中与西之间的纠缠和冲突,“真善美”想象、主体性的建构、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等本身都面临考验。垂暮之岁而作的《雨中行》就表露了彭燕郊相关的感受,虽然表面上都无涉所谓“宏大叙事”。作品写道一对夫妇风雨人生路上共撑一伞,保持“五公分距离”而一路无言,直至“雨已经下够,伞已收起,总算走到头了”,“两个人,相对无言,是在/回味大雨保持五公分距离的滋味/体验五公分距离的尴尬和无奈吗/依然默默,平静//平静到连自我解嘲的苦笑都没有/——如果有,该是何等灿烂鲜亮的苦笑”。此情此景,“说”与“不说”都有欠妥当:“无言”于此只是“沉默”,而不是“默契”;“有说”可能将是对“平静”的破坏甚至毁灭,这又是谁都不愿率先开口和迈出的。现实生存中有着太多如许的“左右为难”令你无所适从,“一大串话语硬往肚里吞”(《听杨靖弹〈霸王卸甲〉》)。基此困惑,彭燕郊选择过“注(凝)视”、“倾听”及其“艺术欣赏”等视听生存体验来对“说”与“不说”这种困境予以突围的。“注(凝)视”、“倾听”及其“艺术欣赏”等是主体放弃了“明修栈道”的“说”,但又“借道过境”地“说”了,其根本在于这是对“思想”的尊重和践行。事实上,彭燕郊又是疾恶各种轻浮的“欣赏”行为的:“我们这些欣赏者”(《画仙人掌》)、“围住它叫喊的人群”“闹哄哄的现场炒作”(《围观孔雀》、“把瀑布当作画屏那样好看的摆设来欣赏”(《瀑布》)。
首先,“注(凝)视”是“思想”在“不说”中的“说”。“注(凝)视”在彭燕郊诗歌中首先释放了灵魂的目光,是对“光源”的注视,在“无声”中“言说”了“思想”和“智慧”。柏拉图曾说过:“我们将要求他们把灵魂的目光转向上方,注视着照亮一切的光源。在这样的看见了善本身的时候,他们得用它作为原型,管理好国家、公民个人和他自己。”[6]“光源”是象征、是“善本身”、是“理念”、是最高智慧。饶有意思的是,在“注视光源”上,彭燕郊惊人地与柏拉图精神邂逅。《月夜》是他“归来”后的早期作品。“影子一会淡,一会儿又浓了/闪过去,又闪过来/吸引我久久地注视它”(《月夜》,“月影”就是光源,阴晴盈亏、盛衰消长,但也是人们梦幻的眼睛,有梦就有希望与理想,所以诗歌结尾写道:“壮游归来的天上的大眼睛/你看见了吗,在我的眼睛里/跳动的这许多梦的影子”,更直接将“月亮”比喻“大眼睛”。《一朵火焰——呈孟克》中:“一朵火焰”“并不摇晃,并不闪烁/可以长久的注视”,注视中是“把我的心照亮”。“水手有个习惯,/总是手搭凉棚/默默地注视前方”(《黄昏之献》)同样表达了对“光源”的搜索和探求。“悄悄凝视你,直到此刻:天已大亮,白昼已来临”(《放射》),“长久长久凝望夜空/忽然发现,银河上面/还有一条银河”(《湖滨之夜》)、“影子,你想到了没有/有人在注视你,寻找你/在向你企求……”(《影子》)等等都如此的。其次,这种“注(凝)视”又是与主体的想象力激活相联,是生命的超升。正如上文所提柏拉图认为“注视”与“灵魂”密不可分,彭燕郊也是多次写到“注(凝)视”会带来“灵魂出窍”的生命体验即“想象力”的无限丰富。而诺瓦利斯就说过:“人的心灵——内在世界有着比理性及其要求更高的东西,这就是想象力、自我感觉、兴奋的感受性。”[7]同时他又认为,“思维就是言说,言说也就是思维,一种言说方式,也就是一种思维方式。”“语言是人解放自身的一种原初力量。诗的语言既然是自我的表达,那么,它也就是自我对自我的启示。”[8]也就是在“想象力”这种“思维”中抵达了“诗的语言”的言说。“吸引我久久注视地注视它,我猜想”(《月夜》),“月亮在凝望里模糊了/止不住的泪水一滴滴地落到月亮上”(《读信》),“一边注视/展开眼前的浩瀚田野/一边注视我的小小手掌//我沉入想像”(《金色的谷粒》)等,都是将“注视”和“想象”并置在一起,所以“想像是一种高贵的享受”(《画山九马》)。第三,“注(凝)视”更是沉思默想的一种途径。“我尽情凝视,和凝视中的沉思默想”(《漓水竹林》,“每个人都用若有所思的凝望回答你的凝望。/而你,从连续变化的每一个不同角度/像孩子般若有所思地凝望我们。”(《陈爱莲》……“思考”是理性,是现代性的徽标,是中国“立人”的目标,当然也是现代诗的气质。确乎,在“注(凝)视”中人回到“小孩”般的澄澈和了无机心,这更是彭燕郊“立人”的一贯主张。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都像才醒来的孩子/用甜蜜的眼光注视这个亲切的世界/世界史变得更加可爱更加可留恋了”(《钢琴演奏》)。
“倾听”是听取大自然的清音之言说,是对“生命”的唤醒。自然是不能言说的,但它正如老子所言:“大声希声”的,敞开心灵的耳朵予以倾听,便是人性的复归和生命的唤醒,亦自是“思想”的敞开。《林语》中的“幽静的树木”在“沉思”,但“小鸟们的歌声”“把多年积淀下的香气唤醒了”,这是“树木”境界的提升,显然此“树木”是隐喻“人”的,“鸟声”乃为天籁。《雷》、《雨》、《桃花开》等系列乡土诗中都是写到了“听”,“听”给主体带来由衷的快乐,让他们感受到生命的异样美好,且无一例外的是这些声音都源于自然。《歌声》是将来自大自然界的声音赋魅书写。“无边的水一般的夜里/传来了总也溶化不了的/影子般的歌声”,这“歌声”像“沉静的/婴儿的呼吸般均匀的歌声”,给“我”唤回对“存在”的观照,甚至使“我”都愿意“同于大道”、“天人合一”,和它“溶化”“在这春夜里去”。《万年寺蛙声》更直接表达了“生命运行”是“最优美的声音”,我们必须敞开心灵予以聆听这自然界最宝贵的馈赠。《金山农民画》中:“我总是把手伸到狮嘴里——它不会咬我的/不停地玩那滚圆的石珠子/抓起来,丢下去/石珠子丁零丁零的,好听极了/我开始幻想”,正是在“幻想”中“我”的“生命意识”开始萌发,“我”对人生开始充满梦想,以至于对“菩萨”“我”都好奇“她在想什么”。总得说来,这些“谛听”是排除社会的喧嚣和自我的聒噪,在聆听自然的同时,也就在真正聆听自我的内心。能有自我内心声音的发出无疑便是“思想”的声音,而这种声音绝对是“无声”的。
“艺术欣赏”是主体关于“生存之思”的最佳表达。在彭燕郊这里,“艺术欣赏”绝非是满足一般意义的精神休憩,而是常与“生存之思”这个最大“思想”系扣在一起的。《东山魁夷》下笔就是:“你的画使我静默/在你的画前我进入沉思”,引起“我”沉思的不止是东山魁夷的画,还有小泽征尔的指挥、钢琴演奏、金山农民画、杨靖弹《霸王卸甲》以及陈爱莲的舞蹈等等。这是彭燕郊诗歌生涯中的一道独到而有意味的风景。“我”“沉思”什么呢?它们都分别给出相应的答应。其中,《小泽征尔》的答案最铿锵有力:“我们听着,一边我们给自己/挖下一个又一个洞穴/一边让我们心头的某一块肉/在某一洞穴里得到栖身之处/然后我们把它填平/为了我们好就此飞升/到底,每一个人都终于看到‘人’了/像我,像你/这具有最普通的‘人’的特征的/人的勇气又一次得到肯定/这个守望在自己所发出的声音的旋风里的/这个和我们一样通红炽热的/永远在我们的理想里沸腾的人/提炼出来的一堆的血肉,熔岩般地颤动着!”,是的,没有比“这个守望在自己所发出的声音的旋风里的”说得再妙不过的!它明白无误地将“人”之“思”归结为“自己所发出的声音”。此正是彭燕郊有关于“说”与“不说”这个难题上的全部奥秘。从艺术中获得“生存之思”,获得这“无言”(即《钢琴演奏》《小泽征尔》《听杨靖弹〈霸王卸甲〉》中所说的“手”)所发出“言”,这也正是与绝望的叔本华认为艺术是拯救自我的最后手段,与尼采对音乐的病态般地钟爱,与海德格尔对《农鞋》的百般凝眸……在内蕴上构成了最大的精神共振。
三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问题是平凡人生能够时刻处在这种“注视”、“倾听”和“艺术欣赏”而最终“同于大道”吗?显然,这只是一种生命的最高理想:“‘跌落可悲/跳跃危险’/用不着议论了,议论就是害怕/害怕就会去寻求平静/奔流的路上,存在平静吗?//当然/把瀑布单作画屏那样好看的摆设来欣赏/也是可以的/那么/你就站开些吧,站远些吧/用你的方式去‘欣赏’吧”(《瀑布》)以及“这个和我们一样通红炽热的/永远在我们的理想里沸腾的人/提炼出来的一堆的血肉,熔岩般地颤动着”(《小泽征尔》)。其实,这才真正道出彭燕郊——以“不言”而实现“言”和抵达“思想”的深刻认识——“难”。另一角度,这又表明了彭燕郊非但虚无和悲观,反倒闪烁着理想的光芒,喷薄出“反抗绝望”的坚毅和勇气[9]。这种有着精神红线所牵系而在整个行走过程中又充满矛盾悖论的世界观和生存论,坐实到诗学道路中就具化成浪漫抒情与现代性、散文化与意象化、审“真”与审“美”等之间的纠缠和辩证。
第一,浪漫抒情与现代性。彭燕郊掊击浪漫主义是不遗余力的。他的认知就是现代诗的登堂入室与浪漫主义的消歇告退相反相成。他说过:“现代诗越过浪漫主义依靠激情认识世界、反映世界、改变世界的抒情至上主义,从转向对隐藏在现实世界背后的‘真实’的探究、思考,到隐藏在‘大我’背后的‘小我’的发现,对‘更重要的现实’——人的内心世界的挖掘。”[10](P96)《再会吧,浪漫主义》、《两世纪之交:变风变雅:浪漫主义困惑》等曾相继面世。其背后的哲学理路正是“言”和“不言”的关系处理:浪漫主义是过分“抒情”——“说”,而现代诗以“思考”——“不说”(“人说”)而完成“说”(“道说”)——“使自我得到超越自己的精神飞跃,成为一个有力量凭感性直觉而非凭理性观念进行宇宙心灵的神秘幽玄的探测,从而在人与宇宙、人与历史的新的交涉里发现人的本质、人的价值。”[10](P96)言下,“现代性”的立足点在于对“主体性”的肯定、建构和完善。就此,彭燕郊并没有所谓的“与众不同”。问题的是,浪漫主义的诞生正应命于彰扬人的“主体性”而来。席勒、诺瓦利斯、谢林、狄尔泰、叔本华、尼采、荷尔德林等对此的勘定十分清晰。而前面论析过在对“自我”或“主体”的肯定上,彭燕郊也是坚持“说”的必要性。确乎,在标识和张扬“主体性”上,不藉助激情、想象、灵感等这些人才具有的“非理性”(即“人说”)的元素,又如何将“人”在保持又舍弃动物性中而获得身份的自足和意义的建构?
事实上,彭燕郊这些以“视听生存体验”为题材的诗歌其浪漫抒情成分是浓郁的。搁置其他不议,单就“艺术欣赏”中的《钢琴演奏》、《小泽征尔》、《听杨靖弹〈霸王卸甲〉》、《陈爱莲》、《东山魁夷》等而言。首先、它们都标显出“我”之意象。“只有今天我才看见这样亲切的画”(《金山农民画》),“我们清楚地感到”(《钢琴演奏》),“音乐落入我怀中”(《听杨靖弹〈霸王卸甲〉》),“我难以说你走了出来”(《陈爱莲》)等都充分表达了“我”的存在性、参与性。而在艾略特看来,“非个人性”是现代诗的灵魂,其旨在排除情绪的汪洋恣肆。而“我”的大势介入,显然就是对“非个人性”的放弃。“我”的零距离性又是直入诗学中的一个命题——“言,我也”。对此,有学者曾精辟地指出:“诗人要走向存在,就得先进入言说,然后才能在言说过程中获得自己的存在性。这就是‘言’对诗人生存来说的全部意义所在。它的意义就在于,它能使生命的意义得以寄寓和呈现。但是,对于诗人之‘我’来说,言说既是一个自我对象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自我分裂的过程因为具体的‘言’只能表‘意’(且不说能否‘尽意’),因而他人在其‘言’中所见的,也只是‘我意’而不是‘我’。‘我’只有在我的全部言说过程中,才能得以呈现。因此,对诗人来说,‘言’,就是‘我’的使命和命运。‘我’只有在具体的言说中先遗忘和丧失掉自己,然后才能在全部言说过程中,重新获得或再建自己。因而,‘我’就在我的言说之中,我的全部言说就是‘我’:言,我一也。这是诗人全部的欢乐与痛苦所在。”[11]换言之,艾略特等人的“非个人”强调的只是“具体的言说中先遗忘和丧失掉自己”,而不能从本质上捐弃“言,我也”,这就意味着抒情、情绪等是无从规避的。其次、这些诗歌不仅洞开了作者内在充沛的情感世界,而且其丰盈充沛的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都是浪漫抒情的最直观表征,作者寄寓其中的情感倾向也是一目了然的(限于篇幅,就不拟展开了)。大概正是体验到浪漫抒情与现代性之间难以剥离,所以彭燕郊其后多有补白过:“诗,不单单是抒情;现代人的抒情,可以也应该是思考的抒情”[12]等思想。
浪漫主义强调从“人说”而走近“道说”;现代诗注重的是由“道说”切入“人说”。“人说”与“道说”的介入路径和所处语境总存差异,而这两者的价值坐标指针始终又是由“人”本身来判衡的,稍有倾斜都是对“人”的偏离,这岂不正是两难?
第二,散文化与意象化。众所周知,以“不言”来实现“言”,这又恰好是中国古典诗词孜孜以求的美学境界。通达此境界的终南捷径便是“象”,所谓“意在象外”等便是明证。“意”“象”被中国古人并置,且荣膺着诗歌精神的核心。另一方面,对现代文化的拥趸与否是事关现代诗的合法性有无,而现代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身份认同便是对自由精神的毫不妥协地捍卫。诗的散文化因其从格律、形式等“樊笼”中逃逸出来并凸显出放达无羁、通脱无碍的人格意志(这本身又是否可归位于浪漫主义范畴之内呢?)而备受人们青睐。彭燕郊对诗的散文化推崇备至:“自古以来,诗就韵文……但现代诗人从波德莱尔算起,反对诗依靠音乐性。押韵等于一种欺骗手段。”[13]当然,诗的散文化,无论波德莱尔还是彭燕郊都不只停留在音韵的考量之上,诸如收缩“纯诗”的思维跳跃性,相当更着意于语法结构等等都应是题中之义。不过,“言”的繁琐冗长、艺术空白的逼仄紧张进而艺术效果的折杀就相应地派生了,与轻“人言”而重“道言”的现代诗想象渐行渐远。彭燕郊相关诗歌就表现出“散文化”和“意象化”的胶着纠缠。
首先,散文化中却拒绝叙述化。与“诗化”相比,“散文化”的最大特征之一便是讲究叙述的条理化、逻辑的清晰度。而《钢琴演奏》、《小泽征尔》、《听杨靖弹〈霸王卸甲〉》、《陈爱莲》、《东山魁夷》等还是上文中所征引的其他诗歌,是很难见出对时间、空间的重视和情节过程的刻意。《金山农民画》或许是个例外,讲述了一段回忆,但它只是情绪记忆,与其说是回忆不如说就是对眼前农民画的一种“幻觉”、一种跨越时空的生存体验。也只有如此,才能体现该诗的写作初衷和命意指归——对金山农民画的高度礼赞。其次,反对格律中又恪守生命内在的节奏感。早在《论感动》中,彭燕郊就说过:“节奏,是力。/如果停顿,也应该是奔马跃过栅栏之前的那一停顿。/如果收缩,也应该是鹰隼展翅翱翔之前的那一收缩。//不单有语言的节奏,而且有意象的节奏。/追随语言的节奏得到的快感是生理的,追随意象的节奏得到的快感是精神的。”[10](P167-168)这种观点根深蒂固,一直延伸到他的创作终点,所以在诗歌《节奏感》下笔就是:“没有节奏感就不会有音乐/没有音乐就会烦躁”“什么都可以失去/重要的是不能失去节奏感”,但这种“节奏感”绝然不是来自“韵律”,“诗不是音乐,是不想把一切都溶化在韵律里。”[10](P167)事实上,彭燕郊相关诗歌中基本上是难以觅见“韵脚”之类的,但它们对节奏感的拿捏又是相当“精明”的。《东山魁夷》所表达的是对日本“物哀”文化的理解,这样的氛围是冲淡恬静的,所以“我没有见过这样的画,从来没有/这样的调子,这样的形象,这样的单纯和质朴/这是画吗?或是大自然无意中留下的痕迹”,这样的节奏舒缓到了让人感觉简直是午夜梦醒后在隐约浅月下的走廊上喃喃自语。而《小泽征尔》整个节奏是跌宕起伏的,和“小泽征尔”的指挥步骤有着“格式塔”式的共舞,譬如描述开始时是平静的,“多么虔诚,多么平静:他走出来”,这种均匀齐等的节奏无疑是极为熨帖的;而到了峻急高潮之时:“呵,时间!呵,大气!呵,人类奇思妙想的表达者!”此刻的节奏就便极显短促、交错之势。最后,相关诗歌都是集中某一“意象”而展开。正如前文中已经重点分析过了无论是“注(凝)视”还是“倾听”还是“艺术欣赏”,作者都是紧扣某一意象诸如“光源”、“手”等具体展开,它们是凝聚了诗人的独到感受和别样情思的,甚至隐现出一种图腾崇拜式的精神迹象,从中我们是可以得“道”的。所以,总的说来,这些以“视听生存体验”特别是“艺术欣赏”为题材的诗歌在骨子里“意象化”的写作,但它们都以“语言瀑布”的方式展开了,其意在语言的“自由”来领略和契合“视听艺术”的本质——“自由”吧!这是不是在反其道而包抄“道”呢?
第三,审“真”与审“美”。不似康德在宏观体系中对“真”“善”“美”的司职分工已经昭然了,彭燕郊单就诗歌这“一亩三分地”却说过:“文学要求的是几乎不可能达到的真善美融为一体的完美。艰难在于,美是极富诱惑的,单纯的美是很可怕的、有毒的,能够像鸦片一样麻醉你,沉沦在美里面是会丧失一个人的坚强意志的,是会使你堕落的。但是文学又不能不是美的,是必须有高的意义上的美的,真正意义上的美的。从真、从善来的,具有真的、善的本性和素质的美才是文学的热、力和光,单一的美和文学无关。艰难在于,到哪里去发现这个和真、善融和在一起的美,这是需要认真思考而且有勇气用实际行动去探索的。”[14]仿佛之中,我们又是听到“美而不言,言而不美”、“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等这样的声音。确乎,以“不言”而实现“言”,在很大程度就表现为对“真”的追求,对对生命、生存之“真”的勘探和追求。所以,与其说彭燕郊诗歌的文化追求是“审美”倒不如说是“审真”。当然,这是与彭燕郊隶属于“七月派”这一“左翼”文学流派的文化品格不可约分的。问题是正如彭燕郊自己所说的——“文学又不能不是美的”。实际上,关于“审真”还是“审美”之间的博弈在上文中所论述的两个方面中已经触及和展开了。如何将“真”与“美”兼顾起来呢?当然也就复归到“说”还是“不说”的难题之中。
彭燕郊曾经就作为表意工具的“语言”做出过探讨,他说过,“语言有它的与生俱来的使命:预先决定一切精神现象(现在最主要的是思维现象)的符号表达形式。矛盾就在这里:符号看起来是万能的,而又往往是无能的。现代诗人在使用它时,更多的情况是不可能得心应手,表达的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符号(语言)作为媒介必然要伴随着一种阻力”“我们要探讨的却是更为特殊的的一种语言,文学语言中的诗的语言。而我们又必须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两个不同的断面来考察它。”[10](P122)就此,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它一方面再次道出了“说”与“不说”的精神窘迫,一方面又是将“语言”、“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三者置于一炉予以深切思考,还在于它为何就单将“语言”和“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者搁置在一起。在我们看来,此处的“浪漫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审“美”的代名词,“现代主义”也就相辅相成地成了审“真”。既然“语言”本身给人带来如此之多的挑战,“其最终的结论只能是:纠缠于最好用某‘种’语言(现成的、人工的、通俗的、高深的等等)写诗歌最好的想法是多余的。”所以,企图在审“美”与审“真”做出个非此即彼的判断,显然是徒劳的。在彭燕郊看来,在审“美”与审“真”之间杀出一条血迹斑斑的生路来,或者干脆就在两者夹缝中生长才是诗歌的生命与魅力;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彭燕郊为何要说:“第五组六首(注:即上文中我们征引过的《钢琴演奏》《小泽征尔》《听杨靖弹〈霸王卸甲〉》等)写音乐及艺术欣赏的,写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艺术的欣赏是需要细腻感觉和细腻感情的,难得有这样一个短暂的好时光。好梦无长夜,如今回想起来,却有些苦涩了。”[12]
小结
众所周知,中国诗歌在当下是落寞和边缘化的。对于这种状态所产生的原因,人们从多方面、多角度予以了归纳和总结。而彭燕郊立足于“视听生存体验”的角度道出了“说”与“不说”的尴尬与困惑,毋庸置疑这是在深层次中对新诗做出了一种自白、一种剖析。透过这种自白或剖析,我们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形而上与现实、文言与白话、中与西、抒情与写实、“我”与“非我”等等之间的矛盾和错乱,这些矛盾和错乱对我们更好地“问诊”中国新诗的过去和摸清它在未来的精神命运、历史走向,毋庸置疑是大有裨益的。“说”与“不说”的难题充分地表明了这是一个“非诗”的时代,而彭燕郊依然坚持在写诗,直至生命之灯熄灭的最后一刻,这行为本身又是不是一种富有启示意义的人文精神?
[1]陈坚.语言其实不重要或不那么重要——儒道释三教对语言的看法[J].中国佛教,2010年,总第28期.
[2]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302.
[3]张广华.艺术欣赏[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295.
[4]杨大春.超越现象学——列维纳斯与他人问题[J].哲学研究,2001(7):54-60.
[5][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54.
[6][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节译本.解东辞,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2:254.
[7]孔建平.作为文学元理论的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08.
[8]刘小枫.诗化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6-88.
[9]刘长华.彭燕郊评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289.
[10]彭燕郊.彭燕郊诗文集(评论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
[11]徐麟.“言,我也”与中国古代诗学[J].文艺理论研究,1996(6):275-283.
[12]彭燕郊.彭燕郊诗文集(诗卷下)[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358.
[13]孟泽,陈太胜.彭燕郊的诗与诗学[J].诗探索(理论卷),2010(3):134-171.
[14]彭燕郊.历史的规定,我的选择[A]//男性生存笔述[M].荒林,主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