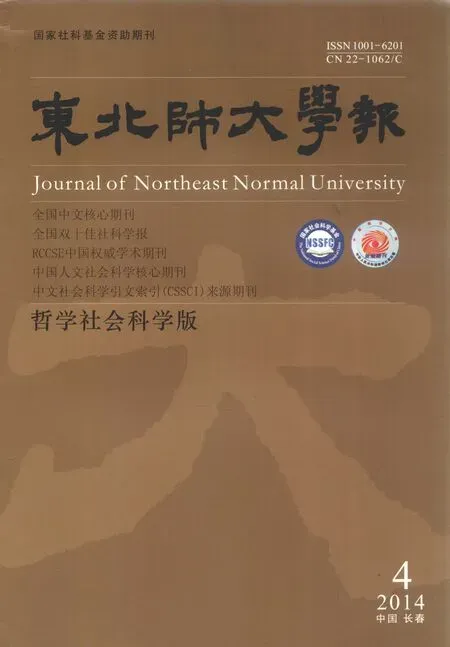学生观问题的再认识
2014-03-24刘弋贝
刘弋贝
新课程背景下的学生观问题研究,许多问题业已变得清晰明确并取得广泛的共识,这使得接踵而来的讨论呈现大同小异的重复现象,结论似乎不约而同且天经地义,这种阐释的重复除了具有强调作用之外,看不出更有价值的深入拓展的意义。事实上,无论在理论思考还是在实践落实的层面,还存在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并非想象的那样清楚明了。
一
学生观在通常的表述中是指教育者对学生的某种理解、认识和评价,是教育者一定的认识立场、观察角度、评价尺度的反映。学生在教育者眼中心里是怎样的群体形象,对他们进行怎样的性质特点的认知与定位,无疑会关系到教育者对学生采取怎样的教育策略和方法,并且,学生观的立场、认知前提与价值判断,也将成为教育理念、课程设置和教学实践方式确定的基础。教育者能否根据学生的生理、心理、智能发展的规律和特点认识自己的教育对象,而不是站在成人的立场想当然地理解学生,这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学生观对学生的判断不能离开作为学生的角色前提。
新课程改革的初衷首先来自对学生的重新认识。针对普遍存在的“把学生当做任人摆布的物的现象”,发出“学生是人还是物”的诘问,这种将“人”与“物”的差异性对比,旨在揭示“人”的“主动性”与“物”的“被动性”的根本区别,以强调如何将学生视为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的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自然是针对过往教育现实存在的问题而言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人”与“物”的对立比照中,“几乎任何人都认为学生是人”,却出现“把学生当做任人摆布的物的现象”,这意味着在对学生认识的层面,学生是“人”而不是“物”是不存在分歧的,即在认识的层面不存在“人”与“物”的对立。问题出在教育实践中,是死板灌输式的教育把学生变成了被动“物”。这种认识与实践的偏离、主观愿望与实际效果的相悖才是问题的根本。因此,对以往教育者“把学生当做任人摆布的物”的否定,不应该从主观动机上怀疑他们的初衷,将失误判定为主观故意,这种根本的否定显然有失公允,因为,这是瞄准靶心而脱靶和故意脱靶的本质区别。
在“学生是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源自天性论的学生观一直为研究者津津乐道。这种天性论的学生观基于对人的天性认识的前提,将人定位在“性善”、“性恶”、“善恶兼具”的定性判断基础上,认为人性的善恶与生俱来,具有前在的决定意义。论者往往列举古今中外贤哲对人性的论断,用以证明人的人性差异。战国中期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而告子主张“无善无恶论”,各执一端莫衷一是。此后,董仲舒又提出“性三品说”,即把人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他认为“圣人之性”与“斗筲之性”均不可以名性,因为圣人之性乃“纯仁淳粹”之性,是一种超人的神性,不必施以教,而“斗筲之性”如“苟为生、苟为利”的鸟兽,这种鸟兽之性并无善质,王教也不能使之为善,所以不可教。只有“中民之性”具备可教的潜质,但潜质并不等于善,即“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当其未觉,可谓有质,而不可谓善。”他认为只有“中民”才具有施以王教的可能性。西方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伊壁鸠鲁到卢梭,形成性善论的传统,认为人具有潜在的善性,主张设计一种理性的社会,通过教育使人格得到发展。而奥古斯丁、马丁·路德、霍布斯、休谟等人,则坚持主张性恶论思想。性恶论来自基督教的“原罪论”,认为人有原罪,人性是邪恶的,人与生俱来就有恶或自私自利的本性。这种“原罪论”的性恶论至今依然影响着教师对学生的认识,认为学生是生来就恶,需要训练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将学生观与古今中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人性善恶观问题搅在一起,这无疑是在把问题复杂化的研究策略。这种将“学生”泛化为“人”的规定,将学生观变成人性观,变成对人的善恶本性的探讨,这无疑是一种舍近求远的研究策略。
事实上,学生观对学生本质的理解和把握,首先应坚持的前提是对学生身份的准确规定,应该明确“学生是以学习为主要任务的人”,在这个基本前提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认识“学生是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在“儿童”、“孩子”和“学生”的称谓上,不加区别地混用常常造成理解上的混乱,因为“儿童是中性词,指处于特定年龄阶段的人,与青年、中年、老年相并列;孩子与成人相对,既表示需要成人的关心和爱护,也表示相对于成人的弱势地位;学生则与教师平等相对,与教师一样,是一种社会身份,承担着特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1]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将0—18岁统称为“儿童”,旨在划定和强调“未成年人”的年龄范围和受法律保护的权利,这种粗略宽泛的年龄划分如果等同于“学生”的概念,显然存在涵盖关系上的矛盾。因为,在0—18岁的年龄范围内,显然包括婴幼儿时期的“学龄前阶段”,这一期间的婴幼儿虽然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儿童”,但这个所谓的“儿童”阶段还不具有“学生”的身份。另外,18岁以后进入成年阶段的“青年人”,在进入高等学校学习阶段,依然可以称之为“学生”。这意味着只要进入任何一所学校或在完成某一专业的学业,不管多大的年龄都具有“学生”的社会身份和责任义务。所以,笼统地将“学生”称为“儿童”,不但是一种粗疏的称谓,而且存在着涵盖关系上的自我矛盾。
学生观作为教育者对学生的认识与评价,其观察角度和评价立场的客观性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作为对象化的存在,教育者是否按照自己的理解在阐释成人的学生观,用自己的主观想象建构学生形象,使学生观的认识成为某种主观臆断和脱离对象实际的自我言说,从而造成对象本质认识的自我遮蔽。学生观对学生本质的理解不能离开学生身份的特殊规定,学生观视野中的“学生”也不应该被泛化为哲学或伦理学意义上的人,把学生观认识引向人的善恶观纠缠不清的泥淖,这不仅使问题变得复杂化,而且也是一种作茧自缚的研究策略。
二
新课改推进过程中,突出强调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这实际上是针对将学生视为被动接受者的反拨。在教学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上,研究者围绕“教师是主体还是学生是主体”、是“教师与学生都是主体”,还是“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的问题争论不已。这些针对教师和学生“谁是主体”问题的讨论,由于存在研究视角、价值立场、理论资源的差异,导致各执一端自说自话的结果。其实,从哲学认识论视角仅仅讨论“主体”的问题,如果忽略主客体互为存在与规定的对应性关系,离开则无法说清“谁是主体”的问题。因此,与其说在理论上讨论“谁是主体”的问题,不如在实践的层面讨论“主体性”更有实际意义。
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确认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的观点一直得到普遍的认同。在教学实践中,“主导”与“主体”虽然称谓不同,但在强调各自主体性发挥问题上无疑是一致的。教师在组织推进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和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性,其实是互为主体和各行其职的作用发挥问题。承认和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放弃了教师主导,并不意味着教师的作用要降低。因为,“放弃了教师主导,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就失去了保证,就可能降低到日常生活水平,因为处于发展中的儿童青少年是无法凭借自身完成所需要的教育的”[2]。事实上,强调和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教师的缺席”和教师主体作用的放弃。
摒弃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模式,确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原则,这无疑是一种教育观念的重大转变和进步。雅斯贝尔斯曾经告诫:“教育者不能无视学生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况,而认为自己比学生优越,对学生耳提面命,不能与学生平等相待,更不能向学生敞开自己的心扉。这样的教育所制定的教学计划,必然会以我为中心。”[3]1然而,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由于强调学生学习中的主体性地位,教师出于鼓励学生充分发挥学习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同时,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不但有意从中心地位撤离,而且成了只有身体在场的精神缺席者。以学生为主的满堂问,无目的地让学生交流讨论,表面上课堂十分活跃,但实际上收效甚微。讨论的问题几乎不成其为问题,学生在没有任何准备情况下参与讨论,问题在平面上滑行,无端地浪费课堂的时间,教师事实上沦为一个“报幕员”和“旁观者”。这种“教师的缺席”不是指教师不在课堂,而是教师身在课堂却没有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和应该承担的责任,使学生在课上展现的是学生肤浅的、表层的,甚至是虚假的主体性。事实上,教师在组织推进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没有组织的教学是不可想象的,教师是教育教学的实施者,不能因为强调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而忽略教师的地位和不可取代的作用。
在学校教育中,学生的主体性是具有明确学习任务和内容,承担明确责任和义务,在教师教导下的主体性。与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性不同的是,学生的主体性是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培养与发展起来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它在学生的成长中具有渐进和未完成性特点。新课改要求师生之间建立民主、平等的关系,彼此之间应当学习、合作,这是我国历次教育改革所一贯倡导的。但是人格上的平等不能泛化成为知识水平的相同,似乎教师懂不懂学科知识都可以,只要有一颗与学生平等的心,和学生一起讨论和探究,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如果真的是这样,教师的专业性体现在哪里?教师存在的必要性又体现在哪里?在教与学的关系中,教师要承担起传授知识的责任,在学业上教师可以而且应该做主,这是教师的使命。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必须确立,但是学生的主体地位与教师的主导作用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学生的主体地位是在教师主导作用下确立的。“教师要把学生的注意力从教师身上转移到学生的自身,而教师本人则退居暗示的地位。师生之间只存在善意的论战关系,而没有屈从依赖关系。”[3]8教学中学生在自主学习时需要教师发挥主导作用是前提,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服务的,离开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学,教师的教就没有意义;反之,学生的学不仅得不到保证,难以保证效率,失去了教学中“学”的意义。这意味着,“人必须靠自己完成自己,必须决定自己要成为某种特定的东西,必须力求解决他要靠自己的努力对自己解决的问题。他不仅可能,而且必须是创造性的。”[4]在学校教育中,学生学习的特点就是有教师教,有指导、有规范。我们在基础教育领域不断要探索和进行改革的是教师在发挥主导作用中存在的问题,不是否定教师的教,削弱教师的教。学生是需要帮助和引导的学习者,也是需要不断完善和提高的学习者,自主、合作、探究的空间和可能性需要不断拓展和现实化,学生的“未完成性”也意味着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过分持乐观态度当然是教育者一种良好的愿望,但并不等于一切都如愿以偿。这意味着,教师在组织推进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没有组织的教学是不可想象的,教师是教育教学的实施者,不能因为强调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而忽略教师的地位和不可取代的作用。
三
在教育者认识与评价视野中的学生,通常指称与教师构成对象性关系的群体,这个群体实际上是一个宽泛笼统的所指。这种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认识与把握,虽然能够着眼于整个学生群体,但关注的只是这个群体的一般性特征,对群体中的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则往往是忽略的。如果教育者眼里的学生仅仅是一个具有群体性特征的抽象概念,而无法体现对学生个体差异性的理解和把握,那么,教育者的学生观也便仅仅具有宏观普泛的认识意义。
事实上,当教师面向一个群体对象展开教学实践之前,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就已经成为一个事实的存在。为什么在同一个教师的课堂上,“有些学生学的快,有些学生学得慢”,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个体之间存在的差异无疑是原因之一。教育者往往从教学角度寻找差异的原因,力图通过改进教学缩短差异的距离,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差异。正视和承认个体之间差异的存在,分析学生在感知、记忆、理解、表达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原因,将教学的针对性落实到每一个差异的个体,才有可能实现因材施教的目的。这其中因材是施教的前提和基础,施教如果缺乏对具体对象的了解,缺乏对每一个学生特点和需求的关注和认知,施教的针对性和实际效果就无法得到保证。
从抽象意义和总体特征上认识和评价学生的学生观,还存在评价中的不完全归纳认识和对特殊性忽略的倾向。面对一个不断成长发展的学生群体,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变化使注重普遍性和一般规律的评价变得力不从心和捉襟见肘。教师对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评价,往往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教学过程、教学效果、学生学习效果等环节进行评价,研究和反思教学过程与方法的有效性与针对性问题,进而提出教学改进的策略实施计划。这种对教学有效性的反思与评价,其基本依据是课堂效果和学生的考试情况,而且这种观察和分析也仅仅是一个粗略和大致的评估。正像杜威分析的那样,“教学可以被比作销售商品,除非有人买入,否则没有人可以卖出。如果一个商人说他已卖掉了大量的物品,而实际上并没有人买走任何东西,我们会嘲笑他。但是,或许也存在这样的教师,他们认为已经完成了一天的出色的教学任务,而不管人们已经学到了什么。教学和学习之间的这种确切的等同关系就如同买与卖的等同关系一样。”[5]其实,判断学生是否学到了什么要比判断商品是否被人买走复杂得多,因为商品销售情况有据可查,而学生掌握学习内容的经历却是一个内隐的变化过程,课堂上群体的热闹场面并不意味着学习的真正有效,而且,表面的现象往往掩盖着个体之间差异存在的事实。
在如何促进学生发展的问题上,教师首先要真正了解和研究自己的学生,了解他们不同时期的成长规律和特点,研究他们在智能发展、知识积累、思维认知、情感态度、兴趣和爱好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和个体差异,真正在自己心目中为每个学生“建档”,让学生的“形象”变得清晰和完整,而不是一些模糊不清的“面孔”。对于学生应该发展成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教师如果真正了解自己的学生,他就应该能够对学生的发展的未来做出具有前瞻性的预测,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给出未来学习发展的建设性意见,并在学习实践中进行具有针对性的指导与鼓励,让学生在一个明确的目标设计中进行自觉而有效的学习。一个教师如果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因材施教则不再是一个向往与渴求的理想。
教育者对学生的认识和评价,除了因各自立场的差异形成不同的学生观之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作为成人的教育者是否真正了解和理解学生的问题。我们是否按照成人的价值立场和期待在想象一个并不了解的对象?我们的想象和判断距离学生的实际究竟有多远?由我们的立场构建的教育是否真正符合教育的规律?我们的教育实践是否实现了我们的判断和希望?这是需要认真反思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反思学生观的目的不在于证明学生的对与错,而在于思考学生观的合理性,在于探讨教育实践中的实际问题。
[1]郭华:儿童·孩子·学生[J].人民教育,2006(11):26.
[2]丛立新.平等与主导——师生关系的两个视角[J].教育学报,2005(1):30.
[3][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4][德]M·兰德曼.哲学人类学[M].阎嘉,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228.
[5][美]奈尔·诺丁斯.教育哲学[M].许立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