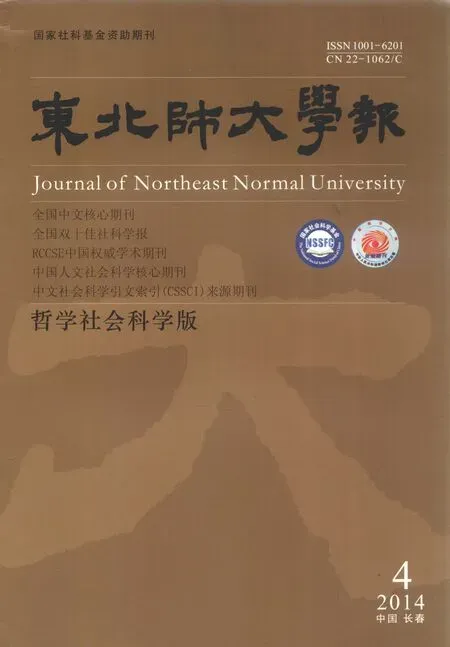舞踏中的身心关系问题研究
2014-03-24孙慧佳
刘 炼,孙慧佳
(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舞踏中的身心关系问题研究
刘 炼,孙慧佳
(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作为后现代舞代表之一的舞踏通过瓦解意识的客体化作用、解除视觉的优先地位等手段,用独特的身体语言对传统二元论和“表现”的身心关系进行解构,建构起以身心感知为本质的身心关系。对舞踏身心关系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这种后现代舞形式,对发展我国的后现代舞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舞踏;身心关系;身心感知
舞踏,又叫暗黑舞踏(Ankoku Butoh),是日本后现代舞的一种形式,由日本舞蹈家土方巽和大野一雄于20世纪50年代所创建。20世纪80年代以后,舞踏开始逐渐引起欧美舞蹈界的注意,并在21世纪后成为风靡世界的后现代舞形式,频繁出现在国际各类艺术节、舞蹈节的舞台上。如今,日本舞踏已和德国舞蹈剧场以及美国后现代舞蹈并称为当代三大新舞蹈流派。
以往对舞踏的研究比较注重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进行探讨①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的克里斯托弗·金以舞踏身体的“形”(カタ)为核心概念,从中探寻重大社会事件的影响,认为舞踏的身体是日本在美军占领后“身份转换”和“存在焦虑”的表达。(Christopher King.Japanese Body and Self[C]//Sociological Sites/Sights,TASA 2000 Conference.Adelaine.Flinders University Press,2000:4.)野田学夫认为舞踏的身体形态是日本身体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和现代化影响局促不安的表现,在西方文化的压力下,日本的身体文化已经显得麻木不仁。(Manabu Noda.The Body Ill at Ease in Post-War Japanese Theatre[J].New Theatre Quarterly,2007:274.)米歇尔·登特把舞踏描述为“在传统日本文化和战后日本文化之间摇摆不定的身体技巧”和“对毁灭意象的错位表达——这毁灭中既有广岛和长崎的宏观性的毁灭,又有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微观性的覆灭”。(Michelle Dent.The fallen body:Butoh and the crisis of meaning in Sankai Juku's“jomon sho”.Women &Performance:a journal of feminist theory,2008:178-180.),却鲜有人关注舞踏这种艺术形式在哲学领域的贡献。舞踏极端的艺术语言中呈现出日本民族的身心状态并引起了世界的共鸣,其中对人的身心关系的独特理解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
一、舞踏对传统身心关系的解构
(一)“尸体的舞蹈”——舞踏对二元论身心关系的解构
舞踏的开创者土方巽曾为舞踏下了一个知名的定义——“舞踏是拼命站立起来的尸体”[1]。这个定义不仅说明舞踏用扭曲的身体形态表现人性中黑暗的一面,从身心关系的角度来解读,“尸体的舞蹈”更是对传统二元论身心关系的解构。
二元论身心关系把人的身体和心灵看作是两种不同性质又相互作用的实体。自笛卡尔以来二元论身心关系得到确立,其后一直主宰着人们对身心关系的看法。二元论的身心关系是以“心”为主导的二元,认为身体是受到心灵控制的客体存在。
土方巽所谓“尸体的舞蹈”消解掉了身心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把传统意义上属于“心”的东西移除,只剩下“身”的部分,如此人也便成了“尸体”。舞踏正是通过这种方法“去除社会借由理性思维强加给人的反应,揭示身体与心灵的无意识联系,让人把精力集中于无意识和抽搐、痉挛等非同寻常的身体动作本身”[2]。土方巽所谓的“尸体”对应的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而是理性思维与意志的死亡。而移除了“心”的内容的“尸体”也不是以物质形成存在的一具人的躯壳,而是成为新的充满开放性的存在。舞踏的另一位开创者大野一雄也曾用“尸体”一词来形容舞踏的身体,他所谓的“尸体”是一种“随时准备接纳意想不到的外界刺激与内心欲望的活跃的身体状态”[2]。
舞踏舞者在演出前会通过禁食等手段清空身体,用极度的饥饿让意识涣散,让身体像一个空空如也的容器,随时等待对外界刺激做出最为原始直接的反应,或在内心隐蔽欲望的驱使下舞动起来。活跃在东南亚的日本舞踏女舞者武藤理香在1998年菲律宾举办的一次舞蹈工作坊的发言中曾说到:“与其他舞种考虑如何站立不同,土方巽创立的舞踏的基础在于不能由意志支撑或操控的无法站立的身体。”“意志”被有意识地从身体中剥离开来,二元的身心关系被消解掉了,而在剩下的身体中又孕育着新的一元的身心关系。可见“尸体的舞蹈”是对传统二元论身心关系的解构和一元身心关系的建构。
(二)舞踏对“表现”身心关系的解构
传统身心关系的另一个主流看法就是“表现说”,认为身体是“表现”心灵的工具,而心灵是被“表现”的内容。这种看法在舞蹈领域尤为普遍,特别是伴随着近代以来编舞艺术的发展和舞剧艺术的日趋成熟,舞蹈被人们强行框进了语言逻辑之中——舞蹈的动作被分为舞段、舞句,舞蹈的身体成为“表现”思维与情感的工具。
关于舞踏与“表现”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需要进行说明。尽管舞踏致力于发现、探索和解放被社会文化所禁锢压抑的身心,但如果简单地把舞踏理解为“表现”一些被压抑的东西就大错特错了。
美国舞蹈学者桑德拉·霍顿·弗雷利曾经先后跟随德国表现主义舞蹈的创始人玛丽·魏格曼和舞踏的创始人之一大野一雄学习舞蹈。她曾写到:“在魏格曼舞蹈学校学习,我们是根据指示即兴地做出动作,然后向全班展示自己是如何从即兴动作出发完成编舞的。而大野一雄的舞蹈课堂则没有如此多的指示,也不像魏格曼的课堂那样充满展示与交流,大野一雄要求我们在内心当中睁开一只眼睛来关注动作和自身。”[3]从弗雷利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舞踏训练要求舞者“在内心当中睁开一只眼”,对自己的身心状态进行感知,而且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把感知到的身心状态表现出来,而只是对其进行体验并由此而引发动作。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舞踏与德国表现主义舞蹈之间有着一定的传承关系。舞踏的创建者土方巽和大野一雄在创建舞踏之前都曾经接受过德国表现主义舞蹈的训练。这种历史上的联系以及两者之间都具有的即兴的特点使一些研究者给舞踏贴上了表现主义舞蹈的标签。但很多舞踏舞者却对此极为不满。兴膳沙舞踏舞团的负责人和栗由纪夫在一次采访中曾说到:“如果‘表现’是一种身份的标签的话,那么我决不同意把舞踏看作是表现主义舞蹈的一种。”[4]和栗由纪夫认为,西方文化更强调个人主义,因此“表现”才有意义。而在日本文化中,个人的概念十分模糊,“表现”的意味也就不那么明显。表现主义是外界强加给舞踏的标签,是西方文化对舞踏的扭曲。“‘表现’意味着将一个人的内在与外在割裂开来,我认为需要改变这种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4]
从上述例证我们可以看出,舞踏舞者在刻意与“表现”划清界线。“表现”是一种由内而外的释放过程,而舞踏中释放并不是重点。舞踏舞者不会对自己身体的形象和观众的反应进行关注,而只是强调要时刻保持对内在身心状态的关注。“舞踏舞者在舞台上追求的并不是让观众看懂或理解什么,他们只是自顾自地在舞台上体验着动作和内心,而观众也会与他们产生一种神秘莫测的共鸣。”[5]可见,舞踏并不是以“表现”为目的的,舞踏的身体动作不表达任何情感,不传递任何信息,这些舞蹈动作与其他所谓“内容”因素的联系被割断了,只是舞者体验的对象和结果。可见,舞踏解构了传统的以“表现”为核心的身心关系。
(三)舞踏解构传统身心关系的方法
为了对根深蒂固的身心二元论及其“表现”关系进行解构,舞踏舞者一般会采取以下两种做法:
第一,瓦解意识的客体化作用。
日本舞踏表演者和研究者葛西俊治认为,在日常状态下人的意识具有客体化作用,总是把关注的对象作为客体化的目标,把身体作为供意识主体驱使的工具。而舞踏表演中的身体是“非客体化的身体”,这种“非客体化的身体”排斥意识对其进行的客体化、工具化,将身体与意识看作是密不可分的一体存在[6]。
为了去除意识根深蒂固的客体化作用,使身体从意识的遮蔽中走出而与心灵融为一体成为“非客体化的身体”,首先就要对意识进行瓦解。舞踏舞者经常会借鉴宗教中的修行方法来使自己进入这种状态,最常见的就是佛教中禁食修行以获得开悟的方法。土方巽曾要求他的一个学生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只吃一个苹果。山海塾和其他的一些舞踏表演团体会在演出前几天就开始禁食,甚至有的演员在禁食后因为饥饿与虚弱动弹不得。在演出时,极度的饥饿与虚弱会使人神志恍惚,意识涣散,轻易进入催眠状态。通过禁食可以使身体从意识的客体化作用中解脱出来,成为“非客体化的身体”,使人的精神与肉体进入一体的状态。
第二,解除视觉的优先地位。
视觉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最多的感觉,也是人类最为依赖的感觉,与其他感觉相比有着突出的优先性。长期以来,人类的视觉已经和传统的身心关系观念建立了深刻的联系。往往人们在运用视觉进行感知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地运用传统的身心关系去观察理解自己与世界。舞踏舞者认识到,要想对传统的身心关系进行解构,就必须要解除视觉在感知过程中的优先地位。
舞踏舞者在训练中是不使用镜子的。“一个人跳舞的时候如果始终观察着镜子中的自己,那你就不是在跳舞,而是在分析你的身体表现,这样会错失你身体当中真实的、微妙的感觉。”[7]镜子会诱使舞者过多地关注自己的身体形态,在潜移默化中使身体处于客体化的位置,也会分散舞者对自己身心当中微妙变化的注意力。“观察一个人在镜子中的身体需要依赖我们日常使用最多的视觉,这会影响舞者调动其他感觉器官的能力,比如嗅觉、听觉,特别是触觉。”[8]260-262只有不使用镜子,舞者才会不依赖视觉,而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在嗅觉、听觉、触觉上。这些感觉不像视觉那样被过多的社会、文化因素所浸染,更具有个体特色。依赖这些感觉——特别是触觉——去对自己的整个身心进行感知才可能挖掘出个体身心中所深度隐藏的东西。不使用镜子能避免通过视觉对身体进行客体化处理。有时候尽管没有镜子,人们还是会在头脑当中有意识地呈现自己身体的形象以随时将其调整到符合社会习俗及多数人审美观念的状态,这仍然是意识对身体的客体化。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舞踏舞者在舞蹈的时候会时刻保持一种对本体感受的感觉状态,有意识地用身心感知来代替视觉在感知中的优先地位,这样才能使自身从传统的身心关系中解脱出来。
除了在训练中排斥镜子以外,舞踏舞者还会在训练与演出时紧闭双眼,或让眼睛微睁,并将眼球上翻,只露出白眼球。优秀的舞踏舞者虽然可以保持双眼睁开的状态,但目光却并不聚焦,在舞蹈过程中保持身心感知的状态而不堕入视觉的樊篱中去。美国的琼·拉格曾在日本学习舞踏多年,她在回忆自己学习舞踏的经历时说到:“芦川、大野和田中不断提醒他们的舞者眼睛要‘无视’。芦川常把一个只有一只大眼睛的头部模型或者全身满是眼睛的身体模型摆在舞者面前提醒他们。她还习惯用一张报纸在舞者眼前不断晃动来混乱他们的视觉,扰乱他们目光的焦点。”琼·拉格强调说:“散乱或无视的目光焦点可以使富于交流功能的头部,特别是面部与身体的其他部分处于平等地位。”[9]
二、身心感知——舞踏身心关系的建构
(一)身心感知是舞踏身心关系的本质
所谓“身心感知”,简单的说,就是身心既是感知的媒介和手段,又是感知的对象,是指舞踏舞者用身心整体去感知平日里被压抑的冲动、欲望,接受外界给予身心的各种刺激,并由此而引发动作的过程。之所以使用“身心感知”的概念是因为舞踏中的感知与一般意义上的感知有着明显的不同。二者具体的区别如下:
第一,身心感知强调身心的整体性。
舞踏舞者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感知是建立在身心二元论基础上的概念——人用眼睛、耳朵等感觉器官接受外界的刺激,再把这种刺激通过神经系统传递到大脑当中,由大脑作出相应的判断后再通过神经系统控制人体肌肉的运动使人做出反应,这是一个由外至内再到外的过程。而身心感知则刻意避免这种内外分割的身心二元论,人的身心既是感知的主体,又是感知的对象,是一个统一的一元存在。人的身心是紧密联系的整体,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舞踏舞者经常会用一个问题来描述这种身心的一体性——当一个人受伤的时候,身体和精神哪个处于疼痛之中?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莫过于“我很疼”。“我”是身体与精神协同构成的整体,很难分割开来。舞踏舞者经常会提到一个词汇——舞踏泰,在日语直译的意思为“舞踏的身体”。但在舞踏舞者眼中,舞踏泰却并不单纯是指舞者的身体,还蕴涵着一种精神的内容,是指舞者训练和表演时保持的一种关注身心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身心感知的状态。
第二,一般意义上的感知更侧重对外在世界的感知,身心感知更侧重对内在世界的感知。
一般意义上的感知是用人的感觉器官对外界环境中的光线、声音、味道等对象的感知,这种感知主要是对外在世界的感知;舞踏中的身心感知则侧重于对人的内在世界的感知。一般意义上的感知即使以人的内心为感知对象,其本质仍然是对外指向的。在日常状态下,一个人的感知会受到社会习俗的深刻影响,人们会时刻感知自己的身心状态是否符合社会习俗的要求并对其做出调整,对自身产生的不符合社会习俗的冲动和需要进行控制与压抑。外界环境中的刺激对舞踏舞者来说并不是直接感知的对象,他们会集中精力来感知外界刺激给自己的身心带来的影响,以及身心在刺激作用下的原始反应,这样的身心感知本质上仍然是对内指向的。
身心感知是舞踏身心关系的本质。一个人是否进入舞踏状态的关键取决于其是否进入身心感知的状态。因此,在身心感知状态下建立起来的身心关系就是舞踏身心关系的核心。身心感知既是舞踏身心关系存在的环境,又是舞踏身心关系的本质。我们可以从舞踏名家野口三千三对自己舞蹈时身心状态的描述中得到这种启示。野口三千三是舞踏训练体系之一——野口体操的开创者,他认为,我们的身体并不是附着有肌肉的骨骼框架,而是像一个大水袋,骨骼和内脏飘浮于其中。他还特别强调重力对人的重要意义,要求他的舞者们“听从重力之神的召唤”。他曾写到:“肌肉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对抗与控制重力,肌肉是倾听神的召唤的耳朵,这个神就是重力”[10]。在野口眼中,人的身心同时在感受着重力带给人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身心不仅是感知的手段,也是感知的对象。因为重力需要作用于人的身体,身体在重力的引领下又会给人的身心形成一种刺激,从而引发身心进一步的活动与发展。正是在这种身心感知的基础上,舞踏的动作过程才得以继续和发展。
舞踏的目的是要去除社会习俗等外在因素对人的遮蔽,让人充分认识和感受自己身心的需要,从社会人的状态转变成舞踏的状态。这个转变过程中最首要的就是“让感知来激发身体的动作,让被我们平时忽略的刺激引导自身的行为。平时在社会环境中为我们所忽略的稍纵即逝的欲望成为舞踏舞者进入舞踏状态最主要的暗示和线索”[8]260-262。可见,一个人是否进入舞踏状态的关键就是从日常受理性规范的身心状态转变为以身心感知为核心的状态。这种感知的状态可能会让人很不舒服,因为经由感知而引发的身体反应与动作不由舞者的理性控制,是舞者不可预期的,可能会让舞者自己大为惊奇。舞踏中的身心感知可能会给人一种消极的印象,其实却有着积极的开放性,在身心感知中的舞者更容易接受来自外界和自身的各种刺激。当舞者把全部身心都集中在感知当中,在身心中压抑的冲动和情感才得以充分释放。这个过程可能让人醉心其中,也可能使人痛苦不堪,但无论如何,这种以整个身心参与的,对身心整体进行的身心感知可以引领舞者走向身心一体的境界。
(二)舞踏中进行身心感知的过程和方法
舞踏中身心感知的方法可以促进人身心的整合,这对于治疗某些身心分裂造成的身体和心理疾病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有研究者将舞踏身心感知的方法与亚历山大技术、感官知觉技术、格式塔心理治疗、生物能疗法等并列在一起①参见Nicholss,J.Carey,S.The Alexander Technique:In Conversation with John Nicholls and Sean Carey[M].Brighton:The Brighton Alexander Technique Centre,1991.110-112.,足见身心感知的训练方法在促进人身心一体化方面的有效性。
为了使舞者进入身心感知的状态,让舞者对周围环境中的刺激进行感知,释放身心当中压抑的冲动和欲望,概括来说,舞踏训练会采用如下方法:
放松方法。放松是引导人从日常理性状态向舞踏身心感知状态转变的关键。在放松过程中,人可以摒除理性思维,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对身体感受和内心欲望的感知上面。不同舞踏流派的放松方法也不尽相同。竹内训练课程中采用的是手臂放松法。具体做法是两人一组,一人放松,同伴缓慢提起其手臂再放开。这个过程虽然简单,但九成以上的人都会下意识地帮助同伴提起自己的手臂,在同伴放开手后手臂依然不会放松下垂。这个过程可以帮助人们充分认识身心一致的困难性,从而在后面的训练中避免身心不一致的问题。
扭曲方法。扭曲的方法在其他舞种和身心治疗方法中从未出现,因此几乎成为舞踏训练的标志。故意地扭曲身体的某个部分可以引起身体其他部分的扭曲、变形,并使扭曲融入整个身心当中,这有利于将人身心当中黑暗的一面揭露出来,使其从身心当中隐蔽的深处走向前台。
震动和摇晃方法。当人把重心降低屈膝站立的时候,身体自然会产生震动和摇晃。身体的震动和摇晃往往会让身体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反应,比如突然的痉挛和抽搐、没有目的方向的跳跃和踢打,等等。这种方法在生物能疗法当中也可以见到。
呼吸方法。呼吸方式的改变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身心状态,缓慢的呼吸可以使人平静,短而急促的呼吸甚至可以使人昏厥,不断调整呼吸方式可以带来出其不意的身体反应。舞踏训练中往往采用深呼吸的方法作为开启身心感知的第一个步骤。
重复方法。在人们不断重复一组动作的时候,身体就会从有意识地主动完成动作逐渐转变为下意识的动作,然后伴随着外界刺激的进入或内心欲望的涌现,重复的动作中就会产生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这个过程会引导人们进入身心当中未知的领域。
三、结 论
舞踏之所以会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获得世界范围的认可,部分原因是其怪诞的身体形态中蕴涵着对人们身心关系的哲学思考,这些思考迎合了当下的哲学和美学发展趋势,引起了世界的共鸣。舞踏通过瓦解意识的客体化作用、解除视觉的优先地位等手段,用独特的身体语言对传统二元论和“表现”的身心关系进行解构,建构起以身心感知为本质的身心关系。对舞踏身心关系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这种后现代舞形式,对发展我国的后现代舞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1]刘青弋.土方巽:舞踏是一种拼命站立的尸体[J].舞蹈,2011(10):49.
[2]Simon Tate.Physical Theatre from Asia's Largest Island-Australian Butoh[DB/OL].http://ibtheatre.wikispaces.com/file/view/DQ+Butoh+article.pdf.
[3]Sondra Horton Fraleigh.Dancing Into Darkness:Butoh,Zen,and Japan[M].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9:76.
[4]Yukio Waguri.Interview in“2nd Butoh &Related Arts Symposium and Dance Exchange Project.Ex it!'99 document”[DB/OL].http://www.ne.jp/asahi/butoh/itto/ex-it/pamph99.htm.
[5]Tara Ishizuka Hassel.BUTOH:ON THE EDGE OF CRISIS?——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Japanese Avantgarde Project in a Postmodern Perspective[D].University of Oslo,2005:73.
[6]Toshiharu Kasai.A Note on Butoh Body[C]//Hokkaid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emoir of Hokkaid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okkaido:Hokkaid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2000:357.
[7]Toshiharu Kasai.Notes on Butoh Dance[DB/OL].http://www.ne.jp/asahi/butoh/itto/kasait/k-note.htm.
[8]Toshiharu Kasai,Kate Parsons.Perception in Butoh Dance[C]//Hokkaid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emoir of Hokkaid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okkaido:Hokkaid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2003.
[9]Joan Elizabeth Laage.Embodying the Spirit:The Significance of the Body in the Contemporary Japanese Dance Movement of Butoh[D].Texas Woman's University,1993:78.
[10]野口三千三.野口体操:响应重力之神[M].东京:白寿书局,1979:87.
Study on Mind-body Relationship in Butoh
LIU Lian,SUN Hui-jia
(Music School,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of post modern dance,Butoh deconstructs traditional dualism mind-body relationship and“expressive”mind-body relationship by collapsing the objectifying function of consciousness and crumbling priority of visual perception.Also,Butoh considers psychosomatic perception as the core of its new mind-body relationship.Study on the mind-body relationship in Butoh helps us understand this post modern dance form comprehensively.The study also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st modern dance.
Butoh;Mind-body Relationship;Psychosomatic Perception
G44
A
1001-6201(2014)04-0172-05
[责任编辑:何宏俭]
2014-01-27
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12DE22);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2BS12)。
刘炼(1962-),男,山东章丘人,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孙慧佳(1980-),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舞蹈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