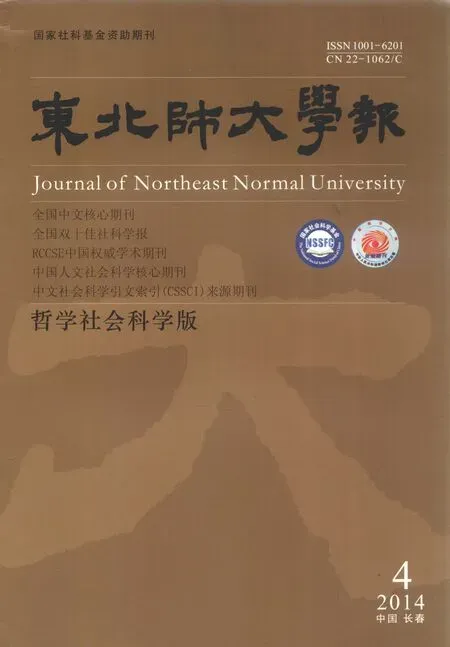“毒胶囊”事件关联行为之刑法定性研究
2014-03-24逄晓枫刘晓莉
逄晓枫,刘晓莉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吉林长春130117)
“毒胶囊”事件关联行为之刑法定性研究
逄晓枫,刘晓莉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吉林长春130117)
对“毒胶囊”事件关联行为进行定性分析,必须要确立罪刑法定之形式正义的立场,将形式理性思维贯彻于定性分析过程之中。明确“毒胶囊”与“毒胶囊”剂的法律性质,将两者分别界定为伪劣产品与假药,这是行为准确定性的前提。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结合刑法共犯理论,应当将制售“毒胶囊”的行为纳入制售伪劣产品罪的评价体系内进行定性分析,将制售“毒胶囊”剂的行为纳入制售假药罪的评价体系内进行定性分析。
制售“毒胶囊”;制售“毒胶囊”剂;行为定性
所谓“毒胶囊”是指制造医用胶囊的原料重金属含量超标,其中铬含量超标问题更为严重。铬元素易于进入人体细胞对肝、肾等器官造成损伤,甚至可能产生致癌风险。在“毒胶囊”事件中,制售“毒胶囊”与制售“毒胶囊”剂之行为更具有社会危害性和争议性,对其准确定性不仅关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而且关乎我国刑法对民生保障的问题。鉴于此,本文拟围绕上述行为的定性问题展开探讨,力求为司法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一、行为定性之立场:罪刑法定之形式正义
(一)罪刑法定之形式理性
“罪刑法定”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一原则是由刑事古典学派最初倡导的,是法治原则在刑法中的直接体现,是法治社会刑法与专制社会刑法的根本分野[1]85。罪刑法定是现代刑法的基本精神,将罪刑法定视为刑法的核心原则已经取得了广泛共识。罪刑法定已经被写入国际条约,成为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罪刑法定的终极价值在于防止罪刑擅断,使民众免受不可预测的刑罚惩罚,从而保障民众的合法权益。有学者指出:“罪刑法定主义实际上是在国家权力和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2]35
根据韦伯的理性区分理论,可以将理性分为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总体而言,形式合理性解决的是事实问题,是关于事物是什么的认识问题;而实质合理性解决的是价值问题,是关于事物为什么的判断问题。”[4]具体来说,形式理性强调规则效力的一致性,其不以个人或者集团的好恶情感为转移;而实质理性更加注重主观和结果,它把规则看作是支配结果的工具。形式理性与罪刑法定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两者在逻辑表达上具有同一性。罪刑法定之形式理性视规则为正义的基石,它崇尚法律的明确性与稳定性,反对任意解释条文,其目的在于培养规范意识,以此凸显公民权利与自由的确定性,这是一种形式正义的法治立场。具言之,只有刑法明文规定某种类型行为是犯罪的,才能定罪量刑;刑法未规定某种行为类型是犯罪的,无论该行为具有多么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都不能将其入罪。为获得形式合理性,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能不以丧失实质合理性为必要的代价[2]35。
(二)罪刑法定之现实困境
尽管罪刑法定已在我国“生根发芽”,形式理性思维也越来越受到推崇,但是传统思维范式未从根本上得以改变,罪刑法定要从文本彻底走向现实还需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一直具有实质性的思维传统,这导致我们经常轻视纯客观的东西、客观的规则、客观的标准,在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之间往往导向实质理性。”[5]实质理性因其诉求目标具有正当性而在司法实务界聚集了众多的追随者,但实质理性所彰显之理念确实与现代法治精神不相符合,司法者以其思维模式处理刑事案件必然会对罪刑法定原则产生强大冲击,动摇法治根基,当前“量刑反制定罪”之思维就是实质理性在司法领域中的典型表现。
“所谓量刑反制,就是在行为定性的时候首先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然后根据量刑的需要寻找合适的罪名。”[6]48支持“量刑反制定罪”理论的学者认为:“刑事责任才是具有实质意义的刑法结论,也是被告人和民众关注的核心;如果根据犯罪构成判断出的罪名会使量刑明显失衡,就应适度变换罪名以实现量刑公正,让罪名为公正的刑事责任让路,不能把准确判断罪名作为优于量刑的司法重心。”[7]相比定罪与量刑的传统关系而言,这是一种极具颠覆性的观点,它改变了“定罪是量刑的前提”这一传统的逻辑思维,认为司法实践的重心应从准确定罪转移到公正量刑上,量刑真正代表了刑法正义;而罪名只是用来辅助刑事责任的认定,过分追求罪名的准确性只会伤害民众的正义情感。显然,这是一种实质理性的思维方式。该观点的提出引发了其他学者的激烈争论,其中,持反对观点的学者认为:“弱化罪名的重要性,隐藏着一种风险,即在某个案件事实符合法定刑较重的犯罪构成要件时,为了判处相对较轻的刑罚,就认定为法定刑较轻的犯罪,这容易违反罪刑法定原则。”[8]
在当前存在量刑畸轻问题的典型个案中,“量刑反制定罪”理论不失为解决量刑不公现象的一种路径,但是依照“定罪为手段,量刑为目的”之思维所得出的结论很容易被个人直觉或民粹正义所左右,这就无法保证刑法的公正性;另一方面,为求量刑合理而变换罪名的做法,反而使罪名丧失了其行为定性的价值,甚至直接损害了犯罪构成的类型化功能,可以说,这是一种无视具体事实的主观擅断。不仅如此,“在没有罪名争议或刑法规范依据的前提下,赋予法官更改罪名的权力,本来就是一种巨大的风险,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赋予法官改变罪名的权力,法官就会打着量刑公正的旗帜,以司法权入侵立法权,破坏人类社会来之不易的刑事法治”[9]。综上,“量刑反制定罪”理论有其无法克服的缺陷,它的实践必然会危害现代刑法的规范效果,改变定罪与量刑的逻辑关系,偏离罪刑法定的轨道。因而,这种理论观点是不可取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的审理中,“量刑反制定罪”的情况较为突出。例如,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中的广泛适用。在认定某些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行为的性质时,由于较多关注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实践中往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定罪,以求能够在法定刑较重的量刑范围内对行为主体作出处罚。这种以量刑推导罪名的做法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应该坚决予以摒弃。如果量刑出现不合理之处,则应通过必要的立法修订或解释来处理,“而不是通过司法僭越立法的方式来解决”[6]48。在下文讨论的“毒胶囊”事件中,形式法治立场的确立对该事件关联行为的刑法定性研究至关重要,因为这是逻辑推演的理论根基,也是事物认知的思维方向,它体现了一种正义理念的现实选择。
二、行为定性之前提:行为对象之法律性质
“特定的行为对象在大多数犯罪中是客观构成要件的要素之一,行为只有作用于特定的对象,才能构成犯罪。”[10]通过对刑法分则条文分析表明,行为对象与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关系具有多重性:有的具有指向与被指向的关系;有的是作用与被作用的关系;但更多的是说明与被说明的关系[11]。可见,行为对象是行为评价结果的实体要素,它与行为作为整体共同诠释行为的构造价值。行为对象体现特定法益或者行为类型,所以,行为对象不同,犯罪性质亦不同,行为对象是行为定性的前提。可以说,对“毒胶囊”事件关联行为的刑法定性争议,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行为对象性质的不同理解而造成的。
(一)“毒胶囊”之法律性质
[12] HELCOM, The Baltic Sea Declaration, http://www.helcom.fi/Documents/About%20us/Convention%20and%20commitments/Ministerial%20declarations/RonnebyDecl1990.pdf.
在界定“毒胶囊”性质之前,首先要明确其前身即药用空心胶囊的法律性质。药用空心胶囊是用于填装固体药物的一种产品,它往往与药物合并为整体供患者服用,所以其质量问题关涉药品疗效和用药安全,一旦出现事故,危害不可估计。2010年卫生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以下简称新版药典)将药用空心胶囊命名为明胶空心胶囊,并把它归入药用辅料类,在效力上首次明确了铬在明胶中的含量标准即不得超过百万分之二。“至此,药用空心胶囊才有了具体的可操作控制标准,并在实质意义上将明胶空心胶囊质量的控制转换为胶囊生产原料——药用明胶的质量控制。”[12]891药用空心胶囊在药典中被规定为药用辅料,那药用辅料又是什么呢?在新版药典中,药用辅料是这样定义的:“生产药品和调配处方所使用的赋形剂和附加剂,是除活性成分以外,在安全性方面进行了合理评估并且包含在药物制剂中的物质”。简言之,药用辅料是药物制剂的一种物质载体材料,其本身并不具备疗效成分,它仅对药物的疗效起到提高、改善的效果。故药用空心胶囊是完全符合药用辅料的标准。
尽管药用空心胶囊在类别归属上已得到明确,但其法律性质还需要进一步的阐释。药用空心胶囊既为药用辅料,它进入人体内部辅助药物发挥其疗效作用,尤其他具备释药功效,这就与药品包装材料在性质上相区分开来,而后者只是用于制造包装容器、包装装潢、包装印刷、包装运输等满足产品包装要求所使用的材料,不具有药效辅助性。此外,药用空心胶囊是可直接供患者服用的,那么,是否可以据此认定它为食品呢?食品在《食品安全法》中被定义为是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由此可见,食品概念并未将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列入其中,而药品空心胶囊是一种以辅助治疗为目的的物品,所以说,药用空心胶囊在性质上不是食品。
药用空心胶囊在性质上既不属于药品包装材料,也不属于食品,那么是否可以因其具有疗效辅助性而视为药品呢?这也是本文的疑难所在。《药品管理法》第102条对药品与辅料的概念分别作了规定①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辅料是指生产药品和调配处方时所用的赋形剂和附加剂。,并对药品范围作了举例说明,从条文表述上看,两者是性质不同的两种物品。对于以上概念,有学者指出,我国《药品管理法》对药品概念界定的局限,既无法与“中国药典”药用辅料部分有效衔接,也置《药品管理法》自身于一种尴尬境地,应遵循药典精神将药用辅料解读为药品同类[12]891。在情感上,我们赞同该观点,因为药用辅料与活性成分相结合具有整体功效,两者对维护人类的生命健康具有等同重要性,故对两者应实行相同的安全管理标准,将药用辅料作为药品或准药品进行严格管理是大势所趋,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在此方面已作出了有益实践,并取得了巨大成效。尽管如此,但基于形式法治的立场,该观点是欠妥当的。不可否认,现行法律对药用辅料的性质定位是模糊的,但以上观点对药用辅料性质的理解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这与形式正义的立场是相背离的,故在法律框架之下药用辅料不应被认定为药品,药用空心胶囊也就不是药品。既然药用空心胶囊无法纳入以上物品的性质评价内,那么就应该回归它的上位概念即产品之中进行讨论。从物品的价值属性来看,药用空心胶囊实为胶囊生产者生产的一种产品,它符合产品的一切特征即被人们使用和消费,并能满足人们某种需求的东西,在性质上它可被界定为产品。就此而言,“毒胶囊”是以工业明胶替代食用明胶而制成的一种铬含量严重超标的空心胶囊,它是一种质量存在严重瑕疵的不合格产品,因此,“毒胶囊”在性质上应被认定为伪劣产品。
(二)“毒胶囊”剂之法律性质
将药物按剂量装入“毒胶囊”中而制成的固体制剂就是所谓的“毒胶囊”剂。“毒胶囊”剂以其对人体潜在的严重致害性使之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毒药”,那么,对这种“毒药”又该如何认识其法律性质呢?我们认为,且不论“毒胶囊”剂功效如何,它已然具备药品的外观形式特征,且指向特定的病患群体,所以其性质评价就应在药品范畴内展开。“毒胶囊”剂因其囊材质量瑕疵,成为一种问题药品,根据法律对问题药品的定性,显然,它的法律性质要在假药与劣药之间进行界定。
《药品管理法》第48条、第49条对假药、劣药以及按假、劣药论处的情形分别作了说明,两者共有14种参照标准,那么“毒胶囊”剂到底符合哪种判断标准呢?对此,有学者认为,在药物制剂成分合乎国家药品标准的前提下,“毒胶囊”剂性质的判断应以囊材的性质为主要标准,也就是说,此种情形下,不存在成分合格与否和成分含量达标与否的问题[12]894。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割裂事物统一性的认知思维,将部分脱离整体单独评价不利于事物性质的把握,而过多强调囊材性质很容易忽视药品的基础功能即药品疗效性,从而可能导致性质评价偏离药品本身。还有论者指出,“毒胶囊”剂符合《药品管理法》第49条第3款第4项之规定即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和容器未经批准的情形,这是因为胶囊外部的保护层所含有的铬元素超标,而且利用废旧的皮革下脚料生产胶囊的外部保护层无疑不为国家许可,故可以依此而认定“毒胶囊”剂为劣药[13]。前文已提及,药用空心胶囊是一种药用辅料,它在性质上不属于药品包装材料,故“毒胶囊”这种质量存在瑕疵的空心胶囊也就不是未经批准的可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所以认为“毒胶囊”剂为劣药的观点也是不成立的。此外,“毒胶囊”剂是否与《药品管理法》第49条第3款第5项之规定相符合也是需要明确的问题。《药品管理法》规定,擅自添加着色剂、防腐剂、香料、矫味剂及辅料的药品视为劣药,一般认为,擅自添加就是未经允许而私自添加的意思,其表述的重点在于超越权限而自作主张。对于生产“毒胶囊”剂的药品生产者来说,“毒胶囊”是一种从外购进的生产原料,行为主体只是在其物质基础上加工使用,并不是把它私自添加于制剂药品之中,所以,即使行为主体违反了有关质量检验义务,也不能说是“擅自添加”,而“毒胶囊”剂也就不符合关于劣药的这项规定。
基于以上分析,空心胶囊虽为药用辅料,但其与匹配药物相结合后,就成为胶囊剂药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药品疗效的整体属性所决定的,而囊材本身成分也因此应被视为胶囊剂药品中的所含成分。当“毒胶囊”装填药物制成“毒胶囊”剂时,胶囊中重金属含量超标也就意味着“毒胶囊”剂所含成分不符合药典规定即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①《药品管理法》第32条规定: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药品标准为国家药品标准。,由此可见,“毒胶囊”剂属于《药品管理法》第48条第1款第1项之规定情形即药品所含成分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分不符的,故在性质上应将其认定为假药。
三、行为定性之思路:关联行为之样态分析
(一)制售“毒胶囊”之行为
前文已将“毒胶囊”界定为“伪劣产品”,故对于胶囊生产者的制售“毒胶囊”之行为,就可以通过刑法第140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来进行评价。胶囊生产者是否取得有关胶囊的生产许可证,不影响该罪的成立,行为主体只要明知其生产的胶囊违反了国家的禁止规定,即在原材料使用上以工业明胶代替药用明胶,而仍然予以生产、销售,就具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就构成该罪。在客观方面,胶囊生产者制售“毒胶囊”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之行为符合该罪的行为要件。
以上结论是将制售“毒胶囊”行为作为单一事件来定性的,由于制售“毒胶囊”行为是“毒胶囊”事件链条中一环,所以,全面评价胶囊生产者的行为性质还须将制售行为置于整个事件中来考察。从行为发展阶段来看,制售“毒胶囊”是制售“毒胶囊”剂的上游行为,它是一种辅助供应行为,胶囊生产者向药品生产者提供“毒胶囊”的行为在本质上是共犯性质,所以当胶囊生产者知道或者推定知道他人生产、销售“毒胶囊”剂而向其提供“毒胶囊”,就可以以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共犯论处。以上定性思路符合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之规定,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而提供生产技术,或者提供原料、辅料、包装材料的,成立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共犯。
值得注意的是,制售“毒胶囊”之行为又往往与制售工业明胶之行为相关联,即一些不法厂商(单位或个人)利用废旧皮革熬制成工业明胶,并将其销售给胶囊生产者用以制售“毒胶囊”。就行为类型来说,这是一种提供有毒、有害产品原料的行为,由于在现行法律中并无关于提供有毒、有害产品原料行为的专门刑法规范,所以在立法缺失的情况下,同为提供有毒、有害产品原料的行为,就出现了非法经营罪以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不同的定性结论。
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在罪状表述方式上具有高度抽象性,不当的解释将导致非法经营罪在刑事司法中被扩张,例如司法解释将非法经营罪扩张至生产、销售某种有害产品的行为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用水中使用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饲料中添加盐酸克伦特罗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或者销售明知是添加有该类药品的饲料和动物饮用水,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225条第(4)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有学者指出:“非法经营罪由刑法典中的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买卖进出口许可证、批文,或至少是与此性质相当的行为。经过司法解释的扩张,再经过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而形成的判例,一步步扩展成为一个几乎没有限制的罪名。”[14]我们认为,在具有经营资格的前提下,该罪不宜再超出条款所列范围讨论其他经营行为类型,否则极易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违背形式正义;而用非法经营罪打击提供有毒、有害产品原料的行为,现有司法解释也仅限于非法生产、销售瘦肉精的行为,故以非法经营罪难以完全评价提供有毒、有害产品原料之行为。至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因行为对象不能将食品以外的产品包含其中,故也就不能选用此罪来定性提供有毒、有害产品原料之行为[15]。对该行为不宜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的分析同下文,在此不予赘述。那么,在罪刑法定框架内对此种行为该如何予以定性呢?
有学者认为:“在刑法分则仅仅对最终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规定了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借助共同犯罪的理论,将提供有毒、有害产品原料的行为作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共同犯罪处理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16]136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妥当的,以共同犯罪理论惩处提供有毒、有害产品原料之行为符合形式法治的精神,具有处罚的正当性。在“毒胶囊”事件中,提供有毒、有害产品原料行为,即不法厂商制售工业明胶之行为,是制售“毒胶囊”行为的上游行为,在双方主体具有犯意联系的基础上,它是帮助行为,故在制售“毒胶囊”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前提下,制售工业明胶之行为也应被定性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二)制售“毒胶囊”剂之行为
“毒胶囊”剂在法律性质上被界定为假药,故药品生产者制售“毒胶囊”剂之行为就可能触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在主观方面,该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即明知是生产或销售假药的行为而有意实施。有学者指出:“对于行为犯来说,行为人只要对行为的危险有认识,并且实施这一行为,就应当认为具有故意,这是一种行为故意;在行为故意的情况下,认识要素对于故意具有决定作用,而意欲则被认识所包裹,隐藏在其身后。”[2]434我们赞同该观点,此时的故意主要是通过认识因素来认定的,而意志因素并不是表现在对结果的支配而在于对行为的支配。在客观方面,该罪的实行行为是实施生产或销售假药的行为,现实危害结果的发生与否不影响该罪的成立。有学者认为:“行为人只要有生产、销售假药行为之一的,即构成犯罪,而无论生产、销售的方式和过程怎样,以及购买者是否实际使用以及使用的效果怎样。”[17]总之,对于制售“毒胶囊”剂的药品生产者而言,只要它明知其所加工使用的空心胶囊不符合国家标准而仍用于生产、销售“毒胶囊”剂的,即可认定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
“毒胶囊”剂一经流入市场必将危及公众的生命健康,极易酿成公共安全事故。那么,此种情况下是否可以认定行为主体触犯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抑或造成生产、销售假药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竞合呢?药品生产者是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关键在于认定制售“毒胶囊”剂之行为是否属于该罪行为要件中的“其他危险方法”。笔者认为该行为不能与放火、决水、爆炸等行为相提并论,是因为其本身不具备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直接性、迅速蔓延性与高度盖然性[18]33。而“在性质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等罪的兜底性罪名,在犯罪构成上,此罪具有开放的构成要件;在法条表述上,此罪具有‘其他’等概念表述的模糊性。”[16]13还有学者指出:“‘其他危险方法’的要件关注的是实行行为本身的危险,要求具有如放火、决水、爆炸等行为所具有的导致多数人重伤或死亡的内在危险性,它区别于结果意义上的具体危险,即后者是独立于实行行为之外的构成要件要素。”[16]31我们赞同此种观点,所谓危险方法的相当性仅指行为性质相当而不包括行为后果相当,不能由结果的严重性反推行为本身的危险性,如果以后果相当来评价危险方法,则危险方法的外延必将无限扩大,势必会造成构成要件之限定机能的丧失,这也是基于形式法治立场而得出的结论。就此而言,难以认为药品生产者制售“毒胶囊”剂之行为与放火、决水、爆炸等行为具有危险的相当性,两者在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上不具有同质性和等价性。故不能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评价制售“毒胶囊”剂之行为。
[1]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陈兴良.教义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刘风景.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法治意义[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18-23.
[4]邓子滨.中国实质刑法观批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67.
[5]于志刚.罪刑法定原则认识发展中的博弈[J].法学,2010(1):18.
[6]孙万怀.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量刑反制思维应摒弃[J].人民检察,2012(19).
[7]高艳东.从盗窃到侵占:许霆案的法理与规范分析[J].中外法学,2008(3):459.
[8]张明楷.许霆案的刑法学分析[J].中外法学,2009(1):40.
[9]姜涛.批判中求可能:对量刑反制定罪论的法理分析[J].政治与法律,2011(9):122.
[10]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51.
[11]薛瑞麟.关于犯罪对象的几个问题[J].中国法学,2007(5):127.
[12]叶慧娟.“问题胶囊”案的刑法定性研究[C].//赵秉志.全国刑法学术年会文集:刑法与宪法协调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
[13]张红昌.毒胶囊事件的刑法学分析[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2(6):37.
[14]徐松林.非法经营罪合理性质疑[J].现代法学,2003(6):92.
[15]高杭.论惩罚性赔偿在侵权领域中的设置[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206-208.
[16]劳东燕.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解释学研究[J].政治与法律,2013(3).
[17]于志刚,李怀胜.提供有毒、有害产品原料案件的定性思路[J].法学,2012(2).
[18]曲新久.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286.
Study on the Quality of Criminal Law of the“Poison Capsule”Event Correlation Behavior
PANG Xiao-feng,LIU Xiao-li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7,China)
The qualitative behavior of“Toxic capsule”event correlation analysis,first of all should establish the form of justice of a legally prescribed punishment for a specified position,to form a rational process of thinking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Clear“Toxic capsule”and“Toxic capsule”preparation of the legal nature,will be respectively defined as fake products and counterfeit drugs,this is the premise of accurate qualitative behavior.Under the current legal framework,combining the accomplice theory of criminal law,these should be the behavior of“Toxic capsule”,to produce the behavior of“Toxic capsule”preparation into the production,sales and shoddy produc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production,sales and counterfeit drugs crime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in the evaluation.
Manufacturing and Selling the Toxic Capsule;Manufacturing and Selling the Toxic Capsule;Principle of Legality
D914
A
1001-6201(2014)04-0079-06
[责任编辑:秦卫波]
2013-09-20
中国法学会2013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CLS(2013)C80)。
逄晓枫(1983-),男,山东青岛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晓莉(1963-),女,内蒙古通辽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