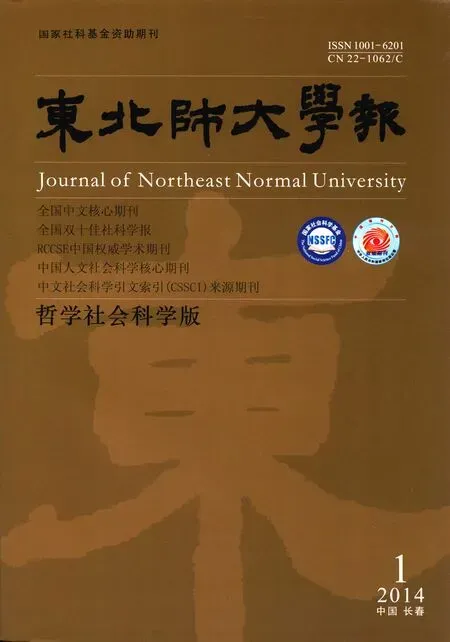论韩国现代主义文学旗手李箱对日本现代主义文学的受容
2014-03-22刘妍
刘 妍
(清华大学 外语系,北京 100084)
一、现代主义文学的越境
朝鲜半岛的文学和日本文学的关联,是东亚近现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本文以朝鲜殖民地时期的诗人兼小说家李箱(1910—1937,原名金海卿)为考察对象,探讨上世纪30年代朝鲜现代主义文学对日本现代主义文学的受容和差异问题。
韩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争议的作家就是李箱。被誉为“鬼才”的李箱出生于1910年,此时,日本正式开始对朝鲜进行殖民地统治。1930年他发表处女作小说《十二月十二日》(《朝鲜》2~10月连载),翌年7月起他在《朝鲜和建筑》上发表日语诗《乌瞰图》、《异常的可逆反应》和《三次角设计图》。1934年加入朝鲜现代主义文学的文学团体“九人会”,同年发表朝鲜语诗《乌瞰图》。但由于诗文过于晦涩而被批评为“神经异常者的戏言”,受到读者的强烈抗议,连载被迫中止。为了寻求一种“新天地”,他于1936年10月奔赴东京。翌年3月17日在他向往的东京去世,享年26岁零7个月。
今天“李箱文学奖”是韩国文坛三十多个文学奖中最权威的文学奖之一。虽然当今学界对李箱文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然而对其作品的具体分析依然没有充分展开,即便在韩国也未能够对李箱文学给予准确的定位。笔者认为解读李箱的文学有两个要点,其一是殖民地的近代化问题,其二是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关联。这种视点对东亚现代主义文学和日本文学的关联以及对东亚现代主义文学的横向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近年来,一些日本学者对李箱与日本现代主义文学的关联做出了分析。川村凑指出与安西冬卫、北川冬彦和春山行夫等现代主义诗人相比,李箱的诗缺乏一种明快感,如《乌瞰图》的诗第1号中就鲜明地表现了处于殖民地统治下的人们不安和恐惧的心情[1]。佐野正人最早关注李箱和横光利一的关联问题,他认为“与日本其他现代主义作家相比,李箱更加从本质上捕捉到横光《机械》的本质,并拓展了其可能性”[2]。此外,他在《1930年的东京?上海?京城》(《比较文学》1994,3)一文中从东亚文学的视点来考察李箱和横光文学的特性和意义,是一篇标志性的论文。辛大基从写作手法的角度分析了芥川龙之介、太宰治和伊藤整对李箱的影响,他认为《断发》、《终身记》、《翅膀》等作品中皆有芥川龙之介的影子[3]。
此外,一些韩国学者已经考察出了李箱阅读日文作品的来源。宋敏镐在《絶望?技巧???》中指出李箱经常阅读日本的现代主义杂志《诗和诗论》(1928年9月—1931年12月,全六册,厚生阁)以及其后的《文学》(1932年3月—1933年6月,全六册,厚生阁)等杂志。他的友人高银(1933年—)也提到李箱曾经热心地阅读过日本的综合杂志《改造》(1919—1955,改造社),并且希望能够有一天见到常在该杂志上发表作品的长谷川如是闲。除了长谷川以外,李箱在作品中常提到横光利一。在短篇小说《金裕贞》(《青色纸》1939年5月)中写道“朴泰远听到这个故事后说,‘这就像横光利一的机械嘛’”。横光利一的许多代表作品,如《机械》(1930年9月)、《上海》(1928—1931)皆发表在《改造》上。我们可以从中推测李箱是通过《改造》接触到横光利一的作品。另外,1931—1932年是日本介绍乔伊斯的繁盛时期,《诗和诗论》改编为《文学》后,几乎每一期都有关于《尤利西斯》和乔伊斯的介绍。由此可见,对于从小接受国民化“国语教育”的李箱来说,日语比英语更为接近母语,他是通过日语和日本现代主义文学学习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写作手法的。
二、李箱和横光利一两位现代主义旗手对“国语”的挑战
虽然李箱的创作生涯仅有7年,但是他发表的多篇朝鲜语诗和日语诗、小说以及随笔,开拓了朝鲜现代主义文学新的领地。不同于朝鲜近代诗的创始人崔南善(1890—1957)和韩龙云(1879—1944),李箱的诗歌更具有实验性。受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直接影响,他将许多现代主义文学的手法(例如立体派、表现主义等)融合在一起,使用汉字和片假名混用的文体,并且加入了许多数字、符号和科学用语。与朝鲜近代文学的始祖李光洙一样,当时许多作为殖民地的朝鲜作家都处于一种二重语言创作的状况,即先用日语创作,然后再翻译成朝鲜语,李箱也不例外。李箱最初用日语写作,此后才用朝鲜语创作诗和小说。
李箱积极吸收并仿拟横光利一、北川冬彦(1900—1990)和春山行夫(1902—1994)的写作手法,以重复的短句增强速度感,强调文字的“表意作用”,突出视觉性效果等创作手法。与此同时,打破韩语和日语里面要“分かち書き”(分写)的写作规则,去除句逗点,得到一种无限延续下去的旋律。这种写作手法与横光《机械》中通过不分段、不断句、无标点的句式来描写人物的方法极为相似。对照一下《乌瞰图》中的《颜》(1931年6月18日)和横光的《机械》(1930年9月)两部作品就会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他的日文诗可以说是完全不符合日语语法规范的,将无生命的“点”、“线”、“圆”作为主体,用平假名表示的地方用片假名表示,这种误谬的表记法遍布在他的诗歌和小说中,与横光所主张的“形式决定内容”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极为符合。
横光出生于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的1898年,他的幼年正是日本向近代产业化、军事主义国家转变期。这个时期也是由言文一致运动发起的从古代的文言体向新的口语体转变的时期。横光登上日本文坛的1923年前后正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盛行后口语体作为主流被完全确立下来的时期。他认为这种文体是由欧洲带入日本的文体,他提出要打破自然主义文学的局限性,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即“像诗一样写小说”,重视形式和文字的视觉性,强调文字本身具有的能量。新感觉派时期的横光用他自己的说法即“与国语的极其不安定的血战时代”。其主要作品就是反抗自明治时期以来被欧化的近代口语体写法,反对“像说话一样书写”(“話すやうに書く”),而是要“像书写一样写”(“書くやうに書く”)。虽然李箱和横光处于两种全然不同的历史环境,但两人对于打破旧文学的束缚,力图创立一种反映近代化社会的新文学表达形式的意图是一致的。
三、殖民地的“恋爱”问题
从1930年到1936年这一时期正是李箱从事文学活动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创作的《翅膀》、《童骸》、《终生记》被称为“爱情三部曲”。“恋爱”这个西方的概念是经由日本传入朝鲜的。在1920年代的朝鲜社会,封建思想还根深蒂固。作为近代精神的“恋爱”伴随着殖民地都市京城的近代化在1930年代开始为人们所认知,摩登女郎、摩登男士的自由恋爱成为新文化的代表之一。其描写了许多新时代男女的恋爱。李箱16篇小说作品中描写男女恋爱关系的一共有8篇,皆以都市中颓废的男女恋爱关系作为主题。作品中出现的女性以自传体的角度可以分为“锦红”、“贞姬”、“权纯玉”三个类别。从内容上可分锦红系列和贞姬系列。锦红系列主要描写妻子的通奸和其丈夫的悲伤与绝望。贞姬系列是以周旋在“我”与其他男性之间的新时代少女为主人公。这些小说的焦点是女性的贞操问题,通过恋爱来突出主人公的不安和苦恼。
《翅膀》是李箱1936年10月发表在《朝日》上的短篇小说,在当时受到了很高的评价,并使李箱在朝鲜文坛的地位最终确立。今天的韩国高中教科书中皆收录《翅膀》这篇小说,被誉为是“现代主义文学的杰作”。正如作为遗书所写的《终生记》所示,该时期李箱对现实深感绝望,时刻思考着自杀的问题。《翅膀》具有自传性特点,主人公“我”是作家自身的影射,以作者本人1936年和妓生锦江的同居生活为背景,描写了时刻思考自杀的“我”的虚幻、孤独的思想游戏。然而这种自杀仅仅是一种姿态,最终选择了“我依然设计着和女人生活”的恋爱游戏。“我”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每天无所事事,靠妻子莲心卖淫来维持生计。唯一的乐趣就是在房间“阴湿的被窝中研究各种发明、论文和诗”。但这只是“我”思维的幻觉,实际上妻子在隔壁的房间里接客,而“我”则在相邻的房间里睡觉或拿着妻子给予的钱外出游荡。
对照《翅膀》与横光的《眼に見えた虱》两部作品,妻子除了丈夫还和其他数名男性保持肉体关系的人物设定很相似。诚然,两者的场面设计和表现手法上具有类似性,但不可忽视的是在男主人公和妻子的关系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笔者认为虽然都是描写都市中颓废的男女和人格的分裂、疯狂,但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眼に見えた虱》与《爱卷》、《皮肤》属于一系列的作品,皆描写妻子的不贞和对此苦恼的丈夫。然而《眼に見えた虱》中“我”虽然自闭并且厌世,但却具有主动行为的能力。他时而“用钱来购买她的身体”、时而进行“观察妻子在隔壁接客的实验”、时而“在抽屉里放砒霜”并思考“到底是我吃还是她吃”的问题。相比较之下,《翅膀》的“我”是“依附在妻子身上生活”的,其存在是被动的、无生命的、被“剥制”的存在。妻子“像监禁一样对待我”,“将安眠药伪装成阿司匹林让我服用”。虽然不能排除这是“我”的被害妄想,但可以说这里的妻子影射着日本的殖民统治。李箱在小说中时常用“去势”、“剥制”来形容男性,这种男性往往是以失败者的形象出现。妻子这种行径造成“我”的无感情、无能力和无性格化。在《翅膀》的结尾处,“我”将夫妻的关系比喻成“宿命般两条腿不齐的瘸子”。“我”在“我”这条腿的去向问题上彷徨迷惘,最终登上当时朝鲜半岛最大的三越百货店屋顶上,在“人们的手脚长出了鸡一样的翅膀,各种玻璃、钢铁、大理石、纸币、墨水滚走”的幻觉中迎来了“最绚烂的正午”。最后,作者用“飞啊、飞啊、飞啊,只要再让我飞一次!”结束了小说,也使作品叙事达到了高潮。
飞翔这一动作和“飞啊、飞啊、飞啊”的呼喊声相呼应,突发性的自杀愿望促使“我”带着幻想中的翅膀飞翔,然后向下坠落。这里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众所周知,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张,对朝鲜的殖民统治也愈发严酷。1931年和1934年的KAPF(朝鲜普罗艺术同盟)的检举事件后,出版物受到了总督府严格的监控的言论统治。李箱从事文学活动的1930年到1937年也是日本向中国进行侵略战争的时期。在这种时局下,李箱采用极具象征性的语言,通过描写被阉割了的精神和虚幻性的生活,影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人们的恐惧、不安和绝望。
四、殖民地近代化的二重性
李箱和横光皆活跃于朝鲜和日本向近代化发展的进程中。横光既崇尚西方科技文明带来的都市文明和现代的科学技术,又渴望能够打破由此带来的人们精神上的迷失和内心的苦闷。这种二重性可以说是东亚的共性,而这一点也反映了李箱对日本殖民统治带来的“暴力性的近代化”的接纳和抵触的复杂心情。
《翅膀》的“我”最终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来到了最繁华的三越百货店,这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精神状态,可以看作是对日本带有强烈向往意识的李箱自己的心象表现。“去哪儿?我见到每一个人都豪言道去东京”(《逢别记》)。我们不能单纯从李箱作品中提及的“亡命”、“妄言”等只言片语中推断他的东京之行是逃避之旅。由于李箱所患肺结核的加重和受远渡日本的友人金起林的影响,这一时期李箱为了寻找文学的新起点奔赴东京的愿望愈加强烈,希望能够作为作家在东京的文坛上登场。但事与愿违,最初的计划并没有实现,在日本他未见到想见的日本作家,作品也未能够在日本文学杂志上刊登。正如横光在远赴欧洲后所感到的“失望”(《失望的巴黎》)一样,李箱到达东京后看到的是近代化的阴影和“幻想的破灭”。
我脑中描绘的“丸之内”大厦——通常的丸楼——至少比眼前的丸楼要大四倍般的壮大。是否到了纽约的百老汇我会有同样的幻灭呢。总之,这个都市有汽油的味道!是对东京的第一印象(《东京》)[4]270。
日本/日语带给李箱的不仅仅是一种创造文学作品的手段,同时也带给他一个想象的空间。李箱试图用日语来构筑机械的几何图形,用无机的、人工的语言来隐藏内心世界的写法构筑一种独自的言语空间。他从这种实验中得到的写作手法最终被融合在中、后期用朝鲜语创作的小说中。从李箱的作品来看,他的创作更接近于对日本语的一种挑战。在《乌瞰图》被迫中止发表后,李箱这样写道:“为什么说是发狂了呢?难道说我们还要安于比他们晚数十年的现状吗?”[4]342从中可以看出李箱对于朝鲜文学比他国落后了数十年的现状感到焦虑和不安。虽然韩国的一些学者认为李箱没有描写朝鲜的贫困现状,批判其文学“无国籍性”[5],但从他的诗和小说当中,我们依然可以捕捉到殖民地统治下的黑暗。李箱通过对以横光利一为代表的日本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通过数字、科学符号、几何图形等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具有高象征性的语言营造出不安的、恐怖的殖民地京城景象。
1936年横光在欧洲之行的归途中飞机到达平壤时写到:“这时的我已经没有旅行的感觉。如同回到日本内地的喜悦,我换上和服走在路上”(《欧洲纪行》)。对横光利一来说,京城不是一个异地,而是在日本政府所鼓吹的“内鲜一体”的口号下,把朝鲜看作为日本的“内地”。这种认识的差异、对京城的感受,居住在殖民地的李箱与身在“内地”的横光是截然不同的,恐怕也是横光难以捕捉得到的。
てふてふが一匹韃靼海峡を渡って行った(一只蝴蝶飞过鞑靼海峡)
这首代表着日本现代主义诗歌起点的安西冬卫(1898—1965)的诗《春》,正象征着李箱为寻求更大的飞跃,奔赴东京的悲剧性人生。以上针对李箱与横光的关联作了史料分析与讨论,但是有关李箱的诗歌与《诗与诗论》等现代主义诗歌的关联问题是一个尚未言及的重要课题,需要今后进行细致的调查和考证。
[1]川村湊.酔いどれ船の青春―もう一つの戦中·戦後[M].東京:講談社,1986(12):162-163.
[2]佐野正人.韓国モダニストの日本文学受容——李箱詩と横光利一をめぐって[J].第14回国际日本文学研究集会会议记录,1991:89-105.
[3]辛大基.李箱と日本モダニズム小説:伊藤整の初期小説との比較を中心に[J].千葉大学大学院社会文化科学研究,2004(2):67-75
[4]崔真硕.李箱作品集成[M].東京:作品社,2006(9).
[5]金玉.论韩国社会的多元文化价值观[J].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