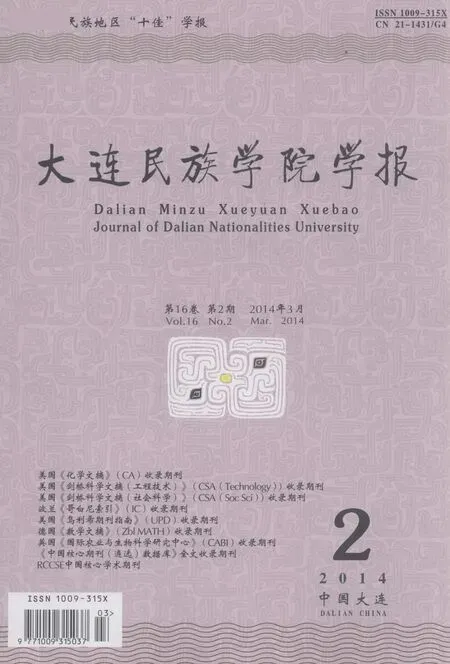草明作品中女性话语与主流话语关系的转换
2014-03-21王莉
王莉
(大连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辽宁大连116605)
草明作品中女性话语与主流话语关系的转换
王莉
(大连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辽宁大连116605)
以草明20世纪30年代的短篇小说和四部代表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草明作品中女性话语与主流话语的关系。认为草明的早期作品呈现出女性话语对主流话语的寻找,从进城的农村女儿的视角描写她们物质的贫穷和对生存出路的寻求;后期作品呈现出女性话语与主流话语的重合,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角塑造符合主流期待的社会主义新女性。两种话语关系的转换是时代潮流和草明个人选择的结果,尽管女性话语和个人视角的匮乏使草明的作品在新时期遇冷,但终生为工人阶级写作成就了草明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地位。
草明;女性话语;主流话语;转换
草明以“工人阶级的代言人”“终生为工人阶级写作”为读者和文学史所铭记。她的作品主流话语的特征明显,主要描写工人阶级如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工业岗位上锻造成社会主义新人,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新女性。不过,她作品中的主流话语并不是一出场就如此清晰,而是存在着一个由女性话语到主流话语的转换。
一、女性话语对主流话语的寻找
草明的早期作品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由农村进入城市谋生的女青年。从进城的农村女儿的视角写出了她们生活的困窘无望和精神的无路可走,更写出了她们对社会不公的追问和愤怒,挣扎、沉沦和寻求。使她们觉醒的,不是五四时期自由、独立的现代思想,而是生活的严酷、经济的衰败、社会的威逼和日常生活的无望。这些作品里大都有一个“我”,既是主人公,又是叙述人,是困窘生活的参与者,批判灰暗的社会,怀有改变的希望。草明所描写的理想城市女性和社会是对立的,批判的,带有理想主义的。《倾跌》展示了30年代进城谋生的农村女儿的窘境:广东的农村已经破产,农村女儿们正经历着丝厂关门,吃不上饭的艰难境地。她们迫不得已进入城市谋生,城市也已沦落为一片资本主义风习熏染下的色相市场,在这一巨大市场中,一切尊严、价格、价值都可以出卖[1]113。她们能做的工作只有廉价的保姆或者下等妓女。“我”做了保姆,给女主人支使得像风车一样乱转,回到住处累得像醉鬼一样一头睡倒,一个月才得五块钱。活泼的苏七和倔强的阿屈先后做了私娼。城市对于她们,最初是谋生的希望,在乡下饿鬼也不许人做,偷、抢也得在城市才有可能;几个月找不到工作,城市逼她们追问这个社会:为什么生活如此苦,活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的饭碗在东家手里?为什么我们愿意拿双手来劳动,却没有人给我们饭吃?纯朴勤劳的农村女儿在衰败的城市里只有出卖劳动力和色相才能生存。生存重压和社会不公的深切体验酝酿着社会革命的汹涌暗潮。即便读了书,也只有嫁为人妇,磨灭了对社会的愤怒,加入亲戚邻居姐妹们的麻将圈子。《进城日记》里的五姐就是如此。桂英、五姐、四嫂三个城市女性都厌弃自己的生活,为逃离消沉乏味的婚姻生活抗议、挣扎过,但最终投降了自己所诅咒的生活。四嫂主张一个女子不嫁人是幸福的,只有在每日招待客人时焕发光彩;女工桂英主张摈弃一切男人,坚决反对她母亲为她安排的婚事,最终还是嫁给了那个男人;女学生五姐猛烈地攻击各种社会病象,最终收敛起锋芒,与一个教员同居。一切都是无望的。小说结尾,“我”离开了这些投降的女性,奔向生命力蓬勃的女伴。
农村无法供养女性生存,城市也只容纳投降商品市场和婚姻生活的女性,然而这一切并不能破灭一个心怀希望和变革理想的女性。草明否定这一切贫穷、绝望、麻木、死气沉沉的社会现实,她怀着变革的理想和冷静的期望,向社会发出质问和不甘堕落的反抗。草明描写的女性与社会的对立更多是一种外部的对立,物质生活的困顿如失业、饥饿、赤贫、老板的剥削和政府的压迫所引发的朴素的质问和寻求出路的需要,保持着一个寻求变革的姿态。农村女儿们没有反抗封建家长的爱情梦想,农村生活的困窘和沉重使她们只想摆脱农村摆脱做妻子做母亲的重负,非常现实地不想“做母猪”,看到女雇主为丈夫彻夜不归吵闹而深感其愚蠢。进入城市的农村女儿与城市之间的紧张呈现为荐头、雇主、嫖客等奴役者与被奴役者之间的矛盾。磨灭城市女性的自我、呐喊与梦想的是男人、婚姻以及自我的懦弱、安逸,最终向生活投降。草明的早期作品表达了社会女性对生存、婚姻、生育的体验和观点,女性是受压迫的、沉沦的,也是抗争的、倔强的,保留了女性寻求改变的理想、希望,灰暗中有明朗,有一颗向往光明的心。1941年,作者自己也奔向延安。女性意识包含在社会问题的揭示之中,存在但并不强烈。
草明是个独立的人,也终生是党的女儿。正如戴锦华所说:罗淑、草明、白朗等女作家的性别意识显然被时代框架所同化或淡化了。这一点在草明、白朗这两位在党周围成长的女作家那里尤为触目,在这种环境中,性别意识或许根本就没有生长形成[1]139。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草明的创作加入了革命、抗战的背景。本就不强烈的女性意识进一步让位于客观的现实批判和积极的革命理性。此后草明的叙述视点与30年代的左翼社会思潮更加接近,从大众的革命的视点把女性的命运放在中国历史的变迁中加以关照和叙述,女性意识与主流意识趋向重合,将女性个体作为大众的一个成员来呈现,女性命运汇入革命的洪流。女性与社会的外部对立融入大众与剥削阶级的对立,其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衰败的经济与生存的矛盾、抗战与不抗战的矛盾,几乎不再有女性意识。第一人称的“进城女”叙述人“我”出现得越来越少,换成第三人称,只有《新嫁娘》是“我”叙述的,但主角已换成表妹李雅莲。不再讲述“进城女”的挣扎和困惑,而讲述作为大众一员的城市底层女性的极端贫苦和鲜明的“奔向”光明的姿态。农村女性奔向城市尚属自发,革命家属从国统区奔向解放区出现了罢工、解放区等革命因素(《绝地》)。这种投奔主要出于解决生存问题的需要,当农村和城市都无法供养底层女性时,解放区是她们唯一的出路了。
需要指出的是,30年代末草明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并没有完全与主流意识重合,仍然存在着,主要表现为女性遭遇的封建压迫。如《绝地》和《受辱者》。《绝地》里真嫂的精神境遇类似祥林嫂,因为克夫被周围的女人认为是灾星,让她花钱赎罪,她花了钱仍得不到接纳;工厂罢工后她的粥摊难以为继,几个和她相好的工人送来了救命钱,给她的孩子买吃的,这些女人却因此攻击她。《受辱者》里的女工梁阿开的遭遇类似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贞贞,但她没有贞贞那么淡然,她被日本人污辱后,自己觉得“这一辈子的羞辱,用尽桂花河的水也洗不干净”,她对别人说被掉进河里了,还被流氓敲诈。在女性意识与主流意识之中,草明在突出主流意识的同时,保留了一些女性意识。
二、女性话语与主流话语的重合
草明30年代作品中的女性作为大众的一员在“寻求”出路和光明。40-50年代,草明的代表作《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里的女性作为大众的一员在“建设”。从建设的角度写工业领域的女性,女性话语几乎完全与主流话语重合。以至于陈顺馨认为杨沫和草明的叙述视点接近男性[2]。郭冰茹曾指出:建国初十七年,包括“文革”阶段的文学书写始终给读者一个淡化性别的印象[3]。性别不是50年代叙事的焦点,不符合新政权对建设者的期许。作为一个在党周围成长起来的女作家,草明描写走出家庭、在工作岗位上实现价值的新女性有着必然性。与30年代的女性苦难者相比,女性建设者更加符合主流意识形态,更少女性意识。主要包括两种女性形象,一种是党的女儿,女干部,这类形象最符合建设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如《火车头》里的机车厂党委副书记方晓红,《乘风破浪》里的市委宣传部长邵云端。她们沉稳干练能力强,有女性的优雅也有坚定的立场和原则,是“建设”时期的完美女性。作为宣传部长的妻子邵云端以女性的隐忍包容,规劝主张技术路线而且出轨的丈夫宋紫峰回归家庭,意味着他改正错误、回归党的怀抱。一种是农村女性进城后成长起来的工业建设者,她们作为工业英雄的家属出现。《乘风破浪》里的小兰嫁给李少祥,使他拥有了完整的爱情和家庭;《“姑奶奶”》里的吕素珍跟随工人丈夫进工厂,自身接受了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改造,经过波折矛盾后成长为优秀的接线员,因而拥有了完满的家庭和丈夫的关爱。这两种女性都展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新女性的训导和期待,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以此实现自身价值。还有一种反面女性,她们最具女性特点,但却是作为反面形象被批判的。如《乘风破浪》里的女工程师汪丽斯,《神州儿女》里的姚巧凤。女工程师追求爱情、自由,做了宋紫峰的情人,姚巧凤爱打扮喜欢吸引异性,享受西式的现代化生活,但她是文革的帮凶,是一个荡妇和有胸无脑的形象。从正面、反面的女性形象可以看出,个人、女性的立场在草明的小说里是次要的,至此,她的女性话语完全隐没于主流叙事之中。
三、结语:两种话语关系转换的得失及影响
毋庸讳言,时代所限,草明的女性话语主流话语越走越近,最后几乎完全重合,只呈现出了主流意识形态希望看到的“风景”:工人阶级的乐观主义、集体主义和豪迈气概。她没有建立个人和性别的视角,也就没有呈现出属于她自己的“风景”。她深入工厂,深入工人群众,但她的作品似乎少了思考。与刘宾雁、王蒙比,她缺少了思想的批判性,与茹志鹃比,她缺少了女性的柔美。70年代末80年代初,《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发表后,《神州儿女》的思路还停留在表面的与四人帮斗争上,始终与主流政策交织在一起,认同并用她的作品解说政策。作品便如政策文件一样随着时代成为过往,少有味道。以至于现在的中文系研究生对草明的名字陌生而茫然[4]。这从一个侧面回答了魏巍发出的“谁来追踪草明”的问题[5]。
草明看到的工业“风景”成就了她。终生为工人阶级写作,是草明最值得称道之处。曾做过草明4年秘书的王世尧这样评价她:草明把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工人阶级[6]。2013年,作协主席铁凝在的草明百年诞辰上的讲话中说:“草明是新中国工业文学的拓荒者和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她的名字已经与中国现当代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高度评价了草明的创作:“回望草明的一生,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她的足迹一直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建设的进程叠合在一起,她的笔端流淌出的真诚而明亮的文字,也总是和时代的潮音、人民的心声尤其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思想情感交响、共鸣。”[7]
[1]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郭冰茹.性别的消隐与呈现:关于1950年代女性写作的一种考察[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5):111-118.
[4]刘朝兰.《世纪风云中的跋涉》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5]魏巍.谁来追踪草明[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4): 53-56.
[6]王世尧.草明与一机床工人作家群[N].光明日报,2013-05-17.
[7]铁凝.在草明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4):54-55.
Conversion of Female Discourse and Mainstream Discourse Relations in Cao Ming’sWorks
WANG Li
(Editorial Office,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Dalian Liaoning 116605,China)
Taking Cao Ming’s short stories and four representative workswritten in the 1930's as research objects,the paper probe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o Ming's female discourse and mainstream discourse.Her early works show the pursuit of female discourse for themainstream discourse,depicting the desire of the impoverished rural female in towns for survival from their perspectives.Her later works reveal the coincidence of female discourse with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modeling the socialistnew female coming up to the expectation of the society from the angle ofmainstream ideology.The conversion of the two kinds of discourse relations is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nd the personal choice of Cao Ming.In the new period her works were unnoticed because of the lack of female discourse and personal perspective,but her lifelongwriting for the working class has established her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Cao Ming;female discourse;discourse;conversion
I206.7
A
10.13744/j.cnki.cn21-1431/g4.2014.02.034
1009-315X(2014)02-0222-03
2013-12-12;最后
2014-01-10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3DZW019);辽宁经济社会发展课题与批评研究(2014lslktw)。
王莉(1975-),女,蒙古族,辽宁北票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研究。
(责任编辑 王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