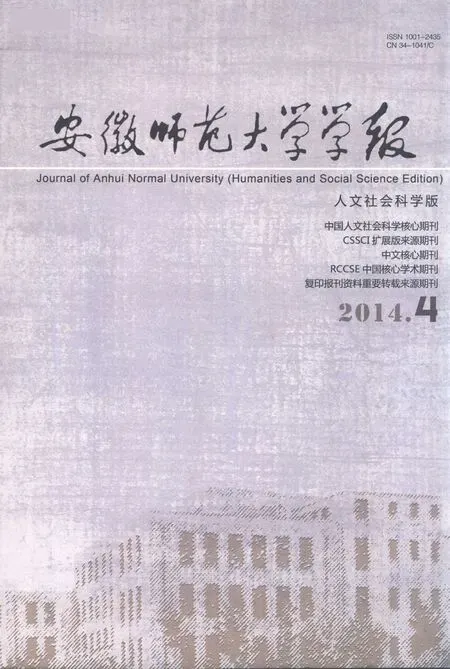郑天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2014-03-21段晓亮
段晓亮
(1.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300071;2.石家庄铁道大学 思政部,石家庄050043)
郑天挺 (1899-1981)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以明清史研究享誉史坛,于边疆史地学、隋唐史、元史以及音韵、校勘学等领域也造诣精深,是新历史考证学①“新历史考证学”,学术界已多有论述,张越认为:“新历史考证学既得益于传统考证学所打下的坚实基础,又受到了五四时期特定的时代条件和学术环境的深刻影响。对西方学理的借鉴,对史学 ‘求真’的重视,对 ‘科学’的历史学的追求,都成为历史考证学的内涵,也是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形成的主要原因。”(张越 《五四前后新历史考证学兴起原因初探》,《人文杂志》2003年第6期)相关论述还有瞿林东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历史教学》2000年第3、5期;侯云灏 《20世纪前半期的新历史考证学及其历史地位》,《求是学刊》2001年第6期;陈其泰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考证学的新境界》,《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等。陈其泰首次从理论上探讨了1949年以后新历史考证学和唯物史观之间的关联,考察了谭其骧、唐长孺等将实证方法和唯物史观相结合在学术上达到的新境界,令笔者深受启发。的重要代表人物。学术界对于郑天挺的研究,前期以其弟子的回忆与追思为主,如冯尔康、郑克晟编 《郑天挺学记》,三联书店1991年版;《郑天挺诞辰百年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0年版;封越健、孙卫国编 《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郑天挺诞辰110周年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等。近年来在整理郑天挺学术卡片之同时,也有几篇专题论文问世①参见王晓欣 《郑天挺教授的元史教学与思考》(《郑天挺元史讲义》,中华书局2009年版);王力平 《传宋贤之薪火,得乾嘉之余绪——郑天挺先生隋唐五代史教学卡片整理后记》(《郑天挺隋唐五代史讲义》,中华书局2011年版);常建华 《郑天挺先生关于清代军机处的研究——读郑天挺 〈清史讲义〉7〈军机大臣〉》(《郑天挺诞辰110周年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孙卫国 《郑天挺先生与20世纪的明史研究》(《中国文化》2012年第1期)。,对进一步梳理郑天挺学术成就,颇具启发。郑天挺治学原承继乾嘉考据学风,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掀起了一股新风。在这个新时代,学者如何因应,作过哪些努力,学术上有何转变②孙卫国在 《历史主义对 “史学革命 “的一次反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一文中比较详细地梳理了郑天挺与翦伯赞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编修历史教科书一事,初步涉及了这个问题。,是认识郑天挺一生学术业绩的重要问题。本文拟就郑天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史学研究的成就和特点做粗略探讨,进而对这代史家的某些共同特征略加评述,以就教于前辈和方家。
一、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中国史学孕育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由边缘走向中心,史学研究的整体风格也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由贵古贱今转向注重近代史研究[1]。郑天挺早年深受乾嘉学风和章太炎、黄侃、刘师培的影响[2]379-380,五四以后又经新学风熏陶,具备深厚的古文根底和扎实的史学训练,尤精于史料的搜集、鉴别与考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便以边疆史地学和明清史研究享誉史坛,被视为孟森的传人③参见孙卫国 《郑天挺先生与20世纪的明史研究》,《中国文化》2012年第1期,第147页;王永兴 《忠以尽己,恕以及人——怀念恩师郑天挺先生》,《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5页。和中国明清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是新历史考证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49年以后,伴随着政治和学术环境剧烈变迁,新历史考证派阵营里,除陈寅恪等极个别学者仍延续着传统治学路径外,以郑天挺为代表的多数史家,都面临如何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型的问题④王学典在 《近50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66页)一文中将这类以传统路数治学的学者统称为史料派或考订派,并将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转变归纳为三种类型的姿态:幡然醒悟型、遗世独立型和艰难改造型。事实上,即便是王所称幡然醒悟型的学者,其转型之路也并不平坦,郑即属于这类学者的代表。。
北平解放以后,通过土地改革和思想改造运动,郑天挺深受鼓舞和感召,开始学习并尝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历史。自1949年到1960年代,郑天挺研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留下很多读书卡片。经详细梳理,我们了解到郑天挺阅读的理论著作主要有《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等60余部论著。概括而言,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最早阅读的经典著作有毛泽东的 《论人民民主专政》、列宁的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斯大林的 《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以及恩格斯的 《德国农民战争》,特别是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 《毛泽东选集》反复阅读,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学习笔记。郑天挺曾拟定学习目标,自1958-1962年五年内精读 《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和 《列宁文选》[3],到1967年学完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资本论》和《列宁文选》等经典著作[4]。
二是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培养并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信仰。恩格斯的 《费尔巴哈与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 《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以及前苏联学者依·孔恩的 《历史科学的特性与任务》、葛烈柯夫的 《斯大林和历史科学》、康士坦丁诺夫的 《历史唯物主义》、亚历山大罗夫的《辩证唯物主义》等是郑天挺学习的重点。此外,他还阅读了不少 《史学译丛》《学习译丛》以及《历史问题译丛》等期刊翻译、转载前苏联学者的文章。
三是将阅读经典著作与自己的教学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将理论运用于研究与教学中。20世纪50年代初,郑天挺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曾开设《马列主义史学名著选读》以及 《社会发展史》等课程,他非常关注沙发诺夫的 《中国社会发展史》、沈志远的 《社会形态发展史》、解放社版的《社会发展简史》等以唯物史观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著作。此外,将很大精力投入到学习《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并将重要论点摘录到卡片中。在他的一张阅读卡片的右下角便曾注明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第四次读记”,可见从1949年到1959年,他多次阅读过这本书。
四是学习态度非常虔诚。为了钻研理论,他不仅坚持上南开大学马列主义夜大学,还经常要求历史系师生多读马克思主义史学专家的论著,并邀请翦伯赞、吴晗、白寿彝等唯物史观派学者来南开讲学[2]108。文革结束后,学术环境大为宽松,不少人出于对 “以论代史”极左学风的反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颇有微词,郑天挺提出:“历史学之所以被称为历史科学,就是因为历史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历史研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探求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导人们自觉地创造历史,建设新世界。”①《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的几位专家教授认为历史研究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光明日报》1981年3月18日。在听到马克思主义灵不灵的疑问后,他表示马列主义比其他主义要高明的多,在课堂上也反复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重要意义[2]144。可见,与陈垣、徐中舒、唐长孺等许多由旧时代过来的老先生们一样,郑天挺深受时代感召,以虔诚的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那种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单纯看成外在环境过于严酷所致的看法[5],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新成就
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实证研究相结合,郑天挺开创了其晚年学术新境界。具体来讲,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治史的新成就包括:
(一)以社会形态理论分析元初和清初社会性质
郑天挺曾深入探讨元初的社会性质。前苏联学者乌拉吉米佐夫认为,成吉思汗初期蒙古已经由氏族社会进入游牧封建制社会,但这种说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模式,在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引起争议。日本学者青木富太郎认为当时蒙古社会处于氏族制末期;秋泽修二则认为元代是奴隶制的复活。中国学者吴泽、邓初民、吕振羽、范文澜等也提出由氏族制飞跃到封建制、半奴隶制社会等不同观点。郑天挺认为:“蒙古族原为原始公社制之游牧民族,依血缘关系组成之氏族社会,由女系走入男系。在铁木真父祖时代,早已有私有财产,是已入氏族社会末期。入中国而后,适应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一跃而进入封建制社会阶段。”[6]100两年后,他进一步确认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社会 “以游牧封建为近实”,理由主要有:蒙古人对成吉思汗有人格的依附性,成吉思汗的万户、千户制度正是封建制的阶梯制,成吉思汗用政治力量统治部属,蒙古部族均须当兵,等[6]102-103。尽管他并没有深入展开论述,但对蒙古早期社会性质的探讨,推动了蒙古社会发展阶段的讨论走向深入,到20世纪60年代国内史学界在激烈的争论后,多数观点近似于 “游牧封建说”。
满族入关前的社会形态也是当时学术界争论的热点,不少学者主张满族没经历过奴隶社会,直接飞跃到封建社会②参见莫东寅 《满洲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尚钺 《清代前期中国社会之停滞、变化和发展》,《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6期;张维华 《满族未统治中国前的社会形态》,《文史哲》1954年第10期。;也有学者认为满族经历过奴隶社会,但对满族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看法有分歧,对满族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发展的时代特点上见解也不同③赵展和杨孟雄认为努尔哈赤兼并各部落建立的是奴隶制国家,不是封建国家;傅乐焕也认为努尔哈赤兴起时满族处于奴隶社会,只是在实行 “计丁授田”以后才开始向封建社会转化。参见 《辽宁举行满族史学术研讨会》,《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郑天挺1962年在 《历史研究》发表 《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一文,认为努尔哈赤在19岁时和父母分居,得到些许 “家私”,“家私”在满语里解释为 “阿哈·乌勒哈”,即奴隶和家畜的意思,说明努尔哈赤出身于没落奴隶主家庭;又据 《李朝实录》记载证明奴隶在建州可自由买卖,随意处置。郑天挺认为满族的确经历过奴隶制,1616年满族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但仍处于封建制初期,其封建化进程是逐步深化和上升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学界广泛重视。文革结束后,郑天挺又撰写 《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于1979年在 《南开学报》发表。该文利用最新考古成果和 《满文老档》等新材料,重新论证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属于封建制。文章将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融入到具体史料考证当中,其观点也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二)归纳明清时期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位和特点
郑天挺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制度面临严重的危机,“但还没到行将瓦解的程度,还不可能使中国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在1840年以前,中国的 “资本主义仅仅是在孕育之中,还没有诞生,更说不上取代封建制度”,这个时期不能叫做封建社会末期,因为 “晚期表示该时代的社会制度的衰败,即已开始逐步走向崩溃,但在某些方面还有一定发展余地;而末期则揭示那种制度灭亡和被新制度代替的过程”,所以中国1840年以前的明清时期是封建社会的晚期或者后期,而不是末期。郑天挺还总结出明清时期的七个特点:中国历史上较长的统一时期;中国封建经济最发达的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阶级矛盾的尖锐;封建依附关系的变化;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时期;抗拒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时期[7]13-17。1962年郑天挺到中央党校讲述清史,讲稿整理后命名 《清史简述》,由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全书勾勒出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历史发展脉络,总结了这一时期的特点和重大事件,很多独创性的见解使人深受启发,比如他高度评价了摊丁入亩和取消人口税的重要历史意义;恰当地分析了这一时期是 “满族封建社会的上升期”和 “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时期”,公正地评价了清代的历史地位。这是郑天挺数十年研治清史的成果,也是其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晶,被誉为 “建国以来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概述有清一代历史的专著”[2]532、348,对清史研究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三)实事求是地研究农民战争问题
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问题是当时史学界研究的重点,一些学者基于同情农民的政治立场,对农民战争片面歌颂的多,实事求是研究的少。郑天挺在1949年之前讲授明清史时便主张客观看待农民战争,他认为明末农民战争 “起于经济压迫,我人不应以其未成功而不悯怜其动机;同时不应因其动机可悯而宽容其 ‘纪律之纹乱与政治知识之幼稚’”①郑天挺 《明清史讲义卡片》(未刊)。“对于明清史应具的认识”,这部分明清史讲义卡片,是郑天挺数十年讲授明清史所作教学卡片,凝聚着其明清史研究独到的心得和创见,非常感谢郑天挺哲嗣郑克晟的支持,使笔者有幸见到 《郑天挺明清史讲义卡片》和 《郑天挺杂存》(未刊)等珍贵材料。目前,《郑天挺明史讲义》以及 《郑天挺清史讲义》均被中华书局纳入出版计划。。1949年以后郑天挺主持整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和 《宋景诗起义史料》,并发表 《宋景诗起义文献初探》《农民起义和秘密宗教的关系》[2]《红巾军起义的历史背景——元末社会主要矛盾的研究》《明末农民起义史中的两个问题》《关于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几个问题》[7]等文章,仍延续着客观研究农民战争的理念,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其理论深度和学术视野均大为开阔。马克思说过宗教色彩是一切东方运动的特点,有学者据此以为中国的农民起义多以宗教为掩护。郑天挺认为尽管农民起义经常以民间宗教迷信为纽带,这些宗教教义个别方面确实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因此在民间广为流行,但秘密宗教与农民起义并非一开始就结合在一起,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农民革命的工具。农民起义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人民的智慧,并不是宗教教义。当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朱元璋为农民起义出身,后来背叛了农民起义。郑天挺认为:“现在人们研究朱元璋,往往急于找他何时背叛农民革命。其实,这等于封了门,已经否定了他,就很难正确评价他的各项政策了。这样的研究方法,无异于作茧自缚,不利于研究的深入。”[7]78
郑天挺认为朱元璋完成民族革命,结束了北方自唐代天宝年间以来的割据和纷争,部分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历史功绩不容抹杀。朱元璋参加了农民革命,后来脱离农民做皇帝是历史局限,但不能说朱元璋背叛了农民革命,因为农民革命的要求是改朝换代、反对暴君拥护好皇帝的,朱元璋做皇帝是自然的事[2]312。在谈及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研究农民战争的区别时,郑天挺坦然表示:“我们认为是起义的,他认为是流寇、叛逆。观点上确是截然不同,内容倒没有什么。”[2]373可见,郑天挺并没有因政治立场改变其客观实证的研究态度,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立足于扎实的资料和具体的时代环境,所以他的见解更有说服力。
(四)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
早在1956年,郑天挺在 《关于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史料处理的初步意见》提出自己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看法。他以制墨业和官僚资本从唐代到清代的发展状况为例,认为应详细归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萌芽在不同时期的具体特点。他还提出要考虑不同地域、不同行业具体情况,搜集更多的史料,比较研究,才能了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7]237-247。 《鸦片战争前清代社会的自然经济》分析了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特点,认为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受到严重摧残和阻碍[7]224-229。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方一样,在历史上有资本主义萌芽,但对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却看法不同,很多人将徐一夔 《始丰稿》中 《织工对》所反映的情况,当作明初资本主义萌芽的证明。郑天挺1958年在 《历史研究》发表 《关于徐一夔 〈织工对〉》一文,根据《始丰稿》编排体例,以及 《织工对》“日佣为钱为二百缗”一语中 “缗”为元末一千钱的通用说法,认定 《织工对》为徐一夔在元末所写。他还从织工数目比例判断 《织工对》反映的是丝织业,不是棉织业状况。他并未生搬结论,而是以精密的考证方法澄清了一段重要事实,因此受到学界普遍称赞,被誉为 “将旧国学考证辨伪再赋予生机”的典范[2]360。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特色
郑天挺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历史,但他丝毫不轻视尊重史料、言必有据的治史传统,每篇著作都有扎实的考证根基和独到的见解,有深远的价值。具体来讲其晚年史学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特色:
(一)科学理性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
郑天挺真诚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始终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看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1962年他在作读书报告时说:“没有详细资料,就无从分析,没有正确理论就无法分析;即不能以理论代替历史,也不能使历史脱离理论。珠花是用珠子贯穿的,没有红线穿不成。”①郑天挺 《怎样读历史书》,1962年9月15日在中央宣传部报告,载 《郑天挺杂存》(未刊)。《郑天挺杂存》乃是郑天挺所作读书笔记和学术讲话的草稿,尚未整理发表。他反思以往治学经验时也说:“马克思主义也要占有全面史料,但光占有全面史料不行,还要有理论。”[2]280但是在学术泛政治化年代,到处弥漫着拔高理论,忽视史实的风气。郑天挺对这种风气相当警惕,经常告诫学生 “不要抛开事实来迁就理论,也不要用事实套理论,更不要引用自己还不明白的理论”②郑天挺 《团历史系支部学习报告》,1956年11月16日,载 《郑天挺杂存》(未刊)。“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是企求指出 ‘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③郑天挺此为郑天挺学习列宁著作所作札记,引自列宁 《什么是 “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26页),载 《郑天挺杂存》(未刊)。“学习理论应避免乱贴标签,断章取义”④郑天挺 《怎样学习历史》,1961年12月18日,载 《郑天挺杂存》(未刊)。“以理论代替事实……就成公式化”⑤郑天挺 《百家争鸣与历史研究》,1957年5月17日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讲座,载 《郑天挺杂存》(未刊)。等。
郑天挺的这种认识并未因为政治环境变化而改变。文革结束后,一股重史轻论、提倡 “回到乾嘉去”的史学思潮潜滋暗长[8]。郑天挺对此深不以为然,呼吁史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他说:“我们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学习它的基本原理,学习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去记诵个别结论或只言片语。”[9]坚持从学术角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郑天挺1949年以后史学研究最显著的特点。
(二)注重科学理论指导和扎实严谨的实证研究相结合
郑天挺注重科学理论指导和实证研究相结合。他曾说:“历史即是具体的科学,它当然首先就跟具体材料,跟具体事实有关。一定的历史事实,一定的经验材料就是历史的基础。”⑥载 《郑天挺杂存》(未刊)。郑天挺很喜欢毛泽东的两句名言:“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2]3241950 年 他 主 持 整 理 《明 清 史 资 料 丛书》,出版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 《太平天国史料》和 《宋景诗起义史料》等数种,1954年他开设史料学课程,探索和讲授马克思主义关于史料方面的知识。
郑天挺反复强调历史科学的具体性,认为没有具体史料也就没有史实,没有史实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2]435。1961年,为解决 “大跃进”以来教研秩序混乱局面,中央启动高校教材编写工作。郑天挺任历史教材编写组副组长,并具体负责编选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和 《中国史学名著选》,在编选意见中,他提出 “系统地选择比较完整 (具有首尾)的原始资料”“尽量多选时代较早的文献,不用转手资料”“资料只许删节不许改动”[7]505等要求,以实际行动抵制了 “以论代史”的思潮[10]。
郑天挺的论著也很好地体现了理论和史料的统一,《关于徐一夔的 〈织工对〉》就是用百余条史料澄清了一段重要史实,解决了理论争论中的关键性问题,其他理论性较强的文章如 《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和 《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等都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说服力很强。对于曹操评价问题、清官问题等政治色彩浓厚的热点问题,郑天挺既没有刻意回避,也没有卷入政治纷争,而是以严谨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正因为他具备实证史学根基和真诚的学术良知,所以对学术泛政治化的倾向保持相当的警觉,非常重视从深层次理解和把握经典著作的科学内涵,时刻注意避免陷入空谈理论的泥潭。郑天挺立足于扎实的史料批判,以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和观点分析问题,而不顾及具体的 “政治是非”,在当时的环境下尤为可贵。
(三)从较长历史时段和深层次把握时代特征
郑天挺在解放前治史风格以 “探微”见长,也不乏 “通识”眼光。1949年以后,郑天挺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更注意从较长历史时段和更深层次,探求历史规律和时代特征。20世纪60年代初,郑天挺将明清史放在全部封建社会发展史上考察,精辟地提出明清时期是封建社会的晚期或后期,而不是末期的观点[7]12。冯尔康总结郑天挺明清史研究四大创造性贡献第一点即是 “对明清时代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地位提出精辟见解”[2]293。常建华也认为这是郑天挺“着眼重大问题”“重视从总体上把握历史的时代特征”[2]352的表现。《清史简述》高度概括了清代从入关到鸦片战争前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基本状况,将鸦片战争前清代历史特点精确地归纳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而不是末期;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封建经济发展期;满族封建社会的上升期;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期;抗拒殖民主义侵略进行斗争的时期;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农民战争后的一个朝代六个方面,也体现了他宏通的学术视野和从深层次把握时代特征的眼光,这些新成就和新认识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光芒,是郑天挺晚年学术境界的重要升华。这种治学路径对其学生陈生玺和哲嗣郑克晟均有深刻影响,陈生玺 《明清易代史独见》对明末清初重大问题提出很多新见解,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郑克晟 《明代政争探源》从元末到清初三百多年历史进程中,考察明代政治斗争的根源,被誉为 “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运用于传统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一种富于建设性的尝试”并 “获得某种文化层面上的体验”[11],得到学界广泛好评。
四、余 论
新历史考证学和唯物史观是影响中国现代史学最大的两股思潮,两者均以 “科学史学”相标榜,但治学路径有明显差异,前者注重科学实证和史料批判,后者强调对历史作科学的解释。1949年以后,新历史考证学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开始与唯物史观相结合,开创了新历史考据学发展的新阶段。很多以考据见长的学者,纷纷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型。
1949年以后,陈垣治学经历与郑天挺相似。首先,他们都由衷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以唯物史观考察历史,突出史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其次,两人都担任过学术和政协等机构的领导职务,陈垣一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后出任中国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历任北京市政协常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郑天挺也历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史学系主任,后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又担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尽管由于社会活动多,挤占了学术研究时间,但他们均坚守学术良知、无私奉献社会、严格砥砺后学,学术人品几无可挑剔。再次,陈垣和郑天挺均参与和主持了由国家组织的古籍整理和校订工作,在治学上延续了尊重史料、实事求是的实证传统。陈垣曾主持编辑 《洋务运动》和 《辛亥革命》史料,校订 《册府元龟》,并主持中国史学会筹委会组织的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 《旧五代史》和 《新五代史》两部分的编印工作。郑天挺亦曾主持整理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太平天国史料》和 《宋景诗起义史料》,主编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和 《史学名著选》,并承担 《明史》点校工作。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备受史学界关注的历史分期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热点问题,陈垣所撰学术论文几乎无一涉及[12]。与陈垣不同,郑天挺对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多有论述,但并没有顾及所谓政治是非,仍然将准确理解史料,追求历史真相作为最高标准,对抵制极左思潮蔓延起到极大作用。除陈垣和郑天挺以外,岑仲勉作为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其晚年接受唯物史观后,视野更加开阔,在隋唐史、黄河变迁史以及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上取得重要成就[13]。唐长孺、王仲荦等在接受唯物史观以后,治学方法和路径也发生巨大改变,既延续了精于考证的传统,也非常注重从社会经济形态角度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土地制度、赋役制度、部门经济、整体经济以及依附关系等重大论题均有突破性进展”[14]。
综上所述,郑天挺作为新历史考证学的重要代表,其晚年的史学研究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普遍原则和方法,也延续了优良的实证传统。对比新历史考证派学者在1949年以后的治学历程,既有共同特征也有各自鲜明的特点。探讨新历史考证派学者在1949年以后治学经历和特点,有助于从学术史角度梳理自清末以来中国传统考据学发展演变整体脉络,也有利于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1] 郭沫若.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摘要)[N].光明日报,1951-07-29.
[2] 封越健,孙卫国.郑天挺先生学行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 郑天挺.落后一步就有落后一万步的危险[N].人民南开,1958-03-14.
[4] 诸庆清.修订红专规划,登上跃进坦途[N].人民南开,1960-01-20.
[5] 谢泳.当年大学教授如何看待胡风事件[J].杂文选刊,2010,(7下):46.
[6] 郑天挺.郑天挺元史讲义[M].王晓欣等,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
[7] 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M].北京:中华书局,2002.
[8] 王学典.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118.
[9] 郑天挺.怎样学习历史[J].历史教学,1981,(2):5.
[10] 孙卫国.历史主义对“史学革命”的一次反拨[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11] 刘志伟,陈春声.揭示传统中国政治斗争的经济和文化内涵——读《明代政争探源》[J].广东社会科学,1992,(2):136、121.
[12] 乔治忠,钟学艳.坚守求真理念致力新中国史学整体建设——陈垣1949年之后的学术建树[J].学术与探索,2011,(2):260.
[13] 陈峰.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密切关联——以岑仲勉晚年的史学成就为中心[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84-89.
[14] 曹文柱,李传军.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J].历史研究,2002,(5):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