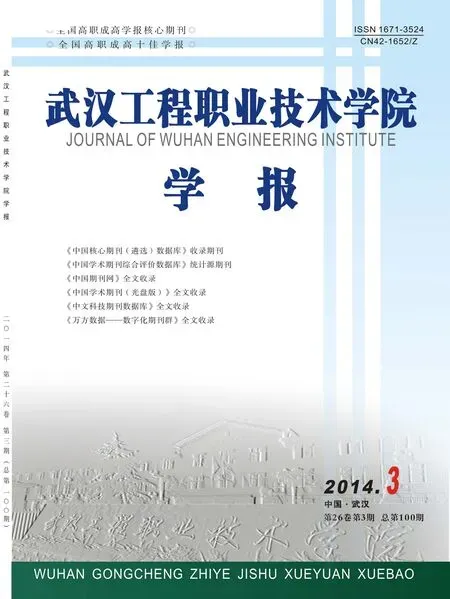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丑
2014-03-21区翰子
区翰子 李 佳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510275)
美丑之分并不是从人类诞生之初就出现明确清晰的区分,而是随着人类实践活动而形成。从美丑之分出现在人类文明中起, “审丑”经历了比 “审美”曲折得多的发展历程,美学史上关于丑的理论探讨也远不及美那样深刻。柯汉琳认为,“苏格拉底是西方最早谈论丑并且试图给丑作出理论规定的人”[1],也就是说,从苏格拉底开始人们有了审丑的朦胧意识。本文将进行一次浅尝,通过对古典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三人的“丑”观进行分析,一窥审丑在最初时期的状况。
1 苏格拉底与“丑”
虽然不乏如美杜莎这类丑陋的怪物形象,在古希腊,关注美是主流,对外在形体美的推崇更是达到了顶峰。在这么一个极其崇尚外在美的世界里,形貌丑陋的苏格拉底作为公众人物,必定要为自己的丑争取合法地位。他首先提出“有用即美”的审美观点。在《回忆苏格拉底》中,阿里斯提普斯问苏格拉底,同一事物是不是既美而又丑,苏格拉底回答道:
的确,我是这么说的——既好而又不好。因为一桩东西对饥饿来说是好的,对热病来说可能就不好,对赛跑来说是美的东西对摔跤来说,往往可能就是丑的,因为一切事物,对它们所适合的东西来说,都是既美而又好的,而对于它们所不适合的东西,则是既丑而又不好[2]。
由此可见,他认为,事物本身无所谓美丑,美与丑是相对的,判断标准在于功用。因此,粪筐可以是美的,而金盾牌可能是丑的,关键在对于其各自的用处来说,哪个做得更好。
苏格拉底忠告克雷同:“一个雕塑家就应该通过形式把内心的活动表现出来了。”[2]也就是说,要表现出人的内在美,或精神美。而这种“精神美”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就是“有用即美”在人身上的体现。年迈的苏格拉底认为,“如果我活得更长久一些,很可能我就不得不忍受年老的痛苦,记忆力越来越衰退,以致那些我曾经比别人强的事情,反倒变得不如别人了。”[2]也就是说,苏格拉底一旦失去了过去引以为傲的智慧,没有用处了,只剩下丑陋的皮囊,毫无疑问会被世人所嫌弃。
然而,苏格拉底的“有用即美,无用即丑”说似乎站不住脚。他在色诺芬的《会饮》中在与布里托布鲁的比美中完败,就是对此观点的最好反驳。“有用”这一特征也许能让人对某事物增添好感,但美就是美,丑就是丑,显而易见。而这个观点的价值在于苏格拉底已经使得美丑之审从具体事物上升到抽象层面。
2 柏拉图与“丑”
除了对苏格拉底的观点有所继承外,柏拉图对美学也有自己的另外一套见解。
首先,柏拉图认为美“本质在于秩序、尺寸、比例匀称和和谐”,并说“畸形不就是那总是丑的不合比例性的呈现吗?”[3]也就是说,比例失调、不和谐是引起丑的原因。
其次,在柏拉图看来,理念世界才是绝对的,真实的,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影子和摹本。在《巴门尼德》中,巴门尼德问苏格拉底,人们一提到就会引起一阵莞尔的那些事物,即头发、烂泥、垃圾,或者一切讨厌、琐屑的事物,是不是各自有其“理念”时,苏格拉底回答说,“我当然不会这么认为,有形的事物就是我们所看到样子。说它们都各自有其理念,可就荒谬了。”[4]也就是说,理念世界不存在丑,丑是物质世界不完美的一面。
既然现实世界中有丑,在柏拉图看来是第三性、是理念世界的“摹本的摹本”的艺术世界自然不能幸免,从他对诗人的驱逐可以看出。他认为,丑是出于“语文坏和性情坏”,因此要求诗人只能写好的东西,并且禁止其他艺术家在作品中表现“罪恶、放荡、卑鄙和淫秽”,以“防止我们的保卫者们在丑恶事物的影象中培养起来”[5]。
结合上文,也许我们可以尝试总结一下柏拉图的丑观:对于理念世界来说,丑是不存在的。丑存在于感性的现实世界中,是摹仿理念世界所产生的感性形象缺失比例、秩序、和谐的那部分。艺术世界中的丑会扭曲心灵对美的理解和感悟,因此要拒绝丑。
3 亚里士多德与“丑”
亚里士多德非常强调有机整体的概念[3]。他在《诗学》中这么说到:
……美取决于提及和顺序。因此,动物的个体太小了不美(在极短暂的观看瞬间里,该物的形象会变得模糊不清),太大了也不美(观看者不能将它一览而尽,故而看不到它的整体和全貌——假如观看一个长一千里的动物便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就像躯体和动物应有一定的长度一样——以能被不费事地一览全貌为宜,情节也应有适当的长度——以能被不费事地记住为宜[6]。
因此,事物的美丑既倚赖于事物的客观性质,也与人的主观感受紧密联系。丑的产生是由于秩序被打乱,或规模过大过小,给审美者带来感受上的困难。
亚里士多德还把“丑”与喜剧联系起来。他认为,喜剧摹仿“低劣的人”,但这种低劣并不因为“恶”,而是与“丑”有关,它所表现的是带有错误或者丑陋,但不会招致痛苦或伤害的滑稽。柯汉琳指出,亚氏的丑论有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是把丑与恶作了区分,认为丑“不等于恶,是一种不造成伤害和痛苦的恶”;其次,该丑论既涉及伦理(“低劣的人”),又涉及形式(喜剧演员的滑稽面具)[1]。
亚里士多德最早关注丑的快感问题、提出丑可以转化为艺术美。艾柯指出,“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提出了一条被普遍接受的法则:对丑陋事物做美丽的仿制是可能的……”[4]亚里士多德认为,生活中我们讨厌看到诸如“最讨人嫌的动物形体和尸体”的某些实物,但这些实物一旦经过艺术模仿,会让人产生快感,其原因在于学习能给人带来快感,或者是在于“作品的技术处理、色彩或诸如此类的原因”[6]。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现实是对思想不完美的摹仿,而艺术摹仿更拙劣。相反,他把艺术提到一个很高的地位,认为艺术是人的能动性和对现实世界的摹仿这两者结合的产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模仿兼经过理性处理的产物),所以大自然的美可以更美,大自然的丑也可以带来快感。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排斥“丑”。对他来说,事物的丑既由于事物本身带来(或失去秩序,或规模不当),也因为观者的感受力而产生,但丑于人无害,人们还可以通过艺术手法变丑为美。
4 结束语
审丑一直是希腊人审美过程中的副产物。然而,在这种氛围中,苏格拉底从自身出发,开始对“丑”的思考。本文粗略地讨论了古典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三位巨匠是如何看待丑的。我们发现,苏格拉底开始脱离外形美,思考抽象意义上的美,努力为外形丑找到立足点,尽管失败了;柏拉图在进一步发展苏格拉底的想法的同时,形成了自己较为系统的见解,把美归于理性世界,把丑放在了感性世界;而亚里士多德则有与他老师相悖的看法,认为美丑都在感性世界里,但丑通过理性可以变为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萌芽时期审丑的大致发展轨迹。尽管都是些较为朴素的想法,但却为后世的审丑开辟了道路,影响了一大批如康德这样的大哲学家的美学思想,所以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1] 王宏岳.美学的审丑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 沃拉德斯拉维·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M].杨力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4] 翁贝托·艾柯.丑的历史[M].彭淮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1-41.
[5] 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6] 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7]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