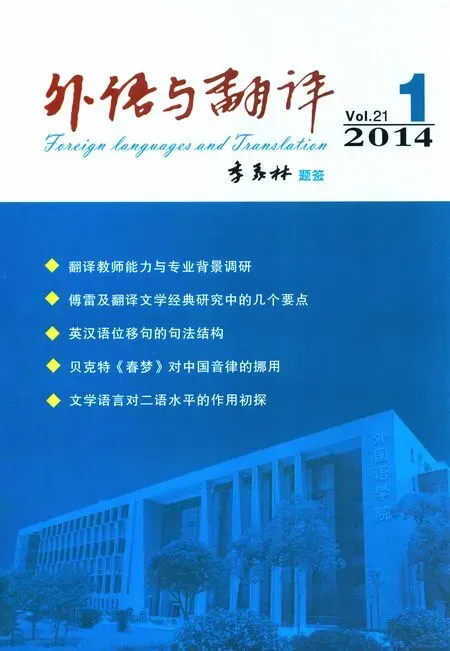异教的后山:《路娜萨之舞》中的隐喻场景与悲剧性∗
2014-03-21向丁丁
向丁丁
复旦大学
异教的后山:《路娜萨之舞》中的隐喻场景与悲剧性∗
向丁丁
复旦大学
爱尔兰当代名剧《路娜萨之舞》中有一处颇富趣味的虚构场景:西北边境多尼戈尔郡某小镇的后山。这里是凯尔特人后裔举行路娜萨节狂欢庆典的所在,与天主教浸润下严肃沉闷的小镇人家构成鲜明对比,承载起爱尔兰原始异教文明的隐喻。戏剧以此种隐喻方式展现两种宗教传统的角力。在工业革命肇始的时代,这种角力在小手工业者的生活抉择层面得到深刻的体现,并成就了一出闪耀着酒神光芒的平民悲剧。
后山,路娜萨节,异教,隐喻,悲剧性
《路娜萨之舞》(Dancing at Lughnasa)是爱尔兰当代最享盛名的剧作家——布赖恩·弗里尔(Brian Friel)的代表作之一,透过一户小镇人家的衰败展现工业文明入侵下手工业阶层生计与尊严的丧失。全剧情节皆完成于西北边境多尼戈尔郡某小镇1居民蒙蒂(Mundy)姊妹家中,然而在这实际舞台空间之外,另有一处人物对话常常提起、却从未真正形于舞台的虚构场景,与实际空间形成呼应与对比。它出现的频次与时机微妙,引人想象,催发思考。这便是小镇后山。这一场景承载着深刻的隐喻含义,展示了爱尔兰的异教与天主教两重传统在工业革命初期的角力,为理解剧作的悲剧性提供了切入点。
1.后山:异教的狂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爱尔兰从传统的农业国家向工业化转变的阶段。蒙蒂一家家境贫寒,仅靠大姊凯特(Kate)在公立学校教书的薪水和艾格尼丝(Agnes)、罗斯(Ross)在家手工编织手套换取微薄酬金。长兄杰克(Jack)原是传教士,在乌干达生活二十五年,却被当地原始文明感化,反向皈依异教,被政教当局遣返回家。邻近地方大工厂的建起冲击手工业,艾格尼丝与罗斯的活计渐渐失去订单。蒙蒂一家的命运显现出无法挽回的颓势。
正是在这沉闷颓败的氛围当中,后山以极具魅惑力的形象出现。八月,快到凯尔特仪俗中的丰收节庆——路娜萨节。五姐妹中最善感和曼妙的艾格尼丝提议,大家应一同赴小镇后山,参加路娜萨节的篝火舞蹈。她说,“我真想去跳舞,凯特。是路娜萨节啊。我才三十五岁。我真想去跳舞”2(Friel 1999:28)。
众姊妹细细描述后山的盛况,表达对那里的向往。她们的述说让那里的各种风物幻化为各样意象,如饮酒跳舞的人群、原始节奏的音乐、熊熊燃烧的篝火和舞池旁边的水井。与寒酸的厨房、荒芜的小花园布景对比,这些幻想的意象令人目眩与神往,且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后山的篝火、泉水与舞蹈提示了它与异教传统的渊源。若对古凯尔特人的世界观有所了解,会发现后山种种风物正是他们自然崇拜中的物事,异教神灵蕴于其中——篝火是太阳在人间的拟象,泉水是纯净、更新、疗伤之水中最具神性的一支(Hitchcock 1906: xii-xx)。在这种种风物的簇拥之下,后山成为了凯尔特异教文明得以保存、生长的处所。那里的种种意象显得自然、神秘,生命力几近透明,令人既易感知、也易汲取。由此,后山构筑起一处隐喻的场景,它象征着古老的异教文明。此一种隐喻场景具象地提供人们认识世界的另一角度——世界并非单一宗教过滤下的秩序,它可以是既古老又年轻、既“异教”又自由、能治愈伤痛也能魅惑灵魂的所在。
路娜萨节的神话起源也为后山的神性添加了注脚。传说中路神的母亲生前为凯尔特人开垦了爱尔兰广袤的土地,她的葬礼逐渐演化为丰收节庆,其时人们汇聚山顶,点燃篝火,跳舞狂欢(MacMathuna 1992:11)。女神开垦土地、归于土地,是生命不息、循环更新的寓言。观众不难感受到凯尔特人寄托于此永生与奇迹的愿望,也不难想象神灵并不与子民分隔,而是隐现在土地、植物、泉水和火苗之间,在迷醉的舞蹈中和人们一同礼赞生命,祈祝丰饶。后山是人与自然、神灵自由沟通的世界。
然而艾格尼丝的提议立遭“家长”凯特否决——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具有近乎苛刻的道德要求,尚勤俭朴素,恶享受纵欲。路娜萨庆典奉献给凯尔特原始宗教之神,对于唯尊一主的天主教徒而言自然既不合教义、更有失体统。后山的第一次邀约,以遭到拒绝告终。有批评家认为,此番拒绝其实源自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凯特是一个“出于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而使内心世界荒芜贫瘠的人,她固执地坚守自己关于正确秩序的理念,拒绝敞开自我,迎接生命的神秘和其他的可能”(Gagne 2007:130)。她心中的“正确秩序”何来,却值得继续追索,从天主教在漫长的年代中将凯尔特异教文明逐出正统,在普通民众当中获得威权的过程中寻得答案。早期传教士极有技巧,他们通过挪用异教神灵和仪式、在修道院中以书面文字改写凯尔特口头历史与传说等方式,以圣帕特里克等天主教圣人取代异教的众多神祗。信徒众多以后,即行禁止异教仪式,将异教祭司贬为巫术方士,将自然崇拜斥为野蛮迷信(Edwards 2005:105-07)。从此,天主教等义于文明,异教等义于蛮荒,此一种二元对立泾渭分明,似不可挑战。路娜萨节奉献给司掌农业和繁殖的路神,正是异教具象神崇拜之一种,在笃信天主的凯特眼中,自是野蛮过往的残痕,唯避之而不及。她拒绝融入围火饮酒、跳舞狂欢的当地人中,拒绝融入凯尔特人的后裔中。
从单个人物凯特放眼开去,整个小镇都困囿于压抑的家庭和社群生活当中。这种困局在弗里尔整体创作中并非绝无仅有,相反,他不止一次描绘令人窒息、几近幽闭恐怖之境的道德气氛:在这些偏僻乡镇,“信仰简单等同于寥寥几条道德规章,此外别无它意,精神追索丝毫不受关注,感官与精神更被切断一切联系”(Cave 2006: 194)。与这困囿截然不同,后山充盈着自由与鲜活的生命力。而由于它仅仅出现在人物或充满向往、或充满敌视的对话中,所以显得隐蔽、神秘,几乎带有乌有之乡的色彩。可是这个乌有之乡贯穿戏剧始终,不受时间与空间所限,成为人物梦想到达的彼岸,达成在熟知的现实世界中断无可能实现的自我价值。
2.后山:酒神精神的感召
“过去五十年间爱尔兰剧场中最动人的一幕”(Walsh 2010:129),就是在后山所代表的生命力感召之下发生的。虽局限在蒙蒂家的农舍中,却与后山上异教神灵相呼应,与凯尔特人庆祝丰收神的生死轮回相应和:
麦吉转过身来。仿佛配合着音乐、节拍,头微微倾下……忽然之间,她的五官光芒熠熠,似在挑战,又似要进攻:像是戴上了一幅朴拙的笑脸面具。有那么几秒钟,她原地立定,侧耳倾听,一边吸收音乐的韵律,一边桀骜地扬眉扫视众姐妹。瞬间,她伸开十指(上面覆满面粉),把垂在脸上的头发撩到脑后,手指再顺着脸庞滑下,脸上便留下花纹,立时又是一张面具。与此同时,她嘴唇开启,爆发一声狂野、沙哑的“呀——”,舞蹈顿时开始,手臂、腿脚、头发、长长的鞋带四散飞舞……大约有十秒,她独自一人舞着,像脸色惨白、神色疯狂的托钵僧……(Friel 1999:35-36)
麦吉的激情是有传染力的。她点燃了罗斯、艾格尼丝、克丽丝,甚至最后凯特的脸庞。除了凯特跳得仍有几分拘谨外,其余姐妹肢体舒展、尽情歌唱,时而狂野长啸。
这一幕之所以打动人心,绝不仅仅是因为观众目睹女性躯体把欲望恣意宣泄,更深层地,是由于其中蕴含一种酒神式的迷醉。在被日常生计琐事淹没的蒙蒂家,这番舞蹈显得与通常气氛格格不入,它打断了惯常的秩序,有逗引、启示的意味。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描述过酒神祭祀场景:
此刻的人成了更高一级性灵的一员,他歌唱、舞蹈来表达自我。他舞着,忘却了如何走路、如何讲话,几乎要振翅而起。每一动作都预示着迷醉。他浑身散发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正是这同样的力量令牲畜开口,令大地产出牛奶同蜂蜜。他感到自己与神灵一样,有着他们一般的幸福与狂喜,与他们一起大踏步前行……(Nietzsche 1965:296-97)
如果把尼采的文字用来描述小镇后山,尤其是路娜萨节期间的后山,正好妥帖。路娜萨之舞蕴含着古老仪式中除去枷锁、赋人自由的能量,与三十年代的爱尔兰小镇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也暗含一种令人不安的违规、僭越。
蒙蒂姐妹在音乐催发下自发的舞蹈,将后山拉近一步。后山不再是遥远的背景,而成为舞台空间的延伸,伴随情节始终。舞蹈方起,“生命的精华与希望全在音符、旋律、静默和舞动中,似入催眠之境”(Friel 1999:71)。催眠意味着现实的苦难被暂时忘却,伤痛在梦境中愈合。后山对剧中人物有吸引力,是因为那里是实现不同人生的可能之所;对观众有吸引力,是因为他们能够想象后山是遭受困囿的人物命运变化的契机。这一意象包含着爱尔兰民族异教过往的神秘召唤,虽然并非以宣教的形式出现,但它形于路娜萨节日庆典,成为凯尔特人乐观欢快的酒神式精神的比喻。批评家皮尔金顿(Lionel Pilkington)曾试图从弗里尔的戏剧中读出历史,结论却与出发点大相径庭,“《路娜萨之舞》不是社会分析,而是更广阔的生存关怀之喻;也不是某一具体历史时期的产物,而是欲望与实现之间普世鸿沟之喻”(Pilkington 2006:500)。这两个比喻揭示出《路》剧的基本戏剧冲突:刻板的宗教思维习惯与古老原始文明吸引之间的矛盾。
3.后山:情欲的释放
在这一基本冲突的背景下,蒙蒂姊妹的欲望得以凸显。在专制而严肃的家庭,浪漫爱情显得不合时宜。然而智力有轻度缺陷的罗斯最为无畏,她设计与情人在后山密会,荡舟湖上,打破家中不成文的刻板条规。
他带我坐上他父亲的蓝色小船……我们俩上得山去。他带我看路娜萨篝火留下的残堆。其中好些还在燃烧……上边儿真是个好安静的地方。一个人也没有,就丹尼和我。(对艾格尼丝)他叫我他的罗斯小花蕾……(Friel 1999: 90)
此时的后山具有了莎剧中亚登森林的色彩,山林与湖泊构成“绿色世界”(Frye 1957:182-83),外界的道德、法则尽可悬置,理智之下的爱欲、冲动尽可松绑。而其他姐妹则默默克制欲望,未能自由和无畏地追求爱情。这固然与性格相关,但若继续追溯性格的形成,天主教教化在三十年代是不能忽略的显因。彼时教会势力达到鼎盛,推行的教义也极为保守,通过影响制定1937年爱尔兰宪法,将私人生活领域的家庭结构、性爱等都置于公共权力监管之下;有关肉体的激情更是被斥为罪孽,与圣母玛利亚所代表的女性理想格格不入(Hadfield 2003:217-18)。立法、宣教对教徒既构成外在的约束,也形成内化的枷锁,凯特心中“教皇庇乌斯十一世定义的神圣婚配”(Friel 1999:63)裁决一切,个人欲求经此过滤,所剩卑微无几。蒙蒂姐妹的爱情失败,与其时保守的信仰不无关系。同样的感情和欲望,在后山的树林湖泊间能够自由实现,在小镇的古板人家却只能压抑蛰伏。两种秩序,分歧凸现。
4.后山的世界性:非洲映射
后山地处小镇边缘,从而拥有与封闭的小镇相异的身份,指向人类追求幸福的权利、选择信仰的自由和对深层渴望的认同。剧中有一处与后山精神极为相通的地方:乌干达一个名叫莱昂格的小村庄,杰克神父返乡前在那里生活了二十五年。
与南非作家库切(J.M.Coetzee)小说《耻》(Disgrace)中的女儿相似,杰克神父也是被当地文化反向改造的殖民者典型。杰克返乡后再未做过弥撒,反而热情地传播非洲的异教文化。他描述下的莱昂格庆典与路娜萨节景象惊人地相似。
开始得非常正式,非常庄重,用家禽、山羊或小牛当作牺牲,在河边献祭。然后举行仪式,切开当年第一批成熟的甘薯和木薯,涂以神油……再念咒语——真是好听的吟唱——既表达我们的感恩,又为仪式舞蹈打拍子、奏鼓点。再之后,等到感恩结束,舞蹈紧接着开始。有趣的是整个仪式自然而然变成一场世俗的欢庆,宗教仪式结束,而部落庆典开始,转变微妙得简直让人难以觉察……我们在外圈点起火,用彩色粉末涂脸,唱起本地民歌,畅饮棕榈酒。跳舞,跳舞,跳舞……(Friel 1999:74)
这是一个宗教与世俗并不截然分开的村庄,人们更多地是遵循自然之法生活。这一世俗化倾向让人想起弗里尔同时代爱尔兰诗人希尼(Seamus Heaney)。他曾对弗里尔的立场心有戚戚,写道:“我们和我们的语言仍旧拥有一种宗教无意识,在这种无意识支配下我们乐于将自己世俗化,或者说接受世俗化的过程也未尝不可”(Heaney 1993:239)。杰克安慰未婚有子的妹妹克丽丝说莱昂格的妇女若能未婚生子,都引以为豪;面对麦吉打趣让他为妹妹们安排丈夫,他认真地回答说无法找到五个男人一一婚配,但可循莱昂格风俗,让五个妹妹与同一男子结婚。很明显,这是一种“未开化”状态的原始文明。然而与“未开化”并行的却是蓬勃生长的生命力。弗里尔在剧中安排了一个次要情节,对这一点加以佐证:杰克神父的同僚由于依赖现代药物奎宁上瘾,被殖民者的医院诊断为恢复无望,但当地巫医却妙手回春,构成了一个微妙的反讽。这种神奇的酒神式能量对循规蹈矩的蒙蒂姐妹,尤其是凯特而言,是令人不安、恐惧的,因为在她们严格的道德词典里,“异教”是无可救赎的贬义词。
篝火、祭祀、美酒和舞蹈,这些意象在非洲村庄和小镇后山两个背景上重叠,形象地展现出弗里尔最钟爱的主题之一:狭隘、近乎清教般严格克俭禁欲的爱尔兰天主教与更为古老的凯尔特文明之间的冲突。当别处的人们饱受贫困之苦,舞者们却在为丰收而感谢神灵;当别处的人们囚禁在压抑之中,舞者们却恣意舒展着身体和灵魂。
莱昂格村和它在爱尔兰小镇的映射——后山,同时也暗示着文明世界里众多二元对立概念的消解。看来黑白分明的结构、伦理和意义,都被异教逻辑消弭,成为不确定的一列可能性,带有强烈的解构意味。不过,这种消弭的目标并不在于摧毁现存的爱尔兰天主教信仰,而更在于提起对“低等的”、“原始的”信仰秩序的重新评价。
5.后山:悲剧性的启示
《路》剧与弗里尔其他多部戏剧一样,关注宏大社会、政治、经济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在这出戏剧中,这种关注聚焦于现代的工业化进程对蒙蒂姊妹的灾难性作用。蒙蒂姊妹是陷入贫困的爱尔兰小镇居民的缩影,她们在感情、经济上的失败,都可归结到更广阔的社会变革上去。
然而在一片颓势的命运之中,蒙蒂姊妹也曾展现过充满神性光辉的时刻。现象学家伊连德(Mircae Eliade)指出,“早在文明历史开始之前,人类就已经开始以舞蹈作为进入神性时刻的途径”(Eliade 1971:28)蒙蒂家较为年轻的姐妹对路娜萨时节后山聚会舞蹈的向往,正与酒神狂欢的精神吻合。从表层来看,两者都是庆贺一年一度的丰收,向深层挖掘,两者都在向生死轮回的基本法则致敬。牲畜祭祀、肢体舞蹈、对神灵歌唱,都表达对个体生命的礼赞、对归于湮灭又重获新生的本能渴望。
此种吻合为体察《路》剧真正的悲剧性所在提供了切入口。蒙蒂姊妹及她们的亲人的悲剧,源于她们将后山所代表的古老凯尔特文化强硬地排斥出生活,同时却没有准备好适应新的时代秩序。她们由此被连根拔起,动弹不得,既不可能往前拥抱工业时代,也不可能转向退回异教秩序。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对现代悲剧的阐述对解读蒙蒂家的悲剧很有帮助。他指出,现代多数悲剧的悲剧性都来自普通人在不利环境中维持或重获尊严的努力,他们愿意为此孤注一掷,甚至不惜牺牲生命(Miller 1965:536-39)。
这样的努力贯穿《路》剧始终。蒙蒂姊妹陷入的不利环境来自正在发生剧变的社会经济秩序。凯特的选择是坚守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固守世代不变的手工业生产方式,并在同时严防凯尔特异教因素对家庭的侵蚀。她对后山狂欢所持的警惕态度不足为奇:因为后山有哪怕仅是残痕,却也真真切切的异教因素,在那里举行的路娜萨庆典充斥着扰乱灵魂的能量。可悲的是,她的坚守并未使她强大,具备抵抗以汹汹来袭的工业革命为标志的命运颓变。三十年代后期,对爱尔兰而言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相同,是被逐渐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时代,而这个传统国家还没有迅速调整好,以适应新的秩序与节奏。凯特关于正确言行的僵硬看法,无非是阻隔于她熟知与陌生世界之间的缓冲带,陌生世界则只是因为拒绝接触而显得危机四伏。
循凯尔特仪俗,丰收时节群聚路娜萨之舞,并不是转头退向已然废弃的过往,而是为情绪和能量找到宣泄的出口,在极乐与迷狂里寻得再生的勇气同力量。总而言之,路娜萨之舞可以是一步跳跃,跃往看似蒙昧、实则丰厚的凯尔特传统。这种传统在爱尔兰大地上存续已逾千年,所崇尚的人与自然、神灵自由沟通,生命繁衍与更新,即使在这变革的时代也并不过时。可悲的是,凯特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困境,她为维持尊严付出的挣扎与努力没有产生希望的结果,反而使得她在自己的土地上愈来愈步履维艰。
杰克神父与凯特努力的路径正好相反。他的追求受到了非洲土著居民的巨大影响,崇尚活力、坦诚、与神灵近距离交流。所谓文明世界的各种禁忌都在近乎原始的理解力中被消解,使得这种文化粗糙、自然而健康。投向异教文明,或者容纳它所鼓励的生命力宣泄、轮回,是为蒙蒂姐妹所弃绝的一条出路,对杰克神父而言却并不如此。《路》剧写作的九十年代,新异教运动在爱尔兰方兴未艾,旨在“为前基督时代的本土神祗争取平等的地位,成为人们信仰的选择之一”(Lewis 1999:ix)。杰克神父不失为一位虚构的先遣。弗兰纳根(Kieran Flanagan)从社会学意义上分析杰克,“一个背弃天主教的神父,他似乎承担起了更具全人类意义的使命,在这一使命之下,他以赞赏的口吻谈论异教的仪俗与庆典,这个转向构成一个谜题”(Flanagan 1995:199)。可惜的是,他固执于非洲的异教魅力,却并未意识到自己的祖国也有伟大的传统。
在小镇乃至爱尔兰全国,新的秩序是以拔地而起的工厂为代表的。轰鸣的机器厂房打破了古老、自然的大地风貌,机械麻木的工人取代了快乐满足的手工艺人。在蒸汽升腾的背景之下,典型爱尔兰小镇的形象渐渐模糊,严谨缓慢的教徒生活开始显得不合时宜。蒙蒂姊妹离后山越行越远,异化和无根成为必然的命运。此时他们面前有三幅截然不同的图景:工业时代的高效与非人性,小手工业时代的狭隘与熟悉,异教世界的蒙昧与生机。姐妹们选择固守陈迹,然而继续小农、小手工业生活所必须的条件已经被剥夺殆尽;杰克神父选择远方的异教,却被老迈和死亡挡住了脚步。剧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物放弃过维持或重建尊严的努力,这使他们令人尊重,值得成为真正的悲剧人物。但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物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精神追索,得到或守护了有尊严的生存,这令他们成为阿瑟·米勒理论中真正的平民悲剧英雄。
蒙蒂家的农舍是一个具有幽闭恐怖感的空间,与实际演出时的演员一样,人物最终遗失的身份和尊严都时时困囿于此。后山上,酒神式的再生与活力不停歇地向凯尔特的后裔们发出召唤,在丰收时节,泉水篝火边的路娜萨之舞更是令这召唤形诸声色。两个空间,一个切实呈现于舞台,一个在对话微妙处形诸观众想象,一方面使得戏剧场景得以大大扩展,一方面提示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根源。
以一己之力正面对抗强大的机器文明,断无取胜可能;因偏执与成见排斥自己民族的古老异教文明,则切断了与精神遗产的最后联结。《路娜萨之舞》的悲剧是贯穿变革时代的悲剧,是先民土地上精神孤儿的悲剧,是每一个古老民族的落寞后山反复述说的悲剧。
注释:
1 名为Ballybeg,在爱尔兰语中即“小镇”之意。是弗里尔戏剧中常用地名。
2 本文中凡引自英文剧本与文献的,均为笔者自译。
Cave,R.Allen.2006.Questing for ritual and ceremony in a godforsaken world[A].Brian Friel’s Dramatic Artistry[C].ed.Donald E.Morse,Csilla Bertha and Maria Kurdi.Dublin:Carysfort Press.
Edwards,Ruth Dudley.2005.An Atlas of Irish History,(3rdedition)[M].London:Routledge.
Eliade,Mircae.1971.The Myth of the Eternal Return: Cosmos and History[M].trans.Princeton UP.
Flanagan,Kieran.1995.Brian friel:A sociological appreciation of an Irish playwright[J]. Contemporary Review April 266.
Friel,Brian.1999.Plays 2[M].London:Faber and Faber.
Frye,Northrop.1957.The Anatomy of Criticism[M]. Princeton UP.
Gagne,Laurie Brands.2007.Three dances:The mystical vision of Brian Friel in Dancing at Lughnasa[J].Renascence 59.2.
Hadfield,Andrew.2003.Sex and sexuality[A].John Goodby Irish Studies[C].ed.Oxford UP.
Heaney,Seamus.1993.For Liberation:Brian Friel and the use of memory[A].Alan Peacock.The A-chievement of Brian Friel[C].ed.Garrands Cross:Colin Symthe.
Hitchcock,F.R.Montagomery.1906.Types of Celtic Life and Art[M].Dublin:Sealy,Bryers&Walkers.
Lewis,James R.1999.Witchcraft Today:An Encyclopedia ofWiccan and Neopagan Traditions [M].Santa Barbara:ABC-CLIO,Inc.
MacMathuna,Seamus.1992.Paganism and Society in Early Ireland[A].Irish Writers and Religion [C].RobertWelch ed.Barnes&Noble.
Miller,Arthur.1965.Tragedy and the Common Man [A].European Theories of the Drama[C].ed.Barrett H.Clark.New York:Crown Publishers.
Nietzsche,Friedrich.1965.The birth of tragedy from the spirit of music[A].Francis Golffing. trans.Barrett H.Clark,ed.European Theories of the Drama[C].New York:Crown Publishers.
Pilkington,Lionel.2006.Reading History in the Plays of Brian Friel[A].Mary Luckhurst,ed.A Companion to Modern British and Irish Drama 1880-2005.Oxford:Blackwell.
Walsh,Martin W.2010.Ominous festivals,ambivalent nostalgia:Brian Friel’s Dancing at Lughnasa and Bill Roche’s Amphibians[J].New Hibernia Review,14.1.
(向丁丁: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讲师,博士)
通讯地址:200433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2013-12-17
∗本文系复旦大学青年学术促进项目,项目编号:GKH315200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