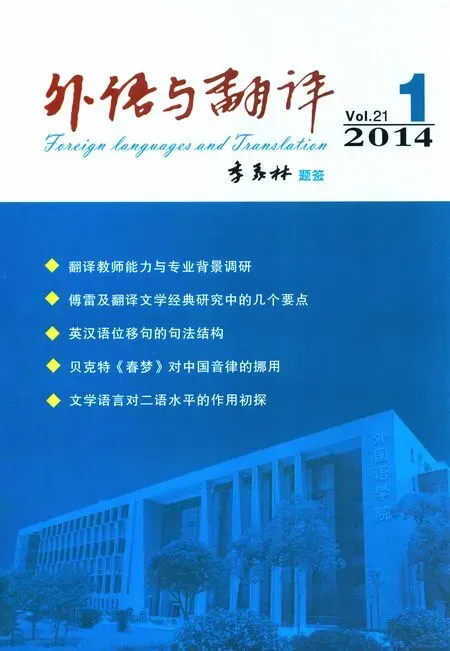贝克特《春梦》对中国音律的挪用∗
2014-03-21曹波
曹波
湖南师范大学
贝克特《春梦》对中国音律的挪用∗
曹波
湖南师范大学
贝克特的长篇处女作《春梦:从靓女到庸女》是引文、典故、元小说片段的拼缀物。其中,有关中国古典音律的片段译自拉卢瓦的法文版《中国音乐》,几乎就是中国《吕氏春秋》片段的严格重译。元叙事者挪用了“伶伦制律”、“孔子击罄”和“凤凰涅槃”三个中国典故,将创作的困境进行类比,希望人物和情节像“十二律吕”那样,通过有序的排列、组合,构成线性的、单声部的曲调,而非众声喧哗的“交响乐”。作为“狂乱思想”的体现,《春梦》对中国音律的挪用和翻译展现了一幅“艺术家年轻时的肖像”;此后,中国文化就很少出现在贝克特的作品中了。
萨缪尔·贝克特,《春梦:从靓女到庸女》,中国音律,挪用,翻译
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是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不懂汉语,但在早期的小说中确实经常挪用中国文化。据保存在英国雷丁大学“贝克特国际基金会”的小说手稿,他是通过法语和英语了解中国文化的。1928年底,他来到巴黎高师担任英语讲师,结识了已经成名的同乡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并接触了因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等人推介的正风行于巴黎的中国文化。1932年1月,他辞去三一学院的教职,从闭塞的都柏林移居先锋派聚居的巴黎,2-6月创作长篇处女作《春梦:从靓女到庸女》(Dream of Fair to middling Women,1992)。这期间,受过良好音乐教育的贝克特认真参阅了法国东方学者拉卢瓦(Louis Laloy,1874-1944)的《中国音乐》(La Musique Chinoise,1903)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A.Giles,1845-1935)的《中国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1911)等,又因业师(乔伊斯)纵横捭阖的创作风格的巨大影响,不免在《春梦》中玩弄中国古代音乐和文化典故,展现自己喷涌而来的学识和对现实主义叙事传统的嘲讽。
1.伶伦制律
《春梦》开篇不久,贝克特就担负起将《中国音乐》中的有关片段英译出来的责任,又摆出乔伊斯一类大家的架势,硬是插入一大段让东西方学者都挠头的文字:
假设现在我们讲一个中国的故事,把我们的意思谱成曲子。好吗?那么就讲伶伦的故事,他来到西部边境,来到嶰谷,断一竹于两节间,吹之,不禁欣喜,定其音为黄钟之宫。接着,凤凰来助,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伶伦又制十一管,和所听之音适合。然后,他将十二律吕上报黄帝,分为六律、六吕,曰: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Beckett,1996:10)
在此,贝克特模仿了业师喜用典故的文风,将有关中国音律起源和吹管乐器发明的故事完整地复述出来,并把故事醒目地插入因而更不连贯的叙事中。于是,此处的叙事流露出他历来痛恶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和他正投身其中的元小说中常见的“作者介入”的痕迹,是篇首所说“狂乱思想”(Beckett,1996:1)的体现。
对于这段纯粹“中国特色的”文字,国内外即使有所论及,其考证和阐释也很成问题。美国学者回避“伶伦制律”的中国典故,转而探讨该段文字与欧洲表现主义音乐的关系,声称“这一段落的背后……是阿诺德·勋伯格:因为贝克特是在戏仿勋伯格早于该小说约十年创制的十二调作曲法”(Albright,1999:30)。读着有关中国音律起源的传说,却谈着欧洲乐坛新兴的“十二调”,这置换的背后是否真有“东方主义”在作祟?英国学者分析了《春梦》对《中国音乐》和《中国文明》等论著的借鉴,尤其是《春梦》在创作主旨和叙事结构上对中国“琴曲”(k’in music)的借鉴,但《春梦》并未直接提及“琴”或“琴曲”,其关联性有待进一步考证。在“贝克特《春梦》中的律吕美学和元叙事”一文中,美籍华人Lin Lidan探讨了《春梦》中“中国音乐作为叙事模式”(2010: 281)的功用,接着在“贝克特小说的中国之源”一文中,她又从“后东方主义”的角度分析了“中国音乐与文化对贝克特小说美学观及伦理观的影响”(2010:294);这是国内外迄今最充分的论述,但其对中国古代音乐的考证不严密,从“东方主义”的角度阐释此后贝克特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元素日渐稀少的现象也不合理。
其实,贝克特在此复述的是“伶伦(Ling-Liun)制律”的传说,而非广义的“中国音乐”或“中国琴曲”(Lin Lidan,2010:294)诞生的故事。该传说通常与“伶伦制管”的传奇合二为一,在历史巨著《吕氏春秋》(公元前239年)中有较为细致的叙述:
“黄帝诏伶伦作音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于嶰谷,以生窍厚薄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九寸,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昆仑之下,听凤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适合,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吕氏春秋·太平御览·卷五六五·乐部三·雅乐下·律吕》)
在稍晚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公元前104-122年)中,该传说也有简略的记载:“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豀,斩而作笛,吹作凤鸣”。经比照,《中国音乐》(正如中国较晚的历史著述)中的片段依据的是前者,而贝克特的行文除体现元叙事者口气的插入语外,几乎就是《吕氏春秋》片段的严格的二度翻译。虽然“大夏之西”并非“西方的疆界”,始祖“黄帝”和圣地“昆仑”也不见了踪影,但核心的音乐术语无一遗漏地罗列在此,可见贝克特“对中国[文化]的挪用”(Lin Lidan,2010: 282)不是随意的。
据现存文献推断,凤鸣如箫笙,音如钟鼓,而伶伦是“取竹于嶰谷”,因此伶伦发明的应是发音类似凤鸣的竹制排箫类乐器,而非西方论者反复提及的古“琴”。中国古人用十二根长度不一的律管吹出十二个高度不同的标准音,以确定乐音的高低,故这些标准音也叫“十二律”。音调从低到高,“十二律”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又依据“阴阳”理论,“十二律”分为两组:奇数六律为“阳律”,叫做“六律”;偶数六律为“阴律”,称为“六吕”,合称“律吕”。可见,贝克特不厌其烦地将“十二律”完整地翻译了出来,而且顺序无误,“阴阳(雌雄)属性”也毫无“混淆”(Ackerley&Gontarsky,2004:322),其准确性超越了西方考据者的论断。另据“凤凰传奇”,雄者为凤,雌者为凰,可以断定“雄鸣”、“雌鸣”的翻译是准确的。不过,庄严的“黄钟之宫”(the Bronze Bell Tone)并非“自己……说话平和时的嗓音”,“六律”(the sixmale lius)、“六吕”(the six female lius)的译文也说不上准确。但贝克特不是疲于“忠实”的职业译者,而且在亢奋的创作状态中是无暇顾及每一处行文的,他只是想借用中国音律起源的传说和中国古代音乐的成就表现元叙事者对叙事连贯和音调之间、人物之间关系和谐的调侃。
在古汉语中,“律”(pitch-pipes)指用来定音的竹管。在此,作为作家的贝克特无意于实现意译的功用,而是沿用了《中国音乐》中的拼音“LIU”,并貌似慎重地补充了声调。在他看来,正如“琴是神秘的纯粹性的物象”(Lin Lidan,2010: 282),“律”和“十二律(吕)”也应保留足够的神秘性和异域色彩。在乔伊斯巨大的身影下,他还没有忘却“写作不关外物;它本身就是存在”(陆建德,2001: 264)的狂言,从事二度翻译时自然也深谙音译的妙用。其实,“直接表现”(陆建德,2001:264)也罢,故弄悬殊也罢,贝克特实现了写作要旨的一部分:让元叙事者“提醒读者,读懂该文本是不可能的”(Drake,2008:235)。当然,他还没有孤傲到完全无视“读者反应”的地步,不至于将业师的“文字革命”进行到底。为该段落的可读性及异域风情起见,他接着又严谨有余地将《中国音乐》相关表格中的“十二律(吕)”的名称直译过来,一个不落地罗列在“伶伦制律”传说的末尾。对于这些包含奇异意象的音乐术语,东西方读者都不必过于诧异,因为汉语原文本身只是用以区别音律的名称,其实际所指和字面意义(所含意象)无关。如此,贝克特实现了写作要旨的另一部分:“读者可以通过意象和音乐的方式体验该文本”(Drake,2008:235)。通过直译,贝克特实现了“功能对等”,又为下文继续挪用中国音乐铺平了道路。
2.孔子击罄
正如通过巧妙的排列、组合,“十二律”可以谱成悠扬的、主调突出的乐曲,“叙事者[也]希望,他描述的人物各为一律,在更为出色、悠扬的曲调中扮演自己的角色”(Ackerley&Gontarsky,2004: 322)。
现在重要的是,我们无比虔诚地希望,笔下至少有一部分人物能像律吕那样。比方说,约翰担任黄钟,丽玛担任仲吕,卡瑟担任夹钟,曼德琳担任姑洗,比拉克本人担任蕤宾或者无射,如此等等。那么,余下的问题就是像孔夫子在玉罄上玩戏法那样奏乐了。假如我们笔下的所有人物都是那样——像律吕的想法那样——那么我们就能写成一本和谐得纯净的小说,想想那会有多好吧,线性的,一段可爱的毕达哥拉斯式的因与果的链式反复独奏曲,一首听起来悦耳的独角哼鸣曲。(Beckett,1996:10)
假如每个人物都温顺地接受自己的角色(律吕),那么《春梦》中的叙事就会像中国古代的乐曲一样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是一段悦耳的“链式反复独奏曲”,众多人物在其中各司其职,互为因果。果然如此,叙事者的职责就简单化了:玩弄排列、组合游戏而已,“像孔圣人那样在石罄上”摆弄律吕。由此,贝克特的类比从传说中的“伶伦制律”转向了有史据可查、对中国古代音乐理论有过较大贡献的孔圣人(公元前551-公元前479)。
这一转向绝不只是因为《中国文明》中有相关叙述,使贝克特对孔圣人的音乐造诣有所敬仰,更是由于孔圣人融入了儒家思想的音乐观以“和”为核心,和贝克特创作《春梦》时的理想不谋而合,正可以用来抚慰他的“狂乱思想”。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可见其对以《韶》乐为代表的“雅乐”的推崇。正如贝克特对音乐和绘画有着非凡的领悟力,孔圣人也能超越“曲”、“数”、“志”三个层次,直抵“人”这一最高境界。他推崇以礼制乐,认为《韶》乐是“美善”统一的范例,能教化百姓趋“美”、近“善”,因而具有安民、治国的功用。在他看来,“音乐必须反映儒家的理想,即社会的和谐”(Ackerley&Gontarsky,2004:322)。苦于将喷涌而来但难于驾驭的素材纳入一部连贯、统一的作品的贝克特,在推崇实用主义音乐观的孔圣人身上找到了知音,幻想着能“像孔圣人那样”奏出和谐因而美妙的音乐。
但孔圣人演奏的,究竟是“罄”、“琴”还是作为“琴”中一种的“琵琶”呢?英国学者指出,贝克特参考的《中国音乐》中介绍了古“琴”,而且“琴曲”为贝克特的短诗“Alba”和“Dortmunder”(Sean Lawlor,2006:1)的扩展提供了灵感。这一论断是有历史依据的:据《纲鉴易知录》等古籍,“琴”发明于神农时代(公元前2370-公元前2338),初为五弦琴,至周文王时发展为七弦琴,远在孔圣人时代之前即已定型、传播,且发明地正是孔圣人的故乡曲阜。而孔圣人也确实擅长鼓琴,而且对琴曲精于鉴赏。《史记·孔子世家》中就记载了“孔子鼓琴”的故事:谙熟琴曲的旋律和演奏的技巧后,他不仅能说出表现的意境,甚至能想象出作曲者的人品,断定该琴曲出自周文王之手。可见,孔圣人“鼓琴”是不争的史实。但问题是,在所有中国古代文献中,“琴”都是指瑶琴(古琴),是一种水平放置的弦乐乐器,不同于竖着弹奏的“琵琶或鲁特琴”(Lin Lidan,2010:281)。“琵琶”虽然是鲁特琴一类弹拨乐器的总称,却出现于中国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6)时代的印度,后于南北朝(公元420-589)时代才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晚于孔圣人的年代约10个世纪。因此,孔圣人擅长的应是约1800年前出现在他故乡的中国古琴,而非1000年之后才现身中原的印度竖琴(琵琶)。
第二个问题是,在此贝克特并没有提及古琴,将“孔子学鼓琴于师襄”的故事复述出来,而是提到了“编罄”(cubes of jade,即the pien k’ing)”(Ackerley&Gontarsky,2004:322)。这一挪用也是有史可据的。据考古证实,中国现存最早的石罄实物已有4000年历史,表明早在夏代,石罄即已从母系氏族社会的片状石制工具演化成打击乐器,用于乐舞活动,开始成为象征身份和地位的“礼器”了。到春秋时期,石罄已历经1500年的历史,成了孔圣人擅长的另一种古代乐器。据《论语·宪问》,“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可见,贝克特放弃《中国音乐》对“琴乐”的描述,并没有犯历史错误,他的读书笔记是准确的。而且挪用这一新的典故时,他还让元叙事者心中充满好奇和羡慕,使其语气有些玩世不恭:“像孔圣人那样在一组石罄上变戏法”。
3.凤凰和鸣
在贝克特的授意下,众位人物狂躁不安,不但不各司其职(充当律吕),还一同哄闹,毫无和谐可言,元叙事者该如何处置呢?是任其混响,还是将其纳入有序的线性系统,构成一段同一性质的旋律呢?
可是,拿尼莫这样的人你能怎么样呢?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浓缩成一律,他根本就不是一个音符,而是最叫人遗憾的众多音符的共鸣。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让(比方说)半打鸣凤像一只不死的祥鸟那样从同一堆干柴的灰烬中腾起,一边齐声鸣唱,只要它们自己觉得合适,心满意足地喊叫也好,大失所望地吼叫也行,那么这位尼莫的状况我们就可以略有所知:是一个众声交响的乐段,不是旋律悠扬的曲子。……着实,转念一想,我们往往会闻到男一号的心中有一只混响鼠。他可以同时担当蕤宾和无射的角色,甚至给一个双性的隆起配上林簇。可是,砰!仅仅是一律而已!我们有权怀疑它。(Beckett,1996:10-11)
为描述这一困境,贝克特受“伶伦制律”传说中“听凤之鸣”一句的启发,化用了另一个古老的中国传说:“凤凰涅槃”。凤凰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之一,据说每隔五百年集香木自焚,从死灰中新生,其羽更丰,其音更清,如此循环往复便获得了永生。在此,元叙事者期望那“半打律吕”能“从同一处柴堆的灰烬中升起”,焕发新的生命,而且摒弃前嫌,相互协作,一道奏响一首主调清晰的“旋律”,而非一曲众声喧哗、杂乱无章的“交响乐”。
凤凰(Phoenix Red)亦称丹鸟、火鸟等,可见在中国古人的幻想中,其画像应以红黄色为基色。但在贝克特的笔下,“丹鸟”换了毛色,成了“紫鸟”(“purple bird”)。不过,西方以紫色为贵,因此《春梦》中的凤凰依旧是“祥鸟”。燃起浴火的“香木”(梧桐枝)也失去了异域传说的色彩,仅保留了语用功能,成了“火葬用的柴堆”。在此,贝克特采用了归化策略,将这两个文化术语意译出来,实现了“语用对等”。但之前的短语“half-a-dozen Ling-Liun phoenix”却词法不通,是误将以凤凰为主人公的两个传说搀和在一起的结果。贝克特先从“伶伦制律”中的“雄鸣为六”(六律)和“雌鸣亦六”(六吕)中取出“半打律吕”,再取共同的意象,将“凤之鸣”和“凤凰涅槃”两个片段混为一谈,于是,他的笔下便出现了意象古怪、令大多数学者也不知所云的名词短语“半打鸣凤”。令人疑惑的“林簇”在前,叫人傻眼的“半打鸣凤”紧随其后,贝克特确无多少“读者反应”的意识。在“风云激荡的‘革命’氛围里”,早年的他“随心所欲地创造文字”,确有些许“让平庸的读者见鬼去吧”的“傲气”(陆建德,2001: 262-3)。
问题是,“凤之鸣”何以能成为伶伦发明“律管”的依据呢?《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了“风吹之音”的诞生:“唯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乐,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而主管“风吹之音”的正是凤凰,因为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凤凰不仅是火鸟,也是风鸟。那么,“凤之鸣”又究竟是怎样的乐音呢?据中国古代音乐典籍推断,雄鸣曰即即,雌鸣曰足足,雌雄和鸣曰锵锵。这里已包含了最基本的乐音排列、组合的规律:“雄鸣为六,雌鸣亦六,”经反复地排列、组合,雌雄和鸣即可产生无数的音乐片段。于是,虽然“中国音乐在古板的程式中成长,却能拥抱创造的自由”(Lin Lidan,2010: 291)。在“凤凰于飞,和鸣锵锵”(《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前景的激励下,元叙事者不禁幻想狂乱的人物都能成为温婉的律吕,共同奏响和谐的乐曲。但“转念一想”,他又有些垂头丧气,因为“在男一号的身上……我们会嗅到交响变节者的气味”。“男一号”(比拉奎)本是一个内心众声喧哗、外表形象不定的角儿,又有轻易变节的品性,怎能担当作为“律吕”之本的“凤之鸣”的重任呢?倘若他只扮演“蕤宾”或“无射”的角色,甚至身兼二职,那元叙事者也尚可将就,因为“男一号”至少没有“乱性”——“蕤宾”和“无射”皆为阳性,属“六律”。
但“凤凰和鸣”依旧是不可触及的幻想。末了,元叙事者自觉无望,语气极尽调侃:“男一号”“倒不如给双性的隆起配上林簇”。“双性的隆起”所指不明,但这一幻象可能脱胎于“凤凰”的简称“凤”(雄为凤,雌为凰),即为雌雄合一、阴阳同体(androgyny)的“梦意象”,表属性混杂、毫无秩序之意。“林簇”(“Great Iron of the Woods”)也并非笔误,而是贝克特生造的术语,应为“六律”之一的“太簇”(“the Great Steeple-iron”)和“六吕”之一的“林钟”(“the Bell of the Woods”)缩略而成,即“雄鸣”和“雌鸣”的混搭,也表双性同体之意。两个“梦意象”叠加起来,表骚动不安、秩序混乱。在贝克特笔下,“凤凰和鸣”奇异地成了“最令人遗憾的数个音符的同现”(Beckett,1996: 11),这和他挪用中国文化的方式有关。在直译“十二律吕”的过程中,贝克特灵光闪现:那些术语充满了异域色彩,究竟指代怎样的乐音那无关紧要,关键是它们全都包含了视觉意象,罗列在一起即制造了一个意象的漩涡;虽无意响应“意象派”领袖庞德的号召,他却正可借此表现自己的“狂乱思想”。因此挪用中国古代音律时,他撇开了听觉,只取字面意义,即音调名称所含的视觉意象,并借此开展文字游戏,表示对业师“文字革命”的效忠。于是,《春梦》中就有了“林簇”这类比单个“梦意象”更令人不知所云的短语。
在《春梦》中,贝克特还提到了“[欧洲]青蛙和秧鸡唱出的中国音律”(S. Beckett,1996:70),以及“克里斯托弗·伶伦”和“竹管吹奏的《扬基佬》”(S. Beckett,1996:178)。可见,在他创作《春梦》的过程中,中国古代音乐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且常和西方的同类典故混杂一起。但只有在这两段文字中,“伶伦制律”、“孔子击罄”和“凤凰和鸣”这三个中国故事才得到了最充分的挪用。虽然情节中断了,但《春梦》却因此获得了显而易见的互文性和元小说性。这两个有卖弄学识之嫌的段落,是贝克特“狂乱思想”的充分体现,也是后来的实验小说《瓦特》末尾的“补编”和小说三部曲中层出不穷的互文片段的前身。在此,贝克特不在乎问题的解决,只关心问题的描述,有些“傲气”地拿他国典故显摆。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春梦》是挪用中国文化最多、最充分的,随后,他就开始背离乔伊斯“文字革命”的道路,实行“极简主义”,绝少借用作为外部世界和业师影响的痕迹的文化典故和生僻术语,因此在其后续作品中,中国文化愈来愈难觅踪影。总之,《春梦》对中国文化的挪用展现了贝克特作为“艺术家年轻时的画像”。26岁的他还沉浸在“全知全能”的境界中,远没有找到“无知无能”(McDonald,2008:15)的道路。他后来的“极简主义”倾向和“东方主义”(Lin Lidan,2010:281)没有直接的关联。
Ackerley,J.&Gontarsky,S.E.2004.The Grove Companion to Samuel Beckett:AReader’sGuide to his Life,Works and Thought[M].Grove/ Atlantic,Inc.
Albright,D.1999.“Beckett as Marsyas”[A].Samuel Beckett and the Arts:Music,Visual Artsand Nonprint Media[M].ed.Lois Oppenheim.New York:Routledge.
Beckett,S.1996.Dream of Fair to middling Women [M].London:Calder Publications.
Drake,J.2008.Building Castles in the Bog:Fantastic Fict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Irish Mind [M].New York:New York Univ.Press.
Lawlor,S.2006“Juggling like confucius on cubes of jade”[A].International Samuel Beckett Symposium in Tokyo[M].http://www.waseda. jp/prj-21coe-enpaku/temp/samuel_html/en/ schedule/1001/LAWLOR.html.
Lin,Lidan.2010.“Globalization and post-orientalism: the chinese origin of samuel beckett’s fiction”[A].《英美文学研究论丛》(11)。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Lin,Lidan.2010.“Chinese usic as a arrative odel:theaesthetics of Liu Liu and metafiction in samuel beckett’s dream of fair tomiddling women”[A]. English studies:a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J],Vol.91(3).The Netherland:Routledge.
McDonald,R.2008.Samuel Beckett[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and Education Press.
陆建德,2001,“自由虚空的心灵”[A],《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曹 波: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
通讯地址:410081长沙市麓山南路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3-01-1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贝克特‘失败’小说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编号:12FWW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