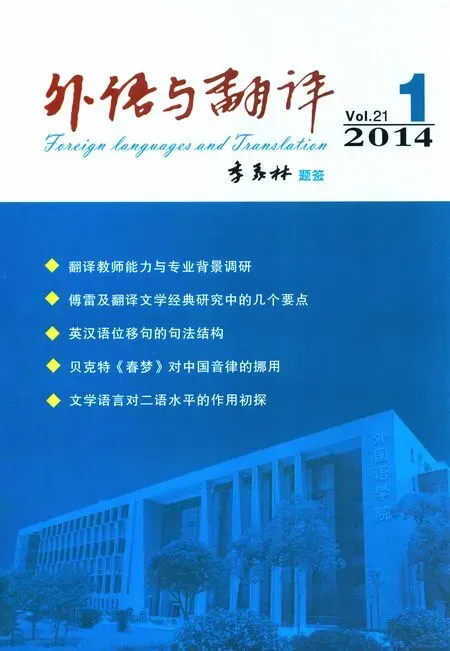处境、主体间性、社会一致性及作为世界经验的语言
——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与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思想共核
2014-03-21周晶
周晶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处境、主体间性、社会一致性及作为世界经验的语言
——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与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思想共核
周晶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从人的历史处境来探讨理解问题的本体论哲学。认知社会语言学是从人的社会文化处境来探讨语言、认知和意义的语言学研究范式。哲学诠释学的基本思想,如理解的历史视域、视域融合、语言创造社会一致性、语言与人类世界经验的同构关系等同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基本思想,如语言与认知的文化视域、语言与认知的主体间性、语言与社会的辩证关系、语言对世界的建构产生共鸣。哲学诠释学关于语言、理解及意义的哲学思想对于认知社会语言学范式下的语言变异研究和话语研究等具有元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哲学诠释学;认知社会语言学;理解;认知;语言
1.引言
哲学诠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开创的诠释学流派。伽达默尔批判了精神科学在自然科学模式影响下排除理解中的主观因素以追求纯粹客观解释的方法论思想,从存在的本体论角度重新评价了理解的历史性,并提出了“视域融合”的理解观,其思想在当今语言、文学、艺术、美学及跨文化研究领域弥足深远。认知社会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产生社会文化转向的一个新的研究范式。该范式结合了语言研究的认知取向和社会视角来解释意义及语言变异。在对语言的探讨中,哲学诠释学与认知社会语言学都对人存在的基本事实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这使得哲学诠释学与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基本思想呈现出令人振奋的一致性。伽达默尔(1999)后期的诠释学思想强调了语言对社会一致性的创造,从而使历史性与社会性的联系更加明确化。理解和诠释无疑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认知活动。从哲学诠释学的理论中,我们不仅可以解读其同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共同内核,还可以获得对于认知社会语言学这个新范式下的语言变异研究和话语研究等领域的元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2.哲学诠释学
诠释学是作为一门研究理解和诠释的学科发展起来的,其最初的形态主要包括以考证古代典籍的语文学问题为主要目的的文献学,和以解释和阐发《圣经》内容为目的的神学诠释学。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将诠释学的理解和解释理论系统化。在他们的推动下,诠释学成为精神科学的方法论而进入哲学领域。这一时期的诠释学称为古典或传统诠释学。存在哲学家海德格尔把理解概括为人在生活过程中的自我理解过程,并主张从人的存在方式来把握理解,从而使诠释学由方法论转变为本体论哲学(Gadamer,2007: 90)。伽达默尔秉承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转变,把诠释学进一步发展为哲学诠释学。哲学诠释学是把理解作为人与世界之间最基本的状态和关系来探讨的,其全部问题就是在探讨理解问题。哲学诠释学关于理解的主要思想包括理解的普遍性、历史性和语言性。
(一)理解的普遍性
近代西方哲学强调人的存在以意识和理性为先,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经典命题即是这一观点的典型表述。从这一立场出发,理解就是主体意识对客体的内容、性质和意义等的把握或认识。海德格尔以“我在,故我思”逆转了笛卡尔的经典命题,宣称作为此在的人及其存在先于人的思维、意识、感知和认识(刘放桐,2006:491)。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提出,理解是构成此在(人)的要素之一,是此在的存在模式,是人的一切活动,包括认识活动的基础。以人及其存在为思维、意识、感知和认识活动之根本成为海德格尔的理解之本体论的思想基础。人因其存在条件而具有先验的、前意识性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得以进行其他认识活动。因此,从人的存在来把握的理解具有先验性和前意识性。
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的思想,把理解概括为人与世界的一切关系,并提出理解的过程发生在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其哲学诠释学的任务就是要通过研究和分析理解的种种条件与特点,发现一切理解模式的共核,说明一切理解的基本条件,论述作为此在的人在传统、历史和世界中的经验,以及人的语言本性,最后达到对于世界,历史和人生释义的理解和解释(涂继亮,1996:398)。
(二)理解的历史性
在哲学诠释学中,理解的历史性成为基本的诠释学原则(伽达默尔,1999: 342)。伽达默尔(1999:354)着眼于人存在的基本事实提出并论述理解的历史性:人总是存在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中,理性依赖于它所处的给定的环境。这些因素总和起来就构成了“传统”与“成见”。理解的历史性就从传统与成见对理解的制约中具体体现出来。伽达默尔以作为历史流传物的文本为例来阐述理解。虽然理解者往往被等同于文本读者,但文本具有双重身份——文本首先在其作者理解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继而才成为读者理解的对象。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把作者和读者在理解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地主体化。伽达默尔之前的古典诠释学家如施莱尔马赫等主张,由于读者和文本之间的时间距离,读者主观的成见和误解不可避免地对理解产生消极的干扰,因此他们宣称诠释学的任务就是摒除理解(者)的历史性干扰,以把握作者的原意,获得关于文本的客观历史事实。而在伽达默尔看来,如果承认作者总是处于其特定的世界中,总有其不容忽视的历史特质,那么,没有理由不承认,读者也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处于一定的世界,他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也是无法消除的,没有理由只承认作者的历史性而要读者否认自己的历史性(Gadamer,1989:352-355)。伽达默尔批判了古典诠释学的不合理成见,并从理解者和理解活动的历史处境为理解的历史性辩护,同时也为作者与读者的主体性辩护。在这里,伽达默尔首次将读者提升到与作者平等的地位。如果说古典诠释学的诠释原则是消解读者的主体性,那么哲学诠释学的诠释原则就是同时尊重读者和作者的主体性。
(三)理解的语言性
在哲学诠释学中,理解与语言是同构的:理解过程就是语言解释过程(Gadamer,2007:90)。这样,理解集语言性、历史性为一体。顺着这一逻辑,我们不难领会伽达默尔对语言—传统与成见的关系的洞见:传统与成见的影响从语言中发散出来,因而理解的历史性通过语言实现和体现,语言、传统与成见融为一体,语言是对传统与成见的承载。因此,语言使用者及以语言为媒介的理解活动都具有特定的历史视域。
伽达默尔批评了从古希腊时期对语言的完全无意识开始一直走到近代把语言贬低为一种工具的传统语言工具观。语言工具观将人与世界武断地二元对立化为主体—客体,世界成为人可以置身其外来观察和言说的对象。伽达默尔指出,语言之所以不等同于工具的原因是“它并不能像工具那样能够离开使用而存在,也不存在外在于语言世界经验的立场,似乎可以从此出发,把语言作为对象。”(伽达默尔,1999:578)人类的世界观、世界经验以及人类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在人类使用的语言中显现出来。
3.认知社会语言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以经验主义(Experientialism)为哲学基础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主要结合语言现象来论证认知的体验性这一普遍特征。在这期间,大量基于不同语言类型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也注意到语言/认知同社会文化语境的共变关系。但由于理论和方法上的局限性,传统认知语言学对这种共变关系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基于个体大脑中的概念化和认知,社会文化层面的认知被等同于社会变项直接作用于大脑而形成的认知表征(Harder,2010:59-60)。按照这一思维推理,社会/文化共同体的个体认知彼此完全相同,个体认知表征了集体认知,社会文化认知研究实质上只是个体认知理论的扩展(同上)。
二十一世纪初,以Dirk Geeraerts为首的欧洲认知语言学派从基于用法的立场呼吁认知语言学研究将其认知取向同社会变异视角相结合,自上而下地考察社会语言和认知系统对个体的认知及言语行为的规范和塑造。Geeraerts(2005:183-184)指出,个体认知同社会规范之间存在辩证互动关系,认知语言学研究有必要把认知取向同社会视角结合起来,阐明这种辩证互动关系。在欧洲认知语言学派的倡导下,以认知社会语言学(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命名的第十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于2007年在波兰克拉科尔召开,认知社会语言学正式确立为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与传统的认知语言学研究相比,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把语言、认知和意义研究的眼界从大脑之内转移到大脑之外,将离境化的语言和认知研究重新语境化,从关注语言和认知的普遍性转向关注语言和认知的社会变异,从关注个体层面的认知转向关注社会互动中浮现出的社会文化认知及其同个体认知的辩证关系。这些共同的信念系统使认知社会语言学成为二十一世纪认知语言学的一个新的研究范式。
目前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将语言研究中的认知取向同社会变异视角相结合:1)认知的社会文化取向,这主要体现在语义和言语变异研究、语言与认知文化模式研究、社会意识形态研究(见Kristiansen&Dirven,2008;张辉周红英,2010),这类研究基于社会/文化认知解释词汇语义、语言变体的意义和用法特征,包括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话语特征;2)语言变异研究的认知取向,主要体现在基于词汇概念特征同社会变项交互作用下的变体/方言词汇及词汇-语义变异研究、基于语言内外因素交互作用下的变体/方言的构式变异研究和基于社会因素同认知的交互作用下的语言态度研究(Geeraerts,Kristiansen&Peirsman,2010),这类研究致力于把传统社会语言学对社会因素同语言变异之间共变关系的社会决定论解释深入到社会文化认知层次(见周红英,2012)。
4.哲学诠释学与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思想共核
4.1 “处境”与前概念
在对理解和语言的探讨中,哲学诠释学与认知社会语言学都以主体存在的“处境”为出发点。基于特定的处境,理解和语言活动首先为某种先于人存在、并注定为人所继承的“前概念”所把握。
哲学诠释学的出发点是理解者的历史处境(historical situation),具体表现为先行给定并为理解者所继承的传统与成见。传统与成见是人作出理性认识的基础(Gadamer,1989:282),因而也是人的历史继承性和历史连续性的根本。伽达默尔关于传统与成见的观点来自于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提出,理解基于先于理解者存在的“前概念”,包括:1)先于个人存在的文化习惯,即“前有”,包括理解者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传统观念,风俗习惯,以及该时代的知识水平,精神状态,物质条件等;2)预先存在的概念系统,即“前见”,规定理解的特定观点或视角;3)预先存在的假设,即“前设”,有了前设,理解者才把某物“作为”某物来理解和解释(伽达默尔,1999:341)。这些“前概念”是特定历史处境中的共同体的固有属性,为理解者所继承并在理解活动中起到不自觉的“筹划”或者说“期待”作用。伽达默尔强调“处境”与“前概念”意在突出人的存在和理解的历史性。哲学诠释学对理解的定位超越了理解者的主体性而着眼于主体存在的历史性:理解基于前见,而个人的前见比起个人的判断来说,更是个人存在的历史性(伽达默尔,1999:355)。
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的出发点是语言、认知及身体的社会文化处境(Bernárdez,2008:149)。对社会文化处境的关注可以追溯到以维果茨基为首的苏联心理学派、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行动理论及法国社会学家波迪厄的“惯习”理论。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强调语言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实践中的生活形式(Zlatev,2003: 306)。对社会文化处境的普遍关注也成为促进认知语言学社会文化转向的重要因素。
资料显示,Zlatev(1997,转引自Bernárdez,2008:1)首次将“处境”(situatedness)概念引入认知语言学,呼吁关注身体经验、认知与语言的社会文化属性和范畴特征。从人作为社会-文化成员的存在处境看,社会互动是语言和认知活动进行的主要方式(Bernárdez,2008:150)。从个体间反复的社会互动与磋商中浮现出集体共享的语言和认知系统即文化认知(Sharifian,2008:111)。“浮现”是自下而上、从个体到集体、从特殊到一般的运作过程。浮现性还意味着,共享的语言和文化认知在文化社团成员间的分布是非均质的。由于个体认知不是相互的镜像映射,从个体间的互动中浮现出来的文化认知具有动态性、开放性和适应性(Sharifian,2009:166)。在忽略“文化”与“社会”这两个概念范畴差异的条件下,“文化认知”同“社会认知”这个社会心理学概念基本对等:社会认知是社会共同体的集体认知表征系统,从社会互动中产生,经历了概括、适应、离境化和规范化,最终形成超越具体语境的、为全体或大多数成员所共享的图式化社会认知结构(van Dijk,1990:164),并在具体语境下的心理模式建构中实例化(van Dijk,2009:68)。在表现形式上,社会认知包括社会的定式(stereotype)、民族成见(ethnic prejudices)等(同上)。
文化认知形成于长期的历史过程,并同时是一个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的范畴(Bernárdez,2008:150)。每一个个体自出生起就属于特定的文化范畴,其言行思维为特定的文化认知所规范:从社会互动中浮现出来的文化认知充当文化成员思维和行为的主要锚点,甚至升华成一个统一的世界观,表现出认知的集体性,使文化成员在社会互动中有统一的思考方式甚至思想(Sharifian,2008:118)。正如传统与成见为理解提供“前投射”或“前概念”、“前意识”,文化认知为具体认知事件提供前概念,为认知主体提供“对世界开放的倾向性”和对意义的预期。从哲学诠释学的理论看,理解是历史的效果。文化认知对具体认知活动也起着“效果历史”的作用——伽达默尔用“效果历史”这个概念来指传统对理解所起的“前概念”作用。伽达默尔(1989:268)对效果历史的评价同样适用于文化认知:“在一切理解中,都有这种效果历史的力量起作用,不管我们意识到它还是没有意识到它。”
对身体、语言与认知的社会文化处境的关注将认知社会语言学的语言认知研究从理想化的大脑转向认知主体存在的基本现实,也使认知社会语言学具有了本体论和诠释学的性质。在这一视角下,语言已不是工具性的符号系统,而是包含了特定前概念的“本体论视域”。前概念是特定历史文化经验与知识的积累、传递和应用,通过语言而到达主体,并规范着主体的思想和行为。对“处境”的认识意味着对人类语言及认知的特殊性、多样性和变异性的认识,也意味着对社会/文化身份的认识。这正是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不同于传统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van Dijk,2009:32)。
3.2 视域融合与主体间性
哲学诠释学将理解定位为主体间性的视域融合过程。主体间性的理解产生主体间性的意义,也解释了语言及其视域的历史性和动态开放性。语言习得的个体发生学研究以及基于用法的语言研究使传统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从个体转向特定社会文化处境中的社会互动,主体间性也成为认知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核心概念。
处于特定历史处境中的人从特定传统与成见中获得前概念,产生看问题的特定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受到了历史视域的束缚而不是自在思考的主体。哲学诠释学对视域的强调不是为了凸显“克服理解者自己的视域、以真实把握被理解者的原意”的方法论。恰恰相反,哲学诠释学主张,理解并不是理解者完全附从于被理解者的视域,也不是理解者完全坚持自己的视域,而是双方视域的交互作用,伽达默尔称之为“视域融合”(Gadamer,1989: 305)。融合的结果是产生超越双方原有视域的新视域。与施莱尔马赫把理解定义为理解者单方面产生的心理学移情过程不同,视域融合的理解实质上是一种(具有时间距离的)主体间性对话与交流:处于不同历史条件的理解者与被理解者,自我与他者,过去与现在对话,并在其中实现交融与统一;公共的语言,公共的视域从中浮现出来并获得主体间性。而意义也成为主体间性的产物:理解的标准不是恢复作者的意义,而是发现共同的意义,即与解释者一起分享的意义(洪汉鼎,2001:213)。在主体间性的理解中,视域以及包含视域的语言在过去与现在的融合中永远处于运动而具有历史性和动态开放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分别以Chris Sinha与Michael Tomasello为代表的发展心理学、发展人类学研究从社会互动及主体间性来探讨语言与认知(Harder,2010:71)。Sinha(2000:163-183)认为,个体的认知表征在个体与(包括其他个体在内的)环境的互动中形成并发展。显然,Sinha的认知观超越了个体的认知系统本身而以人与人及世界的社会互动为核心因素。在社会互动中产生并伴随个体成长的一个必然要素就是主体间性。Michael Tomasello在儿童语言习得研究中提出,人类得以交际的一个重要能力就是理解他人意图,以达到共享这一意图、顺利进行交际的目的。理解他人意图是一个主体间性的认知活动。婴儿在对他人的关注中发展出了共同注意力(joint attention)的能力,这也是婴儿在其成长的社会活动中发展主体间性的表现(Harder,2010:70-75)。Chris Sinha与Michael Tomasello的社会互动和主体间性理论为认知社会语言学的主体间性语言与认知研究奠定了发生学基础。
社会互动就是语言、认知融合的主体间性过程。从存在的基本现实看,认知主体是社会人而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存在的,社会互动是人的存在方式(Bernárdez,2008:150):从一开始,互动就是在参与者不断对对方作出设想的过程中进行的,语言与认知活动实质上是不同主体间的互动、磋商与融合。从这一视角看,意义不再是主体的主观心理活动,而是不同主体间的认知协同的结果(Harder,2010:87)。社会语言系统和文化认知本身也是从个体间语言和认知融合中浮现出来的主体间性产物,文化认知更是一种浮现性(所谓“浮现性”,即共享的语言和文化认知产生于个体之间的社会互动过程,而不是所有个体语言或认知之和(Harder,2010: 166))的文化视域,制约着文化共同体认识世界的方式。文化认知作用于互动中的个体,在具体语境中为个体的行为(包括话语)所实例化(Sharifian,2008:122;Harder,2010:190;van Dijk,2008:71; Fauconnier&Turner,2002:72)。从这一认识出发,认知社会语言学将基于特定认知模式的社会文化实践也纳入研究范围(Harder,2010:391),具体地说,就是在作为社会文化实践的政治、商业、教育等各类话语中探讨浮现性社会/文化认知及其对个体认知及言语行为的塑造,探讨社会/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认知表征如何在具体的语境中实例化,以及在社会/文化认知提供的“前概念”下话语参与者如何在具体的语境中建构主体间性的意义(见Kristiansen&Dirven,2008)。另一方面,文化认知在与个体认知的因果循环作用下具有动态开放性和对不断变化的历史及社会文化环境的适应性(Sharifian,2009:166)。而现存的语言系统也总存在一定的空间来适应新的文化认知,最终促进语言的变化和发展,这表现为语言的共时与历时变异(Frank,2008:243)。
哲学诠释学的视域融合理论通过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流实现了主体间性的理解并产生共享的视域和意义。这里,理解更是人与世界中的他人的基本状态和关系。在理解中融合而浮现出来的语言及其视域永远处于运动中,具有历史性、动态开放性、变异性和适应性。主体间性——而不是个体的大脑——也是认知社会语言学解释语言及认知的发展、变异及意义的重要因素:语言首先是语言使用者参与到与他人互动中的社会行为,而不是抽象的系统。语言中发生的调整、变异不是在语言内部完成的,而是在使用者的社会互动中实现的,是主体间性的产物。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模式,不是心理分析中使用的语言,也不是想象的,没有歪曲的理想化语言,而是在使用者的生活世界的理解过程中实现的活生生的语言”(Gadamer,2007:91)。认知社会语言学主张,自然发生的语料是最基本的现实材料,社会互动是社会语言变异的解释因素。传统认知语言学研究关注个体大脑中的概念化,把社会/文化认知看成是社会文化语境因素直接作用于个体认知的结果,其后果是将个体理想化、均一化,产生了在社会文化共同体中均衡分布的社会文化认知表征,因而无法对社会语言变异作出合理解释;而社会互动中浮现出的主体间性社会文化认知则蕴含了认知的社会性和非均质分布性,从而为社会语言变异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3.3 语言与认知的社会一致性
在其后期论著中,伽达默尔提出了其诠释学思想的又一个重要主题,即理解和语言所包含的社会一致性(social solidarity)。理解和语言的历史性反映了哲学诠释学思想关于理解和语言的历史意识,而理解和语言的社会一致性则反映了关于语言与理解的社会文化意识。理解和语言创造的社会一致性成为哲学诠释学与认知社会语言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又一个重要共核。
社会一致性主要是一个共时性特征,也是对一个社会(共同体)的规定。伽达默尔(1999:567)提出,人在相互理解的生活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相互理解的过程是语言性的过程,在理解中形成的生命共同体也是一个语言共同体。语言永远在创造、承载一种统一的世界观,这种共享的、统一的世界观及对世界的理解,这个共同的社会世界使得社会一致性成为可能(Gadamer,2007:91)。人们并不是在语言共同体形成后才达成一致,一种真正的语言共同体中已经形成了一致:语言的一致,理解的一致,视域的一致(伽达默尔,1999:567)社会一致性蕴含了伽达默尔对语言同社会的辩证关系及语言的本质的看法:相互理解这个语言性过程(也是视域融合过程)通过创造统一的世界观、统一的理解和共同的社会世界而创造并规定着社会;社会意味着共同的语言、共同世界观和理解等一致性。社会预设语言的存在,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语言产生于主体间性的相互理解,而相互理解是一个生活过程,在这个生活过程中生活着一个生命共同体(伽达默尔,1999: 570)。语言的社会基础就是作为生活过程的相互理解和生命共同体。人工语言,例如秘密语言或数学符号语言都没有以在社会互动中结成的生活共同体作为基础,因而不是真正的语言(同上)。
认知语言学虽然从经验主义(Experientialism)的立场反对生成语言学的二元主义,但在大脑内部研究语言和意义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主流倾向。在传统认知语言学理论中,语言主要是大脑思维结构的体现,展现的是大脑的认知功能,是思维和思想的本质、结构和组织,反映大脑的某些根本性能和结构特征,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语言研究大脑的思维结构(Evans&vyvyvan,2006:5);语言作为提示促使大脑中产生意义建构即概念化,意义不在语言中而在大脑中(Turner,1991: 206);意义是大脑在语言提示下结合相关背景知识,进行一系列的认知运作而产生的概念化,是那部分存在于大脑并编码于语言的概念结构(Evans&vyvyvan,2006: 162);意义的建构就是大脑中的概念化过程(同上),比如心理空间的建构和跨空间的认知映射以及产生概念整合的意义建构(见Fauconnier,&Turner,2002),而大脑中唤起相关事件经验的框架图式帮助理解的过程也是意义建构过程(见Dancygier&Sweeter,2005)。
认知社会语言学基于人是群居的社会动物这一本性和事实,把社会作为语言、认知和意义最根本的基础。社会标志着一个生活共同体范畴。从共同体的形成来看,共同的身体经验固然是形成一个共同体的基本要求,而文化学习使得人类的归属感超越了对共同的直接经验的依靠,心理上的认同,包括共同的认知观念,想象等,比之更加重要(Harder,2010:416)。人存在的基本方式——社会互动不仅产生共同的身体经验,更重要的是,社会互动产生浮现性的社会语言系统(Frank,2008: 243),以及以同样的方式浮现出来、并蕴含于语言系统中的文化认知,包括特定文化的范畴、图式、隐喻概念化及视角倾向性等(Shrifian,2008:123)。共享的语言和认知系统使个体之间获得心理的认同而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并从思想和行为上规范、约束着这个共同体。文化成员的生活就取决于对意义的共识和分享(Harder,2010:4)。
基于语言和理解创造社会一致性这一思想共核,哲学诠释学与认知社会语言学都主张,社会并不是个体的简单相加,而是由一群人通过长期共同的生活过程逐渐形成语言的、理解的、认知的和意义的一致性所决定的。这是社会意义上的种群同生物学上的种群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也是语言与其他符号的区别之所在。不同的生活过程产生了不同的语言(文化)共同体。
3.4 语言与世界的关系
在哲学诠释学中,存在、理解、语言和世界是同构的。“语言地被表现并被把握的世界,并不像科学的对象那样在同一意义上是自在的和相对的,它不是自在的,因为它不具有对象性的特性……”(伽达默尔,1999:456)。世界不是作为语言对立面的客观化对象,语言也不是对客观世界的镜像反映。世界“总是已被语言的世界视域所包围。”(伽达默尔,1999:575)绝对客观的世界是不可能被理解的,因为它无从进入人的意识,不是哲学诠释学意义上的存在。世界是从特定的存在条件、特定视域来理解的世界,并以语言的方式被呈现。语言、理解、世界经验和存在浑然一体。哲学诠释学中,语言、理解、世界经验和存在的同构关系消解了古典诠释学中语言与人、世界与人以及语言与世界的对立二分。“语言并不是人可以随意处置的工具,因为根本不存在外在于语言世界经验的立场,似乎可以从此出发,把语言作为对象”(伽达默尔,1999:578)。语言带着特定的历史视域呈现世界经验,从中可以窥见主体的存在特征。
认知语言学从一开始就宣布以体验性为哲学基础(Lakoff,1980:231):语言从人类与(物理及社会)世界的互动中产生出来并反映世界。另一方面,语言不是对世界的被动映射,而是主动的认识。二十一世纪前的主流认知语言学研究站在反对自笛卡尔以来的二元主义的立场上着力论证认知的体验性基础和大脑-身体的连续性:人类的体验性认知——在人的身体与外部世界互动产生的基本感觉—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有意义的范畴结构和意象图式(赵艳芳,2000,33)——参与了对世界的识解。对存在的基本现实的理解使得认知语言学对体验性的认识从其物理和生理意义延伸到社会文化处境及社会互动,并开始关注从特定社会文化成员间的社会互动中浮现出的具有同构关系的集体认知和语言系统及其对于个体语言和认知的塑造。从认知社会语言学的视角看,不同的语言通过不同的内容和用法特征反映文化共同体对世界的概念化方式(Sharifian,2008:123)。特定的语言就是特定世界经验的文化建构,它代表了文化共同体识解世界的方式、视角或立场(Harder,2010:4)。
人类在主体间性的社会互动中实现理解,也创造具有社会一致性的语言、语言共同体和世界经验。历史和社会文化处境赋予语言和语言使用者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视域,也解释了语言与认知的特殊性、多样性和语言所呈现的世界的特殊性与多样性。与其说语言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不如说语言是语言共同体对世界经验的建构。人类多样性的语言构造了多样性的世界经验。把语言与使用语言的共同生命体及其社会历史文化处境和世界经验相剥离,只在离境化的状态中从形式上研究作为自在对象的语言,忽视语言传达的现实内容,就几乎忽略了语言最重要的东西。在这里,认知(社会)语言学与哲学诠释学的观点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立足地,从这里可以获得关于世界的绝对客观的真理;我们只能结合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以及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来对真理和意义作出解释(Lakoff,1980:218)。基于语言的实际用法,考察语言共同体如何基于特定的文化认知来建构其意义和社会世界,这也是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对这一理念的实践。
4.哲学诠释学对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意义
哲学诠释学关于诠释学的原则和思想对作为发展中的新学科的认知社会语言学也具有重要的元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当我们把伽达默尔所说的“时间距离”切换到“文化距离”,从历时维度转换到共时维度,我们就可以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理解外语使用的问题。伽达默尔很赞同洪堡特关于学习和使用外语的本质的看法:使用一门外语意味着使用者把自己的世界观,亦即自己的语言观带入所说的外语(伽达默尔,1999:565)。学会和使用一门外语,一是在自己的语言的世界经验之外获得另一种世界经验,同时我们并不抛弃自己原有的世界经验和视域,而是将其带入我们使用的外语中。从伽达默尔的观点看,这恰恰是诠释学经验的实现方式。基于一种世界经验、世界观和文化视域的语言在为新的使用者所使用的过程中对新的世界经验、世界观和文化视域产生适应,同时也产生变异,成为新的使用者所拥有的一种相对独立的变体。因此,语言变体研究应该具有诠释学性质。这意味着认知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变体研究应该具备诠释学的特征,即着眼于语境,采用以意义和认知为取向的解释方法,而不是对语言形式作单纯的描写。
在语言之外不存在观察和陈述世界的立场,在话语之外也不存在可以观察和描绘社会结构的方式。这是哲学诠释学的蕴含,也是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推论。从这一结论出发,不是社会世界决定话语,而是话语(语言)建构社会结构,建构世界经验。这一命题逆转了传统批判话语分析代表人物Norman Fairclough的社会决定论1,并重新将主体间性的语言和认知置于根本的位置。作为语言共同体唯一共享的现实,语言,或者说话语,使得我们所生存的这样一个有序的世界向我们呈现,这个世界就是按照语言共同体的方式而建构的世界(Teubert,2010:113-115)。认知社会语言学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特定的语言用法来考察特定的主体间性理解和认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构的社会世界。
哲学诠释学的视域交融理论主张,理解是主体间性的平等对话,即理解者的历史处境和被理解者的历史处境都应该平等地得到承认。在全球化语境下,“平等对话”的诠释学原则对跨文化交流及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当今全球化和跨文化交流加强的语境下,英语成为世界语言,西方意识形态大行其道,以美英为首的西方通过其大众媒体在世界范围主宰国际话语与信息的解释和传播,非西方世界的文化独立性和主体性地位受到压制,话语被曲解甚至话语权被剥夺。在这一语境下,揭示这一不平等现象,呼吁被理解者的主体性,呼吁国际话语理解和传播的跨文化意识应成为认知社会语言学具有时代特征的重要任务。
理解的主体间性要求解读异质文化话语要包容理解者的文化视域,也要包容被理解者的文化视域。这是一项基本的平等原则。由于非主流文化视域往往被忽视,主流话语分析已产生严重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并导致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和非主流文化的失语。在基于非洲英语的非洲文化模式研究中,Wolf&Polzenhagen(2009)批评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研究不关注非洲现实政治模式的文化根源而以现代西方政治理论来解读和批判非洲政治体制,并指出这实质上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在学术上的蔓延。在当今西方的批评话语分析已经成为强势的全球性学术话语,甚至被各国学者用于本土话语与文化现象的分析和批判,从而造成本土文化失语的情势下,中国话语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应当立足本土,使认知社会语言学的话语分析理论和方法与中国本土话语和文化资源接壤,而不是完全照搬西方为中心的西方语言分析理论和方法。
注释:
1 Fairclough(1992:63)提出,社会结构(比如阶级或其他社会关系,话语和非话语的各种准则、传统)对话语的各个层面具有塑造和制约作用,不同的话语事件因社会领域或体制框架的差异而不同。
Bernárdez,Enrique.2008.Collective cognition and individual activity:Variation,language and culture.In Roslyn M.Frank,Rene′Dirven,Tom Ziemke,Enrique Berna′rdez and Mouton de Body(eds.). Body,Language and Mind:Sociocultural Situatedness[C].Berlin/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137-169.
Dancygier,B.,&E Sweetser.2005.Mental Spaces in Grammar:Conditional Construction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vans,Vyvyan&Melanie Green.2006.Cognitive Linguistics:An Introduction[M].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Fairclough,Norman.1992.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Cambridge:Polity Press.
Fauconnier,Gilles&Mark Turner.2002.The Way We Think: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M].New York:Basic Books.
Frank,Roslyn M.2008.The language-organismspecies analogy: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approach to shifting perspectives on“language”[A].In Roslyn M.Frank,Rene′Dirven,Tom Ziemke,Enrique Berna′rdez and Mouton de Body (eds.).Body,Language and Mind:Sociocultural Situatedness[C].Berlin/New:Walter de Gruyter,215-264.
Gadamer,Hans-George.1989.Truth and Methodology [M].2ndrevised edition.Translation revised by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Marshall. London/New York:Continuum.
Gadamer,Hans-George.2007.A Gadamer Reader:A Bouquet of the Later Writings[C].(ed.). Richard E.Palmer.Trans.from the German.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Geeraerts,Dirk.2005.Lectal variation and empirical data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A].In Francisco J.Ruiz de Mendoza Ibáñez,M.Sandra Peña Cervel (eds.)Cognitive Linguistics:Internal Dynamics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raction[C].Berlin/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163-189.
Geeraerts,D.,Kristiansen,&Peirsman Yves.(eds.). 2010.Advances in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C]. Walter de Gruyter.
Harder,Peter.2010.Meaning in Mind:a Functional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al Turn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M].Berlin/New York:De Gruyter Mou-ton.
Kristiansen,Gitte&Dirven Dirven.2008.(eds).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Language Variation,Cultural Models,Social Systems[C].Berlin/New: Mouton de Gruyter.
Lakoff,George.1980.Metaphor We Live By[M].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harifian,Farzad.2008.Distributed,emergent cognition,conceptualization and language[A].In Roslyn M.Frank,Rene′Dirven,Tom Ziemke,Enrique Berna′rdez and Mouton de Body(eds.). Body,Language and Mind:Sociocultural Situatedness[C].Berlin/New:Walter de Gruyter,109-136.
Sharifian,Farzad.2009.On collective cognition and language.In H.Pishwa(ed.).Language and Social Cognition:Expression ofSocialMind.Berlin/New-York:Mouton de Gruyter,163-183.
Sinha,Chris.2000.Culture,language and the emergence of subjectivity[J].Culture and Psychology,2:197-207.
Teubert,Wolfgang.2010.Meaning,Discourse and Societ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urner,Mark.1991.Reading Minds:The Study ofEnglish in the Age of Cognitive Science[M].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an Dijk,Teun A.1990.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society[J].In D.Crowley and D.Mitchell(eds.). Communication Theory Today[C].Oxford:Pergamon Press,107-126.
van Dijk,Teun A.2008.Discourse and Contex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 Dijk,Teun A.2009.Society and Discours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lf,Hans-Georg&Frank Polzenhagen.2009.World Englishes:a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 Approach [M].Berlin/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
Zlatev,Jordan.2003.Holistic spatial semantics of Thai [A].In Eugene H.Casad and Gary B.Palmer (eds.).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Non-Indo-European Languages[C].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305–336.
洪汉鼎,2001,《理解的真理:解读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伽达默尔,1999,《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刘放桐等主编,2006,新编现代西方哲学[C].北京:人民出版社。
涂继亮主编,1996,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C].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张辉、周红英,2010,认知语言学的新发展——认知社会语言学:兼评Kristiansen&Dirven (2008)的《认知社会语言学》[J].《外语学刊》,(3):36-43。
赵艳芳,2000,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周红英,2010,音位变体对社会意义的建构.《外语研究》,(4):41-46。
周红英,2012,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最新进展[J].《外国语》,(5):85-89。
(周红英: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二系讲师,博士)
通讯地址:210000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2013-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