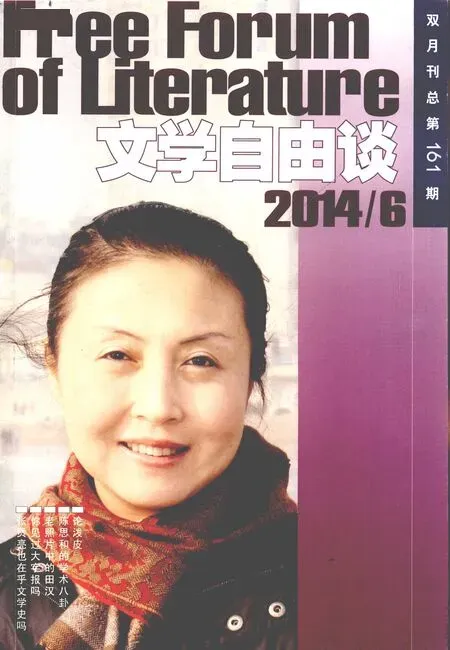写作者的怨气
2014-03-21周荣池
●文 周荣池
文坛是虚拟的江湖,毕竟也是人与关系的集合,写作者就是这个集合的基本单位成员。写作为文的人,大多能灵敏地感知世界,也往往因为这种心灵优势变得格外注意外部的变化与内心的感受,甚至有些敏感过度反而无所适从,本来对社会与事物的本能忧虑则变成一股平复不了的怨气。平日里读书,常常有这种感受,也许这也是自己敏感过度的原因。所谓怨气本是忧虑而来,这种忧虑如果适度倒可防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是过度的、又没有建设性意义的忧虑,则是需防止发酵蔓延的。
忧虑国情,但不知从理性做起
文人忧国忧民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从屈原“哀民生之多艰”,到范仲淹“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到陆游的“尚思为国戍轮台”,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直至近现代百年文人为国家民族呐喊甚至捐躯,忧国忧民已经成中国文人的一个思想传统。这当然是一个优良的传统,文人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可以举笔为文。这种强大有时候能够超过现实的力量,能够凝聚人心、激发斗志,甚而比坚船利炮更为强悍。然而,忧国忧民的这些文人们都有着一定的作为,如范仲淹对自己的忧虑绝非无的话矢,“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是其最为现实的实践方案。最绝望如屈原,自己的抱负不能实现,最终则投江以明志,这种高尚的做法虽然并不值得去效仿,但他确实用实际行动为自己文人身份的忧国忧民做了亲身的实践。这种忧虑是理性的,同时也并不失之虚妄。
然而,忧国忧民失去理性又不能踏实行动的现象也是常有的。笔者介入过一些网络文学群,这些虚拟的圈子借助了先进的网络技术,极大地延伸了文友的交流时空,让文坛内的各界交流更加便捷与广泛。在这些圈子里,笔者在了解和参与一些专业讨论的同时,也常常遇到一些涉及时政的讨论和段子,且这些讨论绝大多数都有着满腔的热忱,涉及面很宽泛,诸如民主法治建设、反腐廉政建设、城乡社会发展等等。文学本身涉及的范围就很广泛,这些热点与时政自然也应该是作家关注的对象,然而,在一些网络群中,笔者也常常见到一些转帖和言论,常常充满着对现实的不满与谩骂,或者有各种所谓的阴暗面、真相的大曝光等等,即便是传播这些内容带着美好的善意,却仍然让人感觉缺乏理性与风度。写作者的知识分子身份为我们从事的劳动树立了一个独特的界别,其言论相对于其他的劳动者对于社会的影响相对更为深远,应保持某种清醒与自律,理性与风度,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角色扮演好。我们忧虑国情与时代的诚心是真挚的,但不要被简单的现象与主观的感受所牵扯,要能够冷静地去分析问题。同时,我们面对种种社会现象,不是去做无谓的围观与谩骂,而应理性地辨析这些网络内容的真假,并躬身于社会实践之中努力地改善这些问题。如果力不能胜,至少可以独善其身,别做那种“拿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文人。
忧虑文坛,但不知从自身做起
文坛是文人自己的江湖,是我们的思考和文字支撑了这个虚拟而又庞大的存在。放眼古今与中外,恐怕眼下的中国文坛的规模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但正如任何一种繁华背后都会有无法避免的阴影,受到传统、体制以及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我们的文坛存在着许多的问题甚至是顽疾,以至于有人不断地进行着反思,也有人忧虑我们的文学实际上是在被边缘化,似乎正在朝着一条万劫不复的不归路上行进。
笔者以为,“文学的边缘化”是这么多年来,中国文坛的一个巨大的伪命题。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写作者正是被这个伪命题所干扰与牵绊着,总是满脸忧心忡忡地对着好似行将就木的亲人一样悲伤,而这些忧虑有很多几乎真的是“杞人忧天”,是无中生有的怨气。“文学的边缘化”的论调无非有两种证据,一个是巨著没有了,一个是巨匠没有了。这两个问题足见我们的文坛是浮躁的。我们总是盼望着回到那个全中国的人都在读文学的狂欢年代,期盼着中国出来十个八个诺奖得主,却从不冷静地想一想,一个国家都在读文学作品,这究竟是文学的荣耀还是国家的问题?作为艺术形式之一的文学,为什么一定要弄到全民为之疯狂的程度才满意呢?全国人民果真要是只读某几位作家的小说,窃以为这不是什么希望,可能是扭曲失常的现象。关于诺贝尔奖,我们扯着嗓子喊了多少年,现在应该心安了吧,事实上我们的文坛一直在被这个奖项绑架着。获奖前,获奖后,我们似乎并没有发现中国文学因为一个人的获奖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我没有对莫言先生获奖有任何微词,只想说的是,我们把这个奖杯看得太重了,却忘了好好写字才是要务。
忧虑文坛,是因为想着文坛更好,但有些写作者的悲观情绪太甚了,而且这种情绪并没有任何的正能量,没有能够在这些情绪之后积极地行动起来做一些实务,比如好好地研究自己作品存在的问题,好好地写每一个字,而不是整天对着电脑想,我为什么成不了大师,我的作品为什么成不了巨著?并且将这些苦恼都归因于所谓的“文学被边缘化”。
忧虑同仁,但不知从学理做起
文学批评是个体与个体、文本以及现象之间发生的文学活动,这种活动无外是对人的关注,即便是涉及作品与现象,也无法排除写作者对于同仁的关注。写作者之间的关注,在文坛有一个不得不提的话题就是“文人相亲”或是“文人相轻”。鼓励同仁的创作可以营造融洽和谐的创作环境,生发促进同仁之间共同进步的正能量;同时,批评要能够直陈同仁在文学活动存在的问题,并诚恳地提出建议与意见。
近年来学界越来越多地关注批评的道德、理论与秩序建设,对于那些毫无原则的老好人的表扬自然是没有什么市场了。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在批评活动中,有些批评是不以学理为基础,不以促进文学发展为目的的批评,这种看似烟火味很浓的批评表面上是忧心忡忡,更多的则是一种个人怨气的发泄。
在《文学自由谈》的显著位置,标记了该刊的选稿标准遵循“六不”思路,即:“不推敲人际关系,不苛求批评技法,不着眼作者地位,不体现编者好恶,不追随整齐划一,不青睐长文呆论。”其中的人际关系、作者地位、编者好恶等三方面的准则,正是切中当下批评界的弊病之所在。很多的写作看似严苛无情,是为追求真理而来,事实上是不以学理为标准,却在人际关系、作者地位和个人好恶上进行着推敲,这种推敲逻辑再严密,语言再精彩,又有什么意义?举一个例子,批评余秋雨曾经是一个风靡的事情,这几乎在一个时期形成了一种时髦,这里我不是想给这个公共事件下一个妄断,而是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有些批评者关注的并非是文本,而是“余秋雨的那些事”。“那些事”至今我也没有找到判断的依据,而且我也没有搞明白:余秋雨的妻子,他的经历乃至于其所出版书籍的版心的大小究竟和文化大散文的优劣之间有什么关系?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种脱离了学理依据的批评其实并不少见,我们倒真要在这些貌似大义凌然的文章背后去查一查,这些作者和被批评对象的人际关系到底是个什么状况。这样的批评是“棒杀”,这样的心思不是去帮助同仁进步,而是恨其不能立地灭亡的怨气。
忧虑自我,但不能从现在做起
搞文字的人喜欢敝帚自珍,天下从来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一点如果做得不过分倒也并不是什么错事,毕竟写作尤其是许多日常的写作多少有些“自娱自乐”的性质。但一些写作者在变相地膨胀着一种自恋的情绪,到处宣扬 “写作很苦逼”,“文学很弱势”,这又是写作者的一种怨妇式的情绪。
常说苦难出诗人,诗先穷而后工,现在的许多写作者却是因写诗而生苦难。总是将文学纠缠绑架于自身的实际生活之中。好像正是文学使得他的生活变得悲怆无比,这种怨气的由来正是很多的写作者并没有将文学当作一种追求,而是当作一种道路,说的白一点就是扬名立万、赚钱养家的道路。然而,这条路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走,写字的人似乎都可以走,但是想走好了走出效益来却不是那么简单。于是,便怨恨,怨恨世界的“无知”,怨恨读者的“浅薄”,这种情绪真的是害人不浅的,他们看似悲凉与无辜的现状背后,是一种很强烈的情绪在将这些写作者引入歧途。其实,文学从来没有契约保证我们一定成功。我们的选择与努力完全是自发的,也必须是自负其责的。当年曹雪芹写《红楼梦》,写到整天喝粥赊酒的地步,并不知道身后这部书会红到这种程度。很多时候,写作者的境遇与作品的境遇总是有相背离的,写作者应该建立一种良好的心态,正视文学与现实境况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文学不会因为个人的命运多舛而改变进程,所以,写作者也不要因为选择了文学而不能得道而归咎于文学。
有梦想是好事情,从文写作的人大抵是因为心里有梦,这比其他工作更需要心灵的品质。只是我们在有梦的时候,两脚要紧紧地踏在现实的泥土之上,多做些务实的事情,少一些无端的怨气,正如杨绛先生劝说一位业余作者的:“你的问题正是书读得太少而想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