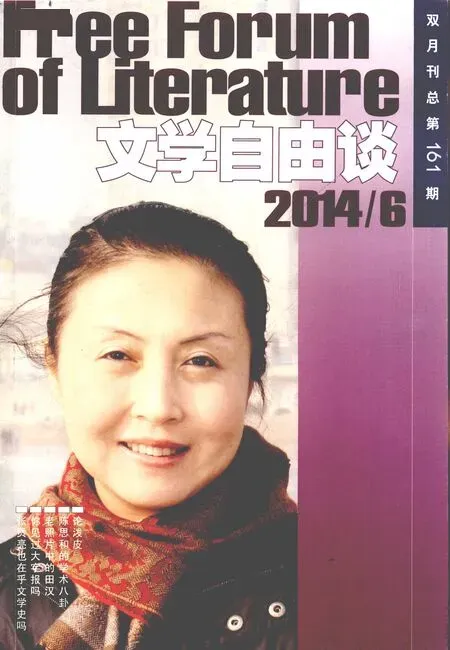《浮生三辑》后记两则
2014-03-21文/吴正
●文/吴 正
《浮生三辑》后记两则
●文/吴 正
“旧”后记
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当我登上耳顺之年的六十层高楼向下俯瞰时,整片的生命记忆竟都变得灰霭而温柔,边缘模糊,亮点不再,让人生顿生一种烟雨苍茫的背景上,有一条天际长河隐约流动而过的感觉,我知道,这便是我那朦胧的人生轨迹了。
这,就是我此时此刻在案前坐下,动手编排这本册集时的心情与目的:心情,为了感慨为了重温;目的.为了总结为了觉悟。在此文集中,之所以所有的篇什都以年代和月份的顺序贯穿起来,动机无非是为了展示我对自己生命轨迹的一种苦苦追寻,但有时也很无奈。
有时想想,当个作家也不能不算是件幸福的事:一点一滴,一字一句,每天,他将自己生命的每一寸推进都归流进了文字的河床中去,待到他老了,他或者可以在某一天溯源回归。在童年或少年的树荫下,他盘腿安坐在一块青苔茸茸的石板上,静静地垂钓一个下午连黄昏。而当那些濒于遗忘的往事突然活蹦乱跳地自他鱼竿的顶端腾空而出时,那份情趣和感动又岂是一个非作家者所能体念得到的?
其实,每个人的生命,自他呱呱坠地的那刻起,就注定会去走一段必然必定也是必行必经的路程。走过了也就走过了,忘却了也就忘却了,唯录下后重阅的感受恰如梦醒未醒时分,手握一把美妙的虚无;眶泪欲滴在微笑的余波中。什么样的形容都是苍白的,什么样的解释也都是徒劳;突然映入你脑屏的很可能是一句类似于“黄粱一梦”的成语,或者更甚——这是某段宗教意味极浓的偈语: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空空即色,难道你这日子串连日子的一生不是对此段经文的最佳诠释吗?
感谢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的L君和出版家C女士,有了他们的鼎力相助,才有了这本文册的问世。在这个拜金主义盛行,追名逐利不择手段的非常时代,不知道我的这些唧唧哦哦着深秋虫鸣般情调的散文作品能否为阅读者的心灵带来些许籍慰?
作者 2009年3月31日于上海寓所
“新”后记
花甲之年,即2008年盛夏,好友,社科院的L君,于其新版旧著问世之时,也向其书的出版商举荐了我,并嘱我自选一散文集,以备付梓。于是,便有了这部《浮生三辑》的诞生。书稿是有了,也交了,但黄鹤一去杳音讯也。事隔年余,才由L君婉言转告说:此集太纯文学了,如今出书须创利,而创利,要么内容抓人眼球,要么作家知名度妇孺皆识,此人两头不着岸,非也!此言伤是伤人了些,然毫不虚饰,切中肯綮,刀及要害,一针见血。我,不就是这么个人吗?在这么个文学必须与权力或类权力相结合才能彰显其影响力的时代,我,正如摇滚歌手崔健所唱的那般,“一无所有”。无权,无势,无背景;无学历,无头衔,无圈子,无组织可归靠,当然也无任何掌控之文学阵地可供投桃报李之用,偏还死心塌地咬定了“纯文学”这块硬骨头不放,绝无商榷之余地。再说,一老把年纪了,还有什么远大的文学或仕任前程可言?故,于此人身上押下投注,回报无期。如此一件“多无产品”,遭此冷遇,实属情理中事矣!
于是,文集之散页便堆砌在案头,蒙尘积垢,一过又是两年,而我,也已六十有三了。直到有一日。有一日,陈先法兄前来陋居叙谈,视及此稿,粗阅之下,便表示愿尽力相助。他是出版行家,理应明白个中因由,却能如此真诚,敢于承担,遂令鄙人感动不已。当然,后记之修改也就事所难免了。L君改成了先法兄不说,某出版社也改成了另某出版机构。如此这般,又过招了几个回合,先法兄大名没变,另某出版社则改为了另另某出版社,进而,另另某出版社再度易帜成了另另另某出版社。至于屡遭拒版的理由亦与北京方面的大同小异。于是就到了这一回,当我已六十有七,直逼古稀了。
期间,也不是没有过明白人指点迷津的。一说是当今出版世道,有一条路是永远畅通的:买书号出书。管他娘的纯文学俗文学,曲高和寡还是低级下流,只要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都行。法,或许也算是个法,坏就坏在我老甩不掉在小学堂里就念诵过的那几行诗的记忆。这是一位被关押在国民党大牢中的革命志士,在被要求写一份悔过书,便能放监出狱重获自由时写下的:让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啊/给尔自由!……少年时代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体系就是如此可爱而又可恨,执拗且无药可救。去与那个曾是不齿之徒的自己还是他人的影子打交道?俺不干!
二是,有人劝告说,如今的互联网,人人都上得——不是吗?虽说,这是片嘈杂不堪的大排档,本不应是个适合我等这般年龄与写作风格的作家们的登台场所,再说了,我对互联网知识之贫乏又几近于零。但毕竟,这是一条通往在遥远遥远处还存有一线依稀光亮出口的甬道,在热心青年朋友们的鼓励和相助下,我毅然上路了。在这片良莠不齐,生态杂交,有时疯长,有时荒芜,有时怪石峋嶙,有时绿洲盈盈的广阔虚拟世界之一隅,我也像社会上所有那些酷爱文学,却也找不到发表渠道的业余写手们一样,从头来过,你蹭我挤地摆设了一席摊位,叫卖自己的文学产品。但我仍是快乐的,自在的,心安理得的。至少,我可以不求人,活得有尊严,有自我。而在这片人熙人攘的表达空间,向我摊位流来的虽仅是一条涓涓细流,但他们都是些真心喜爱文学,不带任何功利企图的人们,这就够啦,他们不就是我要找的知音吗?就这么,我一篇一篇,一章一章,一首一首的剪贴,上传,不急不缓,不慌不忙。我像一尾小鱼,潜游在一口生态蓬勃的池塘的深处。我记起了法国诗人保罗说过的那句话:但愿我的诗能被一个人读一千遍,而不是被一千个人只读一遍。
那一日,先法兄再度屈临陋室,告诉我说,已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基本谈妥,他们愿出我的这本集子。我当然高兴啦,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写作者来说,纸质出版物的情结毕竟是深刻得此生都无法割舍的,一旦有机会,我那内心余烬未灭的希望便又会“死灰复燃”起来。余下的问题是:我的后记是否又要另易其稿了?但这次,我决定换种方式来处理。本来,这册集子所收的文篇,就是我六十数年来生命轨迹行进式的记录:有甜蜜的恋爱季,有美满的婚姻期,更有家变后,个人感受上的,近乎于“百年孤独”的绝望岁月,棘途漫长。然而,我的这次文集出版经历之本身不正也符合这一选稿标准吗?于是,在保留了的旧后记之后更续上了这篇新后记。
其实,此回出书的艰辛与曲折,不仅是对我,一个作家来说是空前的;它折射出的,同样还有出版系统自身面临的日益逼仄的生存空间。纸媒出版业面对这前所未有的挑战时,将如何自处?这是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向一切的曾经是辉煌者们提出的同一道难题。还是达尔文的那句话:适者生存。我们无法改变历史,只有历史来改造我们——当然,这些都是我,一个写书人的题外话了。
数易其稿的故事讲完了。但愿此回能梦想成真——中国宏伟的强国梦, 我们这些当作家的,也有我们小小的,谦卑之梦啊。
甲午年立夏日,识于沪寓。
《我不要你管》
狄 青著 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