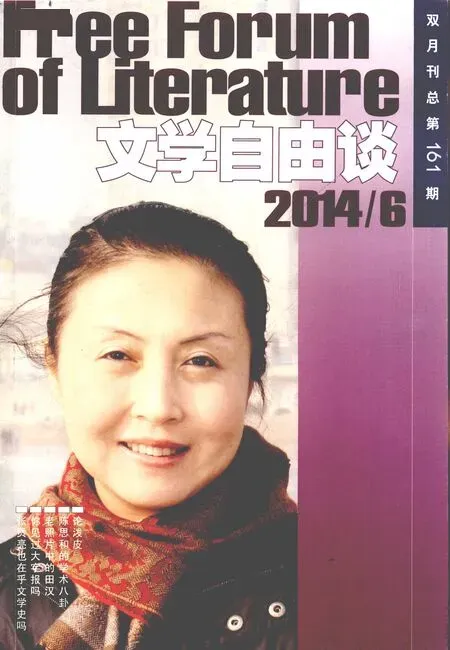无法拒绝(二题)
2014-03-21文/毕亮
●文/毕 亮
无法拒绝(二题)
●文/毕 亮
关于书的书
安妮·法迪曼说,凡是讨论书的书,我一向都难于拒绝。于是,遇到她写的《书趣——一个普通读者的自白》,我也就不拒绝了,其实也拒绝不了。
正如书名,这确是一本有趣的书。和其他许多关于书的书不同之处在于,它除了就书谈书外,谈得更多的是作者的家庭,而家庭也和书关系密切,“我的丈夫乔治·柯尔特和我用书来互相求爱,而且把两人的图书也结成了配偶”。
这样的生活是让许多爱书人艳羡的。这是最终的完美结局,而开始并不如此顺利的。安妮·法迪曼在本书第一篇《书的婚事》就写到了因为两个人把书结合起来,因为在书架上排列规则的分歧,“很少郑重考虑过离婚的事情,但这是其中的一次”。凡事,总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最后终于“我的书,他的书,都成了我们的书,我们是真正结婚了”。书是生活的见证。
真正的爱书人,在自己的书房大概总会有个特别的书架。乔治·奥威尔的特别书架上放的是装订成册的女性杂志。《书趣》的作者自也不例外,特别书架上是 “六十四本有关南北极探险的书”。更特别的是,安妮·法迪曼和她的哥哥,从女服务员的一张“先生,您决不要那样对待书”的纸条上,经过三十年,终于悟出了“爱一个人不止一种方式,爱一本书也不止一种方式”,而文章里提到的爱书方式,也确实让人见识大增。
当安妮·法迪曼和她丈夫乔治还不是爱人关系时,第一次互赠圣诞礼物就是书,当然少不了要题词了。作者在写 《扉页题词》,表面是在写题词,虽然披着“在藏书癖的等级中,这种文人交往的神圣遗留物,远远超过了书的其他因素”的外衣,实则是写爱情经历,“献给我亲爱的妻子……这也是你的书,我的生命也属于你”。这是作者得到的最美好的题词。所以才有“最美好的题词与最美好的情书一样,极少从家庭中流失出去”的感慨。
安妮·法迪曼的爱书,和从小家庭的熏陶不无关系,从小过着“浏览父母的书架便能开怀畅想他们的品位和追求,企图和弱点,比窥视他们的衣橱还要清楚。他们的书架便是他们的自我”的生活,待到自己长大的生活,也成了“住房越来越不像一个家,而越来越像一个旧书店”。
书太多,空间太小。有多少爱书人正在经历呢,作者在《首相的图书帝国》里提到的解决方法,这么多年过去了,可有人一试?“在我看来,十九磅旧书的美味,至少是一磅新鲜鱼子酱的十九倍。你过生日也许喜爱美食,可是我却宁愿要一本价值九美元,1929年出版,文森特·斯塔利特写的《花钱聪明,买书痴迷》。”
——好吧,又一本关于书的书。难道我们都是历史学家高华说的这种人:只有在书斋中面对那些泛黄的书卷才确定自己的存在。
年华重温忆旧书
安妮·法迪曼在主持《美国学者》杂志时,开辟了一个图书栏目,专门评论“重读的旧书”,每期都有一位著名作家选出一本二十五岁前读过的书(或一个故事,一首诗,还有人选了一本唱片集),在多年后重新阅读,记下的感受就是现在收在书里的文章。安妮·法迪曼说:“既阐明了书,又阐明了读书的人,至少两者同样重要。每篇文章都是微型的回忆录,所谈的话题动人心弦,往往是有关爱的变化本质。”旧书重温忆华年,又何尝不是年华重温忆旧书呢。
重温一本旧书,就是重温一段岁月,可以帮助一个人认识过去的自己。“一本年轻时读过的书是情侣,许多年后重读这本书,它便成了朋友”,这样的经历不知有多少人经历过,留意过?就如斯文·伯克茨在文章中写到的:书和回忆的力量实在厉害,能够在刹那间摧毁我们事先建立起来的任何防御系统。
有一年回老家,无意翻到书架上梁晓声的《人间烟火》,这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收有四个中篇的小说集,我都不敢相信曾被我如此认真地读过。这次大致地翻翻才发现几乎每页页眉页脚等空白处都做了笔记,有些页甚至是大段大段地用铅笔或圆珠笔工整地记下了当初的感受,这要是放到现在是不可想象的,这也另一方面说明了年轻时候的无书可读和读书之认真。在本书最后一页空白页上我用铅笔大大地写下了一句:“一本这样的书卖五元钱,是不是对这本书的侮辱呢?是不是对作者劳动成果的否定呢?”那时候的矫情已经不再,读书精神也难以再寻回。这本《人间烟火》购于2004年1月8日,十年过去,当年读得那么认真的四个中篇小说,早已忘得干干净净。再看那些激情四溢的眉批,真有说不出的感慨。
偶然想起的读书经历,正好印证了安妮·法迪曼的感慨:你打开一本平装书,书页边上爬满了笔迹,那是你早年写下的,如今已经不这样写字了。回忆就会猛然跳出来,就像你打开旧日的日记一样。当年要不是随手记在《人间烟火》的三言两语,多年后又怎么会记起那段读书岁月呢。这些文字,为一个人的阅读重建准确的编年记录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和第一手资料。
早年读到的书,至今难忘的,必是影响至深的书。比如戴安娜·卡普尔·史密斯由早年的一本 《北美洲东北部及中北部野花野外指南》而成长为自然作家兼插图画家。我也曾有关类似的经历,详细记录在《十七岁的一本书》中,在看《旧书重温忆华年》时又想到了。关于这些感觉,作为作家在文中都有写到,“重读一本书,能够体会到时间怎样给它不同的待遇,记忆怎样扭曲了它,我逝去的岁月怎样增进了对它的理解”,这是迈克尔·厄普丘奇在重读《所有民族的住所》时说的。
而阿利格拉·古德曼在重温《傲慢与偏见》时说得更奇妙,他认为重读的目的就是为了展现,文章就像编织物一样,多次阅读就能展现它各部分的不同脉络。然而文章每展现一次,在图书馆里,在床上,在草地上,读者的皱纹就增加一些。
增加皱纹的读者里,也有一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