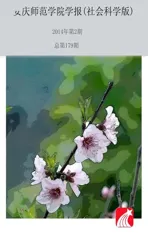物质·情欲·时尚: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文学的特征
2014-03-21吴春平
吴春平,张 俊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物质·情欲·时尚: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文学的特征
吴春平,张 俊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消费主义文学是消费文化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消费主义文学具有如下显著特征:一、迷恋于物质,醉心于商品,体现出强烈的物质化特征;二、突出“下半身”,强化性本能,表现出高调的欲望化特征;三、渲染小资情调、热心追逐时尚,呈现出奢靡的时尚化特征。消费主义文学是文学市场化的产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其负面影响也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消费主义文学;消费文化;物质化;欲望化;时尚化
消费主义文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关于它的确切内涵目前学界尚无权威界定。较为常见的理解是将与传统意义上的那些在明确的政治功利、社会责任和理性精神支配下创作出来的正统典雅、深邃精致的高雅文学或曰严肃文学相区别的,为适应市场需求而生产出来的通俗浅近、猎艳好奇、娱乐消遣类的文学统统划入消费主义文学的范围。这种将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的武侠、言情、警匪、刑侦、官场、玄幻、青春等五花八门的文学一网打尽的观点,一来显得过于宽泛,似乎使消费主义文学变成了通俗文学、大众文学的同义词或代名词;二来并不能突出这一概念的核心要义,所以,在这里我们取一种狭义的理解,即认为消费主义文学特指那种在中国开始步入消费社会后出现的,集中体现了消费文化特征的文学。这种文学聚焦于发达城市,主要以白领“小资”、都市“另类”或中产阶层的时尚生活为书写对象,多用一种夸张的手法去炫耀人物富足、奢靡甚至是放纵的生活,从而吸引读者,赢得市场。
消费主义文学是消费文化的产物。消费文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并逐渐波及和影响到经济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二战结束后,西方社会科技日新月异,生产迅猛发展,产品相对过剩。于是,传统的生产型社会开始步入消费型社会。消费社会的消费具有以下特点:首先,通过符号建立差异。即物只是消费的前提,而并非消费本身,物要成为“消费对象”,必须成为符号,符号的意义在于建立差异,以此将符号所代表的物品区分开来。其次,通过消费建构身份。此时,消费的目的并非以商品为对象,而是消费商品中所蕴涵的符号价值,对商品符号价值的消费成为人们身份构建的方式。最后,消费永无止境。由于对商品符号意义的消费是对欲望本身的消费,是借对物的拥有来确证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因而消费是虚幻的、永无止境的。与消费社会相适应的消费文化倡导这样的观念:追求体面的、奢侈的、无节制的消费,在物质享受和消遣的最大化中实现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正如后现代主义研究者迈克·费瑟斯通所概括的那样:“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1]在消费文化的引导下,消费主义文学应运而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提速,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发达地区尤其是开放都市呈现出明显的消费社会的特征。社会转型使原先贫穷时代所形成的道德文化观念日渐衰微,“一切向钱看”驱使人们开始寻找一种与商品社会相符合的自我认同方式。于是,消费主义文化乘虚而入,成为时代的文化新宠。在消费主义文化潮流的裹挟下,消费主义文学迅速生长、蔓延,并以异样的面孔吸引了一批追逐时尚的文学读者。纵观90年代以来在中国都市流行的消费主义文学,不难发现这样一些明显有别于过去文学的特征。
一、强烈的物质化
90年代以前的新时期文学,虽然因政治气候、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以及作家主观因素的差异而呈现出多样化的色彩,但有一点还是大致相同的,即致力于表现人的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作家讲述的故事要么与道德、理想、信仰、事业、爱情等崇高的事物有关,要么表现在动荡纷乱的社会现实面前人的困惑、迷惘、无奈和悲哀,要么去揭示人性的软弱、阴暗、贪婪和丑恶。总之,是“人的文学”。然而,在新崛起的消费主义文学中,我们却看到了一种另类景观:“物的文学”。在部分“生在红旗下,长在物欲中”的70年代后出生的作家眼中,物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再是人物形象塑造的必要的陪衬和背景,而是显赫地居于文学表现的中心位置,而作为精神存在物的人则开始退隐和“物化”,并沦为物的奴隶和商品的忠实信仰者。也许是女性对物有着天然的敏感和兴趣,一些女作家喜欢将目光对准有形的物品,尤其是有着知名品牌的高档物品,并细致入微地加以描述,几近痴迷。她们流连忘返于华美的家居、时尚的服装、昂贵的珠宝、精美的首饰、名贵的化妆品和可口的美食之中,她们关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寻求的不是精神的自由和解放,而是灵魂的退隐和情感的“物化”。比如,炫耀出场的“美女作家”卫慧在《上海宝贝》中刻意对自己居室里的“三德利”牌汽水、“妈妈之选”牌色拉乳、“德芙”巧克力、“七星”牌香烟,以及空调、唱片等物品进行展示,以显示“我”之物质生活之富有。再比如,颇具人气的网络写作高手安妮宝贝的代表作《告别薇安》,其中男女双方的网恋主要不是在情感和思想的交流中进行,而是在对物质的讨论中展开。她对他说她知道他喜欢穿什么样的衬衣、皮鞋、袜子,喜欢用什么样的手绢、香水,不喜欢用什么样的剃须刀,她还知道他“会把咖啡当水一样”,“她有很好的情趣和他谈论kenzo的新款香水”,而他则告诉她cappuciono的制作方法,可谓不厌其烦。女作家们不仅关注物和物的品牌,而且还关注物的出生地。陈丹燕在《慢船去中国》中以一种十分虔诚和惊羡的目光打量着物的天堂——纽约的街道:“全世界最奢侈、最时髦、最新式、牌子最好的商品,都云集在那些一尘不染的橱窗里,都在追光灯下闪着不可一世的光芒。意大利的珠宝,捷克的玻璃,西班牙的钻石,意大利的皮包,德国的皮鞋,德国的刀,法国的香水,法国的晚礼服,西班牙的酒,即使是一件百分之一百棉布的蓝色短裙,也散发着那种骄傲的光芒,即使,它们并不傲慢,它们在炫耀中默默释放吸铁石般的吸引力。”[2]272这些奢华的商品不仅品质高,更重要的是它们无一例外都来自发达的欧美国家,即使它们并不“傲慢”,其吸引力仍无可抵挡。有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说《慢船去中国》中的女主人公简妮当年对纽约的高贵的物品只有艳羡的份儿,那么,今天中国的富豪甚至大妈们在国际奢侈品市场上的阔绰消费则使一向有着优越感的傲慢的西方人惊羡不已了。
物可以简化和抽象为一种高级形式——金钱,对物的迷恋自然也可以简化为对金钱的迷恋。于是在另一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人物对金钱毫无掩饰的赞美和崇拜。晚生代作家朱文于90年代中期发表的一篇引起轩然大波的小说名字就叫《我爱美元》。作品主人公对长期以来被视为罪恶渊薮的金钱,而且是来自异己力量的世界头号强国的金钱表达了这样的渴望:“那种叫做美元的东西,有着一张多么可亲的脸,满是让人神往的异国情调。一张美元支票在半空中又化为更多的人民币支票,就像魔术一般,往下飘呀飘呀,我双手张开眼望蓝天,满怀感激地领受着这缤纷的幸福之雨。”[3]如此赤裸裸地赞美美元,既有悖于传统的价值观,又有丧失民族尊严之弊,因而,它遭到人们的强烈质疑和批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相似的情景在陈丹燕的《慢船去中国》中也可以见到:“曼哈顿带着挑逗的空气扑面而来,不由得让简妮想到钱。简妮在曼哈顿处处都能闻出美元的气味。钱在这里不光意味着消费,它更是一杆秤,可以衡量一个人的智力、勇气、耐力和运气,衡量一个人是丰富还是苍白、是自由还是局限、是刺激还是平庸,对简妮来说,能不能在曼哈顿感到理直气壮,自由自在,就是人生价值是否得到实现的标志。”[2]382可见,女主人公不仅在物质生存意义上对金钱加以认可,而且还将金钱提升到关乎人生价值能否实现的高度去加以神化和顶礼膜拜。此外,还有一些作家絮絮叨叨地讲述的底层小人物成长历史的故事也让人十分沮丧,因为其结果往往是单纯懵懂的主人公在平庸的世俗生活中被不断增长的物欲所打败,是超脱的精神对实在的物质的俯首称臣。比如,朱文颖在《高跟鞋》中通过一个出身贫穷的女孩安弟对艰辛生活的体验和感悟得出这样一个真理:金钱是这个时代最强大的东西,“她的目标也是明确的:她要有钱,强大,具有力量”。这不仅与十七年文学中以《青春之歌》和《红色娘子军》为代表的女性成长题材小说的主题——在男性英雄人物的指引下走向革命之路有着天壤之别,而且也与新时期以来同样是关注少女成长问题的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和铁凝的《大浴女》热衷于对父权神话的颠覆和拆解,以及陈染的《私人生活》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对隐秘的女性生命体验的惊世骇俗的揭示有着极大的差异。此类写作使女性既远离了国家、民族、历史等“宏大叙事”,与“大我”无缘,又告别了性别、女权、闺密等“女性叙事”,与“小我”无关,最后剩下的只是一个物化人,一个只关心物质和金钱的人。
纵观中国文学史,虽然也为“物”留有一片天地,但所写之物一般都是自然之物,如山川河流、松竹梅兰,等等。人们之所以取物,是取其蕴含的超越现实,超越功利的客观精神,以抒发情感,寄托情思,即所谓“托物言志”。但在消费社会,这一写作传统被打破。此时作家虽仍“取物”,但“物”已被置换为商品,是需要用金钱来购买的,而且这些商品与人格、情操无关,也不具有寄托情感和提升精神的意义,充其量只能给人带来物欲满足的快感。奉行物质至上、金钱至上的原则,人的物化和写作的物化同时推进,这表明文学已开始悄然由精神向物质滑落。这种滑落,既有进入消费社会的某种必然性,又与中国当下特定的国情和某种社会心理有关。社会转型时期,往往伴随着价值迷失、理想混乱和道德失范等精神乱象,以致人的精神无以寄托,于是物质便取代精神,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物化文学的招摇过市不过是这一时代情绪的如实记录而已。
二、高调的欲望化
性、欲望,自古以来就是文学表现的重要对象,无论在民间文学,还是在文人创作中,涉及性话题的作品都普遍存在。但受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道德观念的影响,人们强调的是“天理”,对“人欲”则基本持否定态度,所以,表现“人欲”的作品难登大雅之堂。久而久之,文学的惯例便形成了:正面人物,尤其是英雄豪杰一般都清心寡欲、坐怀不乱,而品行不端或罪大恶极之人往往是好色之徒。也就是说,欲望与人品成反比,欲望是堕落的代名词。尽管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学表现“人欲”也会形成一种风气,但就中国文学的主流而言,仍然是重“情”不重“欲”,重“灵”不重“肉”,到了“文革”时期,甚至发展到连“情”都忌讳的地步。进入“新时期”以后,“人的文学”开始回归。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为爱情正名,呼唤爱情,歌颂爱情之后,文学开始关注欲望,一些大胆涉及性描写的作品陆续出现。比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忆的“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和贾平凹的《废都》等。尽管这些作品曾招致过非议和责难,但应该看到它们并非为欲望而欲望,而是要借表现欲望来达到反抗政治专制,反省历史文化,开掘人性,揭示时代的精神乱象等目的。9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异军突起。以陈染、林白等为代表的女作家们以极其叛逆的姿态坦然揭示以往秘而不宣的女性复杂微妙的深层心理,尤其是性心理。比如,“恋父/弑父情结”、“恋母/仇母意绪”、同性之恋、自恋等,在文坛掀起轩然大波,这种对男性抱有明显敌意的女性情欲的表达同样也因挑战了读者的阅读神经而引起极大的争议和批判。但就创作意图而言,这些作者是想通过对女性个体生命欲望的表达来反抗宏大叙事,颠覆传统的男性中心话语,可以算是一种女权主义的诉求,而且,女性主义文学在描写欲望时,多少还有一些顾忌,难免遮遮掩掩、欲言又止。然而,世纪之交,随着卫慧、棉棉等70年代出生的“美女作家”们的炫耀出场,原先半遮半掩的欲望表达终于褪去了最后一层外衣,直奔性主题而去,公开高调唱出了尖利的“性的颤音”。
1999年,卫慧的《上海宝贝》横空出世。作为当时欲望叙事的代表作品,它向人们讲述了一个都市“宝贝”欲望冲动和性放纵的故事。小说有意设计了一个极端的三角关系:一个毕业于名牌大学中文系的才华四溢、风姿绰约的都市美女倪可,一个“小蝴蝶般纯洁”的阳痿症患者天天,一个“玩意儿奇大”的德国佬马克。这个一女二男的搭配看似要表现一个传统的文学主题:爱与欲的冲突,但实际上作者的目的只是为了展览和炫耀性行为。也许是过于放纵的文字突破了社会的道德底线,也许是将孱弱的性无能的国产小男友与“性趣”盎然威猛无比的洋人的对比大大伤害了国人的自尊心,《上海宝贝》曾一度遭禁,但结果适得其反,竟造成了作品进一步的疯传。更加始料未及的是这本粗糙的小书居然在海外也有相当的发行量,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该书满足了西方读者对当代中国无所禁忌的非主流人群颓废生活的好奇心。与卫慧齐名的棉棉在表现繁华都市“新新人类”群体病态堕落的生活方面也颇为抢眼,她的写作诚如她所坦言的那样:“用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思考。”在其作品中,都市边缘人酗酒、吸毒、自慰、滥交、卖淫、同性恋等行为随处可见。此外,还有“乌鸦”九丹和木子美。前者因出版了一本描写留学新加坡的中国女人自愿沦为卑贱的“小龙女”(来自“龙”的国度的妓女)的小说《乌鸦》,一夜之间暴得大名,后者因秀下限无底线而惊爆网络。木子美把与男人做爱当作“个人爱好”,每隔两周,就要换一个或几个男人上床,然后将床上的细节写在日记里,并在其网上的私人日志中同步登出,取名《遗情书》。卫慧、棉棉、九丹等人的写作虽然尺度很大,但毕竟还穿着文学的外衣,其杀伤力似乎还可以用“想象”、“虚构”和“夸张”等词语去加以缓冲和消解,而木子美的日记写下的却是不折不扣的亲身体验,当不时更新的不堪入目的文字跳动在千千万万的网民面前时,公众因集体窥私而产生的惊愕、刺激、尴尬乃至愤怒的情绪反应也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这些领军人物之外,还有大量知名和不知名的作家也参与到“性的颤音”的大合唱中来。不仅小说乐此不疲,就连诗歌也不甘落后。90年代后期,新诗创作的欲望化倾向也愈演愈烈。一些诗人公然亮出了“下半身写作”的创作宣言。代表人物沈浩波认为:“所谓下半身写作,指的是一种诗歌写作的贴肉状态。……贴近肉体,呈现的将是一种带有原始、野蛮的本质力量的生命状态。”并扬言:“我们亮出了自己的下半身,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我们都这样了,我们还怕什么?”[4]其他一些诗人,如朵渔、伊沙等也积极附和这种主张,强调写作要回归“下半身”肉体快感。
从对纯真爱情的呼唤到对本能欲望的关注,从对隐秘的性心理的揭示到对露骨的性行为的渲染,从为爱而交欢到为欲望和金钱而滥交,中国新时期文学在短短的二十余年间完成了一次惊天大逆转。这次逆转不仅声势浩大,而且理直气壮,尤其匪夷所思的是竟然由受过体面的高等教育且自我感觉良好的女作家们领衔主演,并且,这种表演还博得了为数可观的“新新人类”,也包括一些接受过传统教育的中年读者的喝彩和追捧。这一方面显示了商业社会的市场法则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巨大的难以抵御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另一方面也表明由于时代的变迁,作家和读者的道德观和审美观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以原始生命的激情去反抗理性和现实秩序的“反文化”行为貌似对“自由”的追求和对“本真生命”的回归,然而,纯粹的“肉体法则”只能将社会人、文化人降低到生物人、动物人的层次,这非但不能带来人的解放和对现实的超越,相反,却鬼使神差地走向了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同谋的结局。其实,文学创作在性话语上的一再“突破”和“超越”与其说是一种文学行为,倒不如说是一种市场行为,一种营销策略。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从精神到肉体,从美感到快感,这种写作原则恰好迎合了当下汹涌而来消费主义文化浪潮,对奉行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的消费原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满足了人们对消费市场的最大消费热点——性的想象性消费。诚如鲍德里亚所言:“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它从多个方面不可思议地决定着大众传媒的整个意义领域。一切给人看给人听的东西,都公然谱上了性的颤音,一切给人消费的东西都染上了性暴露癖。”[5]
三、奢靡的时尚化
时尚是在特定时段内先由少数人实验,而后为社会大众所崇尚和仿效的生活样式。时尚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衣着打扮、饮食、行为、居住、甚至情感表达与思考方式等等。追求时尚能给人带来轻松愉悦的心情和高贵优雅的感受,并使人体现出不凡的生活品味和张扬的个性气质。在消费主义时代时尚更多的是与物质消费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使这一特征显得尤为明显。与现实生活中人们尤其是“新新人类”渴望做富人,过时尚、奢侈生活的理想相呼应,消费主义文学用想象的方式构造了一种奢侈化的生存行为和生存感觉来满足人们匮乏的情感需要。
女性是都市的精灵,与时尚有着不解之缘。女作家们在表现时尚方面也显得得天独厚、游刃有余。在卫慧、安妮宝贝、朱文颖、林播等人笔下,“小资”的形象光鲜照人。她们虽然处境不同、身份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迷恋于各种国际知名品牌的商品并醉心于富于情调的生活方式。这些风姿绰约的“时尚达人”被乔治·阿曼尼、香奈儿、梦特娇、圣·洛朗等名贵服饰装扮着,且浑身散发着迷人的法国香水的味道。她们不时出入于名牌云集的商厦、奢华气派的酒店、富丽堂皇的豪宅和温馨浪漫的咖啡店,日常生活总是离不了购物、喝酒、蹦迪、上网和听西洋音乐。她们的故事不外乎谈情说爱、做爱、争吵和分手。自恋、寂寞和感伤是她们精神面貌的主要特征。当然,聚焦时尚也并非女性的专利,以城市书写而闻名的男作家邱华栋在小说中就喜欢大篇幅、高频率地描写时尚生活的发源地——城市的外观:豪华的宾馆,高耸入云的写字楼,光怪陆离的卡拉OK歌舞厅、酒吧、夜总会和按摩院,等等。他的人物大多活动在酒吧、舞厅之类的场所,因为这些场所是最能体现现代城市气氛和情调的地方,是时尚一族和都市“另类”的聚集地。这些地方并非简单的空间意义上的物质消费场所,而且也是文化消费的场所,是最适合表达人类的潜在欲望的文学意象,其中包含着诱惑与暧昧,幻想与欲望,陶醉与麻痹,张狂与放纵等多重意蕴。
“小资”们对时尚追逐的实质与核心往往是对发达的西方的崇拜,这种崇拜包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内容。卫慧曾借人物之口说:“当然我也承认我从骨子里崇尚西方人的某些生活方式。”[6]所以,她的作品中到处堆砌着五花八门的西方符号。这些符号除了涉及物质之外,还大量涉及西方现代文化,光是文化名人就有长长的一大串。比如尼采、弗洛伊德、弗吉尼亚·沃尔夫、博尔赫斯、塞林格、纳博科夫、米兰·昆德拉、艾伦·金斯堡,等等。多数情况下作者是以开列清单的方式罗列这些符号的,而非真正出于具体内容表现的需要。对西方的崇拜势必会落实到对西方人的追逐上,于是,寻找洋人伴侣,寻求异域恋情便成为女作家们热心编制的美梦。《上海宝贝》中的倪可之所以迷恋于“马克”,不仅因为对方有着超强的性能力,更重要的是他来自柏林,就职于德资跨国公司。而且“马克”就是德国的货币单位,所以这一符号就包含了物质的坚硬和异国情调的双重诱人色彩。在旅英作家虹影的小说里,人们也时常看到一个到处晃动的国际情人的影子。虹影的长篇小说《英国情人》讲述了已婚女子闵与英国男子裘利安缠绵纠结的情爱故事。同样是一个中国女人与两个男人的故事,同样是一个疲软无能的中国男人败绩于一个魅力十足的洋人的过程,卫慧和虹影的写作均以一种较为极端的方式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西方文化的特殊载体——西方男人的仰慕和神往,从而迎合了现实生活中部分渴望依傍强健的西方男人而一举融入西方社会的中国女性的心理需要。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开放的中国都市的较为持久的时尚之一就是拥有姿色、身份、知识等诸多优势的中国女子对跨国婚姻的热情追逐。
时尚的面孔千姿百态,不一定总要花样翻新,有时怀旧也可以成为一种时尚。90年代,开发浦东与振兴上海的国家战略使上海又一次被卷入一种关于世界主义的“世界化”和“全球化”进程中。于是,人们突然怀念起昔日的国际化大都市——旧上海,这个曾经的“东方巴黎”因为有着漫长的“租借”的特殊历史而染上了浓厚的异国情调。在众多关于旧上海的追忆和想象的文字中,陈丹燕的作品,如散文《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和小说《慢船去中国》等无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当然,她寻觅和追忆的不是旧上海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不是阴暗、灰色、混乱甚至罪恶的一面,而是那些与繁华的景象、显赫的家族、辉煌的事业以及充满异域风情的生活场景密切相关的人、事、物。陈丹燕像一个出色的导游向人们介绍过去的租界,欧式风格的老房子,文化名人的旧居,别具风情的老报刊、跑车、酒吧、公寓等等,还有那些上层社会浮华生活的流风余韵,使人心驰神往。怀旧使旧上海被不可思议地重新赋予了现代性发达的、充分“全球化”的想象,在回忆中,“旧上海借助于新上海的身体而获得重生,新上海借助于旧上海的灵魂而获得历史”[7]。类似的描写还有王安忆笔下的“平安里”、“上海小姐”,程乃珊记忆中的“蓝屋”,王晓玉记忆中的“永安里”以及“教会学校女生”、“留法的少爷”等等。在这些集体记忆中,没有冲突,没有对立,只有一个浮华四溢的富人的历史。这样的记忆温馨、优雅,且带着些许感慨和忧伤,看起来似乎远离现实,与媚俗无关,但实质上骨子里潜藏的仍旧是对荣华富贵的神往与渴望。
结 语
消费主义文学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以及社会心理的基础。在目标上,它与当下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一致,追求的是物质的富裕和满足;在观念上,它与现实生活中极为盛行的社会价值观——尊重利益原则和注重个人享乐相吻合;在功能上,它以虚拟的快感满足了众多被物质和肉体的双重欲望所困扰的读者对幸福生活的奢望与想象;在艺术上,它不折不扣地奉行“快乐原则”,使长期以来饱受社会文明和主流意识形态压抑的人的本能和欲望得以充分的宣泄和满足。消费主义文学是中国社会步入消费社会后合乎逻辑的必然产物,是一种典型的时代情绪的反映,且有着为数可观的追随者和赞赏者。尽管在总体上我们不能认同其价值取向和艺术趣味,但不可否认它的存在毕竟有着某种合理性。在人们艰难地告别了将人予以神化和圣徒化的空洞的理想主义时代之后,我们终于承认人首先是人,是有着诸多本能欲求的人。所以,才有了大张旗鼓的经济改革,才有了为合理地追求物质财富和身体欲望的行为的正名。消费主义文学以对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人的欲望的书写而使部分读者多少感到了一些生活的意义和精神的满足,哪怕这种意义和满足带有相当的夸张、梦幻和虚假的成分。然而,凡事过犹不及。消费主义文学的宗旨就是炫耀生活享乐,而享乐就是欲望的满足,就是对“物”和“性”的无尽的占有与挥霍。在这样的文学中,生活的苦难与艰辛不见了,人生的努力与奋斗消失了,超越现实功利目的的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和人类在文明进程中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丢失了,剩下的只有极端自恋、自私,被本能和欲望所驱使的人,一群在寻求刺激中走向餍足、虚空和堕落的人。沉溺于这样的文本不仅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自由、超越和解放,相反,只能造成人的精神的颓败和迷失。因此,对势头强劲的消费主义文学浪潮,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戒备和有效的抵御,乃至必要的约束。
[1]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165.
[2]陈丹燕.慢船去中国[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3]朱文.我爱美元[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380.
[4]沈浩波.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 [M]//杨克.2000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
[5]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59.
[6]卫慧.蝴蝶的尖叫[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115.
[7]张鸿生.“上海怀旧”与新的全球化想象[J].文艺争鸣,2007(10).
责任编校:汪孔丰
Material,LustandFashion:FeaturesofConsumerismLiteraturesincethe1990s
WU Chun-ping, ZHANG J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qing Teachers College, Anqing 246133, Anhui, China)
Consumerism literature is induced by consumerism culture. Consumerism literature since the 1990s ha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it is lost in materials and commodities, reflecting a strong trend of materialization; it focuses on “the lower part of the body” and stresses the sexual instinct, reflecting a urgent desire for sex; it dramatizes the petty-bourgeois sentiment and craves for fashion, presenting a luxurious fad. Consumerism literature is the product of market-oriented literature. It is valid in existence but its negative influence should be on our guard.
consumerism literature; consumer culture; materialization; desire; fashion
2014-01-26
吴春平,男,安徽舒城人,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张 俊,女,安徽枞阳人,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时间:2014-4-18 17:23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4.02.002.html
I206.7
A
1003-4730(2014)02-0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