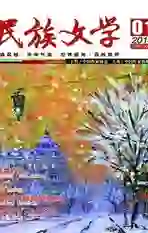急救室
2014-03-21敏洮舟
敏洮舟
靠窗在墙角,一张病床静静地平躺着。晚风从微开的窗缝里,丝丝缕缕地溜进病房,对流着两个世界的呼吸。垂在床边的白布单如一袭轻柔的裙裾,被风一吹,微微摆动着,投在地下像一个虚弱的身影。将母亲稳稳地抬上病床,我长吁一口气,揉着酸软的肩膀,重重地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看看表,夜晚12点了。母亲坐了一天轮椅,躺下不久便睡了。
窗外,火一般的灯光扑闪在两岸,追赶着那一脉永远揣着心事的河流,远远地遁去了。流的是黄河,河水里充盈着浓浓的夜色,只有倒映在河中的灯火,在粼粼波光中印证着那是一条活着的水。外面的世界真好啊!叹口气,转过身来。病床上的母亲把头埋在松软的枕头里,鼻息一声长一声短,青紫的嘴唇偶尔颤抖一下。跟着颤抖的,还有从黑盖头里逃出来的几丝白发。
母亲住的是急救室,兰州一个三甲医院的急救室。母亲是不肯进来的,说寿数是真主的定然,花费这么多钱不值当。我嘴里应承,手下不停,母亲就这样身不由己地被挟持了进来。急救室很大,横竖卧着八张病床,每个床头端放着一部监护仪,仪器声此起彼伏,用不同的音色诉说着对生命的理解。我靠在床边上,眼皮渐渐沉了下来。浅睡的梦里全是母亲喋喋不休的呢喃,我有些烦了,想转身离开,梦便醒了,可耳边依旧乱哄哄的。
是病房外面传来的。走出去一看,一条救护床正从通道拐角处推来,被一堆医护人员簇拥着扑向急救室。床边有个女孩正一瘸一拐地跟着跑,她满面泪痕,浑身泥土,手上和脸上全是已经凝固的血渍,白色的上衣也斑斑驳驳地沾满了血红。救护床迅速推进了急救室对面的手术室,女孩被挡在了门外。她靠着墙壁软软地坐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一对大大的门牙如兔儿的贝齿般时不时地紧咬着下唇,紧抱的双臂不停地战栗着。那情态像极了一只瘦弱的白兔,蜷缩在无人的墙角瑟瑟发抖。
急救室里陪护的家属有一半都去了外面,远远地观望着兔儿牙女孩,只有五号床的家属依旧坐在床边一动不动。是个老阿婆,估计有七十几了。从我看见她起,她的目光就一直未曾离开过床上的病人。偶尔一低头,眼泪成串成串地往外涌。刚才医生跟她说了一阵话,医生走后,老阿婆更像被钉在椅子上,望着病人,连姿势都未曾变一下。
急救室外,兔儿牙已坐在过道椅子上,身边也多了两个警察,一个拿纸笔记录,另一个在询问。好奇心驱使,我往近凑了凑。
兔儿牙拿纸巾不断抹着眼泪,理了理散乱的头发,微颤着声音说:“我们到黄河边已经11点半了,人少得很,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看到有片树林子,就想进去坐会儿。还没等我们坐稳,树林里忽然跳出几个男的,头发全染绿了,年龄都在20来岁。他们把我们围在中间,每人手里拿一把刀子,恶狠狠地说,把钱和手机全拿出来……
“他到处流着血。我用尽力气想背他走,可背不动。没办法只有往回跑,想找人帮忙。跑了一截路,看到河边有个带白帽子的人,正从河里拉羊皮筏子。走近一看,是个留胡子的老人,就走过去央求他帮帮我。老人一听情况连忙跟我跑,嘴里还在叨念:‘安拉乎,这顿亚①咋么了,人心都朽坏了。
“老人把他背上了马路,然后让我去拦出租,可好多司机看到情况都不停车。最后老人把他放到锁在路边的一辆三轮车上,那是拉羊皮筏子用的。到了医院门口,我叫上医生把他抬上病床后,那老人就走了。他擦着手上的血,说他的羊皮筏子还在河边呢。”
听到这里,我的心被扯得紧绷起来。心想自己每次到兰州,也喜欢去黄河沙滩上遛遛,吹吹河风,站在葱郁的河岸眺望一下黄河奔腾而来的风姿和滚滚而去的气势,却怎么也没想到,这恢宏的长流之下,还涌动着如许不为人知的暗流。暗暗举意,抽空得到黄河边找找那老汉去。
急救室里传出了咔嗒咔嗒的声音。赶忙进去一看,是五号病床上发出来的:一会儿时间,病人已经用上了心脏按压器。老阿婆手足无措地站在床边,瘦小的身体微颤着,如一片随时会坠落在风中的枯叶。她年龄与母亲相仿,看着她,我心里莫名地生出一股难过。下意识地走过去,轻声安慰了两句,询问床上病人的情况。老阿婆摊开一个和她的手背一样皱巴巴的手绢,不停地抹着眼泪。病人是她的小儿子,先天性心脏病。她的大女儿和二儿子已相继去世,都是心脏病。她老伴也有病,帕金森症十多年了,严重时无法自理。她一个人,平衡着一个家庭。
老阿婆看着我,也看着病床上的母亲,眼泪像决堤一样。我的心狠狠地拧了一下,在那疲惫而浑浊的一瞥中,我读出了太多意绪,太浓了,也太重了。我陪护的是年迈的母亲,是顺当的,符合常道的;而她却守望着年轻的儿子,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天天衰弱下去。我轻轻地走开了,不敢再说一句轻率而无用的话。
心脏按压器不休不止地叫嚣着,似乎在作某种艰难的抗争。母亲还在睡,鬓间的发丝与枕头一样洁白,浮肿的脸庞上,斑斑点点的青紫块儿如一个个老旧的生命印记。病房里很吵,她却睡得很熟,这与以往的情况大不相同。正想着,过道外面传来一阵哭声,如破裂的音响一般,喉咙已经沙哑了。急救室里很多人都站起来往外看,一个留短发的妇女踉踉跄跄地朝急救室奔来,口中声嘶力竭地哭喊着:“儿子——儿子——”兔儿牙跑过去和她紧紧抱作一团,啜泣着在她耳边说着什么。没一会儿,短发妇女软软地瘫坐在地,眼中布满血丝,呆了几秒,整个过道便被她的长哭淹没了。
手术室打开了。兔儿牙和短发妇女冲过去,站在医生面前微微弓着身子,像在接受某种宣判。医生告知刀伤十分危险,差一点扎在致命处,目前已脱离危险。短发妇女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泪流不止地道着谢谢。医生扶起她,谦逊两声,急忙走开了。众人都松了一口气,战友胜利了,整个战壕都看见了曙光。
受伤的男孩被推进急救室,安排在老阿婆的五号床边。此时,老阿婆的身旁已多了一个老人,双目深陷,头颅不停地点动着——蓦地明白,他就是老阿婆的老伴,那个帕金森症患者。
母亲还在睡,也不吃东西。我揣着忧虑朝医生办公室走去。医生说初步诊断,肾、心脏、肺都有问题,具体病情需要相关科室的医生会诊。嗜睡是肺心病的症状之一,如果再出现意识恍惚,说明病情在加重,在朝肺心脑发展。
走出办公室,我在大厅里徘徊良久,心底有股深深的悲意,怎么也排遣不出。回到母亲床边轻轻握住她的手,细细端详着她的面容,隐隐感觉该多看看她了。以往我开着大车到处跑,和母亲分离得太久,也相隔得太远了。这张时刻牵挂着我的脸,在无数漂泊的时光里渐渐变得模糊起来。现在,当我可以细细打量她的时候,她却不给我太多时间了。我俯下身来,理了理母亲鬓间散乱的白发,眼眶一阵发酸。母亲蹙蹙皱皱的面容上,却盛满一潭静水。
第二天清早,护士叫醒了我。抬头一看,病床边站立着一堆白大褂。已经八点半了。忽想起,母亲今天要会诊。护士说,会诊科室分别是心内科、泌尿科、呼吸科、肾病科,会诊结果出来,就能确定母亲应该转到哪个科室住院。
真主啊,请放赦我的母亲吧!请让苦了一辈子的母亲领受暮年这点浅薄的安详吧!
在我暗暗的祈求中,会诊仅用了半个小时便结束了。母亲没怎么受折腾,急救室的病人做各项检查,不需要离开病床,护士依照要求在床边就可完成。医生走后,正想母亲可以好好休息一阵,可伴随着急促的步伐,一张急救床被推进了急救室。空间本就有限,此时又被加上一个临时床位,就愈发拥挤了。床上的病人是个中年男子,浑身都是水泥渣子,一双劳保鞋被泥灰掩盖了本来面目。脸上的泥灰和汗水拌在一起,流出一条条棕色的蚯蚓,整条胳膊像麻花一样,本应向外的部位扭在里面,朝里的却拧向外面。黑瘦的脸庞也像胳膊一样,疼得变了形。急促的呼吸如正在爬坡的老耕牛,喷着粗粗的热流。
挺至五分钟左右,护士给他注射了一剂止痛针,叮嘱陪护人员赶快去交住院押金,不然没法手术,粉碎性骨折不能耽搁。陪护人的衣着和伤员一模一样,大约是一同的工友,一脸的大胡子掩盖了本来的年龄。听完护士的话,他不停搓动着两只爬满了茧子和裂痕的糙手,嘴里嚅嗫着先让医生做手术,费用缓一天再交。护士的回答温和干脆:医院有规定,不交押金就不能手术。
伤者扭曲的胳膊下,鲜血正一滴滴浸染在雪白的床单上,妖艳得有些夺目动人——也应该是动人的,因为,那是从一个活人身上流出来的!
大胡子拨着手机。从进门开始,他的手机基本没离开过耳朵。拨通之后,他小心翼翼地询问:“金老板,我们到医院里哩,没钱人家不给做手术啊,你调查得咋么样了?”他语气柔软,嗓门却很大,急救室里所有的人都转过头,把目光投在了他身上。被众人的目光一盯,他马上意会到急救室里不能喧哗,赶忙向外走去,语气也愈加急迫起来:“咋么没人见哈,老王手勤,他是午休时候抽空儿清洗搅拌机的,以往都这么着哩,大伙可以证明哩……”说着声音渐渐远去。
急救室里静了许多。只有心脏按压器勤快地工作着,间或夹杂一阵嚣叫声。老阿婆一个人守在按压器旁,须臾不离。守护期间,她几次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瓷瓶,哆哆嗦嗦地打开,倒出几粒药丸塞进嘴里,许久才能重重地呼吸几下。我认得那瓷瓶,母亲曾经用过,是速效救心丸。
母亲从早上会诊后一直沉睡,刚刚被大胡子吵醒,翻了个身,转眼又睡着了。意识恍惚,嗜睡,这两个关键词被医生和恶化归类在一起。母亲似乎在印证着医生的诊断,睡觉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我心里也逐渐沉重起来。
五号床老阿婆的步子更沉重,在床边坐了大半天,腿脚明显僵硬了。帕金森老人走进急救室,替换她回去休息。老两口也不说话,一个不停点着头进来坐下,一个不断抹眼泪低头往外走,除了病床边的椅子外,似乎互不关联。老阿婆走到门外又转过身来,像是忘带了什么东西,可也不进来,就在门口看着病床上的儿子,听着心脏按压器的声音,呆呆站立着。好一阵后,叹口气,又默默地离开了。望着她蹒跚的背影,我不知道那矮小的身躯里究竟装着怎样的一颗心灵。
老阿婆前脚走出去,大胡子就打完电话闯了进来。他脸色赤红,脖子上青筋暴起,鼻孔一大一小地喷着怒气。好一阵后,他的情绪慢慢平复了下来,一屁股坐在床边的椅子上,阴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床上的伤者一阵昏迷,一阵清醒。清醒时,一声连一声地呻吟。
整个急救室静悄悄的,唯有机器在和呻吟对话。巡床医生走进来,询问联系得怎么样了,并强调粉碎性骨折很有可能会压迫神经,时间长了胳膊就废了。大胡子一听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半弯着腰哀求医生先做手术,费用一定不会少,只是一时半会儿凑不齐。说着说着,铁塔似的身躯几欲凹折下去。
所有目光全盯在医生嘴上,仿佛那嘴里会吐出一次金贵的例外。医生有些无奈,面对急救室奇异的氛围和工友卑微的哀求,尽量解释医院的规定谁也没法改变,然后逃出了急救室。大胡子弯着腰,手扶病床,半天说不出话,也起不来身。
母亲不知何时醒了,说口渴。用吸管喂她喝了几口温开水,想起医生的嘱托,长时间嗜睡会加重病情,要多和病人说话。我给母亲讲了受伤民工的处境,母亲听后吃力地撑起身来望着那边的病床。我知道,母亲永远也无法理解医院的规定,她自言自语地说:“人疼着叫唤着呢,还说啥钱着呢。”
这时,急救室外人头攒动,来了很多穿着民工服的人。带头的一脸沉默,走进来时步子放得很轻,和大胡子互相点点头,站在床边看着伤者,蹙蹙眉,手掌伸进贴身的衬衣口袋里抠了半天,摸出了几张旧旧的钞票。钞票卷成了一个圈,圈里还夹带着衬衣上的线头。他往伤者枕边一放。病房里的人都看着他,他一脸通红,低着头很不自然地逃出了病房。接着,十来个民工进进出出,伤者洁白的床单上,不一会儿就摞起了一沓皱巴巴的钞票。钞票上沾满的石灰和水泥渣滓,与医院洁白的床单极不协调。
急救室里寂如深夜,除了心脏按压器的跳动,人们注视着这一幕,没有任何声音。
母亲看着眼前的情景,含泪向我点了点头,又朝受伤民工那边示意了一下。我明白她的意思。母亲时常对我说,人要知感,比起很多难心人,我们的日子已经很宽展了。回民的心是柔软的,遇到困难人,一定要出散“算德甘”②。
在母亲的眼底,我拿着钱走了过去,她在后面低声说:“举个意”。
放下钱回来,只是一霎时间。看着母亲欢喜,我心里塞满了知足。虽然我的处境并不宽裕,但比起母亲一天天减少的欣慰,这太值了。
病房里,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终于,钞票像雪片一样,一张连一张地落在伤者的床上。大胡子给捐助者们一一鞠着躬,这黑铁塔就像装了弹簧一样,一曲一直,上下折叠。
第三天上午。心脏按压器依旧工作着。帕金森老人应和着按压器的节奏,几根稀疏的白发随着响动不停颤抖着。老阿婆回去休息了。
急救室里比昨天清静。我望着熟睡的母亲,心里寻思会诊的结果会是怎样的。所有病理分析今天就应该出来了,医生却毫无动静,难道是在论证母亲该去哪个科室住院?渐渐地,满脑的疑虑拉扯着眼皮往下坠,再往下坠。不知过了多久,一串尖锐的电子报警声钻入耳朵,我被惊得坐了起来,查看母亲床头的监护仪,所有数据却正常无异。
是五号床病人出现了状况。一看监护仪上的血氧指数,从80到70,一下又降到30。护士长加快了心脏按压器的按压频率,作用俨然不大,血氧一直在20和30之间浮动。医生疾步走进急救室,吩咐护士快打强心针。帕金森老人头点得更快了,浑身也跟着剧烈地颤抖。
护士的强心针还没打完,报警声忽然连成了一片,监护仪上的心跳曲线,也从上下跳跃拉成了一条长长的直线。医生忙乱一阵后,从耳朵上取下听诊器,翻开病人的眼皮查看了一下,再看看腕上的手表,宣布五号床病人:死亡。
听着结果,我的心跳骤然加快。帕金森老人颤巍巍走到病床边,双手抚摸着儿子的双腿,双唇从苍白慢慢变得青紫,嘴巴半张半合,却一丝声音也发不出来。老人的帕金森症似乎更严重了,护士长看着他,迅速拿出手机通知了老阿婆。
整个急救室鸦雀无声,偶尔只有三两声仪器的嚣叫。
十多分钟过去了。一阵低沉苍老的哭声从远处隐隐传来,划破了急救室的安静。哭声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嘶哑。老阿婆来了。她的脸颊一片灰白,就像满头的发丝。我心里沉郁,低下头不去看她。人老了,大抵都是相像的,不知为什么,从她身上我总能看到母亲的影子。她望着病床上的儿子时,眼神和母亲一模一样。她踉踉跄跄地栽进了急救室,哭声如同老山羊的呼叫。病床边围观的人纷纷避让,老阿婆身子一摇晃,碰翻了护士手中的器械盘,针管药瓶哗啦啦跌落了一地。可她还没走到床边,却猛然间打了一个趔趄倒在地上,哭声也戛然而止。
一片惊呼。
老阿婆蜷缩成一团,手脚连连抽搐着,慢慢地缓了下来,轻了下来,终于贴在地上无声无息,如一片凋落的枯叶。帕金森老人跪在旁边,颤抖的双手不停摇动着老阿婆,嘴里含混不清地吼着,唇齿间的唾沫拉成了一条条乳色的线。
医生闻讯跑来,先在老阿婆胸前听诊,接着又是敲打又是按压,很是折腾了一阵。最后翻看一下眼皮,取下听诊器,无奈地摇了摇头:刺激太大,心脏猝死。
我心里重重一震。转头看帕金森老人时,他神情木讷,半张着嘴巴,双眼像灌满了鲜血,迟滞地望着地下,又看看床上,苍老的头颅不停地上下点动着。
一转眼,两个人在眼前没了。帕金森老人已经无法走动,护士用轮椅推他出去的时候,他的眼中已经看不到一丝悲意和光泽。
回头看母亲时,她正看着我,双眼噙满了泪水。我上前拉着她的手,怕她悲伤,加重心脏负担,想安慰几句,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母亲却拍拍我的手,嘴角微微下撇着说:“我的娃,别担心我,无常的路上没老小。得病殁了,这是安拉乎的前定,谁都要走一遭。看到亡人,人要拿觉探③
哩。活着的时候,好好干办点儿善功,就是无常临近了,心里也安稳着哩。”
说完话,母亲闭上眼睛,转过身去,嘴里喃喃地念着。望着母亲安详而苍老的面容,忽然觉得眼前发生的这一幕也没有多么突兀了,更像是隐秘的启示。对活人来说,沉重过后,应该会留下些什么,对生命,对那个并不遥远的、在暗处等待的节日,多多少少应该给予认真的注目,哪怕是片刻的。这些,母亲早就领受了。
医生终于把我叫到了办公室。母亲的会诊结果出来了:肾功能衰竭,慢阻性肺心病晚期。同时给出两种选择:进ICU治疗,每天只有一次探视机会,时间不能超过1小时;或者,回家。
我的心被抛出了胸膛,悬挂在很高很高的地方,不停地动荡着。跑到心内科、肾病科、呼吸科要求住院,三个科室给出一个统一的回答:没有床位。心里明白,这是婉转的拒绝。我在大厅里徘徊着,望着,听着,周围的面孔和声音仿佛离我很远很远。
回到急救室,我低头不敢看母亲的脸。母亲却闭着眼,干涩的嘴角节制地蠕动着,微蹙的眉间笼着纤丝般不易察觉的痛楚。哦,我的信道行善了一辈子的母亲啊!我的心似乎成了一团和水的面,被一只粗糙的大手使劲地搓来揉去。脑袋里不断寻索着可以信托的人,出去打个电话,让联系一下其他医院。然而刚转过身,一个沉静如同深水的声音却低低唤起:“我的娃,我们回家吧!”
责任编辑 石彦伟
注释
① 顿亚:回族经堂语,意为“世界”。
② 算德甘:回族经堂语,意为“用行为或金钱救济贫苦”。
③ 觉探:回族经堂语,意为“反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