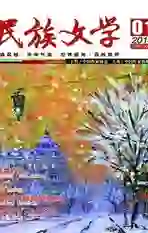老人·狗·皮袍
2014-03-21忽拉尔顿·策·斯琴巴特尔
忽拉尔顿·策·斯琴巴特尔
曲勒腾老人的黑母狗踏吾克失踪已有七八天了。老人在这周围附近能到的牧民家都挨家挨户地去打听,都说没看到。到后来老人抱着哪怕能看到它尸体也行的心情,连着七八天咬着牙,搜遍了所有能去的地方,也没有任何踪影,就像蒸发了似的。最后老人彻底失望了,也累得筋疲力尽,拖着疲惫身躯,蹒跚地回到家,倒地就盖上他那件一年四季不离身的皮袍躺下了。这会儿他连吃饭喝水的力气都没有。踏吾克确实是一条好狗啊!一点也不夸张,全村牧民几乎都知道。它从来都不在野外瞎跑或随便在野外觅食,也不吃除老人以外别人给它的东西,是一条训练有素、习性非常好的狗。平日里不是天天跟着老人,就是在家守门。它还每年下两窝小狗,所下的小狗,个个都是能看家守门的好手。自它走失后老人的心情一直很低落,食欲和睡眠也非常不好,满脑子想的就是他那条黑母狗。曲勒腾老人自他老伴儿去世之后,十多年来一直与这条黑母狗为伴,可称得上相依为命,除了睡觉之外,可以说形影不离。十几年来老人一直与它从一口锅里吃饭,他吃什么,它也吃什么,从不另开灶备食。按照狗的岁数来说,这条黑母狗年时已很高了。说来也是,在这家里没有一个年纪轻的,老人的坐骑枣红马也已三十来岁,还有,冬季骑的那峰骆驼也是老的,是他老伴儿在世时候的坐骑。家里的家具和一些生活用品什么的,也没有新鲜东西,几乎都是与他老伴儿起灶时期便有,可称得上是老古董。这座小蒙古包也是,不仅能给他挡风避雨,还是把老人遮蔽于外界视线之外的私人宫殿。自与他老伴儿结婚起到今天,一直起居于这座小蒙包里。这条黑母狗也是他老伴儿在世的时候,在野外放牧,从芦苇丛里捡来的。他老伴儿每天给它喂羊奶和面糊糊,一直养活至今。现在很多牧民家,养狗只养公的,不养母的。母狗下崽后留下公崽儿,把母崽儿残忍地扔到野外,活活饿死或冻死。据说下边人家,媳妇儿生男孩子就很高兴,要是生了姑娘就一百个不高兴,有的还把姑娘送人或放在别人家门口,甚至放在路边。原先这儿的牧民们听了之后,很是不可思议。现在的牧民们也和他们差不多了。养狗时留下公的,母崽儿给扔到野外。狗崽儿虽然不是小孩儿,但它也是活生生的生命呀。这个世道越来越奇怪,大千世界真是无奇不有。一旦家里的狗死了或老了,个个儿都急急忙忙跑过来,嚷嚷着要狗崽儿。有的还提前一两年就开始预定。全乡所有牧民家几乎都从曲勒腾老人手里领养过小狗,这是一点儿也不夸张。甚至还有邻乡的牧人家,也来老人这儿领养过小狗。远的不说,就眼前来说纳木德克家的白胸、加布德力家的白爪、敖其尔家的四眼、尼玛家的狮子,道尔吉家的长毛、桑布家的霸王……等等都是曲勒腾老人家的黑母狗踏吾克下的崽儿,都是从老人手里领养的。老人的黑母狗所下的崽儿个个都大块头,声音洪亮,每个都是看家好手,对人也不是太凶猛。所以,远近的牧民们都喜欢从他这儿领养家犬。
曲勒腾老人一辈子无儿无女。自他老伴儿去世之后,就与这条黑母狗为伴,度过了十几年,它与老人从没远离过。每当把黑母狗下的崽儿送到预定人家时,看到黑母狗踏吾克,为它的小崽儿撕心裂肺的痛苦呻吟,老人也不由得伤心。于是老人就坐在它旁边抚摸它,嘴里不停地安抚它平静下来。天下所有母亲,没有一个不为失去自己的骨肉而不痛苦的。老人每当看到这一切,更加疼爱和同情这条与他相伴的母狗。母性的伟大,使他更加疼爱和可怜这条不会言语,却能够理通人心的动物。自他老伴儿去世之后,黑母狗除了下崽儿或孕期,从不离开老人。只要他一出门,无论走到哪里,它就像影子一样跟随,到了别人家,它就守在老人的坐骑旁,等到老人再骑上他的坐骑,从这里走向另一个目的地时,立刻起身相伴。如果老人偶尔回不了家,在别处过夜的话,老人就指示它回家,它也很乖巧地听从老人的话,一溜烟跑回家,守家在门口,第二天早上,又早早地跑过来在老人坐骑旁等候他。老人无论去谁家,主人都不用给他看狗,老人也从来不怕这些人家的狗。其原因是,第一,这些狗大部分都是从他手里领养的,狗的嗅觉记忆很强,凭着它的原始记忆,也能够嗅得到老人气味儿。第二,所有的狗,只要看到或嗅到母狗的气味儿就只在乎母狗,而不去理会其他。这就是世间阴阳相吸的自然规律。老人对黑母狗踏吾克的发情期了如指掌,只要到了发情期,他就领着它,到远处的邻乡去找与它没有血缘关系的良种犬,让它们交尾受孕,老人十几年始终如此。
盛夏的夏天哈吉尔草原上牧人们在议论:“曲勒腾老人找他的黑母狗踏吾克找了七八天了,为一条老母狗快把自己也折腾死了,老头儿真是一根筋。”还有的人,为老人的母狗失踪感到有点儿可惜。
“以后可不好找这么好的犬崽儿呀!”
也有不以为然的:“嗨,老的已经不能下崽儿了,丢了就丢了呗,又不是母狗绝迹了。”
“可惜呀!我们家的狗也老得快不行了。正打算从老人那里再领养一条小狗来着,这可从哪儿再找。”
“我们家的狗前段时间也失踪了,不知道是给淘金的人还是地质勘探队的下边人抓走了,连个尸首也没找见,可惜得很。现在这些到处跑的下边人越来越多,别说牛羊,连家门口的狗都被他们抓走。防不胜防,真是不可救药。前几天还给老人说,给我预留一条小崽儿来着。”
“我们家的杜锡(狗名)也是从曲勒腾老人的踏吾克窝里领养。确实是一条好狗,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从不到门口来躲雨躲寒,连家附近的地方也不呆着,始终在羊圈外围卧着。”
“哎呀!我们家那年从呼和高勒的东德布家领养了一条狗崽,看家倒是没的说,就是脾性太烈,白天始终拴着,没法放开它。脾性凶烈的狗也是个麻烦,总是提心吊胆,怕什么时候把人家的孩子或老人妇女给咬了,或把人家的坐骑给惊吓,把人家摔伤了,给闯下大祸。后来从曲勒腾老人那里领养了一条狗挺好的,脾性也温和,对人不凶,看家也不错。现在也老了,早知道这样,应该去年就领养一个好了。”
“据这些下边人说,我们这里的牧羊狗品种特别少,在内地找不到,很多人以很高的价钱买这种狗。养一条母狗,让它下崽儿,然后卖给他们是不是也能赚不少钱呀?”
“趁早打消那种歪念头,你呀想都别想!会遭报应的。你见过哪一个蒙古人卖狗发财的?”有个长者立刻训斥道。
“以后啊,自己家养一个母狗就不用从外面找狗崽儿了。”
“不,那也是个麻烦的事情。一到秋天,狗发情时,所有人家的狗或流浪狗都跑到你家里来,一群狗成天打架,弄得你鸡犬不宁,可不是个事儿。”
“可是在曲勒腾老人家外面好像从没看见过那么多狗呀!奇怪得很!”
“怎么没有啊?只是你没注意罢了。”
“嗨!自曲勒腾老人的黑母狗失踪后,他就像老婆和别人私奔了一样。到别人家话也不说,门也不进。叫他进屋喝口茶,也不搭理人家。”
“一个孤老头,十几年来一直与它为伴过来,现在狗突然失踪了,肯定会很伤心。如果你也和他一样孤身一人的话,也会那样的。”
曲勒腾老人黑母狗失踪,而老人寻狗之事在人们中引起了种种从未听说过的奇特话题。老人这十来天在咚布滩上的所有牧户和沟沟坑坑一个也没落下,都找了个遍。最后连个尸首都没见到,累得疲惫不堪,一回到家只喝了点炒面拌汤,就钻进羔皮袍。这件羔皮袍是他老伴儿在世时给他缝制的,老人无论在家还是野外从不离身。
在咚布滩草原上老人的小六十式蒙古包仿佛是倒扣碗一样,在晚霞半空中悬挂的初三月牙光下隐隐约约显得那么微小。不一会儿月牙光被从西北天涯漂移的黑云团遮盖得严严实实,没有一丝亮光能透过云层。天空伸手看不清五指,漆黑漆黑。老人偶尔从弥漫酥油味的羔皮袍里伸出灰白脑袋,不知道是在倾听外面的动静,还是看是否天亮。里外没有一丁点儿的动静,安静的似乎在地上掉一根针也能听得到。其实老人的耳朵几年前就几乎聋了,基本上听不到什么。除了在他家东北边不远的关其克家四眼小狗偶尔叫两下之外,整个咚布滩草原上老人就听不到任何一丁点儿声音。
老人把头深埋在羔皮袍里继续念着他的经。没有牙齿的嘴里不停地嘟哝着“唔吗呢班咪哄”。如果老人不伸出脑袋的话,别人根本感觉不到皮袍下面还有人。老人在皮袍下偶尔咳嗽几下,仿佛要背过气儿似的,然后就静悄悄的,什么动静也没有。
突然有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划破静夜,渐渐地接近曲勒腾老人的小毡包。老人奇迹般地听到了这个声音,他认得这个声音。又是那只独眼流浪白狗。老人仿佛听到了噩耗似的,心情极其不安。老人在皮袍下面骂道:“真见鬼!”刺耳又让人不安的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几乎来到了门口。老人觉得流浪白狗和那种难听刺耳声音从门缝里钻了进来似的。那种让人惊魂的声音仿佛慢慢地透过他的皮袍和衣服,钻到了骨头里。让老人觉得流浪白狗仿佛钻到他皮袍下面,舔舐着他的鼻子和整个脸面。老人下意识地裹紧皮袍,又把头深深埋进皮袍里面。流浪白狗的那种撕心裂肺的嚎叫声弥漫于整个蒙古包和空气中。老人屏住呼吸,尽可能地不吸这种死讯弥漫的空气。但是这种空气已弥漫于整个家,如雨水一样慢慢渗进老人的身体。流浪狗的声音仿佛在向老人已背多年的耳朵里传递着死讯。老人突然从那凄惨的嚎叫声中仿佛听到了黑母狗踏吾克的音讯。这是否它死后的野魂迷失,让天狗不安呀?或者它与野狼交合在一起了?在老人的脑海里翻腾着各种各样奇思怪想,十分离奇。老人突然感到浑身发凉,牙根都开始打颤。几十年来头一次感到这么孤独。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和恐惧已填满了他的精神世界。老人多少年来把所有的孤独、病痛、喜怒哀乐一统裹在这件皮袍里度过。这是件又温暖、又温馨的皮袍。只有这件皮袍能融化老人的冰点,使老人感到温暖,它是老人的窝中窝。对老人来说,它是件能把温暖或快意裹在里面,把寒冷或寒意阻隔在外面的奇物。是他身体的保温物,生命的保护屏,生活的包装品,是他世界中的小世界。老人平时屋内外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埋在这件皮袍里。现在,老人就像还没破壳儿的鸡蛋一样,把头和身体深埋在皮袍里,生怕外面的空气进到里面,把皮袍裹得紧紧。从此,再也不与外面空气和灰尘沾染。在世的七十多年日日夜夜也不少了。当前或从此往后,我要待得空间就是这毡包里面,裹在这件皮袍下,暖暖呼呼睡一觉,才能远离红尘,顺利走向想要去的地方。老人想尽快结束七十多年坎坷生活,赶紧去与他为伴一生、一起吃尽人间酸甜苦辣的老伴儿那里。老人趁机回忆着能回忆起的一切,也努力想象着从未想象过或未敢想象过的一切。
外面的一切越来越安静,仿佛一切开始慢慢离他而去。独眼流浪白狗的那种刺耳嚎叫声也悄悄地从他皮袍下面流出去。屋里的空气仿佛也慢慢变稀薄。老人的身体就像抽掉了所有的筋络一样逐渐发软变薄,仿佛是漂浮在空中的干树叶,轻飘飘的不敢动,怕稍有动静随风飘走,落地在谁也找不着的地方。老人的肚子不断在“咕噜噜”地响,但他一点儿也不在乎,他想着,只要把屋里的空气深深吸上两口就行了。老人从来没有这么贪婪地呼吸过空气。老人觉得,这个世界的空气从没像现在这么干净,这么新鲜,周围也从没像现在这么安静和温馨过。
可怜的她,虽然吃尽苦难,但走时干净利落,可以说没受一点罪。走的人和留下的人都很省事。她真的是一点儿也没让我折腾过。据佛经讲,造孽不深的人就会那样。不知道我会怎样?我所造的孽也不会太浅的。要是成个半死不活的话可要受罪了。无论怎样,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静静地睡觉,只要能够睡得着觉,就是终结。老人又开始嘴里嘟哝着:“唔吗呢班咪哄”。
老人的耳朵里独眼流浪白狗的嚎叫声越来越远。让人惊魂的嚎叫声从老人的皮袍下悄悄溜出去,慢慢消散于空气,最后消失的安安静静。盛夏的夜晚又沉浸于宁静中。外面的狗声走远了,他的狗“声”越来越近了。快到了,老人想到这儿,感到一丝欣慰。
七三年的冬天,老两口在敖温嘎图放生产队淘汰羊,连续几晚上被狼袭击了他家的羊群,损失了好几只羊。于是他们上报到生产队领导后,巴利吉队长带着他儿子来,在狼穴附近的路径上打了夹子,当夜就抓到了两只狼。没过几天,他老伴儿放牧晚归时,怀里抱着个狼崽儿回来。
她说:“那两个人把狼皮剥了之后把尸首扔在洞穴口不远处。两只崽儿围着尸首转了很久,一个死在旁边,另一个只剩下一口气,正好一只老山羊下了羔子,我用它的初乳喂了一下它,它既然活了,我只好把它抱过来。”老两口只好把它藏在家里,用羊奶和面糊糊喂养它。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豹孩”。任何动物都有通人心的一面,何况还救过它的命。可怜的“豹孩”在两位老人的细心呵护和照料下,一天比一天长大,越来越可爱,小家伙整天尾随着两个老人的后面,缠着他们的腿,玩耍个不停,夜里睡觉也钻到他们的皮袍里。不多久它已长大好几倍,一出去就被狗追咬,吓得它拼命往家里逃。领它到羊圈里,它就追逐羊群,真是本性难改。它经常给他们添麻烦,没办法,老两口就在外面给它搭了个窝棚,拴在里边喂养它。以防被别人发现,就把窝棚搭在离家稍远点儿的地方。一个冬天很快过去,开春之前就得搬离冬窝子。老两口只好把它放到它原来的洞穴里,除了一些冻死或瘦死的牲畜尸骸之外,还偷偷杀了两只快要死的残疾羊羔,一起把尸骸留给了它。好在他们放的是生产队淘汰羊,都是一些老弱病残的、随时准备处置的畜群,个别病死瘦死都属正常死亡,也不太追究多大的责任。
在搬迁的头两天老两口有意识地减少它的食物,使它受点饥饿。这样临走时扔给它点儿食物,它就忙着填肚子,不会跟人缠着不离。临走时老头儿留下来,把它牵到它的洞穴旁等着,他老伴儿提前牵着骆驼,赶着羊群走远后,老头儿才把食物扔给它。它忙着吃食物间,老人偷偷地溜走,躲在暗处观察了一会儿。它只顾着吃,浑然不知老人已丢下它远去。它虽然长大了,但还不到自己独立觅食或学会捕猎其他动物为食的本领。这一切都只能由它父母大狼带着它进行系统训练后才学会。老两口过上十天半个月过来一次,在它洞穴附近扔一些从野外捡来的动物尸骸什么的,然后就悄悄离去。野生动物毕竟就是野生动物。没过几个月,见到人它就逃得远远的,根本不接近人。给它食物也不过来,等到人走远了,才过来小心翼翼地挨个儿嗅闻,觉得这些东西安全,才吃或拖进自己的洞穴里。就这样一冬天加春天很快过去,他们家也搬往夏季草场,远离了冬季草原。在搬家前,老人又带着一些吃的去了一趟,也是最后一次。豹孩也长大了,几乎跟大狼差不多高。它看见老人就躲到远处站着,舔着嘴,摇着尾巴,一会坐下,一会儿站起来,似乎在跟他表达着什么似的。在家的时候,有时也会这样来着,不知道表示感谢呢,还是在告别。并且在原地转圈或来回奔跑,显得非常不安。老人离开食物后,坐在不远处,观察了一会儿。豹孩也在原地转着圈不时地看着老人,也不像往常一样赶紧过去,吃给它的食物。老人和豹孩都在原地相互观望了一段之后,老人骑上马离去,豹孩立刻起身远远跟随他一段距离后,跑到一个较高的凸包上,嚎叫了几声后一直站在那里望着。老人几乎看不清它时,它好像还在那里站着。
不知道被谁发现了这一切,给大家散布出去的,全生产队人都知道了。搬到夏季草场,没几天生产队开群众大会批斗了他们。罪名为“以社会主义生产队的羊,喂养狼崽,实属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家本来就是牧主成分,是属戴“帽子”的黑五类分子,这一下可罪加一等了。老两口还能说什么呀,何况根本不让他们说话。连续几晚上挨批斗后,以老实“认罪”的态度才放过了他们。后来才知道,是巴利吉队长的儿子在外面搭夹子时看到的,他也没能抓到它。
第二年冬天老人到它洞穴口查看时,在洞口没发现任何踪迹,看来它很久没在这里打窝。这里是生产队冬季草场最偏远的地方,水草最差的盐碱地。一般都是家庭成分不好的牧人家或放精羊群(阉割的公羊群)的人家到这草场过冬,是只能够吃三四家羊群的草场。这一年一共三家来这儿过冬。老两口一方面默默地祈求不要有什么狼来袭击人家或自家羊群,另一方面也盼望能发现豹孩的一些行踪。他们每天出去在外放牧时,非常细心地观察一些洞穴和狼可能打窝的地方。可是一个冬天什么也没发现,老两口似乎有点儿失落。来这儿过冬的几家没发生任何事情,很平静地过了一个冬天。到了第三年冬天老两口发现了豹孩它家族的一群狼。老人从远处一眼就认出了它,当老人和它们相遇时,其他狼很快躲到了背处,唯独豹孩转过身来上到高处,看了他很久。老人用望远镜清楚地看到三年前放生它时,专门为它缝制的护身圈仍挂在它脖子上。也就在那年冬天,在北边的两家羊两次被狼袭击,损失了几只羊。生产队派来两个民兵,他们在那一带搜寻了两三天,发现后开了几枪,一个也没打着,最终让它们给跑了。他们两家的羊群也没再遭袭击。以后的三年时间内,偶尔也有几家羊群遭袭击,但没损失几只羊,也就过去了。草原上羊群偶尔被狼袭击,被狼吃掉一两只羊,不足为奇。因为生物链就是这样,相互为食取舍能量而生。
又过了三年只有曲勒腾老人一家来这里过冬。这一年他们家的黑母狗踏吾克有四岁。他们家还有一只满牙的大烈獒。身高几乎跟冬天的小牛犊那么大,非常凶狠,跳起来能拽下骑在骆驼背上的人。有一天夜里他们家的羊圈被狼袭击,咬死了两只羊,还咬伤了几只羊。最可怕的是他老伴儿被狼袭击,差点儿丢了性命。如果踏吾克没跟在她身后,那天夜里他老伴儿的命肯定被狼要去了。老太婆过去想挡住被惊吓的羊群时,恰好与一匹正在咬死一只羊的狼碰了个正着,她靠的距离太近,而狼为了保护它所猎到的食物,袭击了老太婆,在把皮袍的袖子咬下之际,跟在她身边的踏吾克从它后面一跃而上,死死咬住了狼的脖子,始终没松口。就在这瞬间老人和大烈獒赶到,大獒也扑了过去,撕咬在一起,老人用手里拿着的铁管,照着狼的背部和头部猛地抡了两下,狼惨叫了一声趴下。由于铁管比较粗,打得又猛,狼的腰际被打断。被打伤的狼,拖着屁沟挣扎着,想站起来时,老人又照着它鼻梁打了一下,就地倒下一动不动。踏吾克和大獒仍在与它撕咬,老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们拉开时,踏吾克遍体鳞伤,满身都是血。袭击他家羊群的狼不是别的狼,就是他们养大后放生的豹孩。他们为它缝制的蓝布护身圈仍挂在它脖子上。无论是何种食肉动物,为保护自己的食物而与靠近的动物拼死或袭击是它们天性。豹孩小的时候,在他们家被养时也一样,要是在它吃东西时候,人或羊靠近时,它就呲牙咧嘴地“呵儿呵儿”叫。踏吾克咬住豹孩的脖子始终没松口,直到老人拉开它们为止。它的两个耳朵被豹孩撕得一条一条,就像布穗儿似的。第二天它几乎没力气能站起来,浑身没有一处没被咬,老两口每天用盐水给它洗伤口,悉心照料半个月后,伤口才痊愈。狗对主人的确很忠诚,而又能通人性。
……
这座小毡包,虽然没什么人继承,为他续火,但在他离开这世界的最后一刻,仍能给老人带来一丝温暖和温馨。老人把七十八年坎坷不平的一生、七曲八歪的身躯和以及所有凌乱无序的思绪统统裹在这件皮袍里,一动不动,裹得紧不透气。
……
老人突然感觉,从皮袍的缝隙间似乎听到了家里的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和老伴儿的喘气声。在这家里很久很久没听到这样的声音了。
皮袍里面暖呼呼……
“老头子啊!刚才在屋里有一种嘶叫的声音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踏吾克下崽儿了?”老人仿佛听到老伴儿的声音,似乎从皮袍底下钻到了老人耳边私语。虽然几十年没听到老伴儿的声音,但还能够丝毫不差地分得清。对此,老人就像昨天就在一起似的平静,其实昨天就真的和老伴儿一起!?老人好像进入了真假难分的幻觉中。
“踏吾克已经死了”
“喔!什么时候?”
“我也不知道,刚刚那只独眼流浪白狗,来这儿叫唤了一阵后消失了。”
“哪儿来的独眼流浪白狗呀?”
“啊,不不,它可能是天狗,应该叫它天狗。”
“你在说些什么呀?什么一会儿独眼流浪白狗,一会儿天狗地狗之类的,我一点儿也听不明白。”
“哦,流浪狗也罢,天狗也罢,不是前几天从南面来了个独眼流浪白狗,在我们家外面呆了几天吗?”
“什么?我怎么不知道呀?”
“噢,对啦,最近发生的事情你怎么可能知道呀!踏吾克也跟我一样老了。”
“不对,你怎么了?”
“不是说人死了之后,投胎于动物的吗?那条白狗是不是我的灵魂呀?!”
“当一个恶魂,倒不如投胎于一个祥物。在一个放牧人家当条狗也不赖,有吃有喝的。”
“恶魂?”
“是的。”
“……”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什么叫你来这儿干什么?”
“不,是我在走近你呢?或是你在回来呢?”
“什么叫你呀?难道我已投胎于狗了吗?”
“……”
独眼流浪白狗的嘶叫声再次划破盛夏的夜空后,渐渐远去。突然间从四处传来很多狗叫声,一时间冲破了这一宁静的夜晚。
曲勒腾老人的心脏阵阵刺疼。肚子也不断地“咕噜噜”叫。过了一会儿,夜壶也“滴滴答答”地响。
老人手中捻着的佛珠(玛尼珠)就像春天掉群而蹒跚在羊群后面的山羊似的,一颗一颗地慢慢滚动在老人的大拇指和食指间。
不知道是早晨还是夜晚。老人也没心思掀开皮袍看个究竟。或许太阳照着,或许月亮照着,管它什么,躺在暖呼呼的皮袍里,静静地听着刚才那些声音比什么都幸福。外面静悄悄,屋内也死沉沉。老人的皮袍里透不进一丝光亮,然而,在他心理明明晶晶。他心中暗暗祈祷,自他成家立业,在社会风云中跌宕起伏、艰难坎坷的一生就此要画上句号了。
给合作社奉献的资产、五八年的“反革命分子”、文化大革命中的“牧主”、“四类分子”的帽子,还有“文革”后退还给他的几万元钱的折子亦就是作价给的合作社的资产费、八十年代政府颁发的平反昭雪书、五保户及政协委员证等等,都在这座不起眼的小毡包里,锁在摆放于正堂的两口小黑木箱里。这两个小黑木箱是他与老伴儿结婚时,老伴儿从娘家带来的嫁妆。自进这家,他俩开灶到现在,从未离开过这个位置,老人也一样。无论给他安什么身份,戴什么帽子,他在这家里的身份和座位从未变过,是属于他的神圣权利。老人毕生的荣辱,生活,所有家产以及喜怒哀乐等,都从这家的门窗(天窗)进出。他就是这座小毡包的皇帝,小毡包就是他的皇宫,这座小毡包就与他的一生共存亡。这座蒙古包装满了老人一生的酸甜苦辣和讲述着他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
明亮的太阳虽然把阳光洒满大地,给万物提供光亮和温暖,但在草原的狂风暴雨中首先被蹂躏的就是所有弱者。
曲勒腾老人的老婆连“帽子”都没来得及摘掉就闭眼,撒手而去。是由于她的“帽子”问题,老头儿连她的后事也没能像样地料理。他老伴儿是属于个头高大的女人。老人自己一个人无法搬的动,他只好向生产队领导求援。生产队派了两个年轻人,给他们说:“别让他去,你们帮他弄到远点的地方就行。”这两个年轻人就按着队长的话,把老太太的尸体运到野外,随便找了个地方,随意放在草丛中就回来了。这个地方是生产队队长放牧的草场。此事又给老人惹了一次麻烦。说是“黑五类分子”把社会主义生产队的草场当作了自家的墓葬之地,玷污和污染了生产队牧场。其实那一带就叫“肚鲁塞图”意为墓葬区。过去有些人,家里有人去世了就在那一带野葬的。老人有一次被一顿批判后,只好自己去,重新料理了老伴儿的遗骸后,才算消停。老人去处理她遗骸时,只剩下头颅和一些骨头,骨头被啃得干干净净。从周围的狼、狐狸和秃鹫等食肉动物的那些脚印看,她很快就被“送走了”。野葬习俗讲究,人死被野葬时,尸首被野生食肉动物啃食的越快越干净为最吉。表明此人在生前所造的罪孽为最轻,认为已被“升天”了。她一辈子与人为善,乐意助人,爱惜所有有生命之物,可以说她从未造过什么罪孽,终生跟随羊群,直到生命的最后。可以说她的后半生没享过什么福,不知什么缘故,这样一个善良厚德的人,也一生遭受如此多的罪。万幸的是她走时倒没受什么太多的罪,在睡梦中很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要是有些人那样半死不活地躺倒了,不定要遭多大的罪呢。这也许是她一辈子与人为善,没造罪孽而最终得到的福分吧。
老两口在年轻时,虽然因为膝下没有个一儿半女而有些沮丧过,但到了后半辈子,经历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劫难之后,觉得没有孩子是他们的万幸,他们时常暗暗给佛合掌默谢永佑。如果他们当初有了孩子,这么些年,在这些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中,孩子不定会遭受什么样的罪。这也许是上天之意吧。老两口在后半生,别说想要什么孩子,连想孩子的精力都没有,应付于各种政治风波和批斗中度过余生。他们每当被揪去批斗时,默默感谢上苍有眼,没给他俩赐予孩子反而是不幸中的万幸。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把那些别人丢弃的小狗崽或被母羊不认的小羊羔,甚至小狼崽等,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一个一个喂养和呵护它们。
老人想,“我倒没什么,目前会有人料理我这几块老骨头的。因为,我现在的头衔是省政协委员,生产队唯一无保户,再加上,我是手中还握有几万元存折的‘有钱人,不会没人管我的。”世上的事情真是无法预料。当初归公的那点儿资产,给老人带来那么多灾难,使他们变得一无所有,真正成为了“无产阶级”,后来又变成了不小的货币,老人又回到了“富人”之列,还从戴“帽子”的“黑五类分子”变成了有头衔,有尊严的省政协委员。可笑的是,这些仿佛都与老人无缘和无关。这几万元,自老人拿到手到今天,几乎没花几个子儿,一直压在老人的箱底儿,等老人走后肯定是会充公的。无论怎么样,老人一辈子没享用到这些,到了那边更不会享用这些了。
屋里屋外静悄悄,老人突然觉得独眼流浪白狗的声音彻底消失了,偶尔传来邻家们的狗叫声,觉得声音还蛮清楚,这儿的狗叫声越清楚,说明他想去的地方还远着呢。越是听不到什么声音,他想去的地方就越近,以此看来,时候还没到。其实老人的耳朵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实际上他所听到的这些声音只是个幻觉而已。现在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不知道还等什么,老人觉得奇怪,心里也很着急。老人决心一直裹在这件皮袍里。老人深埋在皮袍里一动不动,坚持到最后一刻……
唉,该不会是却晋这个家伙合伙与过路的下边人把我的踏吾克给拾掇了吧?前些天老人看到他,领着几个下边人路过这儿来着。他那双手没有伸不到的地方。他那眼睛无论看到什么就顺手牵羊。前几年夜里从别人羊圈里把人家的一部分羊群赶回家,光天化日之下在自家门口正要屠宰时,失羊家的主人跟随其踪迹来到他家附近后,立即报警,警察过来当场把他逮了个正着,就此蹲了几年监狱。据说最近才出来。也是在前些年,周围牧民家里的狗突然个个都莫名其妙地死掉。大家以为是有什么犬科疫在传染,而惊慌失措,上报防疫部门来检验,检验结果是,认为投毒。过了很久,有人才发现又是却晋这个满脑子坏水的家伙,给人家的狗偷偷投毒,害死不少人家的狗。大家知道事情真相等报警时,人已跑的无影无踪,最终也不了了之。
原来王吉勒家的白爪子是踏吾克窝的崽子。也是这却晋打夹弩被弄死的。王吉勒老汉把皮剥下来后,来邻家喝酒,恰好却晋也来这里碰上了王吉勒老汉,老汉气不够他,正好也喝了一点酒,他趁这个劲儿,与却晋吵了起来,手里还拿着刚剥下来的狗皮。当时曲勒腾老人也来这家,突然踏吾克冲了过去,袭击王吉勒老汉,幸好老人反应快,把狗皮甩了过去,躲过了被踏吾克咬伤的危险。从那时起,踏吾克见不得王吉勒老汉和他家的任何人。偶尔王吉勒老汉来他家,坐在屋里说话时,踏吾克就不停地围着蒙古包跑,一听到他说话的声音,它就对着声音叫唤,恨不得钻进来狠狠地咬他几下。有一年王吉勒老汉家与曲勒腾老人邻家几个月,它就不分白天黑夜,只要他们家稍有一丁点的动静,它就对着他家,叫个不停,几个月几乎天天如此,连他家的坐骑也不放过。狗也记得,那是它的孩子,是它身上掉下来的肉,这大概是天然的感应吧。
俗话说,“红眼了”是指却晋这样的人吧。他已不少次被惩罚,一点也不吸取教训,死不悔改。偷盗别人家门口的坐骑,盗窃别人的财物,合伙与社会盲流,偷盗和屠杀人家羊圈里的羊群,撬门溜锁,没有不沾手的。不仅这些,据别人说,他现在与下边盲流一起吃狗肉,真是五毒俱全。最近领着几个氓流以收羊皮、买牛羊为名,挨家挨户串门来着。其实很有可能在预谋为再一次的大偷盗行动而在踩点儿呢。近几年常常一些盲流或里外勾结的团伙白天踩好点,夜间开着车去牧民家,明目张胆地进行偷盗。更可恶的是,常常把一些野外骆驼的四蹄和峰囊活活割走,遭残害的骆驼被发现时还活着,那种惨状,简直可谓惨不忍睹。这些人连野兽都不如,野兽捕猎动物时,也先咬死它后才吃。还有的把一些动物的嘴,用铁丝封口袋似的封死,使它无法吃草喝水,活活饿死或渴死。可以说,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能干得出来的事。
俗话说,干尽坏事,残害生灵,造孽罪深会遭报应的。却晋的大儿子去年突然瘫倒,失去知觉不久离开人世。据说,今年春天他自己喝酒后夜里出去不慎掉进一大坑里,摔断了几根肋骨,好了没多久,他老婆又得病去城里,最终也没能治愈就去世了。不知是真是假,听人们议论,有个活佛还是什么圣人之类的说他,“你现在造孽太深,还经常吃一些不该吃的东西。你呀,该慈悲为怀,尽量做些善事,如果现在你能减轻一些罪孽,或许将来你的灵魂还能得点宽恕。”所有灾祸都落在了家里人身上,他却无动于衷,丝毫没什么感觉,也许他的情感神经已麻木了。世上万物都有其守护神,如果未准许肆意残害其生命,会受到其守护神的惩罚。老天爷是有眼的,没人能逃脱得了老天爷的惩罚。
老人越想越觉得他的踏吾克失踪,就跟这却晋有关,他路过这儿没几天,踏吾克就失踪了。这家伙连一个临死的老狗也不放过,它也没招他惹他。该死的家伙总有一天,他那两只沾满污垢的手指不被别人剁也会因手指甲溃烂而手指坏死,成为无指秃手的惩罚。老人在皮袍里面想那些似乎已与他无关的事情,把自己气的浑身发抖,几乎把那最后几颗还没脱落掉的黄牙咬碎……
老人就这样在这件皮袍里面躺了多久,他自己也已不清楚了。他的肚皮几乎已贴到了脊梁骨上,觉得身体也越来越变薄,要不是裹在皮袍里面,似乎能飘起来。究竟是什么缘故,他觉得身体越来越变轻,感觉就像漂浮在空中。看来很快就能听到“狗叫声(快到终点)”了。很快能离开这红尘世界。在他脑海中浮现的那些嘈杂声,开始越来越淡漠,知觉也慢慢变模糊……
盛夏冉冉升起的朝阳把哈吉尔草原照亮的一丝无漏,通亮的朝霞已灌满了草原上的每一座蒙古包。牧民家一天的生活,平常天刚刚发亮就开始,挤马奶的人家,一大早把马群赶回来,已拴好所有马驹。挤牛奶的人家也已挤完了早晨的奶,开始放走母牛。
曲勒腾老人的小蒙古包外面,在拴马庄上拴着两匹已备好的马。临近的一些人,在忙碌中偶尔投去好奇的目光。他们往老人的家方向望两眼后,心想“哦,这么大清早会是什么人呢?”谁也没有再仔细想就忙于自己的事情去了。
顿珠布的儿子纳木扎布、其外甥哈杜尔夫两人是经常挨家串门,要酒喝的酒鬼,每到别人家,帮人家干点活儿,解决一下肚子,向人家要个一瓶半罐的酒,解解酒瘾或挣两个钱,立马跑到乡上去醉上几天,把那点钱花光了,再去挨家串门。最近听有些人讲,偶尔也有顺手牵羊的时候。两人进老人屋后,呆呆的看了老人一阵,悄悄交耳说了几句后,慢慢过去掀开老人的皮袍领子,睁大眼睛瞅了一会儿。两人都咧着嘴相互看了看,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然后又目不转睛地注视了老人的皮袍很长一会儿,看是否有动静。
“是不是已经死啦?”
“啊!不会吧。”
他们又一次掀开老人的皮袍,观察了一阵子,看老人没任何反应后,互相点了点头,又把皮袍盖好后,两人都笑得浑身发颤,但谁都没有笑出声音。他俩笑完后,开始随手翻动屋里面的东西,连老人枕头边的黑匣子(用了多年的一个小木盒)都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找到什么可值钱的东西。最后两人各自拿了老人吃饭用的银碗和熬茶用的铜壶后,把那些翻动的东西稍稍归位,收拾了一下后,又互相点头示意出来,两人谁也没说话,快步走到了拴马桩前,解下马绳骑上马,纳木扎布犹豫了一下,给对方说:“哈杜尔夫!老头儿已经死了,不管怎样,我们应该给队里的领导或给什么人说一声吧。”
“舅舅,他真的死了吗?”
纳木扎布回答说:“如果没死的话,刚才我们俩在翻动屋里东西时,不会起来吗!?”
“倒也是。”
“大家不是说,老头儿很富裕,有很多金银财宝吗?黑匣子里面什么也没有啊,他把那些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了呢?”
“哪儿有什么金银财宝,听说在‘文革期间,所有的东西都被没收后弄没了。听人们讲,‘文革后赔偿了些钱。加上五几年给合作社充公一些资产和牲畜被作价后,应该有个几十万元钱。”
“啊,那些钱应该在什么地方?刚才为什么没找到呀?”
纳木扎布回答他的外甥说:“据说把折子长期存放在乡政府信用社那里,找到折子也没用,那个钱到不了你我的手里。”
“噢,那那些钱会不会到尼玛手里?”
“不可能到尼玛手里的。生产队会把它转到集体账户里充公的。”
“会那样吗?”
“当然了。又没有一儿半女的,也没有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什么的,你看着,肯定被充公到生产队的账户里。”
“好吧!好吧!那我们现在要通知谁呀?”
“去碾毡的地方,那儿人多,也许生产队的领导就在那儿。”
“好吧!”两个人说着,朝正在碾毡的桑布家,一溜烟策马飞奔。
曲勒腾老人仿佛模模糊糊知道一点儿有人进屋来,但他始终没理会,一直深埋于皮袍里面丝毫没动。好像还有意识地憋着呼吸,慢慢地呼气送气,似乎怕他们发现他还活着,好像又怕吓着他们。他想,随他们拿吧,反正我现在也不需要这些。所以,刚才他一直没动静,甚至在他们掀开皮袍,看他时还憋着气,使他们信以为他死了。“唔吗呢班咪哄”老人又在皮袍里面默默地念着玛尼,数着佛珠,祈求道:“老天爷,请快点告诉我,我现在是人是鬼,我现在自己也不知道在何处,求求老天爷!”老人从没动摇过对苍天的信任和崇拜。上天的存在在他心中是不可动摇的,这一生无论遭遇什么灾难或不公,他从未怀疑过。他把对上天的崇拜深埋于心中,自己一个人时,经常默默地对上天祈祷。他的意识一阵清醒,一阵糊涂。现在的人们都不去寺院拜佛念经,也没有任何信仰。曾有点信仰的一些人已老的老,死的死。他们也肯定和他一样终身把信仰深藏于心底。
常言用“屋外听不到狗叫声,羊圈里看不到半头羊”来形容一家的一贫如洗。这句话仿佛在说我,要是我的踏吾克在,哪有刚才那两个家伙的胡作非为。任何动物都有通人心和天然聪明的一面,人人都觉得,它们是动物,不能思考,不能说话,除了吃什么也不能。但事实不是那样。我的踏吾克尤为聪明伶俐,无法用言语来表述它,让人想象不到的聪明之处。由于它的搭救,我才多活了这么些年,不然老天早已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五年前的冬天,我一个人骑着骆驼在乌戈湖芦苇丛中走时,不慎骆驼在冰上滑倒,右腿被压骨折,冰冻的三九天一个人在芦苇丛中,躺在冰上,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应,活活被冻死是无疑的。幸好,踏吾克跟在我身边,我才得救。乌戈湖芦苇丛比骑骆驼的人还高,芦苇又高又密,要是在里边寻找什么,不直接撞上的话,根本就看不到什么。就在你眼前,两三米的距离内也看不到的。我的腿骨折后无法动弹,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刺骨的冰面上,虽然有气无力地喊了几声,可在这儿没人能听得到我的声音的。何况我这嘶哑的声音只能传到十几米以外。踏吾克到我身边来,不时地嗅闻我的鼻子,又舔舐我的脸,看似很着急,还“嗯嗯”呻吟着,或“嗡!嗡!”叫两声后围着我转。我突发奇想,把我的帽子和念珠牢牢地拴在它脖子上,给它说:“快去叫人过来,你能行的,快去,我在这儿等你,你一定行的。”然后抱着它的脖子,拍了拍它脊背,又亲吻了它几下。又对它说:“快去吧!宝贝儿!我等着你。”踏吾克似乎明白了我的意图,“嗡!嗡!”叫了两声后,消失在了芦苇丛中。踏吾克一溜烟跑到邻家门口不停地叫唤。邻家人看了后,觉得它不对劲,出来仔细地观察它,发现在脖子上拴着的我的帽子和念珠,他们就知道我出事了。几个人立马跟着它来找我。是踏吾克给他们引路,他们才找到我的。我得救后,在乡政府卫生院住院治疗的几个月里,它还跑了几趟到乡政府医院看我。它专门来到我病房门口叫几声,医院的人或病友把我推出来时,那个高兴劲儿,爬到我身上不是嗅闻就是舔我的脸。比那些不懂情面的人还热情。可怜现在连个尸首都没找到。这样也好,眼不见耳不闻,由它去吧!何况我还抱有一丝希望,它没准儿还活着。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倒霉,总是落在后面,让我受罪。究竟是什么鬼东西揪着不放我呢?想死都不肯让我死。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现在只想尽快离开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去,可就是走不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彼岸,死神只在我身边转悠,却始终钻不进我的命脉里。该不会让我在非死非活之间受罪吧?要是那样的话生不如死。我这辈子也没做过那么多罪孽至深的事情,我的上祖辈们也不至于造那么多不可饶恕的罪孽吧……
不管多久,白天也罢,夜间也罢,只要不放弃,老天有眼,会把我带走的。其实老天爷一直在召唤我,就是不知道什么鬼魂缠着我不放……
“贡齐克松”、“唔吗呢班咪哄”,老人虽然在心中默诵着玛尼咒语,但仍一动不动地继续深埋于自己的皮袍下面,以非常微弱的气息默默地念叨着经,他的意识慢慢变模糊。
生产队队长得到老人不幸去世的消息后,为了料理老人后世,召集了几位长者,来到老人家里。进屋后大家把现场扫了扫,观察了一下室内的情况,然后队长嘎拉生轻轻掀开老人的皮袍,简单地看了一会儿就出来了。也有些好奇的年轻人和邻家的几个小孩儿和妇女也在老人的屋外低声“叽里咕噜”说着话。还有个别好奇的年轻人,偷偷跑到蒙古包后面,掀开盖毡(苫毡)往里瞧,还有些小孩也偷偷从门帘缝隙里往里看了后,相互“唏唏嘘嘘”地说着什么。有位年长者还压低着声音说道:“你们在看什么呀?到一边儿去!”
以嘎拉生队长为首的几位年长者坐在草地上,商谈着老人的后世。往哪里送,怎么送,送葬有谁谁去和用什么运尸之类的事情。
有个长者对着在蒙古包周围转悠的孩子们喊道:“嗨!那些孩子到一边儿去,别再往里看了,有什么可看的!”
“哎呀!前两天还骑着马,在寻找他那条狗来着,没想到现在人已归天了。”
“俗话说,树被积雪压断、人被岁月腐蚀,人已到这个年纪就这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命归天,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会把他们带走的,何况老人这些天没吃没喝地一直在野外寻狗而劳累。”
“孤身一人就这点可怕,死了尸体腐烂了也没人知道,幸好被纳木扎布和哈杜尔夫两人发现,不然还要多久才被发现。”
“是啊,虽说在我们队里老人算富裕,但死后,没有一儿半女、继承其家业,也没人亲手料理老人后事的人,也够可怜。”
“曾听一些与老人同辈们讲,老人家在年轻时家境很有富余,人也帅气又热情善良,温和可亲,乐意帮助别人,可以说是个世上少有的好人。老人的后半生却很不幸,几乎在‘运动中度过,每次‘运动都被揪出来批斗,可是受尽了磨难。”
“呼咦!不是还当了几年省政协委员了吗?”
“嗨!那都是最近的事儿,在那之前老人什么罪没受过呀?对一个几乎是耳聋眼瞎的老人来说,那玩意儿有什么用,重要的是连会议餐也没能好好吃上几顿。被别人硬拉去了两次,都因饮食不适拉肚子而住进院,受了不少罪后,再也没去。”
“嗨!嗨!扯那些没用的浪费时间干什么呀!尽快把事儿定下,赶紧动身!”
“那把他这座毡包怎么办?”
“这有什么可难的呀!看看有什么可用的东西,挑选出一些给料理后事的人答谢后,其余的都火化,让老人自己带走就完事。”
“没人想要这座毡包吗?”
“谁想要?你要啊?再说,谁愿意被戴继承曲勒腾老人遗产,而发财的名声呀?”
“老人自成家立业起,就没离开过这座毡房。老人毕生的生活及其灵魂都附在每个缝隙间,要是老人的灵魂留守在里面不肯走,带来祸可怎么办?”
“哎呦!说的也是。”
“银行里的存款怎么处置呀?”
“你操哪门子心呀!那都是银行或国家的事情,不是充公就做慈善呗。”
“嗨!嗨!言归正传,说定了早点儿动身!”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定好计划后,正准备动身时,在拴马桩旁很多狗打起架来,使拴在桩上的马都被惊吓,脱绳跑掉,人们为追逐各自的坐骑而乱成一团。
“嘿!这些狗跑这儿来,为抢什么东西打起架呢?”
“嗨!你快骑上你的马,去帮我把马赶回来怎么样?”
老人在皮袍下面以很微弱的呼吸,静静地躺着,屏住他那几乎要停止的微弱呼吸,而费力地倾听着屋内外的一切动静,想知道究竟在发生什么事情。老人似乎感觉到,从很远很远传来一阵骚动后又静下来。老人仍然一动不动地深埋在皮袍下面,丝毫没有动一下身子的念头,仍觉得浑身如纸片一样薄,感觉轻轻一动就能漂浮起来。谁知道还有没有能动的力气。据嗅到的气味来判断,肯定与心爱的皮袍一起还在自己的小屋里……
“走开!跑这儿来抢什么呀?”
“去!”
“嗨!嗨!快从前面挡一下!”
“布尔古德!快骑上你的马,从前面截住它!”跑掉马的一帮人,为了抓各自的坐骑,在外面又喊又叫的乱成一团。
“嘎拉生哥!运尸用的马被牵来了。”
“噢,太好啦!趁早行动吧!”
大家齐声道:“好的,好的。”便起身你前我后地往老人的毡房走去。
突然不知是谁喊道:“嘿!这不是老人家的黑母狗踏吾克回来了吗?”
“嘿!还真是,就是它,它这是从哪儿跑出来的呀?”
“脖子上还拴着绳子呢,是什么人把它抓去的呢?”
“看这个绳子,不是淘金者就是盲流下边人。不是他们还会谁在这么老的母狗脖子上套这么一个破绳子呀!”
“啊!闹半天,刚才这些狗打架,原来是由它而引起打的架呢。”
“哎呦!看它饿成啥样了,肚皮都贴到脊梁骨上了,快抓住把绳子给它解开了。”
“能抓得住吗?不会咬我吧?”
“不会,不会,你放心吧!它从不咬人。不然怎么会有人在它脖子上能套绳子呀。”
“好吧,好吧。”
“喂!有没有一点儿吃的?给它一点儿。不然抓不着它吧?”
“在这儿哪有什么可吃的。”
“屋里不会有吗?”
“谁知道呀,得进去看看吧。”
“可怜的老人,就为找它,没吃没喝地,骑着马在野外连续漫游了几天,一下子就给累塌了。”
“可不是嘛,它也老的已经到头了。”
“唉!你说,它现在能不能下崽儿?我想把它领回家去。”
“都已经老成这样了,还下什么崽儿呀。哦?”
“也说不准。”
“……”
“……”
就在这时,那些狗又激烈群殴,再次出现狗叫人喊的嘈杂声。于是有些人为驱散打架的狗你喊我叫的。
“去!走开!”
“你快去把那黑母狗抓住!不然这些狗不会罢休的。”
为驱散打架的群狗,嘈闹了一阵。
在这些嘈闹声中曲勒腾老人,从皮袍下面清楚地听到,踏吾克安然无恙地回来的消息。其实他什么也没听到,只是一种感觉。但他相信这是千真万确。他有气无力地掐了掐自己的皮肤。
“见鬼!这是真的,真是活见鬼了,我怎么就死不了呢?!”老人在心中默默地骂道。也不知道骂自己还是骂其他什么的。老人突然感觉浑身发热,几乎凝固的血管,就像开春时的河流一样,老人浑身的血管极速循环开来,其周身瞬间发热,仿佛浑身的血液在沸腾。老人打算坐起来,他慢慢地呼吸,酝酿着浑身的力气。他想一定要一下子就坐起来,否则很有可能再也起不来了……
准备送葬的人们已松开老人小蒙古包右侧的围绳,掀开苫毡。四个人进屋要抬老人的“尸骨”。他们正在清理脚下碍脚的一些杂物时,老人突然掀开皮袍“嗯”的一声坐了起来。老人的两个眼窝虽然有些下陷,但两眼瞪得还是炯炯有神。
门旁站着的四个年轻人“啊!啊!”的一声,你挤我拥的跑出去后只顾拼命往前跑。大约跑出去二三十米后才停下脚,转过身来定定神,双手按着胸口,喘着气,一声不吭地盯着蒙古包。外面在蒙古包附近站着的一帮人也莫名其妙地跟着他们跑。在屋里靠右上座站着的年长的两个人仿佛木橛子一样,一动不动地张着嘴巴,站了半分钟左右后,其中一位慢慢地蹲下来,目不转睛地瞅着老人的脸和眼神。老人也不眨眼地盯着他们,仿佛在问“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屋里屋外鸦雀无声。外面的人们也个个死盯着蒙古包的门,想知道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有人的眼睛瞪得比牛眼还大,仿佛能透视蒙古包里面的一切。
被惊吓而脸色苍白的一个小伙子,指着蒙古包说:“天呐!鬼,鬼!”
“什么?哪儿有什么鬼呀?”
“在,在,在屋里,曲勒腾……”他喘着气,结结巴巴说了半截,也没说清楚,接着拍打自己的胸口。
“啊!曲勒腾怎么啦?快说呀!”外面的人们都压低了嗓门,围着小伙子在追问。
从屋里跟他同时跑出来的另一个小伙子在旁解释道:“曲勒腾老汉起来了!”
“啊!你在说什么呀?他不是死了吗?已经死了的人怎么可能起来呀?” 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都傻乎乎地相互你一眼,我一眼。
“嗨,是真的吗?”
“我有病啊?开这种玩笑?!”
屋里的两个人盯着老人,大约半分钟左右后大声问道:“嗨!曲勒腾叔叔,您没事儿吧?”老人仍然一声不吭地盯着他俩,过了一阵才轻轻点了点头。
“您怎么啦?身体不要紧吧?”
老人仍旧一声不吭,稍许后轻轻地点了一下头,然后慢慢地环视屋里的一切。
他俩也小心翼翼地摸了摸老人的手,相互看了看,其中一位说道:“体温还行。来,找个东西给他后背垫起来。” 另一个人找了个东西垫在他背后。年长者说道:“来,得先生个火,烧点开水或茶什么的,给老人润润嗓子,也不知道老人家没吃没喝地躺了多久,看来身体很虚弱。”
突然间听到蒙古包里有人说话的声音,外面的人们瞬间“呼啦”一声起脚,往蒙古包跑过去,跑到门口急停脚步,谁也不敢进屋,就在门口堆积在一起,憋着呼吸听屋里的动静。有的慢慢掀开门帘往里探头看个究竟。假如有什么不测,大家都有随时往回逃跑的准备。
大家都以为老人早已过世,没有一个人仔细留意过他,也没多想什么。大家都很自信老人已去世。年长者、领导者都各顾各的,各忙各的,没有一个人想起,去看看老人是否有脉动或心跳什么的。
有半个月左右,在哈吉尔草原上飞传着有关曲勒腾老人的各种各样版本的故事,热闹了好一阵。有的人家不仅在自家门口煨桑驱邪,还有的人家,在家里点上长明灯,磕头求保佑。更有意思的是,有那么一两个,会一点儿弄神装鬼把戏的人说什么,要给老人驱鬼招魂。在嘴里还念叨着:“嘟!”之类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咒语。更为可笑的是有些人,好像亲眼见过似的,添油加醋地编造一些,不着边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地传着。
“肯定,鬼魂附体了,不然死了的人怎么会复活了呢?”
“是啊!”
“你们发现没发现,他那条老母狗的眼睛发绿光?不是说绿光是鬼火的吗?!”
“噢,对。好像就是那么说的。”
“嘿,还真是,自那以后曲勒腾老人的眼睛就发绿光来着。据他们在场的人说,首先从皮袍里发出两道绿光后,老人即可坐了起来。眼窝子都陷下去了,可眼睛却发着绿光,还面带着一丝的微笑呢。肯定鬼魂附体,使他发笑的。”
“啊!真的?”
“说假话不是人,进他屋里亲眼看见的人给我说的。”
“唉,那咋办呀?真可怕。”
“真叫人害怕呀!”
“据说鬼魂不会伤及无冤无仇的人,只要不去惹怒它的话,不会有事的。”
“天呐!那多可怕呀!我反正从没得罪过老人家,请老天爷保佑我吧!哦。”
“我也是。”
“我也一样。”
关于曲勒腾老人鬼魂附体的故事,就在哈吉尔草原上旋风似地流传。有鼻子有眼地一家传十家,十家传百家,很快传遍了全乡牧民,传得神乎其事。甚至还传到了更远的地方。还传,“哈吉尔草原,一到夜晚,就有一道绿光在野地里跳来跳去,可能是附体于老人的鬼魂,在夜间流窜于每家每户” 之类的话。
纳木扎布和哈杜尔夫,把从老人那里顺手牵走的铜壶和银碗,夜里偷偷拿来,丢弃在老人门口。类似稀奇古怪的事情和谣传究竟持续了多久,谁也不知道。没过多久,老人依旧骑着那匹老枣红马,领着那条老母狗,到邻乡最远的牧民家,给老母狗配对公狗。据说,有些胆子小或疑心大的人家,怕遇见老人,更害怕老人到他们家去。有些妇女和年轻小孩子,在路上遇见老人后,怕的连话都不敢说。老人去他们家,谁也不敢阻拦他不让进屋。大家都很小心翼翼,还不能不热情,生怕有什么地方惹得老人家不高兴。就那一阵子,遇见老人的人们,没有一个人不仔细观察过老人及其黑母狗的眼睛,看是不是发绿光。等老人走后,互相答问,老人和狗的眼睛,有没有发绿光或和从前有什么不同。
“怎么样?你有没有发现老人的眼睛发绿?”
“不知道。好像有点儿发绿,但不敢肯定。”
“我觉得好像有点儿发绿。反正觉得,与从前似乎有些不一样。”
“不,我倒觉得老人的眼睛比以前更加红了似的,没发现绿光。”
“嗨,那就对了,不是说鬼火白天发红光,夜间发绿光嘛。”
“啊,是吗?”
“不,我也不知道,我听萨满老人那么讲过。”
“吃饭喝茶不?不是说鬼是不吃不喝的吗?”
“嘿,不仅吃喝,我觉得比以前更能吃了。”
“据说鬼是不会拉屎拉尿,看没看见他拉屎拉尿?”
“看见他撒尿来着。那天到我家来时撒了一次尿,走时也撒了一次。”
“老人的下巴颏还在吗?听说仔细看的话,鬼的下巴颏和人的下巴颏不一样。”
“嗨,我觉得,所有跟以前没什么两样,没看出来与正常人有什么不同之处。”
“不是说,鬼跟孙悟空一样,想变什么就能变什么的吗?或许鬼已化作曲勒腾老人了吧。”
“不,反正我是什么也没看出有什么异常。好像跟以前没什么两样。”
“是啊,没什么明显之处。越疑神疑鬼,越觉得好像有什么不一样似的。”
“……”
关于曲勒腾老人是人是鬼的话题,没过多久也慢慢平静了。但仍有一些人不敢面对老人随便说话,还是很小心翼翼。个别妇女小孩子正好在路上遇到老人时,尽可能绕着走或目不转睛地盯着老人快速过去。更不敢与老人打招呼。
俗话说:“众狗的叫声是随头一声狗叫声的”。很多人随众人的道听途说添油加醋地相互传。其实谁也没真正看到什么。有些长辈们和有理智的人早已与老人说说笑笑,拉家常讲故事什么的。
已过半年多了。在这里什么也没发生。关于老人和鬼的话题也不议论了。没多久,人们在传老人的老母狗又要下一窝崽儿了……
责任编辑 郭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