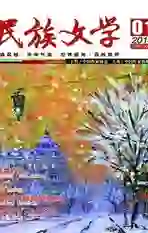旧天堂
2014-03-21钟二毛
一 偷书贼说
还是想说说“旧天堂”。
倒不是说他死一年了。而是因为我自己不快乐。
这一年,我升职了。从一个埋头写稿的愣头青,升到公关三部经理,手下有四五人,天天晚上带着美女去应酬、喝酒、唱歌,甚至找小姐,把客户搞得晕晕乎乎,然后签下合同。公司给的提成很高,老板见了我就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你也”。手下的美女一个月工资有时候高过别的部门经理,每次有大客户都抢着去,我看着她们一脸的壮烈就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你也”。
钱包和啤酒肚臌胀着,一天比一天明显。有个晚上,美女同事送我回家,问我怎么还住城中村?她的意思,我应该买房了,或者至少租个高档点的地方。我说,小婷,我不是跟你讲醉话,我喜欢住在这里,是因为这棵大榕树。
那天晚上,我真的没醉。但我得在客户、手下面前装醉。这样,客户才会满意,手下的美女才有借口替我喝酒,然后一杯杯发起反攻,直到敌我混乱、是非不分。每次从包房外推门进来,看到手下已经坐到客户的大腿上,我就悄悄退出,要么点根烟守在门前,像个保安禁止打扰;要么返回洗手间,把没吐干净的吐干净。吐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起,他妈的,一年前,我还说自己是个纯洁的人。
今天,是我来到这个城市的两周年纪念。我一毕业就来到深圳,因为我无处可去。我毕业的大学不算太差,至少是一类本科。求职简历印了一百份,我想,这些充满真诚的句子,撒向人间都应该是爱,都应该得到善报。结果,屁,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南京成都还有老家长沙,都没有一个城市愿意收留我。我不可能真的卷着铺盖回到生我养我的那个小镇,我必须找个去处。
我就这样到了深圳。在一个初中同学的介绍下,进了罗湖一家私人医院,编一本非法刊物。从网上找一些少女堕落、少妇出轨、换妻俱乐部的“口述实录”,配上一些日本AV女郎照片,每一篇文章后面跟着医院的各项业务:皮肤病、肝炎、妇科……
这些杂志成箱成箱地拖到菜市场门口、超市门口,免费派发。
我在这个医院干了三个月就遇见了他。
他是收二手书的。
后来熟了,每次他来医院找我,前台小妹都会打内线给我,唐哥,那个收破烂的又来找你了,可以上来吗?我总是纠正说,人家不是收破烂的,人家是收旧书的,你别瞧不起人。小妹操着一口烂普通话反问,不一个意思吗?
那天早上,我正把杂志分给派送工人,他站在一边要了一本看。他骑着一辆三轮车,一件白衬衫被汗水几乎浸了个全湿。白衬衫扎在黑西裤里,穿着皮鞋。大热天,手上戴着白手套。手套是纱线的,显得特别笨。翻杂志的时候,用嘴咬掉手套,才能翻过一页。咬着手套,一边看,一边嘿嘿地笑。
我问他笑什么。他说,这是你编的杂志?
我说,是啊。
他说,你是个诗人呐。
我说,你也是诗人?
我们互相嘿嘿地笑。杂志里每篇文章的标题,我都给改了,全部改成了诗,如讲少女堕落的,我就用徐志摩的诗句“别拧我,疼”,讲少妇出轨的,我就用戴望舒的“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有时候我还用博尔赫斯的“在黑暗的守夜里将他吸引”。
他在一张报纸上写上一个地址,撕给我,说,你有空可以来我的书店看书,很多诗集。
那个地址离我有点远。南山区了。至少我每次坐车都会晕吐一次。但去了一次之后,我就总盼着第二次。
他的书店全是二手书,安置在一个城中村的出租屋里。很好找,因为书店是在一楼,而且门口是一棵巨大的榕树,根系发达,盘横裸露,像老人暴突的青筋,看得我十分震惊。
书店的面积大约是四十平方,结构是一房一厅。房也是厅,厅也是房,因为都站着书架。客人都不多,甚至是很少,零零星星的,穿白背心的老人、孕妇裙的妇女,还有背着彩色书包的小孩。都是翻一翻、看一看,买的不多。
倒是书真的是很多。啥都有,天文地理、文学医学、课本杂志。有的书旧得一打开,订书针裂成两半,一看,六几年出版的。
他总是穿着长袖白衬衫、黑西裤、皮鞋,我都怀疑他只有一身衣服,晚上睡前洗干净,第二天早晨再穿上。
他叫我唐诗人。然后拉着我的手,转到一个书架前,说,你的最爱。
每次他都拉我的手,领我到诗集书架。一个大男人拉一个大男人的手,像个同性恋似的,我不习惯。但无法拒绝。
为了缩短去书店的路程,我辞掉了医院的工作,并且就租住在书店的楼上。
运气算好,找到了现在这家公关公司。我整整写了三百六十五天的公关稿,产品介绍、新闻通稿、话题炒作,雇佣“水军”、买通版面、诬陷对手等等。要么恶心自己,要么恶心别人。
有次,我跟部门经理说,干不下去了。经理说,这个行业就是这样,你必须这样。少不更事的我,一副傻鸟样,说,这是个肮脏的世界,我是个纯洁的人。
好在有他的书店。
不管有多晚,有多累,我都会去他的书店里呆一会,像只傻鸟,被他牵着手,来到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诗集书架。我有时会打开一本读了部分内容的诗集,找到折过的页码,在白炽灯管下默念一首短诗。有时什么都不干,靠在书架上,喘口气,休息几分钟。这种感觉很美好,像我高中时第一次写诗,然后被同学发现,被老师发现,被文学社发现,然后发表在黑板报上、校园小刊物上。那种悄悄地被流传、被议论的感觉,真的很美。
他从来不过来打扰我。我一直以为他有一天会过来跟我谈论一首诗,一个句子,或者一种写法。但是从来都没有。我怀疑他不懂诗。
有天晚上,不知出于什么缘故,我偷了他的一本诗集,《博尔赫斯诗选》,记得很清楚,绿色封皮。可能是心虚,我把博尔赫斯放进包里,然后假装买了一本顾城。
这是我第一次在书店里花钱,三元。他很高兴,说顾城是个纯洁的人。
我心虚极了,反问一句,那你觉得我是不是个纯洁的人?
他说,你不是。
我的心颤抖了一下。他知道我偷了他的书?怎么可能!
我故作镇静,哈哈一笑,现在还有谁是纯洁的人?
他接过话,我。
我这个偷书贼,再也不敢说自己是纯洁的人。有一次,经理打趣我,纯洁的人,晚上部门去酒吧HAPPY,准时到啊。我反驳说,我不是纯洁的人。
确实,自那之后,我去书店的次数少了,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我想买车,我想找一个固定的女朋友。再牛叉的博尔赫斯给不了我一个汽车轮子,一次不慌不慢的床第之欢。
我开始主动出击,参加各种活动,展示实力,混个脸熟,请客吃饭,私拉客户,积攒人脉,最后成立公关三部,带领一帮打了鸡血的愣头青,打入食品行业,做危机公关,找内线、黑客、水军,帮人灭火、擦屁股、补漏子,混淆视听、转移话题……
不要脸,不要脸,坚持不要脸。
你黑,我更黑,我更黑黑黑。
就这样,我成功了,成了车主,成了领导,成了请客买单者,成了合同乙方签字负责人,成了在女人床上打滚的烂人。
成功意味着没有了时间。我当然没有忘记那个书店,还有纯洁的他。但半年多来,我们再也没有一次交集。这么说吧,半年,一百八十天,有六十天,我在外地拜访客户,或者请客户游山玩水玩女人;有六十天,在公司里加班到天亮,讨论方案,修改稿子,精疲力尽睡在格子间下面;剩下的六十天时间,倒没那么悲催,吃喝玩乐、花天酒地,不是我勾引别人,就是别人勾引我,没有一个晚上不是凌晨两点后才罢休(因为酒吧都是凌晨两点打烊)。这狂欢六十天,有三十天以上不是睡在酒店里,就是睡在女人的家里。
有一次,半夜,我回到自己的出租屋里,按开灯,看到两只硕大的老鼠在床上吱吱叫。它们也不怕我,仿佛这是它们的床,一前一后,嬉戏的样子,像在求欢。这让我想起,我刚来这个城市时的第一份工作,在医院里编黄色小报,就经常找一些夫妻做爱的技巧文章。两者好像没什么关联,但却我莫名难过起来,觉得自己每天都过得他妈的好荒唐。
我下到一楼,看着关闭着的书店,情不自禁地轻轻叩了下玻璃窗。无人应。我看到门与窗之间的墙上,钉着一副新招牌:旧天堂。三个字是用木棍拼起的。木棍钉在板上,板钉在墙上。趁着亮光,还看到,木板右下角用毛笔写着营业时间:中午十二点到晚上十一点。
那晚我在楼下没呆到十分钟,困意就上来了。回到小屋,赶走老鼠,定好闹钟,呼呼大睡。更多的客户、单子、女人等着我去消灭,瞬间的感触,一文不值,就是一个屁,放出来完了就完了。
只是没想到的是,等我再一次想起书店和他的时候。一切都完了。消失了。有人说他是出家了。我认为是死了。但不管是出家,还是死,真的就像放了一个屁。轻得没一点重量,甚至,连点臭味都没有。
二 大榕树说
我就是书店门口那棵树啦。大榕树,枝叶茂密,根系发达;下雨的时候,可以在我下面躲雨,大太阳的时候,可以在我下面乘凉;还可以在我下面摆摊,烧烤,啤酒,喝醉了唱歌跳舞;深夜,人们散去,还可以靠在我身上,男女抱着接吻、抚摸。都可以,我乐意看到人间处处欢乐。
可是,我现在看不到了。我现在只剩下一截埋在土里的树根,水泥盖着我,呼吸都困难,简直可以用“垂死”二字来形容。
我的上半身怎么没了呢?还不是因为这个伟大的国际化城市。这么好端端的一个小区,三十年历史啦(我也就是三十年前就来到这里的)。房屋不高、间距宽敞、绿树成荫、邻里和睦,干吗非得拆掉重建呢?真搞不懂。
拆掉重建,一开始是很多人反对的。他们选出代表到管理处闹过,还打过横幅,上过报纸。我想,这些人还是重感情的,念旧的,心里很高兴。
其实我傻。他们到管理处闹,打横幅反对,是因为房地产商给的补偿太少,他们要一比二的面积补偿,还要送精装修和终身免物业管理费。房地产商只答应一比一点五。
我以为他们真的是念旧,是留恋这份延续了三十年的生活气息和共同记忆。屁哦。
谈判谈了两个月,就达成了协定。一比一点六的面积补偿,终身免物业管理费。
协定一达成,反对的横幅改成了“热烈庆祝我市首个旧城改造项目正式启动”。电视台来采访,居民脸上堆着亲切的笑容。
旧城改造规划时间是五年。但我是第一个被改造的。按理说,大家都有保护意识,我顶多是被迁移走,不至于牺牲。谁知,开放商一队人在勘测时,一个大胖子说,整个小区五十多棵树中,就数我的根部最庞大,碗口大的根须吃到建筑下了,不移植,会影响到规划,移植,工程会很大,预算要增加……唧唧歪歪的话说了一堆,最后胖子潇洒地挥了下手,轻声说了句,无所谓啦。
无所谓让我有所谓。没有人开会讨论,没有人声张反对。一把电锯让我从此深埋地下,一瓢水泥稠浆让我从此呼吸困难。
在黑暗的世界里,我只能靠着回忆维持最后的生命。
所以,我想同你们说说“旧天堂”。
毕竟,那三个字就是从我身上折下的木条。想起那些木条,我就觉得自己还活在光明世界里。
他上午出去收书,下午回来营业。有个习惯,下午开门,头一件事,是把收到的书从袋子里取出来,码上书架,这个过程很快的,因为他在收书的时候就已经暗地分好类了。那天却没有直接码书,而是打了个电话。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歪靠在书架上,边打电话,边瞅着书,很高兴的样子。
电话打完后,啥事没发生。第二天下午两点,一个女孩出现了。白T恤,牛仔裤,头发扎得高高的,长得蛮漂亮。他从桌子下拿出那本厚书,交给女孩。两人说着笑着,走出来,坐在我的树荫下。
那本书叫《丛林故事》,封面上写着罗德亚德·吉卜林,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大家,童话小说巨匠。
看到头发扎得高高,我想起,之前,这个女孩来过一次书店,也是下午两点多的样子。每次来,看她眼神,都好像没睡够似的,泡着个眼,脸上血色也不多。那天,女孩在书架上转了一圈,然后给他留下一个纸条,想必那纸条上就是“丛林故事”这四个字。
一个爱看童话书的女孩,好少见。
他是单身啦。至少这么多年我没见过他有女朋友。他第一次追着人出门,喊住她,问她的电话是多少。女孩又在纸条上补了一行字。女孩走了,他半天没回过神,依依不舍的样子。鬼都看得出,这小子动了芳心。
难怪,找到《丛林故事》后,他那么开心。
两人就这么认识了。后来我看到的是,隔三岔五,下午两点多的样子,女孩来书店,取不同的童话书。他们蛮聊得来,总是走出书店,在树荫下依依送别。
过了很久,有一个晚上,女孩破天荒地出现在书店门口,那天晚上好像都快过了十二点了吧。书店没关门,好像特意在等她。换了个人似的,她打扮得好妖艳,短裙、高跟鞋、头发打着卷,从背后就可以猜得到她肯定还化着浓妆。他们搬着凳子,坐在树荫下。我闻到浓浓的香水味。听他们一聊,事情明白了一大半。
这个女孩是夜总会里的“公主”,站在门口迎接宾客,帮人点歌,拿小费。通宵工作。我们伟大的书店老板,早就摸清了情况。一次跟踪就够了。几个月的交往中,他不停地鼓励女孩辞去夜总会工作,找个白天上班的工作,再报个大专班,两年后拿个文凭,比什么都好。女孩被说动了。他当天就帮她报了名,交了一年的学费。“公主”连夜把职辞了。
就这样,女孩找到了一家外贸公司,做前台,晚上上夜校。他们自然成了一对,情投意合。书店生意好不好,我不晓得,但那段时间,他的脸上是笑眯眯的。两年后,女孩还真拿到了大专文凭,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上班第一天,黑西裤黑西装,一身利索。
就是那天晚上,他们在我身上折下一堆小木棍,在木板上钉出“旧天堂”三个字。
他说,这个店名,他早想好了。就是想等到一个心爱的人,一起把它挂上去。
女孩在律师事务所当的是律师助理。
就是这个助理当坏了事。不出一周,女孩就开始不准点地出现在书店里。接着,一个月后,就压根看不到人啦。
这个城市很多事情,变化得比台风还无常。天气预报说,台风要来要来,结果影都没有。书店老板和律师助理的爱情,也是这样,眼看呼之欲出,结果,影都没有。
律师助理有了更好的出息,丢下一个灯影暗淡下的瘦男人。
恢复单身的瘦男人,倒没看出他有多伤心,或者消沉。照旧,上午收书,下午营业。我经常看到他打女孩的电话,手握一本书,花花绿绿的封面,无疑还是童话书。有时见他和女孩通着电话,但都很短暂。有时候,看他皱着个眉头,然后把手机合上,十有八九是对方没接。没接,没关系,他把书名发短信告诉她。
女孩始终没有来拿她的童话书。那些童话书被藏在桌子下,被我们的痴心爱人用牛皮纸包着,谁也不卖。
他们俩的事,我能讲的,就这么多。
后来,女孩是否回心转意,是否回来取她的童话书,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被埋到了地下。
三 准爸爸说
今天我辞职了。昨天,我还是一家新闻周刊的记者、主笔,负责封面报道的专题策划、统筹。这本全彩色铜版纸杂志,收益很好,记者的工资高过同城党报、都市报。但我厌烦了。我不想贯彻主编的三项基本原则:要么揭秘,要么娱乐,如果这两个都不靠,那就实惠点,换点广告创点收。我不想让每条新闻都被改成《××行业大揭秘》、《××骗局大起底》,我也不想采访每个名人都绕着弯子问,你和那个明星是怎么回事。
回顾这么多年的记者生涯,我问自己,策划的专题报道,大大小小,近百个,有哪个是可以留底欣赏的?没有。
在我辞职之前,有个报道,我想“做一回自己”。因为,我马上要当父亲了,我不想天天唯唯诺诺地过着。我想给未来的孩子做个榜样。
这个报道就是“旧天堂”事件。提交选题时,我说,这三万本书,扫地出门,扔在地上,天一下雨,全部泡汤,要报道,拯救这三万本书,关注民营书店的生存;可以不发封面报道,但至少可以发阅读版。
主编说话很犀利:咱们周刊确实有阅读版,但那都是书商给钱买的版面。要搞文化,也可以,但,钟二毛,我问你,每天多少本新书出来,有哪本书是必读不可的?有哪本书是必报道不可的?没有!没有利益关系的书,我们为啥给他做宣传?任何版面都是钱,版面也是生产力。当然,也包括阅读版。
主编顿了顿,又呵呵地笑着说,当然,也可以破例搞一回,但你要想一个问题,报道出去了,万一没有人响应,拯救不了怎么办?这涉及到我们杂志的影响力。影响力也是生产力。所以,我要一个圆满。你能圆满,就去报道。
好。我豁出去了。不管怎样,我都要把这个事搞圆满。
报道一:
这么大个城市,容不下一个“旧天堂”?
本刊讯(记者钟二毛)旧天堂。一个二手书店的名字。一个关于书的悲情故事。
故事主人公的名字和书店名字一样美:田园诗。田园诗十年独自一人坚守“旧天堂”,做着他的书店梦。书店就是家,家就是书店。连厨房、卫生间都摞满了书,晚上就在书垛上铺一门板,枕书而眠。
一个月前,因为交不起房租被房东赶出门外,三万本书也失去了栖身之所,撒在门前空地上。一周前,他说去广州找买家,就再也没回来。他在“旧天堂”招牌背面留下三个字:书无罪。多名逛过书店的书友,自发找来硬纸板、塑料泡沫,把书垫起来,免得书受潮。但随着雨季来临,书的命运揪着爱书人的心。田园诗的六旬老父天天拨打儿子电话,却换来一遍一遍的“暂时无法接通”……
书店梦:让所有人都爱看书
“旧天堂”藏匿在偌大的旧城改造小区里,很不好找,但只要问问小区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详细的路线。可见,这个书店,街坊邻居很熟悉。找到“旧天堂”,书店变成了露天书摊。满眼旧书暴露在空地上,一排排的书架摆放在楼梯前,一个老者——田园诗的父亲,正在招呼零星的两三位顾客。“这还是微博转发后,才有这么多人。”热心书友姚先生说。
田园诗的父亲说,儿子被赶出来之后,就喊他过来帮忙。他来的第二天,儿子说他要去广州找买家,第二天中午回来,还交代他晚上别走,书不能离人。结果第二天没回,第三天没回,第四天接到电话。电话里,儿子让他办三件事:拖车要还给十二栋三零一的黄老板;借楼上二零三全老弟的两千元,先还上;书堆里有一捆书,是油纸包起的,全是童话,不要卖,直接烧掉,一定要烧掉。这个电话之后,儿子就音讯全无了。
在父亲的记忆中,田园诗高中毕业从老家月拢沙出来,几乎身无分文,一路扒车先去了北京,再下广州,之后来到深圳。这一离家就十年了。在父亲印象中,田园诗内向,不爱说话,就喜欢看书。前些年,应该是积攒了些钱,他搬到这个小区,租了个一楼的房子开旧书店。每年春节大年初一,田园诗都会打电话回去,让父母不要担心,说他在城里要开一个最大的二手书市场,让每个来的人都有收获,找到自己喜欢的书,要让不爱看书的人都跑来看书,闲着没事的人也跑来看书。
爱书成痴:完全不是在做生意
“每个爱书的人都有一个书店梦”。熟悉田园诗的朋友说,他的梦做得太无边无际。
光顾过“旧天堂”的朋友,向记者回忆起田园诗的一些事情。楼上住户邢先生说,他搜集来的书,种类繁多,人文、历史、哲学、科技、文学、自然,无所不包。有爱书之人曾在他这儿淘到了三联版叶灵凤先生的《读书随笔》、王元化先生和夫人张可合著的《莎剧论集》。但有时候觉得他就是一个怪人,完全超出了做生意的样子。每次收了旧书回来,田园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每本书细细擦拭,然后挨页翻,缺页的书就不要了,破损的地方则修补好,折角的地方给抻平。一本旧书折腾半天,还做笔记。
艺术家坚果回忆说,旧书无价,碰到顾客喜欢,讨价还价是常事,但田园诗碰到聊书聊得高兴的,不仅便宜卖,还附赠几本书;费孝通的《中国乡村考察报告》,在网上,这书得四十块,他才卖五块钱。坚果感叹,他完全不是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经营书,他坚守的是关于书的理想。
隔壁一栋的李先生这么评价田园诗,对旧书太执着,个性内向,不善经营,太过理想化,收书只因兴趣不为利益,是他书店失败的原因。“两年前,我就说他会失败,”李老先生说,“他天天吃馒头,但是卖书却很便宜,我跟他说定价要保证不能低于同行的半价,但他却半卖半送。遇到爱书的人买完书,还问人家有没零钱坐车,两块、三块,给人送路费。”
众多热心书友都在出谋划策找线索,希望田园诗早日出现,让他看到这么多人在关注他,把“旧天堂”继续经营下去,完成他未完成的梦。而对田父来说,他只想让儿子尽早回来,把书处理完,回家种田去,因为“睡在书上,很难受”。
报道二:
“旧天堂”事件追踪报道
田园诗疑已出家
本刊讯(记者钟二毛)一周过去,“旧天堂”主人田园诗仍未现身,手机仍然联系不上。天降大雨,幸好有众多书友伸出援手,拉起防雨毛毡布,盖住了三万册旧书。本刊独家报道刊发后,全城媒体跟进报道,同时微博上也有网友呼吁大家关注这家旧书店的命运。很多读者周末以购书的方式,支持“旧天堂”。
记者在协助田父整理旧书的过程中,翻出了田园诗的两三本笔记本。里面有账目,有读书文摘,也有零星类似日记的感想,并夹杂了他与寺院的书信往来。笔记本里记有一些寺院的电话,包括六祖寺、南普陀寺、广化寺等。
借过钱给田园诗的全弟推测,田园诗极有可能已经出家,因为他本来就是佛教徒。全弟说,他被房东驱出门外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病过两次,“一次感冒,半夜吐得厉害,我去看他,叫他去医院看病。他说医院贵,他准备去一个小门诊拿点药吃。但他最终连这个小门诊都没去。他还有肾病。有次,痛起来,他头抵着书,骂了句粗口,说自己连乞丐都不如。”
记者试着联系了小区管理处,能否先将书存放在他们那里,以确保不淋雨,田父也不至于睡在露天书摊上。管理处说这不是他们的责任,可不可以存放还要请示领导。
也有几家旧书店打来电话,表示要一口气全部买走。但价钱开得很低,用书友们的话说,“简直是趁火打劫”。
几个热心的书友商量,继续发动热心市民,关注“旧天堂”,在田园诗出现之前,保护书,卖书,确保每一本书都能找到它应有的归宿。
报道三:
“旧天堂”事件追踪报道
悲情故事有了圆满结局
本刊讯(记者钟二毛)田园诗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一个与书有关的悲情故事终于画上了圆满句号。一个多月来,在热心书友的帮助下,旧书终于有了归宿。截至昨日,三万多册旧书全部售出,这一结局多少给众多牵挂此事的书友们增添了几许暖意。
值得提到的是,昨日,被挑选下的一万多册旧书,由一神秘男子悉数买走。他说,书无好坏、时髦土旧,任何一本书都会有适合它阅读的人,这些挑剩的书仍有价值;田园诗是个有理想的人,但其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甚远,他愿意为他把梦圆完;希望每个人为理想活着,并祝福所有坚持理想的人们。
责任编辑 安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