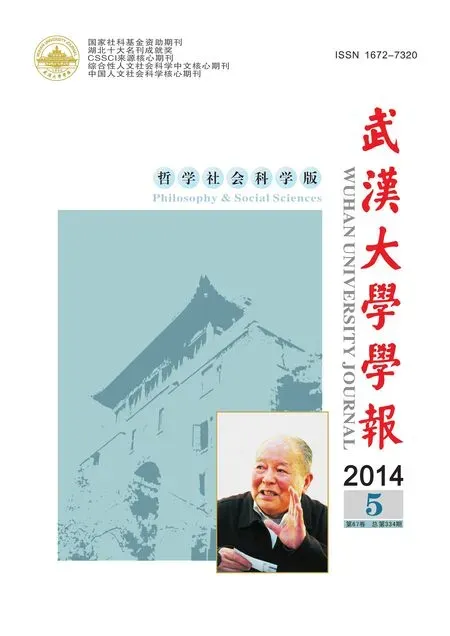慎终追远与国人之灵魂归宿
2014-03-19陈仲庚
陈仲庚
“慎终追远”是中华民族高度智慧的结晶,它不仅为农耕文明需要的道德教化找到了一条捷径,也为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形成和大一统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还为个体生命的精神寄托找到了温馨而永久的终极关怀。可以说,无论是在中国文化或世界文化的背景下,都没有任何一种文化理念有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时至今日,我们只要看看清明祭扫的盛况,就不难体察其影响力的深入人心。
一、慎终追远与民德归厚
就现有的文字资料来看,“慎终追远”的最早出处来自于《论语》。《论语·学而》载:“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记载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往往只有结论而没有解释,所以我们得通过后人的注解来了解其内涵;而在后人的诸多注解中,孔安国和朱熹的注解应该是最权威的。孔安国注曰:“慎终者,丧尽其哀;追远者,祭尽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归于厚也。”朱熹的《论语集注》曰:“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民德归厚,谓下民化之,其德亦归于厚。”在“慎终”的问题上,孔安国似乎更重“情”,强调“尽哀”;朱熹似乎更重“理”,强调“尽礼”。但在“追远”的问题上,孔安国强调“敬”,偏重于“理”;朱熹强调“诚”,偏重于“情”。所以,二人的注解并无本质的区别,后人也一直沿袭他们的注解来理解其含义,如杨伯峻将这两句翻译为:“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追念远代祖先,自然会导致老百姓归于忠厚老实了”(杨伯峻,1980)。邓球柏则翻译为:“统治者若能尽礼治丧、竭诚祭祀祖先,人民的品德就会美好起来。”(邓球柏,1996)这些翻译,几乎就是把孔、朱的注解由文言文变成了白话文。
但是,到了21世纪,则有了一些不尽相同的看法,如周远斌认为“曾子‘慎终'一语应理解为:孝、悌等德行善举,自始至终,一而贯之,不但有始,而且还要能终”;“以曾子的行仁之道、‘死而后已'之语句,来解释‘追远'一语,是再恰当不过了”;“理解‘民德归厚',关键在‘归'字上,民德变得敦厚,可简言为‘民德厚矣'。”(周远斌,2006)作者完全排除祭祀、念祖的宗教性内涵,而给予一种纯“现世主义”的解释,显然是受到孔子“未知生,焉知死”一语的影响。还有人从当代现实需要的角度进行解释,如迟宇宙认为,“曾子最初说这句话的意思就可以解释为:如果每个人都能在做事前三思其动机、初衷,并且能遥想至其后果,那么民风就能淳厚,人们就能少做错事”(迟宇宙,2010)。该文发表在《商业生活》的《成语别裁》栏目,那么作者的解释自然也是“别出心裁”了,这是在商业背景下对“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一种实用性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到了21世纪会产生一些“现世”而“实用”的“别解”呢? 这大致是因为孔、朱的解释正切合了农耕文明的社会实际,因而无人怀疑,也无需“别解”;进入21世纪,孔、朱的解释似乎与当今的社会生活实际有点格格不入了,需要有人对它进行“别出心裁”的解释。这也足可说明,“慎终追远”在当今社会仍然有着顽强的影响力。
需要深究的问题是:“慎终追远”为什么能够使“民德归厚”? 按照荀子的解释,应该是“礼义”的作用。《荀子·礼论》云:“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现代人重视功利,所以用现代眼光来看,“厚生薄死”才是符合常理的。古代人重视道德,要培养“厚德”之人,即使是面对无知的死者,也绝不能有欺瞒之心,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亦即如同面对生者一样,要始终保持“诚”“敬”之心,以此达到“心诚则灵”的效果。这里的“灵”,更重要的是“民德归厚”的灵效,也是“礼义”所施行的目的。
还需进一步追问的是:“民德归厚”之“厚德”是一种什么样的德? 周远斌认为“归厚”是“使人之德性复归于本然意义上的淳厚”。这是不切合实际的,从人之本然意义上说,人与动物一样具有天然的野性,这种野性在“物竞天择”自然规律的作用下,只会有“本然的”攻击欲,不会有“本然的”淳厚。因此,“淳厚”是后天培养教育的结果。那么,“淳厚”是怎样培养出来的? 《礼记·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颖达《礼记正义》解“温柔”:“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敦厚”是何义? 孔颖达没有解释。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说:“论诗者动辄说‘诗人忠厚之旨',‘忠厚'是温柔敦厚的约言。”(青木正儿,1982:40)也就是说,温柔敦厚与敦厚、忠厚、淳厚应该是同一个意思,它主要是指一种温和顺从的人格,而这种人格是后天通过“诗教”和“礼教”的方式培养出来的。
关于“诗教”对人格培养的作用,笔者曾展开过较充分的讨论(陈仲庚,1998),本文重点讨论一下“礼教”的作用和意义。《礼记·中庸》云:“敦厚以崇礼。”这里应该是一种双重因果关系:因敦厚而崇礼;因崇礼而敦厚。也就是说,当人们参与祖先祭祀的时候,首先得有温和顺从的心态,才能做到如孔安国、朱熹所说的诚心诚意、毕恭毕敬;而在诚心诚意、毕恭毕敬的祭祀礼仪中潜移默化,人们的心态自然也会变得温和顺从。
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什么如此重视温柔敦厚的人格培养? 从根本上说是适应大一统农耕文明的特点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农耕文明尤其需要社会的稳定,因为农业生产有着严格的周期规律,春耕、夏管、秋收、冬藏,其中任何一个季节发生社会动乱,都可能导致农业的绝收,这也就意味着来年很可能会“饿殍遍地”,这是无论统治者或普通百姓都不愿看到的。正因为如此,统治者与老百姓基本达成了共识:希望从心理上弱化人们的攻击欲,减少犯上作乱的可能性,以维系社会的稳定。因此,温柔敦厚的人格,正是农耕文明社会的必然产物。
二、祖先崇拜与民族认同
作为大一统农耕文明的需要,温柔敦厚的人格培养,只是减少了动乱的可能性,还不能从根本上凝聚全民的人心。要凝聚人心,还得寻找另外的途径。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要讨论“礼教”的作用和意义,不是指一切“礼教”,而是特指与“慎终追远”相关的“礼教”,这恰好是凝聚人心的有效途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辨析:“慎终追远”究竟是官方的事还是民间的事,抑或是官方、民间共有的事? 从古代注解看,孔安国点明了“君能行此二者”;从现代翻译看,邓球柏则点明了“统治者若能尽礼治丧”,说明“慎终追远”是官方的事。朱熹和杨伯峻说得很笼统,似乎认为是官方、民间共有的事。究竟那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
《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刘子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古代国家的两件大事是祭祀和战争,战争肯定由官方组织,这是毋庸置疑的;祭祀是否也只能由官方组织?
《国语·楚语》载观射父言:“古者民神不杂”,“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及少皞之世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从这里可以看出,颛顼即帝位之后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任命南正重和火正黎为国家级的祭司,专司祭祀天地鬼神之事,断绝了“家为巫史”也就是民间祭祀的通道,将祭祀之权收归“国有”,这就是上古史中有名的“绝地天通”。不管这一事件在上古历史中的真实程度如何,其影响力则是很重大的,所以在先秦典籍中一记再记。作为孔子的后裔又生当西汉,自然深知国家祭祀的权威性,所以孔安国一定要点明“君能行此二者”,说明古代的祭祀是国君亦即官方的事;同时也说明,“民德归厚”与君之“教化”分不开。
颛顼虽然将祭祀的权力收归国有,但作为国家级的“祭法”是怎样的? 典籍却没有记载。从现有资料来看,作为国家级的“慎终追远”,形成定制的“祭法”,似乎是从虞舜开始的。《礼记·祭法》载:“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历史上将这种国祭定制称之为“三代祭法”。其实,加上“有虞氏”,应该是四代。有虞氏作为第一代反而被忽略,其实是暗含了一个民族融合的问题。
根据徐旭生的考证,上古时代的中国存在三大部族集团,即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华夏集团“是三集团中最重要的集团,所以此后它就成了我们中国全族的代表,把其他的两集团几乎全掩下去。此部族中又分两个大亚族:一个叫做黄帝,一个叫做炎帝”(徐旭生,2011:335)。《孟子·离娄下》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其时的山东属于东夷集团,舜出生在山东诸冯,自然是“东夷之人”,他被尧选为继承人,本是两大部族融和的标志。但这种“融和”,不是两大部族的平等“联合”,而是以虞舜“入赘”尧家,并认尧的先祖为自己的先祖。在上述“祭法”中,因为虞舜的帝位不是从父亲瞽瞍那里继承来的,而是继承了岳父的基业,所以他要以尧的先祖颛顼为远祖,以尧为近宗。正因为有虞氏是宗异姓为先君、先祖,而继任的子、孙也为异姓,所以他不能独立地构成一代,后人也只能称“三代”而不能称“四代”。然而,也正是通过这种宗异姓的“慎终追远”祭祀形式,虞舜本人也成为了华夏部族的祖先,后人还千方百计地给他梳理了一条自黄帝、颛顼而下的华夏血脉系统。这似乎意味着,东夷部族完全融入了华夏集团,或者说,是华夏集团把东夷集团“全掩下去”了。
而且,虞舜的这种“祭法”,在当时恐怕不是特例,而是通例。《孝经·孝治章》云:“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 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作为“明王”之孝治,就是要得“万国之欢心”,然后万国就会“事其先王”。这里的“事”也就是祭祀,亦即奉“明王”之先祖为自己的先祖;这样的祭祀时间一长,就会形成为一种定制,后来的“万国”之君为抬高自己的身价,想方设法也要找到一个“明王”为先祖;于是,历朝历代的“万国”也就有了共同的先祖。这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据旧史则唐虞夏商周秦汉,皆同祖黄帝;而后世所传姓谱,大抵非太岳胤孙,即高阳苗裔;似吾族纯以血缘相属而成立。”(梁启超,2011:9)这样以来,所导致的最后结果就是:全体中华民族都认炎黄为祖先,每个人都认定自己是炎黄子孙。
因此,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直稳定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慎终追远的祖先崇拜,应该说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
三、血缘链条与灵魂归宿
万国“事其先王”,这种“孝治”模式经过三代大一统体制的逐步规范,形成为一种“宗法制”,其特点就是将国家的治理与宗教性祭祀结合成一体:“就治道的角度说,王者为天下共主;就宗教的意义而言,王者祭天,为最高祭司”(李景林,2004)。“王者祭天”,这个“天”不仅仅是自然之天,更重要的是人类最早的祖先。《礼记·郊特牲》云:“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万物本乎天”,人是万物之灵,同样也“本乎天”。古代典籍中的“天”至少有三重含义:一指自然之天,二指天国,三指天神或曰上帝。那么,“人祖”与“上帝”是如何“配”起来的? 《孝经·圣治章》云:“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文王为周公“严父”,严父配上帝;后稷为周公远祖,远祖直接配天。这样一来,周公——文王;上帝——后稷;天——就形成了一个双重的“血缘”链条:直接的血缘链条是与祖先的连通;间接的血缘链条是与天神、天国乃至于天地自然的连通。所以《孝经·感应章》云:“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这里的连通,当然不仅仅是周公个人的事,作为国家的最高祭司,他首先代表了周朝姬姓家族的全体成员,同时也代表了全体国民。因此,文王、后稷不仅是天下“共主”,也是天下“共祖”。这不仅从制度上凝聚了全体国民的向心力,还促使中华民族从“祖先认同”走向了“民族认同”。
“慎终追远”如果仅仅是往上连通祖先,那还是很不完善的;还必须往下连通子孙,旁系连通兄弟及其他家族成员。这样不仅可以连通人与天的“血缘链”,还可以将天道运用于人道。《孝经·三才章》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民如何“则天”、“因地”呢? 《大传》云:“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人道的根本就是亲亲与尊尊,“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礼记·丧服四制》)。没有祖祢与子孙的上下连通,无以定尊卑;没有兄弟等其他亲属的旁系连通,则无以别亲疏。有了上下尊卑、左右亲疏(直系旁系)之别,尊尊与亲亲才会有明确的目标,自我才能在家庭亲属中找到明确的定位。这从社会需要来说,是建立了稳定的“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的伦理秩序;从个人需要来说,则是找到了很好的自我归宿。
首先,从现实需要来看,个体必须得到家族的庇护。中国古代的经济,是以小农个体生产为基础的,而个体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使个体农民必须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协同劳作,以增强自身力量,抵御自然灾害的侵扰。也就是说,个体小农的力量,必须通过群体的组合,在群体力量的显示中才能得以实现。这样,为了自身的生存,人们就必须加入某一特定的群体,并注重群体关系的处理,以便更好地得到群体亦即家庭、家族的庇护。同时,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也要求把分散的个体小农束缚在土地上,通过不同家族、不同地域的春种秋收,将收成的相当部分向国家缴纳,从而在客观上向国家政权认同。因此,无论从经济需要或政治需要来看,都要求个体必须融入到家庭、家族群体中去。这是自我归属的第一需要。
其次,从精神需要来看,个体要通过家族的认同来寄托情感。人是群居的动物,无论是物质需要或是精神寄托,都必须有所归属;而且,从某种意义说,精神寄托更显重要。李景林认为:“古初文明时代的‘绝地天通',拉远了人与神的距离,使‘天'具有了终极超越性的意义;而上述尊尊与亲亲的内在连续性,又使得这终极超越性的天,能于人各本孝思而‘追远'的情感生活中得到不同层次的亲切体证。”(李景林,2004)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体证”不是一种枯燥的哲理思辨,而是一种温馨的情感认同;其次,“追远”不是一种“终极超越”,而是一种“原初回归”。我们从客居他乡的游子身上,或许可以更好地看到这种“体证”。游子们总是“低头思故乡”,他所思念的故乡、故土、故人,都带有“原初”的意义,因为他生于斯、长于斯,所以归属于斯。也正因为回归故土的情感过于强烈,使得他无法与他乡的群体从精神上很好地融合起来——强烈的归属感与强烈的拒斥心成正比,同时存在,同样强烈。再者,即使是被社会所抛弃的“浮浪者”,也仍然忘不了要找到自己的家族归宿,《阿Q 正传》中住在土谷祠的阿Q,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但他一定要说自己姓赵,从物质需要说,已无实际意义;从精神寄托说,则是试图在未庄显赫的家族中找到自己的归属,使自己飘泊的灵魂能得到赵氏家族的情感认同。而赵秀才说阿Q“不配姓赵”,同样是家族归属感使然,似阿Q 之类的“浮浪者”,即使真的姓赵,也有可能被逐出家门,更何况阿Q 本来不知姓甚名谁,赵秀才当然更不会允许他玷污赵氏家族的荣誉。在传统社会,逐出家门,就是对家族成员最严厉的惩罚,这也可以从反面证明,家族的情感认同、情感归宿,在国人心目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再次,从终极关怀来看,个体要通过家族血缘链,给自我的灵魂找到归宿使其获得永生。在人类繁衍的问题上,中国与西方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理念。西方的理念认为,人是上帝的子民,每个人与上帝都是一种直接的“父子”关系;相反,人类真正的父子关系,倒成了平等的朋友关系。中国则把人的繁衍看成是上接祖先、下连子孙的血缘链,父子关系只是这个链条中的一环。人们“通过自我生命精神与先祖以及子孙之生命精神的契接,而体认一己生命之永恒的意义”,“正是在自我生命精神与先祖及子孙之生命精神不断契接的过程中,个人就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己生命的源远流长与流衍无穷,从而体认‘吾性自足'的生命价值”(李翔海,2010)。在祖先——自我——子孙的血缘链条中,自我生命的消亡,不是链条的中断,而是链条的接续,或者说,是回归到祖先的怀抱:生是从祖先那里来,死是回祖先那里去。中国人强调叶落归根、魂归故土、入土为安,那一坯黄土下所掩埋的不是冰冷的墓室,而是祖宗的怀抱。回到祖宗的怀抱,并能享受子孙的祭拜,这自然是十分温馨而惬意的事情。因此,与西方的灵魂超越肉体、试图到天堂寻找永生不同,中国人则是灵魂与肉体一同回归,通过血缘链的接续来寻找灵魂的归宿;并通过子孙“慎终追远”的香火祭祀,使灵魂获得永生。
[1] 陈仲庚(1998).由“声教”而“诗教”.零陵师专学报,2.
[2] 迟宇宙(2010).慎终追远》.商业生活,11.
[3] 邓球柏(1996).论语通解.北京:长征出版社.
[4] 李景林(2004).儒家的丧祭理论与终极关怀.中国社会科学,2.
[5] 李翔海(2010).“孝”: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学术月刊,4.
[6] 梁启超(2011).中华民族之由来(节选).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一).长沙:岳麓书社.
[7] 青木正儿(1982).中国文学概论.隋树森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8] 徐旭生(2011).我国古代部族三集团考.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一).长沙:岳麓书社.
[9] 杨伯峻(1980).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10]周远斌(2006).《论语》“慎终追远”章释义正误.滨州学院学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