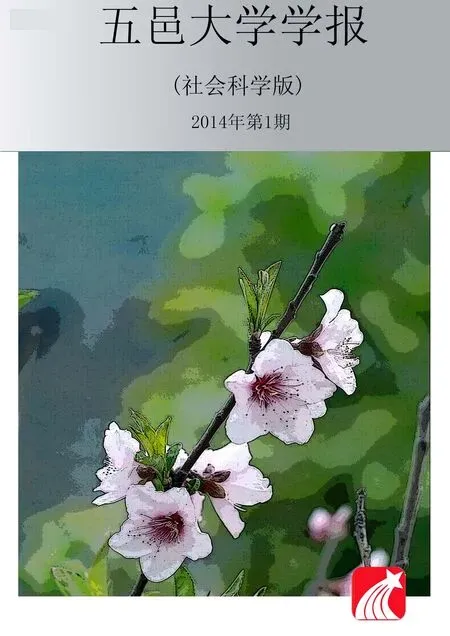论梁朝乐舞诗的才色分离
——兼与唐代乐舞诗比较
2014-03-19杨林夕
杨林夕
(惠州学院 中文系,广东 惠州 516007)
一、梁朝乐舞诗概论
关于乐舞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唐代,而对于唐前乐舞诗的研究甚少。据笔者粗略检索,只有郭春林的《诗经中的“舞蹈”诗及其民俗阐释》(《九江学院学报》2006年第二期)和贺威丽的《南朝乐舞诗兴起原因之探微》(《学术论坛》2013年第三期),前者主要探讨《诗经》中舞蹈诗的民俗价值,后者主要是论述南朝梁大量出现乐舞诗的原因。两者都较少对乐舞诗本身的分析。其实南朝尤其是梁代的乐舞诗不仅数量不少,也有其特点,笔者试做分析。
中国古典诗歌主要从“情才色德”即婚恋情感、才能才艺、容貌服饰和妇德品行四个方面来书写女性,其中对女性婚恋中的各种情感以及贞专品德吟咏最多,但是也有些诗歌涉及到了女性的才能和容色。这些对女性才能的书写在唐前多是穿插在婚恋诗中,或是某些诗中有所涉及,而有一类乐舞诗就是专门展现女性的歌舞才艺的。所谓乐舞诗,本是指咏绘音乐、舞蹈的诗歌。原始时期的音乐和舞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乐舞多是音乐伴奏下的舞蹈,乐舞诗一般要描写所奏曲调、所演歌舞的情致气氛,赞扬表演者的歌神舞韵,摹写乐器的形状音色,阐发听乐观舞的感受联想,甚至从音乐歌舞中引申开去,喻哲理、叙人事、论治乱等,即包括境、人、情、艺、理等方面。虽然真正展现女性歌舞才艺、赞颂女性才华的乐舞诗直到唐代才出现,但它早已产生,南朝梁还数量不少。
梁诗中所表现的舞蹈比以前丰富,简文帝萧纲的《舞赋》中就写到了扇舞、鞞舞和巾舞或说白纻舞。“白纻”诗也是咏舞诗系列,如萧衍的《白纻词二首》、张率的《白纻歌九首》等也是咏舞的。《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曰:“(白纻诗)古词盛称舞者之美,宜及芳时行乐。”梁乐舞诗有33位作家80首作品,其中以咏舞为主的乐舞诗,据粗检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有21位作家47首。
梁朝有的咏舞诗把重点放在舞者的容颜、服饰、姿态、表情甚至情感上,这些咏舞诗实际上就是以舞女为表现对象的宫体诗。梁朝乐舞诗除了何逊《咏舞妓诗》和江洪的《咏舞女诗》外,其他诗题中都没有出现女性或者美人等的字眼,但是他们咏舞就是咏美人。正如宋人吴幵《优古堂诗话》所论:“古今诗人咏妇人者,多以歌舞为称”,作为当时宫廷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的歌舞是表现美人们绰约风姿的最佳情境。梁朝咏乐诗很多干脆就以看妓、听妓、咏妓为题,如何逊的《离夜听琴诗》、萧统的《咏弹筝人诗》、刘孝绰《夜听妓赋得乌夜啼》、萧纲《夜听妓诗》和《弹筝诗》、萧绎《和弹筝人诗二首》和《咏歌诗》,邓铿《奉和夜听妓声诗》等。乐舞是“以人体姿态、表情、造型特别是动作过程为手段,以表现人们主观感情为特征”[1]的艺术,所以歌吟乐舞的诗歌应该是描写舞蹈的动作、舞者的姿态表情以及舞者和观众的情感交流,但梁朝乐舞诗的特点主要是重人轻艺(动作)、重色轻情、重色轻才(表演效果),较少写演出效果和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交流;与唐代乐舞诗相较,表现手法上多白描而少比喻和烘托,即使比喻也多拟人而少喻艺。
二、梁朝乐舞诗的主要特点
(一)重色轻艺
1.摹态而轻艺。梁朝乐舞诗主要注重描写表演者,而不注重表现歌舞技艺。因此他们的咏舞诗多描摹舞者的情态而少舞蹈动作(舞艺),如梁武帝萧衍的《白纻辞二首》:“朱丝玉柱罗象筵,飞琯促节舞少年。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转私自怜。”“纤腰嫋嫋不胜衣,娇态独立特为谁?赴君曲前未忍归,《上声》急调中心飞。”[2]1520其一写舞蹈的只有四个字“飞琯逐节”,且只是为了点题而已。第一句点明这是一次宴会舞,接着具体描述舞女流目顾盼的情态、“未肯前”的娇羞,而转身的舞蹈动作也变为状其羞涩之态:“含笑一转私自怜”,诗人对此赏玩不已。第二首都是描状舞者的情态,没有动作描写,“赴君曲前未忍归”主要是写表演者舞到奏乐伴舞者前面流连不去迁延不前的不舍情状,音乐都仿佛代其倾诉心中的盈盈爱意。
梁朝乐舞诗一般先摹写表演者的情态容饰,所舞多是衫袖和腰部的动作,也注意描摹表演者的衣饰妆容,如“争妍学楚腰”、“纤腰蔑楚媛”、“纤腰袅袅不任衣”、“回腰觉态妍”、“倾腰逐韵管”、“促舞不回腰”、“折腰应两袖”、“折腰送余曲”等,前四个都是摹写气质姿态,后四个都是写腰部的舞蹈动作。
梁乐舞诗所写的舞蹈动作或者歌唱情状有举腕、扬袂、飞袖、敛裾或者斜身、折腰、顿足等,其中以倾腰、发袖的动作最多,与之相关写衫袖和衣饰较多:
衫:“低衫拂鬓影”、“衫飘曲未成”、“到嫌衫袖广”、“飞燕舞衫长”、“衫随如意风”、“举腕嫌衫重”(刘遵)、“长袖拂面为君施”(沈约)、“飘衫钿响传”等;
袖:“管清罗袖拂,响合绛唇吹”、“弦惊雪袖迟”、“舞袖写风枝”、“发袖已成态”、“广袖拂红尘”、“飞凫袖始拂”、“舞袖岀芳林”、“袖轻风易入,釵重歩难前”、“敛袖待新歌”、“转袖随歌发”、“飞袖拂鬓重”、“从风迴绮袖”,以及相关的裾、袂等服饰,如“回身乍敛裾”、“延履裾香散”、“顾影时回袂”等;
履:“顿履赴余弦”、“延履裾香散”、“巾度履行疏”、“入行看履进”、“顿履佩珠鸣”等。
描写首饰的也较多:“映日凤钗光”“金翠钗环稍不饰,雾榖流黄不能织”、“袖轻风易入,钗重歩难前”、“因羞强正钗”、“悬钗随舞落,飞袖拂鬓重”、“低钗衣促管”、“映襟阗宝粟,缘肘挂珠丝”、“从风迴绮袖,映日转花钿”、“垂翠逐珰舒,扇开衫影乱”、“飘衫钿响传”“回身钏玉动,顿履佩珠鸣”、“凝情眄堕珥”等。
写表演者意态的如:“美人多怨态,亦复惨长眉”、“如娇如态状不同,含笑流眄满堂中”、“含情送意遥相亲”、“嫣然一转乱心神”等。有的将容饰、动作与表演者意态描写结合:“因风且一顾,扬袂隐双蛾。曲终情未已,含睇目增波”、“扬蛾为态谁目成”、“发袖已成态,动足复含姿。斜睛若不眄,娇转复迟疑”、“凝情眄堕珥,微睇托含辞”、“含情应节转,逸态逐声移”。眼波流动、衣袂翩翩、环佩叮当中含情含态的歌舞,分不清孰主孰次。而对于容饰的精细描写更使得写舞蹈动作、歌唱技艺也是为描摹表演者娇姿逸态服务了。
2.状艺以显色。舞蹈技艺主要是靠舞蹈动作来展现。梁朝咏舞诗很多却直接描摹舞者的外貌表情,从舞者的服饰到容貌、身段、眼神等一一描画,不是为了展示舞艺,而是为了摹写舞女。如江洪的《咏舞女》:“楚腰蔑楚媛,体轻非赵姬。映衬阗宝粟,绿肘挂珠丝。发袖已成态,动足复含姿。斜睛若不眄,娇转复迟疑。何惭云鹤起,讵减凤惊时?”[2]2074在对舞者的细腰、轻巧之身和服饰的介绍后才写到舞蹈动作,但是“发袖”、“动足”、“斜睛”、“娇转”等的描写与其说是赞扬舞艺舞技,不如说是描摹舞姿娇态:先于举手投足中点明其“已成态”、“复含姿”,接着用眼波斜、旋转迟状其娇姿意态,最后用“云鹤起”、“凤惊时”的比喻,舞姿、娇态莫辨。可见,梁朝乐舞诗歌咏了舞女动作也是为了显其娇态。
以上乐舞诗写舞蹈动作多是简略写意式的,但梁朝也有一些咏舞诗对舞者动作加以细致描写。如萧衍《咏舞诗》:“腕弱复低举,身轻由回纵”、殷芸《咏舞》“斜身含远意,顿足有余情”、刘孝仪《和咏舞》“转袖随歌发,顿履赴弦余。度行过接手,回身乍敛裾”、萧纲《咏舞》二首之一:“入行看履进,转面望鬟空。腕动苕华玉,衫随如意风”、庾信《和咏舞》“顿履随疏节,低鬟逐上声。步转行初进,衫飘曲未成”。举腕、顿履、入行、回转,这些动作的描写,将舞者的局部姿容精雕细刻而出,但是这些咏舞诗往往于结句回到艳情的本色,如何逊的《咏舞妓》在写其舞姿舞态“管清罗荐合,弦惊雪袖迟。逐唱回纤手,听曲动蛾眉。凝情眄堕珥,微睇托含辞”后,以“日暮留嘉客,相看爱此时”作结。萧纲的《咏舞》“上客何须起,啼乌曲未终”和《夜听妓》“留宾惜残弄,负态动余娇”亦然。他的《咏独舞》“非关善留客”和邓铿的《奉和夜听妓声》“乐众倶不笑,座上莫相撩”更是欲盖弥彰,正话反说。可见即使是描写了舞者的技艺,也没给人以整体的观感,写舞蹈动作还是附着于舞态的描写中。
3.重色而轻艺。作者(观者)的身份和他们咏舞观舞的目的决定了对乐舞的态度。梁朝乐舞诗的观舞者是王公贵族,他们咏舞观舞的目的不是为了艺术的熏陶引发向上的力量、灵魂的净化或者审美的提升,而只是娱乐或说娱情练笔而已,因而他们的咏舞诗就没有对舞女歌舞才能的赞美和欣赏。以萧纲《咏舞》二首为代表。其一:“可怜二八初,逐节似飞鸿。悬胜河阳妓,妍与淮南同。入行看履进,转面望鬟空。腕动苕华玉,袖随如意风。上客何须起,啼乌曲未终。”诗分三个层次歌咏舞女的色艺,前四句概括地赞美了眼前的舞女:首句“可怜二八初”写其年轻可人,次句“逐节似飞鸿”绘其姿态轻盈,三四句从描写转向用事,把诗人眼前的舞女与石崇的家妓和傅毅的《舞赋》中的场景联系在一起;中间两联为细节描写,集中摹写舞女的姿态和动作,同时对某些局部做特写镜头式的勾画,如应节而动的手足,引人注目的发鬟随着低头昂首而转动;最后以留客继续观舞作结。《咏舞》其二:“戚里多妖丽,重聘蔑燕余,逐节工新舞,娇态似凌虚。纳花承衤聂衤既,垂翠逐珰舒。扇开衫影乱,巾度履行疏。徒劳交甫忆,自有专城居。”十句诗中真正写舞蹈的只有“扇开衫影乱,巾度履行疏”两句,说明她跳的是《扇舞》或《巾舞》,是对第三句“新舞”的补充。三四句是写舞姿。其他都是对舞女的描写。
可见,萧诗名为咏舞,实际并不关注舞者的舞艺,而主要是歌咏舞女。色艺中重的是色,包括舞者的容貌和身体各个部位的描写,如年龄、体态、发鬟、手、足等,没有前面提到的鲍照《白纻歌三首》之二对舞女的感情描写。
唐朝咏舞诗有时候也描写表演者的容貌姿态和动作表情,但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表现舞艺并加以肯定。如白居易的《胡旋女》写了舞女的动作,但目的是以人体的连续动作展现超群的舞蹈技艺:“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白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其服饰、姿态、表情的描写都是为了展现舞艺:应鼓而举的双袖、如转蓬一般迅疾的胡旋舞,带动裙裾如白雪飘飘,轻盈飘逸。诗中对其高超的舞艺表示由衷赞美:“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而梁朝咏舞诗表现了重在描摹舞女而不在展示舞技的倾向。它们致力于描摹静止的姿态、服饰和局部的容貌,其笔下的舞女只是现成的诗题、被玩赏的对象,不过是一个色相、一个专供诗人摹写的模特。所以梁陈诗人一般不会关注舞者的舞艺才华,而主要是对舞女的欣赏,如她们因灯光舞步而更娇媚的容颜姿色、因“逐节”、“转袖”而更轻盈更迷人的身段体态。他们只是以男性的目光做上下左右、有动有静的赏玩,以之为一朵解语花、风摆柳,以形成一种莱辛所谓的流动美。这种流动美的表现较之静态美的描摹所产生的艺术魅力更大。
(二)重色轻情
梁朝咏舞诗热衷于描摹舞蹈者的容貌服饰、动作姿势、神态表情,没有触及舞蹈表现情感以及由此引发或者感染观者情感的本质特征。何逊和王训的咏舞诗都描写到了女性某种传情的“笑态千金动”、“凝情眄堕珥,微睇托含辞”,这些情态其实也与动作一样只是虚幻的“舞蹈要素”。舞女在这些诗歌中,难免从一个舞蹈艺术的承担者角色堕落到一个单纯呈现美色的角色,所以这些咏舞诗对于表现舞蹈艺术而言是不成功的,对女性表演者而言更是一种扭曲。从与唐以后同类诗歌的比较可见,作为表现舞蹈艺术的咏舞诗,必须脱离单纯的对表演者身体的凝视,才能进入抒情的境界。
1.观看者与表演者的交流:一为调情,一为感动。诗歌和舞蹈都是抒情的艺术。舞者的表演是自身情感的抒发,它同时也调动观者的情感,舞者和观者有互动和交流,即舞者通过身体语言、形体动作诉说对生命的体验甚至自己的情感,观者由此得到体验,通过观舞的反映传达给舞者。如白居易的《与牛家伎乐雨夜合宴》就写出了舞者和观者共同的生命体验:“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因为美妙的舞蹈,使人觉得天堂都不那么令人神往了。唐乐舞诗中更多地是感动泪流(如李颀《古意》“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白居易《琵琶行》“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韩愈《听颖师弹琴》“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等),甚至“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沉默回味(如白居易《琵琶行》“东船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等)。而梁朝乐舞诗却是以舞者的“含情应节转,逸态逐声移”与观者的互通款曲、含情脉脉来表现,甚至带有色情的倾向。如萧衍的《白纻辞二首》之二写舞女主动挑逗的娇态:“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转私自怜”,“纤腰嫋嫋不胜衣,娇态独立特为谁?赴君曲前未忍归。”又如梁武帝萧纲《咏舞》的“腕弱复低举,身轻由回纵。可谓写自欢,方与心共期”,写舞者以柔婉相招,欲去还回。
2.有无寄托:梁多咏舞写人,唐多象征寄托。梁诗纯粹咏舞写人,别无寄托;唐诗多有象征寄托,尤其是中晚唐的咏舞诗,通过咏舞来“稽其成败兴亡之理”,对安史之乱的历史进行反思,如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元稹和白居易的《胡旋女》等。前者对公孙弟子的舞蹈仅用一句“妙舞此曲神扬扬”描写,不作仔细摹状,而着力表现作为健舞的剑器舞所爆发的勇武精神和感染观者使之油然而生的“豪荡感激”之情,以及作者“抚事慷慨”而发的“五十年间如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的深沉感叹。元稹的《胡旋女》曰:“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主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回风乱舞当空霰;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元稹就其“旋”而联想到此舞的迷惑君王,甚至认为天宝末年君昏臣佞是由其“旋目”而“旋心”的结果。白居易先描写胡旋之美后,也将舞蹈与政治事件联系起来,将国家衰落归咎于舞蹈:“中有太真外禄山,两人最道能胡旋……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感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虽过分夸大了舞蹈艺术的作用,委罪不当,但是诗中掩饰不住的是对其疾如流风回雪、蓬草飞旋的精妙舞艺的赞赏,因此比梁陈单纯地为赏歌舞而写歌舞更有意义。
3.态度的差异:一赏玩,一赞美。梁诗的歌舞伎女无名无姓,无来历无个性,诗人只是从类型化的手法描写其舞姿舞态、歌声歌喉。她们不是以独擅的艺术知名,更不是因为高超的歌舞技艺而受到尊敬或者引起“同是天涯沦落人”式的同情和共鸣,更毋谈精神交通,因为诗人写乐舞诗不过是流连光景,仅仅满足于铺陈声色之乐。这类诗歌的创作动机不是宣泄感情,而是描摹外物,因此远离了古典诗歌“抒情言志”的传统。而唐乐舞诗有很多有名有姓的表演者,虽然不一定都是女性(如胡腾儿、李凭,蜀僧濬、安万、颖师等是男性),但确有不少女性,如张云容、杨玉环、胡旋女、公孙大娘及其弟子、曹十九、善财、秋娘、琵琶女,永新娘子等,诗人都对其大为赞赏,将她们比为上元仙人或者西王母身边的仙女萼绿和飞琼。
(三)多用白描
在乐舞诗的表现手法上,梁陈多白描,即使比喻也多拟人而少喻艺;唐诗则多比喻、烘托。梁代乐舞诗多用白描,可以更好地摹写舞女的服饰、容色、体态等。梁代乐舞诗也间用比喻,如“鸾回不假学,凤举自相关”,以鸾回、凤举喻写舞姿舞艺,而“鸾回镜欲满,鹤顾市应倾”动作的比喻是衬托容姿的魅力。其比喻多是描状舞女而不是展示舞艺,所以多以美女拟之,而非唐诗之多以自然景物和日常事物为喻。如庾信《和赵王看妓诗》:“常思浣纱石,空想捣衣砧。临邛若有便,空想解琴心”,连用西施、卓文君两美女来比喻。其中尤以飞燕为喻的最多,如“飞燕掌中娇”、“将持比飞燕”、“绿珠歌扇薄,飞燕舞衫长”、“虽称赵飞燕,比此讵成多”、“体轻非赵姬”等。而唐诗的“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浆迸”、“浮云柳絮无根蒂”、“芙蓉泣露香兰笑”和“美人舞如莲花旋……回裾转袖若飞雪”、“红蕖袅袅轻烟里,青云岭上乍摇风”等,是纯粹对音乐和舞蹈的比喻。
唐人用比喻或间接烘托,是为了更好地表现歌舞的技巧和表演的效果。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的“曤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用“羿射九日”来比喻公孙手持红旗、火炬或剑器作旋转或滚翻式舞蹈动作;用“骖龙翔舞”拟写公孙翩翩轻举,腾空飞翔;用“雷霆收怒”形容舞蹈将近尾声,声势收敛;用“江海凝光”描写舞蹈完全停止,舞场内外肃静空阔,好像江海风平浪静、水光清澈的情景。杨玉环的《赠张云容舞》(一名《阿那曲》)除了第一句“罗袖动香香不已”点明舞者,其后三句“红蕖嫋嫋秋烟里。轻云岭下乍摇风,嫩柳池塘初拂水”以红蕖嫋嫋、轻云下岭、嫩柳拂水三个优美的自然景象来比喻舞蹈之美。岑参的“回裾转袖若飞雪,左铤右铤生旋风”状胡旋舞的旋转动作极其传神。另外如颜真卿《赠裴将军》“剑舞若游电,随风萦且回”、元稹《曹十九舞绿钿》“腰袅柳牵丝,炫转风回雪”、白居易《霓裳羽衣歌》“翔鸾舞了却收翅,唳鹤曲终长引声”等,都是用比喻手法描写舞蹈动作,表达了作者欣赏、赞叹之情,更好地反映了舞蹈的审美特征。其他写音乐的唐诗也是多用比喻手法,化抽象的音乐为具体可感的各种物象。如白居易的《琵琶行》主要是以声喻乐,韩愈的《听颖师弹琴》主要是以形喻乐,李贺的《李凭箜篌引》主要是用有关音乐的典故来比喻音乐的各种声音、效果。其他如李颀的《听安万善吹筚篥声》之“雨堕瓦”、李白《听蜀僧濬弹琴》之“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等也是以声拟声,李颀的“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听董大弹胡笳》)是以形写声。“三绝”(白居易《琵琶行》、韩愈《听颖师弹琴》、李贺《李凭箜篌引》)是形、声、典三者结合以比拟音乐的。如韩愈《听颖师弹琴》也有拟声,甚至写出了声音由儿女情话般低微到战士喊杀声的高昂之变化。白居易与韩愈诗相似而拟声拟形的有“小弦切切如私语”、“铁骑突出刀枪鸣”、“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滩”等,都是形声兼具。
唐乐舞诗几乎篇篇都用烘托手法,用听众或者观众的强烈反应写歌舞的美妙神奇。如《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的侧面烘托,白居易的《琵琶行》分别在诗的开头、中间和结尾等三处描写了听众的感受。再如李白的《听蜀僧濬弹琴》“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都是用听众的感受来衬托演奏者技艺的高超和音乐感人的效果。也有以现实或者超现实的自然物的反应来渲染乐舞的神奇韵味,如“川为静其波,鸟亦罢其鸣”、李颀《听董大弹胡笳》的“深山窃听来妖精”、杜甫的“天地为之久低昂”等。还有李贺调动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和五彩缤纷的动物世界:凤凰和鸣、芙蓉泣露、“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写出了李凭出神入化的技巧。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和元微之》是如《七盘鼓舞》般的大舞,舞曲分“散序”、“中序”、“曲破”三个乐章,用对比衬托“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元稹《胡旋女》在用一连串的比喻描摹了《胡旋舞》的舞容之后说“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是用观者的感受来形容舞者旋转之多和速度之快。另如“四座无言皆瞪目”(刘禹锡《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体轻似无骨,观者皆耸神”(刘禹锡《观柘枝舞》)、“当时乍见惊心目,凝视谛听殊未足”(白居易《霓裳羽衣歌》)、“买笑未知谁是主,万人心遂一人移”(施肩吾《观舞女》)等诗写观舞的感受,通过观者目瞪口呆或耸神凝视的情态,来烘托舞蹈感发人心的艺术魅力。而梁陈多是白描,如“衫飘”、“顿履”、“转鬟”、“逐节工新舞,娇态似凌虚。纳花承躡概,垂翠逐珰舒。扇开衫影乱,巾度履行疏”等,对舞蹈动作、舞女情态和服饰进行直接描摹,较少写到与观众的交流和歌舞的效果。
唐人即使用白描手法写舞姿,目的也是指向舞蹈的效果以歌颂舞女舞技的高超。如李益《观石将军》和岑参《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铤歌》,虽也对舞姿做了传神的描绘,但是重点却是以舞蹈所产生的效应表现舞者的技艺和舞蹈的感染力:“高堂满地红蠷屿,试舞一曲天下无。此曲胡人传入汉,诸客见之惊且叹”,处处是为了表现舞蹈的魅力。而梁朝乐舞诗的感人效果是以观赏者迫不及待地想留宿、轻薄来说明:“徒劳交甫忆”,“犹足动文君”,舞蹈舞艺成为表演者“留宾”、“留客”的色诱手段,乐舞诗就成了艳诗了。
总之,梁朝是咏舞女,唐朝才是真正的咏舞(艺)。梁朝咏舞不是为了抒情而是为了调情,不是为了表现歌舞感人的效果而是通过描摹女性容色以诱人;唐朝咏舞诗多是为了抒写舞者和观者的情感及其交流、为了展现舞蹈感染力。这种差异是由于梁朝娱乐文学观和将女性等同于山水田园一样的物的观念所致,同时它也为唐朝乐舞诗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略论艺术种类[N].文汇报,1962-11-15.
[2]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歌[M].逯钦立,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