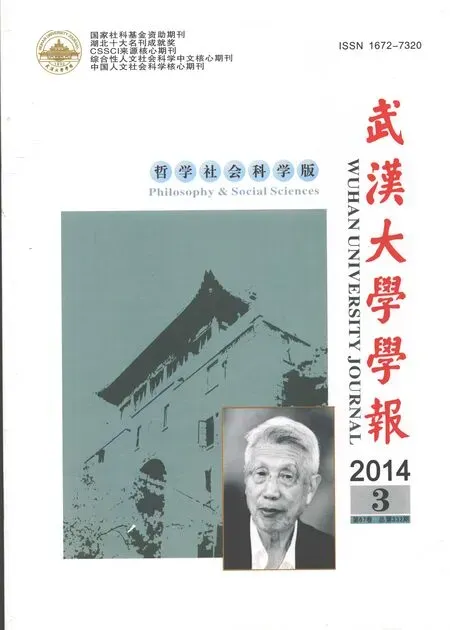立民与立国: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话语选择
2014-03-19郭忠华
郭忠华
尽管当下中国知识界很少有人会对citizen应该翻译成何种术语和具有何种涵义产生怀疑,但其在近代历史上的情况却远非如此,它不仅被翻译成不同的术语,而且被赋予不同的涵义。翻译术语的选择和涵义的赋予具有深刻的含义。它既反映了政治学意义上的“翻译现代性”思想,又反映了翻译学意义上的“翻译目的论”现象。本文以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早期知识分子对于citizen的翻译作为研究对象,透视知识分子对于该概念的翻译方式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政治现代性想象。
一、现代国家构建的早期话语策略
中国的现代性想象和追求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鸦片战争中中国的败局为西方现代技术和现代性思想的输入创造了条件。这种输入既有开明绅士自主选择的因素,也有西方传教士强制灌输的因素,是一种主动追求和被动驱使相结合的结果。
西方citizen概念的最初引入更多是被动灌输的结果,而且只是当时现代性巨流中的涓涓细流。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最早将citizen概念翻译成“人民”(万齐洲,2011)。例如,“他国被害,并他国人民受屈”、“自主之国,莫不有内治之权,皆可制律,以限定人民之权利、分位等事”(惠顿,2003:34)等文本中的“人民”所对应的均为citizen概念。除此之外,通过翻译《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等著作,丁韪良还使“人民”概念系统地建立在citizen内涵的基础上,使之完全成为一个表达政治现代性含义的术语。例如,《星轺指掌》第4卷指出:“按美国律法,美国人民在外国生有子女,其子女亦作为美国之民,惟欲传民籍之权利于子女者,必身曾居住美国方可。”“人民”从而与“国籍”联系在一起。《公法便览》指出:“人民迁徙之权利,自不可夺,除有牵涉官事及未完亏累,别无可以拘制之。”“人民”从而与“权利”、“行动自由”等涵义联系在一起。《公法会通》第4卷指出:“人民侨寓某国,应恪遵其法律,盖虽未入民籍,仍当钦服其主权。”“人民”从而与遵守法律等“义务”联系在一起。《公法会通》第10卷指出:“律法之设,原为保护人民之权利起见。人民无论贵贱,其在律法之权利几同。”“人民”从而与“平等”观念联系在一起。归纳起来,通过与citizen的涵义对接,“人民”成为一个表示“国籍享有者”、“权利拥有者”、“义务承担者”和“地位平等者”涵义的概念。
但在当时,除“人民”之外,citizen概念也存在其他对译术语,尤其以“国民”和“公民”两个最为重要。例如,在翻译救国论思想的指导下,1898-1909年间,严译名著源源问世。在《法意》中,严复大部分时候将citizen翻译成“国民”。例如,在“盖聚中材之众以成国民,以言其小己,往往其人虽不足举,而以举则有余”、“故用阄之制,于人无心,若虚舟之运物,而国民人人怀事国之意”(孟德斯鸠,1981:14、15)等表述中,“国民”所对译者皆为citizen。其次,“公民”也表达citizen的涵义。例如,康有为在《公民自治篇》中指出:“……但其以立公民之事,望诸政府,又以立公民为筹款一法门,则与记者所见,不无异同。记者以为公民者,自立者也,非立于人者也,苟立于人,必非真公民,征诸各国历史,有明验矣。至公民之负担国税,则权利义务之关系,固当如是,非捐得此名以为荣也。”(康有为,1977:173-176)与“人民”一样,此处的“国民”、“公民”与citizen的涵义基本等同,表示独立、自治、权利、义务、选举、参与等现代政治涵义。
当然,citizen在那一时期还存在被译为“民”、“齐民”、“臣民”、“私家”等情况。在诸如“夫一国之民,固多庸众,然使之举人而畀以权,其智尚足任也”、“尝以二万户之齐民,拒波斯之侵暴”、“假使有之,将使私家之权畸重,是其制所大不利者”(孟德斯鸠,1981:13、14、15、31、324)等表述中,“民”、“齐民”、“私家”所对译者皆为citizen概念。其实,正如某些学者所言,在传统与现代接驳的历史关头,通行于西方文献中的citizen概念甚至必须翻译成“籍民”、“草民”或者“臣民”才能为当时的知识和官僚阶层所接受(刘禾,2008:324)。但是,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历史没有选择它们作为现代性转型的对象,而是单单选择了“人民”、“国民”和“公民”等三个同样潜含着中国传统政治底蕴的术语。因为只有后三者才在此后的历史中流传开来,成为知识分子进行现代国家想象的凭借,其他则悄无声息地遁入于历史之中。
实际上,不要说“齐民”、“臣民”、“私家”、“草民”等概念早已存在于中国古汉语词汇库中,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关系的写照,即使是“人民”、“国民”、“公民”等后来成功实现现代性转型的概念,在古汉语词汇库中亦可见其踪迹。“人民”由“人”、“民”连缀而成,含义基本与“民”一致,表示君主、官员之外的“庶民”,因此与臣民的涵义大致吻合。例如,“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和说不通,解泽不流”(司马迁,1959:1177);“臣伏思汉夷交易,系属天朝丕冒海隅,以中原之货殖拯彼国之人民,非利其区区赋税也”(金观涛、刘青峰,2009:513)。“国民”在中国古代主要表达以下几种涵义:一是一国或一藩所辖之百姓,如“先神命之,国民信之”(左传·昭公十三年)、“威行於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史记·东越列传)等;二是指外国人,如“国民经营希利,算悉锱铢,亦多情普济之意。崇奉世主耶稣之教,舍身捐财,以招教师,颁文劝世”(魏源,1998:1667);三是分指“国”、“民”。如秋瑾在《赠浯溪女士徐寄尘和原韵》中写道:“今日舞台新世界,国民责任总应分。”“公民”在中国古代则主要表示“为公之民”、“公家之民”或“居住于公地之人”。例如,《韩非子·五蠹》写道:“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列女传·齐伤槐女》写道:“(婧)对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为公民’。”康有为《大同书》写道:“凡未辟之岛皆为公地,居者即为公民。”由此可见,无论是“人民”、“国民”还是“公民”,在中国古代都不具有“国籍”、“平等”、“义务”、“权利”、“参与”、“自治”等现代含义。正是通过外国传教士和本土知识分子的翻译和改造,它们才与西方citizen涵义联系在一起,从而成功地实现现代性转型。
知识分子对于citizen的最初翻译尽管带有几分非计划性,但由此形成的对译术语却依然为知识分子进行现代国家想象提供了空间和武器。19世纪末,伴随着“人民”、“国民”、“公民”等术语的流行,知识分子不仅开始懂得何谓国家,而且开始使用它们来想象中国的现代国家。
例如,梁启超对于国家的定义是:“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所谓之完全成立之国。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梁启超,1999:410)这种国家观和对中国国家现状的认识不啻是知识分子认识上的一场哥白尼革命。这场革命同样发生在陈独秀身上。根据《实庵自传》记载,直到1902年,陈独秀才知道世界“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唐宝林、林茂生,1988:17)。严复则从“三民主义”的角度构想应当如何来建立中国的现代国家,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严复,1960:43-44)。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中国未来记》,提出未来中国的理想国号为“大中华民主国”。所有这些表明,伴随着citizen的翻译及相关术语的流行,知识分子不仅习得了现代政治知识,而且开始按照人民、国民、公民的新语义来想象中国的现代国家。
当然,从话语权力角度来看,这种多元化的话语策略尽管催生了丰富的现代国家想象,但多元化的话语能量终究不如单一话语策略来得那么有力和集中。因为多元化的话语不仅容易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和混淆人们的思想,而且容易形成话语之间的内耗和相互抵消(王树愧,1969)。这种情况在1902年之后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二、国民、国家主义与现代国家
梁启超在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逃亡日本。一是变法败亡的经历迫使他思考个中原因,二是环境变化使他接触到经由日本所翻译的大量西方近代政治学著作,三是切身濡染在经由明治维新而建立的现代国家中,为反思中国现状提供了便利。梁启超的认识一时大变,深感中国现代转型所缺乏者并非戊戌变法时致力推行的“新制度”,而是支撑这些制度的新“国民”。因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政息焉……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梁启超,1994:2-3)。国民问题被看作是中国问题的总根源,并由此得出结论:“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梁启超,1994:2)梁启超后来在回顾当时的认识陡变时说道:“自东居以来,广接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梁启超,1994:6)
认识的转变很快便转化为行动的动力。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取《大学》的“新民”之义,从“欲以维新吾国,必先维新吾民”的政治立场出发,“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作为办报原则,为国家前途起见,培养和创造新国民。通过梁启超以及各派政治势力的共同号告①当时,梁启超尽管在推动“国民”建设工程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取道“国民”来建构中国现代国家的路径却几乎是各政治派别的共识。经由“保皇派、革命党人及其他人士的共同努力、鼓荡,‘国民’一词才流行起来,成为知识界最常用的词汇之一,‘国民’问题也才成为‘天下第一等议论’的热点问题”(载郭双龙、龙国存:《“国民”与“奴隶”:对清末社会变迁过程中一组中坚概念的历史考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1期)。,“国民”迅速超过“人民”、“公民”而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政治词汇。作为宣传“国民”的主要媒体,“尽管清廷一再严令禁止《新民丛报》在国内流行,但它仍能畅销无阻,几乎成为士子们的必读教材”(宋志明,1994:7)。章士钊在描述当时“国民”概念的兴盛状况时说道:“近世有叫号于志士,磅礴于国中之一绝大名词,曰:国民。”②章士钊:《箴奴隶》,载《国民日报汇编》(第1集),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八日。同时,以“国民”命名的报刊和革命团体也显著增多。相关统计表明,1900-1902年左右,“人民”、“国民”、“公民”的使用次数都较多,但在1903-1915年期间,“国民”的使用频率明显增多,其他二者则明显减少。其中,“1903年,‘国民’的使用次数达到顶峰,此后直到1915年,使用次数都较多”(金观涛、刘青峰,2009:511)。
尽管梁启超是一名翻译家兼“翻译救国论”的主要倡导者,亲自翻译过《十五小豪杰》等诸多政治小说,但由于其“译意不问词”的“豪杰译”风格,我们已很难通过文本对比的方式指明citizen的英汉对译关系,而只能根据其赋予“国民”的语义来加以推断。梁启超之所以选择“国民”而不是其他概念,相关推断或许言之不谬:“国民”建构出一种符合历史和未来发展的民族身份(黄兴涛,2002);“国”混合了作为文明天下的空间、作为人民生存空间的国家、作为体制的王朝等几种认识,“民”则包含了作为中华文明之民、作为天下之民和作为满、汉、蒙、藏、维吾尔等五族之民,因此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勾口雄三,1999:53)。但更重要的原因或许还在于本土现代国家构建的需要:选择“国民”,将“国”置于“民”前,一者突出“国民”与“奴隶”、“臣民”等“有君无国”之人的对比,二者以一种直接和直观的方式说明国民翻译的目标乃在于“国家”。
那么,当时知识分子倾力打造的“国民”话语后面又隐含着一幅什么样的国家建设蓝图?其实,伴随着20世纪转折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西方政治知识的大量引入,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国家的知识、世界政治的形势、满清政府的本质和中国国家建构的方向等问题已具有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对于他们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何种方式来建立类似于西方的民族国家。正是在这一目标的规范下,晚清知识分子从三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将“国民”与国家契合在一起,用国家观念来塑造国民。梁启超对民众的国家观念进行检讨,认为,中国的教育历来以“独善其身”、“忠孝仁德”为本,以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国民从而成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的“有君无国”之民,他们唯“一身一家之荣瘁是问”,即使是“其上焉者”,也无非是“高谈哲理以乖实用”之人,其“不肖者”则更是为虎作伥、卖国求荣(梁启超,1994:28)。以这种国民为基础的国家如何能与“有一民即有一爱国之人”的西方国家相竞争?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国家思想成为其“新民”之道的基础。《清议报》1900年载文指出:“国民者,与国家本为一物,异名同实,不能离而为二者也。”(伤心人,1900)国家与国民从而被看作是同一件事情。同样的情况也反映在当时出版的教科书上:“须知国民二字,原是说民人与国家,不能分成两个。国家的名誉,就是民人的名誉;国家的荣辱,就是民人的荣辱;国家的利害,就是民人的利害;国家的存亡,就是民人的存亡。”国家与国民的关系被比作鱼水和枝干的关系。“国家譬若一池,民人就是水中的鱼。水若干了,鱼如何能够独活?国家又譬若一棵树,民人就是树上的枝干。树若枯了枝干如何能够久存?”(陈宝泉、高步瀛,1905:1-2)诸如此类论述传递出来的共同信息是:国家重于国民,国家乃国民之本,国民建设以国家为依归。
第二,在确立“国家至上”的前提下,通过正反两方面措施来建立现代国家:一是以citizen的涵义来改造国民,二是以奴隶的镜像来反衬国民。从前一个方面来看,例如,梁启超把“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私德”、“民气”、“政治能力”等16个方面作为国民必须具备的精神(梁启超,1994:22-203);邹容把独立、自由、平等、法律、进取、公德、冒险、互助等观念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邹容,2002);陈天华把“除党见”、“讲公德”、“重武备”、“务实业”、“兴学堂”、“立演说”、“兴女学”、“禁缠足”等10个方面作为实现与英美并驾齐驱的“妙计”等(陈天华,1994:22-28)。从这些作者的话语策略可以看出,新的价值体系主要以citizen的核心价值为基础,包括权利、义务、责任、自由、平等、独立、自信、自治、尚武、进取、合群和爱国等(梁景和,1999:18-43)。
把国民与奴隶对立起来,通过奴隶的镜像来反衬国民,则是晚清知识分子构想中国现代国家的另一种策略。他们认为,中国有的只是“奴隶”而非“国民”,“奴隶性”是造成中国问题的根本原因。梁启超说道:“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梁启超,2010:179)《国民报》也把“奴隶”看作是中国之大弊:“中国之无国民也久矣。驯伏于二千年专制政体之下,习为佣役,习为奴隶。始而放弃其人权,继而自忘其国土,终乃地割国危,而其民几至无所附属。”(佚名,1901)奴隶弊害如此深重,国民自然必须与其划清界限,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章士钊指出:“奴隶者,国民之对点也。民族之实验,只有两途,不为国民,即为奴隶,断不容于两者之间,产出若国民非国民,若奴隶非奴隶,一种东倾西倒不可思议之怪物。”与奴隶相对立的国民则是一幅如火如荼、势如破竹的形象。“如火如荼者,国民之气焰也;如风如潮者,国民之势力也;如圭如璋者,国民之价值也。吾安得不顶礼膜拜,馨香祝之,而愿我国民之早日出世,以增进我同胞之幸福也。”(佚名,2003)在他们看来,这种充满力量感和神圣感的现代国民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现代国家的新生。在这种国家里,“国民之全体及其个人,皆非统治权之目的物。盖国民非奴隶,乃人格者,为权利义务之主体。其服从统治权,乃义务之主体,非统治权之目的物,明甚也。在民权国,国民全体,为国家之最高总揽机关;其非统治权之客体,固不待言。”(精卫,1906)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晚清知识分子倾力打造的以“国家主义”为基础的国民话语策略并没有唤来期待中的崭新国家。辛亥革命尽管终结了千夫所指的满清政权,建立起具有共和、民主外观的中华民国,但国家的本质没有改变,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翻译现代性的角度衡量,晚清的“国民”翻译和本土化打造尽管极大地激发了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现代国家的想象力,但这种想象却没能兑现在现实社会中。在这种背景下,同样以“国民”作为话语策略和以“现代国家”作为目标追求的民国知识分子掀起了新一轮的翻译和话语改造运动。
三、国民、个人主义与现代国家
1914年,一场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华大地隆重登场。这场囊括了文字、文学、政治、性别、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运动尽管可以归结到“民主”和“科学”的总标题下,但从“国民”的角度衡量,它显然有着具体得多的内容。在许多民初知识分子看来,晚清知识分子的“国家主义”方略之所以壮志未酬,关键在于国权掩盖了民权,国民没有真正得到发展(沈松侨,2002;勾口雄三,2011:189)。要建立中国的现代国家,关键还在于回到根本,培育出真正的现代国民。在未培育出现代国民从而奠定现代政治之基础的条件下,过于强调国家显然是一种操之过急的做法。在这一方面,胡适的言论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共同看法:“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胡适,1998:188)
从这一立场出发,民初知识分子同样将现代国家建设的话语策略瞄准“国民”,但把其置于“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国民、个人主义、国家等形成一个概念群。与晚清知识分子对于citizen的翻译一样,我们很难从文本的角度考察“国民”与citizen的对译关系。实际上,民初知识分子对于“国民”的重塑是在综合吸收citizen、citizenship、individual、individualism等诸多概念涵义的基础上形成的。民初知识分子的“国民”话语策略主要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在“国民性”批判的标题下,继续揭露中国的国民性问题;二是适度分离“国民”与“国家”,强调“只有先救出自己”,才能有益于社会;三是将个人主义、自我利益等改造成积极的价值,使之成为实现自由、平等、权利等价值的基础。个人空间的增长、个性主义的发展成为民初知识分子新一轮“国民”建设的重点。
在肯定“国民性”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关联的前提下,民初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猛烈的批判,把它看作是造成国民劣根性的根源。鲁迅以其卓越的文学笔法塑造出阿Q、孔乙己、祥林嫂、润土、华老栓、华小栓、七斤、九斤老太、鲁四老爷、赵大爷、假洋鬼子等一系列人物肖像,以鞭辟入里的文学笔法挞伐国民的奴性、羸弱和愚昧。《狂人日记》更是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描写成“吃人”的历史。在陈独秀看来,传统文化是“尚谦让以弱民性”,“儒者作伪干禄为吾中华民德堕落之源”,“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陈独秀,1993:162、175、320)。在李大钊看来:“……两千多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礼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哪一样不是牺牲被统治者的个性以事统治者……,尊奉封建伦理首先不是使他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李大钊,1984:178)通过从文化深处挖掘个性压制和国民劣根性的根源,传统文化从而成为必须抛弃的东西,个性则成为国民建设必须张扬的重点。
当然,除向传统文化展开猛烈批判外,民初知识分子没有忘记晚近“国家主义”方略的问题。因此,大部分知识分子主张适度分离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给个性以自由发展的空间,甚至把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倒转过来,把前者看作是实现后者利益的手段。例如,陈独秀认为:“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陈独秀,1993:166)。从这种关系伦理中不难看出,国家成为实现个人自由、权利和幸福的手段。与晚清知识分子把国民与国家的关系比作鱼水和枝干关系的做法相反,在胡适看来:“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就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素,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胡适,1996A:456)独立自由的人格被看作是酒里的酒曲、面包的酵素、身体的脑筋和国家进步的希望。在国民与国家的关系中,孰重孰轻不难看出。
在批判传统文化和倒转国民关系之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个性发展成为民初知识分子重塑国民话语策略的重点。在此之前,个人主义负载的主要是一种负面的价值,被看作是自私自利、离散国民、漠视公益等的同义词(郭忠华,2012)。但经过民初知识分子的语义改造,个人主义不仅负载正面的价值,而且还被看作是西方政治文明的基础和中国政治现代性的希望。例如,胡适认为:“欧洲有了18、19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胡适,1996B:456)陈独秀提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陈独秀,1993:131)鲁迅认为:“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鲁迅,1981:24-25)在正名个人主义价值的基础上,民初知识分子继续阐发其内容,把它看作是“个人自身的充分发展”和“个人对社会责任”的有机结合。例如,陈独秀主张,个人主义的发展在于“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陈独秀,1993:186);胡适提出:“发展个人的个性,需要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胡适,1996A:466)
但是,随着五四运动的出现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这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想象没能走得更远。自此之后,以阶级、政党、集体等为基础的话语策略取代了以个性、权利、平等、自由等为基础的话语策略。国民话语从此黯淡下去,或者逐步退出政治话语的舞台,或者与政府(如国民政府)、党派(国民党)、革命(国民革命)、武装(国民革命军)等联系在一起。一时高扬的个性发展、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等旗帜不仅不再成为话语的主流,而且重新被污名化为危险的修辞。
由此可见,清末民初的citizen翻译始终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进程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集文本翻译、语义改造、政治想象于一体的过程。鸦片战争后的政治形势为西方citizen的引入和翻译提供了契机。这一时期的citizen翻译尽管表现出偶然性和对译术语多元性的特征,但它依然催长了本土知识分子的政治现代性知识及其关于本土政治现代性的初步想象。戊戌变法后,晚清知识分子有目的地在citizen涵义的基础上翻译和改造“国民”概念,旨在在“国家主义”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的现代国家。晚清国民话语策略的失败激发了民初知识分子的进一步思考。在总结“国家主义”话语策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综合citizen、citizenship、individual和individualism等概念涵义的基础上,民初知识分子重新翻译和改造“国民”的语义,企图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重绘中国现代国家的蓝图。以citizen为基础的术语翻译在华夏故地尽管历经波折,但中国“现代国家”的追求却是其中一以贯之的旋律。
[1] 陈宝泉、高步瀛(1905).国民读本.上海:南洋官书局.
[2] 陈独秀(1993).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3] 陈天华(1994).猛回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4] 勾口雄三(1999).作为“方法”的中国.林右崇译.台北:台湾“国立”编译馆.
[5] 勾口雄三(2011).中国的公与私·公私.郑静译.北京:三联书店.
[6] 郭双龙、龙国存(2003).“国民”与“奴隶”:对清末社会变迁过程中一组中坚概念的历史考察.中国文化研究,1.
[7] 郭忠华(2012).清季民初的国民语义与国家想象:以citizen、citizenship汉译为中心的论述.南京大学学报,6.
[8] 胡 适(1996A).胡适文存:第1集.合肥:黄山书社.
[9] 胡 适(1996B).胡适文存:第4集.合肥:黄山书社.
[10] 胡 适(1998).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
[11] 黄兴涛(2002).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创刊号.
[12] 惠 顿(2003).万国公法.丁韪良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3] 康有为(1977).公民自治篇.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
[14] 金观涛、刘青峰(2009).观念史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
[15] 精 卫(1906).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4号.5月1日.
[16] 李大钊(1984).李大钊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7] 梁景和(1999).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8] 梁启超(1994).新民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 梁启超(1999).论译书.张品兴编.梁启超全集:第1集.北京:北京出版社.
[20]梁启超(2010).戊戌政变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1] 刘 禾(2008).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和被译介的现代性.北京:三联书店.
[22] 鲁 迅(1981).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3] 孟德斯鸠(1981).孟德斯鸠法意:上册.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4] 伤心人(1900).论中国国民创生于今日.清议报:第67册.12月22日.
[25] 沈松侨(2002).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1895-1911.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四分册.
[26] 司马迁(1959).史记·乐书第二: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
[27] 宋志明(1994).编序.梁启超.新民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8] 唐宝林、林茂生(1988).陈独秀年谱.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
[29] 万齐洲(2011).“公民”观念的输入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湖北大学学报,6.
[30] 王树愧(1969).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
[31] 魏 源(1998).海国图志:第16卷.长沙:岳麓书社.
[32] 严 复(1960).原强.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
[33] 佚 名(1901).叙例.国民报:第1期.5月10日.
[34] 佚 名(2003).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
[35] 章士钊(1903).箴奴隶.国民日报汇编:第1集.5月8日.
[36] 邹 容(2002).革命军.北京:华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