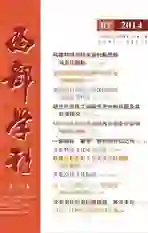写意:江河记述的别样传统
2014-03-19李菁
摘要:写意是与撰经完全不同的记述江河的方式,是一种以诗人为审美主体、以流水为审美客体、以诗歌为主要媒介而形成的意象撰写传统。流水既可以被严谨书写,上升为“经”,也可以被审美观照,行之于诗。水经撰述让我们认知江河的自然特性,写意江河则让我们读到不同河流的性格与品质、灵性和精神。
关键词:江河记述;写意;长江;黄河;湘水
I206.2
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环境关怀中,古人对与其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河流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形成了颇具代表性的水经撰写传统,《尚书·禹贡》《山海经·五藏山经》《山海经·海内东经·附篇》《水经》《水经注》以及《水道提纲》等皆为这一传统的具体体现,对此学界研讨之声不乏。与这种基于理性层面的记述方式不同,另有一种别样的记录江河的传统,这里姑且称之为“写意”。流水既可以被严谨书写,上升为“经”,也可以被审美观照,行之于诗,在古人对河流认知、探索以及渐次亲近的过程中,写意与撰经同等重要,并行不悖。当撰写水经的传统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时,写意江河似乎也不应当被忽视,值得我们返顾一论。本文试在唐诗语境下,以横贯大陆西东的长江、穿越中原腹地的黄河和地处中南一隅的湘水为例,展现唐代诗歌中充满着文人情怀的江河印象。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面对流水,性情不同,趣味也不同,此非一个“乐”字可了,品读唐诗意象,见此情形多矣。能够进入唐代诗人眼帘的江河并不多,文学意象较为丰富的大水脉只有长江、黄河、渭水、汉水、湘水等,他如辽河、珠江或闽江,彼时尚远在多数诗人的视线之外。河流大都有着不同的性格和品质,在诗歌世界里,其灵性、其精神往往通过多个意象体现出来。意象让河流变得诗意,河流因意象而丰富厚重;江河意象的形成固然与其水之清浊缓急、流之长短曲直有关,但主要还是历史文化背景使然。
一、长江:一脉水流,两重遗恨
唐诗中与长江有关的意象很多,如江水、江岸枫林、滟滪堆、猿啼、子规、巫山神女等等,其中涵义最为丰富和隽永的是江水意象。流动是水的特性,逝者如斯,但在诗人眼中,流走的不仅是水,更是水上所载之舟与舟上济渡之人,而那人,又是刚刚道过珍重依依惜别渐行渐远的至爱友朋。所以,江水意象之内涵与世间情事联系得最为密切的便是离恨。水边多别离,非独长江如此,但在唐人笔下,江水着墨最多因而也最为突出。一脉水流咏出两重离恨,仿佛世间所有的离愁别绪,都融进那无语东流的江水中了。首先,诗人以江水喻永恒,恒长但无情。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云:“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祇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此数句道出了永恒宇宙与无常人世的强烈对比,永远的江月、恒长的江水把这种对比推向极致,诗人的感伤喟叹在诗行间显现无遗。这是江水意象喻指的第一重离恨——死生之离、终极之恨。不废江河万古流,江水永远东去,而人类纵然绵长永久,个体生命在存留瞬间之后,却不得不匆匆舍下亲朋故旧、辞别所依所恋,永远地消失离去。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与江水相比,人是渺小的,生命是短暂的;世间的死生之离日复一日无休止地上演,对应着江水年复一年表情似霜地流过。只要这一幕无情的对比仍在,诗人的离恨便永远不可能消解,这一层别离,留给读者的是关于生命深邃的哲理性的关怀。非但生命如此,历史的风云变幻、朝代的昔更今替在江水面前也只是沧海一粟、天地一刹。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寺即陈将吴明徹战场》云:“古台摇落后,秋日望乡心。野寺人来少,云峰水隔深。夕阳依旧垒,寒磬满空林。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至今。”吴公台为南朝古迹,位于扬州江都县西北。诗人登古台而“惆怅南朝”,托古咏怀,发思古之幽情;人事已往,惟馀旧垒古台,只有那江水,昔也东流,今也东流,江潮起落,日日如此,任凭诗人洒落再多的惆怅感伤,也留不住它匆匆的步履。
其次,诗人托离情于江水,诉不尽别愁,这是江水意象在唐诗中喻指的第二重离恨——情感之离、久别之恨。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云:“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老友与诗人辞别,乘舟东下,诗人久立黄鹤楼头,向舟行方向眺望。他掠过江面上点点帆影,目光惟聚老友所乘之舟,直至孤帆消失在碧空尽处。其时正当百花争艳的阳春三月,长江之上必是舳舻相属、万里连樯,何以仅见“孤帆”?正所谓一切景语皆为情语,“孤帆”者,实乃诗人彼时唯一用心凝神之处,伤别、惜别,千般不舍都在此二字中了。诗歌至此,情意已见,但高明的诗人于诗尾巧用江水意象,再吟七字,将诗意伸足。舟帆行出视线之外,诗人的情感却并未因之戛然而止,那兀自东去的江水,不正似诗人满腔的依依惜别之情,追随着友人离去的步伐,滔滔汩汩流向天边、言虽尽而意无穷。明人唐汝询言:“帆影尽则目力已极,江水长则离思无涯,怅望之情,俱在言外。”[1]632诚是。托离情于江水,无江水意象入诗,诗人的言外之意恐怕得不到如此完美充分的体现。这种寓无尽之别情于无边之长江、赋抽象之思绪于具象之流水的写法在唐诗中可谓俯拾即是,伴随着“无情”的恒长,唐诗中不时响起一声声喟叹。上引张若虚诗句于“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下吟道:“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诗情在此由自然之景转向了人间之情,这一转变的巧妙实现,得力于有情江月与无情流水的互衬,孤月年年执着守候、江水却日日兀自流走的意境描写与世间男女“郎无情妾有意”的无奈何其相似、足可比照。江水是恒长的,但这恒长中带着大自然的冷漠与无情,任凭人世的聚散离合一番番你方唱罢我登场,它且汩汩流淌、滔滔东去。他如韦承庆《南行别弟》云:“澹澹长江水,悠悠远客情。”李商隐《妓席暗记送同年独孤云之武昌》云:“迭嶂千重叫恨猿,长江万里洗离魂。”所抒情怀皆属此类。
唐诗中的长江,既有上述鲜明的江水意象,也有夹峙江水的两岸意象,后者主要集中于三峡地区,如枫林、滟滪堆、猿啼、子规、巫山神女等等。诸意象中,属猿啼着文人之色较多,因而文学意味也更浓。此意象常见于江上行舟诗中,所谓“猿声一叫断,客泪数重痕”[2]388,举凡游子客愁、失意怅怀、舟人漂泊、生计多艰之悲全由“猿啼”二字起,而这数种悲感,又皆自“别离”而来——客愁因离乡起,失意因去国起,漂泊因辞亲起。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云:“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3]1748这使人听罢泣下沾裳的泪,其实质依旧是离恨泪。因此,猿啼意象在唐诗中的使用,给江水又平添了一层离恨。借猿啼写离思客愁的诗例极多,如僧贯休《三峡闻猿》云:“历历数猿声,寥寥渡白烟。应栖多月树,况是下霜天。万里客危坐,千山境悄然。更深仍不住,使我欲移船。”马戴《巴江夜猿》云:“日饮巴江水,还啼巴岸边。秋声巫峡断,夜影楚云连。露滴古枫树,山空明月天。谁知泊船者,听此不能眠。”二诗表面上只写猿啼而不言客愁,但不言愁非无愁,实无须径言也,所谓“更深仍不住,使我欲移船”、“谁知泊船者,听此不能眠”者,均是愁苦离恨极深之语。可见“猿啼”或“猿鸣”在长江行水诗中是一个诗意的符号,有“闻猿”、有“夜猿”,有“啼”、有“听”,则“离”、“思”、“愁”、“苦”等情感自见,而诸语皆不必明白道出也。刘禹锡的《竹枝词》似乎是个例外,诗云:“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个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末二句说愁人自愁,愁肠自断,干猿啼何事?诚然,清猿晨啼,其声本无所谓喜,亦无所谓悲,但愁人若非自悲,又怎能听出悲来?此诗感情深沉,一反常语,也一反常意,离思恨意明明因闻猿而生,却偏说不是此声悲。品其诗味,究其实质,岂非反语正意?因了猿啼又撇开猿啼,其间愁肠百结,比正用猿啼意象更增十倍。
江水可代永恒的自然,反衬出人世之短暂,又可代离愁,喻其不舍,谓其难止。永恒出自无情,感伤缘于短暂。诗人以有情写无情,以无情衬有情,死生之离也好,情感之离也罢,两重恨都从无情中来;而无论流水,或是猿啼,又都在有情之中。江水,原只是一脉长流蜿蜒,却如此生动地化作诗人笔下的一个语码,任其撷入诗行表情达意,唐之诗人赋予长江者,何其多情而生动!
二、黄河:天水豪迈,难求一清
黄河以其奔腾的气势、不羁的性情入唐诗,而唐人笔写黄河者,又以李白最为特出。举凡河水一泻千里之壮阔、撼山动地之咆哮、横空出世之超迈、落天走海之豪放,都能在李白笔下找到非凡的描摹,河水的自然意象因之在唐诗中定格。
著名的《将进酒》开篇即云:“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在唐人心目中,黄河之水好似从天而降。这种对河源的有趣认识和诗性定位大概出于两方面缘由:一是古人认为“河出昆仑”,而昆仑连带着天庭西王母的各种传说,陌生与不知导致了神秘和猜测;二是河水自高原冲落,沿途经过龙羊峡、黑三峡、青铜峡、晋陕、崤函等多个峡谷,坡降极大,水流湍激,其势威、其情壮,恰好比银河自九天陡然坠落。当然,河水不可能从天上来,但诗人瑰奇的想象、夸张的语词足以写尽黄河源远流长似从天降、万里雷鸣东走大海的非凡气势。同样以精彩绝伦的诗笔描摹河水之壮阔宏大的还有《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谷转秦地雷。荣光休气纷五彩,千年一清圣人在。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箭射东海。三峰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开……”这是李白在华山之巅看到的黄河。河水源长,像一根细丝自天际逶迤而来;然甫出龙门,山开地阔,便豁然奔放一泻千里,洪波滚滚直冲西岳。山阻水势,但见河水咆哮着,劈山开道,奔腾入海,声如雷霆,壮若被激;河面上浪花四溅,在阳光的照射下五彩缤纷、绚丽斑斓。李白笔落惊天,仅此数句便将河水的神韵——不可遏制的力量、排山倒海的气势、怒涛卷起的色彩、生命跳荡的动感刻画了出来。“气势”是河水的性格,也是其自然意象在诗国中最主要最突出的所指。笔写这一意象者,还有骆宾王《晚渡黄河》之“通波连马颊,迸水急龙门。照日荣光净,惊风瑞浪翻”、王之涣《凉州词》之“黄河远上白云间”、孟郊《泛黄河》之“谁开昆仑源?流出混沌河。积羽飞作风,惊龙喷为波”、温庭筠《拂舞词》之“黄河怒浪连天来,大响谹谹如殷雷。龙伯驱风不敢上,百川喷雪高崔嵬”等等。就唐诗中描写河水气势的作品言,不论阶段抑或风格,与李白咏河诗句相较,皆可谓内容无出其外、成就无出其上。
河水入诗,不独在自然意象,亦在社会意象,此其与长江不同之处。自然意象以气势胜,社会意象以悲凉或深沉胜。唐时,黄河上游陇西至河套一带实为胡汉之间的界河,乃边塞所在,渡河即出塞,渡河者多为与胡人作战的将士或边地幕府文人。从这一意义上说,河水又与戍边、边战有关,并进而与边关之思、征人之恨等情愫结下了不解之缘。王昌龄《旅望》云:“白花原头望京师,黄河水流无尽时。穷秋旷野行人绝,马首东来知是谁?”首句“白花原”一作“白草原”,当以后者为是。《(雍正)陕西通志》卷十三“山川六·绥德州清涧县”条载:“白草原,在县东百三十里,黄河岸侧。”[4]诗歌之作地既明,则“望京师”、“旷野”、“行人绝”、“马首东来知是谁”云云,其情其景,皆有了着落。唐汝询评曰:“京师辽远,边土萧条,彼马首而东者谁乎?大都皆狄虏也。此出塞之初,周览边庭之景象如此。”[1]648唐氏所解或未可尽信,然昌龄之诗意显豁:河水奔流无尽,可诗人并不想彰显其落天入海永不停息的力量,而是借此抒写渡河者的孤独、寂寞和一眼望不到头的乡关之思、盼归之怨。河水在这首诗中呈现出的是与上一意象完全不同的面貌,不见声之洪势之壮,而是绵长不绝的离恨和凄苦。又有柳中庸《征怨》云:“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王偃《明君词》云:“北望单于日半斜,昭君马上泣胡沙。一双泪滴黄河水,应得东流入汉家。”诗语不仅明确表达了黄河两岸胡汉相隔之意,而且在河水中融入了背井离乡渡河出塞者无尽的幽怨泪,烙进了浓重而悲凉的历史感。
作为社会意象的河水,还有着深沉的政治蕴含。河水在流经黄土高原时裹挟了大量泥沙,所以,“清湛”二字与河水无缘,早在战国时期,“浊河”便是黄河的名称。黄河中游冲刷下来的泥沙大都沉积在下游,下游河床因此不断淤高,水患严重威胁着下游民生的安宁和祥和。于是,决溢、改道、泛滥、治沙与河水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如影随形。古人有“千年难见黄河清”的说法,所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人寿促而河清迟,一个人想在有生之年见到河水清流,几乎没有可能。河水总是浑浊的,浊时常有清时难,由此,联想到政治清明的难求难遇,“海晏河清”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君主圣明、天下太平的象征,一如传说中的天下大治即有凤凰朝仪。于是,雄浑奔放的河水因为“圣人出则黄河清”的政治期待而拥有了严肃的政治意义,“临河俟清”或“河清喻治”成为它最常见的社会意象,其诗歌抒写特点是只重意象内涵而无须临河望河,实其意而虚其水,上引李白诗句“荣光休气纷五彩,千年一清圣人在”便是“临河俟清”意象径直的表白。有不少唐诗直接喻盛世为河清加以正面颂扬,如张说《东都酺宴》云:“尧舜传天下,同心致太平。吾君内举圣,远合至公情。……喜气连云阁,欢呼动洛城。人间知几代?今日见河清。”杜甫《洗兵马》云:“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淸颂。”薛逢《九日曲池游眺》云:“正当海晏河清日,便是修文偃武时。绣毂尽为行乐伴,艳歌皆属太平诗。”这些诗句逢盛世而咏河清,用朴素的语言极好地诠释了河水“河清喻治”的意象内涵。“河清”在诗人笔下,或用于开启全篇,导引出如泉诗思;或用于总括全诗,使诗意戛然而止。它代表的是盛世、治世、太平和一统,是诗人热烈洋溢的歌咏、激情满怀的颂扬。河水在这类诗中,失却了它雷霆万钧不可阻挡的气势,但拥有了深邃的历史政治内涵。
此外,河水还有其他喻义。李白《行路难三首》其一云:“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今安在?”诗中所谓“渡黄河”者,乃是虚写,是比喻,诗人并非真有过河的打算,只因河水波洪浪险,难以航济,故而在诗人眼中,河水意象有着世路维艰、欲进无途的现实蕴涵,“欲渡黄河冰塞川”是这一蕴涵最为生动形象的体现。同样是写河水,李白还有“黄河若不断,白首长相思”[5]、“阳台隔楚水,春草生黄河。相思无日夜,浩荡若流波”[6]等诗语,诗人以滔乎莫知其极的河水比喻绵长不断的人间情思,给声威气壮的黄河增添了温情柔美的一面。在这类诗语中,壮美的河水与秀美的江水一样,都化作了无穷无尽的人间相思。
三、湘水:怀古幽情,隐逸之思
相对于横贯大陆西东的长江和穿越中原腹地的黄河,偏于中南的湘水拥有更为丰富的楚地传说语境和人文神秘色彩,可谓集南方河流的神秘与楚风骚韵于一身。而这,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颇有关系。湘水流域唐时大体归入江南西道西部,较之关中、山东和江南,此地尚属不甚发达之区,尤其是唐前期,直可谓人事两寂寞,此其一。其二,沿湘水溯洄的唐人多为坐事流贬此地,或经由此地谪向岭外者,行人特殊的身份和别样的情感使湘水与众不同,何况早在唐前,湘水就已然在传说中变得凄美而神秘。这种特定的地理文化积淀使进入唐诗的湘水充满了迁客骚人的怀古幽情和隐逸之思,因此,“怀古”和“隐逸”演绎着湘水意象的两大内涵。
先说怀古,这一情感有两个方面,一为湘妃怨,二为屈子恨。唐代诗人泛舟江上、临江写怀甚或异地遥想时,常提及传说中挥泪染竹、泪尽投江的湘水神即湘妃(又作湘君、湘夫人、湘灵),歌咏频见。如张九龄《杂诗五首》云:“湘水吊灵妃,斑竹为情绪。”卢仝《秋梦行》云:“客行一夜秋风起,客梦南游渡湘水。湘水泠泠彻底清,二妃怨处无限情。”施肩吾《湘川怀古》云:“湘水终日流,湘妃昔时哭。美色已成尘,泪痕犹在竹。”不可胜举。这是帝尧之女娥皇、女英殉舜传说在唐诗中的再现,其文献依据主要有《山海经》《楚辞》《列女传》和《博物志》。在这几部史料(或文学作品)的递进中,湘妃故事逐渐成型并丰富,其悲失良偶、泪染丛筠、遗恨千年不能散去的身姿馀韵,为唐人提供了极富象征意味和生发力的诗材。于是,诗人的字里行间便有了诉不尽的生离之苦、死别之恨、孤独寂寞与哀怨幽愁,湘水也因之披上了一抹凄清幽怨的色彩,其意象内涵之一由此生成。唐诗所云“目极楚云断,恨连湘水流。至今闻鼓瑟,咽绝不胜愁”[7]、“心断绝,几千里,梦中醉卧巫山云,觉来泪滴湘江水”[8]、“今夜灯前湘水怨,殷勤封在七条丝”[9]、“有美一人兮,婉如青扬。识曲别音兮,令姿煌煌。绣袂捧琴兮,登君子堂。如彼萱草兮,使我忧忘。欲赠之以紫玉尺、白银铛,久不见之兮,湘水茫茫”[10]等等,其间之“湘水”,因了这样的传说背景,都有了特殊的内涵。不言湘妃怨,不言湘竹泪,不言湘灵瑟,只言“湘水”、“湘江水”,便自然有怨在、泪在、瑟音在。在这类唐诗中,湘水非水,而是一串串为相思、思念而流淌的泪,是一首充满了感伤情绪的歌。
较之凄清幽怨,湘水怀古蕴涵之“屈子恨”明显地多了一份人生悲感,并由此而显得悲凉甚至沉重。因为这一蕴涵的来源和主体是信而见疑、忠而被放、自沉汨罗的屈原,一缕忠魂入唐诗,为这类作品增添了厚重的历史感。“独馀湘水上,千载闻离骚”[11]、“灵均昔日投湘死,千古沈魂在湘水”[12]、“莫问灵均昔日游,江蓠春尽岸枫秋。至今此事何人雪,月照楚山湘水流”[13]等诗句,都将湘水与屈原同歌并赋。昔日屈原怀沙自沉的是湘水支流汨罗江,但唐人过湘即思屈原,显然,怀古是因为叹今,吊屈是为了伤己,与史实的具体发生地无须有太大关系。千年前发生在湘水之上的灵均之悼,最大的意义莫过于迁客骚人的自伤身世之悲,他们借史实明志,以屈原之怀忠见逐比况自身之怀才不遇,借他人酒杯浇一己块垒。“北阙九重谁许屈,独看湘水泪沾襟”[14]、“一掬灵均泪,千年湘水文”[15],在一枝枝充满悲悼之情的唐人诗笔下,湘水的灵动淡出了,取而代之的是凝重。刘长卿有著名的诗句云:“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16]当年贾谊谪为长沙王太傅渡过湘水时,尝为赋以吊屈原,追伤之而自喻。刘长卿诗谓:昔日自沉于此的屈原,焉能知晓百年后有贾谊远至湘水之滨来哀悼自己,而贾谊,又怎会想到近千年后有谪臣刘长卿迎着瑟瑟秋风前来凭吊呢?湘水无情,不知古今人心曲,不为人情而驻足,而今人之心曲,只有同命共运的古人能懂。其实,湘水本无所谓有情无情,多情的永远是世人,隔着悠远的时空吊古伤怀,给流水平添了多少愁绪多少恨!
湘水意象的第二内涵是隐逸之思。诗人驾扁舟于水上,感受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平静悠闲时,原本极易生出遗世独立甚至羽化登仙的遐想,非湘水而独然。但遍览唐诗可以发现,较之长江、黄河,湘水碧波似更能唤起诗人的归隐之思和绝世之想。这或许与上文所及湘水的历史蕴涵有关,与此地士多隐逸的文化风气有关,也与湘江水清波澄的天然特质有关。湘水又名潇湘,“潇者,水淸深也。”罗含《湘中记》云:“湘川淸照,五六丈下见底石,如摴蒱矢,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是纳潇湘之名矣。”[3]1949知湘水得名于其水质之清深。至唐,其清依旧,《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七“江南道三·岳州湘阴县”条云:“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了了见底。”[17]无怪乎“湘水清”、“清湘”、“湘水碧”等语常见于唐诗中,如“湘水清见底,楚云淡无心”[18]、“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19]、“雪霁楚山碧,月高湘水清”[20]、“澄澈湘水碧,泬寥楚山靑”[21]等等。诗人南行至湘水,泛舟于茫然万顷之上,见水波清滢,想上古传说,情思远扬,不由得把世情看淡,直想抖落满身尘迹,高唱渔歌远去。职是之故,清澈幽深的湘水使诗人涤烦去虑,在诗人尤其是入仕士子眼中,湘水是一片远离宦情、挣脱物役的净土,他们浮沉宦海的种种艰难、坎坷、不幸,都在这一泓碧水中淡化、消逝,取而代之的是远离尘网的淡泊之情和旷远逸致,哪怕这澹澹闲情仅只停留在刹那瞬间。张九龄《南还湘水言怀》云:“拙宦今何有?劳歌念不成。十年乖夙志,一别悔前行。归去田园老,倘来轩冕轻。江间稻正熟,林里桂初荣。鱼意思在藻,鹿心怀食苹。时哉苟不达,取乐遂吾情。”所抒之情即为此意,颇具代表性。他如“猿声湘水静,草色洞庭宽。已料生涯事,唯应把钓竿”[22]、“岚收楚岫和空碧,秋染湘江到底清。早晚身闲着蓑去,橘香深处钓船横”[23]、“是是非非竟不真,桃花流水送青春。姓刘姓项今何在,争利争名愁杀人。必竟输他常寂默,只应赢得苦沉沦。深云道者相思否,归去来兮湘水滨”[24]之类,其中“湘水”,既不见思深别苦之幽,也没有悲士不遇之怨,而是远离世情羁绊的自由乐土,是诗人情感的栖息地。于是,在唐人的期待和认同中,湘水意象于清寂、凄美、悲怨之外,又多了一份荡尽尘埃的桃源之念。
哲学家认为: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但在诗意的河流之上,人们可以无数次地往返。可以这么说,河流既是自然景观,故而催生了撰经的记述传统;也是文化景观,由此触发了写意的传录方式。从新文化地理的角度看,文化景观不是一个客观“现实”,一个可以在世界的“某处”被发现的“现实”,而是多重现实的并存,意象的河流即是一例。唐人踏进不同的江河,犹如跨入不同的诗意领域,由此引发的感触和诗兴也全然不同:伫立江岸或泛舟江上时,诗人就进入了多愁而有情的水上意象空间;相反,面对着自天际逶迤而来、裹挟着大量泥沙的黄河,无论济渡还是远眺,诗人总免不了因其壮美而感发吟哦,又在浊河岸上浮想期盼河清海晏。而远在江、河之南的湘水,其水体之清绝、传说之凄美,加上多重的历史元素和南来北往的失意士子,给这一文化景观增添了一抹悲怨而又超然的色彩。我们通过水经撰述,可以阅读到不同水系、不同河段在不同地形、不同季节的流淌,字里行间的目移让我们认知江河的自然特性;而当我们解读了唐诗中的流水意象,熟悉了江河诗性的奔流,就能临水而神思,远隔万水千山悠远时空,在唐人笔底诗意的流水中徜徉,和它们情感共鸣。写意之河与撰经之河的不同,或即在此。
参考文献:
[1]唐汝询,选释.王振汉,点校.唐诗解[M].河北: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2]牛肃.纪闻“巴峡人”//太平广记:卷328(“鬼十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郦道元.水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按《艺文类聚》卷7、《太平御览》卷53所引稍异。
[4]沈青峰.(雍正)陕西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曹寅.全唐诗:卷175[M].北京:中华书局,1960.
[6]李白.寄远十一首(其六)//曹寅.全唐诗:卷184[M].北京:中华书局,1960.
[7]陈羽.湘妃怨//曹寅.全唐诗:卷348[M].北京:中华书局,1960.
[8]卢仝.有所思//曹寅.全唐诗:卷388[M].北京:中华书局,1960.
[9]裴夷直.赠美人琴弦//曹寅.全唐诗:卷513[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0]贯休.善哉行//曹寅.全唐诗:卷826[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1]陶翰.南楚怀古//曹寅.全唐诗:卷146[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2]李群玉.競渡时在湖外偶为成章//曹寅.全唐诗:卷568[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3]黄滔.灵均//曹寅.全唐诗:卷706[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4]刘长卿.送侯中丞流康州//曹寅.全唐诗:卷151[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5]孟郊.楚竹吟酬卢虔端公见和湘弦怨//曹寅.全唐诗:卷372[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6]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曹寅.全唐诗:卷151[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7]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8]刘长卿.入桂渚次砂牛石穴//曹寅.全唐诗:卷151[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9]柳宗元.渔翁//曹寅.全唐诗:卷353[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0]李中.览友人卷//曹寅.全唐诗:卷749[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1]皎然.杼山禅居寄赠东溪吴处士冯一首//曹寅.全唐诗:卷815.北京:中华书局,1960.
[22]刘长卿.却赴南邑留别苏台知己//曹寅.全唐诗:卷147[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3]秦韬玉.长安书怀//曹寅.全唐诗:卷670[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4]贯休.偶作因怀山中道侣//曹寅.全唐诗:卷836[M].北京:中华书局,1960.
作者简介:李菁,女,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隋唐文史。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度青年基金项目“唐代运河与文学创作的关系”(07JC75101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