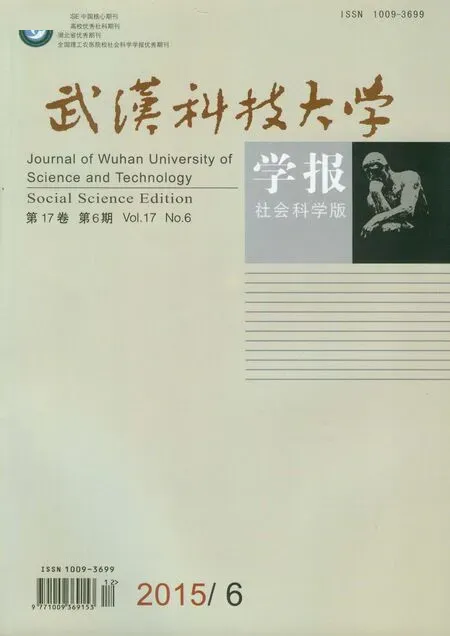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观念的汉代“黄老”展观
——《淮南子》行政管理思想论纲
2014-03-18高旭
高 旭
(安徽理工大学 楚淮文化研究中心,安徽 淮南 232001)
《淮南子》是秦汉思想史上的一部奇书,博采百家之长,自成一家之言,由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共同编撰而成,试图“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1]1437,反思和总结先秦以来国家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为西汉统治者提供一种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帝王之道”和“治国之道”。淮南王刘安身为西汉前期著名的诸侯王之一,“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2]3082,十分注重自己封国的政治发展,在“拊循百姓”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并系统地体现在《淮南子》一书中。作为“秦汉道家最成熟的著作”[3],特别是“黄老道家思想的总结性著作”[4],《淮南子》的行政管理思想也显示出引人注目的黄老色彩,很大程度上既可视为西汉前期黄老政治发展的理论产物,又可视为西汉黄老道家一派关于国家管理思想的重要代表之作①。本文拟通过道论、无为论、因循论、法度与仁义论和兼用论五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具体揭示《淮南子》行政管理思想的实际内容、原则、特色及价值,以求深化和丰富该问题的学术认识,并见教于大方之家。
一、道论——《淮南子》行政管理思想的哲学依据
道论是《淮南子》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也是《淮南子》行政管理思想的哲学依据。《淮南子》对道的理解和阐释,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道的宇宙论的哲理思辨,二是道的治国论的人间论证,这两个层面都受到先秦时期老庄哲学和黄老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历史承续中有所时代发展。
其一,在道的宇宙论思辨中,《淮南子》主要承袭先秦的老庄哲学,也受到黄老思想的一定渗透,对道的根源性、无限性、创生性和整体性进一步地深化认识。
道原本是一个普通概念,意指人们日常“所行道也”,是老子将其抽象提升为“极其重要的哲学范畴”,并“第一次在中国哲学史上建立起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5]。在道家思想发展中,老子首先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6]225的观点,庄子也认为“道”的存在是“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7]246-247,老庄认为“道”不仅是宇宙万物得以产生的终极根源,而且是宇宙万物发展演化的内在规律,“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6]254,“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6]194,“道者,万物之所由也”[7]1035。与此相近,稷下黄老学派也认为:“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8]937而《黄帝四经》同样强调:“虚无形,其裻(寂)冥冥,万物之所从生。”[9]5
对先秦道家这种道的宇宙论思辨,《淮南子》不光认同和接受,且有着更为深入具体的哲学阐述:“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浡,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1]2-3《淮南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之本源,具有超越时空的无限性,无形无象地弥漫于万事万物之中。而且,道充分发挥着创生、演化宇宙万物的功能,“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1]60,“夫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跂行喙息,蠉飞蝡动,待而后生,莫之知德;待之后死,莫之能怨”[1]9,道乃万物发展变化必须遵循的自然规律。“道者物之所导也”[1]706,道最终影响万物发展的前景,并决定其命运,“夫道者,无私就也,无私去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顺之者利,逆之者凶”[1]458。在《淮南子》看来,正是在这种无形无穷的存在过程中,道成为宇宙万物赖以存在、演生的终极根源和内在规律,显示出浑然不可分的整体性,“朴至大者无形状,道至眇者无度量,故天之圆也不得规,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道在其间,而莫知其所”[1]797-798。
其二,在道的治国论证明上,《淮南子》坚持和推崇先秦老庄哲学的道治理念,同时,又从西汉王朝的政治现实出发,接受黄老思想的治国主张,强调道在行政管理中的具体落实和操作,突显其应有的人间性、政治性和实用性。
“以道莅天下”[6]286是老子的政治理想,在他看来,为政者管理国家必须遵循道的规律,既要顺应自然之天道,又要合乎世俗之人道,因为“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6]188,只有坚持以道治国,才能让天道与人道和谐统一,实现国家政治的良好发展。而要真正治国以道,则需要为政者在国家管理中无为而治,“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6]203。和老子相比,虽然庄子更为关注道对生命个体的精神作用,但在治国上仍然认同道治理念,庄子认为:“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7]369要求为政者坚持无为的治国路线。
相比老庄哲学,战国稷下以来的黄老思想有着更加强烈的治国诉求,尽管二者都是先秦道家的重要构成,但显然后者并不认同疏离或逃避政治的做法,而是主动强势地参与、介入,力图通过道与法、术的密切结合,赋予原本形而上的道以前所未有的形而下的政治性、实用性,形成一种适应秦汉时期政治变革趋势的治国论。作为战国后期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归本于黄老”[2]2146的韩非提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10],试图用道为其功利主义的法家治国论提供坚实的哲学支撑。《管子》亦云“明君之重道法而轻其国也”[8]563,将道与法紧密关联,认为“夫静与作,时以为主人,时以为客,贵得度。知静之修,居而自利。知作之从,每动有功。故曰无为者帝,其此之谓矣”[8]882-883,要求为政者善于无为而有所为,在管理国家时动静得宜。《黄帝四经》更是充分展现出战国黄老的治国主张:“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9]2,“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必审观事之所始起,审其刑名。刑名已定,逆顺有位,死生有分,存亡兴坏有处,然后参之于天地之恒道,乃定祸福死生存亡兴坏之所在”[9]173,从实质上沟通道与法、刑名的内在关联,把法度刑名作为道在人间政治中重要的落实手段,变老庄哲学的以道治国为黄老思想的以道法治国。
先秦道家的道治理念,不论老庄抑或黄老,对《淮南子》的治国思想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但须指出的是,由于《淮南子》作为“王者之书”的根本立场,使得“帝王之道”、“治国之道”成为淮南王刘安关注和思考的核心议题,“治在道,不在圣”[1]46,《淮南子》延续了先秦道家以道治国的根本主张,强调“国有亡主,而世无废道”[1]624,“不因道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达矣”[1]625。《淮南子》还突出了法在国家管理上的重要效用,要求为政者治国用法,“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1]659,“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执下”[1]667,故而为政者在政治实践中应做到“言事者必究于法”[1]644。这种黄老式的治国理念,在《淮南子》中多有所见,充分反映出《淮南子》道论所具有的人间性、政治性以及隐含其中的迫切希望道发挥治国实效的“求治”意识。
概言之,《淮南子》在政治上探求国家管理之道,而这种道不但有着宇宙论的哲学思辨作为根本依据,而且有着治国论的人间证明作为实现途径。只有同时取得源于自然天道和国家政治的合理性支持,为政者才能创造出一种具有现实操作性的治国模式,使行政管理实践体现出道治理念及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淮南子》的“道”既被“作为万物本源的抽象的、形而上的范畴,它还被当作具体的、形而下的人间政治的基础”[11]26,促使《淮南子》产生“在思想上对道家的倾向,在政治上对黄老治术的推崇以及将二者糅合的努力”[11]31,而这最终让《淮南子》在治国上构建出理想的无为而治的行政管理方式。
二、无为论——《淮南子》行政管理思想的政治核心
在国家发展上,《淮南子》一方面追求道治的理想目标,另一方面也理性指出,道治如要从一种形而上的哲学内涵转化为形而下的政治现实,就必须充分借助无为而治的行政管理方式,既在治国理念上有体现,也在治国实践中去践行。而且,《淮南子》强调在国家管理中君主无为而治具有关键作用,因为从专制政治的现实出发,君主能否秉持无为思想,积极有效地管理自我与国家,实现“内圣外王”之道,将最终影响和决定国家政治的发展方向和状态。因此,《淮南子》对无为而治的政治诠释②,始终将“帝王之道”和“治国之道”紧密相融,试图通过前者带动和确保后者的现实运作,全面发挥出君主作为国家管理者所应有的无可替代的主体作用,促使无为从一人之治走向国家之治,进而合乎道治。
在治国理政上,《淮南子》十分反对过度的“有为”政治,认为“人无为则治,有为则伤”[1]1106,为政者应秉持无为而治、安国利民的根本精神。“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1]613-614,《淮南子》认为国家发展中的政治乱象,往往与为政者的好大喜功、多事烦扰直接相关,这种有为政治对民众的生存发展秩序容易造成消极的影响,导致“上好取而无量,下贪狼而无让,民贫苦而忿争,事力劳而无功,智诈萌兴,盗贼滋彰,上下相怨,号令不行”的“末世之政”[1]611。但是,《淮南子》又指出,在现实政治中,为政者时常意识不到治国理念上的根本歧误,非但不能改弦易辙,变有为为无为,减少自身行政实践对民众生存发展的过度干扰,反而变本加厉,造成更加混乱恶劣的局面,“执政有司,不务反道矫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为治,无以异于执弹而来鸟,捭而狎犬也,乱乃逾甚”[1]611。故此,《淮南子》认为“圣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为而成,块然保真,抱德推诚,天下从之,如响之应声,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1]614,明确反对“事修其末”的有为政治,将无为视为治国之本,强调“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1]48,要求君主在内的“执政有司”应力求实现“以弗治治之”[1]617的管理状态。在《淮南子》看来,一切求“治”之“本”都基于为政者的无为,换言之,只有为政者尽可能减少对民众社会生活的干涉行动,让其根据自身所需和利益自然发展,才能避免“夫水浊则鱼噞,政苛则民乱”[1]612的消极后果。可见,《淮南子》所言无为,作为一种根本的治国理念,具有内在的民本倾向。
《淮南子》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通过为政者的行政管理实践反映出来,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管理、社会风俗管理、人才管理和为政者的自我管理四个方面。
第一,在国家经济管理上,突出民本意识,延续汉初以来黄老政治“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及精神,采取务实有效的行政措施,改善生产条件,解决民众基本的温饱问题,实现富国利民的发展目标。
《淮南子》认为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与否,不但事关广大民众的现实生存,更会影响到国家治理的良序发展。因此,与文景时期“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12]的重农国策相一致,《淮南子》也非常重视为政者对农业经济的管理作用,一方面,要求君主引导民众顺应自然条件,积极从事各种农业生产,解决“足用”的实际问题,“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1]685-686,另一方面,要求君主从国家财政的岁计收支出发,合理赋税,取民有节,适时减轻民众负担,“人主租敛于民也,必先计岁收,量民积聚,知饥馑有余不足之数,然后取车舆衣食供养其欲”[1]681。秉持这种黄老无为的政治精神,《淮南子》认为贤明的为政者应能体察和同情民众的生存艰辛,进而优化对农业经济的行政管理,为民众的农业生产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使其免于饥寒困境,实现“岁登民丰”、“国无哀人”的理想发展。
第二,在社会风俗管理上,主张为政者积极发挥行政管理作用,因顺民性,教化引导民众去诈除伪、移风易俗,形成有利于国家治理的良风美俗。
对国家发展中的风俗之弊,《淮南子》有着深刻认识:“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纪纲不张,风俗坏也。”[1]1403在其看来,民间社会风俗的日渐败坏,往往意味着国家政治走向衰败,“晚世风流俗败,嗜欲多,礼义废,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胸,思心尽亡,被衰戴绖,戏笑其中”[1]602,因此为政者在国家管理上不可不认识到因风俗以治国的重要性。《淮南子》将民性比喻为水,指出:“水之性,淖以清,穷谷之污,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决而高之,使得循势而行,乘衰而流,虽有腐髊流渐,弗能污也。其性非异也,通之与不通也。风俗犹此也。”[1]1402-1403也即是说,为政者在治国上应善于根据民众性情因势利导,扬善抑恶,形成良好的社会风俗,所谓“诚决其善志,防其邪心,启其善道,塞其奸路,与同出一道,则民性可善,而风俗可美也”[1]1403。由此出发,《淮南子》反对为政者在国家管理上片面以刑法治民而轻忽风俗的为治功用,明确指出“若不修其风俗,而纵之淫辟,乃随之以刑,绳之以法,虽残贼天下,弗能禁也”[1]1403。
在社会风俗的变革、移易中,《淮南子》尤为强调为政者的行政效用和影响:“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犹客之乘舟,中流遗其剑,遽契其舟桅,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类亦甚矣。”[1]1169它认为一切制度风俗都应与时俱进,适应国家与民众的发展需求,而不能墨守成规不知变通,因为“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1]921。由于君主在国家政治中处于核心地位,因而《淮南子》强调君主要善于运用所掌握的行政权力,来影响和塑造民众的社会习尚,使其不流于恶俗,“灵王好细腰,而民有杀食自饥也;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由此观之,权势之柄,其以移风易俗矣。尧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为治,而势可以易俗明矣”[1]642-643,所以“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之,经诽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无被创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显之名,民孰不从”[1]1406。《淮南子》认为理想的社会风俗管理方式是,“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为非,其次赏贤而罚暴”[1]621,“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希望为政者能无为而化民,因自然之性而治众,使“民交让争处卑,委利争受寡,力事争就劳,日化上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治之上也”[1]1401。反之,“利赏而劝善,畏刑而不为非,法令正于上而百姓服于下”,只能是“治之末也”[1]1401。《淮南子》这种对社会风俗归于自然朴质的推崇和向往,其间所蕴含的黄老治国理想及精神显而易见。
第三,在人才的行政管理上,主张君主任人唯贤,既要君臣异道而治,把用贤与“用众”结合起来,也要建立人才使用的制度机制,以法、术来管理人才,使人才真正为己所用,发挥实际的政治功效。
(1)举贤而用。“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故一举而不当,终身伤”[1]641,《淮南子》深刻认识到,君主用人是否得当,对国家发展的稳定性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在反思商、周政权更替的历史教训时,《淮南子》指出:“武王伐纣,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钱,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朝成汤之庙,解箕子之囚。使各处其宅,田其田,无故无新,惟贤是亲,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1]694认为西周王朝之所以能稳固发展,与其“无故无新,惟贤是亲”的用人举措密不可分,进而提出“圣主者举贤以立功,不肖主举其所与同”,要求君主在人才的发现使用上,必须以贤为重,而不能根据个人喜好来选用趋同求媚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君主行政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故观其所举而治乱可见也,察其党与而贤不肖可论也”[1]1408。
(2)君臣异道。在人才使用上,强调君主与人才各有其政治地位及职责,为确保人才效用的实际发挥,二者不能混同不分。《淮南子》指出“主道”贵在“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而“臣道”则要“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故此“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1]635-636,“君臣上下,官职有差,殊事而调”[1]732,也就是说,只要君主与人才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互不侵扰对方的职责,国家政治便能合理有序地发展。
(3)用贤和“用众”相结合。对人才的发现使用,《淮南子》具有十分开阔的行政视野,极力主张君主不宜用人狭隘,而是要尽可能扩大人才选用的社会范围,因为“君人者,不下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1]627,换言之,充分发挥人才的群体效应,这有助于君主拓展和强化自身管理国家的能力,不断取得政治事业的成功。《淮南子》还以“举鼎”、“车马”为例,形象说明君主要充分聚集、发挥众人的才智和能力,“夫举重鼎者,力少而不能胜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群无绝梁,万人之聚无废功”[1]627,“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1]634,强调“乘众人之智,则天下之不足有也”,而如果君主“专用其心,则独身不能保也”[1]635。所以,君主在国家管理中要以人才为重,广开用人之途,避免刚愎自用、嫉贤弃才的政治错误,如果能具备用贤和“用众”有机统一的人才条件,那这种“君势”就能以“众势”为坚实基础,发挥出更大的政治效力,“夫七尺之桡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为资;天子发号,令行禁止,以众为势也”[1]638。
(4)以法、术管理人才。在专制政治中,人才的发现和使用并非易事,而是对君主的一种政治考验。“天下多眩于名声而寡察其实,是故处人以誉尊,而游者以辩显。察其所尊显,无它故焉,人主不明分数利害之地,而贤众口之辩也”[1]644,“说谈者游于辩,修行者竞于住”[1]645,如果为政者重于听人之言,却忽于察人之行,则往往得不到真正的有用之才,也失去了人才选用的实际意义。针对这种用人弊端,《淮南子》从黄老立场出发,提出“言事者必究于法,而为行者必治于官。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言不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1]644,“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执下,释之而不用,是犹无辔衔而驰也,群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术则制人,无术则制于人”[1]667-668,主张为政者应以法、术来管理使用人才,促使人才发挥实际的功利效用,这种强调制度化用人的行政主张,被《淮南子》视为“主术”的重要内涵,“所以因作任督责,使群臣各尽其能也。明摄权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责实,考之参伍”[1]1445-1446。以法、术为制度手段,能让为政者有效管理和使用各种人才,做到“百官条通而辐辏,各务其业,人致其功”[1]1445-1446,亦即使百官像枝条通往树干、车辐辏聚车轴一样,各自力求做好本职工作,人人皆可建功立业。
第四,主张为政者要加强自身政治修养,以无为治身,在治国理政中节制嗜欲、清静自持,做到行不扰民、欲不乱政。
《淮南子》承袭“清静为天下正”[6]236的老子思想,主张人性清静论,要求为政者既要重视外在事务的行政管理,更要完善自我的精神修养,坚持清静自守、无为治身,合理节制物质嗜欲,减少扰民乱政的政治行为。《淮南子》认为嗜欲是导致为政者心志淆乱、行为失当的重要原因,“夫人主之所以残亡其国家,损弃其社稷,身死于人手,为天下笑,未尝非为非欲也”[1]552。从历史上来说:“仇由贪大钟之赂而亡其国,虞君利垂棘之璧而禽其身,献公艳骊姬之美而乱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时葬,胡王淫女乐之娱而亡上地”,《淮南子》由此深刻指出:“使此五君者适情辞余,以己为度,不随物而动,岂有此大患哉”[1]553-554,认为君主作为“国之心”,唯有合理节制嗜欲、反己于清静,方能避免随物而动所带来的政治祸患,确保自己的身心和谐和国家的稳定发展。因此,《淮南子》提出:“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1]652-653,要求为政者加强自身清静、无为的精神修养,在国家管理上践行“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的“君人之道”,强调“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节欲之本,在于反性。反性之本,在于去载”[1]997,“节欲”、“反性”是为政者能否推行“安民”、“足用”之政的内在前提,对其“为治之本”的政治实现具有根本影响。这种强调为政者自我管理的观点充分体现出先秦道家一贯主张的“身国同治”理念,《淮南子》不仅强调治身和治国的辩证统一,而且愈加突出治身在道家“治道”思想中的优先性,将政治主体的精神因素提升到决定“为治之本”的理论高度,这对先秦道家内圣之学有着更进一步的历史深化和充实。
概言之,无为论是《淮南子》行政管理思想的核心内涵,作为道论的人间化的政治落实。无为不仅反映在为政者对国家事务的外在管理中,而且深入到为政者主体修养的自我管理上,这使《淮南子》充分实现对道与人之间的政治沟通,让道不再局限于哲学玄思,而是更全面有效地指导国家政治的现实发展,在这种意义上,《淮南子》展示出对黄老治国趋向的务实选择,以此响应西汉统治者强烈的治国诉求。
三、因循论——《淮南子》行政管理思想的基本原则
《淮南子》在治国上坚持无为而治的总体思路,但从实际出发,又提出从事行政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因循”、“守柔”、“持后”和“不争”,其中“因循”最为重要,也最具特色,而“守柔”、“持后”和“不争”都与之密切相关,对前者的政治内涵有所充实深化。《淮南子》之所以强调因循原则,是希望为政者能充分借助和发挥国家政治中的有利因素,减少盲目躁动的有为举措,使自身主观性的治国举措与现实的政治发展规律实现内在的一致性,善于在因顺后者的过程中积极发挥出国家治理的主体性功能,进而取得治国实效的最大化。在先秦道家思想中,“因”不仅是政治哲学的重要概念,“无为之道,因也”[8]771,而且是治国思想付诸实践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因者,君术也”[13]。老子对“因”尽管并未直接论及,但其“无为”、“道法自然”、“柔弱”与“不争”等思想,却成为以后黄老道家因论的理论基础。出于强烈的治国诉求,《淮南子》对因循的思想诠释,主要受到黄老道家的辐射,政治的实用性、功利性较为突出,但是老庄道家偏重于自然主义的因论,对《淮南子》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先秦道家的这种双重作用,使《淮南子》的因循思想更具丰富深厚的政治内涵,成为秦汉时期道家因论的集大成者。
作为重要的治国原则,因循在《淮南子》行政管理思想中有着多方面的渗透和表现,与《淮南子》对“帝王之道”、“治国之道”的政治思考紧密结合。
一是为君之道,要在因循。在道家政治思想中,君主南面之术始终是核心议题之一,《淮南子》亦不例外,视因循为君主有效管理国家的重要原则。“三代之所道者,因也”[1]1019,君主在治国上要善于因循,这是夏、商、周三代取得成功的政治经验,《淮南子》甚至认为:“能因,则无敌于天下。”[1]1386正由于因循的重要性,《淮南子》主张君主在国家管理中灵活运用这一原则,把因循作为主术的核心内容来展现,“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1]605,“主道员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1]635。《淮南子》还要求君主不违背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因循自然以治国,“修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1]33,以无为的精神解决实际的政治问题,“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1]48。《淮南子》强调,君主对国家的政治管理需要合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善于因时制宜以取得实效,在“君道”上突出因循思想,根本目的仍是指向道家的无为而治,其中可贵之处在于,《淮南子》深刻认识到为政者自身能力的有限性,更加突出国家管理的合规律性,反对为政者轻忽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而过度从事主观有为的治国实践,“人知之于物也,浅矣。而欲以遍照海内,存万方,不因道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达矣”[1]625。
二是因资用人,循名责实③。《淮南子》在人才的发现、使用和管理过程中,十分强调因循原则的贯彻和运用。首先,君主应善于发挥人才资源优势,以利于延展和强化其管理国家的能力:“君人者,不下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1]627其次,君主应针对人才的不同特点和类型扬长避短、区别使用,“因其资而用之也”[1]639,“各用之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1]768,使“群臣辐辏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1]635,如此更能促进官僚政治的合理发展,形成“用宜其人”的有利局面。再次,君主应因循法度刑名来管理人才,“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言不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君主“并用周听”、“循名责实”,确保“群臣公正,莫敢为邪,百官述职,务致其公迹也”[1]644-645。
三是因民之性,化风齐俗。《淮南子》重视社会风俗的行政引导和管理,将良风美俗的形成视为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认为为政者不论是对民众的有效管理,还是对社会风俗的积极涵育,都应体现因循原则。首先是因民性情,足民之用,使为政者和民众之间建立良性的政治合作关系。“人之情,不能无衣食”[1]699,为政者只有从实际出发,采取合理的政治举措,满足民众的生存发展所需,才能让民众为己所用,成为国家政治的稳定基础,“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求民为之劳也,欲民为之死也。民之所望于主者三:饥者能食之,劳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1]1090。其次是因民性而治风俗,因礼节而行教化,强化对民众的风俗引导,使其处于安定有序的社会生活之中。“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涤荡之,故因则大,化则细矣”,为政者对社会风俗的行政管理,不应脱离民众的实际发展,而是能根据民众所需积极引导、扬善去恶,以此移风易俗,因俗为治,“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约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县而不用”[1]1090。《淮南子》特别指出,为政者不但要改造利用已有的社会风俗,而且要主动制礼作乐,规范和节制民众的“好色之性”、“饮食之性”、“喜乐之性”和“悲哀之性”,从而教化民众,提升社会风俗的政治文明内涵,充分发挥风俗作为治理国家手段的效用。
和因循原则互为表里,“守柔”、“持后”与“不争”也是《淮南子》行政管理的重要原则,与前者一同反映出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
在道家思想史上,老子首倡“柔弱胜刚强”[6]198、“不敢为天下先”[6]306、“圣人之道,为而不争”[6]348的政治观念,将“守柔”、“持后”与“不争”作为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原则。老子这种认识,成为战国时期黄老道家因循论的思想来源和重要内涵,并深刻地影响到《淮南子》。基于老子的“柔弱”思想,《淮南子》在国家管理上突出因循,反对为政者强势功利的有为政治,“柔弱者生之干也,而坚强者死之徒也”[1]50,“柔之胜刚也,弱之胜强也”[1]856,《淮南子》还进一步深化和突出柔弱的道治意义,将其与治国之道统一起来,“柔弱者道之要也”[1]57,要求为政者在国家管理上实现刚强与柔弱之间的政治转化,能够“以柔治国”,“欲刚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则刚,积于弱则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1]49。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虽强调柔弱的治国原则,但并没有彻底否定刚强,而是试图对二者有所调和折中,显示出刚柔相济的政治智慧,“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1]934。
对道家柔弱治国理念的认同,在国家管理上《淮南子》还要求为政者遵循“持后”、“不争”的基本原则。这种持后、不争,实质上仍是无为而治,但无为绝非是无所作为,而是一种善于判断政治形势,进而把握时机的适时而为:“时之反侧,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时不与人游。故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禹之趋时也,履遗而弗取,冠挂而弗顾,非争其先也,而争其得时也。是故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1]54《淮南子》强调时机的重要性以及不易把握性,认为只有善于因循、能够持后,为政者方可有效掌控时机。这种持后的政治理念,即是“不为物先”,“圣人不为物先,而常制之其类,若积薪樵,后者在上”[1]747,亦即为政者在行政事务的处理过程中,应尽量避免盲目地“争其时也”,而是要审慎观察形势,始终保持自身的政治主动,以此寻求对时机的准确把握,灵活应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故此,《淮南子》曰“得在时,不在争”[1]46,反对为政者缺乏时机观念的有为举措,主张其在国家管理中做到“其行无迹,常后而先”[1]60,善于“争得其时也”,能有所不为而有所为。
总之,受黄老道家“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2]3292思想的深刻影响,《淮南子》在行政管理上十分强调“因循”、“守柔”、“持后”与“不争”的基本原则,因循论成为其行政管理原则的集中体现,具有特殊的理论地位和影响。
四、法度、仁义论——《淮南子》行政管理思想的重要补充
虽然《淮南子》行政管理思想是以无为而治为核心内涵,但在西汉前期黄老政治的历史作用下,也表现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2]3289的思想特色,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包容性,对儒、法、墨、阴阳、名诸家理论都有一定的汲取和融会,其中法家的法度论与儒家的仁义论影响最为显著,成为《淮南子》黄老化的行政管理思想的重要补充和组成,这也深刻反映出西汉前期黄老、儒、法三家在治国思想上日益整合与汇流的重要历史趋向。
从西汉政治现实出发,《淮南子》重视和肯定法度的实际功用,强调为政者应在国家管理上对法度进行有效的掌握和运用。“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县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也”,《淮南子》认为法度的存在出于国家政治的发展需要,不仅是君主用以判断是非、维持现实秩序的基本手段和工具,而且是君主在治国中进行赏罚的重要依据,“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1]660。《淮南子》还认为法度必须具有权威性,能得到君主的公正使用,“衡之于左右,无私轻重,故可以为平;绳之于内外,无私曲直,故可以为正。人主之于用法,无私好憎,故可以为命”[1]621。
对法度现实功用的认识,《淮南子》和先秦法家基本一致,但在法度的本质内涵上,却存在时代性的根本差异。先秦法家不论商鞅、慎到、申不害抑或韩非,都主要从维护专制君主利益的政治立场出发,强调法度的工具性,视其为君主管控臣民的强力手段和重要方式。这种君权至上的倾向性,致使先秦法家眼中的法度在很大程度上缺失民本主义的政治内涵,极易产生过度物化的内在局限,使人的因素脱离了法度的应有之意,从而走上轻罪重刑、任法残民的政治歧途。正因先秦法家对于法度的思想认识潜含着“民本”与“君本”的矛盾,最终导致秦王朝建立之后,极端迷信法度功利化的工具效用,而完全漠视法度本应有的合乎民本诉求的正义内涵,由此造成法度刑罚的全面滥用,促使国家政治赖以存续的制度化基础在泛工具化中崩解。
对秦政的这种历史教训,西汉统治阶层有着深刻的反思和借鉴,“汉兴,除秦烦苛,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2]106,积极推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政治,在慎法约刑中推动社会经济的复苏发展,使民众重获安定有序的生存环境。基于汉初以来的这种政治实践,《淮南子》在思想上明确提出:“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1]662强调法度根源于现实社会发展中民众的生存需求,是合乎人心的政治产物,因此,法度的制定和实施始终应以是否有利于民众利益为衡量标准。“府吏守法,君子制义,法而无义,亦府吏也,不足以为政”[1]699,如果法度在现实中只能体现出功利化的工具效用,缺少与之相适应的民本之义,那么这种法度实践必然对国家政治的稳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也正因此,《淮南子》极力主张法度的发展应该与时俱进,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形势和需要,“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夫能与化推移为人者,至贵在焉尔”[1]796,但是不论法度如何因革变化,对民众利益诉求的充分满足却是不变的根本,“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1]800。出于这种法度重义、以义为本的政治认识,《淮南子》坚决反对片面化的法度路线,深刻指出:“乱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禁而诛不敢。民困于三责,则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故虽峭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何者?力不足也。”[1]814换言之,《淮南子》实际上明智地看到,无法确保民众生存所需的法度实践,只能让法度陷于工具性和正义性的相互背反之中,其结果就是法度的工具效用愈强,则民众受到的现实伤害愈大,而民众也正是在这种不断强化的法度伤害中,日益呈现出“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的政治乱象,最终导致国家管理陷于“虽峭法严刑,不能禁其奸”的严重困境。
对法度内在之义的强调,促使《淮南子》接受先秦儒家的仁义观念,以解决法度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工具化弊端。与法度相比,《淮南子》认为仁义才是国家管理的政治根本,“故仁义者,治之本也”[1]1423,“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1]1422,因为“所谓仁者,爱人也”,而“爱人则无虐刑矣”,“刑不侵滥,则无暴虐之行矣”[1]1434。《淮南子》在这里表现出对儒家仁义政治的时代性的肯定,认为坚持仁义为本的治国理念,不仅有利于法度在国家政治中积极效用的充分发挥,避免引发极端功利化的实践取向,造成滥法虐刑的恶性结果,而且有利于为政者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夯实稳固现实政治的发展基础,“且法之生也,以辅仁义,今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故仁义者,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1]1423。《淮南子》以亡秦为例指出:“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1]1423认为“重法而弃义”是秦始皇在国家管理上的根本失误,其结果只能是加剧为政者和民众之间的矛盾冲突,使国家政治走向民众的对立面,从而丧失其存在发展的社会基础。因此,“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1]1423,《淮南子》认为为政者必须强调仁义对法度所应具有的制约性,推崇仁义内涵的行政伦理价值,突出仁义为本原则,因为“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国无义,虽大必亡”[1]702。
在《淮南子》看来,先秦法家的法度思想对为政者现实的国家管理具有重要作用,其制度主义的法治精神是国家稳定发展不可或缺的政治条件,但是,法度又必须和仁义思想相结合,体现出“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的民本精神,如此才能使其在工具性与正义性之间形成平衡协调的合理关系,从根本上消除现实使用中片面化的工具性弊端,发挥出法度在国家管理上的积极效用。
不论是法度还是仁义,《淮南子》认为都可统摄入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中,因为后者始终坚持“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1]799的思想立场, “既没有像老庄道家那样拒斥其他各家,也没有像儒法诸家那样严守门户之见,而是以其阔达开放的情怀领略百家风骚,于是,成为一个以兼容并包为特色的新学派”[14]。对《淮南子》来说,由于能对法度、仁义进行务实灵活的思想融合,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形成一种适应西汉王朝政治发展的更具包容性和操作性的黄老治国术,故此在行政管理上,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比儒、法两家具有更突出的政治优势。《淮南子》这种以黄老为主,整合儒、法的思想实践,不仅深刻反映出西汉前期先秦诸子治国思想在相互渗透、影响中日趋汇流的历史态势,而且表现出西汉统治阶层在新的大一统条件下,对实现国家理想发展的行政管理之道内在的迫切探求。
五、兼用论——《淮南子》行政管理思想的黄老特色及价值
《淮南子》从西汉前期的政治现实发展着眼,在行政管理上进一步总结和阐发无为而治的黄老道治理念,试图在更大程度上将法、儒、墨、阴阳、名诸家的思想因素与道家的治国主张融合起来,“弃其畛挈,斟其淑静”,以此“兼用而财使之”[1]1396,形成了“兼用百家,一体多元”的理论特色。《淮南子》这种黄老特色的形成,源于其强烈的“务于治”的治国诉求、包容变通的百家意识以及推崇黄老的本位立场。“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1]922,《淮南子》认为百家学说虽然存在显著的思想差异,但其根本点却是一致的,即都是探求现实国家发展的理想政治模式,故而《淮南子》对百家之学具有开明通达的思想态度,体现出汉代黄老重实际、轻门户的政治理性。不仅对“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黄老治国术在行政管理上给予充分体现,而且整合百家之学的思想优长,做到“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而“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1]1462-1463。从这个意义上看,《淮南子》在行政管理上以黄老道家为主体,兼用百家,既是从西汉政治现实出发所作出的实用主义的历史选择,也是西汉前期黄老政治发展的现实选择。对淮南王刘安来说,这种既“没有走上闲暇从容的抽象思辨之路(如希腊),也没有沉入厌弃人世的追求解脱之途(如印度),而是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15],更符合其作为西汉统治阶层中重要一员的政治身份。
刘安身处文、景、武三朝,正是西汉王朝从建立日渐迈向繁荣的历史上升时期,因此,何以治天下成为摆在西汉统治阶层面前最重大的政治议题,与陆贾、贾谊、贾山、晁错和司马迁等人一样,淮南王刘安通过《淮南子》对此也作出了自己的历史回应。一方面,《淮南子》指出:“百家异说,各有所出”[1]117,另一方面,又强调百家之学也有着内在的思想共识,为政者既要看到百家学说的差异性,更要看到百家学说的一体性,从国家管理的高度出发,合理兼采百家优长,打破狭隘的学派门户之见,展开灵活务实的择取运用。当然,《淮南子》虽然强调百家之学的思想共识,但百家的地位存在本末、主次之分。《淮南子》认为黄老道家作为一种能“与化推移”的开放包容的政治学说,比其他学派更具有思想整合的优势。《淮南子》对儒、法、墨、纵横诸家进行批评:“今商鞅之启塞,申子之三符,韩非之孤愤,张仪、苏秦之从衡,皆掇取之权,一切之术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闻而世传者也。”[1]1424很显然,《淮南子》认为从治国之道来看,道家的优越性远非他家可比,这决定了百家之学的思想整合,只能以黄老为本,不论诸子百家思想因素如何多元、丰富,黄老思想都是发挥统摄作用居于主体地位,难以为其他学派所遮蔽和取代。
正是这种推崇黄老的本位意识,使《淮南子》能以开放宏达的思想气度博采和熔铸百家之长,进一步拓展、丰富汉代黄老的治国理念,在行政管理上形成了极富启示价值的思想内涵。要而言之:一是《淮南子》对黄老思想的推崇,并没有局限在战国稷下黄老、马王堆帛书黄老的历史范畴,仅是注重对“刑名”、“因循”的政治阐发,而是深入地“引庄入黄”,将老庄的治身思想充实到汉代黄老的治国理念中,使其对行政管理的主体认知更为深刻和丰富,充分展现出汉代黄老的历史气象和特质。二是《淮南子》深化了汉初以来无为而治的根本理念,要求为政者具有积极的无为精神,增强和优化自身的国家管理能力,而非消极的无所作为、胡乱作为,“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1]1322。由此一来,《淮南子》在行政管理上就把人的合理“有为”纳入了无为概念中,突出为政者按规律办事的治国要求,在西汉时代条件下,“最大程度地扩充了老庄‘无为’概念的内涵,实现对老子‘无为’思想飞跃性的发展”[16]。三是《淮南子》在行政管理上善于折中融合百家之长,使其发挥出综合优势。《淮南子》立足黄老本位,引入儒家的仁义、德治思想来弥补法家法度政治的功利化弊端,充实后者应有的正义内涵。《淮南子》的这种思想努力,反映出西汉统治阶层在深刻总结秦亡教训的过程中,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内在地平衡法度的工具有效性与民本正义性,使法度成为国家政治发展的合理手段,充分显示其制度主义的秩序构建效用。此外,《淮南子》还吸收阴阳家的“时序政治观”,主张“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1]439,将自然时序与治国实践相结合,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上,规范性地设计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框架。对墨家的“兼爱”、“非攻”和“尚贤”,名家的“名实”相符,农家的“重农”等思想,《淮南子》也有着内在的思想汲取,对百家之长的有机融会,使《淮南子》在行政管理上能够体现出“应待万方,鉴耦百变”的政治灵活性,充分发挥无为而治的治国艺术。
以现代视野来看,《淮南子》行政管理思想凝聚着西汉黄老政治的成功经验,其代表的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模式,与儒家推崇礼乐仁义的有为政治,“如同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共同构筑了中国古代管理文化的两大主干”,而且其中“道家的自然主义和儒家的人文主义是相辅相成的互相补充的”[17]。对现代国家的管理者来说,《淮南子》这种汉代黄老的行政管理思想,如同治国智慧的不竭源泉,仍然值得用心反思和借鉴!
注释:
①学界目前对《淮南子》政治思想的研讨较多,已积累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却少有论著从行政管理思想的视角出发,对后者所蕴含的古代黄老国家治理理念进行深入系统的专题探讨,因此这仍有待于学者对《淮南子》研究领域的深化拓展。就现有成果来看,较有代表性的有:吕有云《道教政治管理之道研究——道教黄老传统考察》(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版);李玉用、刘柯言《〈淮南子〉中的管理智慧探微》(《管子学刊》2014年第1期);朱永新、范庭卫《〈淮南子〉人力管理的心理学思想》(《心理科学》1999年第5期);龙国智《〈淮南子〉行政伦理思想研究》(中南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等。
②《淮南子》对“无为”的认识具有多重内涵,其核心要义在于先秦老庄的天道自然论和治国无为论,但是经过战国以来黄老思想的深刻影响,时至西汉前期的《淮南子》,这种先秦道家的“无为”论已经发生重大转向,更加倾向于世俗性、事功性的发展,也更加与王朝政治的现实需求密切相关和结合。本文在此主要着眼于行政管理思想的探讨,结合秦汉政治发展,揭示《淮南子》“无为”论的一个重要面向,阐述其实际内涵和表现。
③行政用人属于《淮南子》“因循”论的重要组成,是司马谈所言“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的重要体现,对此学界相关论著均采取这种看法,如: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169-171),雷健坤《综合与重构——〈淮南子〉与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开明出版社,2000年版,P155-162),刘爱敏《〈淮南子〉道论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P151-153)等。笔者在此也持相同认识,并从行政管理思想的视角给予探讨。
[1] 何宁. 淮南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2]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牟钟鉴. 《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81.
[4] 熊铁基. 秦汉新道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7.
[5] 张岂之. 中国思想学说史:先秦卷[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09-510.
[6] 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7]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61.
[8] 黎翔凤. 管子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9] 陈鼓应. 黄帝四经今注今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0] 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98:146.
[11] 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12]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1131.
[13] 许维遹. 吕氏春秋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2009:447.
[14] 丁原明.黄老学论纲[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1.
[15]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21.
[16] 刘爱敏.《淮南子》道论研究[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134.
[17] 吕有云.道教政治管理之道研究——道教黄老传统考察[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