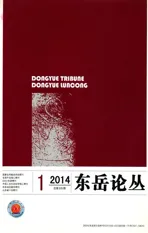论汪曾祺小说的叙事意义
2014-03-14徐文谋
徐文谋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当代小说中,乡土叙事始终是一片抢眼的风景。鲁迅、沈从文、废名、老舍、赵树理、孙犁等等,都以乡土为写作视域和文本对象。汪曾祺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主要以故乡江苏高邮、第二故乡西南联大等地的陈年旧事为题材,用经验化的叙事方式,重写故乡的自然意境,再现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众生相和生存状态。他这种看似平淡的乡土叙事,背后蕴藏着丰富深刻的叙事意义和价值指向,使那些田园牧歌式的乡土意境和平凡人物的生活场景,最终成为书写者文人情结与理想的投射,以及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底蕴和深厚的民族心理特质的诠释。
一、世俗化叙事:底层小人物的生存价值
世俗化叙事是相对于英雄叙事和宏大叙事而言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进程中,英雄叙事与宏大叙事一直占据着文学主流,控制着文学话语权。相比之下,以底层小人物生存状态和日常生活场景为对象和切入点的世俗化叙事,在文学领域经常被遮蔽和边缘化。这不仅淹没了生活意义的丰富性和历史真实的完整性,而且也悬置了审美的多样化和阅读的多种可能性,造成了文学叙事的单一和平淡。毫无疑问,世俗化叙事是对生活真实性和历史完整性的填充,是审美视域不可或缺的特殊地带,具有独立的叙事意义和审美价值。汪曾祺不只是80年代复出后坚守了这样一种世俗化叙事的写作路线,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红色文学、英雄文学等宏大叙事一统天下的历史语境中,他就自觉地选择了世俗化叙事。从四十年代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邂逅集》,到新时期以《受戒》、《大淖记事》复出,他将世俗化叙事策略发挥到了极致。他的小说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人物,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超人,没有改天换地的大事业和惊心动魄的曲折故事,而是从市井商贾、贩夫走卒、学徒工匠、文人雅士,到村姑樵夫、和尚尼姑、三姑六婆、野叟孩童等生于斯、长于斯的小人物。他们过着卑微琐碎、平凡简单的凡俗生活,日复一日、平淡无奇。对这些小人物世俗生活的原汁原味叙事,是汪曾祺的自觉追求:“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没有经历太多的波澜壮阔的生活,没有见过叱咤风云的人物,你叫我怎么写?我写作,强调真实,大都有过亲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写作。我只能写我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不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①
汪曾祺的这种叙事姿态,首先意味着对世俗生活价值的肯定,对小人物生活尊严的认同。在我们的道德判断与价值理念中,曾经被崇高、神圣、伟大、悲壮的情感所统摄。我们意念中的历史是伟人、英雄的历史,所推崇的生活是光芒四射、轰轰烈烈的成功生活,趋向的审美是宏大、时尚、脱俗的审美。我们的思维常被空洞、宏大的概念支配和占据,价值判断中充斥着大而不当、甚至扭曲拔高的公共标签,而历史的真谛、生活的真实存在、个体的尊严与价值反而被遮蔽和消解。汪曾祺小说的叙事意义就在于,还原了小人物生活的合理性、世俗生活的逻辑意义,呈现了边缘化群体的生存状态,透射出了被忽略、被排斥、被贬低的平凡、真实、亲切、温暖的光辉。在这里,普通人的凡俗生活状态与世界存在的真实性桥梁被打通,个体的生命意义与普世的人道主义价值得以链接,生命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得以重构。正如王安忆在解读自己的中篇小说《众生喧哗》时所说的:“社会中总有一些人,与大多数生活在统一格式里的所谓‘主流’不同。他们不具有巨大的历史功能,更不是时代的最强音,但都极具个性,正是这种个性化的东西,使他们具有一些含糊的美感,适合成为小说创作的题材。绝大多数进入美学视野的都是小人物,生活中有很多主流的东西在美学里都不存在。有些人生活得很边缘,但生活得很有诗意,反而是那些穿着笔挺的老板们,看上去就像一部机器。”②基于这样的叙事策略,他舍弃了人为的整合与刻意的塑造,避免了典型的聚焦与意义的放大,自觉地遵循着记忆中的乡土和人物原型,顺其自然地叙述故乡陈旧的风俗习尚,小人物琐碎的生活习性、奇技淫巧、饮食男女、喜怒哀乐、生老病死,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构成一幅人物与乡土自然浑然一体的原始生存状态。如《老鲁》中的校役老鲁、《落魄》中开饭馆的扬州人、《鸡鸭名家》中的大师傅余老五和放鸭人陆长庚、《异秉》中的做“熏烧”(卤味)的王二、《受戒》中的恋人小英子和明海、《大淖记事》中的巧云与小锡匠十一子、《徙》中的国文教师高北溟、《八千岁》中的粮店老板八千岁、《故里三陈》各有专长的陈小手、陈四和陈泥鳅、《岁寒三友》中的陶虎臣、《鉴赏家》中的季匋民和叶三、《星期天》中的教师赫连都和校长赵宗俊等等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他们温良、平和、淡泊,生活得朴实、从容、知足,人与人融洽、温馨、和谐。正是这种原生态的人性与生活叙述,不作过度的人物渲染和解读,不作过度的意义附加和拔高,只呈现自然生活的真实,彰显了生存的本质,填补了宏大生活的“空阙”,为阅读者提供了世俗化叙事的审美领地,“显现出别样的趣味”③。
从更深层次看,这种叙事路线的意义,还在于世俗生活背后蕴含的生命价值的张扬、人本意识的凸显,在于作者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寄托。这使得汪曾祺的世俗化叙事方式 避开了粗鄙化、庸俗化的陷阱,避免滑入纯物质、纯感官、纯欲望的琐碎生活泥潭。这些小人物的地位卑微、境遇困苦,但他们并不自惭形秽、怨天尤人,而是自信、乐观、顽强。他们的生活舞台狭小,生活平淡无奇、波澜不惊,但不带一点灰色、阴霾、低沉,而是在平凡中透着温馨,世俗中闪烁着诗意。他们男欢女爱、生儿育女,但没有丝毫的苟且、猥亵与肉欲,而是充盈着执着、忠诚、美好的人性元素。《受戒》中的小英子和明海、《大淖记事》中的巧云与十一子,莫不是如此。如《受戒》里,和尚可以不做功课,可以自由自在、买地种田、放债赌博、娶妻生子、相好私奔,完全打破了僧俗的界限,过着有滋有味的世俗日子,“充满了世俗生活的欢愉自由和诗意”④。正如作者自述,“我写《受戒》,主要想说人是不能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的解放。”⑤与此同时,汪曾祺小说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他很注意发掘和叙述小人物身上特殊的天赋技艺,各种的“奇技淫巧”。如《异秉》中的王二做得一手好“熏烧”(卤味),靠着他的精明、诚实、勤奋,最后在那条街上发达起来;《徙》中的高北溟不太合群,却颇有国文功底,做一名很好的国文老师;《八千岁》中的八千岁经营粮店精明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故里三陈》中的陈小手接生婴儿那是绝活;《兽医》中外号姚六针的姚有多医术了得;《星期天》中的教师赫连都舞技高超,以及形形色色的教授、锡匠、马贩子、戏子、师爷、团练等,在某个方面都有两下子。他们为不起眼的生计,靠一技之长糊口,而且能在其中发现乐趣,找到精神的寄托,于自我满足中实现生命价值。有人评论说:“他总喜欢选择有一技在身的匠人或艺人,他们尽管清寒,一旦沉浸于自己的技艺,就有可能摆脱生命的粗糙和卑微,显出那隐藏的本来的高贵。即使一般贫民,汪曾祺也乐意写出他们的普通谋生方式抵达的神乎其技乃技进于道的境界。”⑥如果我们把这些与汪曾祺整体的叙事策略联系起来,不难发现,这些小人物身上闪烁着的创造性,正是他们不受压抑的自然天性的流露,是人的内在生命力和本能创造力的迸发,是作者朴素人道主义情怀的流露。因此,汪曾祺撇开宏大叙事,重构了世俗化叙事的意义,那些小人物面对琐碎、重复、艰难、粗糙的底层生活,表现出来的从容、乐趣、温馨,让我们体味、发现、找回那生活的真实感、生命的自然美、生存的信念和精神的寄托。在这物欲横流的当下,在这时尚吞噬的时空,在这灵魂麻木的生活,世俗化叙事给我们提供的人本精神的回归、主体意识的张扬、原始生命的再出发、生活信念的召唤,不正是文学的终极意义所在吗?对此,叶李在《在文学叙事中重寻日常生活的尊严》中有一段十分中肯的阐述:“汪曾祺作品中那种在少年友情、邻里交往、朋友扶携的日常点滴中流泻诗意的书写,使日常生活散发出温润的诗性光辉,恬淡写意的笔调飞升出生活世界里灵魂和精神之美。日常生活这种可亲、可爱、可感的熨帖、温暖正为‘人的存在’提供了支点的意义,而他的尊严与价值也由此彰显。汪曾祺选择中国式的‘抒情现实主义’,用‘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这种以日常生活叙事提供‘审美栖居’的朴素的写作观不应该被遗忘,仍旧具有值得珍视的价值。”⑦
二、乡土叙事:现代书写者的文人情结
倘若要继续深入追寻汪曾祺小说的叙事意义,我们就必须探究为什么他书写的都是故乡的陈年旧事,为什么都是记忆中的乡土存在?从乡土记忆这一叙事原点出发,我们就能窥视到他内在的叙事动力和潜藏的叙事企图。
每位作家内心都有一片恒久不变的书写圣地,这往往是他们所经历的或熟悉的人物、生活、地域、文化。故乡作为“作家童年经验中的重要部分,能充分满足现代作家精神返乡的需要”⑧,因而在许多作家笔下成为其主要的叙事题材。他们用这种经验式的生活叙事,来抵抗异化的现实、麻木的生活、混沌的世界,从而坚守美好的记忆和感觉,照亮写作的灵魂。像汪曾祺这样的一批作家,从小都是在乡下长大,尔后迁徙到城里生活,经验中的乡土对他们具有擦拭不掉的意义和价值。高邮之于汪曾祺,正如绍兴之于鲁迅、湘西之于沈从文、黄梅之于废名、白洋淀之于孙犁、呼兰河镇之于萧红、商州之于贾平凹、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乡土承载着作者的情感记忆和灵魂密码,是其写作的出发点和根据地。他们身在城市,却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他们对城市的消费文化、物质泛滥、人性异化存有本能的排斥,他们的情感已定格在记忆中的乡村自然社会。那个温馨宁静、淳朴自然的田园世界,永远是作家心灵的避风港,是他们的写作之根。正如现代评论家刘西渭发出的感慨:“我是乡下的孩子,然而七错八错,不知怎地,却呼吸这都市的烟气。身子落在柏油马路上,眼睛触着光怪陆离的现代,我这沾满了黑星星的心,每当夜阑人静,不由得向往绿的草,绿的河,绿的树和绿的茅舍。”
这些作家的伤痛与寂寞正源于此。当乡村自然宗法社会在社会动荡中遭到摧残,或在城市化的冲击下被无情瓦解时,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灵魂冲击。鲁迅在小说《故乡》中那简短而有穿透力的几句叙述,正是今古文人这种伤感、失落心态的生动写照:“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点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精神家园的抹平,使他们投向乡土记忆,在乡土的复写中找回心理的平衡。汪曾祺在《菰蒲深处·自序》中就坦言:“我的小说多写故人往事,所反映的是一个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时代。”艺术的领域从来都是理想化的领域,文人天生都是梦想家和乌托邦主义者。他们对于宁静自然的乡土社会的留恋,与对现代物质文明社会的本能拒绝、排斥,构成这类群体写作心态的二元结构冲突。作家的这种特殊精神现象,就是乡土情结。现实困境下的灰暗无序与经验记忆中的乡村美景对抗、排斥,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宗法制文明不可逆转的替换、征服,带给作家的是灼痛的精神焦虑。他们只有退回记忆的角落,抚慰个体的伤痛,抵御现代文明的入侵。这绝不是汪曾祺一位作者的倾向,而是中国几千年来文人情怀的再现。我国自古以来,农村自然经济占据了绝对的统治时间,也生成了中国文人崇尚自然、留恋宁静的文人士大夫情绪。当他们在社会现实面前碰壁,理想抱负不得伸展,对社会的疾苦与黑暗无能为力时,乡土记忆与咏唱,陶渊明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然回归,就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和抒怀的载体。难怪有人说,汪曾祺是中国士大夫文化培养起来的最后一位作家!
因此,我们就不难解读汪曾祺的小说世界里看到的那种美丽与伤感交织的风景画面。一方面,作家书写的是记忆中美化和放大了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图画:美丽的山水风景、温馨和谐的生活环境、舒缓平淡的生活节奏、恬淡自然的人性人情、纯洁坚定的男欢女爱……我们随意撷取一个画面:《受戒》中描写小英子家的环境:
“小英子的家像一个小岛,三面都是河,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到荸荠庵。独门独户,岛上只有这一家。岛上有六棵大桑树,夏天都结大桑椹,三棵结白的,三棵结紫的;一个菜园子,瓜豆蔬菜,四时不缺。院墙下半截是砖砌的,上半截是泥夯的。大门是桐油油过的,帖着一幅万年红的春联:
向阳门第春常在
积善人家庆有余
门里是一个很宽的院子。院子里一边是牛屋、碓棚;一边是猪圈、鸡窼,还有关鸭子的栅栏。露天地放着一具石磨。正北面是住房,也是砖基土筑,上面盖的一半是瓦,一半是草。房子翻修了才三年,木料还露着白茬。正中央是堂屋,家神菩萨的画像上贴的金还没有发黑。两边是卧房。两扇窗上各嵌了一块一尺见方的玻璃,明亮亮的,——这在乡下是不多见的。房檐下一边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棵栀子花,都齐房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栀子花香得冲鼻子。顺风的时候,在荸荠庵都闻得见。”
这就是一幅中国传统简洁的乡村水墨画,是一幅世外桃源的风景。汪曾祺走了一条诗化和散文化的修辞路线,不重情节的完整性,不刻意追求意义的系统性,他擅长呈现小巧单纯的风景、零星片段的细节、轻灵优美的意境,抵达诗化的审美境界。他在《泰山片石》中说过,“我是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写高达穷奇之山,殆矣。”还说:“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抒情诗成分”,“散文化的抒情诗”⑨,“我把作画的手法溶进了小说。”⑩
另一方面,淡淡的伤感、哀愁,甚至是悲戚的元素同时隐藏在这美丽冲淡的画面背后。这里有自然乡村社会生活本身的贫穷、困苦、不平等的感慨,就像《大淖记事》中的巧云,她被水上保安队的刘号长强奸后的内心凄苦与忧伤;像《故里三陈》中的陈小手,在为军阀团长难产的太太接生后,却被团长一枪打死,就因为他太太被陈小手接触过了,那种无言的悲哀。但更多的是作者对逝去或者正在逝去的乡土生活的无奈与伤感。在《大淖记事》结尾:
“十一子的伤会好么?
会。
当然会。”
这透射出沈从文式的伤感:“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边城》)也有鲁迅小说《故乡》里的凄凉,废名小说《桥》里无可奈何的孤寂和《竹林的故事》里弥漫的哀愁。虽然他们各自的伤感并不同质,但是矛盾痛苦的心境是趋同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终将瓦解,乡土美梦总会醒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文人心情难以排解,由此也构筑了乡土书写中美丽画卷与淡淡哀愁交织的特殊意境,从而指向了含蓄深长的审美意味。
三、文化叙事: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望与回归
作为一个身处现代,骨子里却被中国式文人士大夫气所占据的作家,其小说叙事必然潜藏着一定的文化密码,从而获得深层的叙事意味。尽管这种文化意味并非刻意的凸显,迥异于曾受热捧的文化寻根,也非故弄玄虚或故作深沉,绝没有直白的阐述、寓意的提示,而是潜伏在世俗生活叙事和人物生存状态之下。他写作是“要贴到人物来写。”⑪书写者与作品人物的零距离,使汪曾祺身上的传统文化气息,潜意识地渗透到他选择的素材、人物和细节、语言中去,小说和人物自然打上作者的文化印痕。从终极意义上说,这种文化意味是一方水土、一方人传承下来的地域习俗、生活方式与心理惯性,是几千年文明祖祖辈辈积淀下来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和传统文化原型。它沉积于世俗的现实生活之中,附着在具体的人群身上,鲜活可见,绝不抽象。对此,汪曾祺说过:“小说要有浓郁的民族色彩,不在民族文化里腌一腌、酱一酱,是不成的,但是不一定非得追寻得那么远——寻找古文化,是考古学家的事,不是作家的事——我们在小说里要表现的文化,首先是现在的,活着的;其次是昨天的,消逝不久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出,想得透。”⑫正是这“腌”与“酱”,使得我们几千年来的民族传统文化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使得汪曾祺的小说虽然叙述的是某一地、某一群、某一类的小人物生存状态,但激活的不仅仅是美的享受,还有灵魂的触动和文化的启示。
汪曾祺小说所承载的文化元素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形态。他自己说过,“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两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在昆明教中学时案头常放的一本书是《庄子集解》。但是我对庄子感极大兴趣的,主要是其文章,至于他的思想,我到现在还不甚了解。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⑬其文本指向的儒家文化信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和谐。中庸、和谐是儒家思想重要成分,在汪曾祺的小说文本里占据了中心位置。首先,人与自然是和谐的。汪曾祺的小说像是一幅幅风俗画,人物游走、生活在故乡的山水之中,与那寂静寥廓的湖面、幽深曲折的芦苇荡、稀疏孤独的小岛、古韵犹存的荸荠庵、熙熙攘攘的码头街市、眼花缭乱的铺面水乳交融、物我合一,构成了人与自然、与环境和谐均衡的氛围。正如有人解读的那样:“作者极力在小人物的生活方式和风俗描写中发掘一种自然和谐之美,追求一种如陶渊明田园诗那样真醇的诗意。”⑭其次,人与人、与社会是和谐的。汪曾祺小说里的人物天性自然、淳朴、乐观,有的古道热肠、侠肝义胆,他们相处得温馨、和谐。《故里三陈》中的陈泥鳅,好义也好利,好酒好赌,水性也好,他救活人不讨价,但“在死人身上,他却是不少捞钱的”。一次,他捞一具女尸,敲人十块大洋,拿到钱,“大家以为他又是进赌场,进酒店了。没有,他径直地走进陈五奶奶家里”,因为陈五奶奶独自带着的小孙子病得四肢抽搐而无钱就医,陈泥鳅把十块大洋给了陈奶奶,抱着孩子去药房。《大淖记事》中的巧云被刘号子玷污了,乡邻们并没有耻笑,只骂了(刘号子)一句:“这个该死的!”反而在十一子被打后,“他们把平时在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中不常表现的热情和好心都拿出来了。他们觉得十一子和巧云做的事都很应该,很对。”作者的人道主义叙事姿态,对小人物人性的真、善、美,给予自然的描述与渲染,再现出农村自然宗法制温情脉脉的社会关系,传承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仁义、道德、秩序、和谐等的精髓。再次,人与自我是和谐的。自我的和谐突出表现在,面对生活的平淡艰辛与命运的多舛难料,这些小人物能以平常心坦然处之。他们自给自足、清贫平淡,甚至窘困坎坷,但从不怨天尤人,更没有满腹牢骚,甚至连一丝的怨怒都没有。即便是遇到大悲大喜,也有足够的忍耐力和生命元气,来消弭外部世界所造成的冲击。他们依靠顽强、豁达、平淡的秉性与心态,消解生活的困窘、失意、挫折,达到内心世界的平衡。他们顺应自然与命运,日子如淡淡的溪水般流淌,剔除了浮躁、火气,臻于自我人格的和谐完美。
另一个是韧性。儒家倡导积极入世、忧患济民的进取精神,自强不息、包容坚韧的人生姿态,舍生取义、威武不屈的生死意识,怨而不怒、淡泊中和的审美思想。我们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文明历程,儒家这些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融入血液,积淀于民族心理之中,成为超越个体的民族集体无意识。这在汪曾祺的小说中,集中体现为一个“韧”字。他在谈到林斤澜“矮凳桥系列小说”表现温州人的“皮实”时说过:“能够度过困苦的、卑微的生活,这还不算;能于困苦卑微的生活觉得快乐,在没有意思的生活中觉出生活的意思,这才是真正的‘皮实’,这才是生命的韧性。……‘皮实’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普遍的品德。林斤澜对我们的民族是肯定的,有信心的。”“这与其说是讨论林斤澜,不如说是汪曾祺夫子自道。我们从汪曾祺之后的江苏作家群优秀作品中,看到的也是这种‘皮实’,这种‘生命的韧性’。”⑮以《大淖记事》为例,巧云的妈跟别人跑了,巧云和她爸爸并没有痛不欲生、诅咒谩骂,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他们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在小锡匠十一子和巧云身上同样有着可贵的品性——坚韧与执着。十一子为了和巧云相爱,被刘号长的人打得只剩一口气,也不松口,坚决不告饶。特别是巧云,她被强奸后,并没有拼死拼活、大哭大闹。小说写道:
“巧云破了身子,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只是为什么是这个人?真不该是这个人!怎么办?拿菜刀杀了他?放火烧了炼阳观?不行!她还有个残废的爹。她怔怔地坐在床上,心里乱糟糟的。她想起来该烧早饭了。她还得结网,织席,还得上街。她想起小时候上人家看新娘子,新娘子穿了一双粉红的缎子花鞋。她想起她的远在天边的妈。她不记得妈的样子,只记得妈用一个筷子头蘸了胭脂给她点了一点眉心红。她拿起镜子照照,她好像第一次看清楚自己的模样。她想起十一子给她吮手指上的血,这血一定是咸的。她觉得对不起十一子,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她非常失悔:没有把自己给了十一子!”
巧云遭受了如此的耻辱,她没有痛不欲生,而是顽强地活着。在和十一子一起生活后,她从此要挣钱养活残废的爹、受重伤的十一子和自己三个人。但她并不怕,勇敢地挑起这份重担,显示出一个普通女性的坚强。面对巨大的苦难和痛楚,能保持坚强而平静的心态,这种生存的“皮实”与韧性,在巧云和十一子等众多的小人物身上得到形象的诠释。
依照现代批评者杰弗雷·H·哈特曼的观念,“阅读本身便成为这样的工作:我们为理解作为生命形式的阅读所包含的东西而阅读,而不是为解答强硬塞入似是而非的观念的东西而阅读。”⑯也就是说,文本一旦生成,意义就并非只有作者决定,读者的理解也成为文本的再生产。因此,阅读汪曾祺的乡土小说,不仅会感知已经或即将逝去的乡土生活和人物轨迹这些外在形态与表象,而且“作为生命形式的阅读”,会穿透文本,扑捉到蕴含的深层精神内涵和文化寓意。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前面把汪曾祺文本的叙事意义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世俗化叙事—表层意义、乡土叙事—中层意义、文化叙事—深层意义,这就是本文的终极含义。
[注释]
①汪曾祺:《七十书怀》,《汪曾祺说·我的世界》,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②王安忆:《在众声喧哗的时代体味小人物生活的诗意》,《光明日报》第13版,2013年2月26日。
③傅元峰:《中国新文学史论纲》(下),《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④董建雄:《论<猎人笔记>对汪曾祺故乡系列小说创作的影响》,《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5期。
⑤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八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页。
⑥郜元宝:《汪曾祺的两个年代及其他》,《中国作家》,2009年第7期。
⑦叶李:《在文学叙事中重寻日常生活的尊严》,《光明日报》第14版,2012年11月20日。
⑧翟瑞青:《童年经验和现代作家的故乡书写》,《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⑨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八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7、79页。
⑩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六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⑪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第2版,第310页。
⑫汪曾祺:《吃食和文学(咸菜和文化》,《汪曾祺经典散文选》,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页。
⑬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第2版,第316页。
⑭李新平:《论汪曾祺早期小说的思想内涵与叙事风格》,《中州学刊》,2009年第3期。
⑮郜元宝:《汪曾祺的两个年代及其他》,《中国作家》,2009年第7期。
⑯[英]拉曼·塞尔登编,刘象愚等译,《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2版,第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