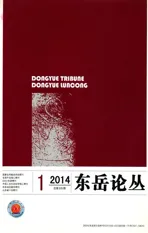正确理解和区分马克思劳动的对象化与劳动的异化
2014-03-14周书俊
周书俊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234)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隐藏了关于人的解放的最高诉求。马克思之所以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对象化看作是劳动的异化,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切生产,一切劳动的对象化所导致的对象性存在是在工人之外,也就是说是与工人相对立的,在形式上这些由劳动创造的产品是劳动的结晶,理应属于劳动者自身所有,而在本质上则是与劳动者自身相脱离,并成为劳动的对立面。因此,劳动的对象化实际就是劳动的异化,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商品越多,工人所获得的东西就越少,他就越贫困,如此等等。马克思正是通过异化劳动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因此“异化概念成为他隐含的人本主义道德观的核心范畴。”①而资产阶级学者往往把马克思看作是一个“非道德主义者”,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看到马克思所要实现的人的解放才是人类真正的正义事业。
一
马克思所建构的是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这个理论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建立在政治解放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社会,政治解放还不是马克思的最终目标。马克思说:“政治解放使社会成员从国家的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这确保了对他们政治权利的承认。然而,仅仅有政治解放并不能使市民社会的成员从市民社会那种分离的、孤立的、个人主义的和自私自利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实现以各种方式提出的‘人权’并不能充分地保证达到一个真正人的或者善的社会。于是,马克思提出了人类解放,也就是‘市民社会的解放’。但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将抽象的、道德的市民归结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个人。”②在这里,马克思认为,所谓由于政治解放而实现了的“人权”并不能使社会达到真正的“善”,只有将人从分离的、孤立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才能最终摆脱抽象的道德对人的束缚,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并以此区别于黑格尔的抽象精神。黑格尔虽然洞悉到异化对人的自我存在的压制,但是面对异化黑格尔所采取的解决方式不是通过现实的运动,而是通过“自我意识”来完成的,将现实中的异化消融在“绝对精神”之中。对于黑格尔来说,“作为意识的精神其目的就是要使得它的这个现象和它的本质同一”。“意识在趋向于它的真实存在的过程中”将“摆脱”它的异化或外化的形式,它“将要达到一个地点……在这地点上,现象即是本质”③。而在马克思看来,情况正好相反,如果不从实际中消除产生异化的根源,那么就不可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④
我们说,对象化是人所特有的能动性的表现,人正是通过劳动使劳动对象发生塑形,形成了人化了的对象性存在,从根本上说它应当体现人的本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会充分享受到劳动的乐趣。不仅如此,对象性存在还为人类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和文化的基础,是文明社会发展的象征。“根据马克思所采用的黑格尔式术语,人类将自身的自然力量和能力对象化,创造出一个充满物质和文化客体的对象性世界。在这些物质和知识产品的历史发展中,人类创造出他们自身,创造出他们自身的历史的人的本质。尽管历史上的所有(正常)人都共有某种基本的或本质的人性,或毋宁说,一套自然力量和能力,但人们的个性和特性是依靠和通过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和文明中物质和文化对象体系的生产而得以创造的。”⑤我们必须清楚在对象化的过程中,作为单独的个人是根本没有力量形成对象化的,即便有这个力量也根本无法形成对象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对象化的过程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个人的能动性的发挥绝不是由孤立的个人来创造的,它必须依靠人类所创造的对象性存在的体系(全部文明的成果),否则,个体不仅不能实现对象化,就连个体自身也根本无法存在。
然而,当劳动成果即对象性存在不再属于劳动者自身时,这种对象性存在就游离于劳动者之外,并且不再体现劳动者的本质。“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⑥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而劳动只不过是满足他“本质”以外的需要。或者说,他不把劳动看作他本身的东西,而是把它看作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劳动已经同他本身分裂开来。劳动本身不仅是肉体的强制,也有精神的强制,一旦这种强制停止,人们就会逃避劳动。异化劳动使人成为一个单纯的“自然人”,成为一个无“人性的人”。它表明人已经失去了作为人的“能动”性,完全服从于外在的由劳动创造的对象性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不是满足劳动的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⑦不仅如此,在这里,对象化的全部过程也不再具有道德的属性。因为这种对象性的活动不再是活动本身的需要,而是由于自身的肉体的需要,是人为了苟且生存的需要,是一种满足于如同动物的需要一样的需要,也就是说这种活动本身违背了活动者的意愿,是被迫的、无奈的,是不道德的。
在这里,人的自身的存在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由这个不情愿的劳动者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对象性存在,如果人们一旦离开了这个对象性存在,人自身的存在便成了问题,也就是说,人的自身存在一刻也不能离开对象性存在,如果离开了这个外在于自身的对象性存在,人也就是“无”。因此,“马克思将‘自然科学的对象和艺术的对象“看作”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⑧。“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⑨也就是说,人一方面是自然界的产物,它无法离开自然界;另一方面,人又不完全是自然的,它同时还是“人的”。然而,如果没有了人化的对象性存在,没有人化的自然界,人的感觉也就失去了作为人的感觉,而人的存在也就失去了作为人的存在。而从本质上来说,人决不等同于自然。因为,就它的本质而言,它应当成为“人的”存在,即人的对象化的性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
事实上,如前所述劳动者在创造对象性存在时其本质在不断地丧失。一是它的生命随着历史的进程或随着创造物在时间中消失;二是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人们所关注的不是人本身而是它的对象性存在这个本来是人的本质的表现而事实上却属于另外一个对象,所以,真实的人的本质只是变成了人的外在的一种形式。这就如同黑格尔把人的本质看作只是一种抽象物一样。“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因此,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自我意识的异化没有被看作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的表现,即在知识和思维中反映出来的各种异化的表现。”⑩这样一来,对于黑格尔来说,自我意识的异化就本质上说也是一种对象化,也是异化的表现,尽管它是人的本质的表现。然而事实上,这种“自我意识”的对象化的异化只不过是现实中异化在意识中的反映而已,进而言之,单纯地克服这种自我意识的异化只不过是从形式上克服了异化,在自我意识中获得了统一,因此,它还不能真正复归于人的本质,还必须进行现实的实际行动,才能使人的本质回复到人的本质中去。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⑪但他没有看到造成人的本质异化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这种自我意识的辩证形式上的异化,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
二
如果黑格尔的异化所强调的是一种辩证的环节,那么在马克思这里,异化概念则过渡到一种道德的评价。异化使人的对象化成为人自身外化的手段,也就是说人的能动性成为人的受动的原因,人的力量成为人的无力的根据。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佩弗所说:“马克思声言,人通过他们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将自身的力量和能力对象化(在vergegenständlichung的意义是)于物质和文化客体上。在劳动分工和私有财产的现代体系中,大部分人性——在entäusserung(外化)的意义上——被剥夺了,或者与人所创造的物质和文化对象相异化。换句话说,这些对象正是在一个人将自己的财产出售给他人,于是在与其财产相异化的意义上与普遍的、劳动的人相异化:他失去了对它的控制。最后,这一社会体系——正如马克思后期所考察的所有以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对立为基础的社会体系一样——使人异化于(在entfremdungr的意义上)生产过程和产品以及他人和人自身(即人自身的本质),因为感到与这些对象相分离、相疏远,并且把它们看作是一种人们无法控制的敌对的力量。”如此一来,异化就不只是如黑格尔所认作那样是单纯的辩证环节,而是一个道德的评价问题,即人的对象化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种活动本身是“善”的还是“恶”的?它满足了那些人的需要?
有人借口马克思所谓的阶级“偏见”,就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典型的非道德主义者Ⅰ伍德和米勒认为道德应当是中立的,由于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里道德是从属于阶级利益的,因此,伍德和米勒据此便认为马克思是“非道德主义者”。。伍德甚至认为,马克思根本没有道德基础⑬。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规范性观点是“非道德的”而不是“道德的”,这是因为“马克思将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建立在这一主张基础上:资本主义妨碍了很多非道德的善,如自我实现、安全、身体健康、舒适、共同体、自由。”⑭伍德从功利主义出发,其所谓道德的善在判断标准上就完全不同于“非道德”的善,甚至认为这与“非道德”的善完全无关。如果真的如此的话,那么“他必须承认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就完全符合‘道德律’而言同康德主义的道德判断一样易于表述。这正是关于‘义务论的’和‘效果论的’或‘目的论的’道德理论之间的传统区分的失误之所在。”“在功利主义者看来,最高的道德律是功利的最大化,因此,遵从这一点就是按照并遵守道德律而行动。”⑮我不赞同伍德的观点,马克思不是反对道德本身,而是资本主义这个不道德的或者说阻碍人们道德地生活的社会是必然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归于消亡。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断定马克思是对道德本身的批判,因而就认为马克思是非道德主义。事实上,马克思所批判的恰恰不是道德本身,而是附着在道德身上的用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恶”的东西。
对于马克思来说,对象化的过程如果仅仅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需要,或者说一些人的享受是建立在对大多数人的剥削与压迫之上,这种对象化的活动就是非道德的和非正义的。“然而,在迄今所有存在过的社会里,这些物质和文化对象在某种意义上都与绝大多数人相分离,处于他们的利用和控制范围之外。于是,它们就被绝大多数人理解为‘异化的’和‘敌对的’。所以,这绝大多数人不仅与物质生产和智力生产的对象和产品相异化,而且在马克思看来,他们还与生产过程、他人、自然界和他们自身(即类生活或他们的‘类存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只有当绝大多数人重新获得对这些对象和对他们自身生活的控制时,这些异化才会被扬弃。这只有当他们成为真正社会性的存在时才有可能,而且后者只能通过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得以可能。”⑯
在马克思看来,对异化的消除所带来的人的解放有三个维度:其一,自我存在的本体论内涵——自由;其二,自我发展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共同体;其三,真正实现了自我发展即每个个体的自由、充分、全面的发展。人的解放三个维度不仅是道德的,而且也是正义的。马克思的阶级利益并不排除他的道德追求,相反正是由于一种关于人的解放的道德诉求,才会形成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三个维度。
在这里,马克思“人的”这一词所表示的是能允许或促进人的本质的或“真正的人的”及自由的、有意识的创造活动的能力实现的东西。而且,正是这两种能力或力量构成了超历史的人性,或者说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将人与其他低等动物区分开来的人的“类存在”。“类存在”无论是在对象化过程中,还是异化中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即人的解放决不可能是单个人的解放,而是真正的人的解放——类解放。也就是说,人的存在始终是一种“类存在物”。“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⑰从价值取向上来看,资本主义理论认为只有强迫下的劳动才可以发挥人的能力,当其完全处于自由的时候,人的能力反而会得不到更好地发挥;而“在马克思看来,当人的本质的能力受到妨碍或阻挠时,当那些为了人类的完整、健康、幸福所必须实现的潜能无法实现时,人就异化了。私有财产和利益的体系使人异化了,因为它阻碍了人的两种本质能力的实现。”⑱
马克思在此回答了为什么要获得解放,而这种解放必须是这种解放,即人的解放。那么,人的解放的任务由谁来完成呢?马克思同样给予了回答:只有依靠他自身——无产阶级。“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⑲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是‘不合乎人性的’或者说是一个‘违反人性的’社会形式,因为它无法使其社会成员受到作为人所应该受到的待遇。它无法使人们实现人性中积极的方面:社会性和自由的、有意识的创造活动”⑳。事实上,要真正做到人的解放,单从对异化的消除上仍然是片面的,因为所有人们的价值期望,如果不从现实中获得所期望实现的客观条件的话,再美好的期望也只能是空想。我们说,不受外在(异己)力量控制而由自己完全支配的活动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人性的社会的目标是(或者说应该是)自主活动,即不受外在(异己)力量控制而由自己支配的活动。实现自主活动意味着个人不再‘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也不再‘屈从于分工’,也不再束缚于种种可能的‘自然局限性’,即并非由个人有意识地计划或决定的局限性,并且只有当它们屈从于有意识的计划和决定时才能被根除。”㉑所以说,共产主义联合体中所联合的个人,必须能够自由地、合作地控制社会生产,而生产资料将“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最后,“才能总和的发挥”和实现“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
所以说,人的解放事实上是类的解放,是集体主义的发挥而不是个人主义的扩张。“没有集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㉒当然,我们还要区分虚幻的集体与真实的集体。当异化盛行之时,那种被支配阶级的集体尽管是集体,但却是虚幻的集体,抽象的集体(宰制的羔羊)Ⅰ如同尼采的“畜群”。这种虚幻的集体所掩盖的恰恰就是个人的专制或对个人的盲目崇拜。。只有解放了的集体,而这种解放了集体决不只是宗教解放(思想解放),或者政治解放(获得了政权),而是真正的人的解放,这样的集体才是真实的集体。
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不仅拓展了使人获取现实解放的路径,同时它还具有道德评价的功能,而这些都源于马克思的对象性。“异化概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如同它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一样具有全部的评价性内涵。……整个产品世界是‘对象化的劳动’,即对象化于物质产品之中的劳动结果。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产品世界与生产者相异化,因为他们对生产产品没有控制能力。雇佣劳动是异化劳动,因为劳动者无法控制这种劳动。此外,资本是‘异化了的物化劳动’,因为价值(或剩余价值)与直接生产者相异化并(在合法的意义上)归属于资产阶级。尽管如此——这是对理解马克思来说最为重要的一点——物化劳动,在任何社会条件下来说,并不一定是异化劳动。物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同一性,即物化劳动产生了异化劳动这一事实,‘决不是生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㉓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对象化、物化只是当对象性存在不再归属于劳动本身时,对象化才成为异化。所以说,在这里“关键不在于对象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归巨大的对象[化]的权力所有,这种对象[化]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㉔如此一来,“个人从属于共同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㉕所以说,异化的状况违背了马克思关于自由“个人自我决定目的”的原则。
三
对象化所导致的对象性存在构成了人化自然的全部,在这个庞大的对象性存在面前,工人显得苍白无力,成为了由自我创造的产品世界的奴隶,自我的能动性只是作为手段。但是,这个强大的产品世界虽然外化于人,但它在未来的社会却仍然具有可以保留下来的肯定内容,这个肯定内容为人的解放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奴役的背后并不总是奴役,而是觉醒和反抗,是异化的“异化”——即异化造成了导致这种异化的异化,也就是说强大的产品世界造成了一个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这种对象化劳动,这些存在于劳动能力之外的劳动能力的生存条件和这些物质条件在劳动能力之外的独立存在,表现为劳动能力本身的产品,表现为它自身创造出来的东西,既表现为劳动能力本身的客观化,又表现为它自身被客观化为一种不仅不以它本身为转移,而且是统治它,即通过它自身的活动来统治它的权力。”㉖一旦这种统治劳动的并使劳动能力自身客观化的对象性存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甚至连资产阶级也无法控制这个产品世界时,这个强大的用来统治的权力,这个貌似公平正义的剥削制度就会被炸毁。
马克思从分析主体的对象化以及异化入手,分析了资本主义内在的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暂时性,得出了共产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结论。在马克思看来,“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被设定为社会劳动。”㉗这种社会劳动不应由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结果必然导致劳动的异化,而“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这些也是亚当·斯密想不到的。……这样一些劳动……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㉘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资本的有机构成也在不断提高,而工人的存在却日益显得微不足道,而这恰恰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因为资本就是不断获取剩余价值的价值,一旦工人的劳动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不断减少并趋向于零时,剩余价值也趋向于零,资本的存在就成为多余的了。不仅如此,整个庞大的产品世界的维持仍然需要消耗大量的劳动,否则它便会随着时间而被自然化[自然损耗]或被精神化[精神损耗](为无)。所以说,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就如同自然界的其他规律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到了那时,善才会真正实现,而人才会获得真正的解放。
人们追求着自由、平等和正义,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则成为强迫的劳动,平等则变成契约的签订,所谓正义却是建立在非正义的基础之上。一切都依靠对象性存在这个外在的东西为依据,它似乎无所不能,它可以使收买变成援助,也可以把侵略当作正义,它还可以使不平等成为公正,使奴役成为自由。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谓的自由、平等、正义以及道德从本质上来说是虚假的、伪善的、抽象的、形式上的,它根本无法真正实现个性的自由发展,也不可能实现真正平等和正义。此外,我们必须看到,单纯地具有强大的产品世界仍然无法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有大量对立的社会统一形式,这些形式的对立性质决不是通过平静的形态变化就能炸毁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藏地存在着无产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㉙也就是说,资本的灭亡是必然的,但需要的是条件,这个条件却是综合的,从根本上是资本的强大和资本内部的矛盾运动达到一定程度后,无产阶级才能够能动地将其摧毁。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㉚“另一个很有可能的必要条件是,构成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发展出一种社会意识,这种意识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致他们坚持每个人的基本需求都要得到满足,而对他们自己来说,则只要拥有过上一种有品质的生活所需要具备的东西就可以了。”㉛
在马克思看来,财富属于自我本质性的东西,而不是外在的对象性存在。外在的对象性存在只是自我本质财富获得的条件,真正的属于自我本质的财富是自由支配的时间。“真正的财富是所有个人的生产力都获得发展。衡量财富的标准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自由支配的时间。”㉜“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财富(现实的财富)不是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支配,而是除了耗费在直接生产上面的时间以外,每一个个人和整个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㉝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使得整个资本的有机构成得以大大提高,这样一来,社会必要劳动便大大降低,而社会财富即世界产品极大丰富。人们自由支配的时间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会大大增长。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便宣告终结。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费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㉞因此,我们说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已经开始创造出了这个必然王国,消费最小原则最有可能地留有自由时间。由此可以预见,到了共产主义,真正的自由王国才能真正实现。“自由(作为自我决定)这一价值也被实现了,因为联合起来的无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化的)个人是自我决定的,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他又是自由的。而且,由于他们的‘社会化’,工人将自发地从事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劳动。既然不再有强制或强迫,那么工人——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在这一意义上也是自由的。不用说,人们也不会再被国家强制去做什么了,因为国家已经不存在了。”㉟到了那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㊱由此我们看到,马克思不仅是一个道德主义者,而且是一个关于人的解放的坚定支持者。在马克思人的解放的社会里,每个个体才能够真正实现“自我决定目的”积极的自由,自我的对象化完全复归于自身。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尽管马克思当然也支持有时被称为‘消极自由’的东西(即一个人不受其他个体干涉其行为的自由),然而,丝毫弄不清楚他是否对于如何保护这一意义上的自由作出了充分的说明,他也许过高估计了市场力量的消除将会造福人类的程度,也过高估计了自我实现对于扬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差别的依赖程度。”㊲“消极自由”是否需要保护,该如何加以保护,也就是说,在人类由此岸向彼岸发展的过程中即还没有取得人的解放的时候,如何获得某种意义上的“自由”并没有作出充分的说明。况且它可能会导致为了实现人的解放就可以扼杀个体的自由,有时会成为人们的必然选择。因此,我们必须在关注人的解放实现的同时,也必须关注马克思的“非道德主义”的道德本身的价值取向,以避免现实中非道德事件的发生。
[注释]
①②⑤⑧⑫⑬⑭⑮⑯⑱⑳㉑㉓㉛㉜㉟㊲[美]R.G.佩弗著,吕梁山、李旸、周洪军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第47页、第53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321、323页)、第53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第54页、第194页、第195页、第198页、第53-54页、第57页、第60-61页、第63页、第71页、第77页、第78页、第81页、第83页。
③[德]黑格尔著:《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译者导言:关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第10页。
④⑥⑦⑨⑩⑪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第270页,第270-271页,第305页,第321-322页,第320页,第273页。
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页。
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4页。
㉔㉚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页,第101页,第102页。
㉕㉖㉗㉘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第444-445页,第122页,第615页,第109页。
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8-929页。
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