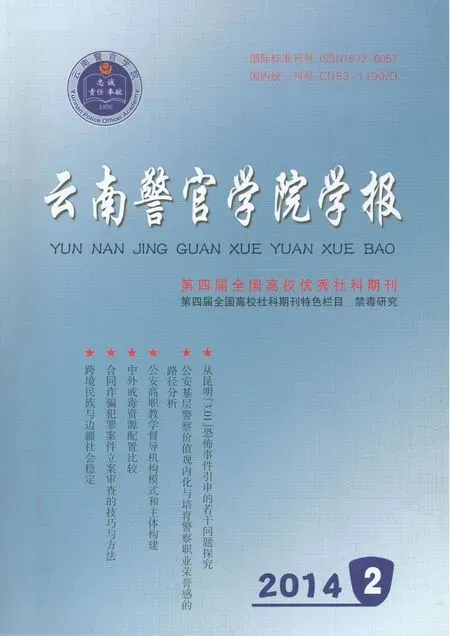寻衅滋事罪司法适用的限定
——以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
2014-03-13王霖
王 霖
(海南大学,海南·海口 570228)
我国《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其前身是1979年刑法的流氓罪。由于流氓罪罪状表述宽泛、外延不清,许多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被认定为该罪,学界将此罪批评为“口袋罪”。鉴于流氓罪的诸多问题,立法机关在制定1997年刑法时将该罪分解为寻衅滋事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聚众淫乱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斗殴罪。流氓罪的消解无疑是我国刑事立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巨大进步,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罪名滥用带来的不当扩大处罚范围,然而立法机关的这一举措并未真正实现口袋罪的消减目的。
审视当前的中国刑法,寻衅滋事罪并没有完全摆脱口袋罪的嫌疑,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成为流氓罪在当今社会的翻版、延伸。故此,我们需要反思寻衅滋事罪扩大化根源何在,是立法之过还是司法之失,从而寻求指导本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的规范解释,以期合理缩限其适用范围。
一、寻衅滋事罪口袋化并非立法之过
部分学者认为寻衅滋事罪在司法实践中被一定程度上滥用,立法方面的问题难逃其责,应在立法层面对本罪进行剔除处理。理由如下:首先外国没有类似寻衅滋事罪的立先例,我国对本罪的规定存在立法问题;其次,本罪法益不具有独特性,被分则其他条文保护的法益所涵盖;再次,本罪罪状表述模糊,司法适用缺乏可操作性。①王良顺:《寻衅滋事罪废止论》.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第111—113页。
口袋罪出现的立法原因有二:一方面缘于立法的不细致,罪状表述具有高度抽象与概括性,致使司法机关在找不到其他罪名可用时往往适用本罪;二是成文法的固有局限,罪状的描述只能是一类犯罪行为的抽象,司法机关利用这一特点对于罪状中的抽象性条款进行解释。②于志刚:《口袋罪的时代变迁、当前乱象与消减思路》.载《法学家》.2013年第3期.第72页。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条文时,必须舍去精确、全面的罪状描述,将犯罪行为类型化。
针对上述废除论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并不恰当。
第一,通过考察德日刑法,可发现其将寻衅滋事的若干行为分散规定为其他罪名。如《德国刑法典》第125条规定: “破坏国家安宁罪,作为正犯或者共犯公开地聚众,共同妨害公共安全的方式对人或物实施暴力,或对人实施暴力威胁的,或鼓励他人实施上述行为的,如其他条款未规定更重的刑罚,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③于志刚:《口袋罪的时代变迁、当前乱象与消减思路》.载《法学家》.2013年第3期.第68页。许久生,庄敬华译:《德国刑法典》.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此种表述与我国刑法寻衅滋事罪第一项所规定“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犯罪行为具有相似性。又如《日本改正刑法草案》在分则第260条规定了暴行罪,“对他人的身体施加暴行,未致他人伤害的,处三年以下惩役、十万元以下罚金、拘留或者科料。”④张明楷译:《日本刑法典》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本罪的行为方式与我国寻衅滋事罪中所规定的“随意殴打他人”具有相似性,皆保护个人的身体法益。
第二,笔者认为寻衅滋事罪侵犯的法益虽与分则某些条文的法益存在交叉,并非完全相同。寻衅滋事罪隶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一章,说明本罪更为注重的是对社会法益的保护。结论应是刑法禁止“随意殴打他人”,旨在保护与社会秩序相关联的人身法益;禁止“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严恶劣的”行为,旨在保护行为人在公共生活领域内的行动自由与名誉;禁止“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毁坏、占有公私财物的”行为,旨在保护与财产有关的社会生活的安宁与平稳;禁止“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旨在保护不特定人在公共场所从事自由活动的安全。⑤张明楷:《寻衅滋事罪探究 (上篇》.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1期.第87页。法益保护的独特性决定了寻衅滋事罪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第三,废除论者认为寻衅滋事罪罪状表述模糊,司法适用缺乏可操作性。笔者认为本罪罪状表述的适当模糊性使得该罪具有堵截犯罪的功能。诚如有的学者所言,“将侵犯的客体不属于其他类罪的客体因而不便纳入其他类罪,或者达不到其他类罪犯罪标准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聚合在一起,另设一类罪加以处罚,以防刑事法网出现漏洞。”①杜启新,安文录:《论寻衅滋事罪的合理定位》.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2期.第103页。对比日本刑法,其暴行罪中的“暴行”只要求对人的身体不法行使有形力,在性质上不要求已发生伤害结果。这与寻衅滋事罪中“随意殴打他人”一项接近。②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第70页。若废除寻衅滋事罪,对他人实施的伤害行为,只能考虑援用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但二者又不适用于寻衅滋事,随意殴打他人并未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行为。所以寻衅滋事罪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堵截犯罪的作用,避免法益保护的真空状态。
二、寻衅滋事罪口袋化缘于司法之失
综上所述,寻衅滋事罪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口袋罪的现象并非立法之过,而属司法之失。司法机关并没有准确地认定本罪的要件,在司法实践中对法条中模糊性表述扩张理解,使得非罪行为皆入罪,违法行为成重罪。因此,与其在立法方面进行争论,不如将目光转移至司法解释方面,以限制解释的方式认定本罪。
其一,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有罪必罚”的思想根深蒂固。许多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并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但由于存在“有罪必罚”的思想,被作为犯罪行为进行定罪处罚。“寻衅滋事罪名被大量的适用于那些破坏社会秩序的严重违法行为上,适用范围不断扩大,最终异化和突破了条文字面意思,用于处罚社会治安领域内没有明确罪名处罚的几乎所有行为。”③于志刚:《口袋罪的时代变迁、当前乱象与消减思路》.载《法学家》.2013年第3期.第68页。许久生,庄敬华译:《德国刑法典》.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寻衅滋事罪罪状表述的模糊性使得司法人员在“有罪必罚”思想的指导下,宽泛地理解条文中表述含糊的词语,导致本罪变成“口袋罪”。虽然起到了堵截“犯罪”的功能,但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道路上也许走得太远,远远超出了堵截性罪名的设立本意。以至于使人误认为本罪设立重在维护一种社会伦理秩序。但刑法的目的并非是维持伦理秩序,而是法益的保护。从这样的理解出发,禁止的对象就是引起了法益侵害或者是法益侵害的危险。①[日]山口厚,《刑法总论》.付立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01页。因此,司法工作人员应摒弃“有罪必罚”的思想,更加注重如何对本罪表述模糊的词语进行严格的限制性解释。
其二,寻衅滋事罪在司法过程中,成为“无恶亦罚”的工具。“无恶亦罚”思想是与刑法谦抑性相对立的一种刑事司法思维。我国重刑思想根深蒂固,司法者更加注重刑法的一般预防。司法机关在特殊情况下,往往会从维护社会成员感情的目的出发,对一些社会影响较大,不入罪又众口难平的违反社会治安的非罪行为以本罪论处。如寻衅滋事罪第一项中“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行为,由于没有限定殴打的严重程度,而“随意”一词又过于模糊,同时忽略本罪侵害法益所要求的“破坏社会秩序”的要求,许多违反治安的殴打行为以本罪论处。
在罪刑法定原则已经明确化的时代,口袋罪的出现主要由于司法因素所致。司法机关存在着解决有罪不能罚问题的冲动,在实现刑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往往会偏向后者。司法机关面对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行为,在无刑法条文明确进行制裁时,就会将其解释到部分外延较广、解释空间较大的几个特定罪名之中。②于志刚:《口袋罪的时代变迁、当前乱象与消减思路》.载《法学家》2013年第3期,第73页。寻衅滋事扩张适用的症结就在于此。故此,笔者认为应以限制解释的视角审视法条中的“弹性条款”,遵循罪刑法定原则进行解释,从而控制解释幅度,限缩本罪的适用范围。
三、对寻衅滋事罪应合理限制解释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国民在享受生活便捷的同时,部分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也遭到了网络犯罪的侵害。2013年9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皆称《解释》)。《解释》的出台无疑对打击网络寻衅滋事行为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是,《解释》对于认定网络寻衅滋事行为的范围不够明晰,人们更多是对本法条规定的“公共场所”的范围产生质疑,公共场所是否包含网络,在“信息网络”上起哄闹事,仅造成“网络秩序”严重混乱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笔者认为,面对寻衅滋事罪在司法活动中扩大化适用的境遇,应对“公共场所”、“公共秩序”、“公共场所秩序”进行学理解释,明确其含义,以期合理缩限寻衅滋事罪成立范围,从而使本已扩大适用的寻衅滋事罪回归理性。
司法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第293条第 (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而《刑法》第293条第 (四)项规定:“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本项中出现了两次“公共场所”的表述。对比《司法解释》第5条第2款与刑法条文第293条第 (四)项可知,司法解释将刑法条文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行为解释为包括在网络上“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将刑法条文的“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解释为“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从论理解释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一方面司法解释认为刑法条文第一处的“公共场所”包括网络领域,这是对“公共场所”范围合理的扩大解释。另一方面,司法解释将法条第二处“公共场所秩序”的范围扩大至“公共秩序”的范围,而对这一扩大解释应该进行合理的限定。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的寻衅滋事行为虽然包括在网络上起哄闹事,但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应严格限定于现实领域的公共场所,而非网络领域。否则“网络秩序混乱”,就可以成为“社会公共秩序混乱”,在“网络”上起哄闹事,造成“网络秩序”严重混乱就可成立寻衅滋事罪。
笔者认为公共场所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前者仅包括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等这种供人们活动交往的现实领域;后者不仅包括上述现实领域的公共场,同时也包括网络空间这种虚拟的公共场所。基于有效规制网络犯罪行为,应对《司法解释》第五条的“公共秩序”进行合理解释。即《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的“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的行为可以发生于广义的公共场所领域(包括网络公共场所)。但其结果应该限定于狭义的公共场所,如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通过这种限制解释,可以使寻衅滋事罪的处罚范围更加合理,避免因司法解释的出台,使得部分并未引起现实公共场所严重混乱的网络寻衅滋事行为也被认定为本罪。理由如下。
其一,“按照体系解释的要求,解释者在解释一个刑法条文时,必须根据该条文在整个刑法中的地位,联系相关法条的含义,阐明其规范意旨。体系解释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在于避免断章取义、避免自相矛盾,以便刑法整体协调。”①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83页。“法律解释的古典规则早就指出,对规范的解释应尽可能避免使规范之间出现冲突”。②【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规定,“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以本罪论处。法条明确了行为结果的发生场所,即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所或者其他公共场所。从法条可知,公共场所皆限定在社会成员活动的现实领域,并未涵盖网络公共场所。虽然法条中也有“其他公共场所”的表述,但笔者认为,既然法条以列举阐明的表述方式罗列了公共场所的对象,那么“其他公共场所”也应该限定为与法条罗列对象性质相同的现实领域的公共场所,既然法条列举的公共场所并未包含网络公共场所,那么“其他公共场所”也不应突破法条应有的含义,包括网络公共场所。因此,为了保证刑法用语含义的协调一致,寻衅滋事罪第四项“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中的第二处“公共场所”,也即寻衅滋事行为结果的发生场所,也应该限定为诸如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这类社会成员交流活动的现实领域。同时作为本法条的《司法解释》也不应突破法条的原有含义,将第二处“公共秩序”解释为网络公共场所秩序,而应限制解释为现实领域的公共场所秩序。
在此次《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其他司法解释中也有对“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行为的相关规定,通过对其分析可知,在“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的行为结果皆为造成现实领域的“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并不包括网络领域的公共场所。
例如2013年7月15日施行的《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寻衅滋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五条规定,“殴打、辱骂、恐吓,或毁损,占用他人财物;追逐、拦截;强拿硬要,毁损财物;在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重要程度、公共场所的人数、起哄闹事的时间、公共场所所受的影响范围与程度等综合判断是否造成了公共场所秩序混乱”。法条于“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之前,明确列举了现实领域的公共场所,因此,起哄闹事行为造成的结果也应限定为现实领域的公共场所,并不包含网络公共场所。
其二,“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其中有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就是刑法上的法益。”①张明楷:《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客观的违法性论认为,违法性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与威胁。现代社会与网络相关的个人及社会法益必须得到刑法的保护。网络犯罪行为依据行为侵害的法益可分为两类:一类侵害法益为网络本身的安全保密及网络系统的正常运行,如《刑法》第285条规定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第286条规定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以及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另一类网络犯罪行为侵害的法益为社会成员的财产及人身安全等,这类网络犯罪行为皆可为刑法的其他相关犯罪论处,如《刑法》287条规定“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相关规定处罚。”
笔者认为,网络寻衅滋事行为属于第二类网络犯罪行为,其法益并非网络秩序本身,而是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在公共场所从事自由活动的安全与顺利。单纯的网络起哄闹事行为及网络寻衅滋事行为,并未侵害现实公共场所秩序法益时,不具有可罚性。正如宪法学者张千帆教授所言,网络行为其实不是“行为”,而是“言论”。最根本的是,“网络秩序”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网络天生是一片乱哄哄的众说纷纭。②http://blog.qq.com/qzone/622007780/1377508275.htm.虽然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张千帆教授的上述观点,因为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正常的网络运行空间才能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在网络上起哄闹事,单纯造成网络公共场所秩序混乱的行为,并未引发现实领域的公共场所秩序的严重混乱时,不能成立寻衅滋事罪。只有当行为人在网络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且该行为造成现实领域的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才能认定为寻衅滋事罪。“网络虽然增加了人的认知范围和活动领域,但网络空间的利益多数仍是现实空间中利益的延伸,差别只在于表现形式不同。可以说,传统刑法对网络空间的适用困境,有相当一部分是人为臆造出来的,还有相当一部分完全可以借助适度扩张解释的方法加以解决,真正具有入罪化必要性的领域是有限的。”③于志刚:《网络犯罪与中国刑法应对》.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122页。
公共秩序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刑法》第293条寻衅滋事罪第四项规定了“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此罪状中第一处“公共场所”应解释为广义的公共场所,包括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这种供人们活动交往的现实领域,同时也包括网络公共场所;第二处“公共场所”应限制解释为狭义的公共场所,即排除广义公共场所中的网络公共场所。对于《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2款,“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中的“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也应限制解释为狭义的公共场所,不包括网络公共场所。应从这种限制解释的角度出发,合理限定寻衅滋事罪中“公共场所”的含义,缩小寻衅滋事罪的成立范围,避免寻衅滋事罪不当地扩大化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