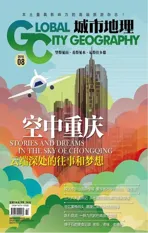重庆人眼中的白象街我们来过,还将温暖地爱下去
2014-03-13陈琰枫曾金Daisy何智亚罗大万胡成
文+陈琰枫 曾金 Daisy 图+何智亚 罗大万 胡成
重庆人眼中的白象街我们来过,还将温暖地爱下去
Baixiang Street in their view They Come, They Love
文+陈琰枫 曾金 Daisy 图+何智亚 罗大万 胡成

一直以来,白象街都住满了人。无论百年前,还是一个世纪后,人,才是这条街上最鲜活的风景。无论是永远飘着蜂窝煤烟味的街巷,还是那支甜到心里的冰糕,抑或是在这里度过的艰苦岁月,以及少年时懵懂情怀……这些都是白象街给予他们最温暖的记忆。


人物档案姓名:肖能铸职业:资深媒体人;文史学者;著名的“重庆通”。年龄:67岁

人物档案姓名:何智亚职业:著名摄影家;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董事长;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委会主任委员。年龄:60岁
英文导读: Baixiang Street leaves too much memory to the people. Four Chongqing ones will tell us some interesting things about Baixiang Street.
“活字书”聊开埠趣事
在观音岩一栋居民楼里,我们见到了肖能铸。精致的客厅里摆满了各类茶具,在我们到来之前,茶已经煮好,在一片氤氲的茶香中,我们开始了这次采访。
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和肖能铸聊天。他几乎不假思索,滔滔不绝地从南宋抗蒙的余玠帅府聊起,一直讲到清末开埠时的百理洋行,从药材工会的建立缘由聊到卜凤居历代主人的轮换,从储奇门药材码头扩展到重庆的九开八闭十七门,从“重庆第一买办”白理洋行聊到江西会馆,从重庆第一代海关的设立聊到到东华观一步步沦为废墟,从民国第一代海归人士聊到来往的客居商旅,从《新蜀报》的历史人文聊到《重庆日报》的沧桑沉浮……
肖能铸就像白象街的一部“活字书”,从白象街的建立到它的繁荣乃至落寞,随便翻到哪一页都能清晰地读出它里面的细枝末节。
肖能铸说,虽然在南宋时期,白象街已经作为重庆的政治、金融中心,但是白象街真正“活”起来是在开埠时期。他告诉我们,1891年,清政府虽然同意开放重庆,但重庆主城却迟迟没有“洋人”入住,从沿海涌来的大批“洋人”只能在南岸聚集,不敢踏上渝中半岛一步。

人物档案姓名:曾清华职业:重庆渝中区餐饮商会会长;重庆美食协会常务副会长;清华实业集团董事长。年龄:56岁

人物档案姓名:邓颖职业:医生;白象街长大的重庆土著。年龄:33岁
原来“高鼻子、黄头发,还穿着怪异衣服”的外国人“吓坏”了“没见过世面的重庆人”。为了安抚重庆人对未知事物的畏惧心理,当时的重庆巴县政府规定:“洋人不准过河。”于是,日法英美诸多商船只能停驻在南岸,眼巴巴地望着朝天门白象街一带。
但是“有商品的地方肯定有集市”,洋人带来的商品最终流入了渝中半岛,买办集市开始在白象街出现,白象街至南宋过后再度繁华起来。各种“洋气”的东西买卖于白象街,钱庄、洋行纷纷出现,各式“洋房”也在白象街拔地而起。
时髦的青鸟冰糕
时光荏苒,到肖能铸小时候,白象街的繁华已然褪去,它如同一个暮年的老妪般铅华落尽,只留下无数建筑风格迥异的老房子。这时的白象街是一条市井之街,但是却依然保持着鲜活的状态。这里住着电报局、轮船公司、长江航运局的职工,从老建筑楼底向上望去,可以看见每层楼的阳台上挂满了正在晾晒的衣服,五颜六色,很是壮观。
在肖能铸的记忆里,白象街的清晨是从点燃蜂窝煤开始的。“报纸、柴火、煤球、蜂窝煤、火钳……家家点火,户户冒烟”,肖能铸说,直到太阳老高了,笼罩在巷子里的烟味儿都还没散尽。很多年过去,蜂窝煤炉渐行渐远,而街巷中沉淀了岁月痕迹的青石板路和百年来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构成了这里最温馨朴素的生活画面。
对于当时年仅十岁的肖能铸来说,卜凤居才是他的乐园。
卜凤居最初是民国首富李耀庭的私家别院,民国后期被民生公司的一个股东买了下来,做成了重庆最早的一家冰糕厂,当年著名的“青鸟冰糕”就出于此处。肖能铸的父母和冰糕厂的老板相熟,常常带着他过去玩,而关于“玩”的所有项目就是吃当时尚属“稀缺物质”的冰糕。我们可以想见,站在卜凤居门口的肖能铸,一面嘴唇和舌头被冰棍冻得发红,一面又接受着其他孩子艳羡的目光。
时间到了上世纪50年代,肖能铸和父母一同搬离了文华街,离白象街也远了。与白象街唯一的联系只是弟弟在长江航运局上班,他偶尔会回来看看弟弟,顺便看看白象街。每回来再见白象街一次,白象街就破败一次,肖能铸也没有想到白象街会“老”得这么快。这里的原住居民要么出国,要么买了新房子搬离,白象街成了外来务工人员最便宜的容身之地,“打工一条街”的名称也渐渐流传开来。
不久前,肖能铸应融创之邀再次来到白象街勘察,小巷寂寂,空无人烟,唯有几只丧家之犬在废墟和空巷深处流浪。再一次见到了卜凤居,古宅无人,蜘蛛结网,阴风簌簌,穿堂扑面令人毛发悚然,老宅的四周已成为一堆瓦砾破砖。
一次尊重文化的改造
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试图去挖掘更多或波折或离奇的往事。肖能铸却说,生活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简单平凡就到了他这个岁数。正如他面对融创对白象街改造的心情,平静而祥和。
“一百多年前,英法日美等外国人一同来到白象街,他们在这里建房,修的房屋代表了他们国家的建筑符号。这些建筑符号被重庆吸收,造就了重庆的文化与繁荣。” 肖能铸告诉我们,“重庆之所以如此繁荣,不是没有根的,它的根就在白象街。”
所以,对于白象街剩余的9栋建筑,融创决定在此基础上打造出具有重庆风貌的建筑群落,还原“重庆母城文化”,对于肖能铸来说,当然是个好事情。“在我这里,我对白象街只有儿时的短暂记忆,但是我的孩子或者更下一代,他们连短暂的记忆都没有,他们根本不知道老一辈曾经是怎样的生存状态。融创对白象街的改造,至少能给重庆人留一点记忆。”

曾经辉煌的白象街,到现在已衰落下来。修复与重建的问题亟待解决。

对于曾经生活在白象街的人来说,面对这样的结局,或许有过哀怨,有过抱怨。白象街上所有关于生活的烙印,每一块砖头,每一缕炊烟,都代表着无数温暖的家,世世代代的人居住在这里,没有人曾经想过会有变化。
“白象街不仅是老重庆的一部分,更是老重庆的一个缩影,只要融创重视文化,将白象街‘修活’,不管怎么动,都是对重庆文化的尊重。”
现今唯一堪称老街的地方
有一本叫做《重庆老城》的书,当中罗列了白象街的诸多历史、文化、建筑等资料,其中也包括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此书实为珍贵。因为这本书我们找到了作者何智亚先生。
何智亚先生是本市知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是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委会主任委员,他主持参与了多个历史建筑、街区、文化名镇的保护规划和修复工作。从1992年开始,他便利用起业余时间,逐一走访老重庆城的历史遗迹,将典型的历史建筑和街区留在黑白底片中。而这些照片当中,就有白象街里诸多建筑文物的影像。当然,由于城市开发,一些历史遗迹现在已不复存在了,他进而翻阅了大量史料,著成了《重庆老城》一书。
“现今唯一可以称为老街的地方,只有白象街了。”
得知记者来意,何智亚发出了这样一声感叹。身为重大建筑规划学院的教授,何智亚先生另一个身份是建筑专家。提及白象街,他便给我们罗列了白象街文物建筑的建造风格。比如江全泰号,坐西北朝东南,典型中西结合殖民主义风格。外墙主要为青砖砌筑非常肃穆,正立面砖砌柱间开有大窗,窗上由3匹砖砌弧形窗拱,极具西式风格。内部保留有木质门窗及雕花窗格等,又有中国清式建筑风格,可说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建筑了。
当我们向何智亚提到现在摩天大楼林立,城市趋同,而老街那些有特点的建筑逐渐消失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回答说:“恰恰像白象街这样的老街,这些中西结合的洋楼,夹居在重庆传统民居吊脚楼之间,这才是重庆独特的城市符号。”

白象街是现今仅存唯一一条重庆老街,其中留存了很多文物建筑。
勘出太平门老城门
谈到白象街大片区,其中一个建筑文物与何智亚有着极深的渊源。那就是勘出不久的太平门。传说中重庆城门“九开八闭”,太平门便是其中之一,只是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这些门大多失去了踪影。
一日,何智亚接到一通电话,说是四方街挖出一座老城门,包括何智亚在内的五位文物专家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对这座老城门进行考证。文史专家肖能铸也在现场,他带着一个指南针,拿着彭伯通(《古城重庆》作者、曾任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提供的相关资料,对着城门看了半天,“一定是在这里,一定是在这里。”
目测了城门的券拱内宽, 何智亚想起他查阅清朝到民国35年期间的大量地图,发现挖掘出的这座老城门与地图上的位置一致。此外,根据城墙的走向、相关文献以及当地百姓回忆等信息,均可断定,此座城门就是太平门。他也给出肯定答案,“是的,这就是太平门!太平门是开门,史书记载, 太平门修建于宋末,开门比闭门要大,现在看来它与同为开门的通远门、东水门的券拱内宽都为3米多。而重庆现存唯一的闭门是人和门,券拱内宽只有2米左右。”
何智亚告诉我们,像太平门这样的古代建筑,已经不止是文物了。它还承载了整个重庆城的历史文脉,能第一时间看到它出土,何智亚很兴奋。只是出土以后,我们怎样去保护它,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给开发者的两点建议
现在白象街的衰败,其实也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只是伫立在白象街上的数个文物建筑,若是久置,也会逐日被损毁。无论是市政项目,或是地产开发,对白象街有保护意识性地开发修缮,从长远来说,也是有必要的。
何智亚对建筑、规划与城市符号都颇有研究,同时也是一个对老街、文脉、历史带有情怀的人。开发白象街虽是情非得已,但也是当务之急了。何智亚便提出两点建议,赠与开发者们。
其一是白象街遗存历史文物无数,建筑、古城墙等必须对其进行保护和修缮,切不可有丝毫损毁。这是何智亚对文物保护的急切之情。
其二则是规划问题上,在新开发白象街时,一定要有与老街有相同风格的规划设计,将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融入设计之中,与文物老建筑形成统一。这一点,则是何智亚希望开发者延用白象街自古以来的城市符号,将重庆文脉繁衍昌盛。
“白象街就是我们的游戏场”
对白象街记忆深刻的,还有现今重庆餐饮行业的巨头:曾清华。

大家都只看到曾清华在重庆餐饮行业干出的大事业,却不曾知道,他在望龙门街区艰苦地生活了近四十年。曾清华自1958年出生后一直住在望龙门二府衙,“我是土生土长的望龙门人,从小都没离开过这片街区。学生时代也是在望龙门街区的二十六中度过的。因为整个下半城中,唯独白象街最为宽敞平整,我们学校的同学们都喜欢去白象街滚铁环,白象街也就成了二十六中学生们的游戏场”,曾清华告诉我们。
曾清华回忆起白象街,只记得当时的重庆是这样一个格局:七星岗以内,千厮门到南纪门这一段称为下半城,这一段是老重庆人居住的区域。白象街当时属于望龙门街区,是于八码头和九码头之间的一条长街。“一到热天,我就会从二府衙穿过白象街,下到码头去长江里游泳。所以到现在我的印象里面,那时的白象街街面都是很闪闪发光的。”诚然,当时的望龙门街区人居密集,生活基础设施逐日落后,但作为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给曾清华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
拥挤的小院和街头的煤店
“当时的白象街不像你们在历史书上看到的那样,什么商号啊、洋人办事处啊、大店铺啊,一概没有了,有的只是住得密密扎扎的人。”曾清华说。
他告诉我们,他经常去到白象街串门。一来因为白象街离住处只有百十来米,二来曾清华父母在西藏工作,自己一人在这里生活,经常靠吃街坊邻居的百家饭度日,而居住在白象街的亲戚家自然成为了首选。他描述中的白象街,无论大院洋楼还是小屋独院,但凡能容得下身体的地方都住着人。沿着街面,随便进得一小院,通通都住着二十来户人家。生活区域也是公用,早间上个茅厕,也得排老长的队伍。当时电力不甚发达,电灯、路灯、壁灯等照明工具稀少,所以白象街居民常年生活在阴沉沉的小院里,活像贫民窝棚区。
“特别是白象街街头上的一家煤店,我记得很深”,当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里,煤是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物资,购煤是每户人家日常生活之一。寄居人家的曾清华每日都要去那家煤店帮每家每户担煤。看着煤条从压煤机中压出来、截断、晾干,成了青年曾清华见过最多的景象。生活艰苦时期,他与小伙伴们还自己收集煤渣、用泥土掺水、和煤、晾干,自制煤球来度日。在同一街区的一个“兄弟伙”出外当兵去了,留着家中老父母,曾清华也尽手足之责,替伙伴家担了5年多的煤。他笑着说:“哥们出外锻炼去了,我担着煤,从白象街这头走到那头替他们家送煤,也是锻炼出了一副好身板。”


中学毕业,曾清华便在望龙门街区的曙光变压器厂拉板车、打冲床,成了一名工人。他一边在街道小厂工作,一边抽业余时间学习。后来去了电视台,接着调到文化局工作直到1992年。再后来下海经商成为重庆餐饮行业巨头,搬离了望龙门街区,远离了白象街。但无论何时何地,曾清华依然会称自己为“土生土长的望龙门街区人”。
倾圮的老建筑里存满回忆
邓颖是我们见到的第四位与白象街有着情感牵绊的人,她与曾清华一样,虽然远离了白象街,但每每提起那条街的名字,心中也会涌出无限感概。
虽说搬进小区新房已有很多年了,但是,在远离白象街的这些年中,邓颖始终怀念那谧静的老房子里的气息和风情。依仗着世代能居于此的荣幸,如同是隐匿在心底的一缕魂魄,一种渗透到骨子里的淡定始终在伴随着她。那种儿时居住在老房子里人之间交流的随意,和这一方天地所给予人们的安全与涵养,是邓颖现在居住的小区所不能比拟的。

左右页图:现在的白象街社区居民均已搬迁,楼下空楼和空地,等待着被重新开发。



在一家咖啡店里我们见到邓颖,不用过多的客套寒暄,当“白象街”三个字从我们嘴里念出来时,她的情感记忆闸门已经自动打开。“那些在老房子里经历过的似水年华,经常以饱满且鲜活的烙印,一而再,再而三生动地再现在我的梦里。”
那日,一个熟识多年的儿时邻里跟邓颖说起白象街将要拆迁的事,说他要去走走,问她是否愿意一同前往。邓颖在初始的震惊之后,不顾重庆四十度的高温,与朋友再次来到了白象街。“或许,就是为了寻找当年居住旧址的痕迹。”
倾斜的电线杆,混乱的电线,破旧的老房子,只有三两个老人还斜倚在门口,老街基本都拆完了,只有那座“江全泰号”还矗立在白象街的废墟中。邓颖和朋友来回徒步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凭着依稀的记忆,在脑海里贯穿描绘着街巷里的杂货店,卖桃干的小摊铺,摆着金庸或古龙武侠小说的书摊,永远静立着的邮局,以及那座黑灯瞎火的公共厕所和一大早儿就飘漫着烧饼油条喷香的早点铺子……还有老住房里那倾圮的门,也从此永远地关上了。相伴了多年的老邻居们都散开了,一如秋后的落叶,四处被风吹的不知了去向。



图为白象街所属的望龙门街区,大多数建筑都是七八十年代建造,现在均已陈旧。
邓颖说,她很后悔,后悔知道得太晚,后悔哪怕在拆迁时带走一片瓦,或是厚如青砖的窗台木,也算是为自己心中的白象街留个念想。那天,邓颖呆呆地站在阳光下淌着汗,就像昔日老邮局的邮筒一样。
老街里的老面馆
邓颖与白象街能有如此强烈的羁绊,除了儿时的家就在白象街末尾,还因为这里住着年少时的意中人,和刘叔煮的那碗体贴的面条。
邓颖初中就读于陕西路中学,初中三年,每天下午她都会和另一个同学去意中人家里做作业。晚饭时如果父母有事来不及回家,就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光。他们可以先去小书摊看会儿武侠小说,等天快黑的时候,就在邮局旁边的小面馆吃刀削面。老板刘叔总是根据他们的口味量身定制:邓颖偏爱面条削得厚实一点的,不要姜蒜,少油多菜,多花椒少辣椒,而他的偏爱是苗条削得薄一点,多辣椒,不要花椒。如果刘叔有空,还会亲自熬卤料给他们卤鸡翅膀。有一次邓颖问意中人:“为什么刘叔只卤鸡翅呢?”他淡淡地说:“不是你说的鸡脚肉少,喜欢鸡翅膀吗?”后来,邓颖才知道,就是因为自己无意中提过喜欢鸡翅膀,他便牢记在心里,转而告诉了刘叔。那些年,在白象街这间普通的面馆里,珍藏下了一对少男少女的情窦初开。
2002年,邓颖和他重回白象街,此时的他早已移民国外。当他们再次来到刘叔的面馆,里面依旧客满,她和他与别人拼桌而坐。已经过去了7年,刘叔老了许多。邓颖原以为刘叔已经不认识他们了,但刘叔端上刀削面时却说:“你的没有姜蒜,少油多菜,多花椒少辣椒。你的削薄一点,多辣椒没有花椒。”两人望着热腾腾的面条,就像回到了小时候一般。邓颖告诉我们,当时除了感动,她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形容自己的感受。
如今,刘叔的面馆连门脸都找不到了。对她而言,白象街,刘叔的面馆,武侠小说的书摊,还有儿时的那个他,就是她的整个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