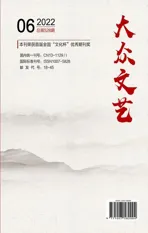浅析电影《钢的琴》的形式与风格
2014-03-13王鹤翔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王鹤翔 (兰州大学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浅析电影《钢的琴》的形式与风格
王鹤翔 (兰州大学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由张猛执导《钢的琴》是一部具有十分明显形式与风格的电影作品,其在赋予影片独特的艺术价值同时,成功地升华了影片主旨。本文旨在通过探讨《钢的琴》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 以期对我国影视作品的创作提供参考。
钢的琴;张猛;钢的情;形式;风格
《钢的琴》是由张猛自编自导的一个关于东北老工业区下岗工人的喜剧片,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女儿的音乐梦想而不断艰苦努力,最后通过身边朋友的帮助用钢铁为女儿打造出一架钢琴的故事,通过小人物幽默与艰辛,展露一段感人至深的亲情和友情。这部小成本电影,从艺术表达来看独特、成熟、到位;从感情表达上极端丰满;在社会认同上口碑极佳。戴锦华说:“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中国电影之一。”
一、通俗却不落俗套的形式
波德维尔及汤普森在《电影艺术——形势与风格》中讲到,对于艺术作品来说,所有的元素都必须和形式发生关联。更为极端的,俄国形式主义者甚至将一件艺术作品比喻为“洋葱头”——形式即为外皮,剥下一层形式是另外一层形式,乃至剥到最后都还是形式。虽然偏激,但形式之于艺术作品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而对于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形式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了。
1.典型的线性叙事
如同大部分剧情片,《钢的琴》有复杂的情节,一条主要叙事线,两条次要叙事线。主要叙事正如影片名字所提示出的,与钢琴息息相关:学琴——画琴——买琴——偷琴——造琴。陈桂林起先还能勉强支付起女儿的学琴费,女儿则在半夜留在学校点蜡烛练琴。但不久老师发现,禁止她再练琴,于是,陈桂林用硬纸板画上键盘给女儿练琴。当陈桂林与妻子在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如火如荼之际,女儿提出谁给她钢琴就跟谁走。借钱未果下,他与一众亲朋好友想在半夜把学校的钢琴偷走,事迹败漏后,他偶得启示,便开始了造琴计划。
围绕着“琴”,牵出另几条叙事线:其一便是陈桂林的爱情线。他下岗后,妻子不堪清贫的生活,要离婚并嫁给富有的药商。 虽然同乐队的淑娴数次表现出很想和陈桂林在一起,但他始终是“欲拒还迎”的态度。在一次聚餐后,他甚至对淑娴说想要娶她是为了“照顾老人”“尽义务”。淑娴认为即使造出钢琴也难以拿到抚养权,而且孩子跟着条件富裕的母亲生活会更好,陈桂林却认为她是出于继母的仇恨心态。之后两人心生嫌隙,淑娴与同做饭的王抗美关系越发亲密。在一个又一个误会之后,陈桂林终于能够坦诚面对新的感情,也学会了爱人,终于能够真心地对淑娴说一句“我现在可以娶你了”。另一条线索则是关于东北老工业区的印象——人们试图阻止将要被炸毁的两根烟囱,却无力挽回它们的命运。在这里,不能单纯地概括说中国人“恋旧”,虽然在有的人眼中那只是两根烟囱,但在老一辈老东北开拓者、建设者眼中,那却是成长的记忆、国家的坐标、遗忘许久的老朋友。时代发展的进程要求它离开,工人们再多的挽留也只能是徒然。正如时代发展,国有大工厂制度被要求离开,这些工业时代遗民只能顺应潮流,自己过活。最后,工人们集体见证烟囱的离开,滚滚烟尘淹没的却不仅仅是时代印记,此外,剧中人物的出场也很有特色。按照好莱坞经典叙事,人物一般在前10分钟全部出场完毕,但《钢的琴》却不然。我们在开头葬礼中可以看到两个主要核心人物——陈桂林和淑娴,但小乐队其他成员却并不是电影叙事的主体。王抗美,大刘,胖头,二姐、二姐夫是在“买琴”之际出现;汪工,季哥,快手则是在剧本已经进行到一多半的情况下——“造琴”阶段才出现的。需要提出的是,两组人物的出场,分别靠陈桂林为给女儿买琴借钱一次又一次被拒,和给女儿造琴找帮手时一人又一人同意所勾连出,而且前一组人物在“造琴”阶段也参与了进来,使得一整个人物团体越来越庞大。
2.喜剧——无时不在的泪点与笑点
这是一部定义为喜剧的电影,却是能够令人流着心酸泪而笑的电影。究其原因,大抵是这些所谓笑点都是出自小人物们的自嘲——在这一点上很类似于周星驰的电影。但不同的是,星爷的笑源于其独创的无厘头“恶搞”式幽默套路,张猛则是认真严肃而平静地述说本是悲凉的故事。
看望二姐时刚说到带了一块肉、肉就被偷,胖头打麻将偷牌被追得爬上烟囱,陈桂林带给汪工的鱼是他在江边炸的;与胖头谈起快手的暴脾气,陈桂林说快手干起仗来5、6啤酒瓶子往人家脑袋上削,就这还没完呢还满地找啤酒瓶呢,胖头只接了一句“打的就是我”;发图纸时淑娴和王抗美问为什么他们没有,陈桂林说做饭的要什么图纸;弃木质结构打算做钢的琴时,大伙说木头可以烧火做饭不能浪费,陈桂林则说:“有困难我们要上,没有困难我们创造困难也要上!要不能把这钢琴给整出来我就跳烟囱!有人跟我跳没?”结果大家却是各吃各饭,根本不理他。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殊途同归是博观众发自内心的会心一笑。观众的笑,或是源于相似的生活体验,或是受其苦中作乐的精神所感染,却未曾,或者说不敢就此轻视他们。在影院,看电影的人往往笑声中伴着哽咽声,甚至哽咽到笑不出——那是一种源于内心深处的肃然起敬与感慨。
3.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难以把握命运的边缘人
张猛并没有看过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但他们之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用热情、酒神精神(狂欢)来描述现实的残酷、生活的颠簸。
陈桂林因为下岗生活拮据,不仅妻子离开他另觅好归处,就连女儿也以拥有自己钢琴为筹码才愿跟着他;他为女儿好不容易才凑齐学琴的钱,甚至还要贿赂老师;因为没有条件,他让女儿半夜在学校点蜡烛练琴;胖头的女儿未婚先孕,他终于找到了那个“流氓”——一个半大的孩子时,所有的悲愤恼怒也只能化为无奈的两个字:“滚蛋”;虽然是昔日的工友,但提到造琴时快手却直接问钱;两方的工人同时挖到一大块废铁,为了争夺这块废铁卖钱,两方大打出手甚至使其中一人脑袋血流不止;昔日重义气负责任的季哥,却终被举报随警察离去……我们看到的似乎都是赤裸裸的现实和一场场的心酸。阔大空荡的车间,有几缕阳光投射下来;或从房内往外,一直拍到房门外的孤单的自行车。这种陌生化的美感,正如我们所熟悉却并不了解的社会群体——他们命途多舛且难以把握,没有人能够为他们的前途指出一条明亮的康庄大道。
当一个社会群体的地位集体坠落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孩子可能遭遇的生命际遇也会随之改变,这让我们看到某些社会的所谓失败者、某些在社会生活当中似乎无能为力、非常无助的人,或许并不是他们个人的原因,而是某种社会历史的缘故。一旦他们能够重新获得他们自己的位置,一旦他们能够组合成一种有高度认同的集体,他们就能把握命运,而这种把握感在电影中较强地体现在两个段落:一个是胖头决定去教训欺负他女儿的人,于是工厂大门打开,陈桂林他们一整个团体或乘摩托或开卡车,相继涌出。有趣的是,在这个片段中导演将这个落寞的群体拍出了黑帮片的那种仗义的气势。我们也感受到了原本涣散的、各扫门前雪的小人物心中浓浓的对他人的深刻关怀之情,一旦他们紧紧团结起来,立刻就有了睥睨天下的气势。另一段落在结尾陈桂林放弃抚养权,但工友仍旧去造钢的琴时穿插的类似于歌舞片的交叉蒙太奇剪辑。这是整部影片的高潮,也是最为酣畅淋漓、回肠荡气的段落。此时能否造出钢琴无力改变陈桂林的命运,但他们偏偏要证明出即使已经被命运所抛弃,仍旧要扼住命运的咽喉。顽强如此,他们也便不再渺小,而是真正的大写的人。
二、语言元素丰满而突出的风格
1.诗意化的间离效果
无疑,《钢的琴》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但其中却又有不少超脱于情节之外的、与叙事分离的部分。与同是表现边缘人物的现实主义题材的贾樟柯《三峡好人》中夜晚突然如火箭般发射升空的烂尾楼的那种间离效果不同,张猛表现出的间离是与情节难分难解甚至难以辨别出的、诗意韵味极浓的间离。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间离情节,是陈桂林一行偷琴被发现,友人四散逃开,但陈桂林死死抓住钢琴不放手,有如抓住所有的希冀一版。接着,影片违背了观众的预期,并没有展现陈桂林一行被抓并扭送到公安局的过程,出乎意料的,导演设置了陈桂林嘴里叼着烟坐在这架钢琴前弹奏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四周一片漆黑,只有大片的雪花纷纷落下。接着,镜头升,影像淡出,淡入的是可以预想到的陈桂林一行或沮丧或精神涣散地坐在公安局的椅子上,这种“意识弹奏”一直持续到警察推门进来,音乐戛然而止。后面有一段,也是在黑暗中投下两束光,分别照向拉着手风琴的陈桂林和站在不远处沉默着的淑娴。这两个片段,极具前苏联50、60年代“诗电影”的特色:一段苦涩的过往被抒情场景及诗性格调代替,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立现。在文学作品中,有“以乐景写哀情”;在这一影片中,我们以直观感受到了其中的悲喜。
影片中的另一种形式的间离,则是与电影“隐藏摄像机”理论相背离的。如在开头葬礼的片段中,陈桂林一行的小乐队面向镜头平铺开成一行,尤其是淑娴,直接对着摄像机演唱。但后来突然有画外音闯入,说:“停停停!”这是一段很值得琢磨的片段。曾有人分析说,这个画外音来自于导演的位置,喊停也是导演的特权;在这里很有可能是张猛自己在喊停,并要求在葬礼上演奏欢快的曲调——他是在开电影的玩笑。撇开这一层意味外,我们还会发现,其实葬礼的会场布置在乐队的左侧,他们在弹奏《三套车》是对着观众,在降B调《步步高》中才是对着葬礼会场。两相对比可以感受出,“有人在唱那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正是这群底层小人物面对观众,唱出自己心酸的生命。这种“面对观众说话”的场景还出现在前往偷琴的路上众人在车厢高歌,及决定造琴大业之际的晚上,陈桂林一众在KTV唱歌的片段中。
最具视觉冲击的,是在结尾处陈桂林已然放弃了抚养权,但昔日工友还是重聚在一起,接着造钢的琴——他们推开工厂大门的那一刹那,紧接着的是歌舞队形态与现实主义情景剧的组合——跳着西班牙热舞的红裙舞女与工人造琴的交叉蒙太奇剪辑。这一段酣畅的剪辑如梦如幻,观众难以分清舞队究竟有没有真的在衰败的工厂中激情起舞。当然,真相在此也不再重要了。
2.低角度的舞台效果
整部电影开篇的第一个镜头,是全黑状态下的几句话,“离婚就是相互成全,你放我一马,我放你一马的事”,之后画面淡入,陈桂林与小菊并肩而立,两人目视前方,没有任何交集。不仅是没有目光的交集,两人一左一右站立,身侧的景致也是没有任何交集:陈桂林身侧是破败的房顶和旧弃的厂房,以及他的摩托车;小菊身侧则是修葺完好的房顶和一条康庄大道。两人虽然站在一起,但各自身旁的景致截然不同,这种构图法极类似于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全景过后,分别是两个人的中近景,完全是相互被割裂开,如同被撕开的照片的两部分。当然,应用于电影尤其是开篇第一个镜头中,除了引人深思外,其中的暗示(两人的生活状况、乃至结局抚养权的归属)极浓,隐喻意味不言自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时的摄影机出于两人正前方,低角度仰拍。这种机位在影片中非常常见,无论是运动镜头还是固定机位拍摄,导演都一直保持着这样拍摄风格。
这是一种非常态的影像画面构图方式,是一种强化性的表意方式,能够造成影像的扭曲和畸变,一般只偶尔参与特定影像的画面构成,用来对特定人物的姿态与环境风貌做造型处理,以强化对象的高大、突兀、压迫感等效果。在本片中,导演大量使用低角度仰拍镜头来拍摄这群社会中的底层小人物,并将这一手法贯彻影片首尾,并非是要制造他们的高大形象,摄影机在低角度中拍摄人物时采取了中规中矩的正面或侧面对准人物的方向,这样就避免了影像的扭曲变形和镜头的主观化,而使镜头保持了一种观众的客观视点。这样的镜头拍摄方式在画面中制造出了一种舞台效果,导演仿佛是要给这群被社会遗忘,被时代抛弃的底层小人物们一个舞台,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他们的生活状态和他们的精神追求。而镜头的视点则恰恰保持了一种坐在电影荧幕前面,仿佛坐在这个舞台下面的我们观众的视点。
3.极具意蕴的水平运动机位
戴锦华称这部电影风格为“以身试险”——违背了电影语言语法的基本规范。其实细细想来,也确实如此。随意翻开一本电影理论或影视批评的著作,我们都会了解到,电影艺术的基本形式规定了,电影是扁平的、二维的;电影艺术的魅力在于如何创造第三维度幻觉。正是因此,明斯特伯格才会在《电影:一次心理学研究》中强调了“深度感”这个概念。为了创造第三维度幻觉,纵深感显得极具重要,无论是《公民凯恩》中经典的景深镜头,还是现在影视剧中常见的主人公之于摄影机迎面走来或背向走去的镜头,这种推拉很容易造成一种张力,将观众带入到电影这个立体生动的幻觉之中。但《钢的琴》的独特在于,导演并不醉心于制造三维幻觉,而是大量使用水平调度。
最突出的一个片段是影片仍是开头的一个片段:在葬礼上,陈桂林的小乐队在雨中弹奏俄罗斯名曲《三套车》,摄影机水平向左移动,接着看到是淑娴面向摄像机演唱,这是人物在静止状态下的水平调度;而陈桂林载着父亲回家,路上叙说将要离婚的消息的片段,则是运动下的水平跟拍。摄影机时时刻刻都在动,拍人时在水平移动,拍物时在水平移动,甚至一个简简单单的空镜头也在水平移动。然而这种水平移动并非毫无意义的刻意雕琢而为之,而是有着深刻的内涵。
[1] 戴锦华.《钢的琴》— 形式、语言与风格.北京大学影片赏析,2012(09).
[2] 张猛.《钢的琴》四人谈.当代电影,2011(06).
[3]孙萌. 轮回的路径——从《艺术家》与《钢的琴》看诗性怀旧电影.文艺研究,2012(08).
[4]杨击. 后现代乡愁:《钢的琴》的情感结构和叙事策略. 艺术评论,2011(10).
[5]刘藩. 《钢的琴》:土法造琴背后的温情、困顿和生活理想.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1(12).
[6]司丽君. 浅析小成本电影所要把握的观众心理需求——以《钢的琴》和《失恋33天》为例.大众文艺,2012(07).
王鹤翔(1992-)女,河南郑州人,兰州大学文学院2011级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学生,兰州大学青年传媒集团《兰大青年》主编, 研究方向:戏剧影视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