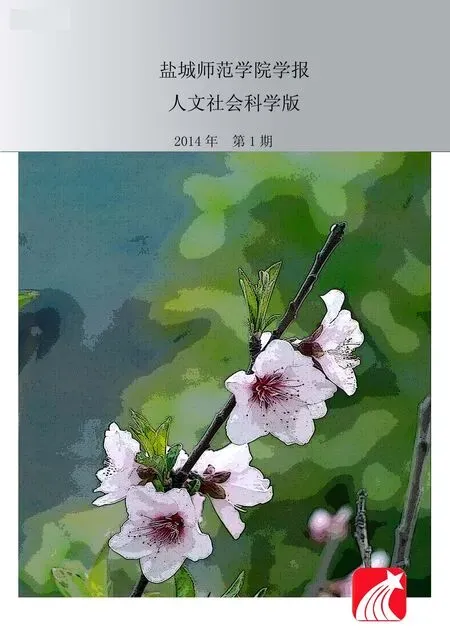文学史料学视野下的春秋文学研究
——评邵炳军教授《春秋文学系年辑证》*
2014-03-12郁贤皓
郁贤皓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从文学研究的整体来看,大致可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运用经验实证方法,考订和还原文学史实;二是运用理性思辨方法,从整体上审视研究对象。前者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后者是文学研究的归宿。因此,把史料视作学术研究之根基,一向是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优良传统。由于春秋文学史料缺漏严重,文学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尤其显得迫切而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近出版的邵炳军教授《春秋文学系年辑证》(全4册,约180万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堪称为春秋文学史料考据集大成之作。该书运用文学年代学(Chronology of Literature)的理论与方法,在“系年”体例框架之下,以“辑证”方式进行艰辛的考据工作。这是作者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篇》)经学研究方法与“推明古训,实事求是”(清阮元《揅经室集·叙》)文献学研究方法有机结合的具体实践。其在文学史料考据集成方面的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搜集与运用已有研究成果的广泛性
作者无论是在考订作家的生平事迹时,还是在考订诗文创作年代时,时常会先列举数种或十数种已有的代表性研究论点,在进行梳理与辨别的基础上,或择善而从,或补证旧说,或自立新说。
比如,平王元年(前770)“周家伯父作《节南山》”条,在考订《节南山》创作年代时,先列举出先哲代表性的七种说法:一为上博简《诗论》第八简之“阙疑”说,二为《节南山》毛《序》之“幽王之世(前781—前771)”说,三为《节南山》孔《疏》引三国吴韦昭之“平王之世(前770—前720)”说,四为《节南山》孔《疏》之“平桓之世(前770—前697)”说,五为宋欧阳修《诗本义》卷七之“桓王之世(前719—前697)”说,六为宋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卷二之“共和元年(前841)之后”说,七为清梁玉绳《汉书古今人表考》卷四之“宣王之世(前827—前782)”说;然后,对上述所引诸说进行辨析,认为韦昭“平王之世”说近是;进而从家父的生平事迹结合对文本的分析中认定,《节南山》为骊山之难、“二王并立”初期,亦即为西周覆灭而平王未东迁时期的作品,即作于平王元年(前770年)。
这种吸收先哲时贤重要研究成果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对春秋文学研究史料进行总结性研究。如果将这些分散在全书的大量局部性研究成果合而为一的话,则称得上是一部春秋文学研究学术史料集成。
二、作家个体研究的概括性与群体研究的历时性相结合
所谓作家个体研究的概括性,是指每当一个作家在书中首次出现时,都要以“简介”方式,介绍其族属、世系、行状及其文学创作基本情况。
比如桓王二年(前718)“鲁公子彄作《谏公矢鱼于棠书》”条,公子彄为全书中首次出现,故对其作出简要介绍:“公子彄(前?—前71年),即隐五年《左传》之‘臧僖伯’、‘叔父’,姓姬,其后以字别氏臧,亦称臧孙氏,名彄,字子臧,谥僖,敬称叔父,尊称伯,季历(公季)之孙、文王昌(西伯)庶子周公旦后裔,懿公戏之孙,孝公称之子,臧孙达(哀伯)之父,世袭鲁司寇。其倡导‘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遵循古制,熟知礼仪,直言敢谏,素有令名,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前期鲁国著名政治家与文学之士,传世有《谏公矢鱼于棠书》一文。”这样,就会使读者对每位作家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与初步认识。
所谓作家群体研究的历时性,是指专门设置“纪人”一项,对于凡辑录有作品创作的作者均标明生卒、年岁或在世年代。
比如,庄王三年(前694)“纪人”一项:“鲁庄公同十三岁 陈公子完十二岁 宋桓夫人生 周周公黑肩卒 鲁臧孙达、申繻在世 楚鬬廉、邓曼在世 卫公子职在世 郑祭仲、原繁、厉公突在世 虞百里奚在世”。这样,将鲁、陈、宋、周、楚、卫、郑、虞等本年在世的作者逐一罗列出来,可以展示出不同历史阶段作家群体的基本特点与整体状况,使读者具有清晰的作者群体感。
如果将“简介”与“纪人”合而观之,则构成了春秋作家“群谱”,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春秋文学作家史料集成。
三、考证材料运用的原始性与翔实性
无论是考订作家的生平事迹,还是考订作品的创作年代;无论是补证旧说,还是自立新说,作者总是对文献资料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搜集整理,以便尽最大可能运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进行考证。
比如,平王元年(前770)“卫武公作《抑》”条,在补证《国语·楚语上》关于《抑》作于“平王之世”说时,提出了“《抑》为卫武公在周平王未除丧时所献之诗”、“诗歌反映了周幽王使宗周覆亡的历史悲剧”、“《抑》是卫武公献给周平王的诫勉诗”等三个分论点,而这些分论点都引述大量诗歌文本、其他传世文献与出土考证材料作为佐证。当然,在每一个分论点材料运用方面则各有侧重。象讨论第一个分论点时,先全部列举出诗中的十一“尔”字、一个“女”字、一个“予”字等十四个人称代词和四个“小子”,再引述郑《笺》“天子未除丧称‘小子’”之说,然后以《诗》、《书》、《逸周书》、《礼记》及宋王俅《啸堂集古录》卷下著录《师簋》、清吴荣光《筠清馆金石文字》卷四著录《小子鼎》等为据,认为周人称未除丧之王为“小子”在传世文献与金文中均多见。这样,就极其自然地得出诗中“小子”及“尔”、“女”、“予”均“指称周王”的论断,有力地支撑了分论点。可见,运用考证材料的翔实性,自然能为研究结论的科学性提供必要保障。
四、编排体例的史料集成性
本书主体部分除上述“纪人”之外,还有“纪年”、“纪事”、“录文”三大板块。
所谓“纪年”,即凡在前770年—前453年期间有文学创作之年,依次标写公元、周、鲁暨与本年“录文”相关诸侯国之年代。比如:“前585年 周简王夷元年 鲁成公六年 晋景公十五年”,因本年有“晋士渥浊作《失位自弃论》”、“晋伯宗作《以信求诸侯论》”、“晋韩厥论国饶则民骄佚而近宝则公室贫”、“晋栾书论善钧从众”等三条,故纪晋国之年;其他诸侯国本年无创作活动,则概不纪其年,以免行文过繁。
所谓“纪事”,即对该年度所发生的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重大事件或文化现象亦予以关注。比如,敬王元年(前519)之“纪事”为:“鲁叔孙婼如晋 晋人执鲁行人叔孙婼 晋人围郊 蔡侯东国卒于楚 莒子庚舆奔鲁 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 天王居于狄泉 尹氏立王子朝 鲁公如晋至河乃复”。
所谓“录文”,即辑录该年度作者所创作的各体各类文学作品,特别是将散见于其他文献的逸诗、逸文、歌谣均予辑录。比如,惠王元年(前767)所辑录陈懿氏妻所作《凤皇歌》,襄王三年(前650)所辑录晋舆人所作《舆人诵》,等等。
即使在“注释”中,对文字学、民俗学史料的考据方面,亦作了很多努力。附录部分的《春秋年表》、《春秋人表》等,同样具有很高的文学史料价值。
当然,分散的、孤立的文学史料,往往是在被体悟分析中进行价值评判。而这首先得以大量占有文学史料为前提,其次是要具有缜密严谨的思辨能力。可以说,邵炳军教授在撰写《辑证》过程中都基本做到了。作为他的博士后合作导师,这正是令我欣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