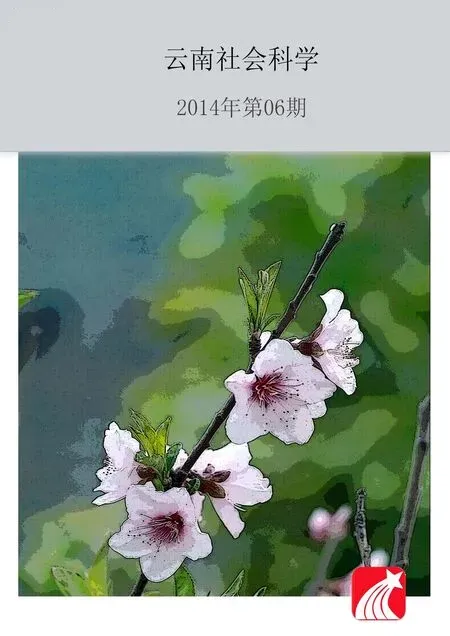由唐入宋石鼓诗之流变
2014-03-12李娟
李 娟
石鼓,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外形似鼓,其数为十,上刻文字。唐初于陈仓出土后,日渐受到重视,苏勖“打本”《叙记》、李嗣真《书后品赞》、张怀瓘《书断》、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皆有提及。唐末五代石鼓散落民间,宋代仁宗时陆续收齐。同时,伴随金石学的兴起,石鼓研究备受重视,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翟耆年《籀史》、郑樵《石鼓文考》、王厚之《复斋金石录》、施宿《石鼓音》皆有论及。
受石鼓出土、搜集、研究的影响,唐宋时期涌现了一系列以石鼓为题材的经典之作。唐有韦应物及韩愈《石鼓歌》,宋有梅尧臣《雷逸老以仿石鼓文见遗因呈祭酒吴公》、刘敞《雷氏子推迹石鼓为隶古定圣俞作长诗叙之诸公继作予亦继其后》、苏轼《凤翔八观·石鼓歌》、苏辙《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石鼓》、张耒《瓦器易石鼓文歌》、吕本中《钱逊叔诸公赋石鼓文请同作》、洪适《石鼓诗》等。考此部分诗作,可以发现,由唐入宋,石鼓诗在内容取向及艺术手法方面发生着变化。具体表现为:内容取向上,宋代石鼓诗的学术性较之此前进一步深化;同时,显现出以史鉴今的现实指向,并将哲学理思融入其中,此系唐代所阙;另外,仅就有唐一朝言之,石鼓诗中创作主体之情感亦呈现出从无到有的变化。艺术手法上,一方面,宋代石鼓诗在承继唐人结构模式的基础上更多地寻求灵活与变化;另一方面,审美风格也发生着转向,宋代石鼓诗多以平易、婉转、整饬消融着前代一贯而下的气势。
一、学术性的深化
李唐时期,继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提到“陈仓石鼓”后,韦应物于大历十年(775年)作《石鼓歌》,系现存较早地专咏石鼓之诗作,全诗如下: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法传,持来比此殊悬隔。[1](P90)
该诗围绕石鼓的制作因由、刻石时代、形制状貌、文字特点、价值地位展开论述。认为石鼓乃周宣王时为表功绩由史籀所刻,石如鼓形、数量为十,经过岁月的洗礼已呈现出斑驳的状貌,文字难懂、形体曲折且与李斯石刻字体大异,进而有着重要的文物与书法价值。暂不论韦应物是否具有明确的学术意识,仅就此诗来看,已为后世提供了一些关于石鼓及石鼓文的学术讯息。此后,韩愈再作《石鼓歌》,在石鼓的制作因由、刻石时代方面依旧延续韦氏;但在论及石鼓文义及文字时云:“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科”[2](P794),可见韩诗对石鼓文字体的判断较之韦诗更为专业,只可惜未对石鼓文义做出进一步辨识。据此可知,唐代石鼓诗已展露出一定学术性,然多流于石鼓及文字的表层,并未深入。
赵宋之后,伴随金石学的兴起及石鼓研究的深入,梅尧臣、刘敞、苏轼、苏辙、洪适等进行石鼓诗创作时,已自觉地将当时研究成果融入其中,从而推动着石鼓诗学术性的深化,这主要于细节处表现出来。首先,宋代石鼓诗多将石鼓文字辨识成果融入其中,致力于解决韩愈面临的“辞严义密读难晓”之困境。如梅尧臣《雷逸老以仿石鼓文见遗因呈祭酒吴公》云:“我车我马攻既良,射夫其同弓矢张,舫舟又渔缚鱮鲂,何以贯之维柳杨。”[3](P1047)刘敞《雷氏子推迹石鼓为隶古定圣俞作长诗叙之诸公继作予亦继其后》云:“词章车攻与吉日。”[4](P5773)苏轼《石鼓歌》云:“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与贯之柳。”[5](P145)苏辙《石鼓》云:“形虽不具意可知,有云杨柳贯鲂鱮。”[6](P28)洪适《石鼓诗》云:“左骖秀弓射糜豕,有鳑有鲌君子渔。”[4](P23477)皆以己所通晓的部分文字入诗,且在一些文字的辨识上各抒己意,彰显了宋人对文字之学的精通,加深了诗歌本身的学术含量。
其次,较之韦诗对石鼓及李斯刻石文字差别的感性评断,韩诗对石鼓文字与隶书、蝌蚪文不同的简要评价,刘敞之诗已接受了雷氏推迹石鼓文为隶古定的结论,苏轼《石鼓歌》更是有意识地将石鼓文纳入文字发展史中去评论。诗云:“上追轩颉相唯诺,下揖冰斯同鷇?忆昔周宣歌鸿雁,当时籀史变蝌蚪。”[5](P146)其中,仓颉相传是汉字的创始人,李斯为小篆的开创者,李阳冰善书小篆,上二句即指石鼓文上承仓颉、下启小篆,在文字发展史上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蝌蚪文是上古文字的一种,籀文是大篆的一种,介于甲骨文与小篆之间,相传由周宣王时史籀变革蝌蚪文而创制,下二句即指石鼓文是史籀变革蝌蚪文而成的文字。可以说,刘敞对雷氏断定石鼓字体结论的接受,苏轼对包括石鼓文在内的文字发展史的考论,一定程度加深了石鼓诗的学术性。
除此之外,宋代石鼓诗亦添加了一些前代石鼓诗未曾注意到的学术讯息。诸如梅尧臣《雷逸老以仿石鼓文见遗因呈祭酒吴公》有“四百六十飞凤皇”,首次提及石鼓文拓本之字数;苏轼《石鼓歌》有“强寻偏傍推点画”,指出了辨识文字的方法,具有方法论层面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宋代石鼓诗所展示的学术讯息,已跨越石鼓与文字的表层,深入至文字辨识、文字发展史考论及辨识方法等学理层面,昭示了诗歌学术性的深化。
二、情感性、史鉴性及哲理性的依次显现
韦应物《石鼓歌》,如前文所分析,处处紧扣石鼓展开,以客观描述为主并兼有议论。虽开诗歌领域专论石鼓之先河,但并未像此后韩愈《石鼓歌》那样较多地渗入诗人的主体情感,也未像苏轼《石鼓歌》那样较深地触及石鼓背后的历史以有补于现实政治,更未像苏辙《石鼓》那样融哲学理思于其中。继韦应物之后,韩愈吸收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之作法,有长达462字的巨作《石鼓歌》。韩愈之作连同苏轼《石鼓歌》,历来被视为后世石鼓诗之楷模。细细品读,可以发现,韩、苏二人在内容取向上有着不同的兴趣,标志着唐、宋石鼓诗之流变;即便是同属李唐时期的韦、韩二人,在对待主体情感的融入方面亦展现出差别。
就韩愈《石鼓歌》而言,全诗围绕石鼓来历,石鼓文字特点,孔子编《诗》不录石鼓,及石鼓有着巨大的文物、文献、书法价值却不被朝廷重视这条线索展开,旨在呼吁官方能够采取妥善的举措保护石鼓,同时也贯穿着建议不被采纳的愤懑之情。较之韦诗,伴随篇幅的扩大,无论是对制鼓因由的分析,还是对石鼓文字的描摹,抑或是对石鼓地位价值的强调,皆详赡生动,极尽铺张之能事。更重要的是,韩诗加强了创作主体主观情感的介入,这便使石鼓诗摆脱了客观的叙述与评价,饱含着流动的情思。节录韩愈《石鼓歌》部分为例:
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忆昔初蒙博士征,其年始改称元和。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度量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毡苞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数骆驼。荐诸太庙比郜鼎,光价岂止百倍过?圣恩若许留太学,诸生讲解得切磋。观经鸿都尚填咽,坐见举国来奔波。剜苔剔藓露节角,安置妥帖平不颇。大厦深簷与盖覆,经历久远期无佗。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媕娿。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著手为摩挲?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继周八代争战罢,无人收拾理则那。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安能以此上论列?愿借辩口如悬河。石鼓之歌止于此,呜呼吾意其蹉跎
该段文字系全诗之重,围绕石鼓保护建议与建议不被采纳二者的冲突展开,几经希望,几经失落,诗人的主体情感三度喷涌而出。第一次,诗人有感于石鼓不见于《诗》抒发了“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之感慨。第二次,陈述将石鼓运往太学仅需“毡苞席裹”并数只骆驼那样方便,且指出石鼓价过郜鼎百倍、方便儒生切磋的文物及文献价值,希冀朝廷“剜苔剔藓”、盖覆藏之于大厦,加以妥当保存。遗憾的是,此建议并未引起官员响应与朝廷采纳,石鼓沦于“牧童敲火牛砺角”“日销月铄就埋没”的境地,有鉴于此,诗人再度抒发“六年西顾空吟哦”之感叹。第三次,诗人虽感失望却不绝望,依旧反复呼吁,强调石鼓超越王羲之书法的意义,以期太平之世予以珍视,并以末四句直陈己之想法及蹉跎之意。此段文字三度彰显内心情感,饱含丰富的情思内蕴。
如果说韦应物到韩愈《石鼓歌》的流变,在于主观情感的介入,那么韩愈到苏轼《石鼓歌》的流变,也即唐至宋代石鼓诗的流变,则在于史鉴性、哲理性的显现。在韩愈《石鼓歌》中,有对历史的追溯:
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珮鸣相磨。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2](P794)
该诗叙述了周宣王南征北战、平定天下后,明堂朝贺、岐阳狩猎、刻石记功的一段事迹,回顾历史仅为单纯地阐释宣王刻石之因由,其主旨在于交代石鼓来历,历史本身仅处从属地位。苏轼《石鼓歌》与之不同,在简要对石鼓文字描摹、辨识并进行书法意义的评价之后,随即将叙述重点转向周秦历史的对比:
厌乱人方思圣贤,中兴天为生耆耇。东征徐虏阚虓虎,北伏犬戎随指嗾。象胥杂沓贡狼鹿,方召联翩赐圭卣。遂因鼓鼙思将帅,岂为考击烦矇瞍。何人作颂比嵩高?万古斯文齐岣嵝。勋劳至大不矜伐,文武未远犹忠厚。欲寻年岁无甲乙,岂有名字记谁某?自从周衰更七国,竟使秦人有九有。扫除诗书诵法律,投弃俎豆陈鞭杻。当年何人佐祖龙?上蔡公子牵黄狗。登山刻石颂功烈,后者无继前无偶。皆云皇帝巡四国,烹灭强暴救黔首。六经既已委灰尘,此鼓亦当遭击掊。传闻九鼎沦泗上,欲使万夫沉水取。暴君纵欲穷人力,神物义不污秦垢。是时石鼓何处避?无乃天工令鬼守!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
“厌乱人方思圣贤”及其后的十二句,是对周宣王功绩的歌颂:宣王东征徐国,北定犬戎,使得诸侯纷纷进贡;方叔平荆,召虎平淮,奖赏有功之臣;而宣王制鼓乃因崇尚武功、表彰将帅,非为自颂。“自从周衰更七国”及其后的十八句,是对秦始皇废礼暴政的记叙: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不用礼仪,专用严刑;并指出始皇刻石乃为自颂。此外,以石鼓义不受秦污,为天工所佑,讽刺始皇为政之暴劣。尾四句,有感于朝代更迭、石鼓依旧,及石鼓在周富贵、于世不朽之实际,生发对世情物理的思考。在苏轼这里,历史早已脱离从属地位跃居诗歌主体,一方面,他通过周宣王、秦始皇两段历史的对比,寄寓褒贬并暗含以古鉴今的现实指向,即希望历代帝王能够以儒家仁义治国;另一方面,他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投射,又超越具体事件,上升为普遍规律的探索,人生哲理的探求。
之后苏辙作《石鼓》,沿着苏轼开辟的道路走得更远。就苏轼而言,以古鉴、今有补于世是其关注的焦点,哲学理思暂居衍生地位;但就苏辙而言,延续以古鉴今史鉴性的同时,哲学理思也成为诗歌之重。在苏辙这首诗中,诗人以224字的大半篇幅集中论述了“有用”“无用”统一于一物并相互转换的道理。论述大致分为三层:首先,诗人总括石鼓集“有用”“无用”于一体的道理。就“扣之不鸣悬无虞”的使用性来看,石鼓似乎“无用”;但就“万物祖”的标志性作用来看,石鼓又似“有用”。其次,就朝代兴衰详述“有用”“无用”相互转换的道理。宣王时期,石鼓因其刻石表功意义备受重视,可谓“有用”;周室衰落,石鼓因无暇顾及而零落,可谓“无用”;后逢思宣之士或历太平之世,因“由鼓求宣近为愈”复受重视,又可谓“有用”。最后,诗人论述了“有用”未必有益,“无用”未必无益的道理。项籍因“猛如狼”,汉欲以千金万户悬赏得其头者,以致其身不能保全;而石鼓正因“无用”无人问津,虽“形骸偃蹇”“文字皴剥”但得以周全。可以说,苏辙在周、秦、汉、唐历史的回顾中,完成了“有用”“无用”的论述,富有哲理内涵。
除苏轼、苏辙二诗外,刘敞、吕本中的石鼓诗也显现出一定程度的史鉴性与哲理性。刘敞《雷氏子推迹石鼓为隶古定圣俞作长诗叙之诸公继作予亦继其后》由金石古器所存者少联想到“道之难行”,从具体物事上升到抽象哲理;吕本中《钱逊叔诸公赋石鼓文请同作》云:“石鼓之文公所知,正是周室中兴时。庶几我皇亦如此,一扫狂虏随风飞。”[4](P18157)贯通古今,具有现实指向性。至此,从韦应物《石鼓歌》到韩愈再到二苏,旁及刘敞、吕本中等,可看出由唐入宋石鼓诗情感性、史鉴性、哲理性的依次显现。
三、结构模式的求变与审美风格的转向
为适应内容取向的转变,由唐入宋,石鼓诗的结构模式及审美风格逐渐发生着变化。从韦应物《石鼓歌》始,经韩愈,至二苏,在诗歌结构上不断调整,以期寻求与表达内容更为切合的模式。而韩愈《石鼓歌》所呈现的一气直下的气势也日渐被梅尧臣《雷逸老以仿石鼓文见遗因呈祭酒吴公》的平易、苏轼《石鼓歌》的婉转流动、洪适《石鼓诗》的整饬所消融。
就结构模式求变而言,还应从韦应物《石鼓歌》说起。关于该诗结构,大致按照追溯石鼓来历、描摹石鼓形制文字、评价石鼓价值意义三个层面展开,结构简单,缺少变幻。其后韩愈《石鼓歌》前半部分大致沿续韦诗追溯来历、描摹形制文字的路径开展,但对于诗歌的重点即“陋儒编诗不收入”之后的部分却呈现出变化,引文见前,此不重复。该部分依据建议提出的逻辑并配合主体情感表达的需要分五个层面推进:第一层至“对此涕泪双滂沱”,揭示石鼓此前被忽视,抒发惋惜之情。第二层至“经历久远期无佗”,陈述石鼓保存的建议与展望。第三层至“六年西顾空吟哦”,指出建议不被采纳,再次表达叹惋之情。第四层至“柄任儒术崇丘轲”,再度劝说官方采纳己之建议。第五层至文末,阐述作诗之由并表达己之情感。通过如此回环往复的结构,营造了石鼓两次被忽视,建议两次被提出,情感三度涌现的情景,将诗人对石鼓零落的痛心及保护石鼓的急切体现得淋漓尽致。
此后苏轼《石鼓歌》,应诗歌学术性、史鉴性、哲理性的表达需要,结构模式较之韦、韩做出了较大调整。如果说韩愈前半部分依旧延续韦应物的思路,那么苏轼则将其逐渐打破。该诗可从“厌乱人方思圣贤”处分截,此前围绕石鼓文字而论,突显诗歌的学术性;此后围绕周秦历史而论,彰显诗歌的史鉴性与哲理性。随后苏辙《石鼓》,应诗歌哲理性表达需要,结构更加灵活,完全摆脱了唐人的结构模式。该诗可从“古人不见见遗物”处分截,此前于朝代的更迭中揭示“有用”“无用”之道理,此后于石鼓文字内容的解读中弘扬以仁义伦理治国的政治主张,而该变化正是由诗歌内容的转向所决定的。
就审美风格转向而言,朱彝尊评韩愈《石鼓歌》:“大约以苍劲盛,力量自有余。然气一直下,微嫌乏藻润转折之妙。”[2](P806)指出了韩诗力量气势有余,但纡徐婉转不足的风格。在他的诗歌中始终透露着刚劲之气,即便是对石鼓字体的描摹:“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鼍。鸾翱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2](P794)亦硬语迭出,瑰丽雄奇。苏轼与之不同,试看其对石鼓字体的形容,虽兼有类似韩愈之硬语“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模糊半已隐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以形容可辨识笔画的稀少;但亦有充满画意之写照“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5](P146),以秀美婉转冲淡刚硬之气,进而呈现出舒卷自如的风格。
如果说苏轼以秀美纡徐冲淡了韩诗的一气直下,那么梅尧臣《雷逸老以仿石鼓文见遗因呈祭酒吴公》则以平淡的叙述消磨了韩诗一贯而下的气势。他对石鼓来历的叙述,对石鼓文字的辨识,对历史长河中石鼓受到忽视的写照,对雷逸老仿石鼓文以见遗的陈述,对石鼓于今受到重视、诗人“效韩”心理的关照,皆如老者一般娓娓道来,没有了韩愈激昂的气势。尤其是“村童戏坐老死丧”“于此岂不同粃糠”“连日道路费刍粮”等俗境俗语的融入,大大削弱了韩诗的瑰奇与刚劲。而洪适,作为著名的金石学家,他的《石鼓诗》,富有学者的严谨与沉稳,以整饬典重消融了韩诗之气势。较之韩诗的驰骋想象、情感洋溢,洪诗大多征引经史,取诸事实,有所依凭。表现有三:其一,首句“天作高山太王荒”,几乎原样转引《周颂·天作》“天作高山,大王荒之”[7](P711)之语;其后对石鼓来历的叙述也削减了想象的成分,皆有经传作依凭。其二,对石鼓文字的陈述部分,摒弃了前人运用的想象与比喻,直录石鼓文字内容。其三,对朝廷及士人重视金石收藏的叙写部分,诸如收齐石鼓、断定文字、保存凤翔碑拓本等,皆有事实作支撑,进而呈现出与韩诗截然相反的风格特征。
四、石鼓诗流变的金石学背景及诗歌史意义
由唐入宋石鼓诗的上述发展流变与宋代金石学的兴起息息相关。所谓金石学,即以青铜器、石刻为研究对象的考古之学。经过魏晋唐时期的沉淀,宋代始兴。石鼓研究,正是其中的重要个案。以《集古录跋尾·石鼓文》《金石录·石鼓文》,《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岐阳石鼓》为例,可以看出宋代石鼓研究,也即金石学研究的几个重要方向为:首先,详述古器的出现、收藏及形制等,以对其具体情况作出介绍。如欧阳修云:“岐阳石鼓初不见称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称之”,暗含石鼓的发现时间。“在今凤翔孔子庙中,鼓有十,先时散弃于野,郑余庆置于庙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传师求于民间,得之乃足。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不可识者过半。”[8](P2079)指出石鼓的再次发现、保存、形制及文字情况。
其次,鉴定古器,考释文字。以欧阳修鉴定石鼓年代为例,他对“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诗,韩退之直以为宣王之鼓”提出质疑,并说明质疑的原因:其一,将石鼓与汉代桓帝、灵帝碑文的磨灭程度进行对比,认为石鼓年代不当早于桓、灵之时;其二,认为石鼓文记载与《雅》《颂》相类,但汉以来的博古之士并未言之,实属可疑;其三,从目录学的角度,认为隋氏藏书并无载录,因此存疑。而薛尚功在《岐阳石鼓》中,对石鼓上的文字进行了详细具体的考释。
又次,以古器考订经史,间或于古器品评中流露个人艺术观念。欧阳修在《集古录目序》中曾谈及作《集古录》的因由,“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8](P600)赵明诚《金石录·序》也表达了相同的思想。反观《集古录跋尾·石鼓文》:“其字古而有法,其言与《雅》《颂》同文,而《诗》《书》所传之外,三代文章真迹在者,惟此而已。”已将其与经史互考,并对其文字做出了“古而有法”的简要评价。
最后,以古鉴今,力求有益于世,此系宋代金石学者自觉主动的追求。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唐盐宗神祠记》中自叙撰写《集古录》之宗旨“不独为传记正讹缪,亦可为朝廷决疑议也。”[8](P2246)认为古器研究考订经史之余,亦有“为朝廷决疑议”的现实意义。李清照《〈金石录〉后叙》指出《金石录》载录的原则“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9](P531),认为古器研究最终目的是“合圣人之道”,探索深层的道理。
将唐至宋代石鼓诗流变与宋代金石学兴起的四个研究方向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金石学研究成果的丰富推动着石鼓诗学术性的深化;以古鉴今、有益于世的研究目的又带动着石鼓诗史鉴性、哲理性的显现。宋代进行石鼓诗创作的诸位诗人,如梅尧臣、刘敞、二苏、张耒、吕本中、洪适等,或与金石研究者交往密切、切磋频繁,或本人即是金石收藏研究的爱好者,他们石鼓诗内容取向的转变,受到金石学兴起的影响也便可以理解。此外,内容取向的转变势必带来结构模式的变化及审美风格的转型,此正是金石学兴起的间接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石鼓诗所展现的新特点,也大致代表着金石学兴起背景下金石赏鉴诗的新特点,这正是研究石鼓诗流变的诗歌史意义所在。试看宋代其他作品,梅尧臣《蔡君谟示古大弩牙》:“黄铜弩牙金错花,银阑线齿如排沙,上立准度可省括,箭沟三道前直窊,其度四寸寸五刻,鋈光历历无纤差。”[3](P637)对古器形制的描摹精准简练,堪称理性科学地描述。文同《晋铭》:“凡百十九字,诡怪摹物形。纵横下点画,不类子与丁。试考诸传说,其源已冥冥。”[4](P5438)揭示了诗人对晋铭文字、来历考证的执着。刘敞《刘泾州以所得李士衡观察家宝砚相示与圣俞玉汝同观戏作此歌》:“我语二客此不然,天宝称载不称年。刺史为守州为郡,此独云尔奚所传。”[4](P5784)依据唐代制度对宝砚真伪进行鉴别,言之有据。而他的《与圣俞君章枢言持国饮因以太公大刀王莽错刀示之》:“愚智共尽令人悲,兴废相寻空史笔。”[4](P5785)将朝代更迭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富有哲思。王安石《和董伯懿咏裴晋公平淮西将佐题名》,在对裴晋公平淮历史进行追溯时,作出“小夫偷安徒自计,长者远虑或可怀”“宣王侧身内修政,常德立武能平淮”[10](P102)的思考,认为深谋远虑、修德立武是古今贤者为政遵循的普遍规律,具有以古鉴今的现实意义。可以说,以石鼓诗为着眼点考察宋代金石学兴起对金石赏鉴诗的影响,具有以一斑窥全豹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