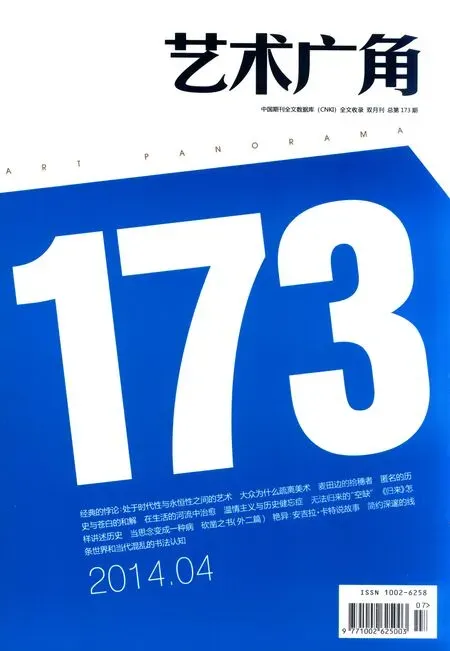寻找书法的精神向度——“重塑书法精神”栏目小结
2014-03-12苏妮娜
苏妮娜
《艺术广角》自2011年至2013年,设立专门栏目,约请作者撰文,共同探讨书法问题,是试图思考书法如何在当代社会“安身立命”的问题,也是因为在书法现象中看到了整个时代的文化症候。书法在这个时代,既遇冷,又遇热:在大众文化的层面,书法成了喧嚣不减、热度不退的流行事物,与此相关的便是书法功利化现象的大量涌现,诸多打着书画幌子的掮客和写手,在这个领域围绕着名与利上演了一出出时代闹剧;另一方面,书法专业学者却在担忧着书法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性与精神性的失落,及其在当代文化生活中的断裂与畸变。书法表象上的热,掩盖了内在的冷,表面的繁华遮蔽了精神的凋敝。书法遭遇到的各种问题,几乎包括了一种艺术在一个大的文化转型时代所能遭遇到的所有问题,是极为典型的文化现象,因此,试图面对、分析、总结书法存在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从宏观的方面上来说,书法是文化现象,关涉的绝不仅仅是书法艺术内部的问题,更是艺术与时代、艺术与市场、艺术与生存等所有问题交织互生而成的一个问题域,是总和性的问题,也是解析我们时代的整体文化乱象的一扇门。从具体的方面来说,书法是特定的艺术门类,它的本体性存在决定于它审美的特定性,诸如特定的创作方式、特定的精神传统、特定的发展轨迹、特定的审美接受、特定的美学阐释,等等,这些具体问题也值得关注和研究,并且会在较深的层次上与前述宏观的方式相遇。《艺术广角》为此专题编发的十几篇文章,都在共同完成同一个话题,即:书法如何面对这个新的时代。通过这个梳理,我们试图回答,作为传统艺术,书法的内在生命力到底存在于何处,创生于古代、生命力顽强的这个艺术门类,到底怎样才能被再度激活。
梳理书法面对的文化时代
对于书法来说,这是一个好的时代还是坏的时代?对这一点,这些文章有基于不同立足点的不同判断,从不同的侧面描述了不同的真实,把这些描述的情况相加,也许更接近于我们希望看到的“真实”。多数篇章在“断裂”的文化环境面前发出了无望的叹息。首先,这是一个消费主义主导的文化。作者们对书法媚商、拜金的批判极为猛烈:“当代社会,书法艺术精神的传承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商业社会市场机制的侵蚀力度早已超越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潮等方面的影响”。(兰浩《中国书法艺术精神的重建》,《艺术广角》2012年第2期,以下引文如无特别说明,均出自《艺术广角》)。而消费文化之所以主导了当下的语境,是名利的驱策使得人们从事书法学习的动机变得不再纯粹。但面对此类指责,还要有辩证的认识,例如,也有人主张,商业化以及市场化在很多时候是促进艺术发展的。因此,与其说伤害了书法艺术本体的是市场这种经济形式,不如说是这种经济形式中滋生蔓延出的短视和逐利的市场化思维,即万事万物皆是交换。消费文化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文化品位的下降,是貌似在消费实则不懂得艺术的独立性价值,导致人们制定了明确的目标来学习书法和欣赏书法,才失落了古人以研习、琢磨书法本身优游卒岁、独与天地往来的逍遥心境。“这种艺术市场中掺杂的文化变异因素,像癌症一样,会扩散。”(李徽昭、赵文《通达于艺而游手于斯》,2012第3期。)这是非常严厉的警告。其次,这是一个视觉传媒时代。具体说来,则可以追究到文字在日常生活中功能的改变,尤其是书写载体的彻底改变,即“传统笔墨工具的退场”。书写本身已经被敲键盘代替,更不必谈及笔墨纸砚。视觉传媒时代中,大众不必凭借文字这一文化符号完成信息的传达,对于作为文化符号的文字淡漠、疏离,必然导致相应的书写方式和书写审美等活动淡出日常生活的视野。与古代的书法日常化思维相对应的是现代的“展览化思维”,“书法的本质与现代展示之间是有冲突的,当代以展览为手段的书法展示正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所在”,“传统的书法是作为个人修身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典时代的书家是写给自己看的,是自我抒发的需要,所以人与书是交融的,‘我’的意识更为强烈”,而在以展览为功能的当下,书法中“个人情性的抒发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陈宇《生命观照与人格呈现》,2012年第4期。)再次,现代社会强调社会分工和职业划分。陈宇、李徽昭等进一步指出书法越来越徒具形式的趋势,是由于实用功能脱落之后,向纯艺术与独立学科的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当书法被进一步职业化之后,支撑书法的传统文化精神的整体性遭到破坏,与书法相表里的古典文学教育、古典美术教育不能配套,导致其功能单一化、精神涵养的源泉干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代书法却是以人们追求个性自由、个性解放,追求个性化的艺术风格为起点和目的的,而最终结果却是没有了个性没有了自我更没有了风格,似乎都是从一个模板中印出来的,这其实是书法精神缺失的表现。”
笼统说来,可以归因于“从社会文化环境来看,当代书法发展最大的问题还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退场。”(兰浩:《中国书法艺术精神的重建》,2012年第2期)。我刊编发的多篇文章大体上持文化失败主义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人文精神日渐萎缩的时代,书法只是暂且寄生在这个时代,而不能生出根来。
也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譬如李徽昭、赵文在《通达于艺而游手于斯——“作家书画艺术”二人谈》(2012年第3期)当中描述的:“因为断裂只是历史表面的割裂,文人书画的根源没有完全断裂,内在的文人书画是有创造的契机存在的。”这一段话对于根脉“断裂”的反驳,很有新意。跨界的作家书画的成就,说明了相对于表面的断裂,延续是存在着的,只是在作家这个文化群体中比较集中。作家,在用纸笔完成书写这一具体行为时,“他能够感觉到他写的方式和风格,和他自身的文学创造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系”,也就是一种自觉。这种自觉之下进行的书写和绘画,是超越功利,却又反映着较高的人文诉求和心灵维度。事实上,前述的判断,是基于大多数人的所在,即大众文化领域作出的判断,而此文所作出的判断,是在一个并未言明的文化精英圈层内发言的,是相对小众的范畴。这两种人群信守不同的审美尺度和文化价值,并非认识的歧异,而是对于书法存在的具体语境的具体认识,这也导致了对于书法文化功能的不同体认。
重寻书法的文化功能
近年来书画大热,在大众文化领域掀起了书写、购买、收藏的热潮,造成跌破眼镜的文化奇观。可以说,这样的现象是书法功利化的一个顶峰。收藏者事实上并不是书画的观赏者,书画的审美功能已经被流通功能所取代,也就意味着,文化消费之地已经直接过渡为资本增值之所。所谓文化消费当中,为欣赏而买单,为了想要张挂在自己书斋或是客厅而购买的文化消费者减少了,剩下的多是从中获利的画廊、个体商人。文化市场化的景观越繁盛,书画的商品价格越被哄抬,书法文化价值、艺术价值越被漠视、挤压,以至归零。书法竟具备了流通和增值的功能,商业属性竟成了书画作品的最显在的属性,这确实是一个使用毛笔书写了几千年的民族始料不及的事情。这个现象中一个特殊的问题是,为一幅书画买单的人,是无法根据书画的艺术价值为之估价的人,书画卖出天价的重大新闻,就证明了这一点。无法估价,既是因为没有成熟的鉴赏能力,也是因为无力左右已经充满泡沫的书画市场。从市场牟利的角度看,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现象,从书画艺术的长远发展来看,这也并非好事,至少证明了普通大众的艺术观念和消费理念还远未成熟。如何从虚高的外在的价格,回到具有艺术实质性衡量标准的“价值”,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话题。也就意味着,重新回到书法的文化功能、艺术功能,重新提出和张扬书法的精神性内涵,既迫切,也很重要。
对书法功能的认识,取决于书写者的立场和心态,由此存在实用功能/审美功能、日常化/职业化、整体性/单一性、针对自我的完成/针对他人的展示,等等,多种功能的对峙和转化。
沈伟棠、胡志平、李徽昭等提出,进入现当代,书法的实用功能已经式微。首先表现为,单向度地强调审美功能,对书法来说是使内容脱落,只余形式,这意味着“抽空”。沈伟棠《无法复制的真切》(2012年第5期)一文,以苏东坡书写《黄州寒食帖》为例,讲述生命体验的深度与艺术创作的高度之间的关联,“艺术创作之要旨是情动于中而形于外”。抽空内容也意味着切断书法外在的艺术表现与人内心情感的关联,即内在情感的干枯。今人的临摹即便酷似,也只是“把书作弄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永远也无法像苏轼一样书写得如此波澜起伏,如此扣人心弦,如此真切自然”,这种精神状态正是当代人最缺乏的。“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书法的艺术身份和学科地位得以确立以后,便躲进了展厅,一味地追求视觉效应,不再有思考的姿态,更没有古代书法艺术那种焦灼的抵达现实和直击人生的欲求”,即便是学传统,也常常是“走上了一条技法表现和形式抒情的歧路”,书写艺术已成“抄写艺术”。沈伟棠《意义传统的失落与追寻》(2012年第1期),阐明了当意义传统失落的时候,书法如何失去了当代生存的普遍性土壤,而成为不接地气的符号式艺术,沦为小圈子精英艺术。古代的书法是具有实用性的,是传播媒介与工具;书法与写作是二合一的,所以古代法帖是神思和笔触的合一、内容与形式的合一,这种情况也是当代无法再现的。由此可见,书法的生命力在于它是有意义的形式,失去了可供表达的意义、可供传播的内容、与文学同一的创作这几种功能,书法就失去立足之点,仅仅可能是在展厅中方生方死。姜栋《大众书写的文化品格与书写心态》则与沈伟棠文构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此文表达了对于毛笔书写的大众传播的乐观态度,认为晚清以降,书法家日益平民化,以文化精英自恃的文化官员没有攀到当时的书法制高点,反而是平民书法家创造出极高的书法成就。这与市民社会的文化品格凝聚这一历史阶段互为因果。此外,书法创作的便捷、工具的廉价易得,也使它十分容易进入普通人视野。作者客观地描述了这一悖论:书写的传统方式和传统意蕴很难再现,但人们又不由自主地亲近着笔墨书写这一行为本身。或许只要这种行为有着当代生长的土壤,它的精神传承是或迟或早会发生作用的。
李徽昭、赵文提出的观点是,书画的职业化,反而伤害了书画的自由本质,(《通达于艺而游手于斯》,2012年第3期)“对于传统的作家来说,书法在很大的意义上不是书法,而是书写本身”,古人的书法是书写的日常化,现代之后的作家延续了这一文脉,而正是日常行为才能表现一个人的心灵状态,“人居住在城市,在这个蜗居过程中,人对自然的失落,人的心理归宿、文化归宿,都迷失了。”
激活和重塑书法的精神性
兰浩提出,“今天我们重申书法艺术精神,就必须在书法中确立现代人的审美观念,其基本前提是审美,不是其他。”“因此书法不能仅仅成为技艺展示,或异化为功利的追求,必须注重境界的提升和时代创新。”(兰浩《中国书法艺术精神的重建》,2012年第2期)关于如何激活和重塑书法的精神性,如何建立书法这门传统艺术与时代的关联,作者们给出了多样的回答。
亲近笔墨。胡志平(《重新拿起笔来》,(2012年第1期)认为,应使书法从这个功利而急躁的时代氛围中,重新回到一种虚、静、慢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不仅仅是人们置身于书法艺术的自由国度的状态,更是人们回归到自身的心性自在、淡泊宁静的状态。在对“状态”的讨论中,我们体察了书法艺术作为古老中国哲学的一种艺术衍生物的思想魅力,而这其实是书法艺术与生命哲学的相通之处,即“人书合一”的一种理念的体现。倡导重新拿起笔来,充分地感受创作、书写过程中回归自我的专注和宁静的心灵状态:“‘自我确证’可以帮助我们感受和理解书写的快乐——以由衷的爱和专注的心神去书写……要在忙里偷闲中真切地感受到作为自由的生命和自我的存在”。
阅读书法。《意义传统的失落与追寻》(沈伟棠,2012年第1期)做出的是比较具体的回答:“要重塑中国书法的文化精神,当务之急就是继承这种意义传统。”这里所说的其实是使书法具备可阅读的书写内容,是陈振濂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提出的“当代书法意义追寻之旅”即书法不是抄写古典诗文的载体,而是本身就具备当代主题和内容的文字形式,“阅读书法”是使书法重新成为意义链条中的一环,承载着书写者彼时、彼地的感受,这才意味着书法承载意义的文化精神在当代的重生。也唯有如此,阅读体验与审美体验才能在内心世界重新成为一体,重新唤起书法予人的全方位的、复杂的精神感受。
通而化育。李浩、李徽昭《美是对平庸的一种拯救》(2012年第1期)中提到艺术回归日常,“今天的书画教育明显是‘不自然’的,是出了大问题的,”书法家不重视文学修养,文学家不重艺术修养,形成相互之间较为隔阂的状态,而诗书画的整体性,是古代书家的书法具备书法灵魂的要旨,书法、绘画与写作之间的同一性,即这几种艺术心理形式是相通的、同构的,“在什么地方统一了呢?应该说在于他(指现代中国作家书法家)对生活的体认。还有一点,就是在于他文化人格的表现”,这就上升到书法作为外在的表现与书写作为内在心性之间的关联,即在“书”中引入“人”的维度。具体到贾平凹等作家的书画创作上说来,是一种对写作的心理补偿机制在发挥作用,古人的书法总是处在一种超功利的“游手于斯”的游戏状态,是玩出来的,这是心灵“放养”的方式,而今人恰恰就是要在“玩”“游戏”而不是“职业”“谋生”的意义上去从事书法。(李徽昭、赵文《通达于艺而游手于斯》,2012年第3期)
形式有“灵”。以当代人的审美理念对接书法这一传统的审美形式。从审美的角度看,从艺术本体的角度看,书法的生命力在于它是与现代艺术精神相接、相通的。它虽然古老,但并没有失去当代审美的需求,甚至是对当代艺术的一种启发和补充。潘学聪《让线条成为一种生命存在》(2012年第2期)提出,正是书法以笔划、线条的方式,把内在于古典文献典籍中的“情趣与心结,感觉与感受,以独特而神秘的方式和形式得以潜存。这种存在包括并体现了社会与时代的历史积淀和现实诉求,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存在和文化存在。”“当实用的艺术原则不再对书法具有绝对的制约性,书写由此在情感与审美活动中获得了更大的存在空间”,强调线条的意义在于,从抽象中表达出具象的美。因此,书写者要有意识地建立文化视野和哲学眼界,才能从书写反观到自身。
回归生命。以上,无论是通过对书法具体形式的研磨来“反观到自身”,还是通过诗书画的传统文化的同一性来“拯救”平庸,其实都涉及到了书法在精神向度上的追求,而这是书法这一古老形式在当代不可能被淘汰和遗忘的根本原因,即,人们永远都需要通过艺术来完成“生命观照”与“人格呈现”。(陈宇《生命观照与人格呈现》,2012年第4期)“以生命的眼光看世界,把包括从自然到艺术在内的一切事物都看做活生生的生命体,这是中国人的哲学观,也是中国人的艺术观,中国的书法正是这样哲学观和艺术观的体现,同时也是写字之所以能成为艺术的精神性元素。”通过书写来整合分离的形与神,使生命回归本真。古典美学历来强调书如其人,文如其人,画如其人,这种同一性,就是在人格呈现的意义上来理解书法的形式表达与精神内核,强调人格精神的外化,强调人格精神的主导性,更进一步,则“苏轼讲‘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所谓‘意造’、‘信手点画’,都是强调主体精神表现要超越形式和法度,以意役法,意即是法。”,就是说人格在艺术创作中的主导。关键是,人文精神或者人生感觉的独立性,才是艺术获得灵性的关键因素。因此,对书法精神向度的诉求,应该回到对人自身生命力量的寻找,生命独特意义的开发。“书的审美内涵的丰富首先取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要强化书写中的人的内容,强化人与书写的交融,强化书写背后人的精神性元素,这才是探讨“重塑书法精神”的意义和价值所在。